
的问题意识、评价立场、观察角度的多元化)。这四点当然说的只是清末 民初以来20世纪中国的历史学,现在虽然已经是21世纪,而且这套“帝 制中国史”也并不是中国史学界而是欧美学术界的作品,不过,无论这 四点变化是否属于“现代性的历史学”(据说“现代性历史学”在如今这 个“后现代”的阶段已经过时),或者只属于“中国的历史学”(中国现 代学术始终与世界现代学术有所不同),但在我看来,它表现出来的历史 研究与通史叙事之变化,仍在这一现代历史学延长线上,这套著作呈现 的历史新意,恰好也可以分别归入这四个方面。 先看“时间缩短”。作为“帝制中国”的历史,这套书是从秦汉开始 而不是像中国学者的中国史那样,总是从上古(甚至从石器时代,即毛 泽东所说“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写起。这一“藏断众流”的写法, 是否暗示了“秦汉奠定·中国”这一历史观念?我不敢断言,因为这 问题相当复杂:但是,这里可以简单一提的是,由于对“中国”/“帝制 中国”的历史这样开始叙述,不仅避免了有关何为“最初的中国”这样 的争论(这些争论现在还很热闹),也表达了秦汉时代奠定“中国”/“帝 制中国”的观念。陆威仪在《秦汉》这一卷中说,“(前帝国时代,人们) 要么以‘秦人··齐人'·楚人”为人所知,要么以其他诸侯国国名命名, 或者以某个特定地域命名,比如‘关内人”,但是,秦的统一,则“把 这些不同的人群在政治上联结起来”。我同意这一看法,虽然殷周时代可 能已经有“中国”意识,但只有到秦汉建立统一帝国,先推行“一法度、 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后在思想上“独尊儒术”,在制度上“霸 王道杂之”,一个初步同一的“中国”才真正形成。陆威仪指出,秦汉历 史的关键之一,就是“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和对国 家边境的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如果说,由于秦汉在制度(在文 字、货币、行政、法律、度量衡以及交通上整齐划一入、文化(通过政治 力量,建立共同的生活习俗与文明规则,由帝国统一去除地方化,建立 共同的神圣信仰,通过历史书写确立帝国边界,形成共同历史记忆)、社 会(在政治上有共同国家观念,在社会上形成声气相通的群体,在思想 上有共同伦理的士大夫阶层)三方面的推进,使得“中国”/“帝制中国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同质性的国家,那么,包括秦之“销锋镝”,即《史 记》所说的“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铸十二金人;汉之削藩平七国之乱, 中央派遣官员巡行天下,使军队统一由中央管理;加上对四夷用兵以凸 显“内部统一,四夷环绕”,都对形成统一帝国起了巨大作用。正如他所 言,“把天下想象为由游牧民族和中国二者所构成,标志着一个巨大的进 步”,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内部的同质化,通过外部的“他者”塑造“我 者”意识,形成国族的自我认同,于是有了明晰的“中国”。 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学界有一种不断发掘历史、把“我们的中国" 向上追溯的潮流,从官方推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文明探源工程” 到近年由于考古发掘而重新认识“最初的中国”,这里面当然有相当复杂 的动机和背景,不过,越追越早的历史也碰到一个理论与方法的瓶颈, 这就是原本“满天星斗”的邦国,什么时候才可以算内在同一的“中国”? 在什么样的历史形态下,那片广袤区域才有了一个“中国”共识?这套 “帝制中国史”用了“帝制”这个概念,把这个问题放在括号中搁置下来 暂缓判断,无疑是聪明的方案。当然,帝制中国是一个“帝国”,既然作 为“帝国”,秦汉疆域内仍然有着多种民族与不同文化,不过重要的是, 在这个“帝国”之内,那个叫作“中国”的政治一文化共同体也在逐渐 形成,并且日益成为“帝国”的核心。陆威仪在讨论秦汉时代的历史意 义时,就指出在这个帝国控制下,“中国”,也就是帝国的核心区域,由 于制度、文化、社会的整合,不仅在内部“去军事化”,而且在政治一文 化一生活上逐渐“同质化”。这一点对我们来说相当有意义,对于此后的 历史叙述也相当重要,因为这可以说明历史中的“中国”的形成、移动 和变化,当然也是在扩大。因此,我们看到《南北朝》卷相当突出“中 国地理的重新定义”,所谓“重新定义”,就包括长江流域以及南方山区 (即属于古人所说“溪洞濮蛮”的地区)的开发,它拓展了“中国”的疆 域和文化,而《唐朝》卷则再一次强调“中国地理的再定义”,指出中国 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和南北经济文化重心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中 国”的形成与扩张才逐渐显现出来。 这一思路几乎贯穿各卷,像卜正民撰写的《元明》这一卷的第二章 推荐序

《幅员》,就非常精彩地从蒙元的大一统,说到它的整合与控制;从明朝 的版图缩小,说到明朝对西南的“内部殖民主义”:从交通邮递系统对 国家的意义,说到元明的南北变化:从元明行政区划,说到人口与移民。 就是这样,把族群、疆域、南北、经济一一呈现出来,在有关“空间”“移 动”“网络”的描述中,历史上的“中国”就不至于是“扁的”或“平的”。 而罗威廉撰写的《清朝》一卷,更是在第三章《盛清》中专列(帝国扩张》 一节,浓墨重彩地叙述了大清帝国的疆域扩张,正如他所说,当这个帝 国“在蒙古、女真、西藏、内亚穆斯林与其他非汉民族,整合成一个新 形态、超越性的政治体上,取得惊人的成功。渐渐地,中国士人开始接 受此重新定义的中国,并认同其为自己的祖国”。传统“中国”在帝制时 代的这些变化,换句话说是“中国地理的定义与再定义”,应当就是这套 历史书的一个主轴。 这当然也带来了“空间放大”。在现代有关中国的历史学变化中。 “空间放大”即历史研究超越汉族中国或中央王朝的疆域,是一个很明 显的特征。但是,这不仅是“中国”/“帝制中国”的空间在扩大,而是 说,理解这个变化的“中国”就不得不了解“周边”,把历史中国放在亚 洲背景之中,这或许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应有的趋势。19世纪末以来, 随着道光、咸丰两朝有关西北史地之学的兴起,以及欧洲和日本学者对 于“四裔之学”的重视,到了20世纪,中国“周边”的历史地理逐渐 被纳入中国史研究的视野,满、蒙、回、藏、朝鲜、苗以及各种边缘区 域、民族与文化的文献、语言、历史、田野研究,使得有关“中国”的 历史研究发生了深刻变化。当然,21世纪更引人注目的变化,则是“全 球史”的流行。中国学界常常引用梁启超所谓“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 国”“世界之中国”这种自我认识三阶段的说法,来证明我们也一样接受 全球史,但在真正书写中国史的时候,却常常“中国”是“中国”,“世界” 是“世界”,就像我们的历史系总是有“世界史”和“中国史”两个专业 一样,甚至我们的各种中国史也对“边缘的”和“域外的”历史关注很少。 这套书的撰写者都来自欧美,当然身在全球史潮流之中,主编卜正民教 授本人就是全球史的身体力行者,他的《维梅尔的帽子》(Vermeer's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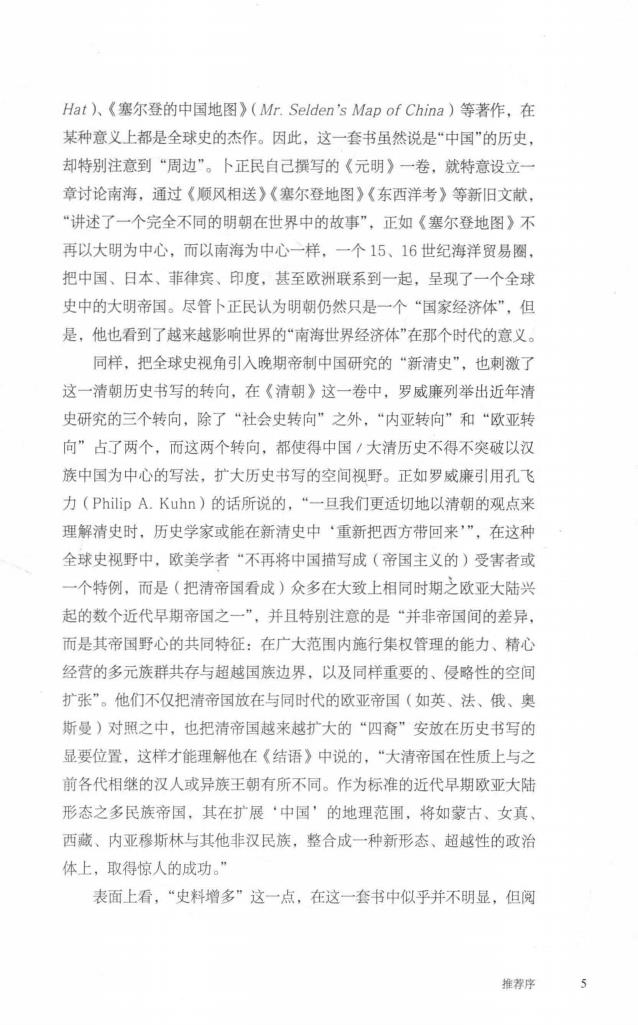
Hat入、《塞尔登的中国地图》(Mr.Selden's Map of China)等著作,在 某种意义上都是全球史的杰作。因此,这一套书虽然说是“中国”的历史, 却特别注意到“周边”。卜正民自己撰写的《元明》一卷,就特意设立一 章讨论南海,通过《顺风相送》《塞尔登地图》《东西洋考》等新旧文献, “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明朝在世界中的故事”,正如《塞尔登地图》不 再以大明为中心,而以南海为中心一样,一个15、16世纪海洋贸易圈。 把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甚至欧洲联系到一起,呈现了一个全球 史中的大明帝国。尽管卜正民认为明朝仍然只是一个“国家经济体”,但 是,他也看到了越来越影响世界的“南海世界经济体”在那个时代的意义。 同样,把全球史视角引入晚期帝制中国研究的“新清史”,也刺激了 这一清朝历史书写的转向,在《清朝》这一卷中,罗威廉列举出近年清 史研究的三个转向,除了“社会史转向”之外,“内亚转向”和“欧亚转 向”占了两个,而这两个转向,都使得中国/大清历史不得不突破以汉 族中国为中心的写法,扩大历史书写的空间视野。正如罗威廉引用孔飞 力(Philip A.Kuhn)的话所说的,“一旦我们更适切地以清朝的观点来 理解清史时,历史学家或能在新清史中·重新把西方带回来'”,在这种 全球史视野中,欧美学者“不再将中国描写成(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或 一个特例,而是(把清帝国看成)众多在大致上相同时期之欧亚大陆兴 起的数个近代早期帝国之一”,并且特别注意的是“并非帝国间的差异, 而是其帝国野心的共同特征:在广大范围内施行集权管理的能力、精心 经营的多元族群共存与超越国族边界,以及同样重要的、侵略性的空间 扩张”。他们不仅把清帝国放在与同时代的欧亚帝国(如英、法、俄、奥 斯曼)对照之中,也把清帝国越来越扩大的“四裔”安放在历史书写的 显要位置,这样才能理解他在《结语》中说的,“大清帝国在性质上与之 前各代相继的汉人或异族王朝有所不同。作为标准的近代早期欧亚大陆 形态之多民族帝国,其在扩展·中国'的地理范围,将如蒙古、女真 西藏、内亚穆斯林与其他非汉民族,整合成一种新形态、超越性的政治 体上,取得惊人的成功。” 表面上看,“史料增多”这一点,在这一套书中似乎并不明显,但阅 推荐序

读中我们也常常有意外惊喜。毫无疑问,中国学者可以先接触新近的考 古发掘、简帛文书、各种档案,这一点欧美学者并没有优势。但问题是 新发现需要新解释,缺乏新的观察角度、叙述方式和论述立场,新材料 带来的有时候只是“增量”而不是“质变”,并不能使历史“旧貌换新 颜”。西方学者虽然不一定能够看到最多或最新的资料,但他们善于解释 这些新史料,并且有机地用于历史叙述。比如,陆威仪撰写《秦汉》卷, 就能够使用各种简帛资料(包山楚简、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居延 汉简),其中《法律》一章,基本上依赖睡虎地、张家山等出土文献,而 库恩所写的《宋朝》卷讨论辽金的佛教,也能够引入诸如房山云居寺、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应县木塔等考古与建筑资料;特别是,往往眼光不 同,选择的史料就不同,卜正民撰写的《元明》一卷,不仅用了《天中 记》这样过去通史一般很少用的边缘史料来作为贯穿整个明史叙述的骨 架,而且用了严嵩籍没时的财产簿、《吴氏分家簿》《余廷枢等立分单陶 书》《孙时立陶书》《休宁程虚宇立分书》以及耶稣会士被没收的物品记 录等,讨论明代各种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的家当,让读者更直观地 感受到,明代各种阶层与各色人等的一般经济状况:同样,他还用《塞 尔登地图》等新发现和《顺风相送》(东西洋考》等旧史料,来讨论南海 以及贸易往来;更特别设立《物华》一章来实践物质文化史,讨论文物 家具、书籍、瓷器、书画,讨论当时文人的艺术品位、文化修养与艺术 商品和市场问题,因此,过去一般通史写作中不太使用的《长物志》《格 古要论》《味水轩日记》之类的边缘史料(当然,如果研究艺术、物质、 文化的著作,会常常使用它们)就成为重要史料。这里显示出他对于史 料有着别具一格的判断、理解和阐释。 当然,作为西方学者,他们常常能够以西方历史作为背景,时时引 入欧洲资料与中文文献互相参照,这就更加扩大了史料边界。 欧美学者写中国通史,当然与中国学者不同;21世纪写中国通史,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