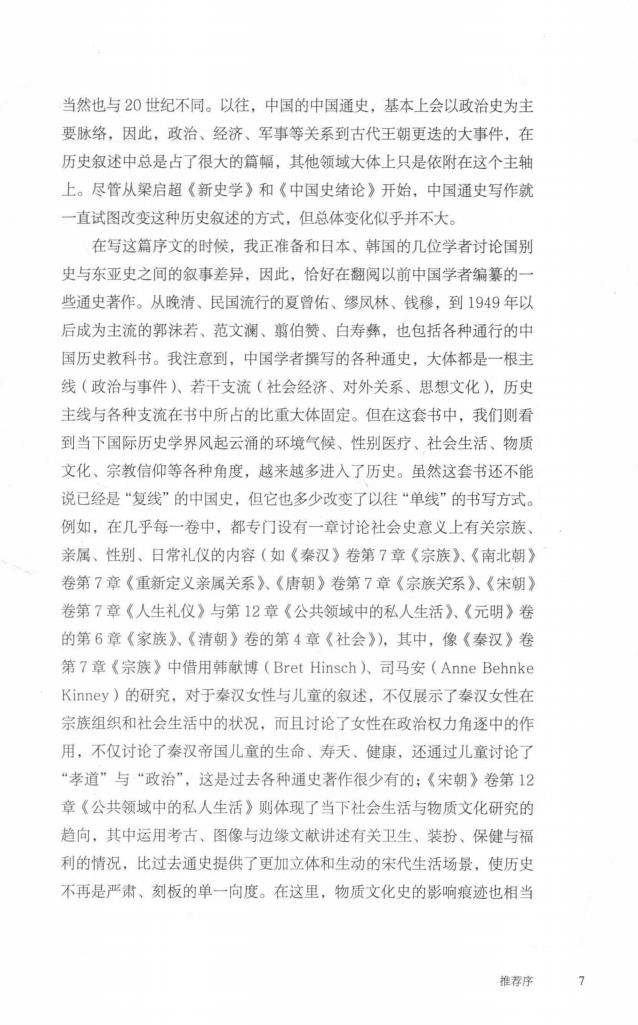
当然也与20世纪不同。以往,中国的中国通史,基本上会以政治史为主 要脉络,因此,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到古代王朝更迭的大事件,在 历史叙述中总是占了很大的篇幅,其他领域大体上只是依附在这个主轴 上。尽管从梁启超《新史学》和《中国史绪论》开始,中国通史写作就 一直试图改变这种历史叙述的方式,但总体变化似乎并不大。 在写这篇序文的时候,我正准备和日本、韩国的几位学者讨论国别 史与东亚史之间的叙事差异,因此,恰好在翻阅以前中国学者编纂的 些通史著作。从晚清、民国流行的夏曾佑、缪凤林、钱穆,到1949年以 后成为主流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也包括各种通行的中 国历史教科书。我注意到,中国学者撰写的各种通史,大体都是一根主 线(政治与事件)若干支流(社会经济、对外关系、思想文化),历史 主线与各种支流在书中所占的比重大体固定。但在这套书中,我们则看 到当下国际历史学界风起云涌的环境气候、性别医疗、社会生活、物质 文化、宗教信仰等各种角度,越来越多进入了历史。虽然这套书还不能 说已经是“复线”的中国史,但它也多少改变了以往“单线”的书写方式。 例如,在几乎每一卷中,都专门设有一章讨论社会史意义上有关宗族 亲属、性别、日常礼仪的内容(如《秦汉》卷第7章《宗族)、《南北朝》 卷第7章《重新定义亲属关系入、《唐朝》卷第7章《宗族关系》、《宋朝》 卷第7章《人生礼仪》与第12章《公共领域中的私人生活》、《元明》卷 的第6章《家族入、《清朝》卷的第4章《社会》),其中,像《秦汉》卷 第7章《宗族》中借用韩献博(Bret Hinsch人司马安(Anne Behnke Kinney)的研究,对于秦汉女性与儿童的叙述,不仅展示了秦汉女性在 宗族组织和社会生活中的状况,而且讨论了女性在政治权力角逐中的作 用,不仅讨论了秦汉帝国儿童的生命、寿天、健康,还通过儿童讨论了 “孝道”与“政治”,这是过去各种通史著作很少有的:《宋朝》卷第12 章《公共领域中的私人生活》则体现了当下社会生活与物质文化研究的 趋向,其中运用考古、图像与边缘文献讲述有关卫生、装扮、保健与福 利的情况,比过去通史提供了更加立体和生动的宋代生活场景,使历史 不再是严肃、刻板的单一向度。在这里,物质文化史的影响痕迹也相当 推荐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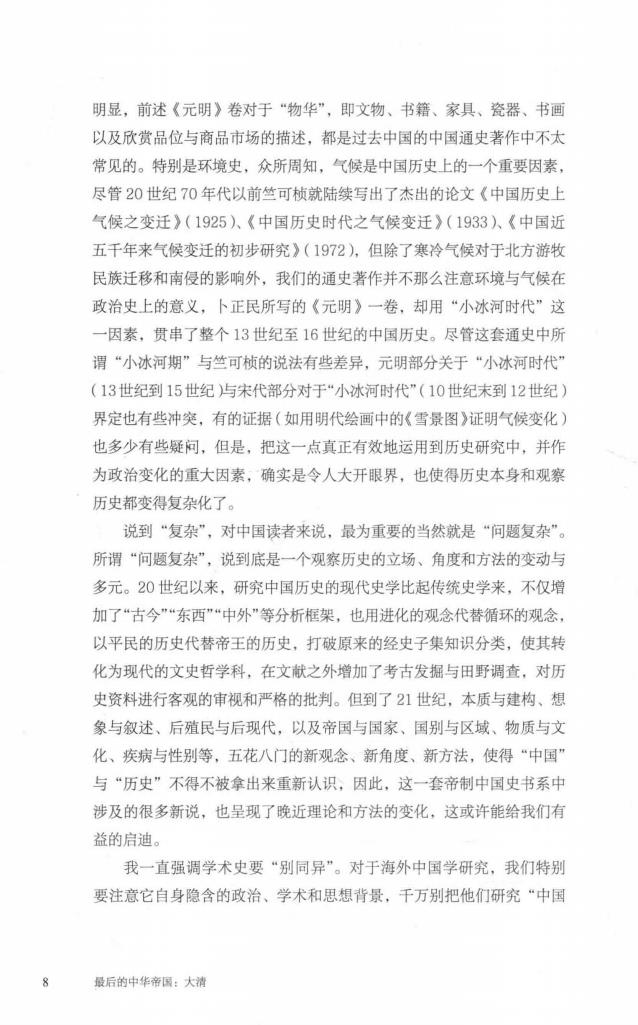
明显,前述《元明》卷对于“物华”,即文物、书籍、家具、瓷器、书画 以及欣赏品位与商品市场的描述,都是过去中国的中国通史著作中不太 常见的。特别是环境史,众所周知,气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前竺可桢就陆续写出了杰出的论文《中国历史上 气候之变迁)(1925)入、《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1933)、《中国近 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972),但除了寒冷气候对于北方游牧 民族迁移和南侵的影响外,我们的通史著作并不那么注意环境与气候在 政治史上的意义,卜正民所写的《元明》一卷,却用“小冰河时代”这 一因素,贯串了整个13世纪至16世纪的中国历史。尽管这套通史中所 谓“小冰河期”与竺可桢的说法有些差异,元明部分关于“小冰河时代” (13世纪到15世纪与宋代部分对于“小冰河时代”(10世纪末到12世纪) 界定也有些冲突,有的证据(如用明代绘画中的(雪景图》证明气候变化) 也多少有些疑问,但是,把这一点真正有效地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并作 为政治变化的重大因素,确实是令人大开眼界,也使得历史本身和观察 历史都变得复杂化了。 说到“复杂”,对中国读者来说,最为重要的当然就是“问题复杂”。 所谓“问题复杂”,说到底是一个观察历史的立场、角度和方法的变动与 多元。20世纪以来,研究中国历史的现代史学比起传统史学来,不仅增 加了“古今”“东西”“中外”等分析框架,也用进化的观念代替循环的观念, 以平民的历史代替帝王的历史,打破原来的经史子集知识分类,使其转 化为现代的文史哲学科,在文献之外增加了考古发掘与田野调查,对历 史资料进行客观的审视和严格的批判。但到了21世纪,本质与建构、想 象与叙述、后殖民与后现代,以及帝国与国家、国别与区域、物质与文 化、疾病与性别等,五花八门的新观念、新角度、新方法,使得“中国” 与“历史”不得不被拿出来重新认识,因此,这一套帝制中国史书系中 涉及的很多新说,也呈现了晚近理论和方法的变化,这或许能给我们有 益的启迪。 我一直强调学术史要“别同异”。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我们特别 要注意它自身隐含的政治、学术和思想背景,千万别把他们研究“中国 最后的中华帝属:大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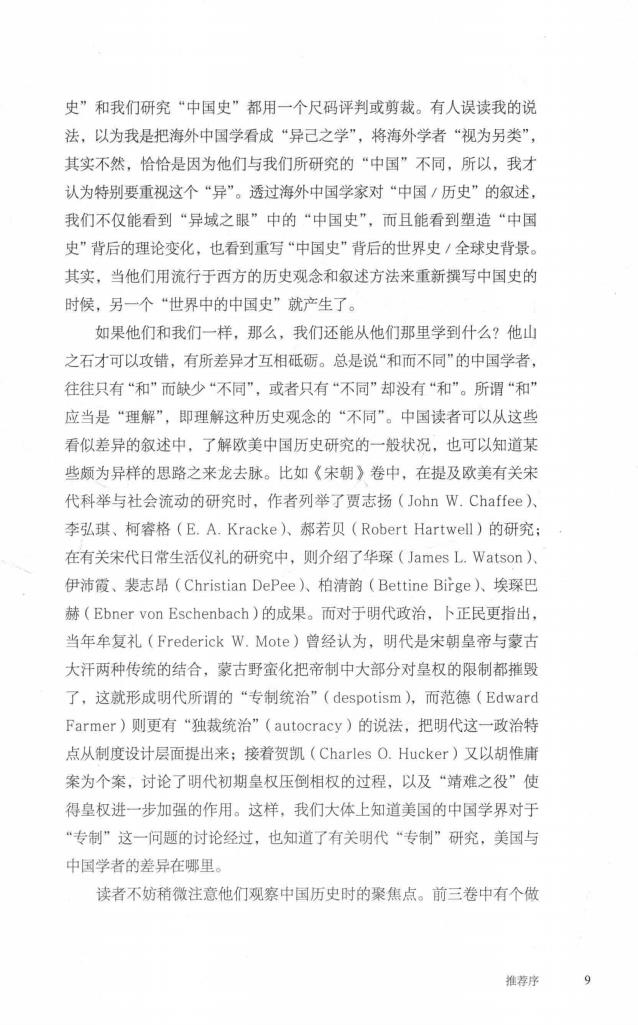
史”和我们研究“中国史”都用一个尺码评判或剪裁。有人误读我的说 法,以为我是把海外中国学看成“异己之学”,将海外学者“视为另类” 其实不然,恰恰是因为他们与我们所研究的“中国”不同,所以,我才 认为特别要重视这个“异”。透过海外中国学家对“中国/历史”的叙述, 我们不仅能看到“异域之眼”中的“中国史”,而且能看到塑造“中国 史”背后的理论变化,也看到重写“中国史”背后的世界史/全球史背景 其实,当他们用流行于西方的历史观念和叙述方法来重新撰写中国史的 时候,另一个“世界中的中国史”就产生了。 如果他们和我们一样,那么,我们还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他山 之石才可以攻错,有所差异才互相砥砺。总是说“和而不同”的中国学者, 往往只有“和”而缺少“不同”,或者只有“不同”却没有“和”。所谓“和” 应当是“理解”,即理解这种历史观念的“不同”。中国读者可以从这些 看似差异的叙述中,了解欧美中国历史研究的一般状况,也可以知道某 些颇为异样的思路之来龙去脉。比如《宋朝》卷中,在提及欧美有关宋 代科举与社会流动的研究时,作者列举了贾志扬(John W.Chaffee)入 李弘琪、柯睿格(E.A.Kracke、郝若贝(Robert Hartwell)的研究: 在有关宋代日常生活仪礼的研究中,则介绍了华深(James L.Watson入 伊沛霞、裴志昂(Christian DePee人柏清韵(Bettine Birge入埃琛巴 赫(Ebner von Eschenbach)的成果。而对于明代政治,卜正民更指出, 当年牟复礼(Frederick W.Mote)曾经认为,明代是宋朝皇帝与蒙古 大汗两种传统的结合,蒙古野蛮化把帝制中大部分对皇权的限制都摧毁 了,这就形成明代所谓的“专制统治”(despotism),而范德(Edward Farmer)则更有“独裁统治”(autocracy)的说法,把明代这一政治特 点从制度设计层面提出来;接着贺凯(Charles C.Hucker)又以胡惟庸 案为个案,讨论了明代初期皇权压倒相权的过程,以及“靖难之役”使 得皇权进一步加强的作用。这样,我们大体上知道美国的中国学界对于 “专制”这一问题的讨论经过,也知道了有关明代“专制”研究,美国与 中国学者的差异在哪里。 读者不妨稍微注意他们观察中国历史时的聚焦点。前三卷中有个做 推差序

法很好,撰写者常常会将他关注的议题开列出来,使我们一目了然。例 如对秦汉,他关注(1)在帝国秩序之下逐渐式徽但并未被完全抹除的 地域文化;(2)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之强化:(3)建立在表意 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 典;(4)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和对帝国边缘族群所 开展的军事活动:(5)农村地区富裕的豪强大族的兴旺。对南北朝,作 者说明这一时期的历史重心应当是:中国地理的重新定义,它的内在结 构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新的社会精英,世袭制的军事人口和新的军 事组织,影响后世的宗教使中国不再严格按社会与政治来划分人群,等 等。对唐代,他关注唐宋政治与文化的转型、中国地理格局的再变化 商人与外部世界、城市中的商业与贸易引起的文化与文学变化,而在 卜正民所撰写的《元明》一卷中,虽然并不像前几卷那样明说要点,但 他一方面说,“我们只需举出元明史上的两大主题一独裁制和商品化 (commercialization,在宋代尚不见其踪影,而到了元明时期,它们在 质和量上已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因此,他“没有把它(1368年元明 易代)当作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换点,而是连接两段历史的纽带。使明 王朝崛起的叛乱,确实终止了蒙古人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但也使蒙古 人的遗产得以历数百年而传承不绝。元明两代共同塑造了中国的专制政 体,将中国社会解体,重新以家族为中心聚合起来:并且,为更好地积 聚商业财富而重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别辟蹊径,不仅把 社会结构(《家族》入、自然环境(《经济与生态》以、宗教信仰(《信仰》) 物质文化(《物华》)以及外部世界(《南海》)各列一章,而且特别指出“这 两个朝代所在的时期恰好是研究世界其他地方的气象史专家所说的小冰 河期(the Little Ice Age”,因此他特别详细地叙述了自然灾害一饥 荒、洪水、干旱、愿风、蝗虫、流行病。从这里,读者或许可以看到他 对于元明两代历史的新认识。同样,对于清代历史来说,我们也可以注 意,为什么罗威廉在《治理》这一章中那么重视“理藩院”“内务府”和“军 机处“这三个他所谓的“创新”?因为这三个“创新”,其实就是“管理”“保 护”和“控制”,它指向清王朝政治统治最重要的三个方面:一是对汉族 10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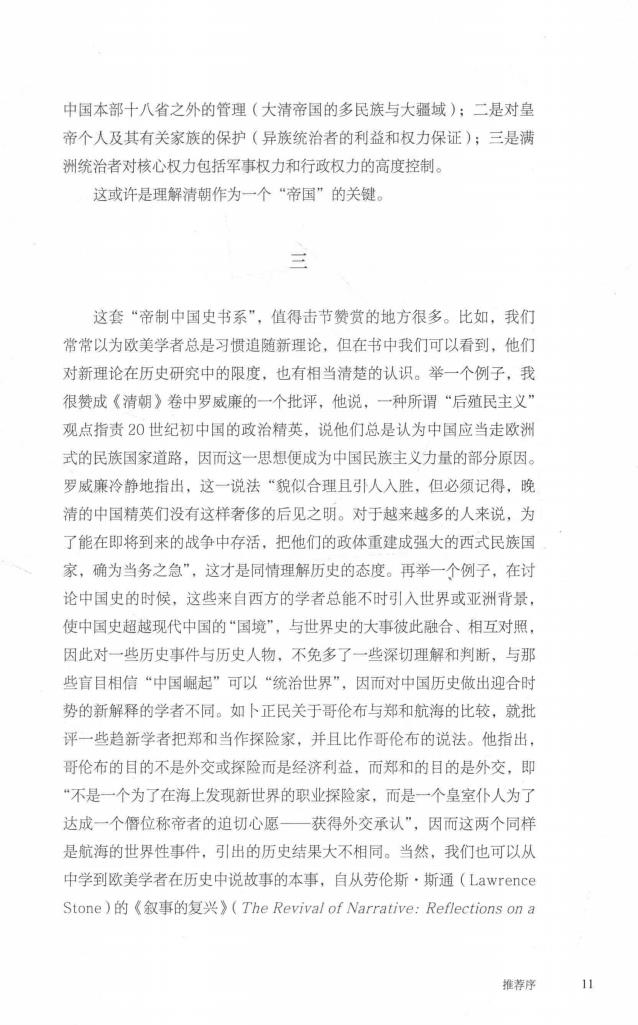
中国本部十八省之外的管理(大清帝国的多民族与大疆域):二是对皇 帝个人及其有关家族的保护(异族统治者的利益和权力保证);三是满 洲统治者对核心权力包括军事权力和行政权力的高度控制。 这或许是理解清朝作为一个“帝国”的关键。 三 这套“帝制中国史书系”,值得击节赞赏的地方很多。比如,我们 常常以为欧美学者总是习惯追随新理论,但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 对新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限度,也有相当清楚的认识。举一个例子,我 很赞成《清朝》卷中罗威廉的一个批评,他说,一种所谓“后殖民主义” 观点指责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精英,说他们总是认为中国应当走欧洲 式的民族国家道路,因而这一思想便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部分原因。 罗威廉冷静地指出,这一说法“貌似合理且引人入胜,但必须记得,晚 清的中国精英们没有这样奢侈的后见之明。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为 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存活,把他们的政体重建成强大的西式民族国 家,确为当务之急”,这才是同情理解历史的态度。再举一个例子,在讨 论中国史的时候,这些来自西方的学者总能不时引入世界或亚洲背景, 使中国史超越现代中国的“国境”,与世界史的大事彼此融合、相互对照, 因此对一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不免多了一些深切理解和判断,与那 些盲目相信“中国崛起”可以“统治世界”,因而对中国历史做出迎合时 势的新解释的学者不同。如卜正民关于哥伦布与郑和航海的比较,就批 评一些趋新学者把郑和当作探险家,并且比作哥伦布的说法。他指出 哥伦布的目的不是外交或探险而是经济利益,而郑和的目的是外交,即 “不是一个为了在海上发现新世界的职业探险家,而是一个皇室仆人为了 达成一个僭位称帝者的迫切心愿一获得外交承认”,因而这两个同样 是航海的世界性事件,引出的历史结果大不相同。当然,我们也可以从 中学到欧美学者在历史中说故事的本事,自从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叙事的复兴》(The 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a 推荐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