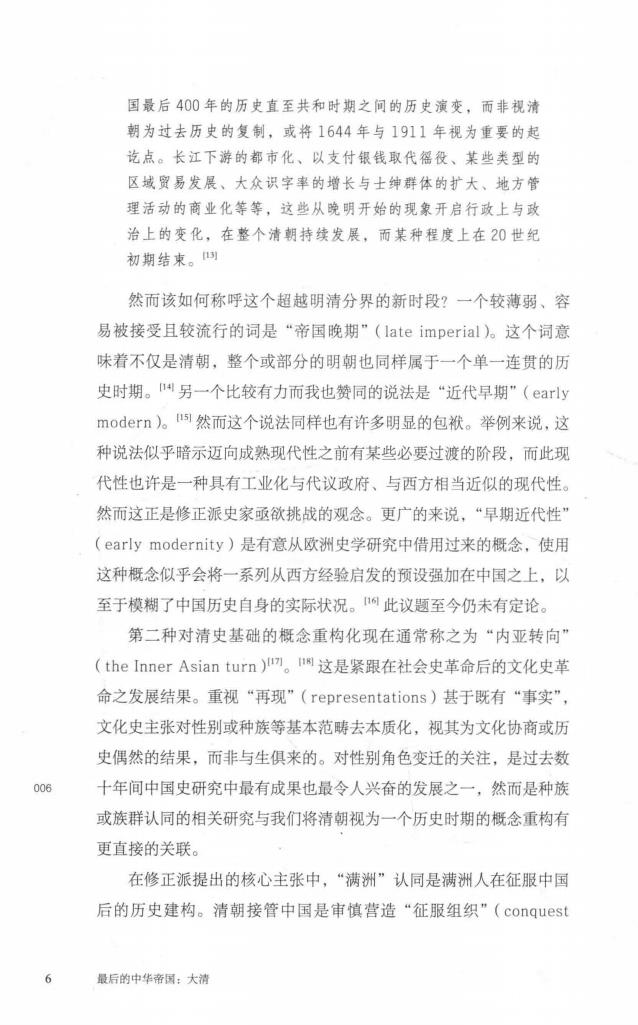
国最后400年的历史直至共和时期之间的历史演变,而非视清 朝为过去历史的复制,或将1644年与1911年视为重要的起 讫点。长江下游的都市化、以支付银钱取代徭役、某些类型的 区城贸易发展、大众识字率的增长与士绅群体的扩大、地方管 理活动的商业化等等,这些从晚明开始的现象开启行政上与政 治上的变化,在整个清朝持续发展,而某种程度上在20世纪 初期结束。回 然而该如何称呼这个超越明清分界的新时段?一个较薄弱、容 易被接受且较流行的词是“帝国晚期”(late imperial)。这个词意 味着不仅是清朝,整个或部分的明朝也同样属于一个单一连贯的历 史时期。另一个比较有力而我也赞同的说法是“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然而这个说法同样也有许多明显的包袱。举例来说,这 种说法似乎暗示迈向成熟现代性之前有某些必要过渡的阶段,而此现 代性也许是一种具有工业化与代议政府、与西方相当近似的现代性 然而这正是修正派史家亟欲挑战的观念。更广的来说,“早期近代性 (early modernity)是有意从欧洲史学研究中借用过来的概念,使用 这种概念似乎会将一系列从西方经验启发的预设强加在中国之上,以 至于模糊了中国历史自身的实际状况。网此议题至今仍未有定论。 第二种对清史基础的概念重构化现在通常称之为“内亚转向 (the Inner Asian turn)。这是紧跟在社会史革命后的文化史革 命之发展结果。重视“再现”(representations)甚于既有“事实”, 文化史主张对性别或种族等基本范畴去本质化,视其为文化协商或历 史偶然的结果,而非与生俱来的。对性别角色变迁的关注,是过去数 006 十年间中国史研究中最有成果也最令人兴奋的发展之一,然而是种族 或族群认同的相关研究与我们将清朝视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概念重构有 更直接的关联。 在修正派提出的核心主张中,“满洲”认同是满洲人在征服中国 后的历史建构。清朝接管中国是审慎营造“征服组织”(conquest 6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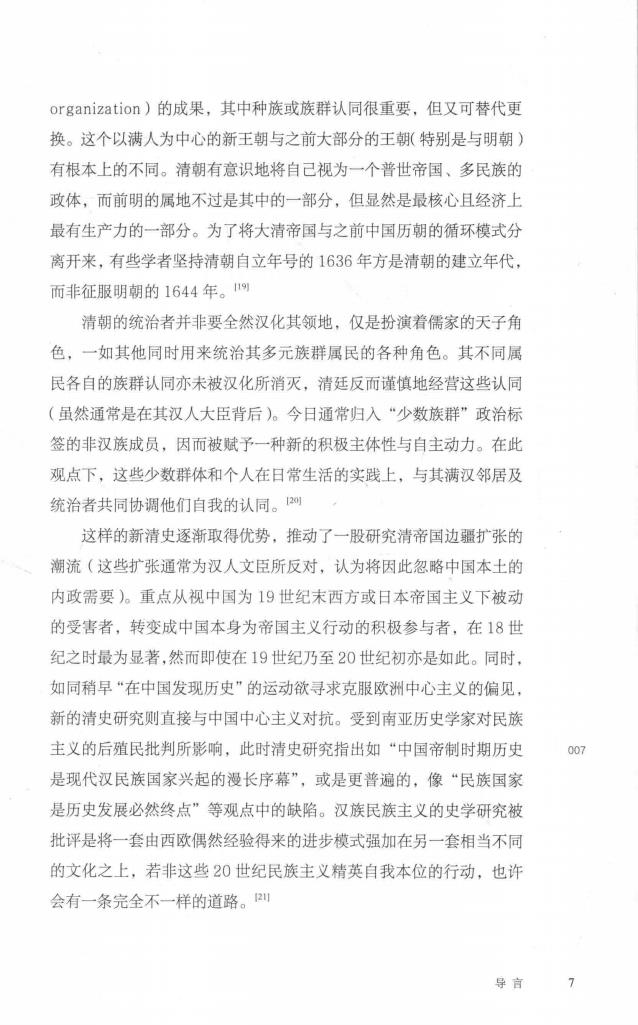
organization)的成果,其中种族或族群认同很重要,但又可替代更 换。这个以满人为中心的新王朝与之前大部分的王朝飘(特别是与明朝) 有根本上的不同。清朝有意识地将自己视为一个普世帝国、多民族的 政体,而前明的属地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显然是最核心且经济上 最有生产力的一部分。为了将大清帝国与之前中国历朝的循环模式分 离开来,有些学者坚持清朝自立年号的1636年方是清朝的建立年代, 而非征服明朝的1644年。1 清朝的统治者并非要全然汉化其领地,仅是扮演着儒家的天子角 色,一如其他同时用来统治其多元族群属民的各种角色。其不同属 民各自的族群认同亦未被汉化所消灭,清廷反而谨慎地经营这些认同 (虽然通常是在其汉人大臣背后)。今日通常归入“少数族群”政治标 签的非汉族成员,因而被赋予一种新的积极主体性与自主动力。在此 观点下,这些少数群体和个人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上,与其满汉邻居及 统治者共同协调他们自我的认同。网 这样的新清史逐渐取得优势,推动了一股研究清帝国边疆扩张的 潮流(这些扩张通常为汉人文臣所反对,认为将因此忽略中国本土的 内政需要)。重点从视中国为19世纪末西方或日本帝国主义下被动 的受害者,转变成中国本身为帝国主义行动的积极参与者,在18世 纪之时最为显著,然而即使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亦是如此。同时, 如同稍早“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运动欲寻求克服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 新的清史研究则直接与中国中心主义对抗。受到南亚历史学家对民族 主义的后殖民批判所影响,此时清史研究指出如“中国帝制时期历史 00 是现代汉民族国家兴起的漫长序幕”,或是更普遍的,像“民族国家 是历史发展必然终点”等观点中的缺陷。汉族民族主义的史学研究被 批评是将一套由西欧偶然经验得来的进步模式强加在另一套相当不同 的文化之上,若非这些20世纪民族主义精英自我本位的行动,也许 会有一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四 导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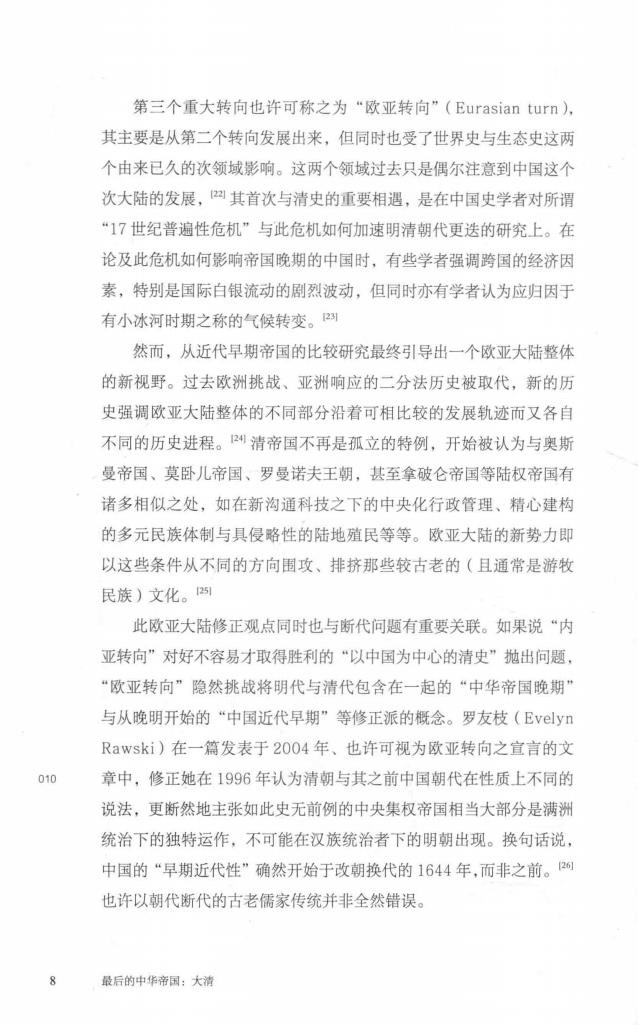
第三个重大转向也许可称之为“欧亚转向”(Eurasian turn), 其主要是从第二个转向发展出来,但同时也受了世界史与生态史这两 个由来已久的次领域影响。这两个领域过去只是偶尔注意到中国这个 次大陆的发展,四其首次与清史的重要相遇,是在中国史学者对所谓 “17世纪普遍性危机”与此危机如何加速明清朝代更迭的研究上。在 论及此危机如何影响帝国晚期的中国时,有些学者强调跨国的经济因 素,特别是国际白银流动的剧烈波动,但同时亦有学者认为应归因于 有小冰河时期之称的气候转变。以 然而,从近代早期帝国的比较研究最终引导出一个欧亚大陆整体 的新视野。过去欧洲挑战、亚洲响应的二分法历史被取代,新的历 史强调欧亚大陆整体的不同部分沿着可相比较的发展轨迹而又各自 不同的历史进程。清帝国不再是孤立的特例,开始被认为与奥斯 曼帝国、莫卧儿帝国、罗曼诺夫王朝,甚至拿破仑帝国等陆权帝国有 诸多相似之处,如在新沟通科技之下的中央化行政管理、精心建构 的多元民族体制与具侵略性的陆地殖民等等。欧亚大陆的新势力即 以这些条件从不同的方向围攻、排挤那些较古老的(且通常是游牧 民族)文化。两 此欧亚大陆修正观点同时也与断代问题有重要关联。如果说“内 亚转向”对好不容易才取得胜利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清史”抛出问题, “欧亚转向”隐然挑战将明代与清代包含在一起的“中华帝国晚期 与从晚明开始的“中国近代早期”等修正派的概念。罗友枝(Evelyn Rawski)在一篇发表于2004年、也许可视为欧亚转向之宣言的文 010 章中,修正她在1996年认为清朝与其之前中国朝代在性质上不同的 说法,更断然地主张如此史无前例的中央集权帝国相当大部分是满洲 统治下的独特运作,不可能在汉族统治者下的明朝出现。换句话说, 中国的“早期近代性”确然开始于改朝换代的1644年,而非之前。啊 也许以朝代断代的古老儒家传统并非全然错误。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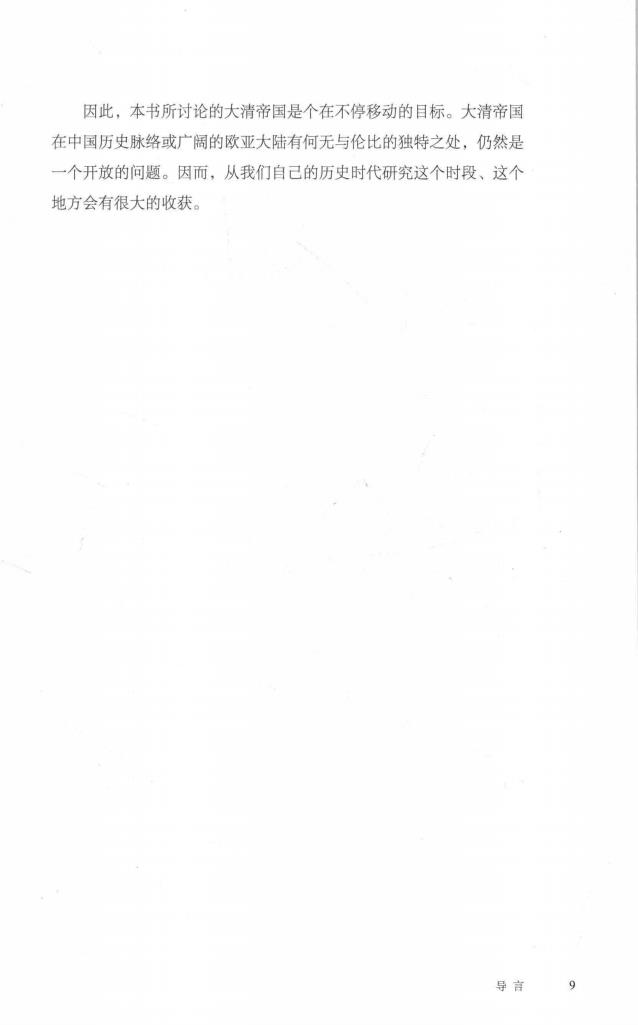
因此,本书所讨论的大清帝国是个在不停移动的目标。大清帝国 在中国历史脉络或广阔的欧亚大陆有何无与伦比的独特之处,仍然是 一个开放的问题。因而,从我们自己的历史时代研究这个时段、这个 地方会有很大的收获。 导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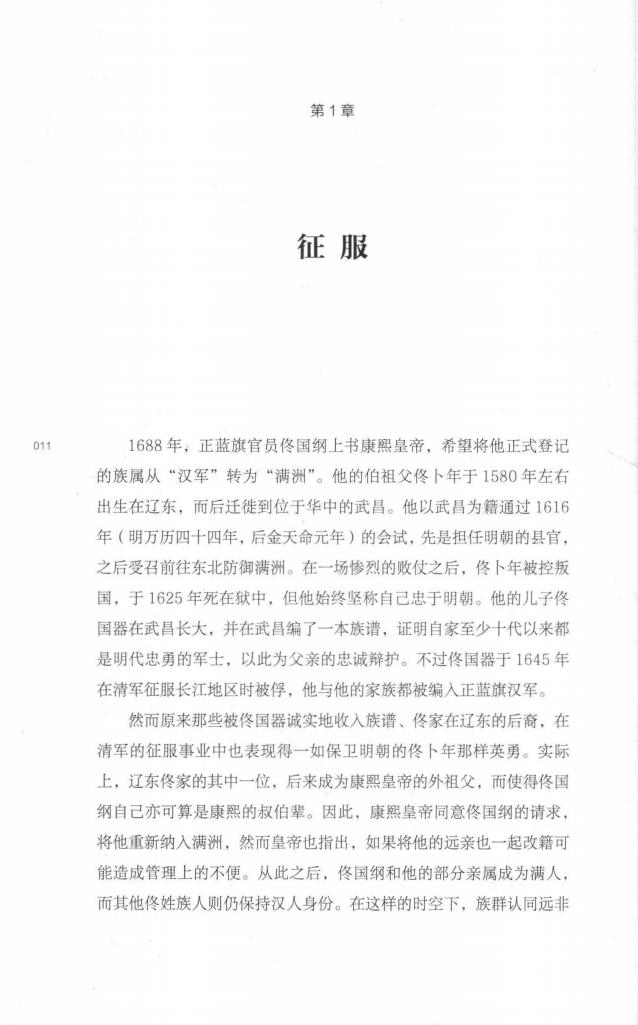
第1章 征服 011 1688年,正蓝旗官员佟国纲上书康熙皇帝,希望将他正式登记 的族属从“汉军”转为“满洲”。他的伯祖父佟卜年于1580年左右 出生在辽东,而后迁徙到位于华中的武昌。他以武昌为籍通过1616 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的会试,先是担任明朝的县官 之后受召前往东北防御满洲。在一场惨烈的败仗之后,佟卜年被控叛 国,于1625年死在狱中,但他始终坚称自己忠于明朝。他的儿子佟 国器在武昌长大,并在武昌编了一本族谱,证明自家至少十代以来都 是明代忠勇的军土,以此为父亲的忠诚辩护。不过佟国器于1645年 在清军征服长江地区时被俘,他与他的家族都被编入正蓝旗汉军。 然而原来那些被佟国器诚实地收入族谱、佟家在辽东的后裔,在 清军的征服事业中也表现得一如保卫明朝的佟卜年那样英勇。实际 上,辽东佟家的其中一位,后来成为康熙皇帝的外祖父,而使得佟国 纲自己亦可算是康熙的叔伯辈。因此,康熙皇帝同意佟国纲的请求, 将他重新纳入满洲,然而皇帝也指出,如果将他的远亲也一起改籍可 能造成管理上的不便。从此之后,佟国纲和他的部分亲属成为满人, 而其他佟姓族人则仍保持汉人身份。在这样的时空下,族群认同远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