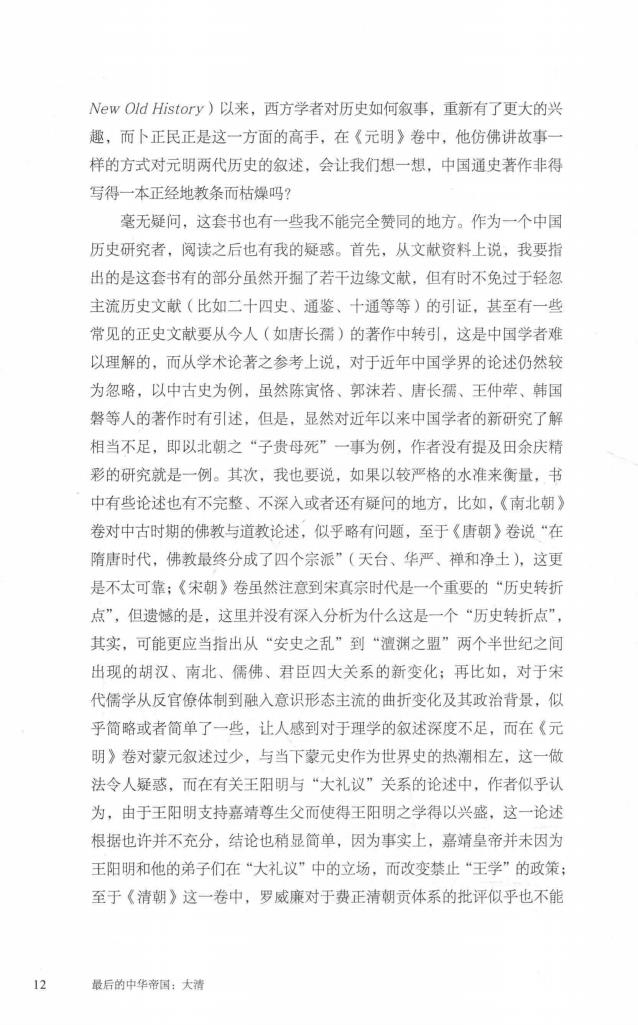
NeWO1 d History)以来,西方学者对历史如何叙事,重新有了更大的兴 趣,而卜正民正是这一方面的高手,在《元明》卷中,他仿佛讲故事 样的方式对元明两代历史的叙述,会让我们想一想,中国通史著作非得 写得一本正经地教条而枯燥吗? 毫无疑问,这套书也有一些我不能完全赞同的地方。作为一个中国 历史研究者,阅读之后也有我的疑惑。首先,从文献资料上说,我要指 出的是这套书有的部分虽然开掘了若干边缘文献,但有时不免过于轻忽 主流历史文献(比如二十四史、通鉴、十通等等)的引证,甚至有一些 常见的正史文献要从今人(如唐长需)的著作中转引,这是中国学者难 以理解的,而从学术论著之参考上说,对于近年中国学界的论述仍然较 为忽略,以中古史为例,虽然陈寅格、郭沫若、唐长孺、王仲荦、韩国 磐等人的著作时有引述,但是,显然对近年以来中国学者的新研究了解 相当不足,即以北朝之“子贵母死”一事为例,作者没有提及田余庆精 彩的研究就是一例。其次,我也要说,如果以较严格的水准来衡量,书 中有些论述也有不完整、不深入或者还有疑问的地方,比如,《南北朝》 卷对中古时期的佛教与道教论述,似乎略有问题,至于《唐朝》卷说“在 隋唐时代,佛教最终分成了四个宗派”(天台、华严、禅和净土),这更 是不太可靠:《宋朝》卷虽然注意到宋真宗时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 点”,但遗憾的是,这里并没有深入分析为什么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 其实,可能更应当指出从“安史之乱”到“禮渊之盟”两个半世纪之间 出现的胡汉、南北、儒佛、君臣四大关系的新变化:再比如,对于宋 代儒学从反官僚体制到融入意识形态主流的曲折变化及其政治背景,似 乎简略或者简单了一些,让人感到对于理学的叙述深度不足,而在《元 明》卷对蒙元叙述过少,与当下蒙元史作为世界史的热潮相左,这一做 法令人疑惑,而在有关王阳明与“大礼议”关系的论述中,作者似乎认 为,由于王阳明支持嘉靖尊生父而使得王阳明之学得以兴盛,这一论述 根据也许并不充分,结论也稍显简单,因为事实上,嘉靖皇帝并未因为 王阳明和他的弟子们在“大礼议”中的立场,而改变禁止“王学”的政策: 至于《清朝》这一卷中,罗威廉对于费正清朝贡体系的批评似乎也不能 最后的中华帝国:太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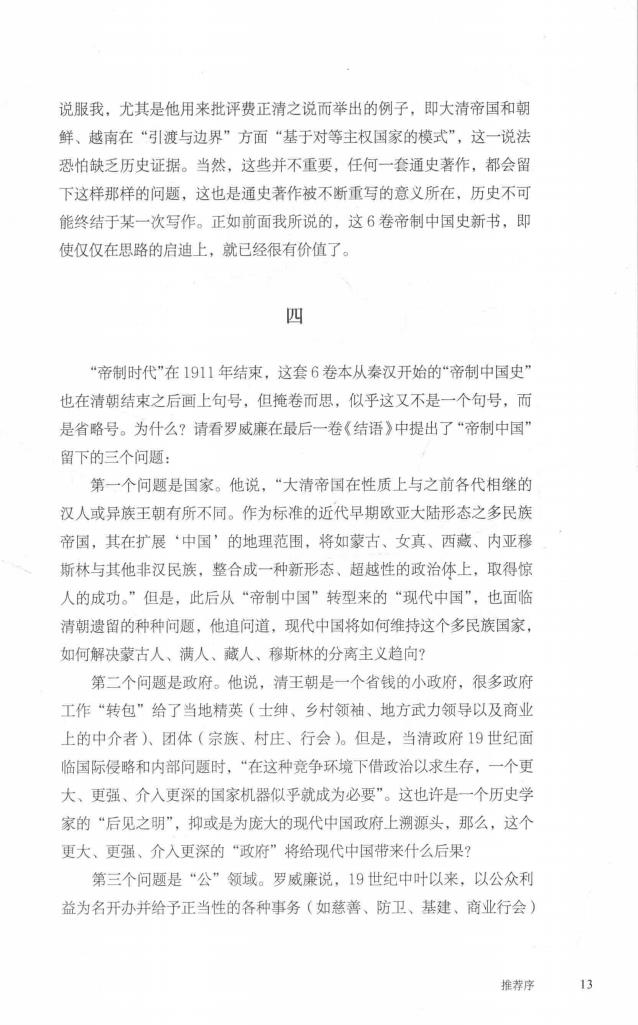
说服我,尤其是他用来批评费正清之说而举出的例子,即大清帝国和朝 鲜、越南在“引渡与边界”方面“基于对等主权国家的模式”,这一说法 恐怕缺乏历史证据。当然,这些并不重要,任何一套通史著作,都会留 下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也是通史著作被不断重写的意义所在,历史不可 能终结于某一次写作。正如前面我所说的,这6卷帝制中国史新书,即 使仅仅在思路的启迪上,就已经很有价值了。 多 “帝制时代”在1911年结束,这套6卷本从泰汉开始的“帝制中国史" 也在清朝结束之后画上句号,但掩卷而思,似乎这又不是一个句号,而 是省略号。为什么?请看罗威廉在最后一卷《结语》中提出了“帝制中国 留下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国家。他说,“大清帝国在性质上与之前各代相继的 汉人或异族王朝有所不同。作为标准的近代早期欧亚大陆形态之多民族 帝国,其在扩展‘中国'的地理范围,将如蒙古、女真、西藏、内亚穆 斯林与其他非汉民族,整合成一种新形态、超越性的政治体上,取得惊 人的成功。”但是,此后从“帝制中国”转型来的“现代中国”,也面临 清朝遗留的种种问题,他追问道,现代中国将如何维持这个多民族国家 如何解决蒙古人、满人、藏人、穆斯林的分离主义趋向?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他说,清王朝是一个省钱的小政府,很多政府 工作“转包”给了当地精英(士绅、乡村领袖、地方武力领导以及商业 上的中介者)、团体(宗族、村庄、行会)。但是,当清政府19世纪面 临国际侵略和内部问题时,“在这种竞争环境下借政治以求生存,一个更 大、更强、介入更深的国家机器似乎就成为必要”。这也许是一个历史学 家的“后见之明”,抑或是为庞大的现代中国政府上溯源头,那么,这个 更大、更强、介入更深的“政府”将给现代中国带来什么后果? 第三个问题是“公”领域。罗威廉说,19世纪中叶以来,以公众利 益为名开办并给予正当性的各种事务(如慈善、防卫、基建、商业行会) 推荐序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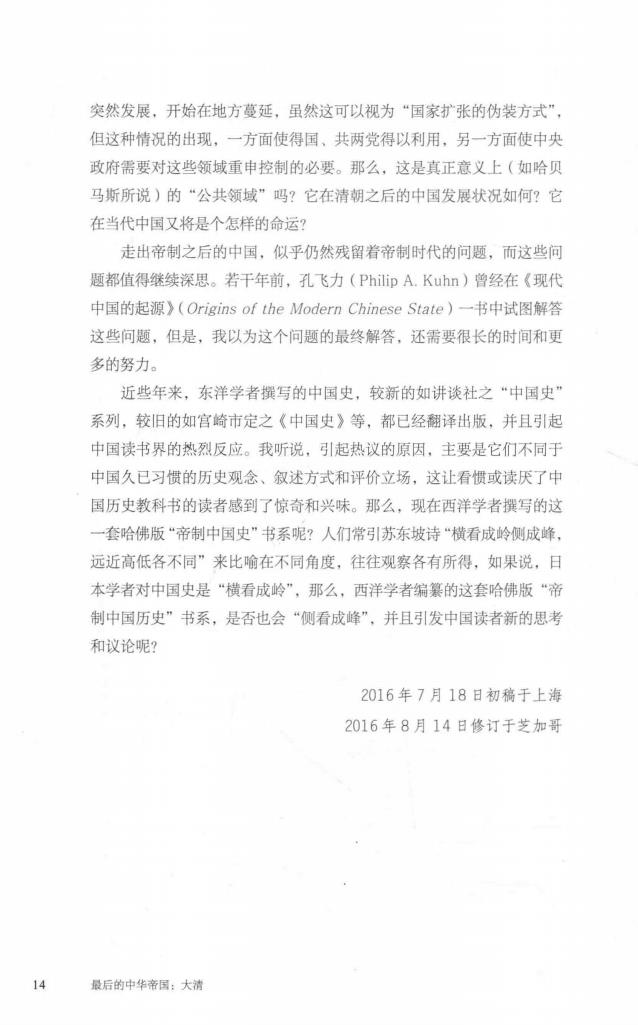
突然发展,开始在地方蔓延,虽然这可以视为“国家扩张的伪装方式” 但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使得国、共两党得以利用,另一方面使中央 政府需要对这些领域重申控制的必要。那么,这是真正意义上(如哈贝 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吗?它在清朝之后的中国发展状况如何?它 在当代中国又将是个怎样的命运? 走出帝制之后的中国,似乎仍然残留着帝制时代的问题,而这些问 题都值得继续深思。若干年前,孔飞力(Philip A.Kuhn)曾经在《现代 中国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一书中试图解答 这些问题,但是,我以为这个问题的最终解答,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和更 多的努力。 近些年来,东洋学者撰写的中国史,较新的如讲谈社之“中国史 系列,较旧的如宫崎市定之《中国史》等,都已经翻译出版,并且引起 中国读书界的热烈反应。我听说,引起热议的原因,主要是它们不同于 中国久已习惯的历史观念、叙述方式和评价立场,这让看惯或读厌了中 国历史教科书的读者感到了惊奇和兴味。那么,现在西洋学者撰写的这 一套哈佛版“帝制中国史”书系呢?人们常引苏东坡诗“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来比喻在不同角度,往往观察各有所得,如果说,日 本学者对中国史是“横看成岭”,那么,西洋学者编纂的这套哈佛版“帝 制中国历史”书系,是否也会“侧看成峰”,并且引发中国读者新的思考 和议论呢? 2016年7月18日初稿于上海 2016年8月14日修订于芝加哥 最后的中华帝属:大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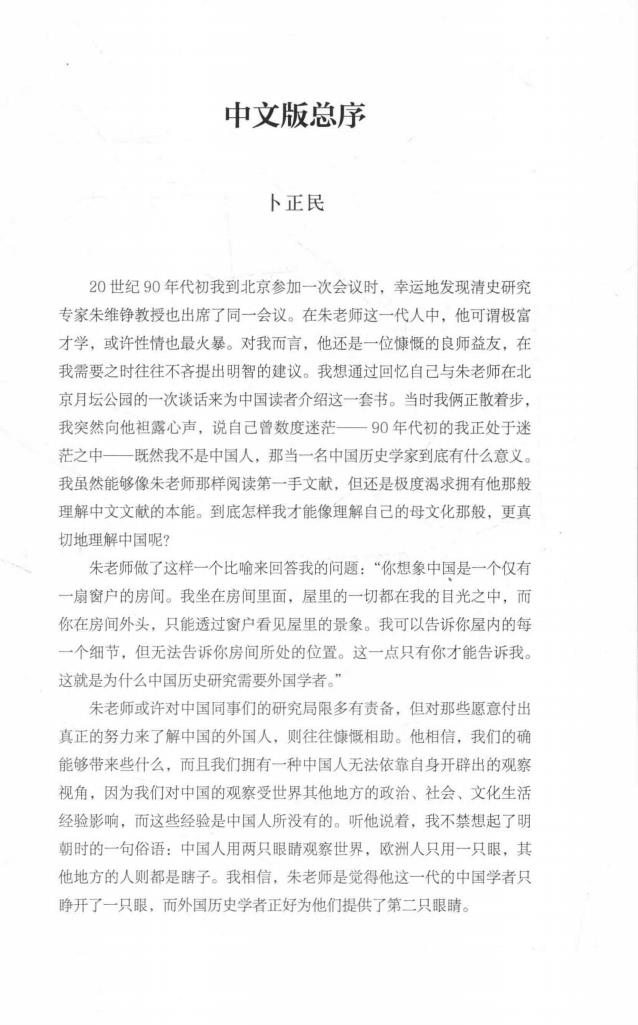
中文版总序 卜正民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北京参加一次会议时,幸运地发现清史研究 专家朱维铮教授也出席了同一会议。在朱老师这一代人中,他可谓极富 才学,或许性情也最火暴。对我而言,他还是一位慷概的良师益友,在 我需要之时往往不吝提出明智的建议。我想通过回忆自己与朱老师在北 京月坛公园的一次谈话来为中国读者介绍这一套书。当时我俩正散着步, 我突然向他担露心声,说自己曾数度迷茫一90年代初的我正处于迷 茫之中一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虽然能够像朱老师那样阋读第一手文献,但还是极度渴求拥有他那般 理解中文文献的本能。到底怎样我才能像理解自己的母文化那般,更真 切地理解中国呢? 朱老师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来回答我的问题:“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 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 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 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朱老师或许对中国同事们的研究局限多有责备,但对那些愿意付出 真正的努力来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则往往慷概相助。他相信,我们的确 能够带来些什么,而且我们拥有一种中国人无法依靠自身开辟出的观察 视角,因为我们对中国的观察受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 经验影响,而这些经验是中国人所没有的。听他说着,我不禁想起了明 朝时的一句俗语:中国人用两只眼睛观察世界,欧洲人只用一只眼,其 他地方的人则都是瞎子。我相信,朱老师是觉得他这一代的中国学者只 争开了一只眼,而外国历史学者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第二只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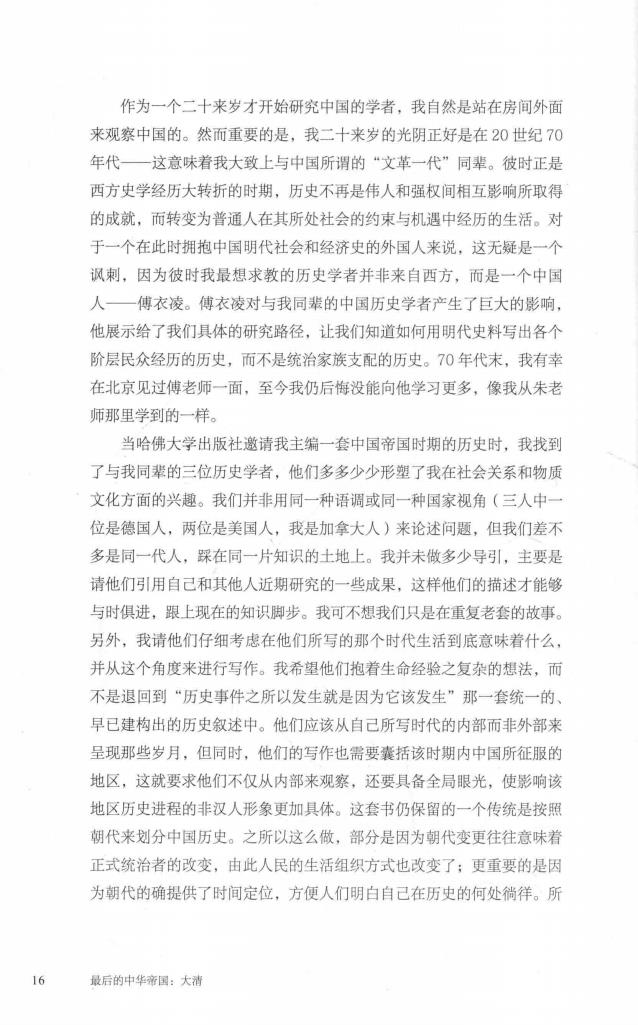
作为一个二十来岁才开始研究中国的学者,我自然是站在房间外面 来观察中国的。然而重要的是,我二十来岁的光阴正好是在20世纪70 年代一这意味着我大致上与中国所谓的“文革一代”同辈。彼时正是 西方史学经历大转折的时期,历史不再是伟人和强权间相互影响所取得 的成就,而转变为普通人在其所处社会的约束与机遇中经历的生活。对 于一个在此时拥抱中国明代社会和经济史的外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 讽刺,因为彼时我最想求教的历史学者并非来自西方,而是一个中国 人一傅衣凌。傅衣凌对与我同辈的中国历史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展示给了我们具体的研究路径,让我们知道如何用明代史料写出各个 阶层民众经历的历史,而不是统治家族支配的历史。70年代末,我有幸 在北京见过傅老师一面,至今我仍后悔没能向他学习更多,像我从朱老 师那里学到的一样。 当哈佛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一套中国帝国时期的历史时,我找到 了与我同辈的三位历史学者,他们多多少少形塑了我在社会关系和物质 文化方面的兴趣。我们并非用同一种语调或同一种国家视角(三人中一 位是德国人,两位是美国人,我是加拿大人)来论述问题,但我们差不 多是同一代人,踩在同一片知识的土地上。我并未做多少导引,主要是 请他们引用自己和其他人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样他们的描述才能够 与时俱进,跟上现在的知识脚步。我可不想我们只是在重复老套的故事。 另外,我请他们仔细考虑在他们所写的那个时代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 并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写作。我希望他们抱着生命经验之复杂的想法,而 不是退回到“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它该发生”那一套统一的 早已建构出的历史叙述中。他们应该从自己所写时代的内部而非外部来 呈现那些岁月,但同时,他们的写作也需要囊括该时期内中国所征服的 地区,这就要求他们不仅从内部来观察,还要具备全局眼光,使影响该 地区历史进程的非汉人形象更加具体。这套书仍保留的一个传统是按照 朝代来划分中国历史。之所以这么做,部分是因为朝代变更往往意味着 正式统治者的改变,由此人民的生活组织方式也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因 为朝代的确提供了时间定位,方便人们明白自己在历史的何处徜徉。所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