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通股东的利益保护研究 深交所博士后工作站 何卫东 流通股东的利益保护是当前证券市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前一段时期, 无论是某商业银行发行数额巨大的“可转债”,还是另一家高科技公司刚刚完成融资就大量 派发现金股利,都引起了流通股东的强烈反感。流通股东(包括机构和个人)在卖掉所持有 的股份“消极”抵抗的同时,还通过各种渠道呼吁监管部门进行政策干预,限制非流通股东 的“自利”行为。非流通股东则提出诸多理由为其行为进行辩护,声称上述行为是有利于公 司长期发展和取得竞争优势的必要之举,并非旨在“剥削”流通股东。上述争论引出了一个 关乎证券市场长期发展的关键问题一为什么需要保护流通股东的利益?本文的研究为回答 这一问题提供了探索性答案,这一答案的核心内容是:在当前的市场状况下,处于绝对“强 势”的非流通股东的“自利”行为导致证券市场未来的“不确定性”提高,流通股东所面临 的风险大大增加。由于流通股东处于绝对“劣势”地位,难以获得相应的风险“收益”,构 成证券市场基石之一的“股份流动性”被动摇。因此,削弱非流通股东的“强势”地位,限 制非流通股东的“自利”行为,保护流通股东的利益,有利于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 一、流通股东利益保护的理论分析 本文从分析拥有控制权的非流通股东“自利”行为对流通股东利益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入 手,探讨流通股东利益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结合具体的非流通股东“自利”行为,指出 提议中的流通股东利益保护政策在可操作性方面的待完善之处。 1.为什么保护流通股东的利益 归纳起来,强调证券监管部门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限制拥有控制权的非流通股东的 “自利”行为,保护流通股东利益的主要依据如下: 第一,非流通股东的财富数量与股价变动无关,非流通股东并不在意由于其机会主义的 “自利”行为而导致的二级市场股价下跌和流通股东利益受损。 第二,流通股东取得股份的成本高于非流通股东取得同等数量股份的成本。流通股东通 常是从二级市场购入股份,支付较高的价格。非流通股东或作为发起人直接持有股份,或通
流通股东的利益保护研究 深交所博士后工作站 何卫东 流通股东的利益保护是当前证券市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前一段时期, 无论是某商业银行发行数额巨大的“可转债”,还是另一家高科技公司刚刚完成融资就大量 派发现金股利,都引起了流通股东的强烈反感。流通股东(包括机构和个人)在卖掉所持有 的股份“消极”抵抗的同时,还通过各种渠道呼吁监管部门进行政策干预,限制非流通股东 的“自利”行为。非流通股东则提出诸多理由为其行为进行辩护,声称上述行为是有利于公 司长期发展和取得竞争优势的必要之举,并非旨在“剥削”流通股东。上述争论引出了一个 关乎证券市场长期发展的关键问题—为什么需要保护流通股东的利益?本文的研究为回答 这一问题提供了探索性答案,这一答案的核心内容是:在当前的市场状况下,处于绝对“强 势”的非流通股东的“自利”行为导致证券市场未来的“不确定性”提高,流通股东所面临 的风险大大增加。由于流通股东处于绝对“劣势”地位,难以获得相应的风险“收益”,构 成证券市场基石之一的“股份流动性”被动摇。因此,削弱非流通股东的“强势”地位,限 制非流通股东的“自利”行为,保护流通股东的利益,有利于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 一、流通股东利益保护的理论分析 本文从分析拥有控制权的非流通股东“自利”行为对流通股东利益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入 手,探讨流通股东利益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结合具体的非流通股东“自利”行为,指出 提议中的流通股东利益保护政策在可操作性方面的待完善之处。 1.为什么保护流通股东的利益 归纳起来,强调证券监管部门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限制拥有控制权的非流通股东的 “自利”行为,保护流通股东利益的主要依据如下: 第一,非流通股东的财富数量与股价变动无关,非流通股东并不在意由于其机会主义的 “自利”行为而导致的二级市场股价下跌和流通股东利益受损。 第二,流通股东取得股份的成本高于非流通股东取得同等数量股份的成本。流通股东通 常是从二级市场购入股份,支付较高的价格。非流通股东或作为发起人直接持有股份,或通 1

过“协议转让”等手段间接取得股份,不支付或仅支付远低于二级市场价格的较低价格。在 派发股息、红利时,尽管非流通股东与流通股东取得同等数量股份的成本不同,二者却享有 相同的收益。 第三,拥有控制权的非流通股东可以通过关联交易将优质资产从上市公司“输送”出去, 据为己有。当投资者意识到这些关联交易的“自利”性,从而降低对公司资产的出价时,流 通股东还要承担股价下跌带来的损失。 上述看法的不足之处在于仅仅看到了投资者持有流通股份的“额外”成本,却在一定 程度上忽略了投资者通过持有流通股份而获取的由股份流动性带来的“额外”收益。 首先,股份的价值是公司未来现金流的贴现值。投资者购买股份是购买公司的未来, 而非公司的过去和现在。投资者更关注的是股份的未来价值,即在未来以何种价格将股份卖 出,而不是当前以何种价格买入。换而言之,投资者关心的是“回报率”,而非成本。因此 简单比较购入流通股份和非流通股份的成本并没有多大意义。 其次,如果持有流通股份的投资者预期到拥有控制权的非流通股东的“自利”行为会 损害公司价值,他们可以通过卖出持有的股份而避免利益受损。 第三,非流通股东只有在掌握控制权的情况下才能肆无忌惮地将“自利”行为付诸实 施。随着股权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分散化,非流通股东的“自利”行为会遭遇到其他股东的抵 抗或监管部门的干预而难以实施。 最后,如果拥有控制权的非流通股东的“自利”行为导致公司陷入破产窘境,流通股 东可以在破产清算之前卖出股份而减少损失,非流通股东却要承担破产清算带来的全部损 失。 因此,对于投资者而言,持有流通股份的价值等于股份的真实价值和相应的“卖出”期 权(Put Option)价值之和。如果“卖出”期权价值较高,则持有流通股份并不会招致损失。 反之,则反是。换而言之,持有流通股份既具有额外“成本”,也具有额外“收益”,只有在 持有流通股份的额外“成本”明显高于额外“收益”,且这种差异将对资本市场的运行和投 资者的信心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时,从政策层面提出保护流通股东利益才有意义。 中国转轨经济体制下的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这一市场的显著特征是大部分上市 公司由国有企业“转制”而来。在“转制”过程中,一系列难以立即解决的棘手问题被搁置 2
过“协议转让”等手段间接取得股份,不支付或仅支付远低于二级市场价格的较低价格。在 派发股息、红利时,尽管非流通股东与流通股东取得同等数量股份的成本不同,二者却享有 相同的收益。 第三,拥有控制权的非流通股东可以通过关联交易将优质资产从上市公司“输送”出去, 据为已有。当投资者意识到这些关联交易的“自利”性,从而降低对公司资产的出价时,流 通股东还要承担股价下跌带来的损失。 上述看法的不足之处在于仅仅看到了投资者持有流通股份的“额外”成本,却在一定 程度上忽略了投资者通过持有流通股份而获取的由股份流动性带来的“额外”收益。 首先,股份的价值是公司未来现金流的贴现值。投资者购买股份是购买公司的未来, 而非公司的过去和现在。投资者更关注的是股份的未来价值,即在未来以何种价格将股份卖 出,而不是当前以何种价格买入。换而言之,投资者关心的是“回报率”,而非成本。因此 简单比较购入流通股份和非流通股份的成本并没有多大意义。 其次,如果持有流通股份的投资者预期到拥有控制权的非流通股东的“自利”行为会 损害公司价值,他们可以通过卖出持有的股份而避免利益受损。 第三,非流通股东只有在掌握控制权的情况下才能肆无忌惮地将“自利”行为付诸实 施。随着股权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分散化,非流通股东的“自利”行为会遭遇到其他股东的抵 抗或监管部门的干预而难以实施。 最后,如果拥有控制权的非流通股东的“自利”行为导致公司陷入破产窘境,流通股 东可以在破产清算之前卖出股份而减少损失,非流通股东却要承担破产清算带来的全部损 失。 因此,对于投资者而言,持有流通股份的价值等于股份的真实价值和相应的“卖出”期 权(Put Option)价值之和。如果“卖出”期权价值较高,则持有流通股份并不会招致损失。 反之,则反是。换而言之,持有流通股份既具有额外“成本”,也具有额外“收益”,只有在 持有流通股份的额外“成本”明显高于额外“收益”,且这种差异将对资本市场的运行和投 资者的信心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时,从政策层面提出保护流通股东利益才有意义。 中国转轨经济体制下的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这一市场的显著特征是大部分上市 公司由国有企业“转制”而来。在“转制”过程中,一系列难以立即解决的棘手问题被搁置 2

或淡化处理,如国有股份的流通问题、被“剥离”的不良资产和人员的处置问题等。随着证 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在国民经济中重要性的增强,这些问题的消极影响逐渐显露出来。在 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持有非流通股份的控股股东最大化自身利益时不可避免地会损及流通股 东的利益,当市场上大部分上市公司由非流通股东控制,迅速扩散的“学习”效应将会使流 通股东在整体上处于劣势和被“剥削”地位。 另外,中国的证券市场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市场机制的缺失和政策调节的滞后增大 了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投资者的信心和承受能力比较脆弱。在市场整体走高的情况 下,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或许能够容忍非流通股东的“自利”行为,因为其所持有的流通股份 的“卖出”期权价值较高。如果市场总体低迷,投资者对未来预期比较悲观的话,其所持有 的流通股份的“卖出”期权贬值,他们显然会对非流通股东的“自利”行为变得难以容忍。 因此,从维护证券市场基础的角度看,证券监管部门有必要提出相应的政策限制拥有控制权 的非流通股东的“自利”行为,保护流通股东的利益。 2.当前保护流通股东利益的政策建议 为了限制拥有控制权的非流通股东的“自利”行为,保护流通股东的利益,证券监管部 门和其他机构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政策建议,并向所有的证券市场参与者征求意见。这些政策 建议包括投票回避制度(当股东大会表决有关涉及流通股东利益的事项时,非流通股东回 避)、分类表决制度(当股东大会表决有关涉及流通股东利益的事项时,非流通股东与流通 股东分类表决,流通股东可以否决非流通股东的提案)和累积投票制度(当股东大会表决有 关涉及流通股东利益的事项时,以“累积投票制”取代“一股一票制”)。 从某种程度上讲,上述政策措施并未形成完整的框架结构,有待于进一步完善。首先, 就回避表决或分类表决制度而言,“涉及流通股东利益的事项”这一定义本身很模糊。由于 流通股东的利益与股价高度相关,任何影响股价变动的事项都会影响到流通股东的利益,而 上市公司又不可能对所有影响股价变动的事项进行回避表决或分类表决。例如,以关联交易 的形式转移公司优质资产是拥有控制权的非流通股东“剥削”流通股东的常用方式,但对关 联交易需要判断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关联交易,政策应该限制的是“异常”而非 “正常”的关联交易。 其次,拥有控制权的非流通股东推动上市公司管理层实施某项战略决策在短期内可能 会对股价产生消极影响,但在长期可能对公司竞争优势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如果实施类别
或淡化处理,如国有股份的流通问题、被“剥离”的不良资产和人员的处置问题等。随着证 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在国民经济中重要性的增强,这些问题的消极影响逐渐显露出来。在 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持有非流通股份的控股股东最大化自身利益时不可避免地会损及流通股 东的利益,当市场上大部分上市公司由非流通股东控制,迅速扩散的“学习”效应将会使流 通股东在整体上处于劣势和被“剥削”地位。 另外,中国的证券市场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市场机制的缺失和政策调节的滞后增大 了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投资者的信心和承受能力比较脆弱。在市场整体走高的情况 下,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或许能够容忍非流通股东的“自利”行为,因为其所持有的流通股份 的“卖出”期权价值较高。如果市场总体低迷,投资者对未来预期比较悲观的话,其所持有 的流通股份的“卖出”期权贬值,他们显然会对非流通股东的“自利”行为变得难以容忍。 因此,从维护证券市场基础的角度看,证券监管部门有必要提出相应的政策限制拥有控制权 的非流通股东的“自利”行为,保护流通股东的利益。 2.当前保护流通股东利益的政策建议 为了限制拥有控制权的非流通股东的“自利”行为,保护流通股东的利益,证券监管部 门和其他机构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政策建议,并向所有的证券市场参与者征求意见。这些政策 建议包括投票回避制度(当股东大会表决有关涉及流通股东利益的事项时,非流通股东回 避)、分类表决制度(当股东大会表决有关涉及流通股东利益的事项时,非流通股东与流通 股东分类表决,流通股东可以否决非流通股东的提案)和累积投票制度(当股东大会表决有 关涉及流通股东利益的事项时,以“累积投票制”取代“一股一票制”)。 从某种程度上讲,上述政策措施并未形成完整的框架结构,有待于进一步完善。首先, 就回避表决或分类表决制度而言,“涉及流通股东利益的事项”这一定义本身很模糊。由于 流通股东的利益与股价高度相关,任何影响股价变动的事项都会影响到流通股东的利益,而 上市公司又不可能对所有影响股价变动的事项进行回避表决或分类表决。例如,以关联交易 的形式转移公司优质资产是拥有控制权的非流通股东“剥削”流通股东的常用方式,但对关 联交易需要判断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关联交易,政策应该限制的是“异常”而非 “正常”的关联交易。 其次,拥有控制权的非流通股东推动上市公司管理层实施某项战略决策在短期内可能 会对股价产生消极影响,但在长期可能对公司竞争优势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如果实施类别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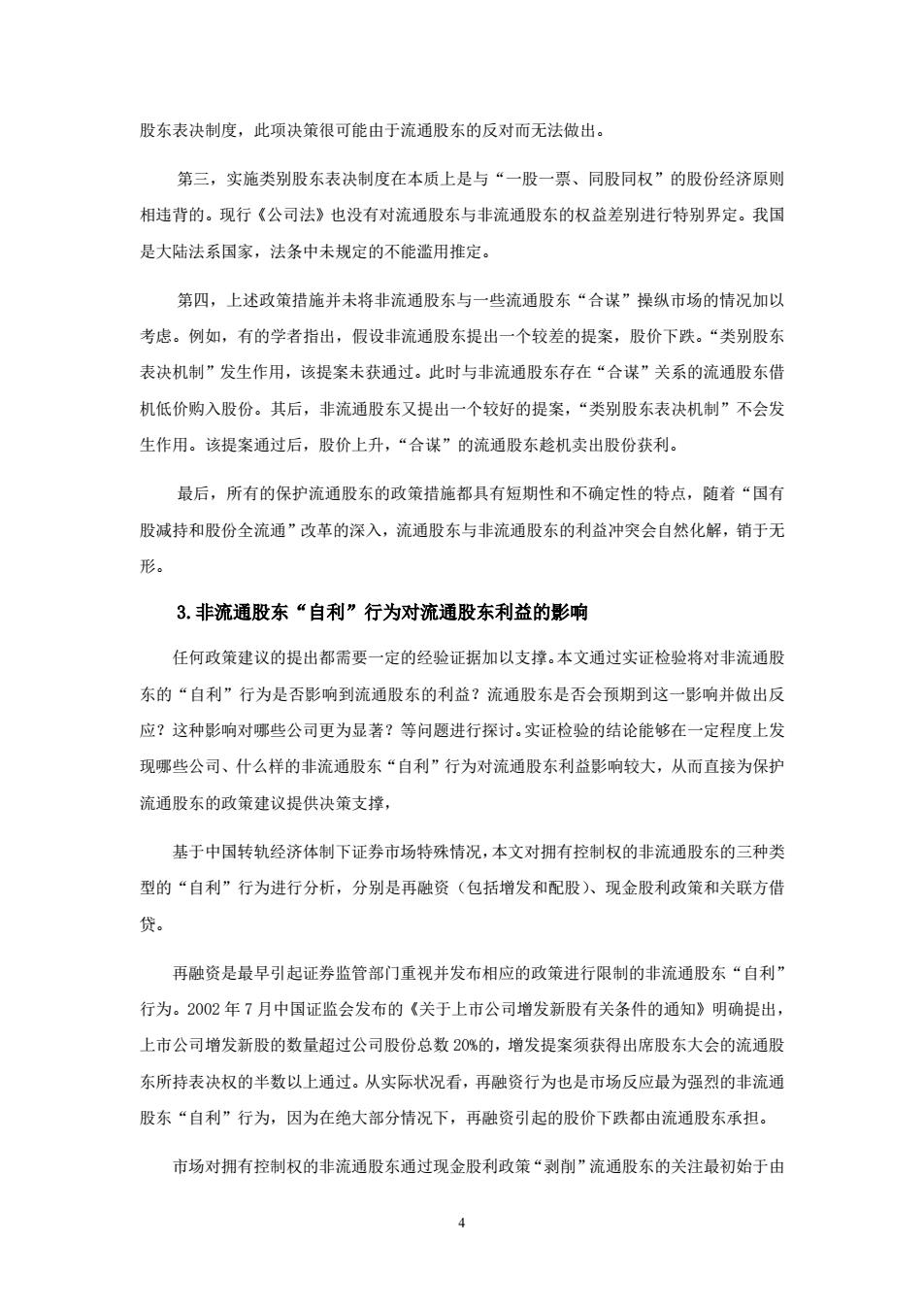
股东表决制度,此项决策很可能由于流通股东的反对而无法做出。 第三,实施类别股东表决制度在本质上是与“一股一票、同股同权”的股份经济原则 相违背的。现行《公司法》也没有对流通股东与非流通股东的权益差别进行特别界定。我国 是大陆法系国家,法条中未规定的不能滥用推定。 第四,上述政策措施并未将非流通股东与一些流通股东“合谋”操纵市场的情况加以 考虑。例如,有的学者指出,假设非流通股东提出一个较差的提案,股价下跌。“类别股东 表决机制”发生作用,该提案未获通过。此时与非流通股东存在“合谋”关系的流通股东借 机低价购入股份。其后,非流通股东又提出一个较好的提案,“类别股东表决机制”不会发 生作用。该提案通过后,股价上升,“合谋”的流通股东趁机卖出股份获利。 最后,所有的保护流通股东的政策措施都具有短期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随着“国有 股减持和股份全流通”改革的深入,流通股东与非流通股东的利益冲突会自然化解,销于无 形。 3.非流通股东“自利”行为对流通股东利益的影响 任何政策建议的提出都需要一定的经验证据加以支撑。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将对非流通股 东的“自利”行为是否影响到流通股东的利益?流通股东是否会预期到这一影响并做出反 应?这种影响对哪些公司更为显著?等问题进行探讨。实证检验的结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 现哪些公司、什么样的非流通股东“自利”行为对流通股东利益影响较大,从而直接为保护 流通股东的政策建议提供决策支撑, 基于中国转轨经济体制下证券市场特殊情况,本文对拥有控制权的非流通股东的三种类 型的“自利”行为进行分析,分别是再融资(包括增发和配股)、现金股利政策和关联方借 贷。 再融资是最早引起证券监管部门重视并发布相应的政策进行限制的非流通股东“自利” 行为。2002年7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增发新股有关条件的通知》明确提出, 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数量超过公司股份总数20%的,增发提案须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流通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从实际状况看,再融资行为也是市场反应最为强烈的非流通 股东“自利”行为,因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再融资引起的股价下跌都由流通股东承担。 市场对拥有控制权的非流通股东通过现金股利政策“剥削”流通股东的关注最初始于由
股东表决制度,此项决策很可能由于流通股东的反对而无法做出。 第三,实施类别股东表决制度在本质上是与“一股一票、同股同权”的股份经济原则 相违背的。现行《公司法》也没有对流通股东与非流通股东的权益差别进行特别界定。我国 是大陆法系国家,法条中未规定的不能滥用推定。 第四,上述政策措施并未将非流通股东与一些流通股东“合谋”操纵市场的情况加以 考虑。例如,有的学者指出,假设非流通股东提出一个较差的提案,股价下跌。“类别股东 表决机制”发生作用,该提案未获通过。此时与非流通股东存在“合谋”关系的流通股东借 机低价购入股份。其后,非流通股东又提出一个较好的提案,“类别股东表决机制”不会发 生作用。该提案通过后,股价上升,“合谋”的流通股东趁机卖出股份获利。 最后,所有的保护流通股东的政策措施都具有短期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随着“国有 股减持和股份全流通”改革的深入,流通股东与非流通股东的利益冲突会自然化解,销于无 形。 3.非流通股东“自利”行为对流通股东利益的影响 任何政策建议的提出都需要一定的经验证据加以支撑。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将对非流通股 东的“自利”行为是否影响到流通股东的利益?流通股东是否会预期到这一影响并做出反 应?这种影响对哪些公司更为显著?等问题进行探讨。实证检验的结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 现哪些公司、什么样的非流通股东“自利”行为对流通股东利益影响较大,从而直接为保护 流通股东的政策建议提供决策支撑, 基于中国转轨经济体制下证券市场特殊情况,本文对拥有控制权的非流通股东的三种类 型的“自利”行为进行分析,分别是再融资(包括增发和配股)、现金股利政策和关联方借 贷。 再融资是最早引起证券监管部门重视并发布相应的政策进行限制的非流通股东“自利” 行为。2002 年 7 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增发新股有关条件的通知》明确提出, 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数量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20%的,增发提案须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流通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从实际状况看,再融资行为也是市场反应最为强烈的非流通 股东“自利”行为,因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再融资引起的股价下跌都由流通股东承担。 市场对拥有控制权的非流通股东通过现金股利政策“剥削”流通股东的关注最初始于由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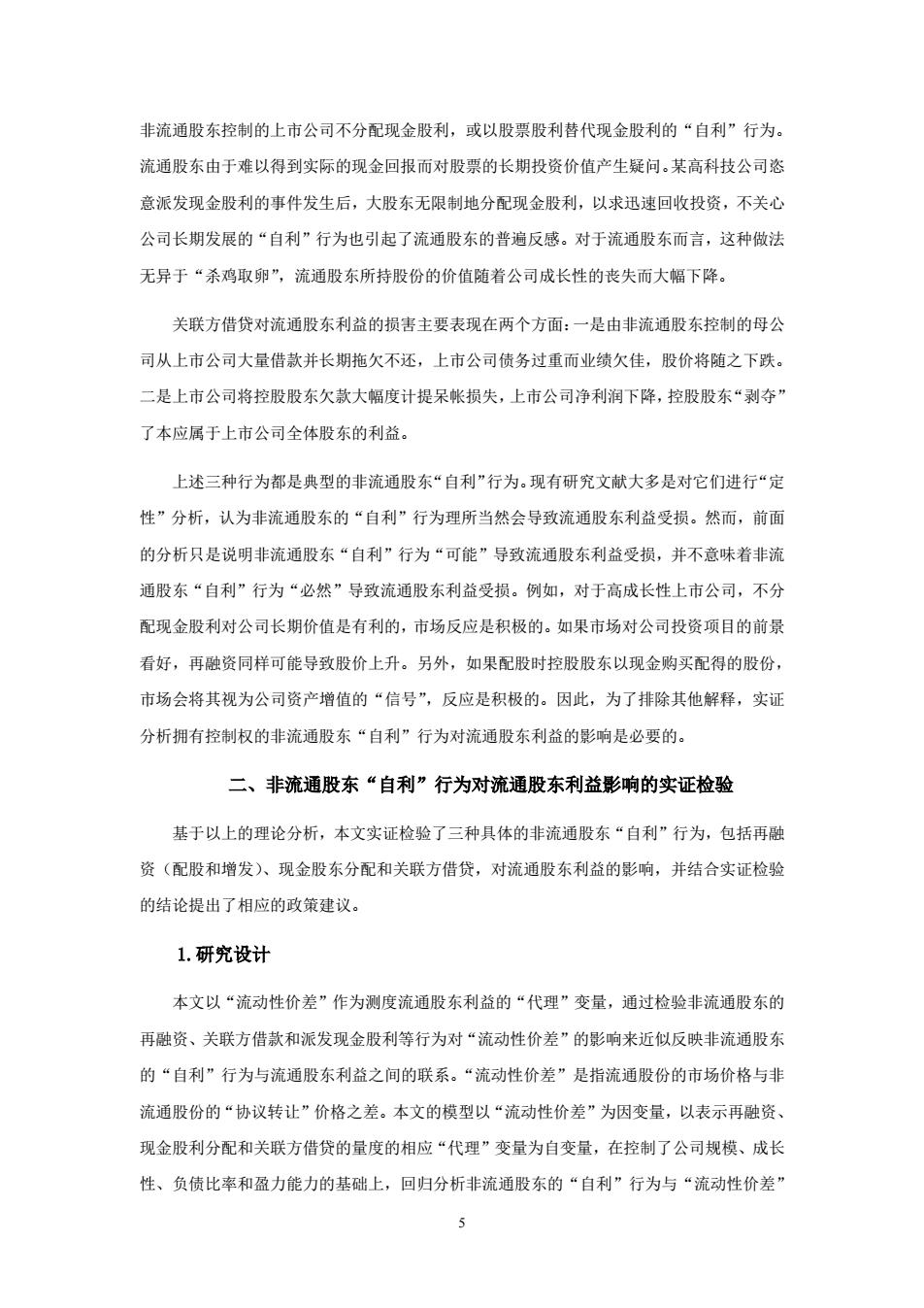
非流通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不分配现金股利,或以股票股利替代现金股利的“自利”行为。 流通股东由于难以得到实际的现金回报而对股票的长期投资价值产生疑问。某高科技公司恣 意派发现金股利的事件发生后,大股东无限制地分配现金股利,以求迅速回收投资,不关心 公司长期发展的“自利”行为也引起了流通股东的普遍反感。对于流通股东而言,这种做法 无异于“杀鸡取卵”,流通股东所持股份的价值随着公司成长性的丧失而大幅下降。 关联方借贷对流通股东利益的损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非流通股东控制的母公 司从上市公司大量借款并长期拖欠不还,上市公司债务过重而业绩欠佳,股价将随之下跌。 二是上市公司将控股股东欠款大幅度计提呆帐损失,上市公司净利润下降,控股股东“剥夺” 了本应属于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三种行为都是典型的非流通股东“自利”行为。现有研究文献大多是对它们进行“定 性”分析,认为非流通股东的“自利”行为理所当然会导致流通股东利益受损。然而,前面 的分析只是说明非流通股东“自利”行为“可能”导致流通股东利益受损,并不意味着非流 通股东“自利”行为“必然”导致流通股东利益受损。例如,对于高成长性上市公司,不分 配现金股利对公司长期价值是有利的,市场反应是积极的。如果市场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 看好,再融资同样可能导致股价上升。另外,如果配股时控股股东以现金购买配得的股份, 市场会将其视为公司资产增值的“信号”,反应是积极的。因此,为了排除其他解释,实证 分析拥有控制权的非流通股东“自利”行为对流通股东利益的影响是必要的。 二、非流通股东“自利”行为对流通股东利益影响的实证检验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本文实证检验了三种具体的非流通股东“自利”行为,包括再融 资(配股和增发)、现金股东分配和关联方借贷,对流通股东利益的影响,并结合实证检验 的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1.研究设计 本文以“流动性价差”作为测度流通股东利益的“代理”变量,通过检验非流通股东的 再融资、关联方借款和派发现金股利等行为对“流动性价差”的影响来近似反映非流通股东 的“自利”行为与流通股东利益之间的联系。“流动性价差”是指流通股份的市场价格与非 流通股份的“协议转让”价格之差。本文的模型以“流动性价差”为因变量,以表示再融资、 现金股利分配和关联方借贷的量度的相应“代理”变量为自变量,在控制了公司规模、成长 性、负债比率和盈力能力的基础上,回归分析非流通股东的“自利”行为与“流动性价差
非流通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不分配现金股利,或以股票股利替代现金股利的“自利”行为。 流通股东由于难以得到实际的现金回报而对股票的长期投资价值产生疑问。某高科技公司恣 意派发现金股利的事件发生后,大股东无限制地分配现金股利,以求迅速回收投资,不关心 公司长期发展的“自利”行为也引起了流通股东的普遍反感。对于流通股东而言,这种做法 无异于“杀鸡取卵”,流通股东所持股份的价值随着公司成长性的丧失而大幅下降。 关联方借贷对流通股东利益的损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非流通股东控制的母公 司从上市公司大量借款并长期拖欠不还,上市公司债务过重而业绩欠佳,股价将随之下跌。 二是上市公司将控股股东欠款大幅度计提呆帐损失,上市公司净利润下降,控股股东“剥夺” 了本应属于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三种行为都是典型的非流通股东“自利”行为。现有研究文献大多是对它们进行“定 性”分析,认为非流通股东的“自利”行为理所当然会导致流通股东利益受损。然而,前面 的分析只是说明非流通股东“自利”行为“可能”导致流通股东利益受损,并不意味着非流 通股东“自利”行为“必然”导致流通股东利益受损。例如,对于高成长性上市公司,不分 配现金股利对公司长期价值是有利的,市场反应是积极的。如果市场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 看好,再融资同样可能导致股价上升。另外,如果配股时控股股东以现金购买配得的股份, 市场会将其视为公司资产增值的“信号”,反应是积极的。因此,为了排除其他解释,实证 分析拥有控制权的非流通股东“自利”行为对流通股东利益的影响是必要的。 二、非流通股东“自利”行为对流通股东利益影响的实证检验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本文实证检验了三种具体的非流通股东“自利”行为,包括再融 资(配股和增发)、现金股东分配和关联方借贷,对流通股东利益的影响,并结合实证检验 的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1.研究设计 本文以“流动性价差”作为测度流通股东利益的“代理”变量,通过检验非流通股东的 再融资、关联方借款和派发现金股利等行为对“流动性价差”的影响来近似反映非流通股东 的“自利”行为与流通股东利益之间的联系。“流动性价差”是指流通股份的市场价格与非 流通股份的“协议转让”价格之差。本文的模型以“流动性价差”为因变量,以表示再融资、 现金股利分配和关联方借贷的量度的相应“代理”变量为自变量,在控制了公司规模、成长 性、负债比率和盈力能力的基础上,回归分析非流通股东的“自利”行为与“流动性价差”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