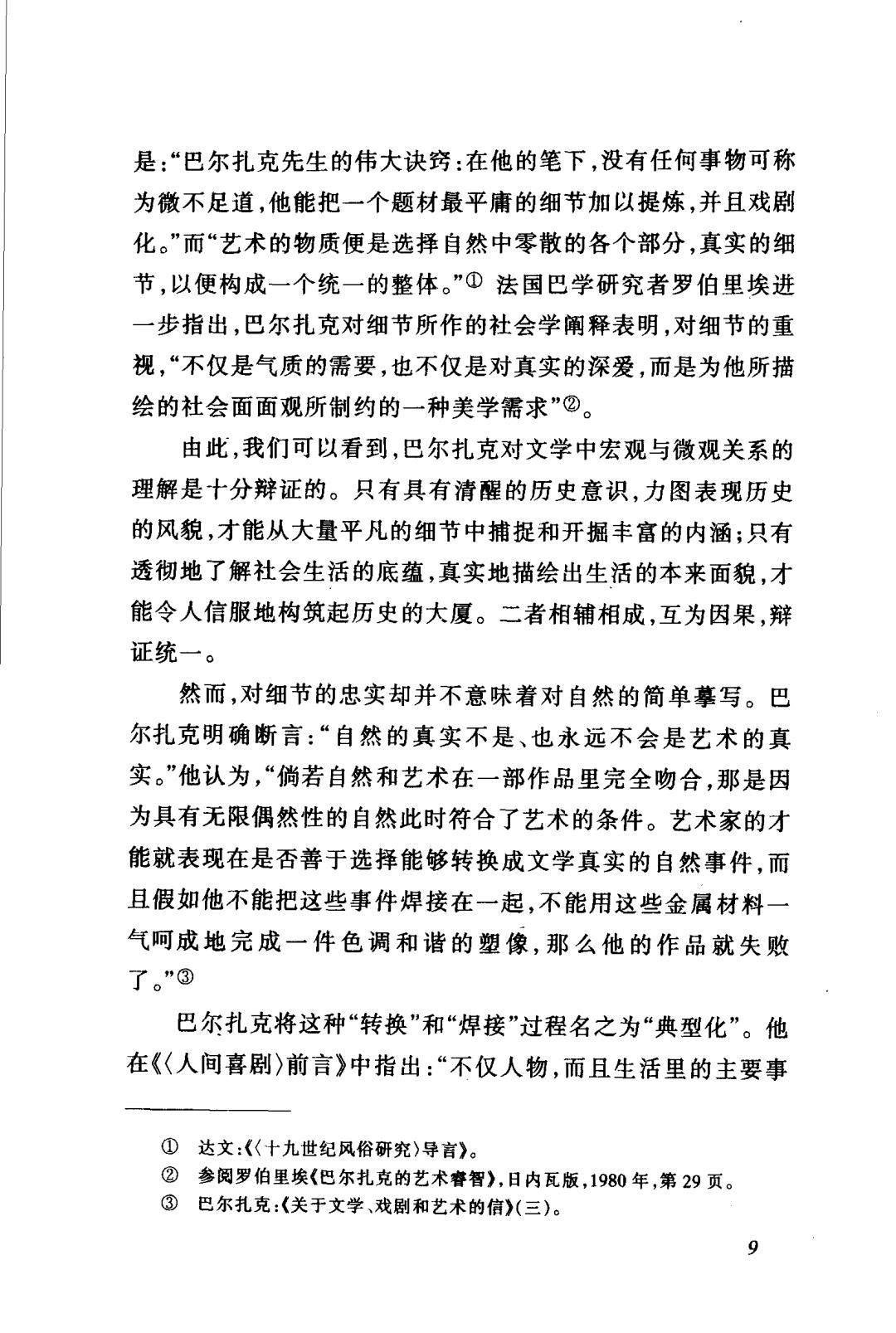
是:“巴尔扎克先生的伟大决窍:在他的笔下,没有任何事物可称 为微不足道,他能把一个题材最平庸的细节加以提炼,并且戏剧 化。”而“艺术的物质便是选择自然中零散的各个部分,真实的细 节,以便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①法国巴学研究者罗伯里埃进 一步指出,巴尔扎克对细节所作的社会学阐释表明,对细节的重 视,“不仅是气质的需要,也不仅是对真实的深爱,而是为他所描 绘的社会面面观所制约的一种美学需求”②。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巴尔扎克对文学中宏观与微观关系的 理解是十分辩证的。只有具有清醒的历史意识,力图表现历史 的风貌,才能从大量平凡的细节中捕捉和开掘丰富的内涵;只有 透彻地了解社会生活的底蕴,真实地描绘出生活的本来面貌,才 能令人信服地构筑起历史的大厦。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辩 证统一。 然而,对细节的忠实却并不意味着对自然的简单摹写。巴 尔扎克明确断言:“自然的真实不是、也永远不会是艺术的真 实。”他认为,“倘若自然和艺术在一部作品里完全吻合,那是因 为具有无限偶然性的自然此时符合了艺术的条件。艺术家的才 能就表现在是否善于选择能够转换成文学真实的自然事件,而 且假如他不能把这些事件焊接在一起,不能用这些金属材料一 气呵成地完成一件色调和谐的塑像,那么他的作品就失败 了。”③ 巴尔扎克将这种“转换”和“焊接”过程名之为“典型化”。他 在《(人间喜剧〉前言》中指出:“不仅人物,而且生活里的主要事 ① 达文:《〈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导言》。 ② 参阅罗伯里埃《巴尔扎克的艺术睿智》,日内瓦版,1980年,第29页。 ③ 巴尔扎克:《关于文学、戏剧和艺术的信》(三)。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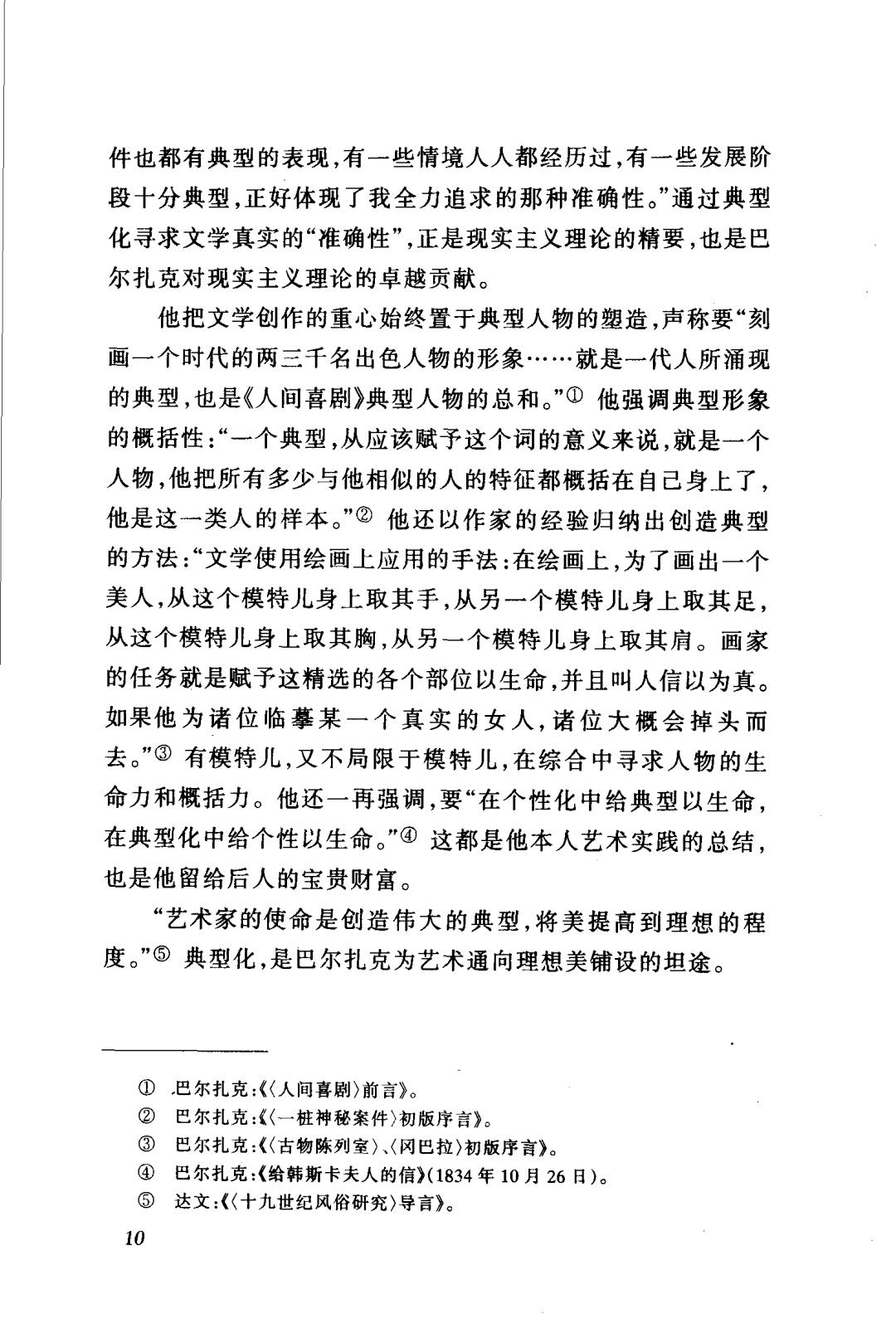
件也都有典型的表现,有一些情境人人都经历过,有一些发展阶 段十分典型,正好体现了我全力追求的那种准确性。”通过典型 化寻求文学真实的“准确性”,正是现实主义理论的精要,也是巴 尔扎克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卓越贡献。 他把文学创作的重心始终置于典型人物的塑造,声称要“刻 画一个时代的两三千名出色人物的形象…就是一代人所涌现 的典型,也是《人间喜剧》典型人物的总和。”①他强调典型形象 的概括性:“一个典型,从应该赋予这个词的意义来说,就是一个 人物,他把所有多少与他相似的人的特征都概括在自己身上了, 他是这一类人的样本。”②他还以作家的经验归纳出创造典型 的方法:“文学使用绘画上应用的手法:在绘画上,为了画出一个 美人,从这个模特儿身上取其手,从另一个模特儿身上取其足, 从这个模特儿身上取其胸,从另一个模特儿身上取其肩。画家 的任务就是赋予这精选的各个部位以生命,并且叫人信以为真。 如果他为诸位临摹某一个真实的女人,诸位大概会掉头而 去。”③有模特儿,又不局限于模特儿,在综合中寻求人物的生 命力和概括力。他还一再强调,要“在个性化中给典型以生命, 在典型化中给个性以生命。”④这都是他本人艺术实践的总结, 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艺术家的使命是创造伟大的典型,将美提高到理想的程 度。”⑤典型化,是巴尔扎克为艺术通向理想美铺设的坦途。 ①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 ②巴尔扎克:《(一桩神秘案件〉初版序言》。 ③巴尔扎克:《(古物陈列室〉、〈冈巴拉)初版序言》。 ④巴尔扎克:《给韩斯卡夫人的信》(1834年10月26日)。 ⑤达文:《(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导言》。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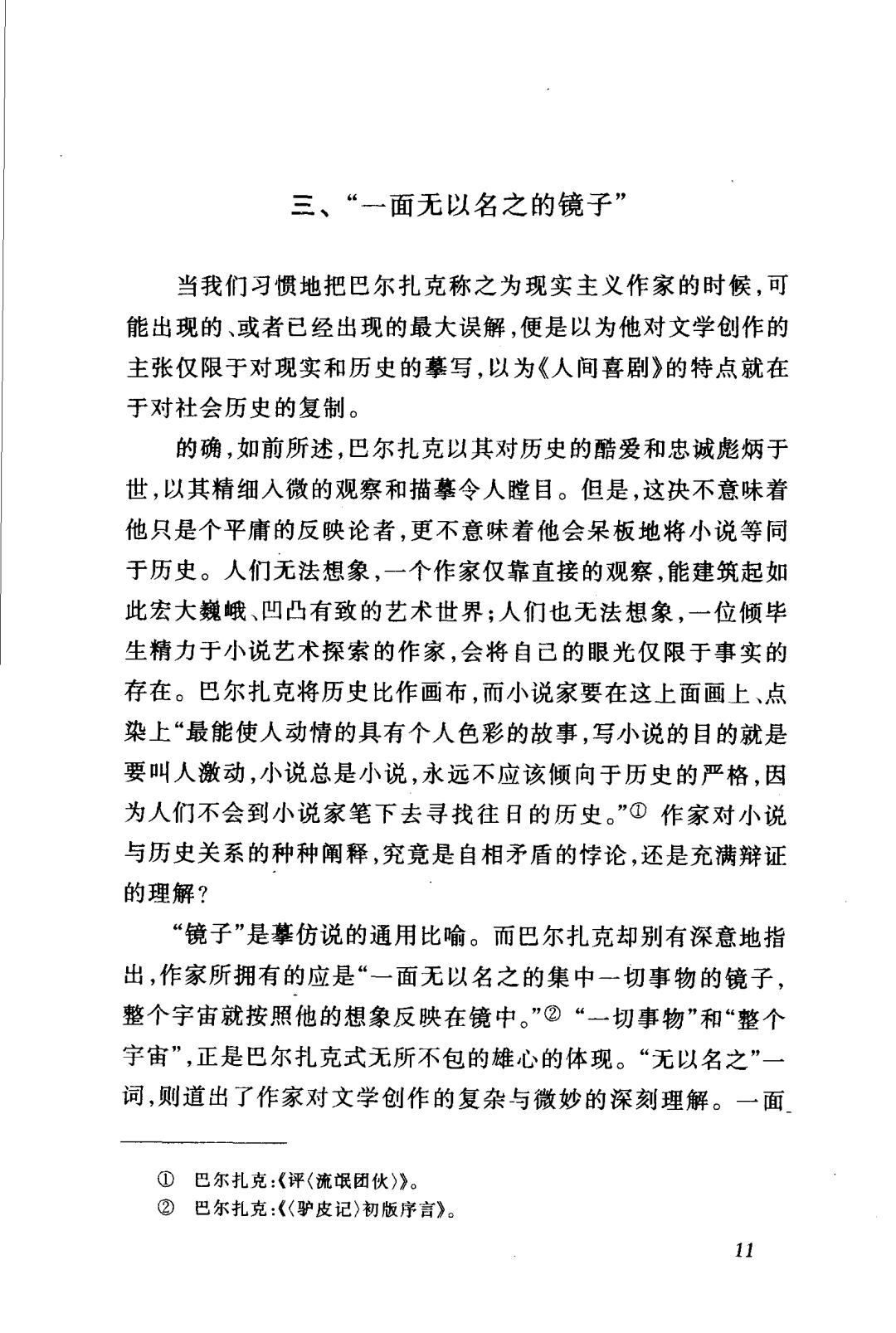
三、“一面无以名之的镜子” 当我们习惯地把巴尔扎克称之为现实主义作家的时候,可 能出现的、或者已经出现的最大误解,便是以为他对文学创作的 主张仅限于对现实和历史的摹写,以为《人间喜剧》的特点就在 于对社会历史的复制。 的确,如前所述,巴尔扎克以其对历史的酷爱和忠诚彪炳于 世,以其精细入微的观察和描摹令人膛目。但是,这决不意味着 他只是个平庸的反映论者,更不意味着他会呆板地将小说等同 于历史。人们无法想象,一个作家仅靠直接的观察,能建筑起如 此宏大巍峨、凹凸有致的艺术世界;人们也无法想象,一位倾毕 生精力于小说艺术探索的作家,会将自己的眼光仅限于事实的 存在。巴尔扎克将历史比作画布,而小说家要在这上面画上、点 染上“最能使人动情的具有个人色彩的故事,写小说的目的就是 要叫人激动,小说总是小说,永远不应该倾向于历史的严格,因 为人们不会到小说家笔下去寻找往日的历史。”①作家对小说 与历史关系的种种阐释,究竟是自相矛盾的悖论,还是充满辩证 的理解? “镜子”是摹仿说的通用比喻。而巴尔扎克却别有深意地指 出,作家所拥有的应是“一面无以名之的集中一切事物的镜子, 整个宇宙就按照他的想象反映在镜中。”②“一切事物”和“整个 宇宙”,正是巴尔扎克式无所不包的雄心的体现。“无以名之”一 词,则道出了作家对文学创作的复杂与微妙的深刻理解。一面 ① 巴尔扎克:《评〈流氓团伙)》。 ② 巴尔扎克:《(驴皮记〉初版序言》。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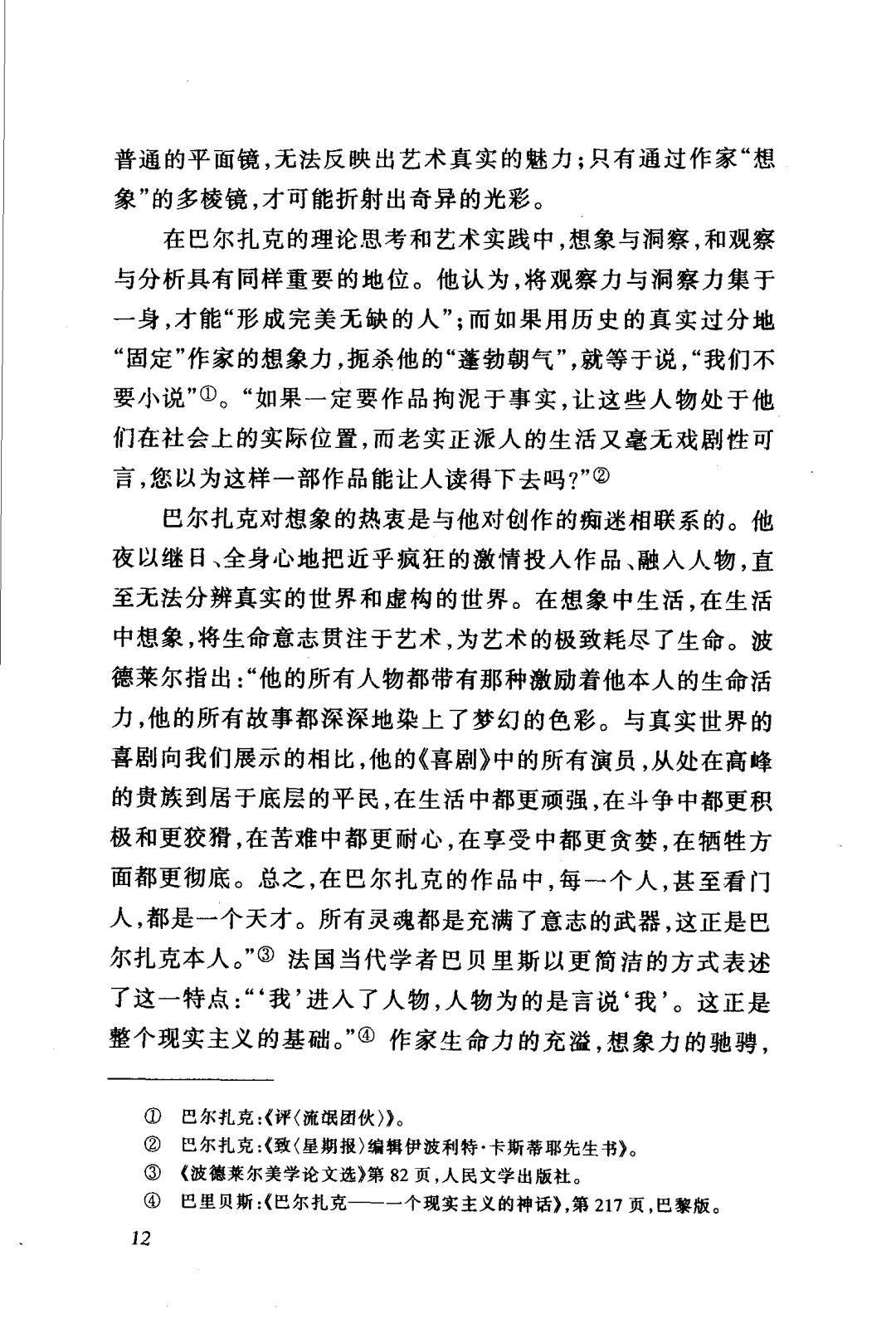
普通的平面镜,无法反映出艺术真实的魅力;只有通过作家“想 象”的多棱镜,才可能折射出奇异的光彩。 在巴尔扎克的理论思考和艺术实践中,想象与洞察,和观察 与分析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将观察力与洞察力集于 一身,才能“形成完美无缺的人”;而如果用历史的真实过分地 “固定”作家的想象力,扼杀他的“蓬勃朝气”,就等于说,“我们不 要小说”①。“如果一定要作品拘泥于事实,让这些人物处于他 们在社会上的实际位置,而老实正派人的生活又毫无戏剧性可 言,您以为这样一部作品能让人读得下去吗?”② 巴尔扎克对想象的热衷是与他对创作的痴迷相联系的。他 夜以继日、全身心地把近乎疯狂的激情投入作品、融入人物,直 至无法分辨真实的世界和虚构的世界。在想象中生活,在生活 中想象,将生命意志贯注于艺术,为艺术的极致耗尽了生命。波 德莱尔指出:“他的所有人物都带有那种激励着他本人的生命活 力,他的所有故事都深深地染上了梦幻的色彩。与真实世界的 喜剧向我们展示的相比,他的《喜剧》中的所有演员,从处在高峰 的贵族到居于底层的平民,在生活中都更顽强,在斗争中都更积 极和更狡猾,在苦难中都更耐心,在享受中都更贪婪,在牺牲方 面都更彻底。总之,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每一个人,甚至看门 人,都是一个天才。所有灵魂都是充满了意志的武器,这正是巴 尔扎克本人。”③法国当代学者巴贝里斯以更简洁的方式表述 了这一特点:“‘我’进入了人物,人物为的是言说‘我’。这正是 整个现实主义的基础。”④作家生命力的充溢,想象力的驰骋, ① 巴尔扎克:《评(流氓团伙)》。 ② 巴尔扎克:《致〈星期报〉编辑伊波利特·卡斯蒂耶先生书》。 ③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第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包 巴里贝斯:《巴尔扎克一一个现实主义的神话》,第217页,巴黎版。 12

使《人间喜剧》成为巴尔扎克对法国社会历史的独特解读 一既 是现实的,又是超验的;使《喜剧》中的艺术形象都律动着巴尔扎 克的激情、凝聚着巴尔扎克的执著一一既是真切的,又是奇特 的。 巴尔扎克对作家的“视力”作过带有几分神秘主义色彩的阐 释:“在真正具有哲学家气质的诗人或作家的头脑里,还发生一 种精神现象,这种精神现象无法解释,非同寻常,科学也难以阐 明。这是一种超人的视力,使他们能够在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 中看透真相。或者,更胜一筹,这是一种难以明言的强大力量, 能将他们送到他们应该去的或想要去的地方。”①这种“超人的 视力”,也就是巴尔扎克多次提到的“第二视力”。凭藉这种视 力,作家能透过纷繁的表象捕捉事物的真谛;凭藉这种视力,作 家能随心所欲地进入任何常人所难以企及的领域,甚至,还可以 在“公众看到是红色的地方”却看到了“蓝色”②。神奇的“视力” 说,显然是通向后世日渐风行的“通感论”和“直觉论”的。 十九世纪的评论家们也许还没有注意到巴尔扎克理论的超 前建树,但却已从他的创作中读出了作家与众不同的天赋。甚 至对巴尔扎克一贯颇为不恭的圣勃夫也承认:“他既想象,又观 察…巴尔扎克先生追求科学,但实际上,他特有的却是一种哲 学的直觉。夏斯勒先生说得好:‘人们没完没了反复说巴尔扎克 先生是位观察家、分析家;无论这个词的含意是更好些还是更坏 些,一他还是一位透视者(Voyant)。”③“通感”论者波德莱尔 则称:“我多次感到惊讶,伟大光荣的巴尔扎克被看作是一位观 ①巴尔扎克:《(驴皮记〉初版序言》。 ②参阅巴尔扎克《论艺术家》(二)。 ③转引自《巴尔扎克一一个现实主义的神话》,第241页。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