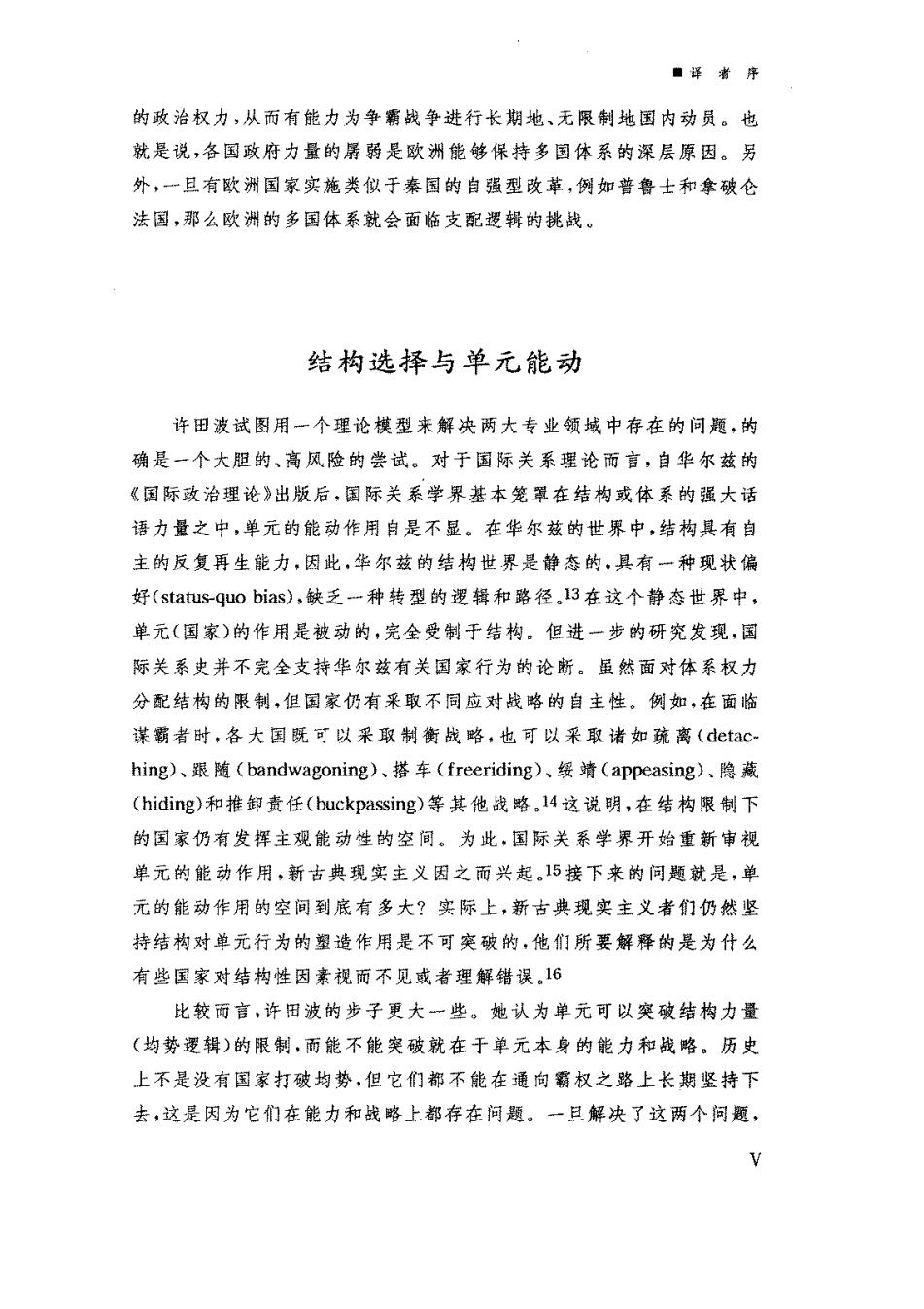
■译者痒 的政治权力,从而有能力为争霸战争进行长期地、无限制地国内动员。也 就是说,各国政府力量的孱弱是欧洲能够保持多国体系的深层原因。另 外,一~旦有欧洲国家实施类似于秦国的自强型改革,例如普鲁土和拿破仑 法国,那么欧洲的多国体系就会面临支配逻辑的挑哉。 结构选择与单元能动 许田波试图用一个理论模型来解决两大专业领域中存在的问题,的 确是一个大胆的、高风险的尝试。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而言,自华尔兹的 《国际政治理论》出版后,国际关系学界基本笼罩在结构或体系的强大话 语力量之中,单元的能动作用自是不显。在华尔兹的世界中,结构具有自 主的反复再生能力,因此,华尔兹的结构世界是静态的,具有一种现状偏 好(status-quo bias),缺乏-种转型的逻辑和路径,13在这个静态世界中, 单元(国家)的作用是被动的,完全受制于结构。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 际关系史并不完全支持华尔兹有关国家行为的论断。虽然面对体系权力 分配结构的限制,但国家仍有采取不同应对战略的自主性。例如,在面临 谋霸者时,各大国既可以采取制衡战路,也可以采取诸如疏离(detac hing)、跟随(bandwagoning)、搭车(freeriding)、绥请(appeasing)、隐藏 (hiding)和推卸责任(buckpassing)等其他战略。l4这说明,在结构限制下 的国家仍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为此,国际关系学界开始重新审视 单元的能动作用,新古典现实主义因之而兴起。15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单 元的能动作用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实际上,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们仍然坚 持结构对单元行为的塑造作用是不可突破的,他们所要解释的是为传么 有些国家对结构性因素视而不见或者理解错误。16 比较面言,许细波的步子更大一些。她认为单元可以突破结构力量 (均势逻辑)的限制,面能不能突破就在于单元本身的能力和战略。历史 上不是没有国家打破均势,但它们都不能在通向霸权之路上长期坚持下 去,这是因为它们在能力和战略上都存在问题。一旦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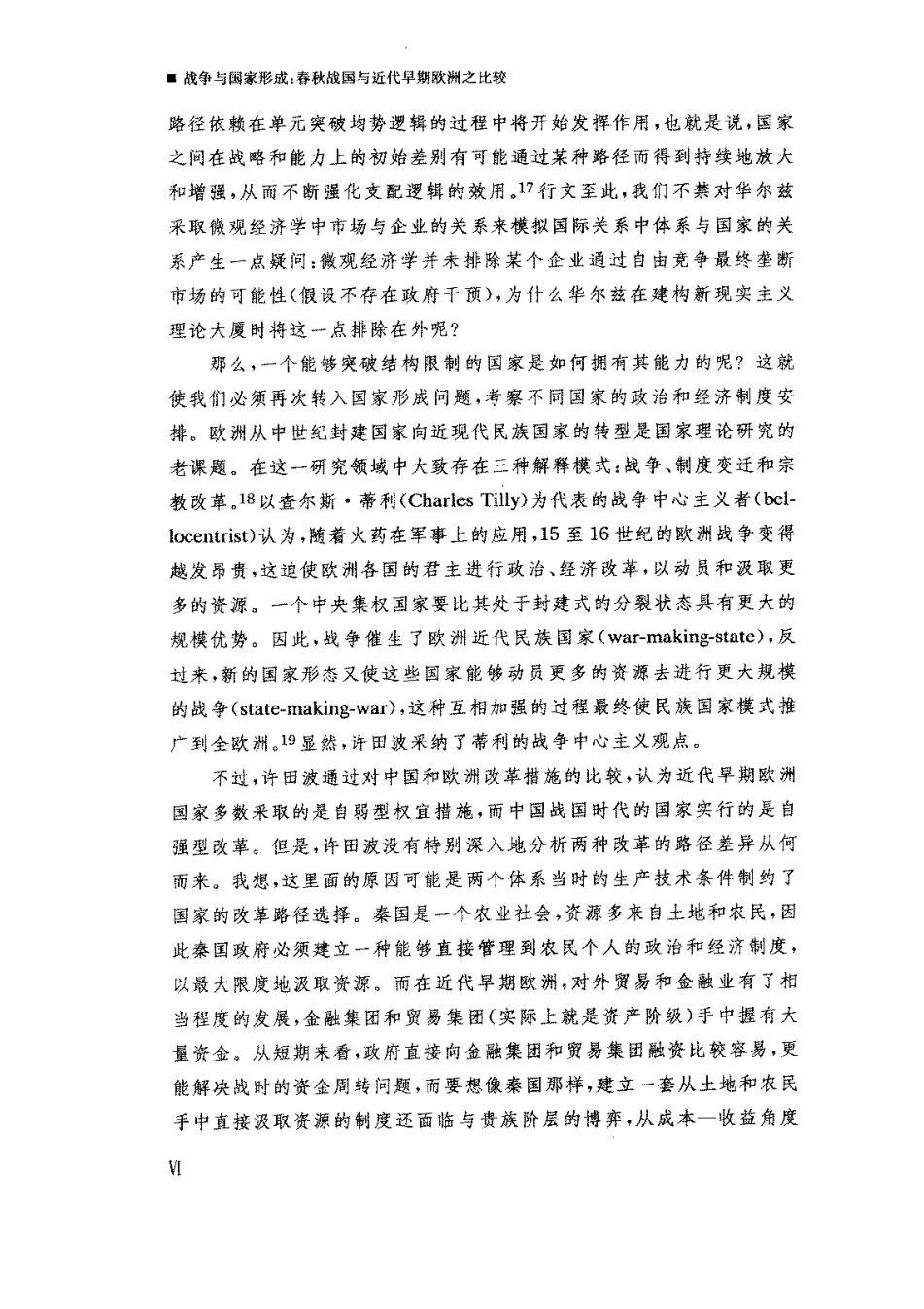
■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路径依赖在单元突破均势逻辑的过程中将开始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国家 之间在战略和能力上的初始差别有可能通过某种路径而得到持续地放大 和增强,从面不断强化支配逻辑的效用。17行文至此,我们不禁对华尔兹 采取微观经济学中市场与企业的关系来模拟国际关系中体系与国家的关 系产生一点疑问:微观经济学并未排除某个企业通过自由竞争最终垄断 市场的可能性(假设不存在政府千预),为什么华尔兹在建构新现实主义 理论大厦时将这一点排除在外呢? 那么,一个能够突破结构限制的国家是如何拥有其能力的呢?这就 使我们必须再次转入国家形成问题,考察不同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安 排。欧洲从中世纪封建国家向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是国家理论研究的 老课题。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大致存在三种解释模式:战争、制度变迁和宗 教改革。l8以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为代表的战争中心主义者(bel- ocentrist)认为,随着火药在军事上的应用,15至16世纪的欧洲战争变得 越发昂贵,这迫使欧洲各国的君主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以动员和汲取更 多的资源。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要比其处于封建式的分裂状态具有更大的 规模优势。因此,战争催生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war-making-state),反 过来,新的国家形态又使这些国家能够动员更多的资源去进行更大规模 的战争(state-making-war),这种互相加强的过程最终使民族国家模式推 广到全欧洲。19显然,许田波采纳了蒂利的战争中心主义观点。 不过,许田波通过对中国和欧洲改革措施的比较,认为近代早期欧洲 国家多数采取的是自弱型权宜措施,而中国战国时代的国家实行的是自 强型改革。但是,许田波没有特别深入地分析两种改革的路径差异从何 而来。我想,这里面的原因可能是两个体系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制约了 国家的改革路径选择。秦国是一个农业社会,资源多来自土地和农民,因 此秦国政府必须建立一种能够直接管理到农民个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以最大限度地汲取资源。而在近代早期欧洲,对外贸易和金融业有了相 当程度的发展,金融集团和贸易集团(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手中握有大 量资金。从短期来看,政府直接向金融集团和贸易集团融资比较容易,更 能解决战时的资金周转问题,而要想像秦国那样,建立一套从土地和农民 手中直接汲取资源的制度还面临与贵族阶层的博弈,从成本一收益角度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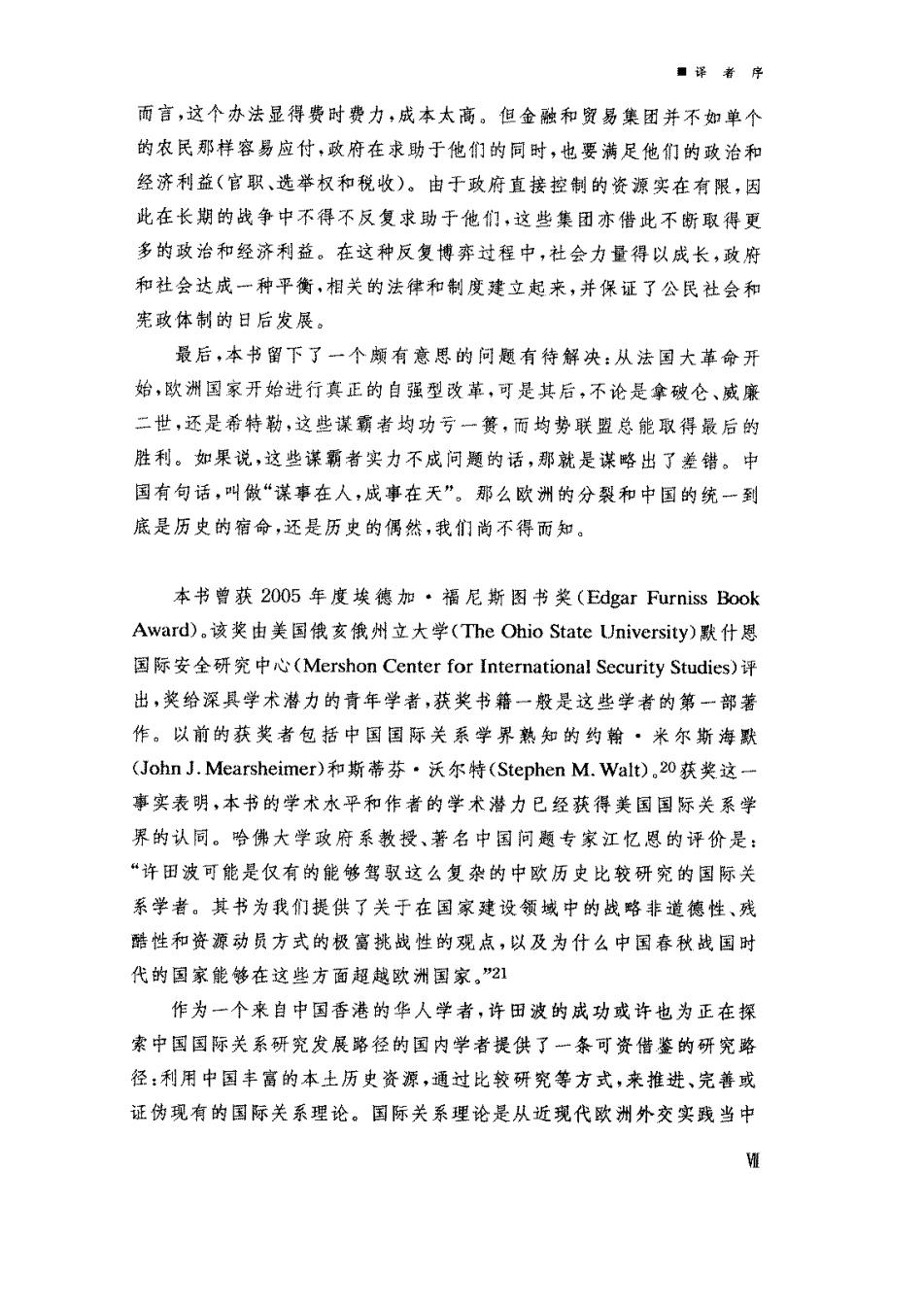
■译者序 面言,这个办法显得费时费力,成本太高。但金融和贸易集团并不知单个 的农民那样容易应付,政府在求助于他们的同时,也要满足他们的政治和 经济利益(官职、选举权和税收)。由于政府直接控制的资源实在有限,因 此在长期的战争中不得不反复求助于他们,这些集团亦借此不断取得更 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这种反复博奔过程中,社会力量得以成长,政府 和社会达戒一种平衡,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建立起来,并保证了公民社会和 宪政体制的日后发展。 最后,本书留下了一个频有意思的问题有待解决:从法国大革命开 始,欧洲国家开始进行真正的自强型改革,可是其后,不论是拿破仑、威廉 二世,还是希特勒,这些谋霸者均功亏一篑,而均势联盟总能取得最后的 胜利。如果说,这些谋霸者实力不成问题的话,那就是谋略出了差错。中 国有句话,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那么欧洲的分裂和中国的统一到 底是历史的宿命,还是历史的偶然,我们尚不得而知。 本书曾获2005年度埃德加·福尼斯图书奖(Edgar Furniss Book Award)。该奖由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默什恩 国际安全研究中心(Mersh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评 出,奖给深具学术潜力的青年学者,获奖书籍一般是这些学者的第一部著 作。以前的获奖者包括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熟知的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 J.Mearsheimer)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20获奖这- 事实表明,本书的学术水平和作者的学术潜力巴经获得美国国际关系学 界的认同。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江忆恩的评价是: “许田波可能是仅有的能够驾驭这么复杂的中欧历史比较研究的国际关 系学者。其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在国家建设领域中的战路非道德性、残 酷性和资源动员方式的极富挑战性的观点,以及为什么中国春秋战国时 代的国家能够在这些方面超越欧洲国家,”21 作为一个来自中国香港的华人学者,许田波的成功或许也为正在探 索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发展路径的国内学者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研究路 径:利用中国丰富的本土历史资源,通过比较研究等方式,来推进、完善或 证伪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从近现代欧洲外交实践当中 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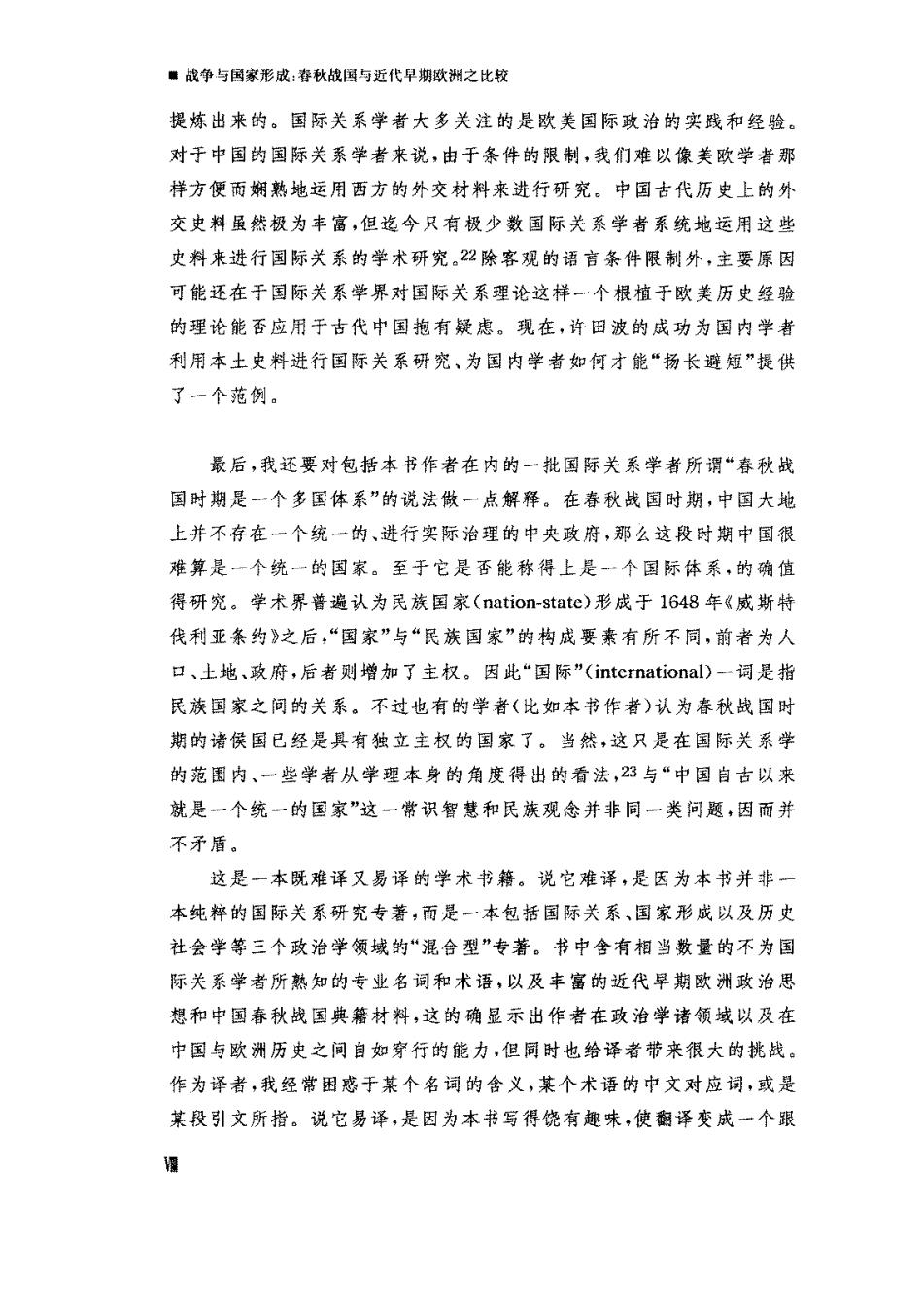
雕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提炼出来的。国际关系学者大多关注的是欧美国际政治的实践和经验。 对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来锐,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难以像美欧学者那 样方便而姻熟地运用西方的外交材料来进行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外 交史料虽然极为丰富,但迄今只有极少数国际关系学者系统地运用这些 史料来进行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2除客观的语言条件限制外,主要原因 可能还在于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关系理论这样一个根植于欧美历史经验 的理论能否应用于古代中国抱有疑虑。现在,许田波的成功为国内学者 利用本土史料进行国际关系研究、为国内学者知何才能“扬长避短”提供 了一个范例。 最后,我还要对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一批国际关系学者所谓“春秋战 国时期是一个多国体系”的说法做一点解释。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地 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进行实际治理的中央政府,那么这段时期中国很 难算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至于它是否能称得上是一个国际体系,的确值 得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形成于l648年《威斯特 伐利亚条约》之后,“国家”与“民族国家”的构成要素有所不同,前者为人 口、土地、政府,后者则增加了主权。因此“国际”(international)一词是指 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过也有的学者(比如本书作者)认为春秋战国时 期的诸侯国已经是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了。当然,这只是在国际关系学 的范围内、些学者从学理本身的角度得出的看法,3与“中国自古以来 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常识智慧和民族观念并非同一类问题,因而并 不矛盾。 这是一本既难译又易译的学术书籍。说它难译,是因为本书并非一 本纯粹的国际关系研究专著,面是一本包括国际关系、国家形成以及历史 社会学等三个政治学领域的“混合型”专著。书中含有相当数量的不为国 际关系学者所熟知的专业名词和术语,以及丰富的近代早期欧洲政治思 想和中国春秋战国典籍材料,这的确显示出作者在政治学诸领域以及在 中国与欧洲历史之间自如穿行的能力,但同时也给译者带来很大的挑战。 作为译者,我经常困惑于某个名词的含义,某个术语的中文对应词,或是 某段引文所指。说它易译,是因为本书写得饶有趣味◆使翻译变成一个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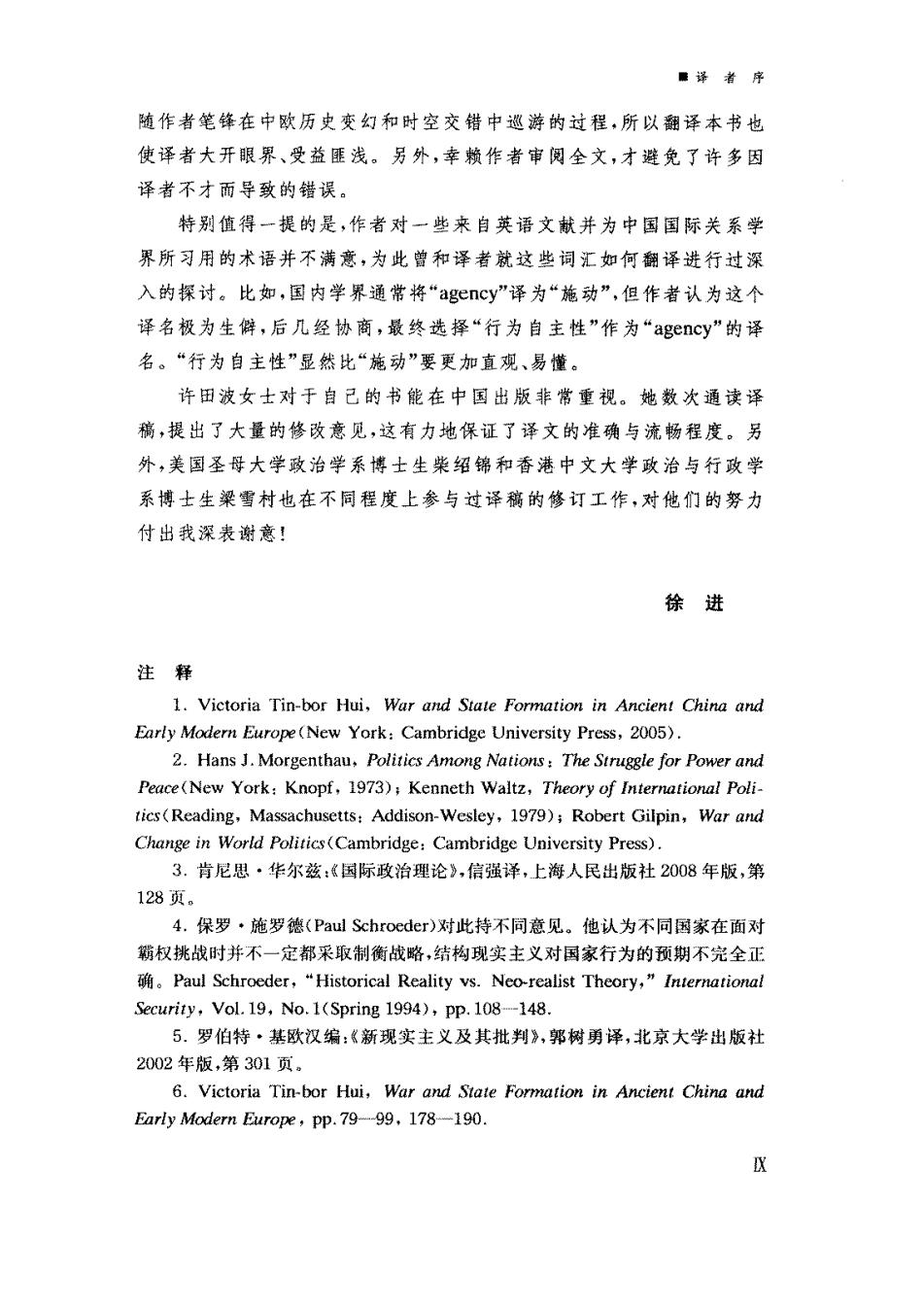
量译者序 随作者笔锋在中欧历史变幻和时空交错中巡游的过程,所以翻译本书也 使译者大开眼界、受益匪浅。另外,幸赖作者审阅全文,才避免了许多因 译者不才而导致的错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一些来自英语文献并为中国国际关系学 界所习用的术语并不满意,为此曾和译者就这些词汇如何翻译进行过深 入的探讨。比如,国内学界通常将“agency”译为“施动”,但作者认为这个 译名极为生僻,后几经协商,最终选择“行为自主性”作为“agency”的译 名。“行为自主性”显然比“施动”要更加直观、易懂。 许田波女士对于自己的书能在中国出版非常重视。她数次通读译 瘸,提出了大量的修改意见,这有力地保证了译文的准确与流畅程度。另 外,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柴绍锦和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 系博士生梁雪村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过译稿的修订工作,对他们的努力 付出我深表谢意! 徐进 注释 1.Victoria Tin-bor Hui,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2.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Knopf,1973);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 tics(Reading,Massachusetts:Addison-Wesley,1979);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 128页。 4.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不同国家在面对 霸权挑战时并不一定都采取制衡战略,结构现实主义对国家行为的预期不完全正 a确。Paul Schroeder,.“Historical Reality vs.Neo-realist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Spring 1994),pp.108-148. 5.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301页。 6.Victoria Tin-bor Hui,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pp.79-99,178-190.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