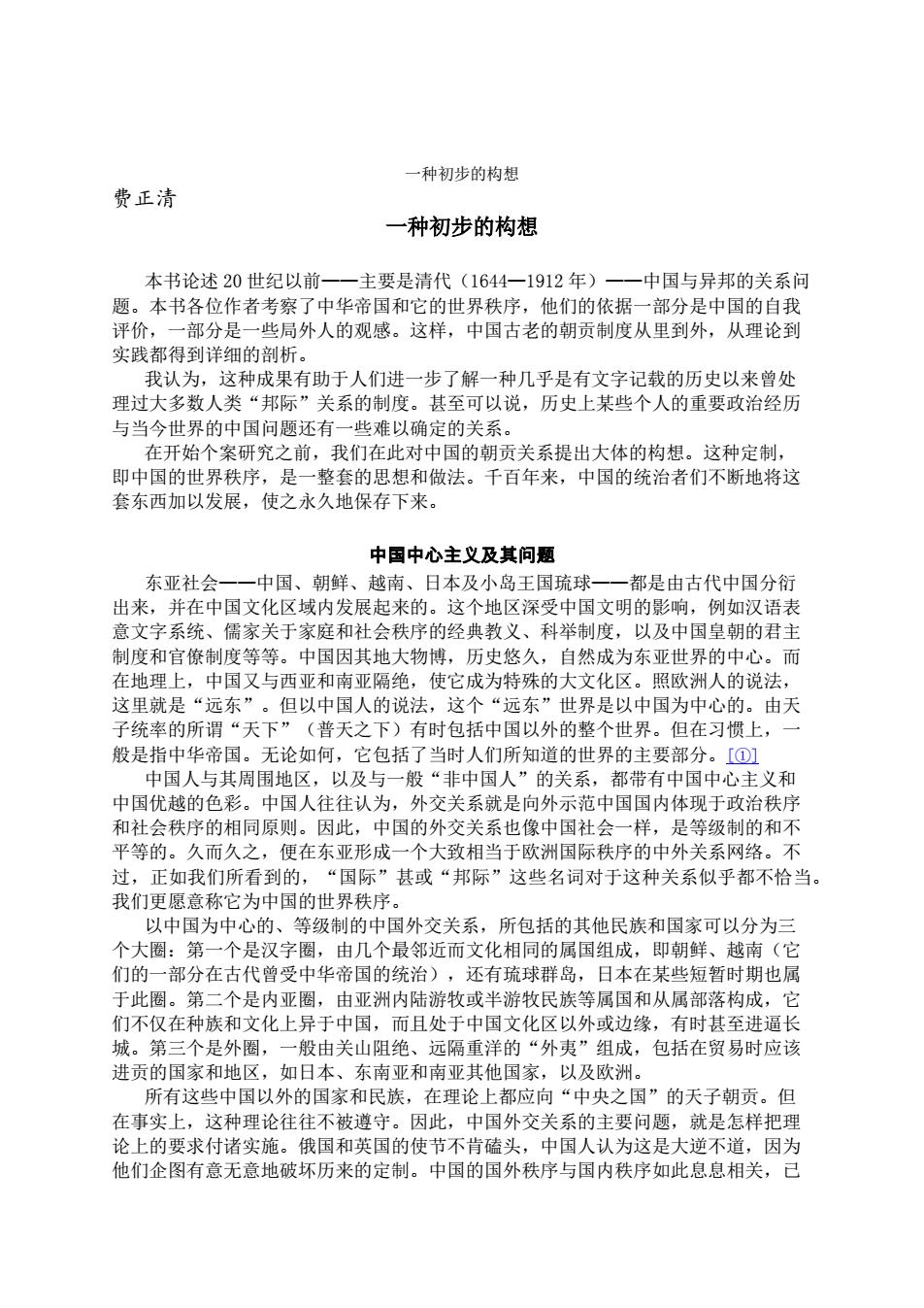
一种初步的构想 费正清 一种初步的构想 本书论述20世纪以前一一主要是清代(1644一1912年)一一中国与异邦的关系问 题。本书各位作者考察了中华帝国和它的世界秩序,他们的依据一分是中国的自我 评价,一部分是一些局外人的观感。这样,中国古老的朝贡制度从里到外,从理论到 实践都得到详细的剖析。 我认为,这种成果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一种几乎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曾处 理过大多数人类“邦际”关系的制度。甚至可以说,历史上某些个人的重要政治经历 与当今世界的中国问题还有一些难以确定的关系。 在开始个案研究之前,我们在此对中国的朝贡关系提出大体的构想。这种定制, 即中国的世界秩序,是一整套的思想和做法。千百年来,中国的统治者们不断地将这 套东西加以发展,使之永久地保存下来。 中国中心主义及其问题 东亚社会一一中国、朝鲜、越南、日本及小岛王国琉球一一都是由古代中国分衍 出来,并在中国文化区域内发展起来的。这个地区深受中国文明的影响,例如汉语表 意文字系统、儒家关于家庭和社会秩序的经典教义、科举制度,以及中国皇朝的君主 制度和官僚制度等等。中国因其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自然成为东亚世界的中心。而 在地理上,中国又与西亚和南亚隔绝,使它成为特殊的大文化区。照欧洲人的说法, 这里就是“远东”。但以中国人的说法,这个“远东”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由天 子统率的所谓“天下”(普天之下)有时包括中国以外的整个世界。但在习惯上, 般是指中华帝国。无论如何,它包括了当时人们所知道的世界的主要部分。[①] 中国人与其周围地区,以及与一般“非中国人”的关系,都带有中国中心主义和 中国优越的色彩。中国人往往认为,外交关系就是向外示范中国国内体现于政治秩序 和社会秩序的相同原则。因此,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像中国社会一样,是等级制的和不 平等的。久而久之,便在东亚形成一个大致相当于欧洲国际秩序的中外关系网络。不 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际”甚或“邦际”这些名词对于这种关系似乎都不恰当。 我们更愿意称它为中国的世界秩序。 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的中国外交关系,所包括的其他民族和国家可以分为三 个大圈:第一个是汉字圈,由几个最邻近而文化相同的属国组成,即朝鲜、越南(它 们的一部分在古代曾受中华帝国的统治),还有琉球群岛,日本在某些短暂时期也属 于此圈。第二个是内亚圈,由亚洲内陆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等属国和从属部落构成,它 们不仅在种族和文化上异于中国,而且处于中国文化区以外或边缘,有时甚至进逼长 城。第三个是外圈,一般由关山阻绝、远隔重洋的“外夷”组成,包括在贸易时应该 进贡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东南亚和南亚其他国家,以及欧洲。 所有这些中国以外的国家和民族,在理论上都应向“中央之国”的天子朝贡。但 在事实上,这种理论往往不被遵守。因此,中国外交关系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把理 论上的要求付诸实施。俄国和英国的使节不肯磕头,中国人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因为 他们企图有意无意地破坏历来的定制。中国的国外秩序与国内秩序如此息息相关,己
一种初步的构想 费正清 一种初步的构想 本书论述 20 世纪以前——主要是清代(1644—1912 年)——中国与异邦的关系问 题。本书各位作者考察了中华帝国和它的世界秩序,他们的依据一部分是中国的自我 评价,一部分是一些局外人的观感。这样,中国古老的朝贡制度从里到外,从理论到 实践都得到详细的剖析。 我认为,这种成果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一种几乎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曾处 理过大多数人类“邦际”关系的制度。甚至可以说,历史上某些个人的重要政治经历 与当今世界的中国问题还有一些难以确定的关系。 在开始个案研究之前,我们在此对中国的朝贡关系提出大体的构想。这种定制, 即中国的世界秩序,是一整套的思想和做法。千百年来,中国的统治者们不断地将这 套东西加以发展,使之永久地保存下来。 中国中心主义及其问题 东亚社会——中国、朝鲜、越南、日本及小岛王国琉球——都是由古代中国分衍 出来,并在中国文化区域内发展起来的。这个地区深受中国文明的影响,例如汉语表 意文字系统、儒家关于家庭和社会秩序的经典教义、科举制度,以及中国皇朝的君主 制度和官僚制度等等。中国因其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自然成为东亚世界的中心。而 在地理上,中国又与西亚和南亚隔绝,使它成为特殊的大文化区。照欧洲人的说法, 这里就是“远东”。但以中国人的说法,这个“远东”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由天 子统率的所谓“天下”(普天之下)有时包括中国以外的整个世界。但在习惯上,一 般是指中华帝国。无论如何,它包括了当时人们所知道的世界的主要部分。[①] 中国人与其周围地区,以及与一般“非中国人”的关系,都带有中国中心主义和 中国优越的色彩。中国人往往认为,外交关系就是向外示范中国国内体现于政治秩序 和社会秩序的相同原则。因此,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像中国社会一样,是等级制的和不 平等的。久而久之,便在东亚形成一个大致相当于欧洲国际秩序的中外关系网络。不 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际”甚或“邦际”这些名词对于这种关系似乎都不恰当。 我们更愿意称它为中国的世界秩序。 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的中国外交关系,所包括的其他民族和国家可以分为三 个大圈:第一个是汉字圈,由几个最邻近而文化相同的属国组成,即朝鲜、越南(它 们的一部分在古代曾受中华帝国的统治),还有琉球群岛,日本在某些短暂时期也属 于此圈。第二个是内亚圈,由亚洲内陆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等属国和从属部落构成,它 们不仅在种族和文化上异于中国,而且处于中国文化区以外或边缘,有时甚至进逼长 城。第三个是外圈,一般由关山阻绝、远隔重洋的“外夷”组成,包括在贸易时应该 进贡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东南亚和南亚其他国家,以及欧洲。 所有这些中国以外的国家和民族,在理论上都应向“中央之国”的天子朝贡。但 在事实上,这种理论往往不被遵守。因此,中国外交关系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把理 论上的要求付诸实施。俄国和英国的使节不肯磕头,中国人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因为 他们企图有意无意地破坏历来的定制。中国的国外秩序与国内秩序如此息息相关,已

经到了唇亡齿寒、休戚与共的地步:如果对外不能对付蛮夷使之臣服,国内的叛乱就 易于发生。中国的历代王朝,大都是在“内乱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垮台的。所以,每 个政权都孜孜以求,务使对外关系能在事实上同理论相符,借此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 权。 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有个根本缺陷,那就是它同中国文化区的范围没有 密切关联。构成汉字圈的异族国家,是由汉字和儒家学说之类的文化纽带与中国连在 一起的。而内亚圈则由显然非中国文化的民族组成(其中包括满、蒙、回、藏等民 族),尽管他们在社会或文化方面都与中国大不相同。例如,他们的文字是用字母的, 经济大部分是游牧式的,政治组织主要是部落式的。然而,他们一直未被排除在中国 的世界秩序之外,因为这些来自内亚草原的能骑善射的民族,在使用火器之前的漫长 的马战时代,是东亚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就是说格于地理形势,以中国文化为根据 的天子至尊的理论,不得不向亚洲内陆游牧民族的战斗力妥协。就战略上说,“中华 帝国”必须是实际的大陆性“东亚帝国”,从帕米尔高原直至釜山,这些地方都是中 国每个大王朝力图控制的。在这个帝国之内,内亚的异族部落源源不断地提供冲锋陷 阵的突击队,成为政府具有决定性的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比 内亚民族优越,可以时时借此控制他们,但这种手段有时也会失效。于是从汉朝至清 朝的2000年间,内亚的异族战士在中华帝国的战争和政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蛮族”入侵终至元(1279一1368年)、清两代达于顶点。[② 这些异族王朝一旦在北京奠基,便采取许多新的措施。但整个来说,他们仍用中 国的传统治理中国,并在很大程度上运用它来处理对外关系。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 是通过经常使用中国中心主义的词汇来保持中国中心主义的理论,这在朝贡制度的各 个方面都表现得很明显。事实上,到了明清两代,朝贡的名称还部分地保持着。如果 外国要同中国接触,就应当朝贡,有时还可能被强制这样做。外国必须把与中国的贸 易视为皇帝给予他国统治者的一种恩赐,外国统治者必须遣使进京,举行朝贡仪式。 只有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中,经济关系才能得到正式认可。到了后来,即使外国人不遵 行朝贡仪式,中国在文字记载中仍对外国人使用朝贡词汇。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勋 爵以专使身份访华。他只对乾隆皇帝行了屈膝礼,但仍被记载为磕头伏拜。这类例子 并非绝无仅有。 因此,中国大陆和台湾继承了这一套历史先例和成为定制的立场。这套东西与欧 洲那种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传统大相径庭。近代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难 于适应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部分是由中国的世界秩序这个重要传统造成的。 这种传统不只是历史趣谈,它还累及当今中国的政治思想。 要研究这个课题,当然要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其他方面,从中国人和非 中国人的观点出发,全面考虑2000年间中国与它所知道的所有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 但是,要充分探讨如此宽泛的一个领域,只能依靠迄今为止只有极少数学者能够写出 来的优秀论文:最好的办法是像本书大部分论文那样,对最近几个世纪,特别是清代 (1644一1912年)的具体事例进行个案研究。 一些假设:中国的世界秩序的源流 本书用现代语言评估近代初期中华帝国外交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分析了由中 国和与之接触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组成的国际秩序的结构和功能。在19世纪中叶西方列 强入侵东亚之前,这种国际秩序十分兴盛。直到1911年,它还像夕阳残照,余晖未尽
经到了唇亡齿寒、休戚与共的地步;如果对外不能对付蛮夷使之臣服,国内的叛乱就 易于发生。中国的历代王朝,大都是在“内乱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垮台的。所以,每 个政权都孜孜以求,务使对外关系能在事实上同理论相符,借此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 权。 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有个根本缺陷,那就是它同中国文化区的范围没有 密切关联。构成汉字圈的异族国家,是由汉字和儒家学说之类的文化纽带与中国连在 一起的。而内亚圈则由显然非中国文化的民族组成(其中包括满、蒙、回、藏等民 族),尽管他们在社会或文化方面都与中国大不相同。例如,他们的文字是用字母的, 经济大部分是游牧式的,政治组织主要是部落式的。然而,他们一直未被排除在中国 的世界秩序之外,因为这些来自内亚草原的能骑善射的民族,在使用火器之前的漫长 的马战时代,是东亚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就是说格于地理形势,以中国文化为根据 的天子至尊的理论,不得不向亚洲内陆游牧民族的战斗力妥协。就战略上说,“中华 帝国”必须是实际的大陆性“东亚帝国”,从帕米尔高原直至釜山,这些地方都是中 国每个大王朝力图控制的。在这个帝国之内,内亚的异族部落源源不断地提供冲锋陷 阵的突击队,成为政府具有决定性的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比 内亚民族优越,可以时时借此控制他们,但这种手段有时也会失效。于是从汉朝至清 朝的 2000 年间,内亚的异族战士在中华帝国的战争和政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蛮族”入侵终至元(1279—1368 年)、清两代达于顶点。[②] 这些异族王朝一旦在北京奠基,便采取许多新的措施。但整个来说,他们仍用中 国的传统治理中国,并在很大程度上运用它来处理对外关系。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 是通过经常使用中国中心主义的词汇来保持中国中心主义的理论,这在朝贡制度的各 个方面都表现得很明显。事实上,到了明清两代,朝贡的名称还部分地保持着。如果 外国要同中国接触,就应当朝贡,有时还可能被强制这样做。外国必须把与中国的贸 易视为皇帝给予他国统治者的一种恩赐,外国统治者必须遣使进京,举行朝贡仪式。 只有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中,经济关系才能得到正式认可。到了后来,即使外国人不遵 行朝贡仪式,中国在文字记载中仍对外国人使用朝贡词汇。1793 年,英国马戛尔尼勋 爵以专使身份访华。他只对乾隆皇帝行了屈膝礼,但仍被记载为磕头伏拜。这类例子 并非绝无仅有。 因此,中国大陆和台湾继承了这一套历史先例和成为定制的立场。这套东西与欧 洲那种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传统大相径庭。近代中国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难 于适应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部分是由中国的世界秩序这个重要传统造成的。 这种传统不只是历史趣谈,它还累及当今中国的政治思想。 要研究这个课题,当然要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其他方面,从中国人和非 中国人的观点出发,全面考虑 2000 年间中国与它所知道的所有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 但是,要充分探讨如此宽泛的一个领域,只能依靠迄今为止只有极少数学者能够写出 来的优秀论文;最好的办法是像本书大部分论文那样,对最近几个世纪,特别是清代 (1644—1912 年)的具体事例进行个案研究。 一些假设:中国的世界秩序的源流 本书用现代语言评估近代初期中华帝国外交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分析了由中 国和与之接触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组成的国际秩序的结构和功能。在 19 世纪中叶西方列 强入侵东亚之前,这种国际秩序十分兴盛。直到 1911 年,它还像夕阳残照,余晖未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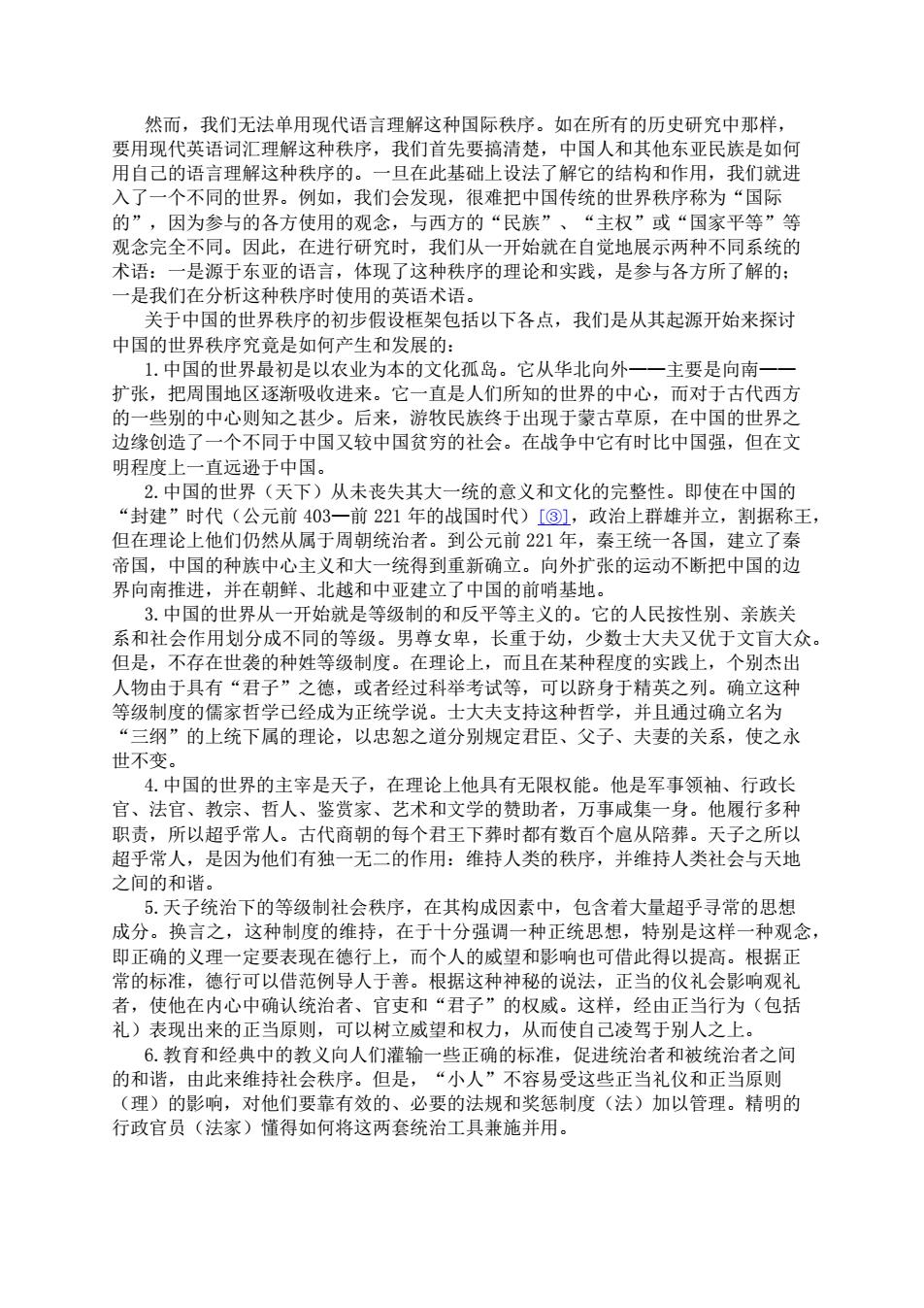
然而,我们无法单用现代语言理解这种国际秩序。如在所有的历史研究中那样, 要用现代英语词汇理解这种秩序,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中国人和其他东亚民族是如何 用自己的语言理解这种秩序的。一旦在此基础上设法了解它的结构和作用,我们就进 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例如,我们会发现,很难把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称为“国际 的”,因为参与的各方使用的观念,与西方的“民族”、“主权”或“国家平等”等 观念完全不同。因此,在进行研究时,我们从一开始就在自觉地展示两种不同系统的 术语:一是源于东亚的语言,体现了这种秩序的理论和实践,是参与各方所了解的: 一是我们在分析这种秩序时使用的英语术语。 关于中国的世界秩序的初步假设框架包括以下各点,我们是从其起源开始来探讨 中国的世界秩序究竟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1.中国的世界最初是以农业为本的文化孤岛。它从华北向外一一主要是向南一一 扩张,把周围地区逐渐吸收进来。它一直是人们所知的世界的中心,而对于古代西方 的一些别的中心则知之甚少。后来,游牧民族终于出现于蒙古草原,在中国的世界之 边缘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中国又较中国贫穷的社会。在战争中它有时比中国强,但在文 明程度上一直远逊于中国。 2.中国的世界(天下)从未丧失其大一统的意义和文化的完整性。即使在中国的 “封建”时代(公元前403一前221年的战国时代)[③],政治上群雄并立,割据称王, 但在理论上他们仍然从属于周朝统治者。到公元前221年,秦王统一各国,建立了秦 帝国,中国的种族中心主义和大一统得到重新确立。向外扩张的运动不断把中国的边 界向南推进,并在朝鲜、北越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前哨基地。 3.中国的世界从一开始就是等级制的和反平等主义的。它的人民按性别、亲族关 系和社会作用划分成不同的等级。男尊女卑,长重于幼,少数士大夫又优于文盲大众。 但是,不存在世袭的种姓等级制度。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实践上,个别杰出 人物由于具有“君子”之德,或者经过科举考试等,可以跻身于精英之列。确立这种 等级制度的儒家哲学已经成为正统学说。士大夫支持这种哲学,并且通过确立名为 “三纲”的上统下属的理论,以忠恕之道分别规定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使之永 世不变。 4.中国的世界的主宰是天子,在理论上他具有无限权能。他是军事领袖、行政长 官、法官、教宗、哲人、鉴赏家、艺术和文学的赞助者,万事咸集一身。他履行多种 职责,所以超乎常人。古代商朝的每个君王下葬时都有数百个扈从陪葬。天子之所以 超乎常人,是因为他们有独一无二的作用:维持人类的秩序,并维持人类社会与天地 之间的和谐。 5.天子统治下的等级制社会秩序,在其构成因素中,包含着大量超乎寻常的思想 成分。换言之,这种制度的维持,在于十分强调一种正统思想,特别是这样一种观念, 即正确的义理一定要表现在德行上,而个人的威望和影响也可借此得以提高。根据正 常的标准,德行可以借范例导人于善。根据这种神秘的说法,正当的仪礼会影响观礼 者,使他在内心中确认统治者、官吏和“君子”的权威。这样,经由正当行为(包括 礼)表现出来的正当原则,可以树立威望和权力,从而使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 6.教育和经典中的教义向人们灌输一些正确的标准,促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 的和谐,由此来维持社会秩序。但是,“小人”不容易受这些正当礼仪和正当原则 (理)的影响,对他们要靠有效的、必要的法规和奖惩制度(法)加以管理。精明的 行政官员(法家)懂得如何将这两套统治工具兼施并用
然而,我们无法单用现代语言理解这种国际秩序。如在所有的历史研究中那样, 要用现代英语词汇理解这种秩序,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中国人和其他东亚民族是如何 用自己的语言理解这种秩序的。一旦在此基础上设法了解它的结构和作用,我们就进 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例如,我们会发现,很难把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称为“国际 的”,因为参与的各方使用的观念,与西方的“民族”、“主权”或“国家平等”等 观念完全不同。因此,在进行研究时,我们从一开始就在自觉地展示两种不同系统的 术语:一是源于东亚的语言,体现了这种秩序的理论和实践,是参与各方所了解的; 一是我们在分析这种秩序时使用的英语术语。 关于中国的世界秩序的初步假设框架包括以下各点,我们是从其起源开始来探讨 中国的世界秩序究竟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1.中国的世界最初是以农业为本的文化孤岛。它从华北向外——主要是向南—— 扩张,把周围地区逐渐吸收进来。它一直是人们所知的世界的中心,而对于古代西方 的一些别的中心则知之甚少。后来,游牧民族终于出现于蒙古草原,在中国的世界之 边缘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中国又较中国贫穷的社会。在战争中它有时比中国强,但在文 明程度上一直远逊于中国。 2.中国的世界(天下)从未丧失其大一统的意义和文化的完整性。即使在中国的 “封建”时代(公元前 403—前 221 年的战国时代)[③],政治上群雄并立,割据称王, 但在理论上他们仍然从属于周朝统治者。到公元前 221 年,秦王统一各国,建立了秦 帝国,中国的种族中心主义和大一统得到重新确立。向外扩张的运动不断把中国的边 界向南推进,并在朝鲜、北越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前哨基地。 3.中国的世界从一开始就是等级制的和反平等主义的。它的人民按性别、亲族关 系和社会作用划分成不同的等级。男尊女卑,长重于幼,少数士大夫又优于文盲大众。 但是,不存在世袭的种姓等级制度。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实践上,个别杰出 人物由于具有“君子”之德,或者经过科举考试等,可以跻身于精英之列。确立这种 等级制度的儒家哲学已经成为正统学说。士大夫支持这种哲学,并且通过确立名为 “三纲”的上统下属的理论,以忠恕之道分别规定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使之永 世不变。 4.中国的世界的主宰是天子,在理论上他具有无限权能。他是军事领袖、行政长 官、法官、教宗、哲人、鉴赏家、艺术和文学的赞助者,万事咸集一身。他履行多种 职责,所以超乎常人。古代商朝的每个君王下葬时都有数百个扈从陪葬。天子之所以 超乎常人,是因为他们有独一无二的作用:维持人类的秩序,并维持人类社会与天地 之间的和谐。 5.天子统治下的等级制社会秩序,在其构成因素中,包含着大量超乎寻常的思想 成分。换言之,这种制度的维持,在于十分强调一种正统思想,特别是这样一种观念, 即正确的义理一定要表现在德行上,而个人的威望和影响也可借此得以提高。根据正 常的标准,德行可以借范例导人于善。根据这种神秘的说法,正当的仪礼会影响观礼 者,使他在内心中确认统治者、官吏和“君子”的权威。这样,经由正当行为(包括 礼)表现出来的正当原则,可以树立威望和权力,从而使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 6.教育和经典中的教义向人们灌输一些正确的标准,促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 的和谐,由此来维持社会秩序。但是,“小人”不容易受这些正当礼仪和正当原则 (理)的影响,对他们要靠有效的、必要的法规和奖惩制度(法)加以管理。精明的 行政官员(法家)懂得如何将这两套统治工具兼施并用

7.天子拥有两方面的主导权,一是借由礼仪宣扬经典的教义,一是用“法”来实 行奖惩。天子是社会和政府的最高核心。人民效忠和敬畏的具体对象是天子,而不是 “国家”、“民族”、“人民”等任何非人格化的抽象概念。天子的统治是人治。 8.皇帝利用两种行政结构进行统治。较古的一种基于君臣之间的个人关系,后来 的一种是官僚式的,这两种结构同时存在。综观1912年前的整个帝制时代,中国内政 方面广泛的官僚结构,同皇帝与皇亲国戚和皇族外某些达官贵人之间以个人关系为基 础的古老权力结构一直并行不悖。从广义上说,这就是各个朝代所建立的贵族政治。 在许多方面,它可以被称为封建制度。若用很笼统的使人容易张冠李戴的欧洲术语来 说明,就是皇帝“封”许多世袭的诸侯(藩),他们反过来向皇帝进“贡”。首先是 封皇族内的“封建领主”(宗藩),给予他们权力和衔位,或者至少是赏赐。这些人 包括皇室亲王,甚至还有皇帝的妃嫔。接着是封“内藩”,最著名的例子是1644年满 族入关时的三位汉族合作者,他们后来在1672一1683年间发动了“三藩之乱”。最后 是封“外藩”,他们是州郡的统治者,或是中国本土以外的统治者。所有这些藩属都 是世袭的,虽然有些藩属的爵位每过一代降低一等,直至消失。“贡”本是纳税之谓, 一般是奉献礼物,特别是土产(方物)。 9.第二种行政结构就是官僚制度。它在秦代和前汉(公元前221年以后)就扩及 整个中原地区。官僚政府起用合格的专业行政官员,给予一定地域的管辖权,付给固 定的薪俸,通过往来公文加以控制,且有预定的任期。这套办法主要是由“法家”发 展起来的,他们以善于运用非人治的法著称,但实际上是整个严密的官僚政治制度的 发明者。他们设法将帝国分为“郡”和“县”,为中国的政治权术开创了久远的传统。 [④] 10.现在我们可以明白,天子独一无二的集中统治所以能够在如此幅员辽阔和复杂 的地域以及如此众多的人口中得到维持,完全是由于这种统治只是表面上的。皇帝作 为国家统一的一个象征高高在上,因为他的臣僚并不想直接统治乡村。而那些得到教 化的地方精英(主要是科举功名的获得者),在作为社会秩序的柱石忠于皇帝的同时, 支配着乡村。这些地方精英(或曰士绅阶级),受到儒家学说的熏陶,因而忠贞不贰, 信奉正统的教义。他们已变为社会特权阶层,对于身在其中的社会秩序具有信心。 11.这种效忠意识不仅及于中国的世界内之精英统治者,而且及于中国境外与中国 有过任何接触的藩属统治者。在中国人看来,这是确定了的:天子全智全能的榜样和 德行所具有的神秘影响力,不仅遍及中国本土,而且可以超越中国疆界,普及全人类, 给予他们和平与秩序。尽管这种影响力已逐渐衰微,但仍然是以天子为中心的等级制 度的组成部分。由于地方行政的官僚结构不能远及中国以外的统治者,所以他们便直 接归附皇帝,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成为皇帝个人的或“封建”的行政制度之残存组织 的一部分。 以上就是栗原朋信教授所做结论的理论背景。[⑤]他从对于古代印章的研究中发现, 天子的内藩包括大臣、封建亲王以及中国本土地位较低的王公贵族。在中国本土,天 子的德行广被,“礼”和“法”均行之有效。外藩的地位较低,他们统治中国的边缘 地区,皇帝的德行尚能发生影响,所以“礼”有效而“法”无存(即天子没有直接的 强制权)。栗原朋信教授指出,匈奴的单于是“客臣”,是属于第三类的,在这个野 蛮的游牧民族中间,皇帝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唯有“礼”的一些特殊方面才行之有 效。 12.就其典型性而言,随着中国统治地域的扩张,一个时期(例如周朝)的“外藩” 逐渐变为后来(例如秦、汉时期)的“内藩”。华南的南越国的统治者就是一个例子, 该国后来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与此相似,汉代居于蒙古草原的匈奴的“客臣”地
7.天子拥有两方面的主导权,一是借由礼仪宣扬经典的教义,一是用“法”来实 行奖惩。天子是社会和政府的最高核心。人民效忠和敬畏的具体对象是天子,而不是 “国家”、“民族”、“人民”等任何非人格化的抽象概念。天子的统治是人治。 8.皇帝利用两种行政结构进行统治。较古的一种基于君臣之间的个人关系,后来 的一种是官僚式的,这两种结构同时存在。综观 1912 年前的整个帝制时代,中国内政 方面广泛的官僚结构,同皇帝与皇亲国戚和皇族外某些达官贵人之间以个人关系为基 础的古老权力结构一直并行不悖。从广义上说,这就是各个朝代所建立的贵族政治。 在许多方面,它可以被称为封建制度。若用很笼统的使人容易张冠李戴的欧洲术语来 说明,就是皇帝“封”许多世袭的诸侯(藩),他们反过来向皇帝进“贡”。首先是 封皇族内的“封建领主”(宗藩),给予他们权力和衔位,或者至少是赏赐。这些人 包括皇室亲王,甚至还有皇帝的妃嫔。接着是封“内藩”,最著名的例子是 1644 年满 族入关时的三位汉族合作者,他们后来在 1672—1683 年间发动了“三藩之乱”。最后 是封“外藩”,他们是州郡的统治者,或是中国本土以外的统治者。所有这些藩属都 是世袭的,虽然有些藩属的爵位每过一代降低一等,直至消失。“贡”本是纳税之谓, 一般是奉献礼物,特别是土产(方物)。 9.第二种行政结构就是官僚制度。它在秦代和前汉(公元前 221 年以后)就扩及 整个中原地区。官僚政府起用合格的专业行政官员,给予一定地域的管辖权,付给固 定的薪俸,通过往来公文加以控制,且有预定的任期。这套办法主要是由“法家”发 展起来的,他们以善于运用非人治的法著称,但实际上是整个严密的官僚政治制度的 发明者。他们设法将帝国分为“郡”和“县”,为中国的政治权术开创了久远的传统。 [④] 10.现在我们可以明白,天子独一无二的集中统治所以能够在如此幅员辽阔和复杂 的地域以及如此众多的人口中得到维持,完全是由于这种统治只是表面上的。皇帝作 为国家统一的一个象征高高在上,因为他的臣僚并不想直接统治乡村。而那些得到教 化的地方精英(主要是科举功名的获得者),在作为社会秩序的柱石忠于皇帝的同时, 支配着乡村。这些地方精英(或曰士绅阶级),受到儒家学说的熏陶,因而忠贞不贰, 信奉正统的教义。他们已变为社会特权阶层,对于身在其中的社会秩序具有信心。 11.这种效忠意识不仅及于中国的世界内之精英统治者,而且及于中国境外与中国 有过任何接触的藩属统治者。在中国人看来,这是确定了的:天子全智全能的榜样和 德行所具有的神秘影响力,不仅遍及中国本土,而且可以超越中国疆界,普及全人类, 给予他们和平与秩序。尽管这种影响力已逐渐衰微,但仍然是以天子为中心的等级制 度的组成部分。由于地方行政的官僚结构不能远及中国以外的统治者,所以他们便直 接归附皇帝,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成为皇帝个人的或“封建”的行政制度之残存组织 的一部分。 以上就是栗原朋信教授所做结论的理论背景。[⑤]他从对于古代印章的研究中发现, 天子的内藩包括大臣、封建亲王以及中国本土地位较低的王公贵族。在中国本土,天 子的德行广被,“礼”和“法”均行之有效。外藩的地位较低,他们统治中国的边缘 地区,皇帝的德行尚能发生影响,所以“礼”有效而“法”无存(即天子没有直接的 强制权)。栗原朋信教授指出,匈奴的单于是“客臣”,是属于第三类的,在这个野 蛮的游牧民族中间,皇帝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唯有“礼”的一些特殊方面才行之有 效。 12.就其典型性而言,随着中国统治地域的扩张,一个时期(例如周朝)的“外藩” 逐渐变为后来(例如秦、汉时期)的“内藩”。华南的南越国的统治者就是一个例子, 该国后来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与此相似,汉代居于蒙古草原的匈奴的“客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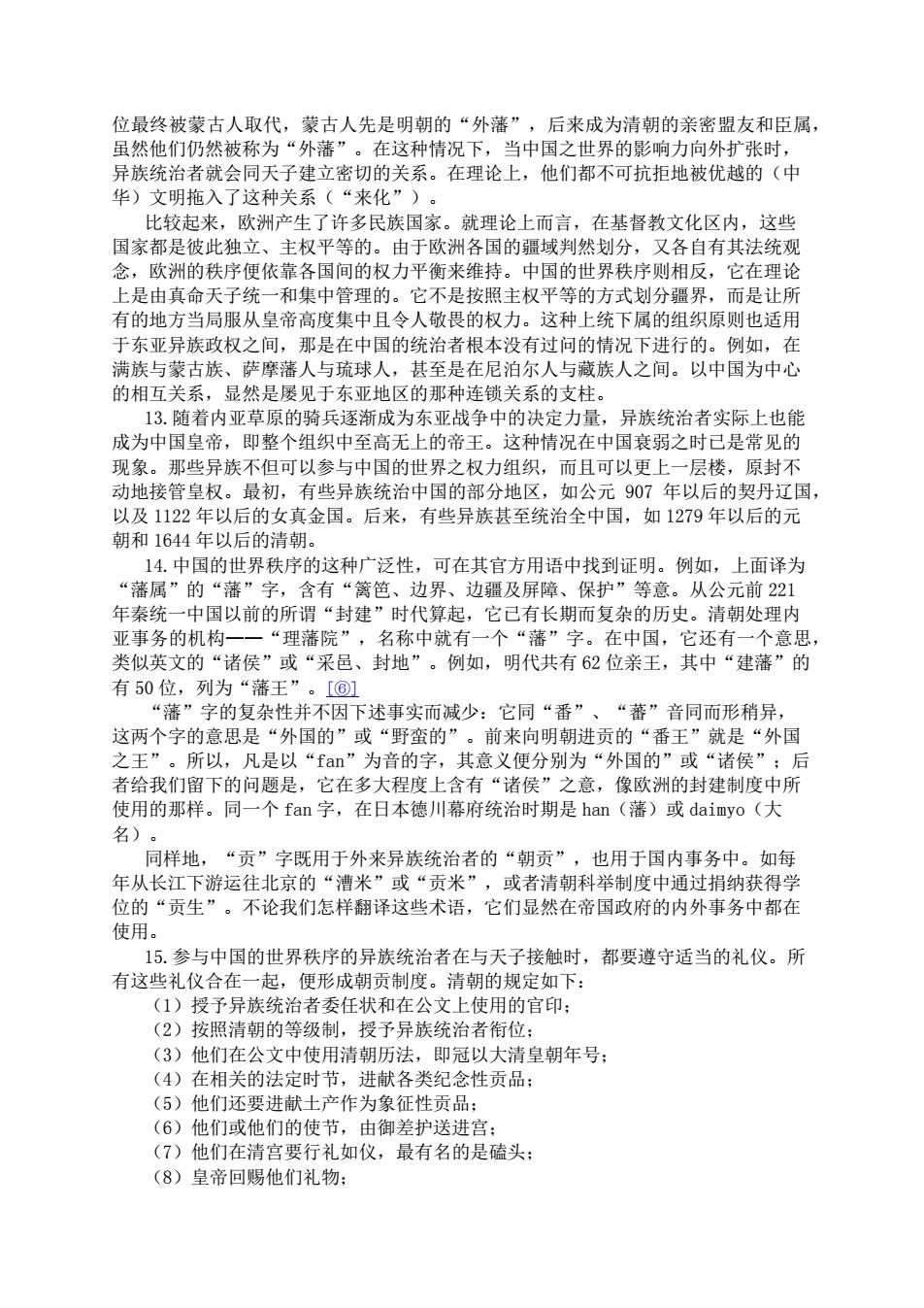
位最终被蒙古人取代,蒙古人先是明朝的“外藩”,后来成为清朝的亲密盟友和臣属, 虽然他们仍然被称为“外藩”。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之世界的影响力向外扩张时, 异族统治者就会同天子建立密切的关系。在理论上,他们都不可抗拒地被优越的(中 华)文明拖入了这种关系(“来化”)。 比较起来,欧洲产生了许多民族国家。就理论上而言,在基督教文化区内,这些 国家都是彼此独立、主权平等的。由于欧洲各国的疆域判然划分,又各自有其法统观 念,欧洲的秩序便依靠各国间的权力平衡来维持。中国的世界秩序则相反,它在理论 上是由真命天子统一和集中管理的。它不是按照主权平等的方式划分疆界,而是让所 有的地方当局服从皇帝高度集中且令人敬畏的权力。这种上统下属的组织原则也适用 于东亚异族政权之间,那是在中国的统治者根本没有过问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在 满族与蒙古族、萨摩藩人与琉球人,甚至是在尼泊尔人与藏族人之间。以中国为中心 的相互关系,显然是屡见于东亚地区的那种连锁关系的支柱。 13.随着内亚草原的骑兵逐渐成为东亚战争中的决定力量,异族统治者实际上也能 成为中国皇帝,即整个组织中至高无上的帝王。这种情况在中国衰弱之时已是常见的 现象。那些异族不但可以参与中国的世界之权力组织,而且可以更上一层楼,原封不 动地接管皇权。最初,有些异族统治中国的部分地区,如公元907年以后的契丹辽国, 以及1122年以后的女真金国。后来,有些异族甚至统治全中国,如1279年以后的元 朝和1644年以后的清朝。 14.中国的世界秩序的这种广泛性,可在其官方用语中找到证明。例如,上面译为 “藩属”的“藩”字,含有“篱笆、边界、边疆及屏障、保护”等意。从公元前221 年秦统一中国以前的所谓“封建”时代算起,它已有长期而复杂的历史。清朝处理内 亚事务的机构一一“理藩院”,名称中就有一个“藩”字。在中国,它还有一个意思, 类似英文的“诸侯”或“采邑、封地”。例如,明代共有62位亲王,其中“建藩”的 有50位,列为“藩王”。[⑥1 “藩”字的复杂性并不因下述事实而减少:它同“番”、“蕃”音同而形稍异, 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外国的”或“野蛮的”。前来向明朝进贡的“番王”就是“外国 之王”。所以,凡是以“fan”为音的字,其意义便分别为“外国的”或“诸侯”;后 者给我们留下的问题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含有“诸侯”之意,像欧洲的封建制度中所 使用的那样。同一个fan字,在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是han(藩)或daimyo(大 名)。 同样地,“贡”字既用于外来异族统治者的“朝贡”,也用于国内事务中。如每 年从长江下游运往北京的“漕米”或“贡米”,或者清朝科举制度中通过捐纳获得学 位的“贡生”。不论我们怎样翻译这些术语,它们显然在帝国政府的内外事务中都在 使用。 15.参与中国的世界秩序的异族统治者在与天子接触时,都要遵守适当的礼仪。所 有这些礼仪合在一起,便形成朝贡制度。清朝的规定如下: (1)授予异族统治者委任状和在公文上使用的官印: (2)按照清朝的等级制,授予异族统治者衔位: (3)他们在公文中使用清朝历法,即冠以大清皇朝年号: (4)在相关的法定时节,进献各类纪念性贡品: (5)他们还要进献土产作为象征性贡品: (6)他们或他们的使节,由御差护送进宫: (7)他们在清宫要行礼如仪,最有名的是磕头: (8)皇帝回赐他们礼物:
位最终被蒙古人取代,蒙古人先是明朝的“外藩”,后来成为清朝的亲密盟友和臣属, 虽然他们仍然被称为“外藩”。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之世界的影响力向外扩张时, 异族统治者就会同天子建立密切的关系。在理论上,他们都不可抗拒地被优越的(中 华)文明拖入了这种关系(“来化”)。 比较起来,欧洲产生了许多民族国家。就理论上而言,在基督教文化区内,这些 国家都是彼此独立、主权平等的。由于欧洲各国的疆域判然划分,又各自有其法统观 念,欧洲的秩序便依靠各国间的权力平衡来维持。中国的世界秩序则相反,它在理论 上是由真命天子统一和集中管理的。它不是按照主权平等的方式划分疆界,而是让所 有的地方当局服从皇帝高度集中且令人敬畏的权力。这种上统下属的组织原则也适用 于东亚异族政权之间,那是在中国的统治者根本没有过问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在 满族与蒙古族、萨摩藩人与琉球人,甚至是在尼泊尔人与藏族人之间。以中国为中心 的相互关系,显然是屡见于东亚地区的那种连锁关系的支柱。 13.随着内亚草原的骑兵逐渐成为东亚战争中的决定力量,异族统治者实际上也能 成为中国皇帝,即整个组织中至高无上的帝王。这种情况在中国衰弱之时已是常见的 现象。那些异族不但可以参与中国的世界之权力组织,而且可以更上一层楼,原封不 动地接管皇权。最初,有些异族统治中国的部分地区,如公元 907 年以后的契丹辽国, 以及 1122 年以后的女真金国。后来,有些异族甚至统治全中国,如 1279 年以后的元 朝和 1644 年以后的清朝。 14.中国的世界秩序的这种广泛性,可在其官方用语中找到证明。例如,上面译为 “藩属”的“藩”字,含有“篱笆、边界、边疆及屏障、保护”等意。从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中国以前的所谓“封建”时代算起,它已有长期而复杂的历史。清朝处理内 亚事务的机构——“理藩院”,名称中就有一个“藩”字。在中国,它还有一个意思, 类似英文的“诸侯”或“采邑、封地”。例如,明代共有 62 位亲王,其中“建藩”的 有 50 位,列为“藩王”。[⑥] “藩”字的复杂性并不因下述事实而减少:它同“番”、“蕃”音同而形稍异, 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外国的”或“野蛮的”。前来向明朝进贡的“番王”就是“外国 之王”。所以,凡是以“fan”为音的字,其意义便分别为“外国的”或“诸侯”;后 者给我们留下的问题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含有“诸侯”之意,像欧洲的封建制度中所 使用的那样。同一个 fan 字,在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是 han(藩)或 daimyo(大 名)。 同样地,“贡”字既用于外来异族统治者的“朝贡”,也用于国内事务中。如每 年从长江下游运往北京的“漕米”或“贡米”,或者清朝科举制度中通过捐纳获得学 位的“贡生”。不论我们怎样翻译这些术语,它们显然在帝国政府的内外事务中都在 使用。 15.参与中国的世界秩序的异族统治者在与天子接触时,都要遵守适当的礼仪。所 有这些礼仪合在一起,便形成朝贡制度。清朝的规定如下: (1)授予异族统治者委任状和在公文上使用的官印; (2)按照清朝的等级制,授予异族统治者衔位; (3)他们在公文中使用清朝历法,即冠以大清皇朝年号; (4)在相关的法定时节,进献各类纪念性贡品; (5)他们还要进献土产作为象征性贡品; (6)他们或他们的使节,由御差护送进宫; (7)他们在清宫要行礼如仪,最有名的是磕头; (8)皇帝回赐他们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