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第一部分科学与革命 自己的创造看作是革命,但是哥白尼和牛顿却没有这样做。牛顿 及其前辈们之所以没有承认自己的事业是革命性的,其部分原因 在于,他们的工作是在“革命”这个词普遍应用于科学领域之前完 成的。不过,还有更深一层的理由;在现代科学最初100年左右的 时间里,许多伟大的富有创造性的科学家们,更愿意把他们自己看 作是古代知识的复兴者或重新发现者(与他们同时代的人甚至也 这样看),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是改善和扩展知识的革新者,但不认 为他们自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那种革命者。 18世纪初,在丰特奈尔认识到数学中已经发生了一场革命后 不久,牛顿的《原理》就被看作是构成了物理学中的一场革命,又过 了没多久,罗伯特·西默宣布,他已经发动了一场电学革命。这些 事件发生时,政治意义上的革命还有着一种温和宽厚的内涵。以 后,法国大革命走向了极端,进入了恐怖时代,以至于“革命”变成 了一个与其说是表述飞速发展的词,莫如说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 的词。曾因参与法国大革命而受到政治迫害并于1794年移居美 国的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为我们说明了18世纪末人们对革命的 态度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在给与罗伯特·富尔顿共同研制汽船的 政治家、发明家R.利文斯顿的一封信中,普里斯特利对他的这件 收信人“在纸的制造方面最有价值的发现“表示祝贺(斯科菲尔德 1966,300)。“如果您能成功地把纸漂白,”普里斯特利写道,“您将 7在整个造纸业中引起一场革命。”此信写于1799年,普里斯特利没 有忘记当时人们对革命的普遍反感,所以他马上加了一个注释表 示款意,他说,利文斯顿的创新决不能“在此时此刻被称之为革命。 虽然它很值得称赞,但这样说只能使它名誉扫地。但是不管怎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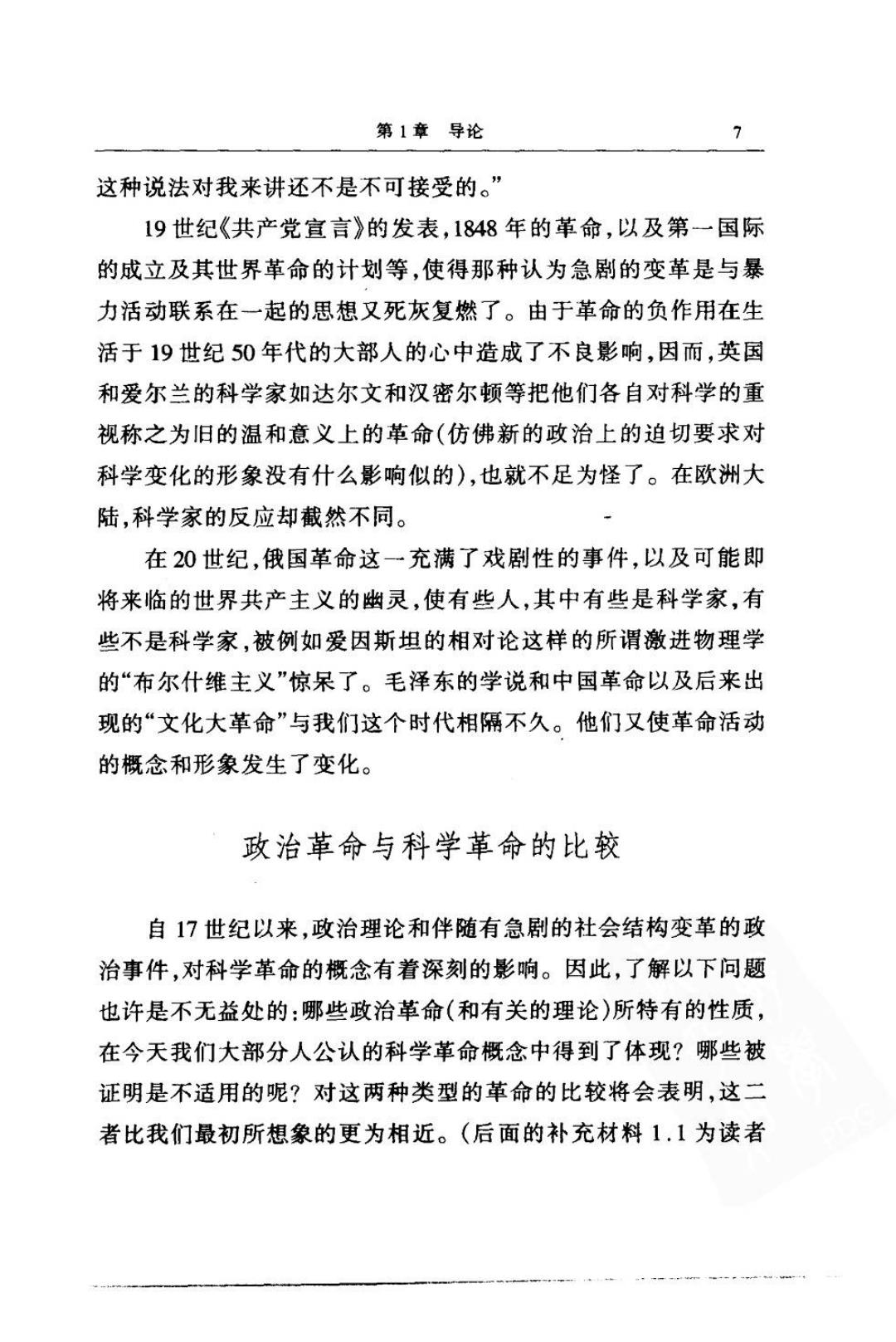
第1章导论 这种说法对我来讲还不是不可接受的。” 19世纪《共产党宣言》的发表,1848年的革命,以及第一国际 的成立及其世界革命的计划等,使得那种认为急剧的变革是与暴 力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又死灰复燃了。由于革命的负作用在生 活于19世纪50年代的大部人的心中造成了不良影响,因而,英国 和爱尔兰的科学家如达尔文和汉密尔顿等把他们各自对科学的重 视称之为旧的温和意义上的革命(仿佛新的政治上的迫切要求对 科学变化的形象没有什么影响似的),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欧洲大 陆,科学家的反应却截然不同。 在20世纪,俄国革命这一充满了戏剧性的事件,以及可能即 将来临的世界共产主义的幽灵,使有些人,其中有些是科学家,有 些不是科学家,被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样的所谓激进物理学 的“布尔什维主义”惊呆了。毛泽东的学说和中国革命以及后来出 现的“文化大革命”与我们这个时代相隔不久。他们又使革命活动 的概念和形象发生了变化。 政治革命与科学革命的比较 自17世纪以来,政治理论和伴随有急剧的社会结构变革的政 治事件,对科学革命的概念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了解以下问题 也许是不无益处的:哪些政治革命(和有关的理论)所特有的性质, 在今天我们大部分人公认的科学革命概念中得到了体现?哪些被 证明是不适用的呢?对这两种类型的革命的比较将会表明,这二 者比我们最初所想象的更为相近。(后面的补充材料1.1为读者

第一部分科学与革命 提供了一些资料,它们说明,在历史上人们是怎样看待政治革命与 科学革命的比较的。) 所有政治革命共同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含有“新”的因素,正 如汉纳·阿伦特(1965)坚持认为的那样。“现代的革命概念,”她写 8道,与“历史过程会突然再现这-一看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 此,革命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局面、一一种鲜为人知或闻所未闻的情 况即将呈现出来。”然而我们将看到,在科学革命中,新与旧之间的 转变存在着某些中间环节[]。在政治革命中也存在着这种联系, 尽管这种联系也许不那么密切。不过,看来与常识相矛盾的是,这 种特点并不会使科学革命或政治革命的作用的强弱和影响的大小 受到损害。 很明显,在确定某一系列的事件是否“真的”构成了一场革命 时,必须对新事物的深度和广度作出判断。也许,正如佩蒂(1938, )所指出的那样,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这样的“伟大革命”到 “麦克佩斯谋杀邓肯一世这样的宫廷政变”,都有着一个连续的阶 段。然而在其他人眼中,coups d'etat或宫廷政变也许会被看作是 “反叛行为”,它们不包括任何根本性的政治的(即政治制度的)或 社会的变化。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指明某一特定的事件为革 命,不仅依赖于判断变化种类(是否有政治制度的变化)的客观标 准,而且还依赖于个人对变化程度的判断3)。这后-一个因素有碍 于任何对革命作出普遍适用的定义的尝试。 凡是研究科学革命的人很快都会发现,这些事件也像社会革 命、政治革命以及经济革命一样,有着不同等级,按其重要性可以 分为重大的革命和小型的革命。有些大规模的变动,使得某一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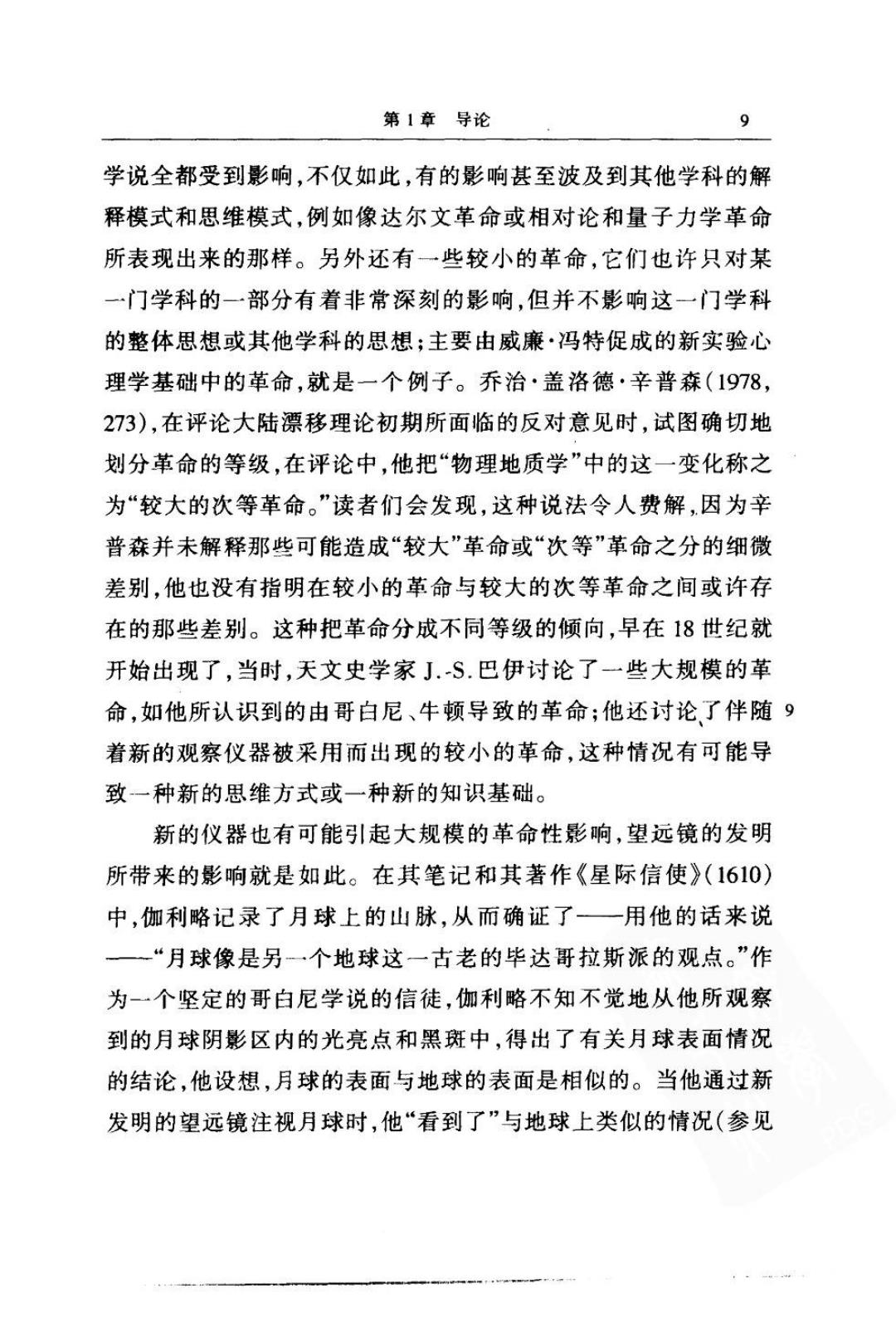
第1章导论 9 学说全都受到影响,不仅如此,有的影响甚至波及到其他学科的解 释模式和思维模式,例如像达尔文革命或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 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另外还有一些较小的革命,它们也许只对某 一门学科的一部分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但并不影响这一门学科 的整体思想或其他学科的思想;主要由威廉·冯特促成的新实验心 理学基础中的革命,就是一个例子。乔治·盖洛德·辛普森(1978, 273),在评论大陆漂移理论初期所面临的反对意见时,试图确切地 划分革命的等级,在评论中,他把“物理地质学”中的这一变化称之 为“较大的次等革命。”读者们会发现,这种说法令人费解,因为辛 普森并未解释那些可能造成“较大”革命或“次等”革命之分的细微 差别,他也没有指明在较小的革命与较大的次等革命之间或许存 在的那些差别。这种把革命分成不同等级的倾向,早在18世纪就 开始出现了,当时,天文史学家J.S.巴伊讨论了一些大规模的革 命,如他所认识到的由哥白尼、牛顿导致的革命;他还讨论了伴随9 着新的观察仪器被采用而出现的较小的革命,这种情况有可能导 致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或一种新的知识基础。 新的仪器也有可能引起大规模的革命性影响,望远镜的发明 所带来的影响就是如此。在其笔记和其著作《星际信使》(1610) 中,伽利略记录了月球上的山脉,从而确证了一用他的话来说 一一“月球像是另一个地球这一古老的毕达哥拉斯派的观点。”作 为一个坚定的哥白尼学说的信徒,伽利略不知不觉地从他所观察 到的月球阴影区内的光亮点和黑斑中,得出了有关月球表面情况 的结论,他设想,月球的表面与地球的表面是相似的。当他通过新 发明的望远镜注视月球时,他“看到了”与地球上类似的情况(参见

10 第一部分科学与革命 科恩1980,211一215)。伽利略发现,木星有四个卫星,这一发现对 天文学来说是一项重大的成果。地球怎么能以惊人的速度(大约 每秒20英里)围绕太阳运动而又不失去其月球呢?在伽利略时 代,这个疑难问题成了反对地球有可能沿轨道运行的一项有力的 证据。伽利略也许永远解决不了那个难题,但是他发现,木星在运 动时并未失去四个卫星,这就使那种认为如果地球运动就不可能 不失去其卫星的反对意见不再有什么说服力了。随后伽利略发 现,太阳上有黑子而且太阳也在自转。他观察到,金星也像月球一 样有不同的相位,他从金星的相位与其外观大小之间的对应关系 中推出这样-个结论:金星在围绕太阳运行,而不是围绕地球运 行。他还发现,许多“星云状物质”只不过是一些很模糊的星星的 集合物。这些星星,人的肉眼是觉察不出的,而天空中还有无数颗 星星,它们在望远镜发明以前从未被任何人看到过。 天文学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过,天文学中的这些革命 性转变(包括对托勒密体系的错误所作的直观说明在内),并非是 由望远镜“导致”的,而是由伽利略精神导致的。伽利略吸收了哥 白尼学说,并且通过望远镜进行了观察,在此基础上他得出了一些 非正统性的结论,而伽利略精神正是这种结论的产物。望远镜使 天文学的数据库在种类、规模和范围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 这些数据内部和它们自身并没有构成一场科学革命。 对计算机来讲,情况就不同了,计算机像概率和统计学一样, 已经对科学的思维和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为世界气 象学提供的那些新的计算机模型就是一例。这就是说,伽利略通 0过望远镜使数据发生的变化,是需要放弃传统的理论并接受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