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意大学料柱督学丛者 必要的张力 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 [美】托马新+库眼著 花的年纪树立等译 北京大学出领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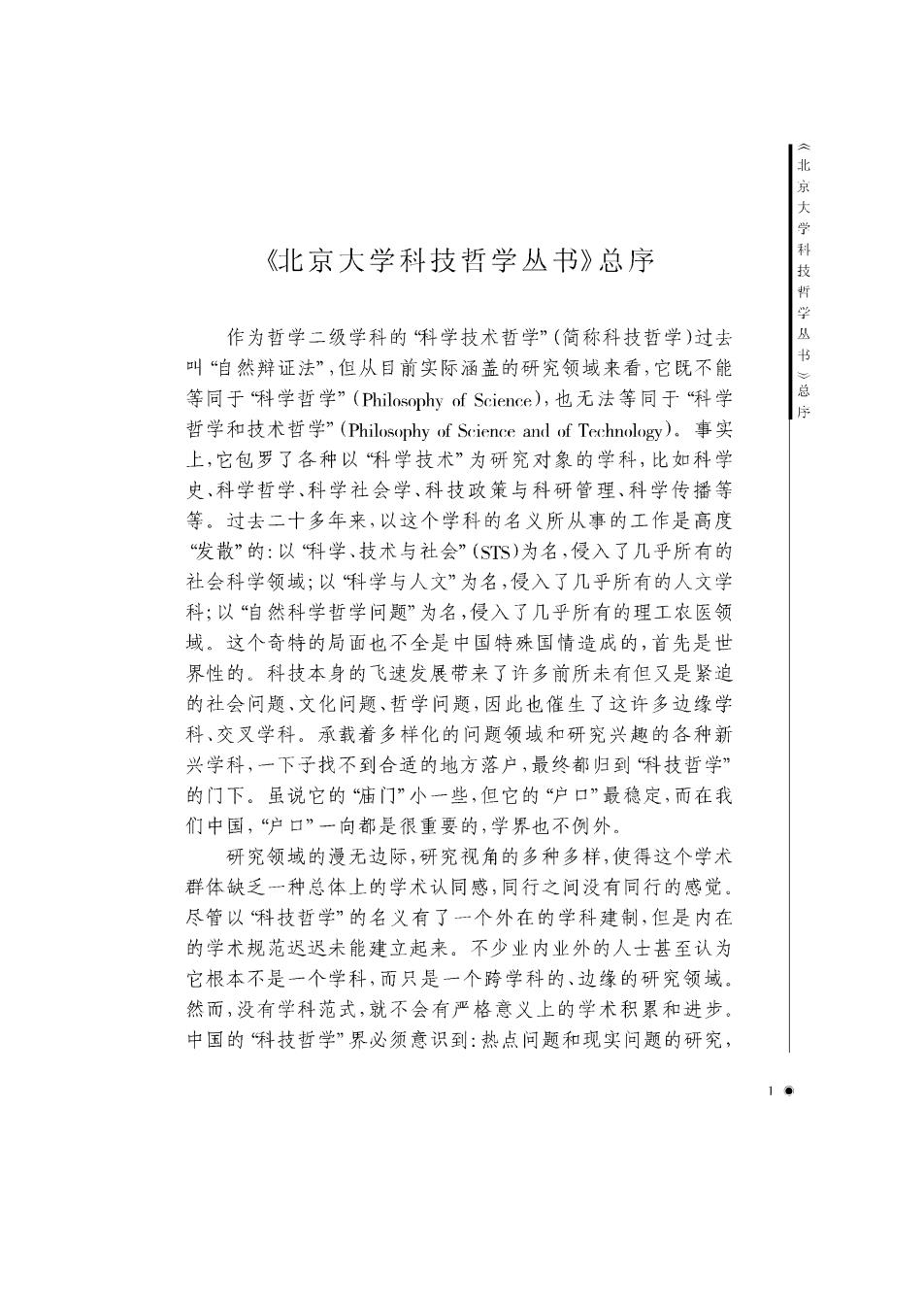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总序 技 是 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简称科技哲学)过去 叫“自然辩证法”,但从目前实际涵盖的研究领域来看,它既不能 8 等同于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也无法等同于“科学 总 序 哲学和技术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of Technology)。事实 上,它包罗了各种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比如科学 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与科研管理、科学传播等 等。过去二十多年来,以这个学科的名义所从事的工作是高度 “发散”的:以“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为名,侵入了几乎所有的 社会科学领域;以科学与人文”为名,侵入了几乎所有的人文学 科;以“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为名,侵入了几乎所有的理工农医领 域。这个奇特的局面也不全是中国特殊国情造成的,首先是世 界性的。科技本身的飞速发展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但又是紧迫 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哲学问题,因此也催生了这许多边缘学 科、交叉学科。承载着多样化的问题领域和研究兴趣的各种新 兴学科,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落户,最终都归到科技哲学” 的门下。虽说它的“庙门”小一些,但它的“户口”最稳定,而在我 们中国,“户口”一向都是很重要的,学界也不例外。 研究领域的漫无边际,研究视角的多种多样,使得这个学术 群体缺乏一种总体上的学术认同感,同行之间没有同行的感觉。 尽管以‘科技哲学”的名义有了一个外在的学科建制,但是内在 的学术规范迟迟未能建立起来。不少业内业外的人士甚至认为 它根本不是一个学科,而只是一个跨学科的、边缘的研究领域。 然而,没有学科范式,就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积累和进步。 中国的科技哲学”界必须意识到:热点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 10

必 不能代替学科建设。惟有通过学科建设,我们的学科才能后继 有人;惟有加强学科建设,我们的热点问题和现实问题研究才能 要 走向深入。 如何着手科技哲学”的内在学科建设?从目前的现状看, 科技哲学界事实上已经分解成两个群体,一个是哲学群体,一个 是社会学群体。前者大体关注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 张 科学思想史、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等,后者大体关注科学社会学、 科技政策与科研管理、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 学等。学科建设首先要顺应这一分化的大局,在哲学方向和社 力 会学方向分头进行。 本丛书的设计体现了我们把料技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来建 设的构想。我们深知,一个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的范式,通常体 现在它的经典著作和教科书中。目前,科技哲学专业的研究生 们还没有公认的必读书目和必修课程体系。我们希望通过本丛 书,为有哲学兴趣的科技哲学教师和学生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 方案。 我们的注意力将集中在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 学思想史四个分支学科上,因为这四个子学科是对科学技术进 行哲学反思的核心和基础学科。我们将在这四个学科方向上, 系统积累基本文献,分层次编写教材和参考书。我们希望本丛 书的出版能够有助于推进科技哲学的学科建设,也希望学界同 行和读者不吝赐教,帮助我们出好这套丛书。 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受到“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 经费资助。 吴国盛 2002年12月于典园四院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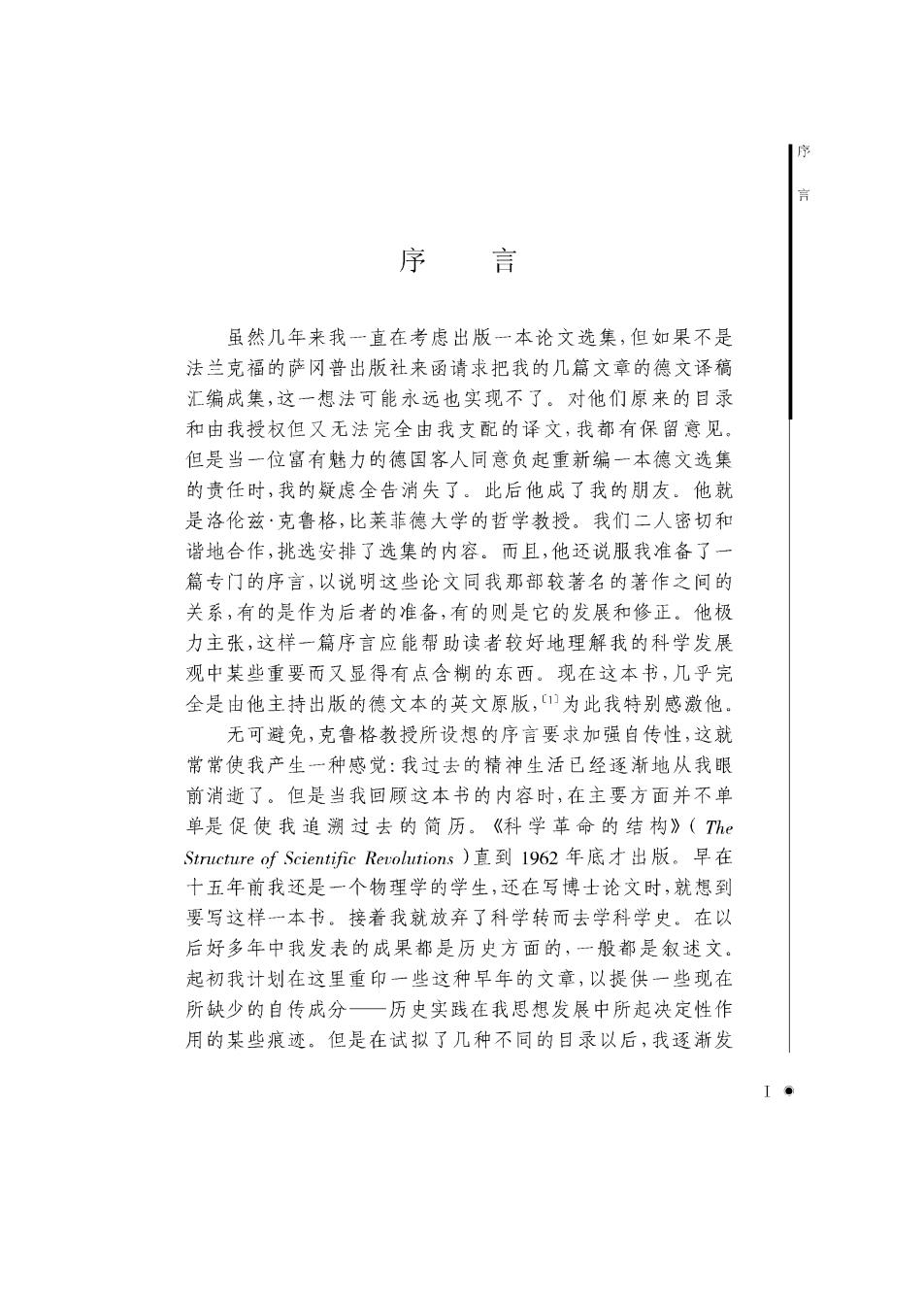
序 言 序 言 虽然几年来我一直在考虑出版一本论文选集,但如果不是 法兰克福的萨冈普出版社来函请求把我的几篇文章的德文译稿 汇编成集,这一想法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对他们原来的目录 和由我授权但又无法完全由我支配的译文,我都有保留意见。 但是当一位富有魅力的德国客人同意负起重新编一本德文选集 的责任时,我的疑虑全告消失了。此后他成了我的朋友。他就 是洛伦兹·克鲁格,比莱菲德大学的哲学教授。我们二人密切和 谐地合作,挑选安排了选集的内容。而且,他还说服我准备了一 篇专门的序言,以说明这些论文同我那部较著名的著作之间的 关系,有的是作为后者的准备,有的则是它的发展和修正。他极 力主张,这样一篇序言应能帮助读者较好地理解我的科学发展 观中某些重要而又显得有点含糊的东西。现在这本书,几乎完 全是由他主持出版的德文本的英文原版,为此我特别感激他。 无可避免,克鲁格教授所设想的序言要求加强自传性,这就 常常使我产生一种感觉:我过去的精神生活已经逐渐地从我眼 前消逝了。但是当我回顾这本书的内容时,在主要方面并不单 单是促使我追溯过去的简历。《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直到1962年底才出版。早在 十五年前我还是一个物理学的学生,还在写博士论文时,就想到 要写这样一本书。接着我就放弃了科学转而去学科学史。在以 后好多年中我发表的成果都是历史方面的,一般都是叙述文。 起初我计划在这里重印一些这种早年的文章,以提供一些现在 所缺少的自传成分一历史实践在我思想发展中所起决定性作 用的某些痕迹。但是在试拟了几种不同的目录以后,我逐渐发 I

必 现历史叙述并不能表明我想表明的东西,甚至还会引起严重的 误解。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的经历尽管使我可以用历史事例去教 要 训哲学,但历史著作一经完成,这种作用就消失了。最初使我转 向历史的偶然事件,可以说明后来发生的事,同时也提供了理解 9 下列文章的有用基础。 已有的历史叙述大都是由过去事实所组成,绝大部分显然 张 无可置疑。因而许多读者都认为,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审查 文本,从中抽出有关事实,再大体按照编年顺序用优美的文字加 以重述。这也是在我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的年代里对我所不大重 力 视的历史学科的看法。当我改变了这种想法(接着也改变了我 的行业),我所作的历史叙述似乎也类似地引起同样的误解。历 史科学所完成的研究成果,总是掩盖着产生这一成果的工作过 程的真相,在这一点上,它似乎比我所知的任何其他学科都更加 严重。 我自己是在1947年才开始彻底醒悟的,当时要我暂时中断 我的当代物理学的研究项目,准备一组关于17世纪力学起源问 题的讲演。为此我首先要查看伽利略和牛顿的先驱们对这个问 题已知道些什么。工作开始才不久,我就接触到亚里士多德的 物理学》(Physica)对运动的讨论以及由此以降的各种著作. 我同以前的大多数科学史家一样,通过这些文本懂得牛顿的物 理学和力学是怎么回事。我也同他们一样对我读的这些文本提 出这个问题: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中已懂得多少力学?它给17世 纪的科学家们留下了多少有待发现的东西?在牛顿用语范围内 提出的这些问题,要求以牛顿的术语来作答,这些答案也是清楚 的。即使就表观的描述层次而言,亚里士多德学派也不大懂力 学,他们如必须谈论力学也大都根本错误。这样一种传统,无法 为伽利略及其同时代人提供任何工作基础。他们必然抛开这一 传统从头重新开始力学研究。 类似这样的说法,曾经是广泛流行的,也是显然不可避免 的。但这也使人困惑不解。亚里士多德如涉及物理学以外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