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议泽世界学术落丛中 尼耳斯·玻尔 哲学文选 [丹麦)N.玻尔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 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 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 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 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 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 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 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 从1981年至1997年先后分七辑印行了名著三百种。现继续编印 第八辑。到1998年底出版至34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 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 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 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副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 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槽粕, 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 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8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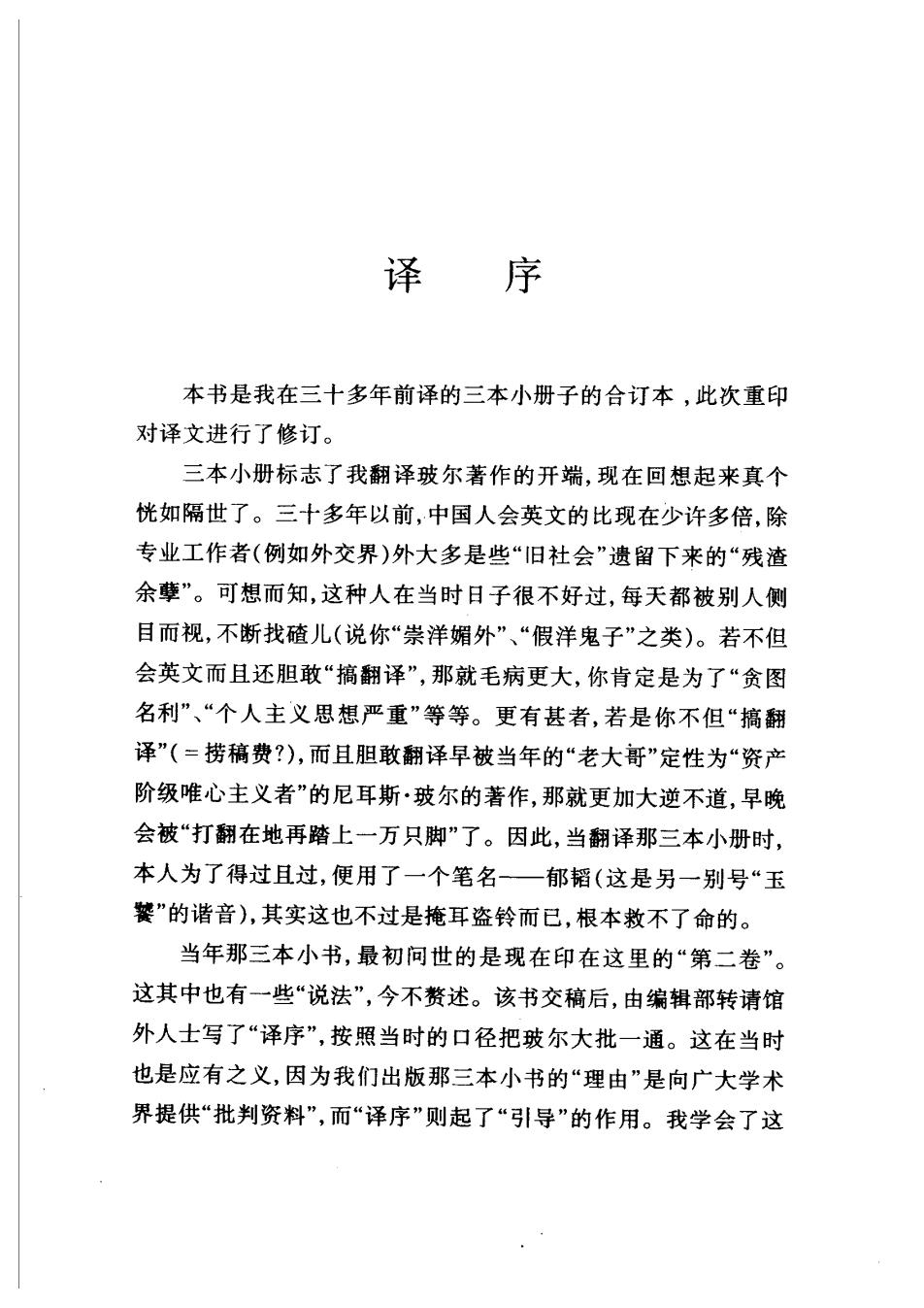
译 序 本书是我在三十多年前译的三本小册子的合订本,此次重印 对译文进行了修订。 三本小册标志了我翻译玻尔著作的开端,现在回想起来真个 恍如隔世了。三十多年以前,中国人会英文的比现在少许多倍,除 专业工作者(例如外交界)外大多是些“旧杜会”遗留下来的“残渣 余孽”。可想而知,这种人在当时日子很不好过,每天都被别人侧 目而视,不断找碴儿(说你“崇洋媚外”、“假洋鬼子”之类)。若不但 会英文而且还胆敢“搞翻译”,那就毛病更大,你肯定是为了“图 名利”、“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等等。更有甚者,若是你不但“搞翻 译”(=捞稿费?),而且胆敢翻译早被当年的“老大哥”定性为“资产 阶级唯心主义者”的尼耳斯·玻尔的著作,那就更加大逆不道,早晚 会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了。因此,当翻译那三本小册时, 本人为了得过且过,便用了一个笔名一郁韬(这是另一别号“玉 饕”的谐音),其实这也不过是掩耳盗铃而已,根本救不了命的。 当年那三本小书,最初问世的是现在印在这里的“第二卷”。 这其中也有一些“说法”,今不赘述。该书交稿后,由编辑部转请馆 外人士写了“译序”,按照当时的口径把玻尔大批一通。这在当时 也是应有之义,因为我们出版那三本小书的“理由”是向广大学术 界提供“批判资料”,而“译序”则起了“引导”的作用。我学会了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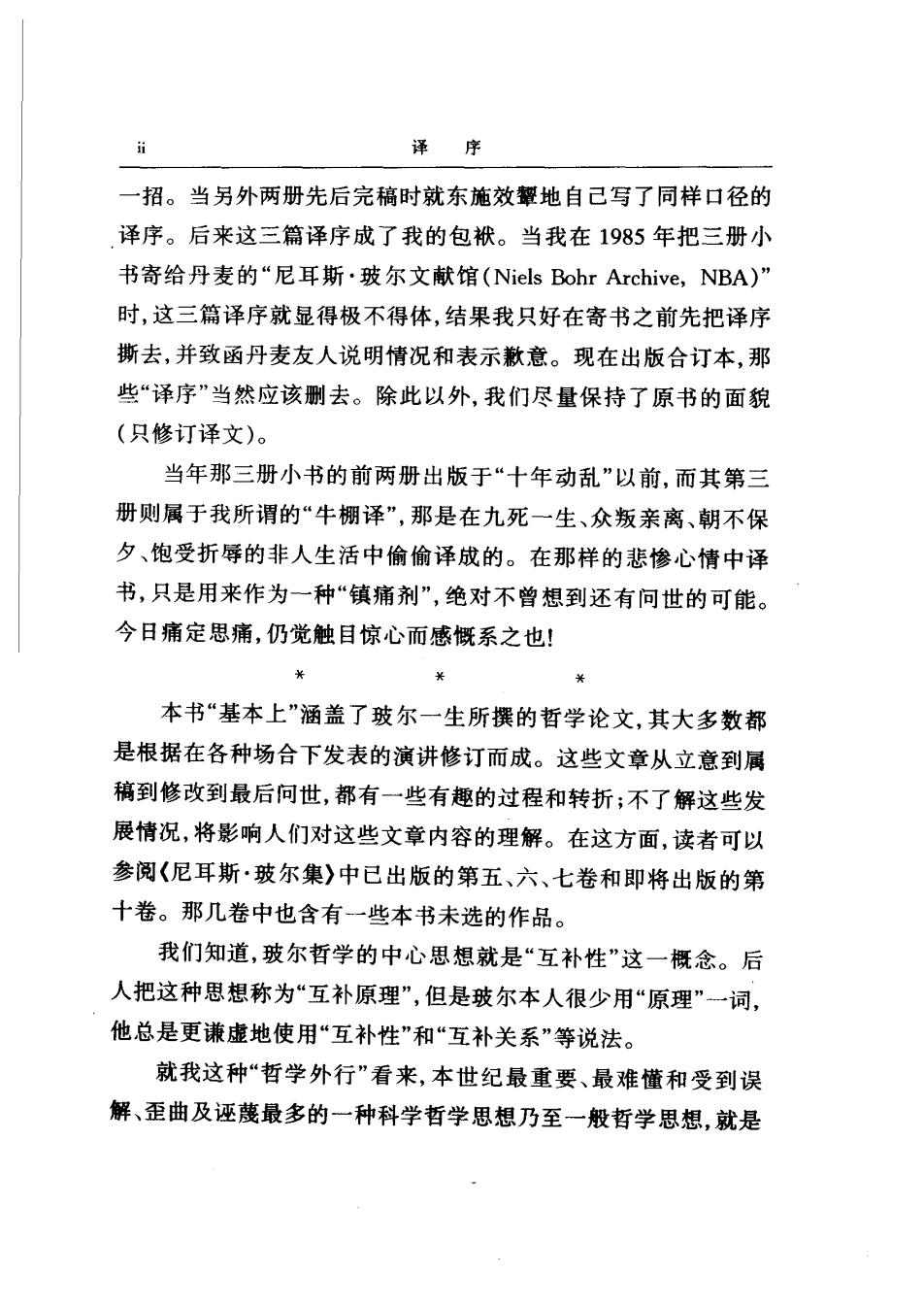
译 序 一招。当另外两册先后完稿时就东施效颦地自己写了同样口径的 译序。后来这三篇译序成了我的包袱。当我在1985年把三册小 书寄给丹麦的“尼耳斯·玻尔文献馆(Niels Bohr Archive,NBA)” 时,这三篇译序就显得极不得体,结果我只好在寄书之前先把译序 撕去,并致函丹麦友人说明情况和表示歉意。现在出版合订本,那 些“译序”当然应该删去。除此以外,我们尽量保持了原书的面貌 (只修订译文)。 当年那三册小书的前两册出版于“十年动乱”以前,而其第三 册则属于我所谓的“牛棚译”,那是在九死一生、众叛亲离、朝不保 夕、饱受折辱的非人生活中偷偷译成的。在那样的悲惨心情中译 书,只是用来作为一种“镇痛剂”,绝对不曾想到还有问世的可能。 今日痛定思痛,仍党触目惊心而感慨系之也! 本书“基本上”涵盖了玻尔一生所撰的哲学论文,其大多数都 是根据在各种场合下发表的演讲修订而成。这些文章从立意到属 稿到修改到最后问世,都有一些有趣的过程和转折;不了解这些发 展情况,将影响人们对这些文章内容的理解。在这方面,读者可以 参阅《尼耳斯·玻尔集〉中已出版的第五、六、七卷和即将出版的第 十卷。那几卷中也含有一些本书未选的作品。 我们知道,玻尔哲学的中心思想就是“互补性”这一概念。后 人把这种思想称为“互补原理”,但是玻尔本人很少用“原理”一词, 他总是更谦虚地使用“互补性”和“互补关系”等说法。 就我这种“哲学外行”看来,本世纪最重要、最难懂和受到误 解、歪曲及诬蔑最多的一种科学哲学思想乃至一般哲学思想,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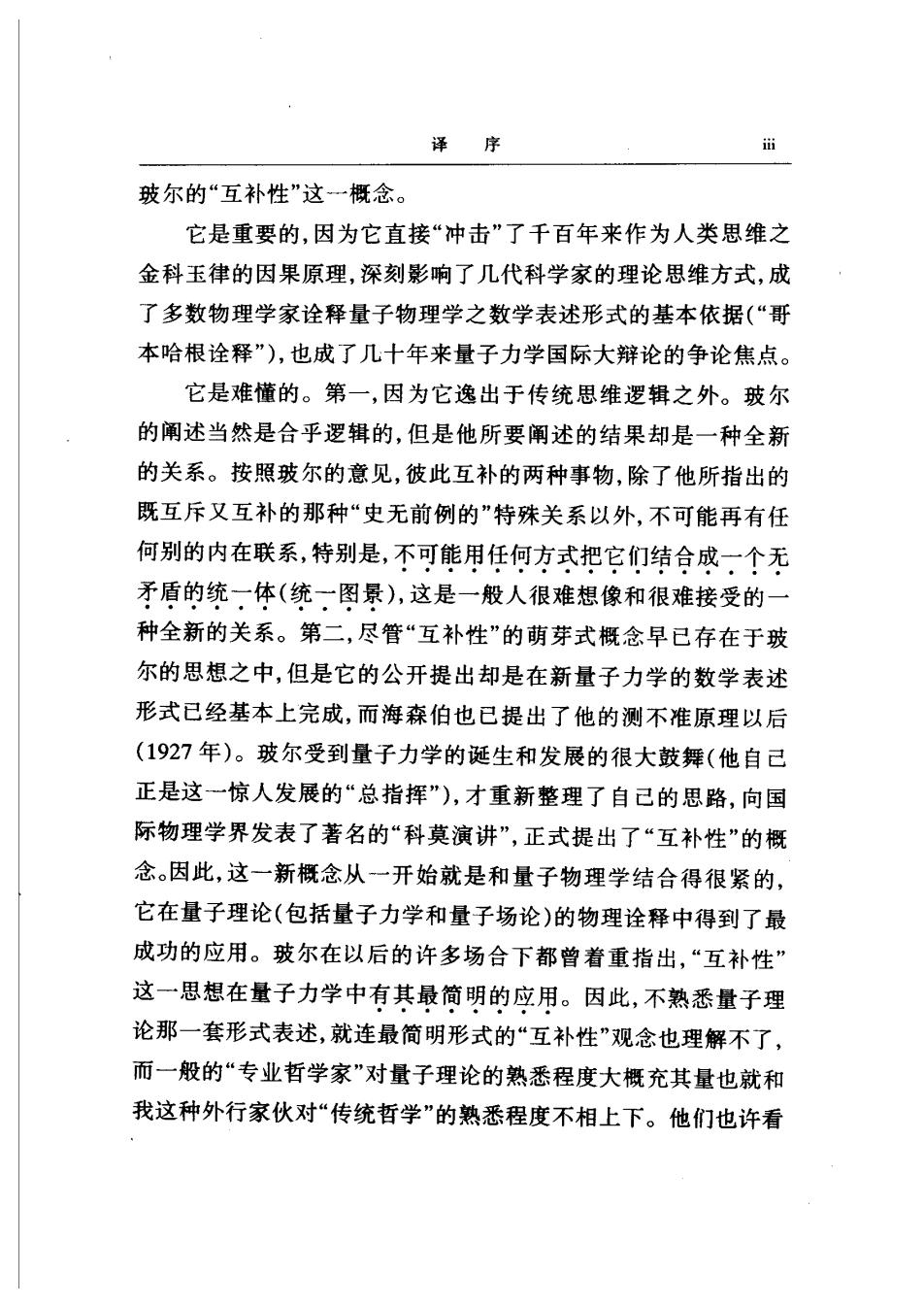
译 序 进 玻尔的“互补性”这一概念。 它是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冲击”了千百年来作为人类思维之 金科玉律的因果原理,深刻影响了几代科学家的理论思维方式,成 了多数物理学家诠释量子物理学之数学表述形式的基本依据(“哥 本哈根诠释”),也成了几十年来量子力学国际大辩论的争论焦点。 它是难懂的。第一,因为它逸出于传统思维逻辑之外。玻尔 的阐述当然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他所要阐述的结果却是一种全新 的关系。按照玻尔的意见,彼此互补的两种事物,除了他所指出的 既互斥又互补的那种“史无前例的”特殊关系以外,不可能再有任 何别的内在联系,特别是,不可能用任何方式把它们结合成,个无 矛盾的统一体(统一图景),这是一般人很难想像和很难接受的一 种全新的关系。第二,尽管“互补性”的萌芽式概念早已存在于玻 尔的思想之中,但是它的公开提出却是在新量子力学的数学表述 形式已经基本上完成,而海森伯也已提出了他的测不准原理以后 (1927年)。玻尔受到量子力学的诞生和发展的很大鼓舞(他自己 正是这一惊人发展的“总指挥”),才重新整理了自己的思路,向国 际物理学界发表了著名的“科莫演讲”,正式提出了“互补性”的概 念。因此,这一新概念从一开始就是和量子物理学结合得很紧的, 它在量子理论(包括量子力学和量子场论)的物理诠释中得到了最 成功的应用。玻尔在以后的许多场合下都曾着重指出,“互补性” 这一思想在量子力学中有其最简明的应用。因此,不熟悉量子理 论那一套形式表述,就连最简明形式的“互补性”观念也理解不了, 而一般的“专业哲学家”对量子理论的熟悉程度大概充其量也就和 我这种外行家伙对“传统哲学”的熟悉程度不相上下。他们也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