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译 序 ix 的,但猎获物却曾经肯定是很可怜的。尽管在玻尔的笔记中 有时可以找到关于古希腊人、斯宾诺莎、笛卡尔、休谟、贝克 莱、玻斯考维契、马赫乃至康德的顺便提及,但却设有任何证 据表明这些哲学家曾对玻尔的工作发生过任何直接的影响。 也有过一些努力,想把玻尔分类为实用论者、唯心论者、实证 论者,如此等等。胡克尔在玻尔身上试穿了不下七种哲学外 衣,结果却承认了错误鉴定的危险性。只要人们还把玻尔说 成一位哲学家,人们就必须从一开始就承认他的哲学是独家 的(sui generis)。 霍纳也很有趣。他写过一篇长文,只因听到海森伯一句话(说玻尔 primarily是哲学家)就找了许多证据来力图把玻尔定性为“超验论 者”。我对他那篇长文甚不同意(尽管曾经翻译了它),因此当在丹 麦看到他这本书时就根本没有注意它,想不到他竟大大改正了自 己的观点。 否尔霍耳特表示完全同意霍纳的观点。就是说,他认为“互补 性”概念完全是玻尔本人的独创,在以前的任何哲学流派中都找不 到可信的“根源”,别的哲学家们在玻尔的“互补性”思想的发生和 发展中也没有对他发生过任何值得一提的“影响”。例如基尔凯郭 尔,玻尔在上大学时确实读过他的书,但那只是欣赏了他的文笔和 机智,而不是欣赏他的观点,而且从那以后就不曾提到过他。这 一点曾经得到玻尔夫人的亲口证实。至于玻尔和赫弗丁的来往, 否尔霍耳特认为那只是师生和世交的往还(赫弗丁是玻尔父亲的 好友),而不是哲学观点上的共鸣。这一点,有人却不同意。译者 曾亲眼看到否尔霍耳特和一位丹麦青年在玻尔研究所的午餐室中

译 序 展开了辩论。但我觉得,那是他们对于什么是“影响”抱有不同的 理解。如果只考虑对于“互补性”思想的影响,恐怕否尔霍耳特还 是对的。 否尔霍耳特承认自己不懂物理学,但他还是写了一本论述玻 尔的物理学的书。那本书用的是丹麦文,我看不懂,但我相信他又 一次强调了玻尔在物理学方面的“独创性”。这也完全是对的。如 果物理学家们认真考虑一下,我相信多数人也会相信这种独创性。 现在人们对玻尔的原子结构理论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觉得那里边 有什么“了不起”了。但是如果任何稍微有点头脑的人结合当时的 历史形势仔细想一想,而又并未抱有极端的偏见的话,他就会承认 那种理论确实是十分“独创的”(与众不同而没有先例)。这表明玻 尔很擅于“独创”,因此如果认为他在哲学方面也会搞出些“独创” 的东西来,那也不会是什么大言欺世的。 至于说玻尔是唯心论者、实证论者还是什么别的“论者”,那也 应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按照霍纳的说法,有一位胡克尔先 生曾经让玻尔试穿了七种“哲学外衣”,结果发现全都不合体。那 么,当年我们那种在玻尔头上乱扣帽子的作法也就越发感到汗颜 不已了。在这方面,有一段爱因斯坦的言论很能说明问题。他在 晚年写的一篇“自述”中谈到了“科学家”(他)的哲学体系,那其实 是他的“夫子之自道”。他写道: “他〔即科学家,或爱因斯坦自己)在系统的认识论学者 眼中必然显现为一个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他显现为一个 实在论者,因为他企图描述一个独立于知觉动作的世界;显现 为一个唯心论者,因为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人类精神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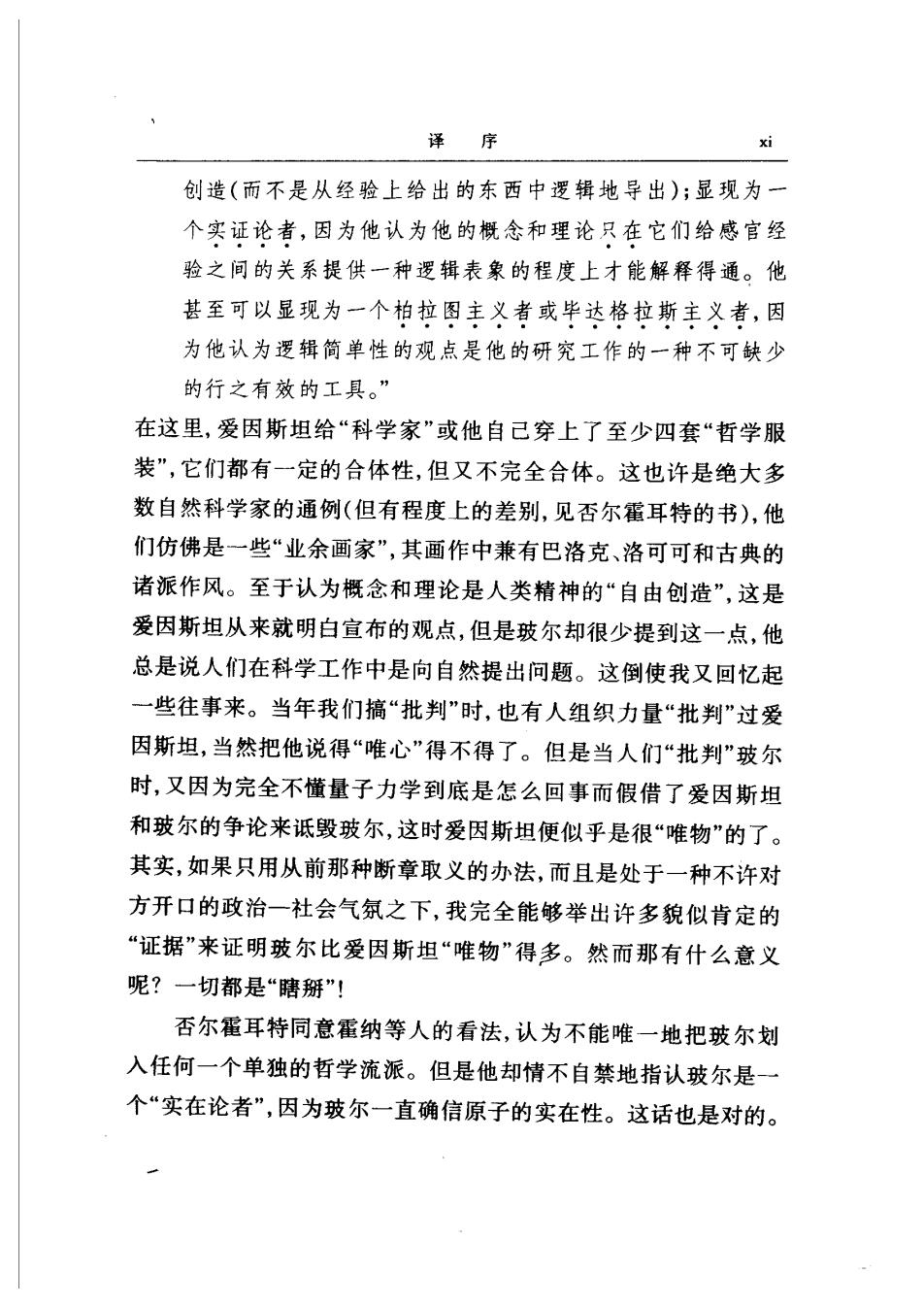
译序 xi 创造(而不是从经验上给出的东西中逻辑地导出);显现为一 个实证论者,因为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在它们给感官经 验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逻辑表象的程度上才能解释得通。他 甚至可以显现为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毕达格拉斯主义者,因 为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的一种不可缺少 的行之有效的工具。” 在这里,爱因斯坦给“科学家”或他自己穿上了至少四套“哲学服 装”,它们都有一定的合体性,但又不完全合体。这也许是绝大多 数自然科学家的通例(但有程度上的差别,见否尔霍耳特的书),他 们仿佛是一些“业余画家”,其画作中兼有巴洛克、洛可可和古典的 诸派作风。至于认为概念和理论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这是 爱因斯坦从来就明白宣布的观点,但是玻尔却很少提到这一点,他 总是说人们在科学工作中是向自然提出问题。这倒使我又回忆起 一些往事来。当年我们搞“批判”时,也有人组织力量“批判”过爱 因斯坦,当然把他说得“唯心”得不得了。但是当人们“批判”玻尔 时,又因为完全不懂量子力学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假借了爱因斯坦 和玻尔的争论来诋毁玻尔,这时爱因斯坦便似乎是很“唯物”的了。 其实,如果只用从前那种断章取义的办法,而且是处于一种不许对 方开口的政治一社会气氛之下,我完全能够举出许多貌似肯定的 “证据”来证明玻尔比爱因斯坦“唯物”得多。然而那有什么意义 呢?一切都是“瞎掰”! 否尔霍耳特同意霍纳等人的看法,认为不能唯一地把玻尔划 入任何一个单独的哲学流派。但是他却情不自禁地指认玻尔是一 个“实在论者”,因为玻尔一直确信原子的实在性。这话也是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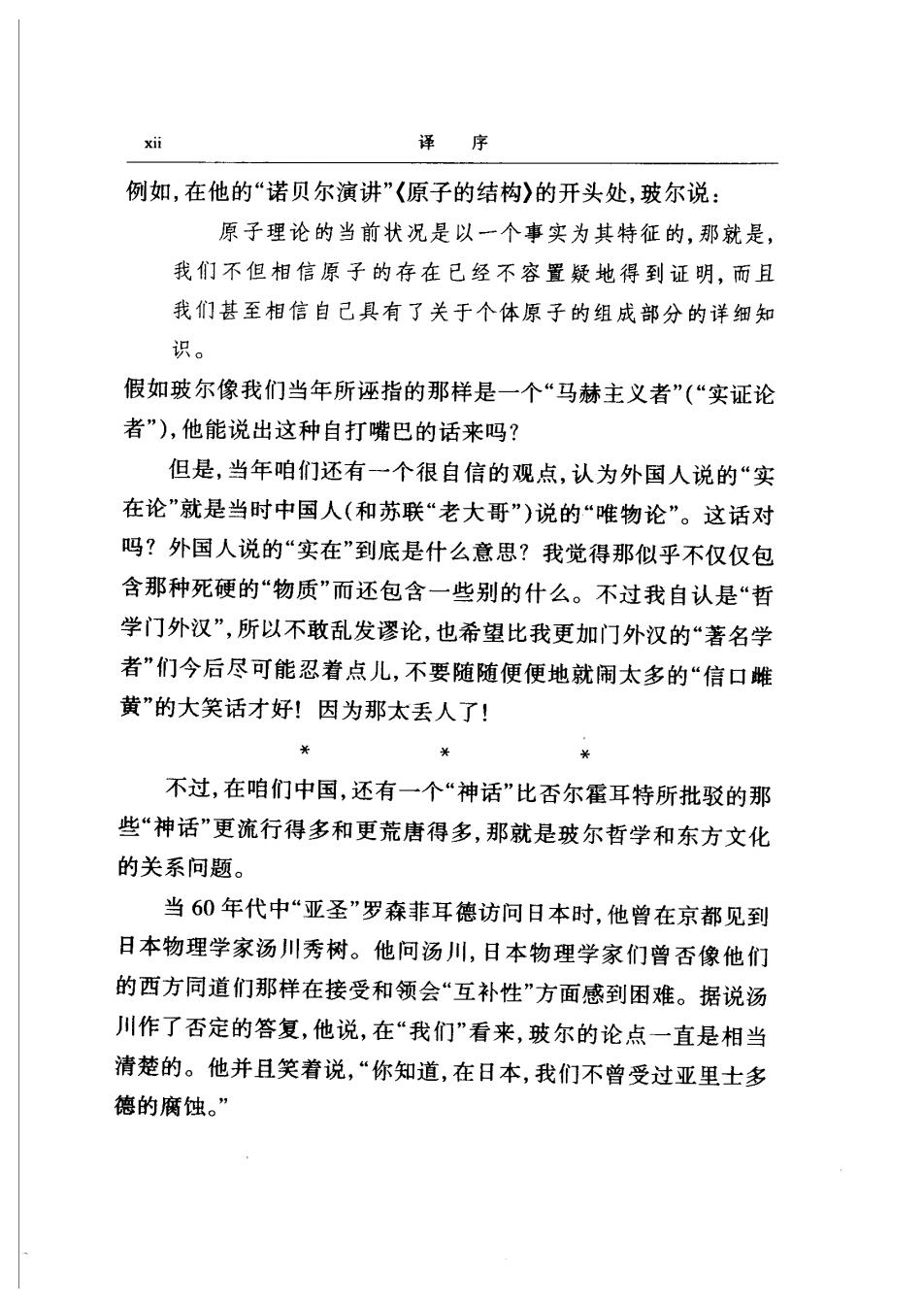
xii 译序 例如,在他的“诺贝尔演讲”《原子的结构》的开头处,玻尔说: 原子理论的当前状况是以一个事实为其特征的,那就是, 我们不但相信原子的存在已经不容置疑地得到证明,而且 我们甚至相信自己具有了关于个体原子的组成部分的详细知 识。 假如玻尔像我们当年所诬指的那样是一个“马赫主义者”(“实证论 者”),他能说出这种自打嘴巴的话来吗? 但是,当年咱们还有一个很自信的观点,认为外国人说的“实 在论”就是当时中国人(和苏联“老大哥”)说的“唯物论”。这话对 吗?外国人说的“实在”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那似乎不仅仅包 含那种死硬的“物质”而还包含一些别的什么。不过我自认是“哲 学门外汉”,所以不敢乱发谬论,也希望比我更加门外汉的“著名学 者”们今后尽可能忍着点儿,不要随随便便地就闹太多的“信口雌 黄”的大笑话才好!因为那太丢人了! 不过,在咱们中国,还有一个“神话”比否尔霍耳特所批驳的那 些“神话”更流行得多和更荒唐得多,那就是玻尔哲学和东方文化 的关系问题。 当60年代中“亚圣”罗森菲耳德访问日本时,他曾在京都见到 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他问汤川,日本物理学家们曾否像他们 的西方同道们那样在接受和领会“互补性”方面感到困难。据说汤 川作了否定的答复,他说,在“我们”看来,玻尔的论点一直是相当 清楚的。他并且笑着说,“你知道,在日本,我们不曾受过亚里士多 德的腐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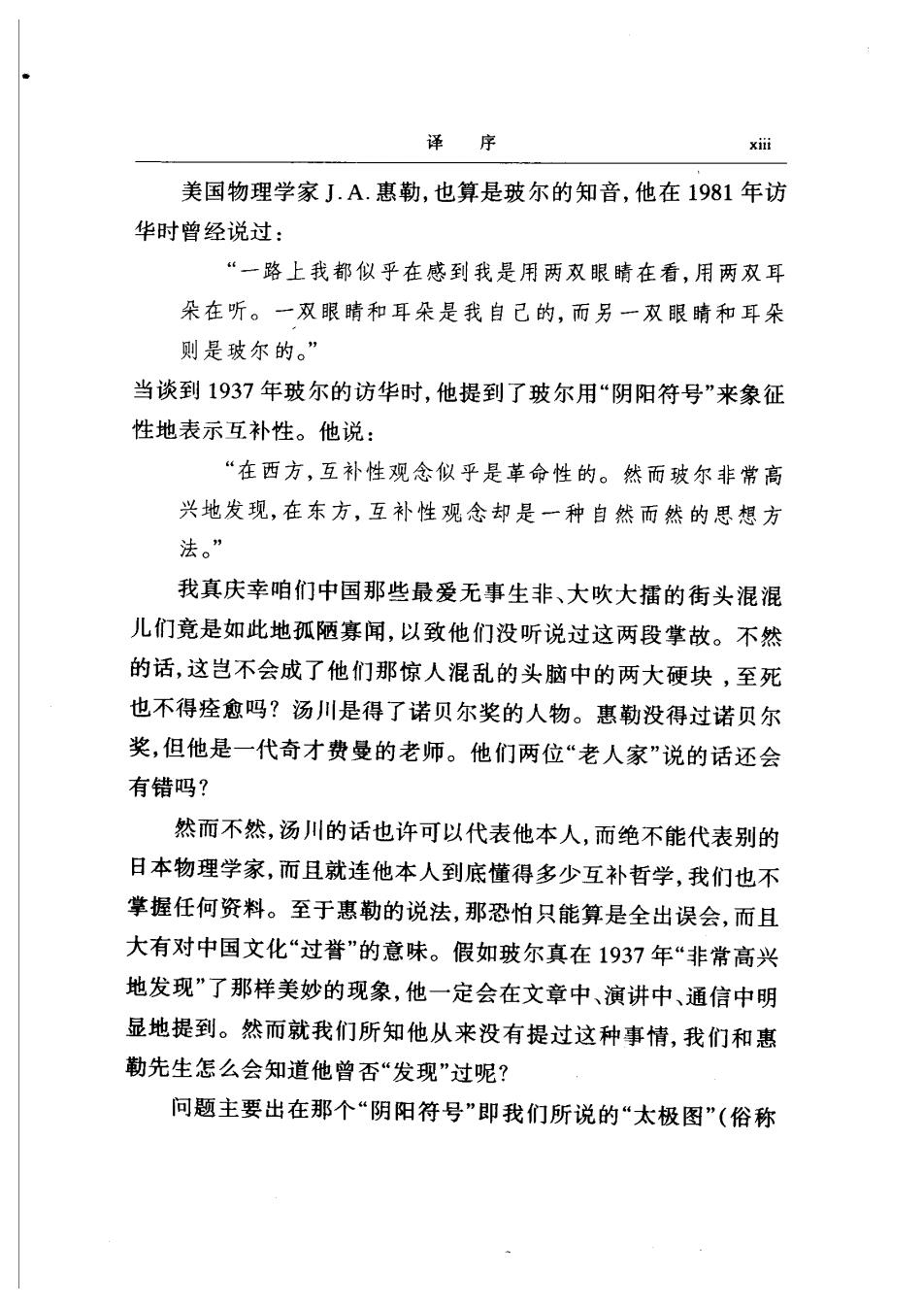
译序 xiii 美国物理学家J.A.惠勒,也算是玻尔的知音,他在1981年访 华时曾经说过: “一路上我都似乎在感到我是用两双眼睛在看,用两双耳 朵在听。一双眼睛和耳朵是我自己的,而另一双眼睛和耳朵 则是玻尔的。” 当谈到1937年玻尔的访华时,他提到了玻尔用“阴阳符号”来象征 性地表示互补性。他说: “在西方,互补性观念似乎是革命性的。然而玻尔非常高 兴地发现,在东方,互补性观念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思想方 法。” 我真庆幸咱们中国那些最爱无事生非、大吹大擂的街头混混 儿们竟是如此地孤陋寡闻,以致他们没听说过这两段掌故。不然 的话,这岂不会成了他们那惊人混乱的头脑中的两大硬块,至死 也不得痊愈吗?汤川是得了诺贝尔奖的人物。惠勒没得过诺贝尔 奖,但他是一代奇才费曼的老师。他们两位“老人家”说的话还会 有错吗? 然而不然,汤川的话也许可以代表他本人,而绝不能代表别的 日本物理学家,而且就连他本人到底懂得多少互补哲学,我们也不 掌握任何资料。至于惠勒的说法,那恐怕只能算是全出误会,而且 大有对中国文化“过誉”的意味。假如玻尔真在1937年“非常高兴 地发现”了那样美妙的现象,他一定会在文章中、演讲中、通信中明 显地提到。然而就我们所知他从来没有提过这种事情,我们和惠 勒先生怎么会知道他曾否“发现”过呢? 问题主要出在那个“阴阳符号”即我们所说的“太极图”(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