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公共财政与公共逸择两种囊然对主的国家观 义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平民主义者旗帜鲜明地反对东部地区的当权 派,强盗般的工业巨头和金融赛头,同时也将控制国家的政治视为 己任。我发现早期阅读的大量书籍几乎都是成堆成堆的19世纪90 年代宣传平民主义论的小册子。我一贯支持伟大的密谋论①的发展 者情感真警的呼吁要求也就不足为怪了。为二战作准备的军事训练 期间我亲身感受到我本人就是歧视南方人的牺牲品,这种个人经历 强化了我的上述态度。 三、治学之路 仅仅在二战之后我才真正成为名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不论你 在那种意义上理解“学院派经济学家”这个术语。在1946年1月 我作为一名坚定的“自由社会主义者”(这个称谓也许看起来有点 自相矛盾,尽管在魏玛时期的德国有个政党采用了这个标签)进人 了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我坚信对于个人自由的政治性约束应降到 最低限度,在这方面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只有 政治行动才能打破和控制权力的集中,而集中的权力总是力图控制 经济生活。 回顾过去,我现在意识到,相当简单,当时我对于市场的协调 特性几乎一无所知。因此,一点都不奇怪,当口才雄辩的奈特教授 向我阐述市场经济的这一特性时,我很容易明智地接受他的观点。 奈特使我认识到市场的作用,很快他也成了我的榜样。因为奈待就 不是一个受思想体系左右的人一一实际上,他曾经写过一篇最富洞 察力的批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论文(奈特,1935),因此他的教 导对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以回顾的眼光来看,我的世界观的发生 变化同样也不令人惊奇,一且我完全理解了通过市场运行自发协调 ①密谋论是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一个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有人密谋策划。一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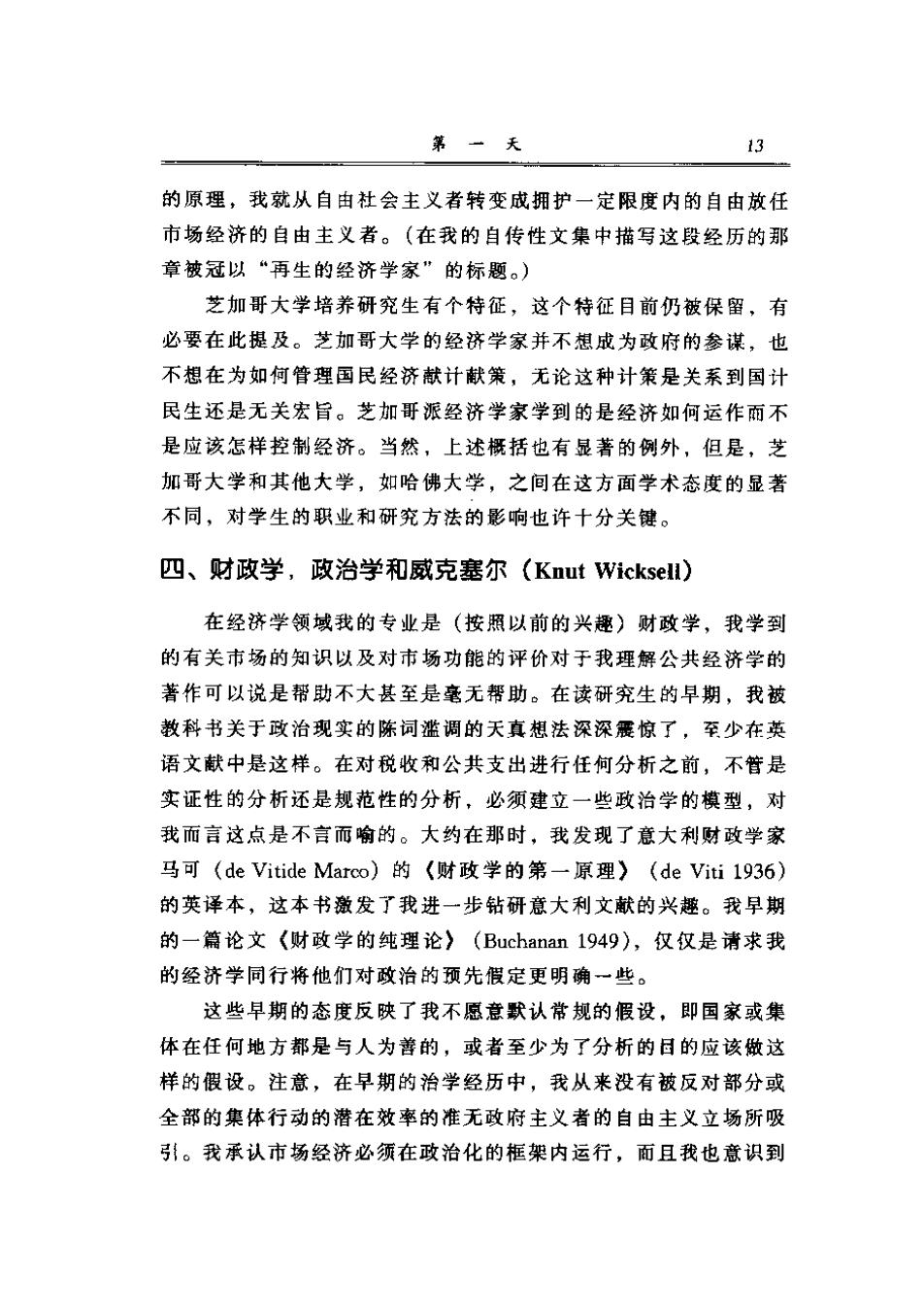
第一天 13 的原理,我就从自由社会主义者转变成拥护一定限度内的自由放任 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者。(在我的自传性文集中描写这段经历的那 章被冠以“再生的经济学家”的标题。) 芝加哥大学培养研究生有个特征,这个特征目前仍被保留,有 必要在此提及。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并不想成为政府的参谋,也 不想在为如何管理国民经济献计献策,无论这种计策是关系到国计 民生还是无关宏旨。芝加哥派经济学家学到的是经济如何运作而不 是应该怎样控制经济。当然,上述概括也有显著的例外,但是,芝 加哥大学和其他大学,如哈佛大学,之间在这方面学术态度的显著 不同,对学生的职业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也许十分关健。 四、财政学,政治学和威克塞尔(Knut Wickse) 在经济学领域我的专业是(按照以前的兴趣)财政学,我学到 的有关市场的知识以及对市场功能的评价对于我理解公共经济学的 著作可以说是帮助不大甚至是毫无帮助。在读研究生的早期,我被 教科书关于政治现实的陈词滥调的天真想法深深震惊了,至少在英 语文献中是这样。在对税收和公共支出进行任何分析之前,不管是 实证性的分析还是规范性的分析,必须建立一些政治学的模型,对 我而言这点是不言而喻的。大约在那时,我发现了意大利财政学家 马可(de Vitide Marco)的(财政学的第一原理)(de Viti1936 的英译本,这本书激发了我进一步钻研意大利文献的兴趣。我早期 的一篇论文《财政学的纯理论〉(Buchanan1949),仅仅是请求我 的经济学同行将他们对政治的预先假定更明确一些。 这些早期的态度反映了我不愿意默认常规的假设,即国家或集 体在任何地方都是与人为善的,或者至少为了分析的目的应该做这 样的假设。注意,在早期的治学经历中,我从来没有被反对部分或 全部的集体行动的潜在效率的准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由主义立场所吸 引。我承认市场经济必须在政治化的框架内运行,面且我也意识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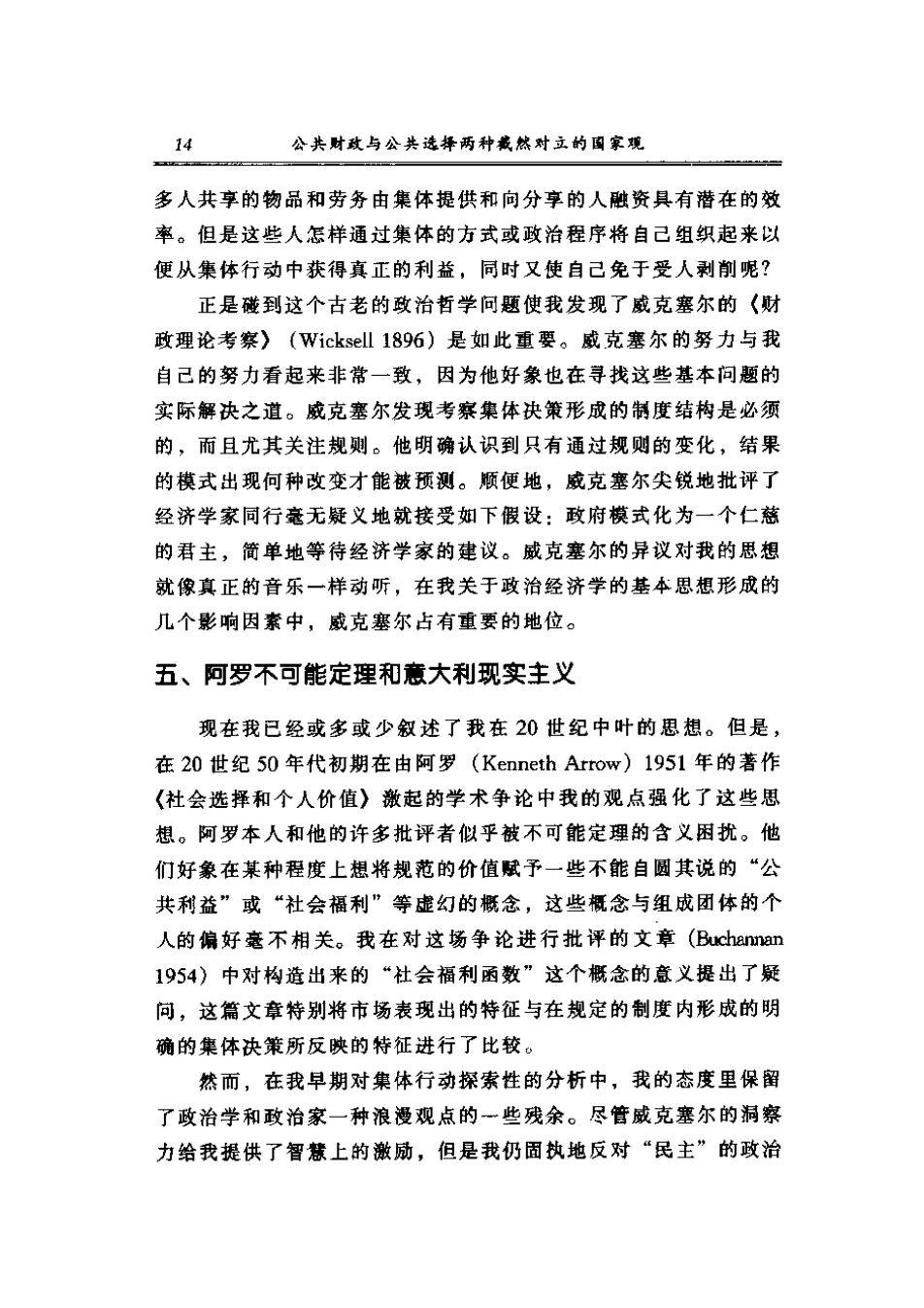
14 公共财政与公共途排两种煮然对立的四家缆 多人共享的物品和劳务由集体提供和向分享的人融资具有潜在的效 率。但是这些人怎样通过集体的方式或政治程序将自己组织起来以 便从集体行动中获得真正的利益,同时又使自己免于受人剥削呢? 正是碰到这个古老的政治哲学问题使我发现了威克塞尔的〈财 政理论考察)(Wicksell1896)是如此重要。威克塞尔的努力与我 自己的努力看起来非常一致,因为他好象也在寻找这些基本问题的 实际解决之道。威克塞尔发现考察集体决策形成的制度结构是必须 的,而且尤其关注规则。他明确认识到只有通过规则的变化,结果 的模式出现何种改变才能被预测。顺便地,威克塞尔尖锐地批评了 经济学家同行毫无疑义地就接受如下假设:政府模式化为一个仁慈 的君主,简单地等待经济学家的建议。威克塞尔的异议对我的思想 就像真正的音乐一样动听,在我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形成的 几个影响因素中,威克塞尔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阿罗不可能定理和意大利现实主义 现在我已经或多或少叙述了我在20世纪中叶的思想。但是】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由阿罗(Kenneth Arrow)1951年的著作 《杜会选择和个人价值〉激起的学术争论中我的观点强化了这些思 想。阿罗本人和他的许多批评者似乎被不可能定理的含义困扰。他 们好象在某种程度上想将规范的价值赋予一些不能自圆其说的“公 共利益”或“社会福利”等虚幻的概念,这些概念与组成团体的个 人的偏好意不相关。我在对这场争论进行批评的文章(Buchannan 1954)中对构造出来的“社会福利函数”这个概念的意义提出了疑 问,这篇文章特别将市场表现出的特征与在规定的制度内形成的明 确的集体决策所反映的特征进行了比较。 然而,在我早期对集体行动探素性的分析中,我的态度里保留 了政治学和政治家一种浪漫观点的一些残余。尽管威克塞尔的洞察 力给我提供了智糠上的激励,但是我仍固执地反对“民主”的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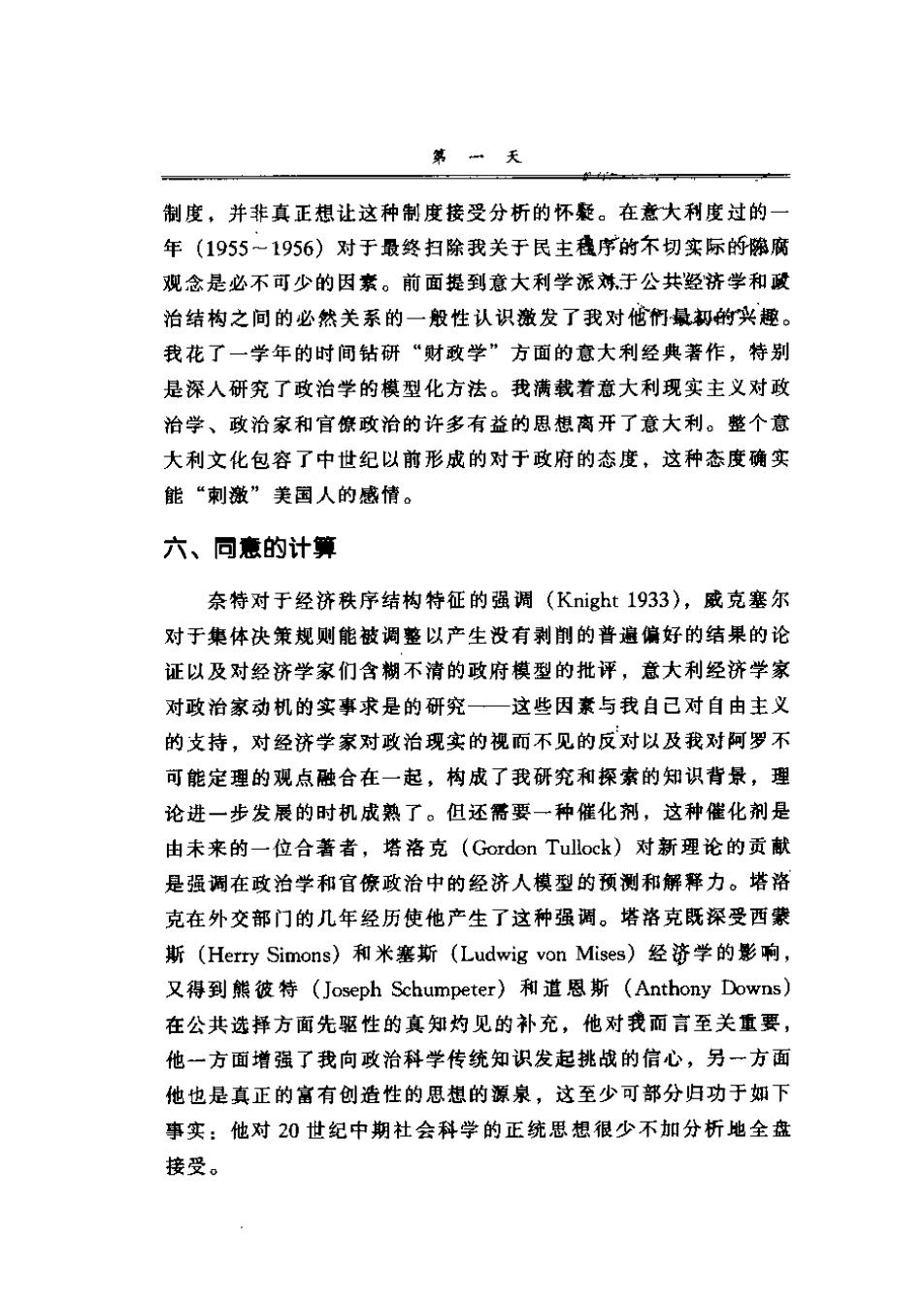
第一天 制度,并非真正想让这种制度接受分析的怀疑。在意大利度过的 年(1955一1956)对于最终扫除我关于民主序的不切实际的隙腐 观念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前面提到意大利学派裤于公共经济学和暖 治结构之间的必然关系的一般性认识激发了我对他们最初的兴趣。 我花了一学年的时间钻研“财政学”方面的意大利经典著作,特别 是深人研究了政治学的模型化方法。我满载着意大利现实主义对政 治学、政治家和官僚政治的许多有益的思想离开了意大利。整个意 大利文化包容了中世纪以前形成的对于政府的态度,这种态度确实 能“刺激”美国人的感情。 六、问意的计算 奈特对于经济秩序结构特征的强调(Knight1933),威克塞尔 对于集体决策规则能被调整以产生没有剥削的普避偏好的结果的论 证以及对经济学家们含糊不清的政府模型的批评,意大利经济学家 对政治家动机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这些因素与我自己对自由主义 的支持,对经济学家对政治现实的视而不见的反对以及我对阿罗不 可能定理的观点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我研究和探索的知识背景,理 论进一步发展的时机成熟了。但还需要一种催化剂,这种催化剂是 由未来的一位合著者,塔洛克(Gordon Tullock)对新理论的贡献 是强调在政治学和官僚政治中的经济人棋型的预测和解释力。塔洛 克在外交部门的几年经历使他产生了这种强调。塔洛克既深受西蒙 斯(Herry Simons))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经济学的影响, 又得到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和道恩斯(Anthony Downs) 在公共选择方面先驱性的真知灼见的补充,他对我而言至关重要, 他一方面增强了我向政治科学传统知识发起挑战的信心,另一方面 他也是真正的富有创造性的思想的源泉,这至少可部分归功于如下 事实:他对20世纪中期社会科学的正统思想很少不加分析地全盘 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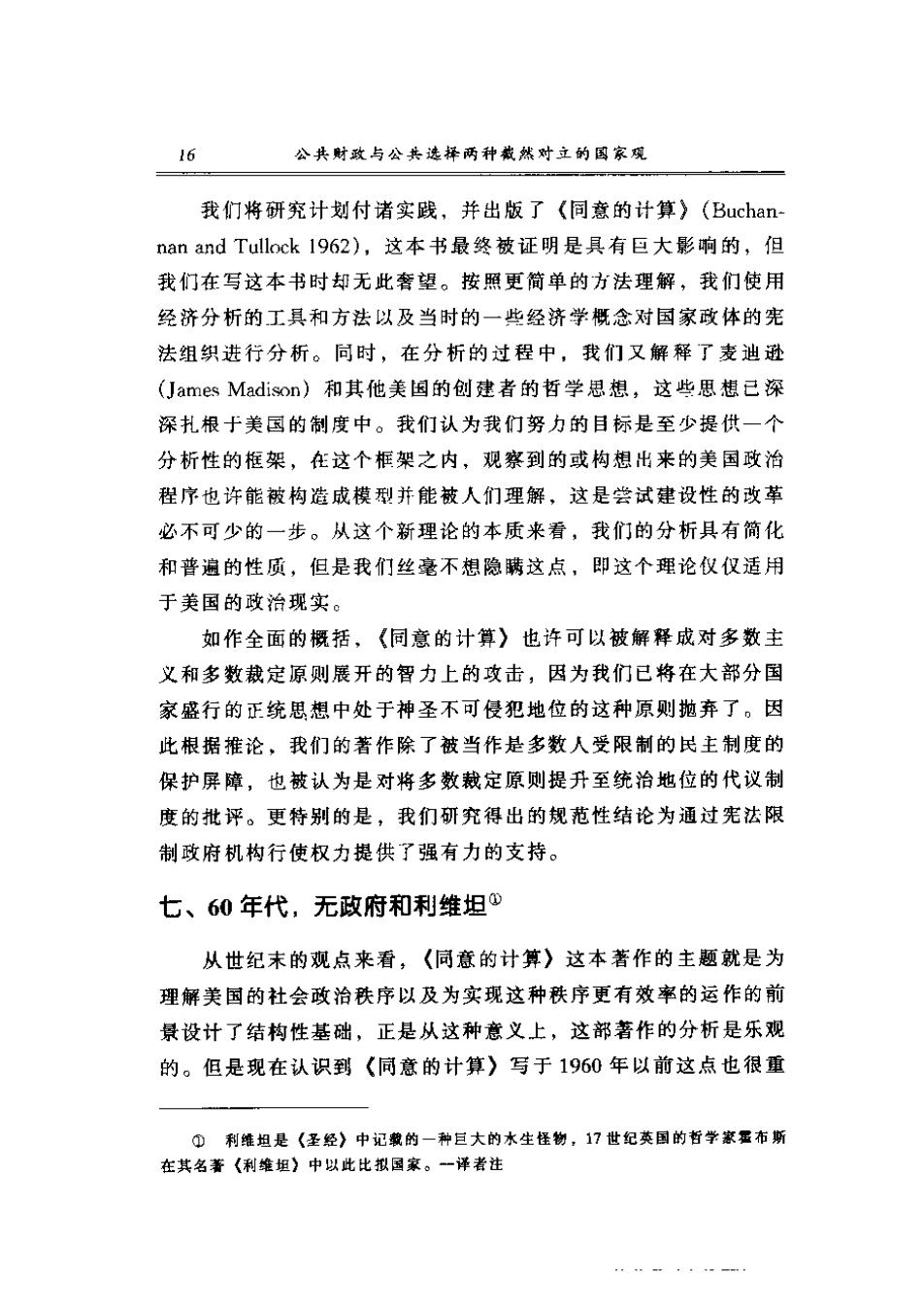
16 公共财政与公其速择两种戴然对立的国家观 我们将研究计划付渚实践,并出版了(同意的计算)(Buchan- nan and Tullock I962),这本书最终被证明是具有巨大影响的,但 我们在写这本书时却无此奢望。按照更简单的方法理解,我们使用 经济分析的工具和方法以及当时的一些经济学概念对国家政体的宪 法组织进行分析。同时,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又解释了麦迪逊 (James Madison)和其他美国的创建者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已深 深扎根于美国的制度中。我们认为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至少提供一个 分析性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之内,观察到的或构想出来的美国政治 程序也许能被构造成模型并能被人们理解,这是尝试建设性的改革 必不可少的一步。从这个新理论的本质来看,我们的分析具有简化 和普遍的性质,但是我们丝毫不想隐藕这点,即这个理论仪仅适用 于美国的改治现实。 如作全面的橛括,《同意的计算)也许可以被解释成对多数主 义和多数裁定原则展开的智力上的攻击,因为我们已将在大部分国 家盛行的正统思想中处于神圣不可侵犯地位的这种原则抛弃了。因 此根据推论,我们的著作除了被当作是多数人受限制的民主制度的 保护屏障,也被认为是对将多数裁定原则提升至统治地位的代议制 度的批评。更待别的是,我们研究得出的规范性结论为通过宪法限 制政府机构行使权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七、60年代,无政府和利维坦① 从世纪末的观点来看,〈同意的计算〉这本著作的主题就是为 理解美国的社会政治秩序以及为实现这种秩序更有效率的运作的前 景设计了结构性基础,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这部著作的分析是乐观 的。但是现在认识到《同意的计算〉写于1960年以前这点也很重 ①利维坦是(圣经〉中记的一种巨大的水生怪物,17世纪英国的哲学布斯 在其名著《利维坦》中以此比拟国家。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