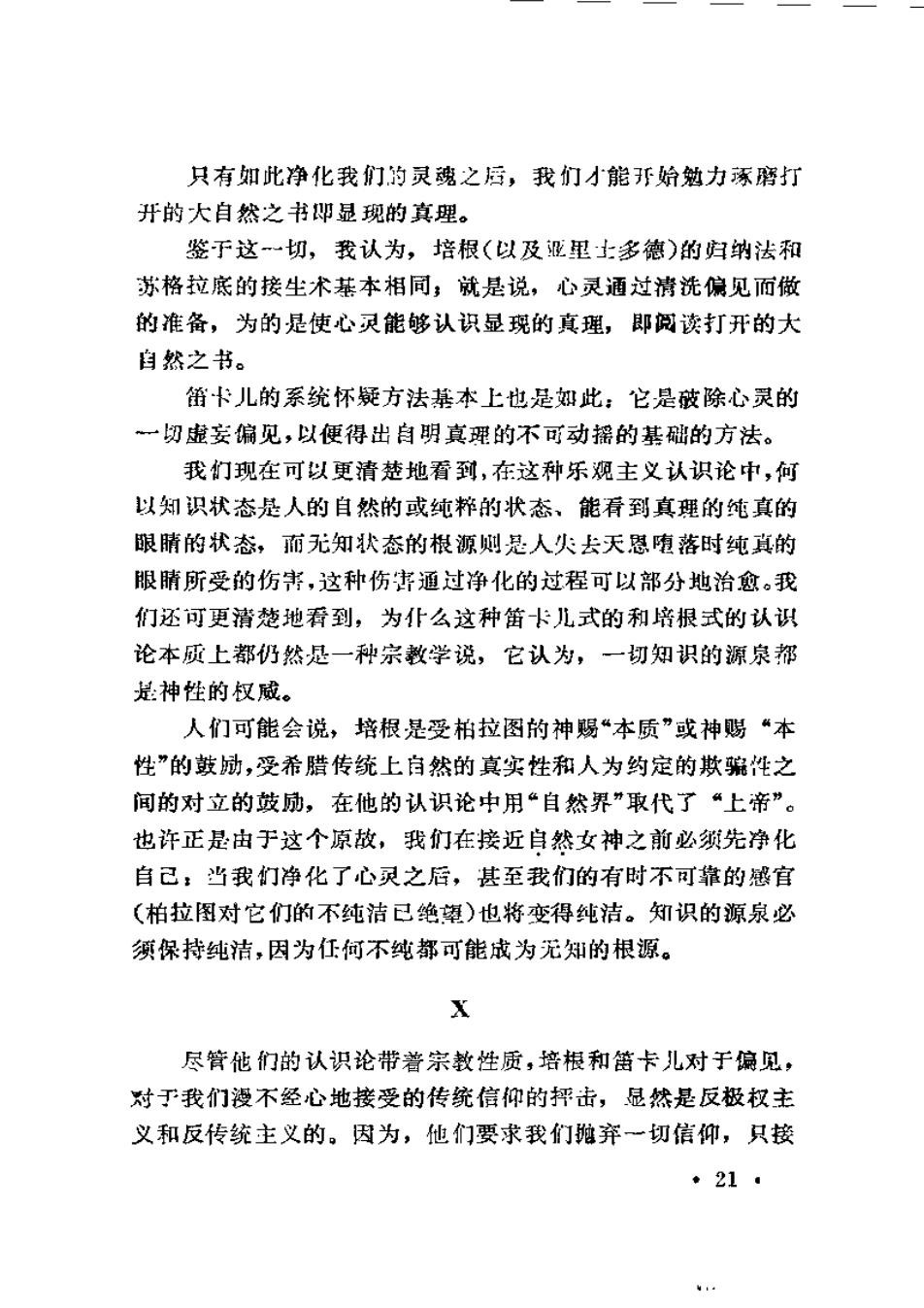
只有如此净化我们的灵魂之运,我们小能开始勉力涿磨打 开的大自然之书即显现的真理。 鉴子这一切,我认为,培根(以及里上多德)的归纳法和 苏格拉底的接生术基本相同,就是说,心灵通过清洗偏见而做 的推备,为的尾是使心灵能够认识显瑰的真理,即阅读打开的大 自然之书。 笛卡儿的系统怀疑方法基本上也是如此:它是破除心灵的 一切虚妄编见,以便得出自明真理的不可动摇的基础的方法。 我们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这种乐观主义认识论中,何 以知识状态是人的自然的或纯粹的状态、能看到真理的纯真的 眼睛的状态,而无知状态的根源则是人尖去天恩堕落时纯真的 眼睛所受的伤害,这种伤害通过净化的过程可以部分地治愈。我 们还可更清楚地看到,为仆么这种笛卡儿式的和培根式的认识 论本质上都仍然是一种宗教学说,它认为,一切知识的源泉都 是神性的权威。 人们可能会说,培根是受柏拉图的神赐“本质”或神赐“本 性”的鼓励,受希腊传统上自然的真实性和人为约定的欺骗性之 间的对立的鼓励,在他的认识论中用“自然界”取代了“上帝”。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故,我们在接近自然女神之前必须先净化 自己:当我们净化了心灵之后,甚至我们的有时不可靠的越官 (柏拉图对它们的不纯洁已绝望)也将变得纯洁。知识的源泉必 须保持纯洁,因为任何不纯都可能成为元知的根源。 X 尽管他们的认识论带者宗教性质,培根和笛卡儿对于偏见, 对于我们漫不经心地接受的传统信仰的抨击,显然是反极权主 义和反传统主义的。因为,他们要求我们抛弃一切信仰,只接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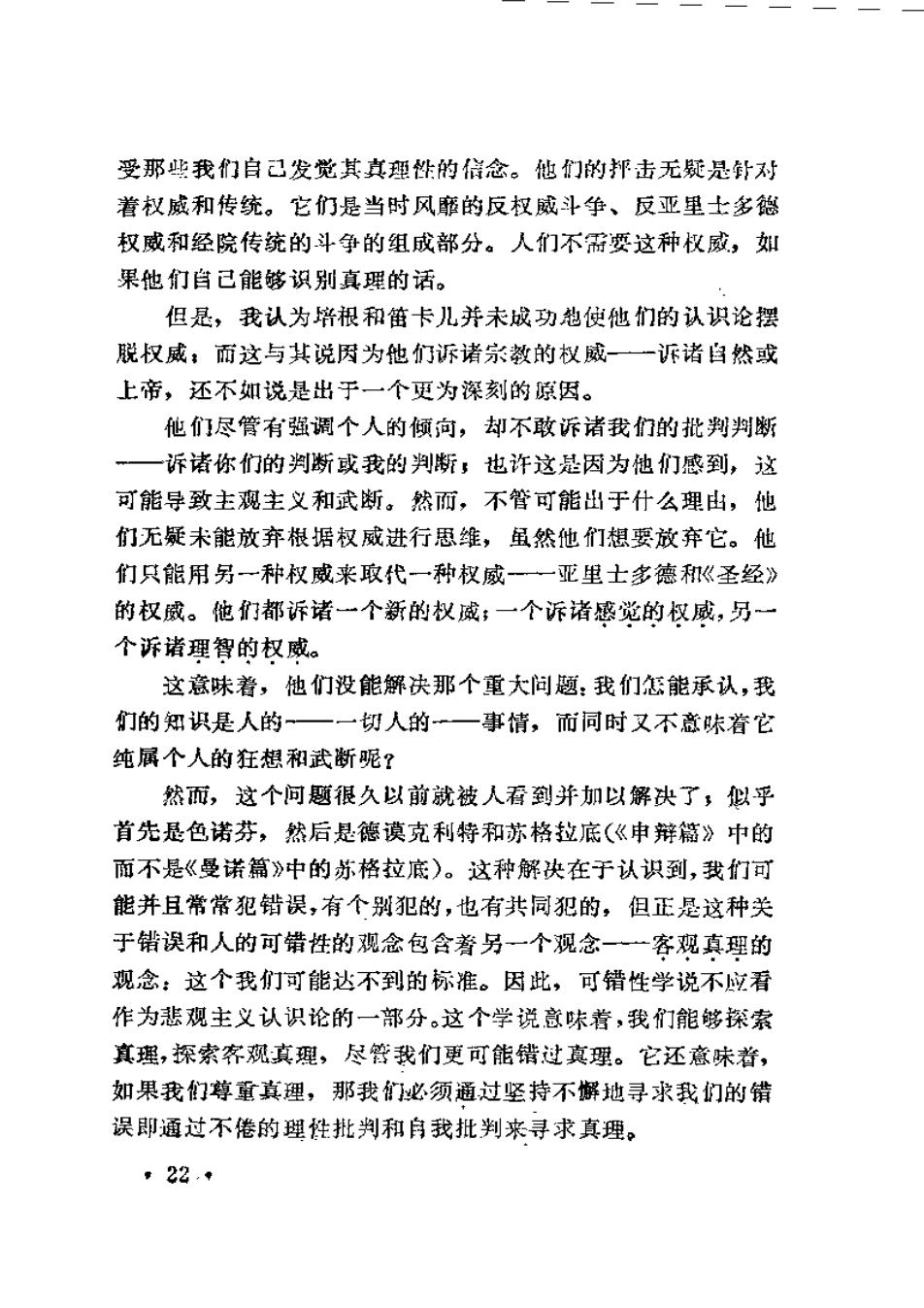
受那竖我们自己发觉其真理性的信念。他们的邦击无疑是针对 着权威和传统。它们是当时风靡的反权威斗争、反亚里士多德 权威和经院传统的斗争的组成部分。人们不需要这种权威,如 果他们自已能够识别真理的话。 但是,我认为培根和笛卡儿并未成功袍使他们的认识论摆 脱权威,而这与其说因为他们诉诸宗教的权威-一诉诸自然或 上帝,还不如说是出于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 他们尽管有强调个人的倾向,却不敢诉诸我们的批判判断 一诉诸你们的判断或我的判断,也许这是因为他们感到,这 可能导致主鸡主义和武断。然而,不管可能出于什么理出,他 们无疑未能放弃根据权威进行思维,虽然他们想要放弃它。他 们只能用另一种权威来取代一种权威一亚里士多德和《圣经》 的权威。他们都诉诸一个新的权诚,一个诉诸感觉的权威,另一 个诉诸理智的权威。 这意味着,他们没能解决那个重大问题:我们怎能承认,我 们的知识是人的一一切人的一事情,而同时又不意味着它 纯属个人的狂想和武断晚? 然而,这个问题很久以前就被人看到并加以解决了,似乎 首先是色诺芬,然后是德谟克利特和苏格拉底(《申辩篇》中的 面不是《曼诺篇》中的苏格拉底)。这种解决在于认识到,我们可 能并且常常犯错误,有个别犯的,也有共同犯的,但正是这种关 于错误和人的可错性的观念包含着另一个观念-一容观真理的 现念:这个我们可能达不到的标准。因此,可错性学说不应看 作为悲观主义认识论的一部分。这个学说意味着,我们能够探索 真理,探索客观真理,尽管我们更可能错过真理。它还意味着, 如果我们尊重真理,那我们必须通过坚持不懈地寻求我们的错 误即通过不倦的理性批判和闫我批判来寻求真理。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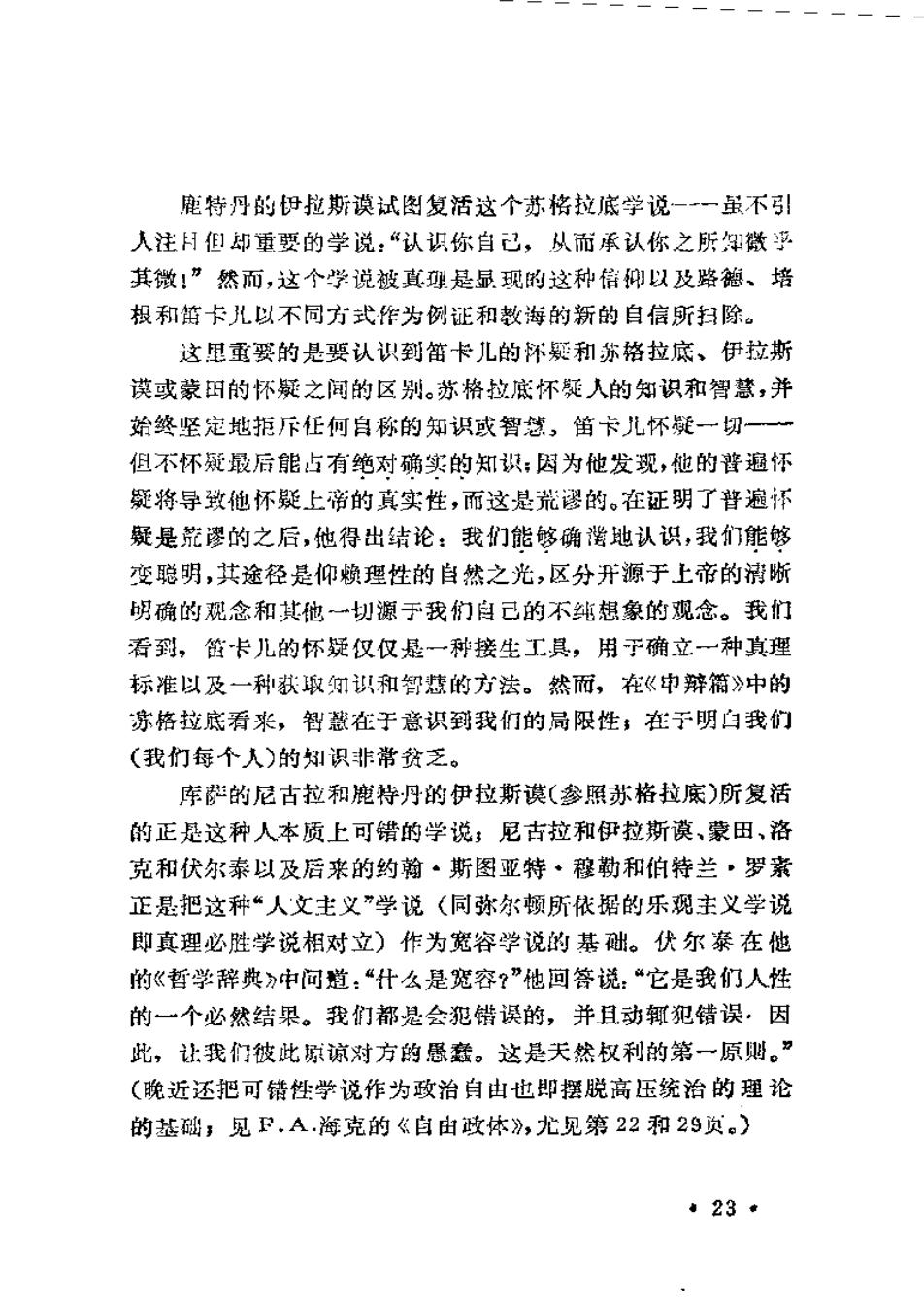
鹿特丹的伊拉漠试图复活这个苏将拉底学说一一一虽不引 人注鬥但却重要的学说:“认识你自己,从而承认你之所微乎 其微!”然而,这个学说被真理是显现的这种倍仰以及路德、培 根和笛卡儿以不同方式作为例证和教海的新的自信所扫除。 这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笛卡儿的怀疑和苏格拉底、伊拉斯 谟或蒙田的怀疑之间的区别。苏格拉底怀疑人的知识和智警,并 始终坚定地拒斥任何自称的知识或智德,笛卡怀疑一切一一 但不怀疑最后能占有绝对确实的知班:因为他发现,他的普遍怀 疑将导致他怀疑上帝的真实性,而这是荒谬的。在证明了普遍怀 疑是荒谬的之后,他得出结论:我们能够确凿地认识,我们能够 变聪明,其途径是仰赖理性的自然之光,区分开源于上帝的清晰 明确的规念和其他切源于我们自己的不纯想象的观念。我们 看到,笛卡儿的怀疑仅仅是一种接生工具,用于确立一种貞理 标准以及一种荻政知识和智慧的方法。然而,在《中辩篇》中的 苏格拉底看来,智藏在于意识到我们的局限性;在于明白我们 (我们每个人)的知识非常贫乏。 库萨的尼古拉和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参照苏格拉底)所复活 的正是这种人本质上可错的学说,尼古拉和伊拉斯谟、蒙田、洛 克和伏尔泰以及后来的约瀚·斯图亚特·穆勒和伯特兰·罗素 正是把这种“人文主义”学说(同弥尔顿所依据的乐观主义学说 即真理必胜学说相对立)作为宽容学说的基础。伏尔泰在他 的《暂学辞典》中问道:“什么是宽容?”他问答说:“它是我们人性 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都是会犯错误的,并且动辄犯错误·因 此,让我们彼此谅对方的愚蠢。这是天然权利的第一原则。” (晚近还把可错性学说作为政治自由也即摆脱高压统治的理论 的基础,见F.A.海克的《自由政体》,尤见第22和29负。)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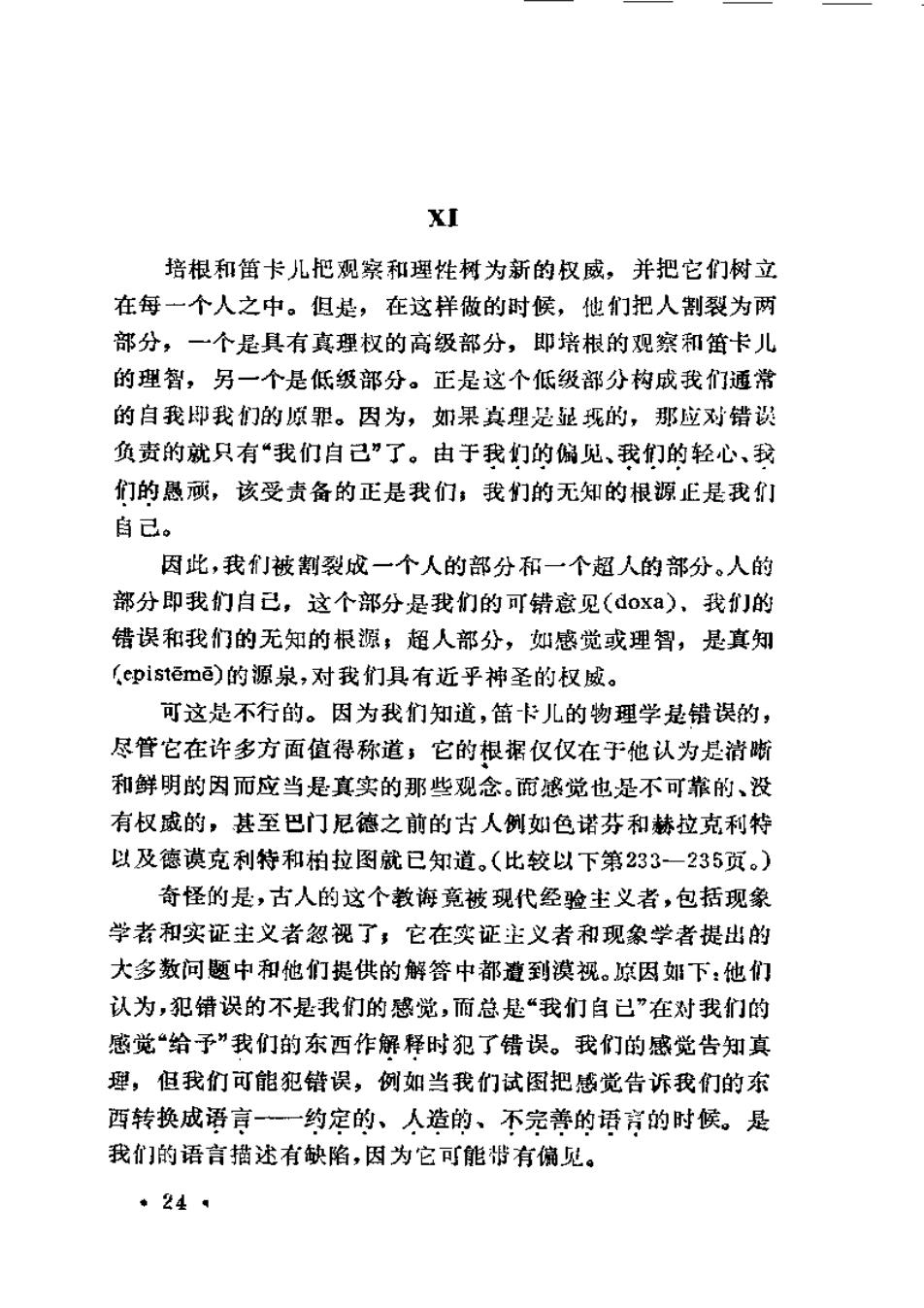
XI 培根和笛卡儿把观察和理性树为新的权威,并把它们树立 在每一个人之中。但是,在这拌做的时候,他们把人割裂为两 部分,一个是具有真理权的高级部分,即培根的观察和笛卡儿 的理智,另一个是低级部分。正是这个低级部分构成我们通常 的自我即我们的原罪。因为,如果真理是现的,那应对错误 负责的就只有“我们自已”了。由于我们的偏见、我们的轻心、我 们的感顽,该受责备的正是我们,我们的无知的根源E是我] 自己。 因此,我被割裂成一个人的部分和一个超人的部分。人的 部分即我们自已,这个部分是我们的可错意见(doxa)、我们的 错误和我们的无知的根源,超人部分,如感觉或理智,是真知 (episteme)的源泉,对我们具有近乎神圣的权威。 可这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知道,笛卡儿的物理学是错误的, 尽管它在许多方面值得称道,它的根据仅仅在于他认为是清瞒 和鲜明的因而应当是真实的那些观念。面感党也是不可靠的、没 有权威的,甚至巴门尼德之前的当人例如色诺芬和赫拉克利特 以及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就已知道。(比较以下第233一235页。) 奇怪的是,古人的这个教诲竞被现代经验主义者,包括现象 学者和实证主义者忽视了,它在实证主义者和现象学者提出的 大多数问题中和他们提供的解答中都遵到漠视。原因如下:他们 认为,犯错误的不是我们的感党,而总是“我们自已”在对我们的 感觉“给予”我们的东西作解释时犯了错误。我们的感觉告知真 理,但我们可能犯错误,例如当我们试图把感觉告诉我们的东 西转换成语言一约定的、人造的、不完善的语言的时候。是 我]的语言描述有缺陷,因为它可能特有偏见。 ◆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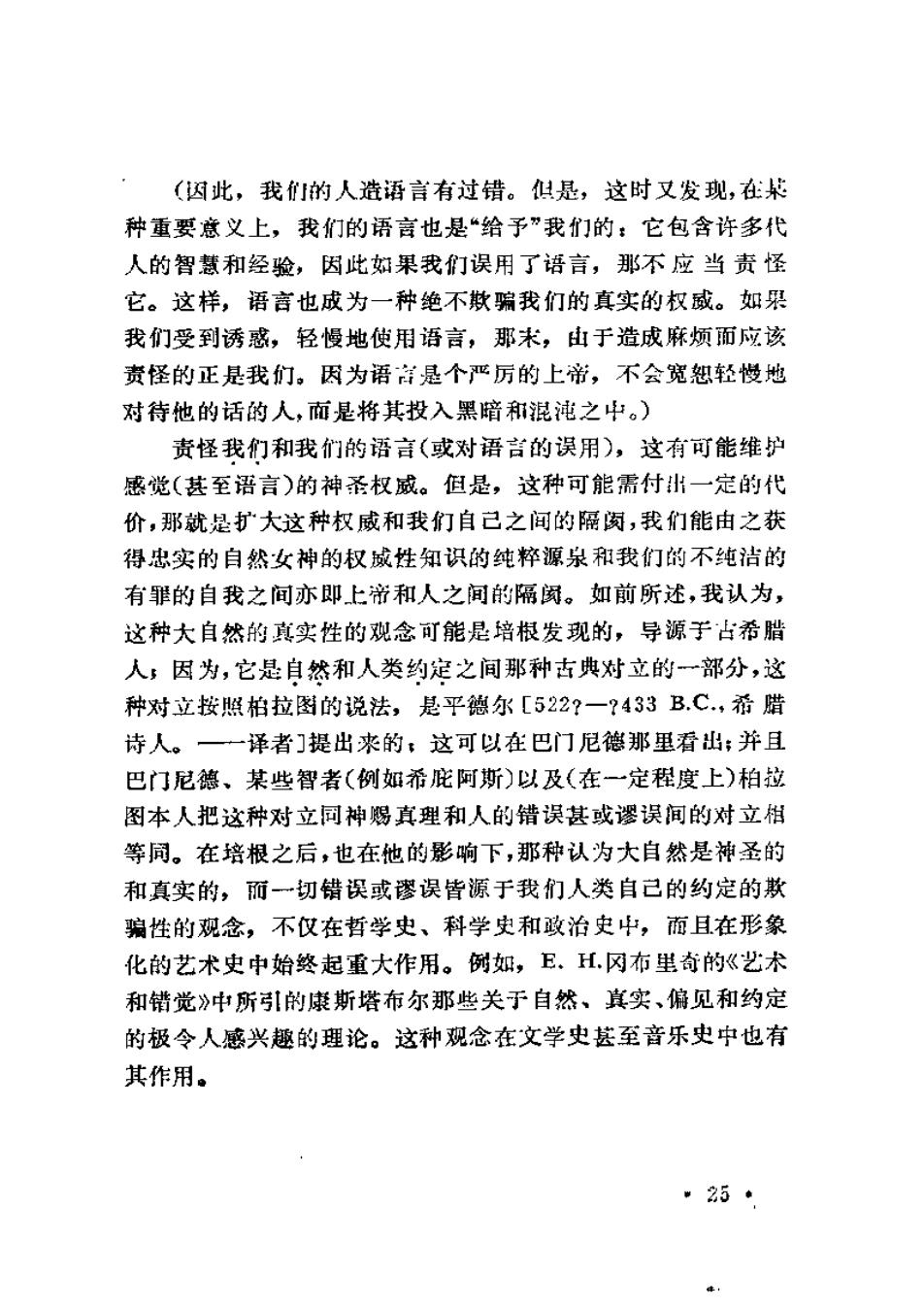
(因此,我的人造语言有过错。但是,这时又发现,在求 种重要意义上,我们的语言也是“给予”我们的:它包含许多代 人的智慧和经验,因此如果我们误用了语言,那不应当责怪 它。这样,语言也成为一种绝不欺骗我们的真实的权威。如果 我们受到诱惑,轻慢地使用语言,那米,由于造成麻烦而应该 责怪的正是我们。因为语苦是个严厉的上帝,不会宽恕轻慢地 对待他的话的人,而是将其投入黑暗和混沌之中。) 责怪我们和我们]的语言(或对语言的误用),这有可能维护 感觉(甚至语言)的神圣权威。但是,这种可能需付出一定的代 价,那就是扩大这种权威和我们自己之间的隔阂,我们能由之获 得忠实的自然女神的权城性知识的纯粹源泉和我们的不纯洁的 有罪的自我之间亦即上帝和人之间的隔阁。如前所述,我认为, 这种大自然的真实性的观念可能是培根发现的,导源子占希腊 人;因为,它是自然和人类约定之间那种古典对立的一部分,这 种对立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是平德尔[522?一?433B.C,希腊 诗人。一一译者]提出来的,这可以在巴门尼德那里看出;并且 巴门尼德、某些智者(例如希庇阿斯)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柏拉 图本人把这种对立同神赐真理和人的错误甚或谬误间的对立相 等同。在培根之后,也在他的影响下,那种认为大自然是神圣的 和真实的,而一切错误或谬误皆源于我们人类自己的约定的欺 骗性的观念,不仪在哲学史、科学史和政治史中,葡且在形象 化的艺术史中始终起重大作用。例如,E、H冈布里奇的《艺术 和错觉》中所引的康斯塔布尔那些关于自然、真实、偏见和约定 的极令人感兴趣的理论。这种观念在文学史甚至音乐史中也有 其作用。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