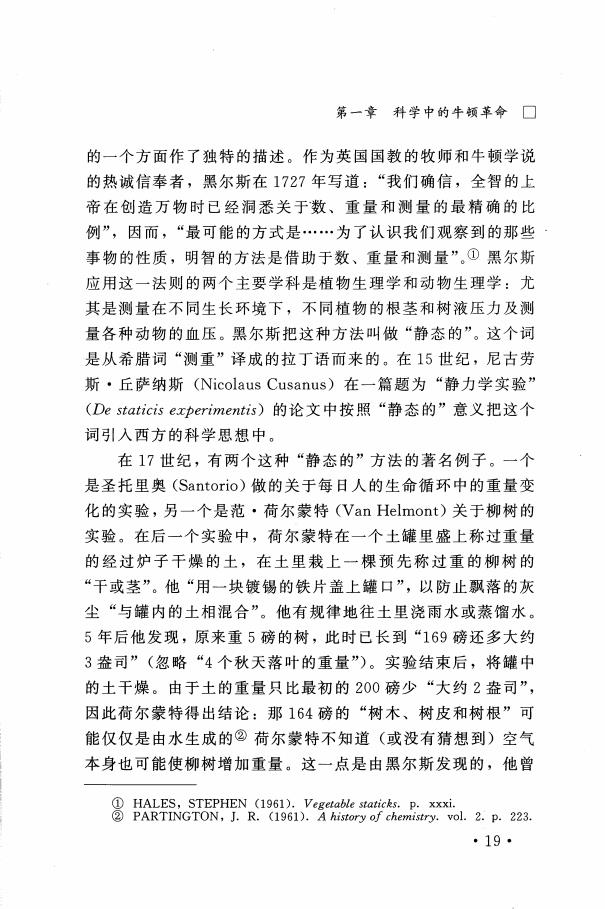
第一章科学中的牛顿革命□ 的一个方面作了独特的描述。作为英国国教的牧师和牛顿学说 的热诚信奉者,黑尔斯在1727年写道:“我们确信,全智的上 帝在创造万物时已经洞悉关于数、重量和测量的最精确的比 例”,因而,“最可能的方式是…为了认识我们观察到的那些 事物的性质,明智的方法是借助于数、重量和测量”。①黑尔斯 应用这一法则的两个主要学科是植物生理学和动物生理学:尤 其是测量在不同生长环境下,不同植物的根茎和树液压力及测 量各种动物的血压。黑尔斯把这种方法叫做“静态的”。这个词 是从希腊词“测重”译成的拉丁语而来的。在15世纪,尼古劳 斯·丘萨纳斯(Nicolaus Cusanus)在一篇题为“静力学实验” (De staticis ex中erimentis)的论文中按照“静态的”意义把这个 词引入西方的科学思想中。 在17世纪,有两个这种“静态的”方法的著名例子。一个 是圣托里奥(Santorio)做的关于每日人的生命循环中的重量变 化的实验,另一个是范·荷尔蒙特(Van Helmont)关于柳树的 实验。在后一个实验中,荷尔蒙特在一个土罐里盛上称过重量 的经过炉子干燥的土,在土里栽上一棵预先称过重的柳树的 “干或茎”。他“用一块镀锡的铁片盖上罐口”,以防止飘落的灰 尘“与罐内的土相混合”。他有规律地往土里浇雨水或蒸馏水。 5年后他发现,原来重5磅的树,此时已长到“169磅还多大约 3盎司”(忽略“4个秋天落叶的重量”)。实验结束后,将罐中 的土干燥。由于土的重量只比最初的200磅少“大约2盎司”, 因此荷尔蒙特得出结论:那164磅的“树木、树皮和树根”可 能仅仅是由水生成的②荷尔蒙特不知道(或没有猜想到)空气 本身也可能使柳树增加重量。这一点是由黑尔斯发现的,他曾 1 HALES,STEPHEN (1961).Vegetable staticks.p.xxxi. 2 PARTINGTON,J.R.(1961).A history of chemistry.vol.2.p.223.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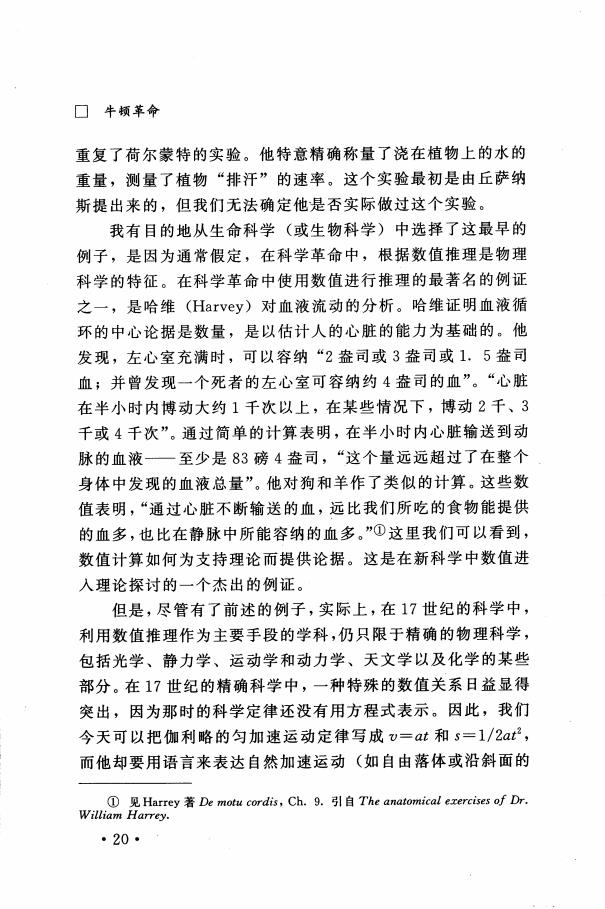
□牛顿苹命 重复了荷尔蒙特的实验。他特意精确称量了浇在植物上的水的 重量,测量了植物“排汗”的速率。这个实验最初是由丘萨纳 斯提出来的,但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否实际做过这个实验。 我有目的地从生命科学(或生物科学)中选择了这最早的 例子,是因为通常假定,在科学革命中,根据数值推理是物理 科学的特征。在科学革命中使用数值进行推理的最著名的例证 之一,是哈维(Harvey)对血液流动的分析。哈维证明血液循 环的中心论据是数量,是以估计人的心脏的能力为基础的。他 发现,左心室充满时,可以容纳“2盎司或3盎司或1.5盎司 血;并曾发现一个死者的左心室可容纳约4盎司的血”。“心脏 在半小时内博动大约1千次以上,在某些情况下,博动2千、3 千或4千次”。通过简单的计算表明,在半小时内心脏输送到动 脉的血液一至少是83磅4盎司,“这个量远远超过了在整个 身体中发现的血液总量”。他对狗和羊作了类似的计算。这些数 值表明,“通过心脏不断输送的血,远比我们所吃的食物能提供 的血多,也比在静脉中所能容纳的血多。”①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数值计算如何为支持理论而提供论据。这是在新科学中数值进 入理论探讨的一个杰出的例证。 但是,尽管有了前述的例子,实际上,在17世纪的科学中, 利用数值推理作为主要手段的学科,仍只限于精确的物理科学, 包括光学、静力学、运动学和动力学、天文学以及化学的某些 部分。在17世纪的精确科学中,一种特殊的数值关系日益显得 突出,因为那时的科学定律还没有用方程式表示。因此,我们 今天可以把伽利略的匀加速运动定律写成v=at和s=1/2at, 而他却要用语言来表达自然加速运动(如自由落体或沿斜面的 ①见Harrey著De motu cordis,Ch.9.引自The anatomical exercises of Dr. William Harrey.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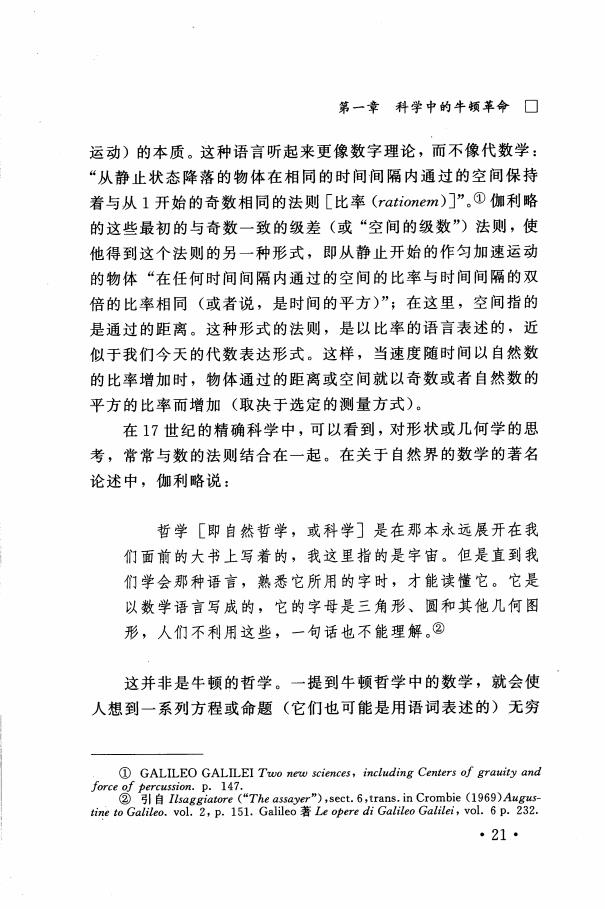
第一章科学中的牛顿革命口 运动)的本质。这种语言听起来更像数字理论,而不像代数学: “从静止状态降落的物体在相同的时间间隔内通过的空间保持 着与从1开始的奇数相同的法则[比率(rationem)]”。①伽利略 的这些最初的与奇数一致的级差(或“空间的级数”)法则,使 他得到这个法则的另一种形式,即从静止开始的作匀加速运动 的物体“在任何时间间隔内通过的空间的比率与时间间隔的双 倍的比率相同(或者说,是时间的平方)”;在这里,空间指的 是通过的距离。这种形式的法则,是以比率的语言表述的,近 似于我们今天的代数表达形式。这样,当速度随时间以自然数 的比率增加时,物体通过的距离或空间就以奇数或者自然数的 平方的比率而增加(取决于选定的测量方式)。 在17世纪的精确科学中,可以看到,对形状或几何学的思 考,常常与数的法则结合在一起。在关于自然界的数学的著名 论述中,伽利略说: 哲学[即自然哲学,或科学]是在那本永远展开在我 们面前的大书上写着的,我这里指的是宇宙。但是直到我 们学会那种语言,熟悉它所用的字时,才能读懂它。它是 以数学语言写成的,它的字母是三角形、圆和其他几何图 形,人们不利用这些,一句话也不能理解。② 这并非是牛顿的哲学。一提到牛顿哲学中的数学,就会使 人想到一系列方程或命题(它们也可能是用语词表述的)无穷 1 GALILEO GALILEI Two new sciences,including Centers of grauity and force of percussion.p.147. ②引自Ilsaggiatore(“The assayer"),sect.6,trans..in Crombie(1969)Augus- tine to Galileo.vol.2,p.151.Galileo Le opere di Galileo Galilei,vol.6 p.232.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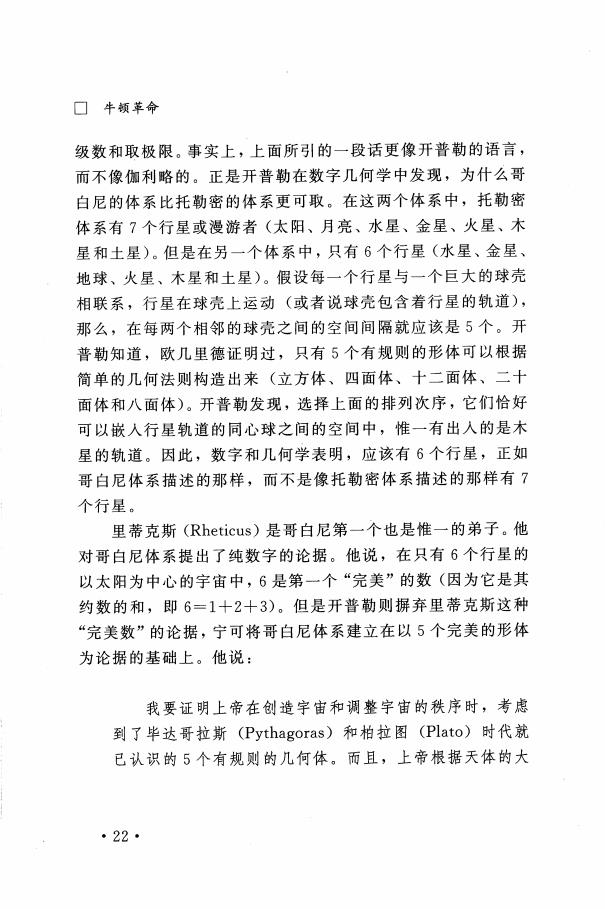
口牛顿苹命 级数和取极限。事实上,上面所引的一段话更像开普勒的语言, 而不像伽利略的。正是开普勒在数字几何学中发现,为什么哥 白尼的体系比托勒密的体系更可取。在这两个体系中,托勒密 体系有7个行星或漫游者(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 星和土星)。但是在另一个体系中,只有6个行星(水星、金星、 地球、火星、木星和土星)。假设每一个行星与一个巨大的球壳 相联系,行星在球壳上运动(或者说球壳包含着行星的轨道), 那么,在每两个相邻的球壳之间的空间间隔就应该是5个。开 普勒知道,欧几里德证明过,只有5个有规则的形体可以根据 简单的几何法则构造出来(立方体、四面体、十二面体、二十 面体和八面体)。开普勒发现,选择上面的排列次序,它们恰好 可以嵌人行星轨道的同心球之间的空间中,惟一有出人的是木 星的轨道。因此,数字和几何学表明,应该有6个行星,正如 哥白尼体系描述的那样,而不是像托勒密体系描述的那样有7 个行星。 里蒂克斯(Rheticus.)是哥白尼第一个也是惟一的弟子。他 对哥白尼体系提出了纯数字的论据。他说,在只有6个行星的 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中,6是第一个“完美”的数(因为它是其 约数的和,即6=1十2+3)。但是开普勒则摒弃里蒂克斯这种 “完美数”的论据,宁可将哥白尼体系建立在以5个完美的形体 为论据的基础上。他说: 我要证明上帝在创造宇宙和调整宇宙的秩序时,考惠 到了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和柏拉图(Plato)时代就 已认识的5个有规则的几何体。而且,上帝根据天体的大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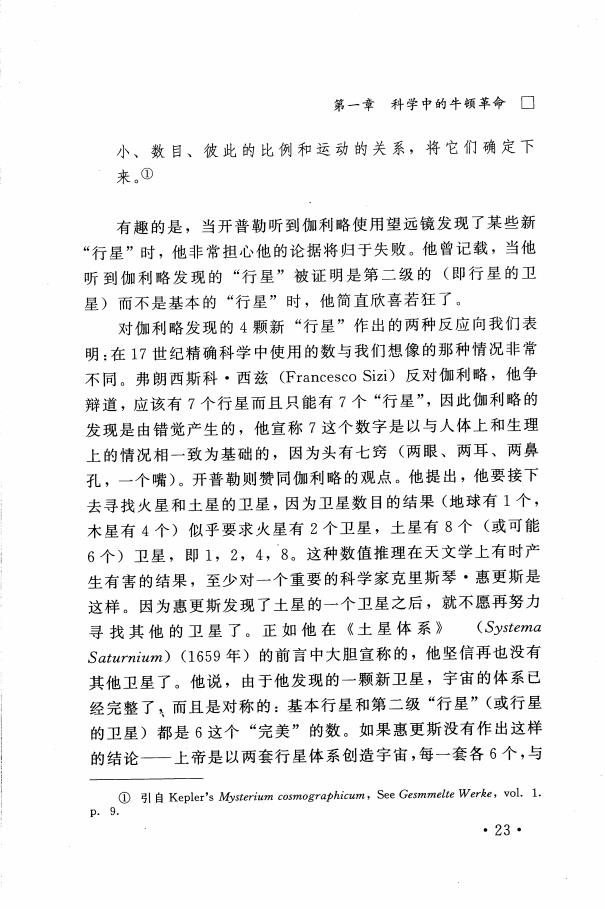
第一章科学中的牛领革命☐ 小、数目、彼此的比例和运动的关系,将它们确定下 来.① 有趣的是,当开普勒听到伽利略使用望远镜发现了某些新 “行星”时,他非常担心他的论据将归于失败。他曾记载,当他 听到伽利略发现的“行星”被证明是第二级的(即行星的卫 星)而不是基本的“行星”时,他简直欣喜若狂了。 对伽利略发现的4颗新“行星”作出的两种反应向我们表 明:在17世纪精确科学中使用的数与我们想像的那种情况非常 不同。弗朗西斯科·西兹(Francesco Sizi)反对伽利略,他争 辩道,应该有7个行星而且只能有7个“行星”,因此伽利略的 发现是由错觉产生的,他宣称7这个数字是以与人体上和生理 上的情况相一致为基础的,因为头有七窍(两眼、两耳、两鼻 孔,一个嘴)。开普勒则赞同伽利略的观点。他提出,他要接下 去寻找火星和土星的卫星,因为卫星数目的结果(地球有1个, 木星有4个)似乎要求火星有2个卫星,土星有8个(或可能 6个)卫星,即1,2,4,8。这种数值推理在天文学上有时产 生有害的结果,至少对一个重要的科学家克里斯琴·惠更斯是 这样。因为惠更斯发现了土星的一个卫星之后,就不愿再努力 寻找其他的卫星了。正如他在《土星体系》 (Systema Saturnium)(1659年)的前言中大胆宣称的,他坚信再也没有 其他卫星了。他说,由于他发现的一颗新卫星,宇宙的体系已 经完整了,而且是对称的:基本行星和第二级“行星”(或行星 的卫星)都是6这个“完美”的数。如果惠更斯没有作出这样 的结论一上帝是以两套行星体系创造字宙,每一套各6个,与 D Kepler's Mysterium cosmographicum,See Gesmmelte Werke,vol.1. p.9.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