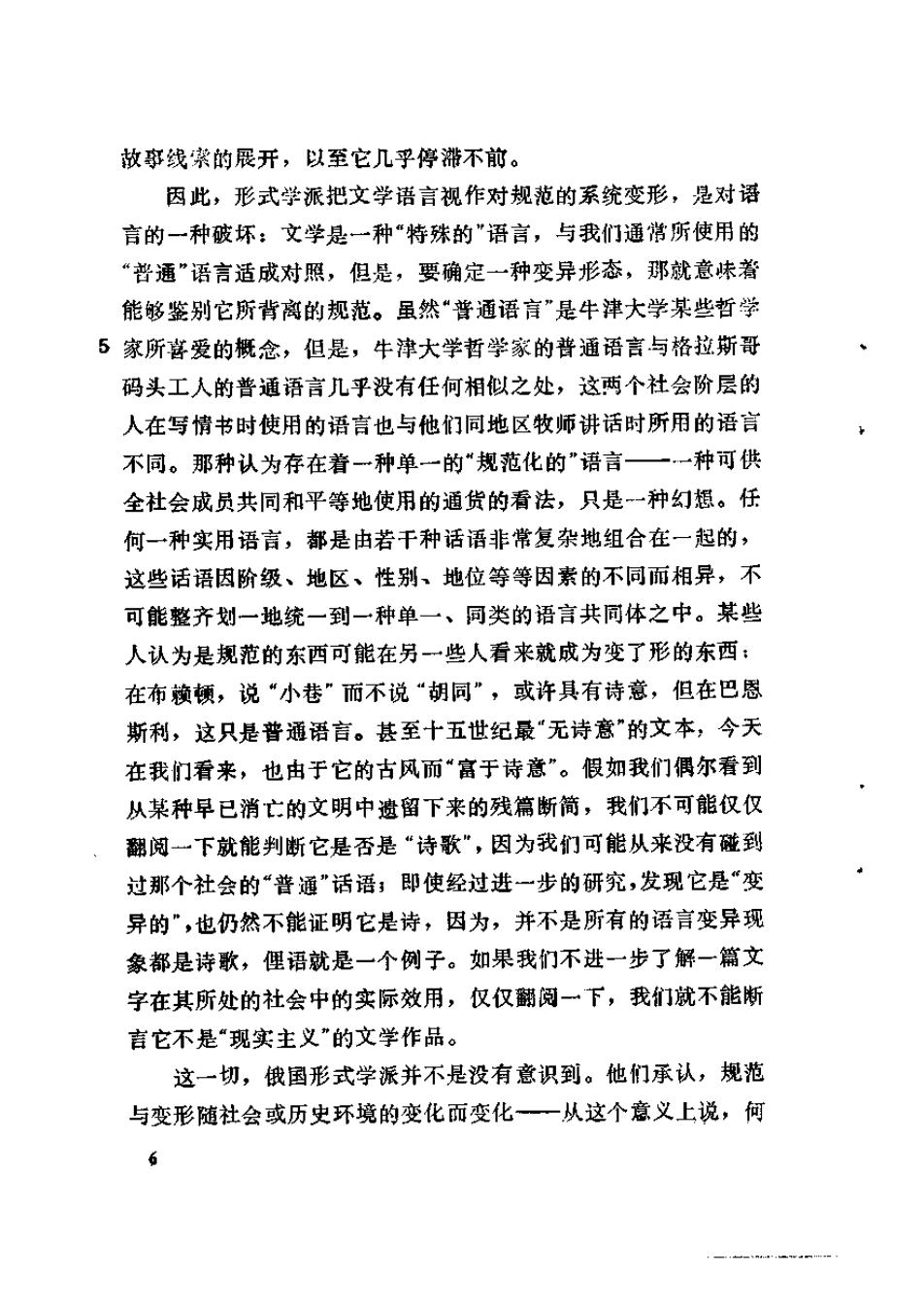
故事线察的展开,以至它几乎停滞不前。 因此,形式学派把文学语言视作对规范的系统变形,是对语 言的一种破坏: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与我们通常所使用的 “普通”语言适成对照,但是,要确定一种变异形态,那就意味着 能够鉴别它所背离的规范。虽然“普通语言”是牛津大学某些哲学 5家所菩爱的概念,但是,牛津大学哲学家的普通语言与格拉斯哥 码头工人的普通语言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两个社会阶层的 人在写情书时使用的语言也与他们同地区牧师讲话时所用的语言 不同。那种认为存在着一种单一的“规范化的”语言一一种可供 全社会成员共同和平等地使用的通货的看法,只是一种幻想。任 何一种实用语言,都是由若干种话语非常复杂地组合在一起的, 这些话语因阶级、地区、性别、地位等等因素的不同而相异,不 可能整齐划一地统一到一种单一、同类的语言共同体之中。某些 人认为是规范的东西可能在另一些人看来就成为变了形的东西: 在布赖顿,说“小巷”而不说“胡同”,或许具有诗意,但在巴恩 斯利,这只是普通语言。甚至十五世纪最“无诗意”的文本,今天 在我们看来,也由于它的古风而“富于诗意”。假如我们偶尔看到 从某种早已消亡的文明中遗留下来的残篇断简,我们不可能仅仅 翻阅一下就能判断它是否是“诗歌“,因为我们可能从来没有碰到 过那个社会的“普通”话语;即使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它是“变 异的”,也仍然不能证明它是诗,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语言变异现 象都是诗歌,俚语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我们不进一步了解一篇文 字在其所处的社会中的实际效用,仅仅翻阅一下,我们就不能断 言它不是“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 这一切,俄国形式学派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他们承认,规范 与变形随社会或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何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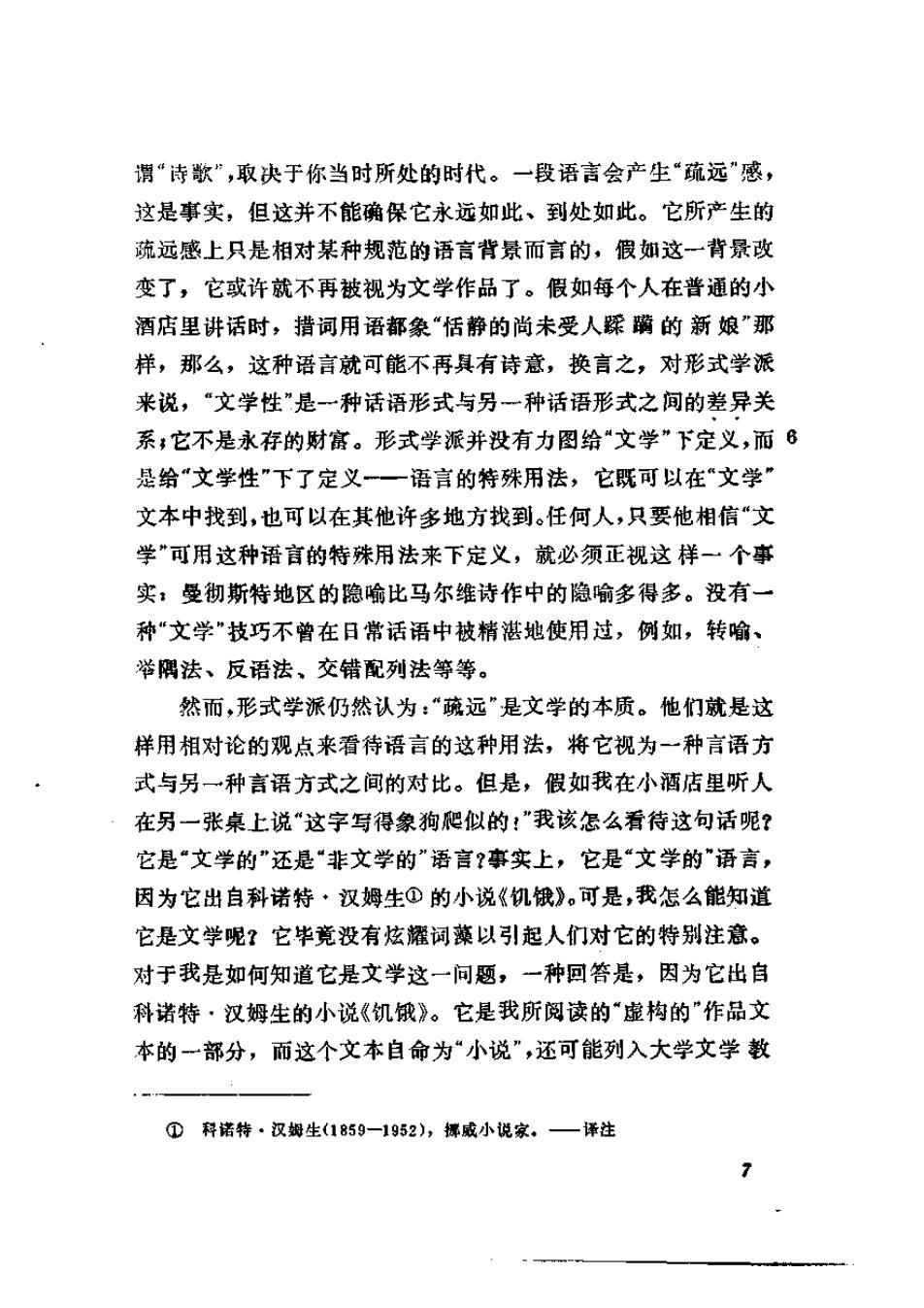
谓“诗歌”,取决于你当时所处的时代。一段语言会产生“疏远”感, 这是事实,但这并不能确保它永远如此、到处如此。它所产生的 疏远感上只是相对某种规范的语言背景而言的,假如这一背景改 变了,它或许就不再被视为文学作品了。假如每个人在普通的小 酒店里讲话时,措词用语都象“恬静的尚未受人踩躏的新娘”那 样,那么,这种语言就可能不再具有诗意,换言之,对形式学派 来说,“文学性”是一种话语形式与另一种话语形式之间的差异关 系,它不是永存的财富。形式学派并没有力图给“文学”下定义,而6 是给"文学性”下了定义一一语言的特殊用法,它既可以在“文学” 文本中找到,也可以在其他许多地方找到。任何人,只要他相信“文 学”可用这种语言的特殊用法来下定义,就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 实:曼彻斯特地区的隐喻比马尔维诗作中的隐喻多得多。没有一 种“文学”技巧不曾在日常话语中被精湛地使用过,例如,转喻、 举隅法、反语法、交带配列法等等。 然而,形式学派仍然认为:“疏远”是文学的本质。他们就是这 样用相对论的观点来看待语言的这种用法,将它视为一种言语方 式与另一种言语方式之间的对比。但是,假如我在小酒店里听人 在另一张桌上说“这字写得象狗爬似的:”我该怎么看待这句话呢? 它是“文学的”还是“非文学的”语言?事实上,它是“文学的”语言, 因为它出自科诺特·汉姆生①的小说《机饿》。可是,我怎么能知道 它是文学呢?它毕竟没有炫耀词藻以引起人们对它的特别注意。 对于我是如何知道它是文学这一问题,一种回答是,因为它出自 科诺特·汉姆生的小说《饥饿》。它是我所阅读的“虚构的”作品文 本的一部分,而这个文本自命为“小说”,还可能列入大学文学教 ①科诺特·汉姆生(1859一1952),威小说京。一译注

学大纲等等。上下文告诉我,它是文学;但是它的语言本身并不 具有内在特征或特质可将它与其他话语形式相区别,某人很可能 在小酒店说过这句话,却无人欣赏它的文学机敏性。象形式学派 那样看待文学,确实是把所有的文学都作为诗歌来看待。重要 的是,当形式学派考虑散文写作时,他们往往简单地把用于诗歌 的技法也用于散文。但是,人们通常认为文学除诗歌以外还包括 许多东西一举例来说,它包括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作品,这 些作品从语言上说,根本谈不上是自我意识或自我显示的作品。 人们有时称某一作品“写得好”,恰恰是因为它没有过分地把别人 的注意力引到它自身上;他们欣赏它的简洁明快或含而不露。还 有象笑话、足球场上的喝彩和标语、报纸的标题、广告等等,它 们的词藻往往是很讲究的,但通常并不把它们归入文学,这又该 怎么看呢? 关于“疏远”的另一个问题是,任何一种写作,只要有足够的 独创性,读后都有疏远陌生感。不妨设想这么一张平淡无奇、相 当明确的布告,就象人们有时在伦敦地铁里看到的:“自动扶梯上 ?要把狗带好。”这张布告也许并不象人们第一眼看去那样明确无 误:它是不是说你上自动扶梯必须带一条狗?你乘自动扶梯时是 不是要抱一只迷了路的杂种狗,不然的话,就可能被禁止乘自 动扶梯?许多看上去明白无误的布告却包含着模棱两可的含义: 例如“Refuse to be put in this basket"①,或者,一个加利福尼亚 人看到这样一条英国路标“Way Out”②。但是,即使将这些恼人 ① 当“refusc”作名词解时,此句意为“废物校人此篮”,当“refu3e”作动词解 时,意为“不可将东西投人此篮。一译注 ② 一意“出口”,一意“此路不通”。—译注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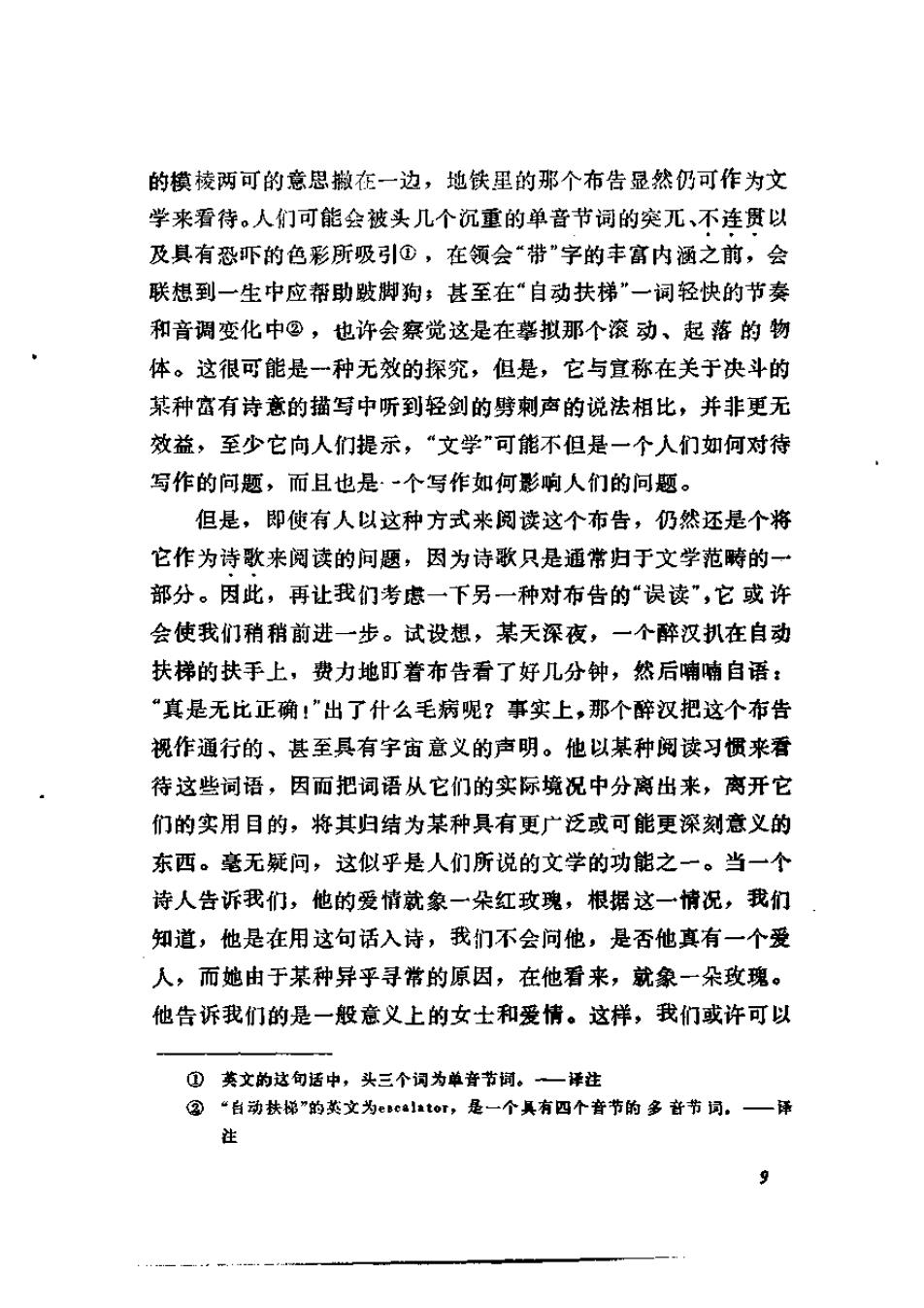
的模棱两可的意思椒在一边,地铁里的那个布告显然仍可作为文 学来看待。人们可能会被头几个沉重的单音节词的突兀、不连贯以 及具有恐吓的色彩所吸引①,在领会“带”字的丰富内涵之前,会 联想到一生中应帮助跛脚狗多甚至在“自动扶梯”一词轻快的节奏 和音调变化中②,也许会察觉这是在莘拟那个滚动、起落的物 体。这很可能是一种无效的探究,但是,它与宜称在关于决斗的 某种富有诗意的锚写中听到轻剑的劈刺声的说法相比,并非更无 效益,至少它向人们提示,“文学”可能不但是一个人们如何对待 写作的问题,而且也是··个写作如何影响人们的问题。 但是,即使有人以这种方式来阅读这个布告,仍然还是个将 它作为诗歌来阅读的问题,因为诗歌只是通常归于文学范畴的一 部分。因此,再让我们考虑一下另一种对布告的“误读”,它或许 会使我们稍稍前进一步。试设想,某天深夜,一个醉汉扒在自动 扶梯的扶手上,费力地盯着布告看了好几分钟,然后喃喃自语: “真是无比正确!”出了什么毛病呢?事实上,那个醉汉把这个布告 视作通行的、甚至具有字宙意义的声明。他以某种阅读习惯来看 待这些词语,因而把词语从它们的实际境况中分离出来,离开它 们的实用目的,将其归结为某种具有更广泛或可能更深刻意义的 东西。毫无疑问,这似乎是人们所说的文学的功能之一。当一个 诗人告诉我们,他的爱情就象一朵红玫瑰,根据这一情况,我们 知道,他是在用这句话入诗,我们不会问他,是否他真有一个爱 人,而她由于某种异乎寻常的原因,在他看来,就象一朵玫瑰。 他告诉我们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女士和爱情。这样,我们或许可以 ①英文的这句话中,头三个词为单音节词。一译注 ②“台动扶梯”的英文为enealator,是一个具有四个音节的多苷节词。一译 注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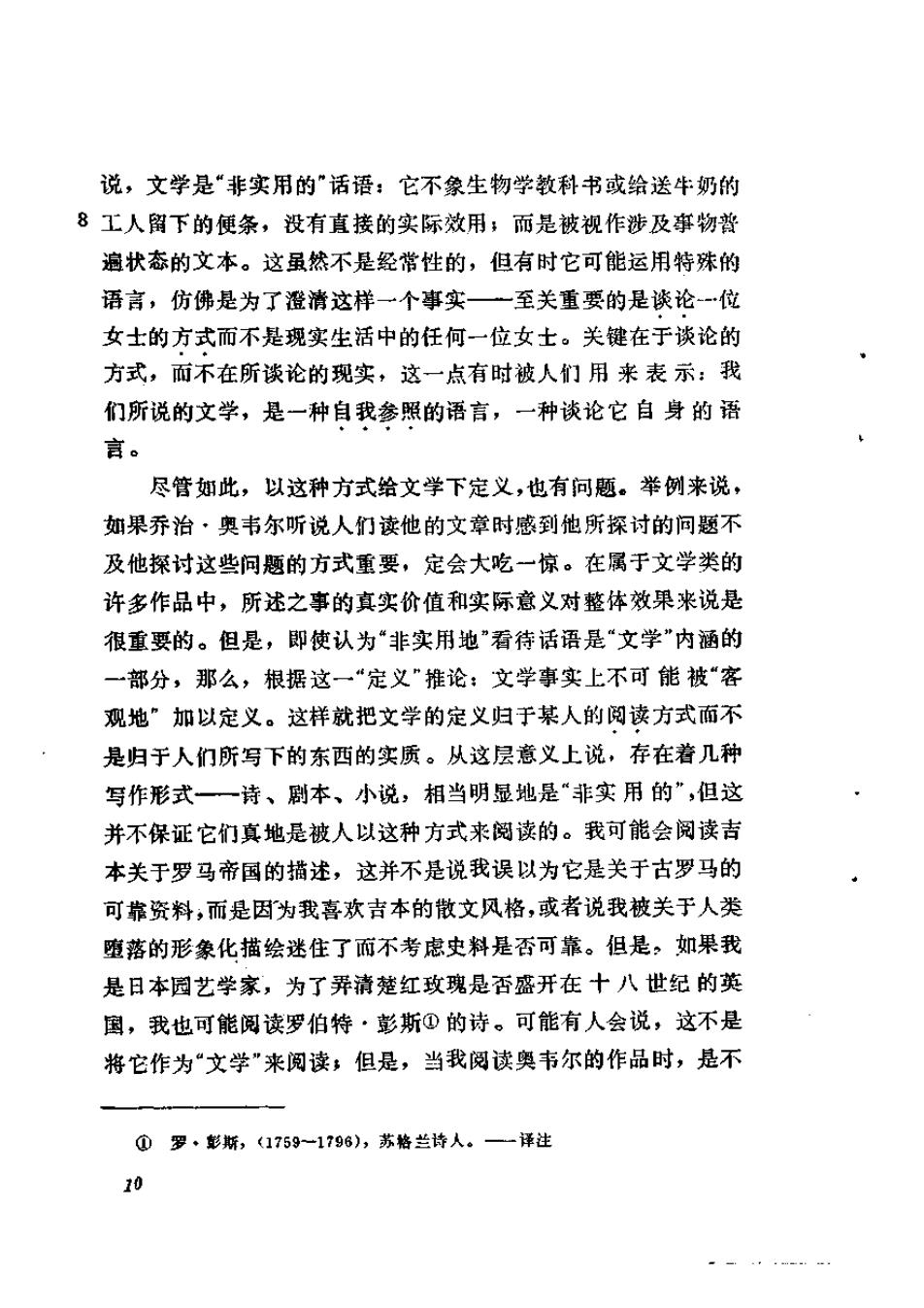
说,文学是“非实用的“话语:它不象生物学教科书或给送牛奶的 8工人留下的便条,没有直接的实际效用;而是被视作涉及事物普 遍状态的文本。这虽然不是经常性的,但有时它可能运用特殊的 语言,仿佛是为了澄清这样一个事实一至关重要的是谈论…位 女士的方式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一位女土。关键在于谈论的 方式,而不在所谈论的现实,这一点有时被人们用来表示:我 们所说的文学,是一种自我参照的语言,一种谈论它自身的语 言。 尽管如此,以这种方式给文学下定义,也有问题。举例来说, 如果乔治·奥韦尔听说人们读他的文章时感到他所探讨的问题不 及他探讨这些问题的方式重要,定会大吃一惊。在属于文学类的 许多作品中,所述之事的真实价值和实际意义对整体效果来说是 很重要的。但是,即使认为“非实用地”看待话语是“文学”内涵的 一一部分,那么,根据这一“定义”推论:文学事实上不可能被“客 观地”加以定义。这样就把文学的定义归于某人的阅读方式面不 是归于人们所写下的东西的实质。从这层意义上说,存在着几种 写作形式一一诗、剧本、小说,相当明显地是“菲实用的”,但这 并不保证它们真地是被人以这种方式来阅读的。我可能会阅读吉 本关于罗马帝国的描述,这并不是说我误以为它是关于古罗马的 可靠资料,而是因为我喜欢吉本的散文风格,或者说我被关于人类 堕落的形象化描绘迷住了而不考虑史料是否可靠。但是,如果我 是日本园艺学家,为了弄请楚红玫瑰是否盛开在十八世纪的英 国,我也可能阅读罗伯特·彭斯①的诗。可能有人会说,这不是 将它作为“文学”来阅读,但是,当我阅读奥韦尔的作品时,是不 ①罗·彭斯,《1759一1796),苏格兰诗人。一一译注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