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8 蔡元培全集第六卷 字读书,以补助正式小学之不足;先试一村,推而至于全国,使家无 不识字之儿童,则十余年后,方克达到国无不学之民。意美法良, 造端宏大,全赖海内贤俊,群策群力,一致提倡,方易收效。素仰台 端热心教育,学界泰斗,用将姚君所拟辅教运动草案,及所草大纲 与章程等件×份,寄请台览,并乞指导修正,共策进行。如蒙惠允 加入发起人,务乞示复,不胜盼祷之至。此请。 据蔡元培手稿 复刘海粟函 (一九三三年) 海粟先生大鉴: 惠书敬悉。弟今晚赴宁,明晨不能恭候为款。属为萨龙民展 览会题签,奉上。公何时赴欧,至念。敬复,并祝 著祺 弟元培敬启 摆蔡元培手札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 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 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在北大服务之 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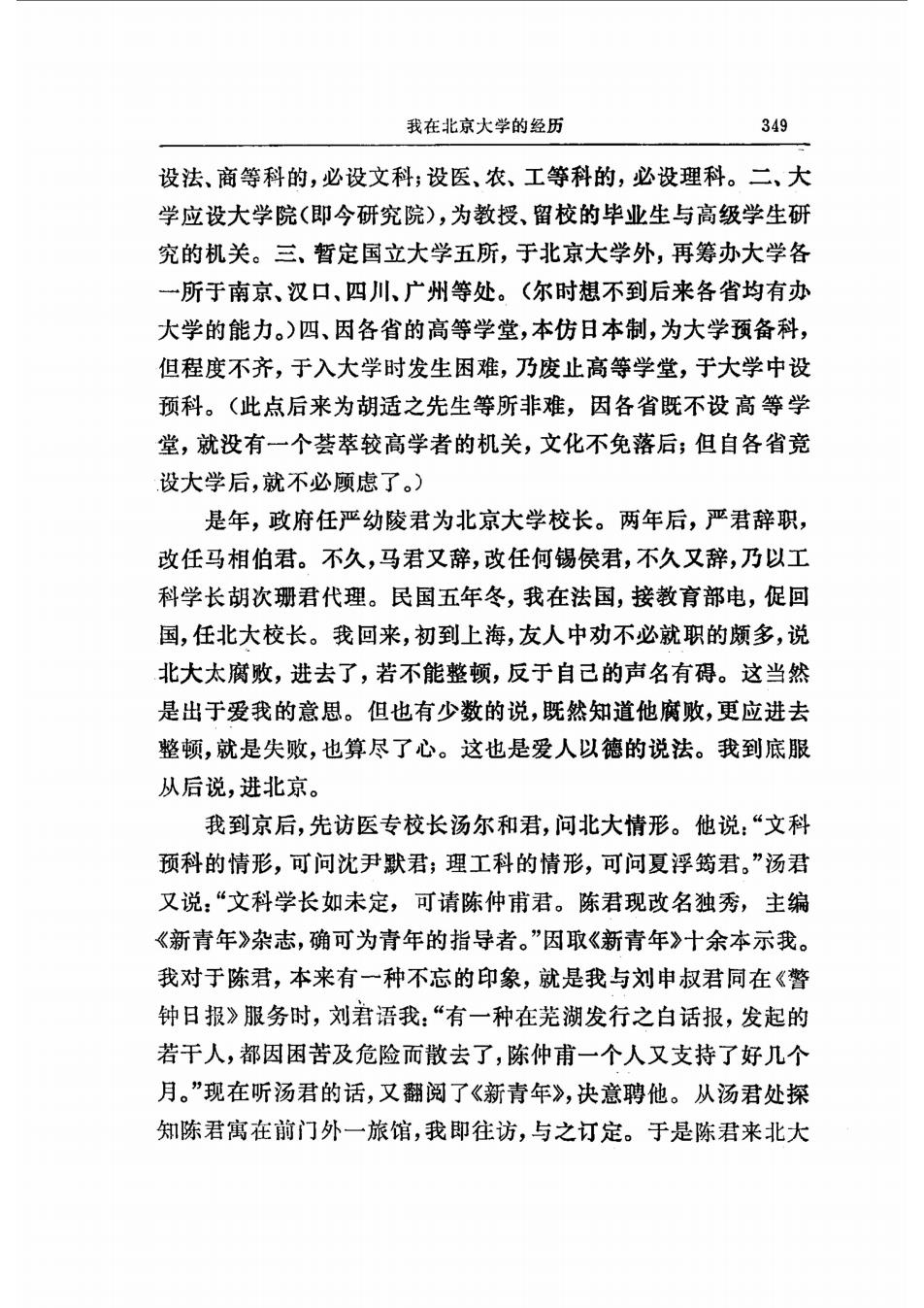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349 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 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 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 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 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 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 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 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 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 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 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 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 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得。这当然 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 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 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 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 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 《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 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 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 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 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 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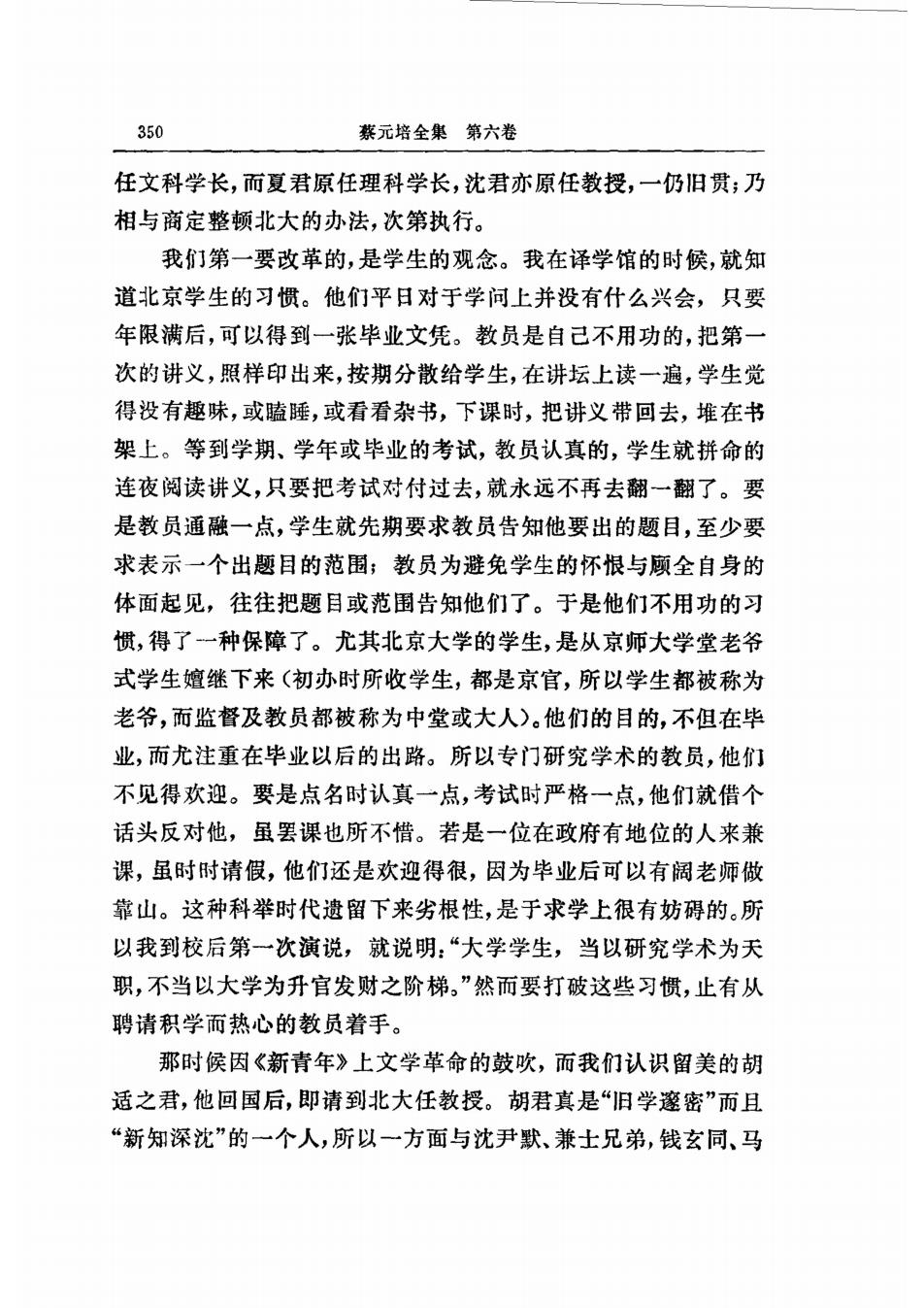
350 蔡元培全集第六卷 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 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 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 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 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 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 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 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 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 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 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 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 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 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 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 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 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 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 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 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 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止有从 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 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 “新知深沈”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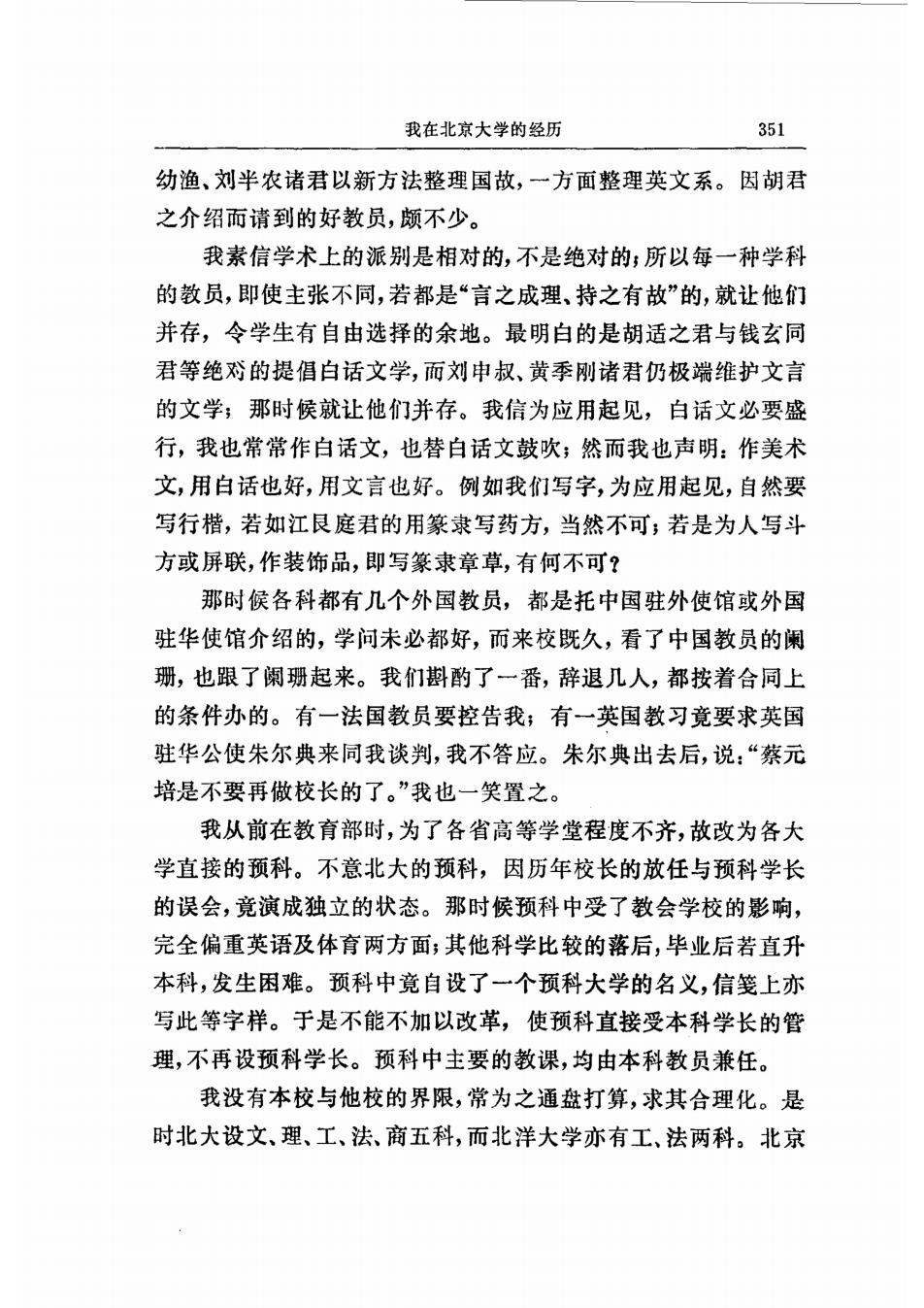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351 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 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 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 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 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 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 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 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 写行楷,若如江良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 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侯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 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 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 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 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 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 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 的误会,竞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 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 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 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 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 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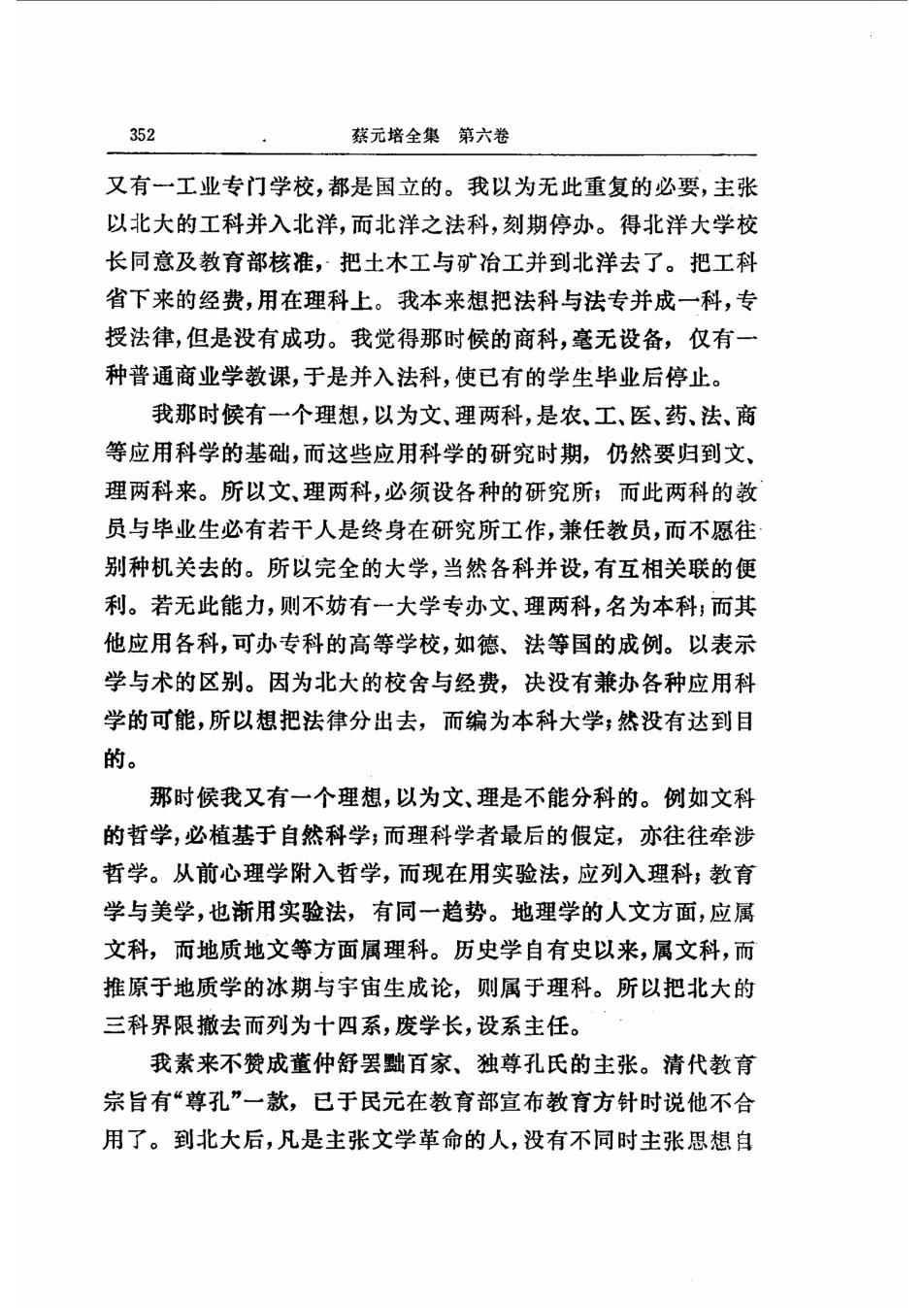
352 蔡元培全集第六卷 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 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 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 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 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 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 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 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 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 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 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 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 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 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 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 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 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 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 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 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 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 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 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