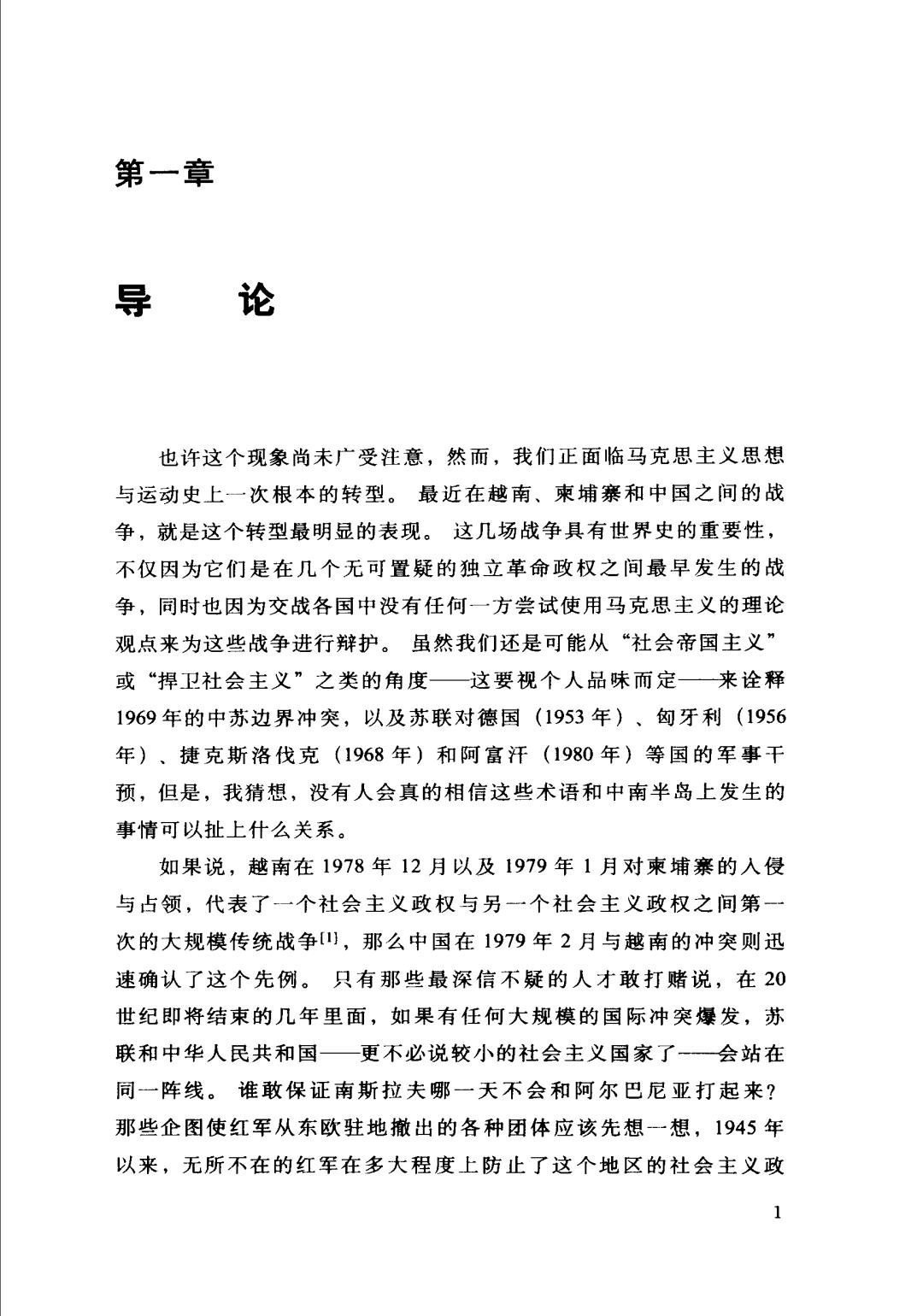
第一章 导 论 也许这个现象尚未广受注意,然而,我们正面临马克思主义思想 与运动史上一次根本的转型。最近在越南、柬埔寨和中国之间的战 争,就是这个转型最明显的表现。这几场战争具有世界史的重要性, 不仅因为它们是在几个无可置疑的独立革命政权之间最早发生的战 争,同时也因为交战各国中没有任何一方尝试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观点来为这些战争进行辩护。虽然我们还是可能从“社会帝国主义” 或“捍卫社会主义”之类的角度—这要视个人品味而定来诠释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以及苏联对德国(1953年)、匈牙利(1956 年)、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和阿富汗(1980年)等国的军事干 预,但是,我猜想,没有人会真的相信这些术语和中南半岛上发生的 事情可以扯上什么关系。 如果说,越南在1978年12月以及1979年1月对柬埔寨的入侵 与占领,代表了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与另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之间第一一 次的大规模传统战争[),那么中国在1979年2月与越南的冲突则迅 速确认了这个先例。只有那些最深信不疑的人才敢打赌说,在20 世纪即将结束的几年里面,如果有任何大规模的国际冲突爆发,苏 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不必说较小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一会站在 同一阵线。谁敢保证南斯拉夫哪一天不会和阿尔巴尼亚打起来? 那些企图使红军从东欧驻地撤出的各种团体应该先想-一想,1945年 以来,无所不在的红军在多大程度上防止了这个地区的社会主义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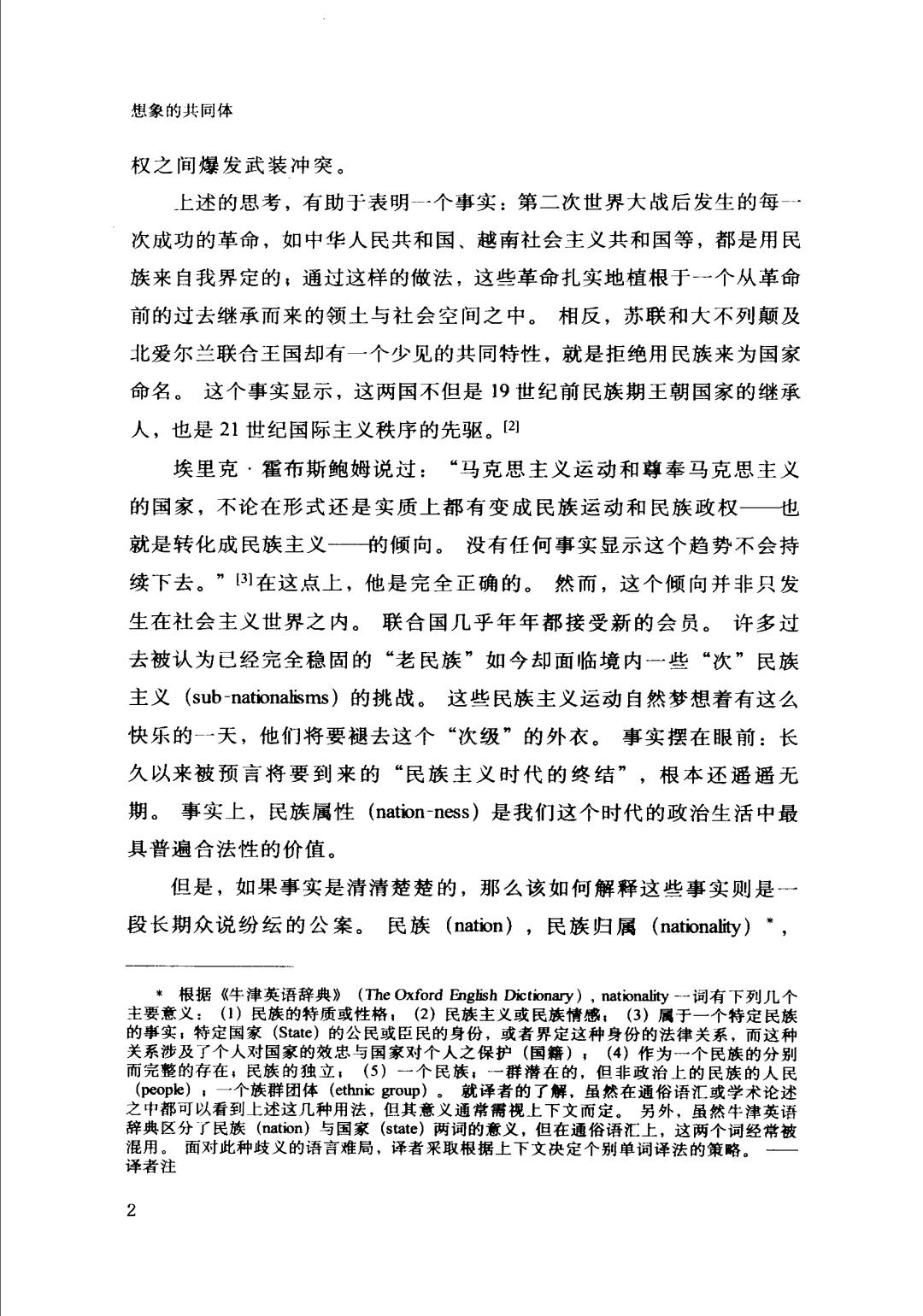
想象的共同体 权之间爆发武装冲突。 上述的思考,有助于表明-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每一 次成功的革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都是用民 族来自我界定的,通过这样的做法,这些革命扎实地植根于一个从革命 前的过去继承而来的领土与社会空间之中。相反,苏联和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却有一个少见的共同特性,就是拒绝用民族来为国家 命名。这个事实显示,这两国不但是19世纪前民族期王朝国家的继承 人,也是21世纪国际主义秩序的先驱。2]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说过:“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尊奉马克思主义 的国家,不论在形式还是实质上都有变成民族运动和民族政权也 就是转化成民族主义的倾向。没有任何事实显示这个趋势不会持 续下去。”3)在这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这个倾向并非只发 生在社会主义世界之内。联合国几乎年年都接受新的会员。许多过 去被认为已经完全稳固的“老民族”如今却面临境内一些“次”民族 主义(sub-nationalisms)的挑战。这些民族主义运动自然梦想着有这么 快乐的一天,他们将要褪去这个“次级”的外衣。事实摆在眼前:长 久以来被预言将要到来的“民族主义时代的终结”,根本还遥遥无 期。事实上,民族属性(nation-ness)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最 具普遍合法性的价值。 但是,如果事实是清清楚楚的,那么该如何解释这些事实则是一 段长期众说纷纭的公案。民族(nation),民族归属(nationality), *根据《牛津英语辞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nationality-词有下列几个 主要意义:(1)民族的特质或性格,(2)民族主义或民族情感,(3)属于一个特定民族 的事实,特定国家(State)的公民或臣民的身份,或者界定这种身份的法律关系,而这种 关系涉及了个人对国家的效忠与国家对个人之保护(国籍),(4)作为一个民族的分别 而完整的存在,民族的独立,(5)一个民族,一群潜在的,但非政治上的民族的人民 (people),一个族群团体(ethnic group)。就译者的了解,虽然在通俗语汇或学术论述 之中都可以看到上述这几种用法,但其意义通常需视上下文而定。另外,虽然牛津英语 辞典区分了民族(nation)与国家(state)两词的意义,但在通俗语汇上,这两个词经常被 混用。面对此种歧义的语言难局,译者采取根据上下文决定个别单词译法的策略。 译者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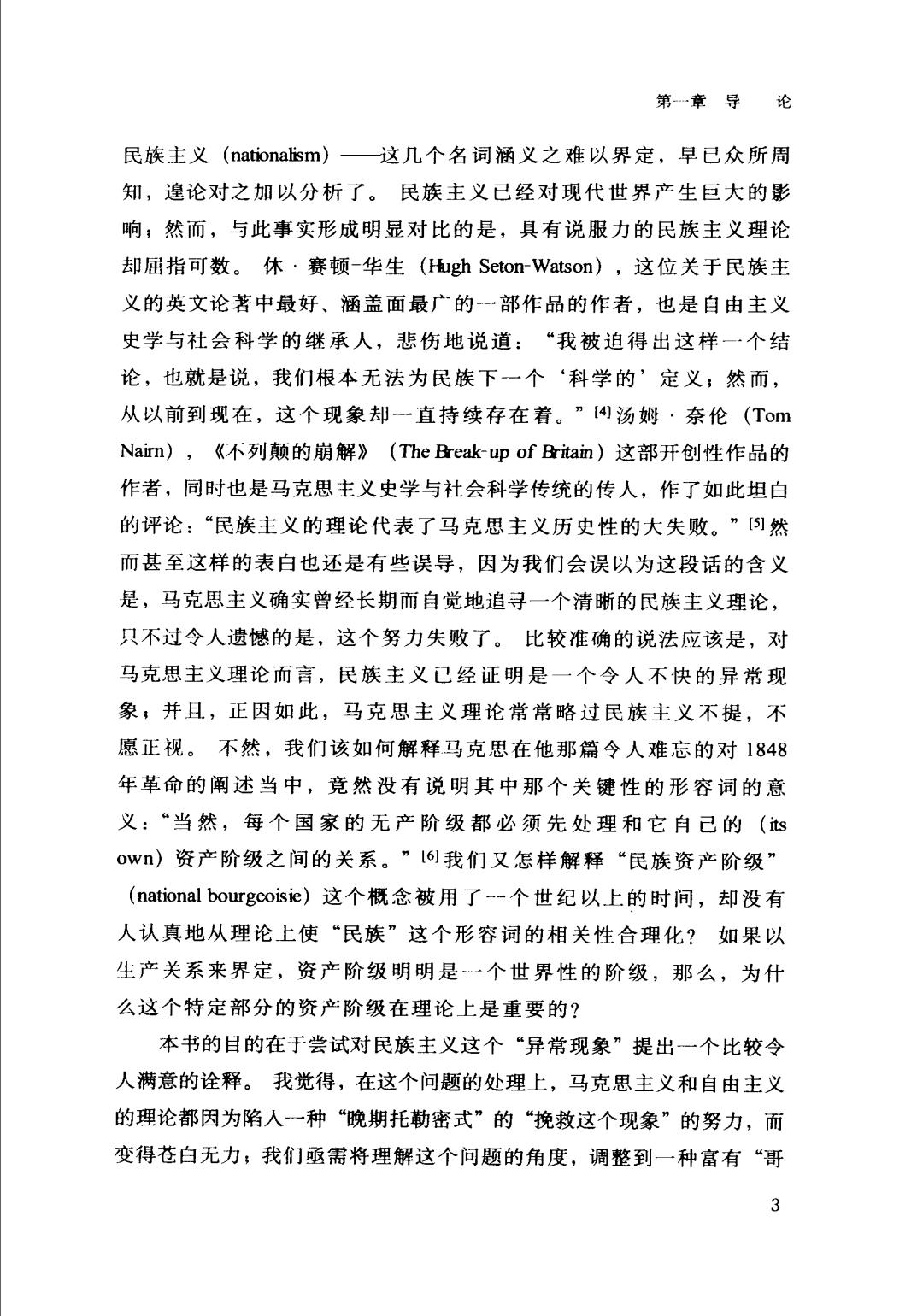
第…章导论 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这几个名词涵义之难以界定,早已众所周 知,遑论对之加以分析了。民族主义已经对现代世界产生巨大的影 响;然而,与此事实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具有说服力的民族主义理论 却屈指可数。休·赛顿-华生(ugh Seton-Watson),这位关于民族主 义的英文论著中最好、涵盖面最广的一部作品的作者,也是自由主义 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继承人,悲伤地说道:“我被迫得出这样一个结 论,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无法为民族下一个‘科学的’定义,然而, 从以前到现在,这个现象却一直持续存在着。”[4汤姆·奈伦(Tom Nain),《不列颠的崩解》(The Break-up of Britain)这部开创性作品的 作者,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社会科学传统的传人,作了如此坦白 的评论:“民族主义的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性的大失败。”]然 而甚至这样的表白也还是有些误导,因为我们会误以为这段话的含义 是,马克思主义确实曾经长期而自觉地追寻一个清晰的民族主义理论, 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努力失败了。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对 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民族主义已经证明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异常现 象,并且,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常常略过民族主义不提,不 愿正视。不然,我们该如何解释马克思在他那篇令人难忘的对1848 年革命的阐述当中,竟然没有说明其中那个关键性的形容词的意 义:“当然,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必须先处理和它自己的(ts own)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61我们又怎样解释“民族资产阶级” (national bourgeoisie)这个概念被用了--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却没有 人认真地从理论上使“民族”这个形容词的相关性合理化?如果以 生产关系来界定,资产阶级明明是一个世界性的阶级,那么,为什 么这个特定部分的资产阶级在理论上是重要的? 本书的目的在于尝试对民族主义这个“异常现象”提出一个比较令 人满意的诠释。我觉得,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 的理论都因为陷人一种“晚期托勒密式”的“挽救这个现象”的努力,而 变得苍白无力;我们亟需将理解这个问题的角度,调整到一种富有“哥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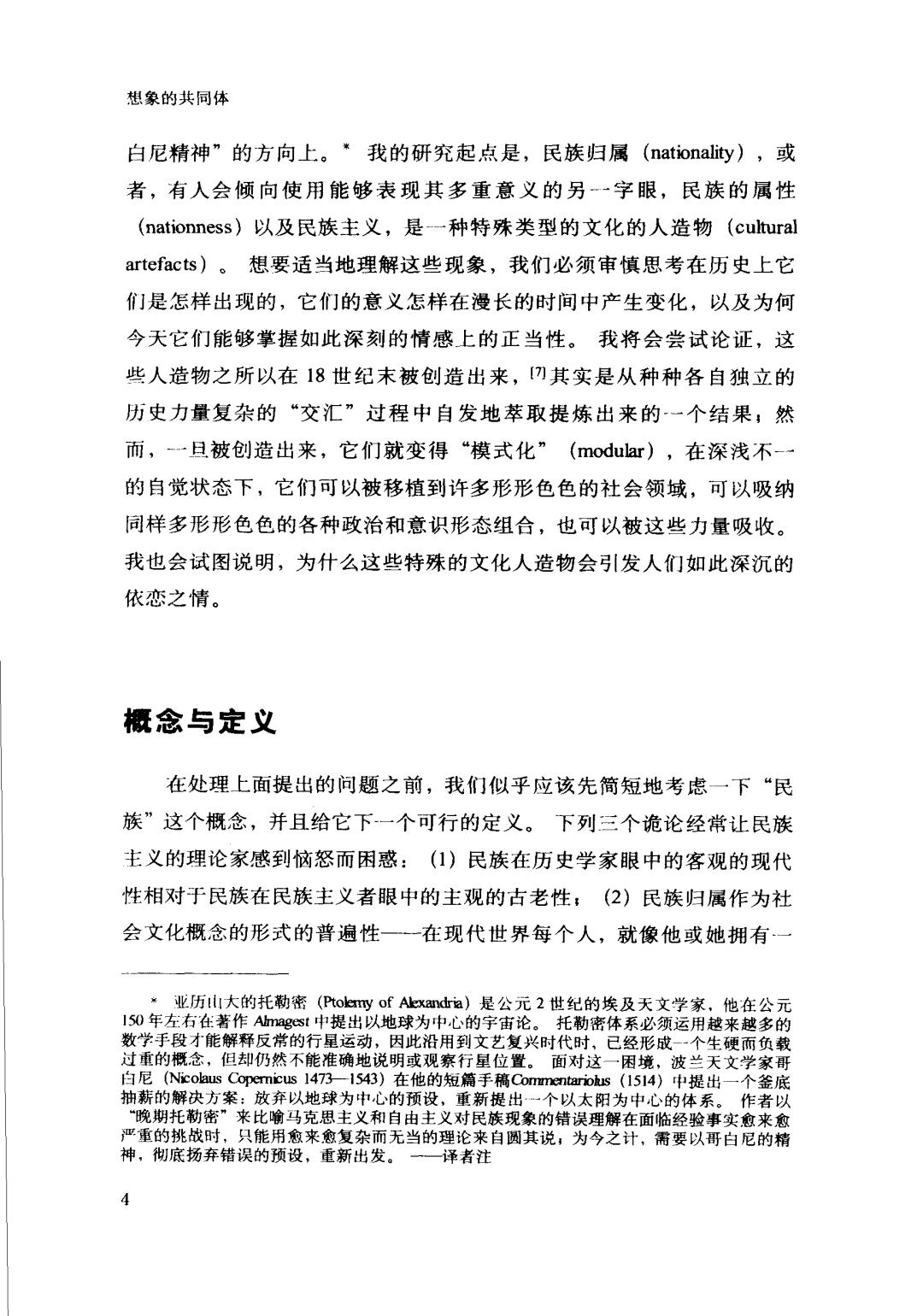
想象的共同体 白尼精神”的方向上。*我的研究起点是,民族归属(nationality),或 者,有人会倾向使用能够表现其多重意义的另一字眼,民族的属性 (nationness)以及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想要适当地理解这些现象,我们必须审慎思考在历史上它 们是怎样出现的,它们的意义怎样在漫长的时间中产生变化,以及为何 今天它们能够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我将会尝试论证,这 些人造物之所以在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 历史力量复杂的“交汇”过程中自发地萃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 而,-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变得“模式化”(modular),在深浅不- 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 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 我也会试图说明,为什么这些特殊的文化人造物会引发人们如此深沉的 依恋之情。 概念与定义 在处理上面提出的问题之前,我们似乎应该先简短地考虑一下“民 族”这个概念,并且给它下一个可行的定义。下列三个诡论经常让民族 主义的理论家感到恼怒而困惑:(1)民族在历史学家眼中的客观的现代 性相对于民族在民族主义者眼中的主观的古老性;(2)民族归属作为社 会文化概念的形式的普遍性一一在现代世界每个人,就像他或她拥有一 *亚历tl山大的托勒密(Ptolemy of Alxandria)是公元2世纪的埃及天文学家,他在公元 150年左右在著作Almagest中提出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论。托勒密体系必须运用越来越多的 数学手段才能解释反常的行星运动,因此沿用到文艺复兴时代时,已经形成-一个生硬而负载 过重的概念,但却仍然不能准确地说明或观察行星位置。面对这一困境,波兰天文学家哥 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一1543)在他的短篇手稿Commentariolus(1514)中提出一个釜底 抽薪的解决方案:放弃以地球为中心的预设,重新提出一个以太阳为中心的体系。作者以 “晚期托勒密”来比喻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对民族现象的错误理解在面临经验事实愈来愈 严重的挑战时,只能用愈来愈复杂而无当的理论来自圆其说,为今之计,需要以哥白尼的精 神,彻底扬弃错误的预设,重新出发。一一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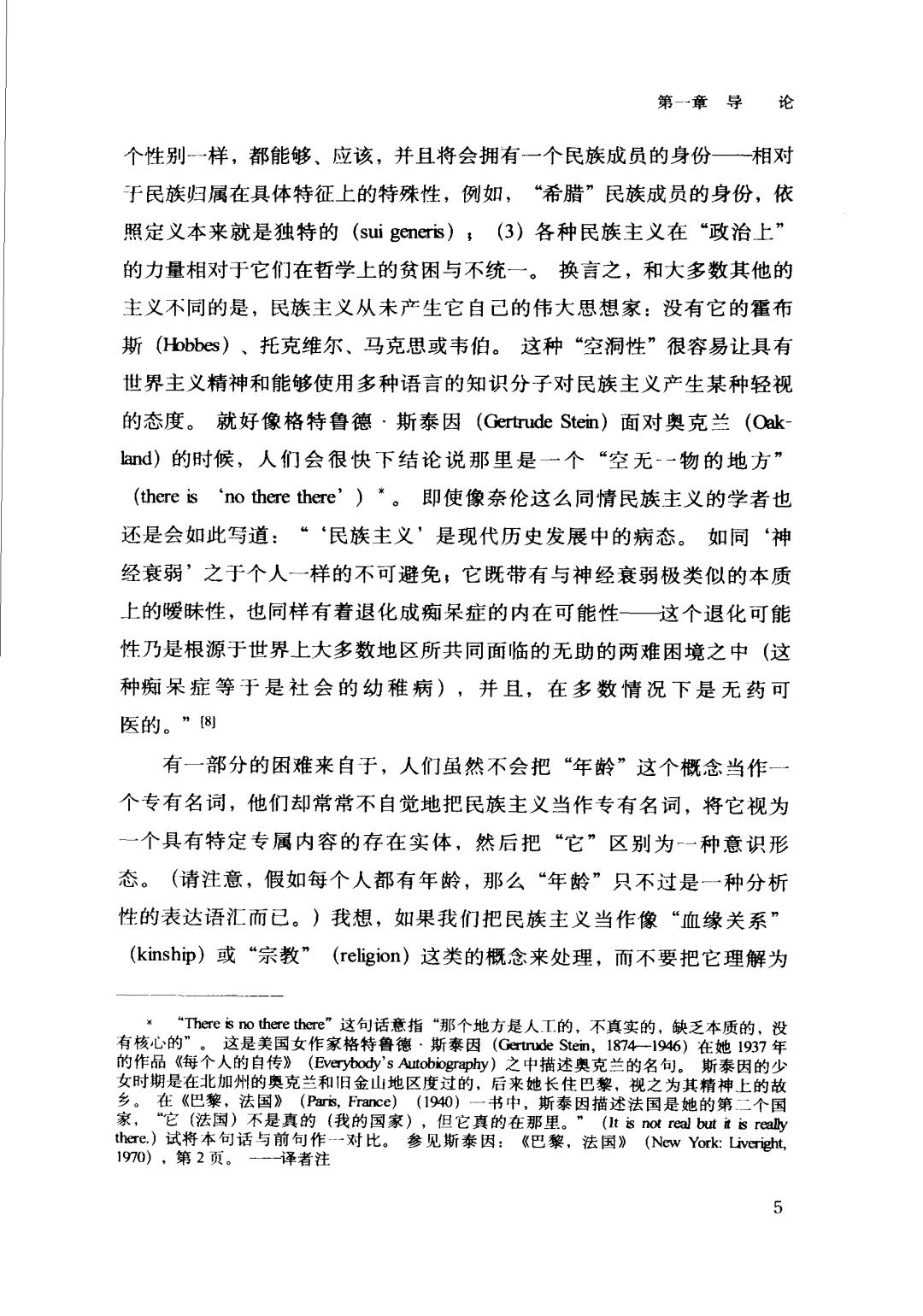
第-…章导 论 个性别一样,都能够、应该,并且将会拥有一个民族成员的身份一相对 于民族归属在具体特征上的特殊性,例如,“希腊”民族成员的身份,依 照定义本来就是独特的(sui generis),(3)各种民族主义在“政治上” 的力量相对于它们在哲学上的贫困与不统一。换言之,和大多数其他的 主义不同的是,民族主义从未产生它自己的伟大思想家:没有它的霍布 斯(bbbs)、托克维尔、马克思或韦伯。这种“空洞性”很容易让具有 世界主义精神和能够使用多种语言的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产生某种轻视 的态度。就好像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面对奥克兰(Oak lad)的时候,人们会很快下结论说那里是一个“空无--物的地方” (there is‘no there there')*。即使像奈伦这么同情民族主义的学者也 还是会如此写道:“‘民族主义’是现代历史发展中的病态。如同‘神 经衰弱’之于个人一样的不可避免,它既带有与神经衰弱极类似的本质 上的暖昧性,也同样有着退化成痴呆症的内在可能性一这个退化可能 性乃是根源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所共同面临的无助的两难困境之中(这 种痴呆症等于是社会的幼稚病),并且,在多数情况下是无药可 医的。”8 有一部分的困难来自于,人们虽然不会把“年龄”这个概念当作-一 个专有名词,他们却常常不自觉地把民族主义当作专有名词,将它视为 一个具有特定专属内容的存在实体,然后把“它”区别为一种意识形 态。(请注意,假如每个人都有年龄,那么“年龄”只不过是一种分析 性的表达语汇而已。)我想,如果我们把民族主义当作像“血缘关系” (kinship)或“宗教”(religion)这类的概念来处理,而不要把它理解为 “There is no there there”这句话意指“那个地方是人工的,不真实的,缺乏本质的,没 有核心的”。这是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1874一1946)在她1937年 的作品《每个人的自传》(Everybody's Autobiography)之中描述奥克兰的名句。斯泰因的少 女时期是在北加州的奥克兰和旧金山地区度过的,后来她长住巴黎,视之为其精神上的故 乡。在《巴黎,法国》(Pars,France)(I940)一书中,斯泰因描述法国是她的第.二个国 家,“它(法国)不是真的(我的国家),但它真的在那里。”(It is not real but it is really there.)试将本句话与前句作-一对比。参见斯泰因:《巴黎,法国》(New York:iveright, 1970),第2页。一-译者注 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