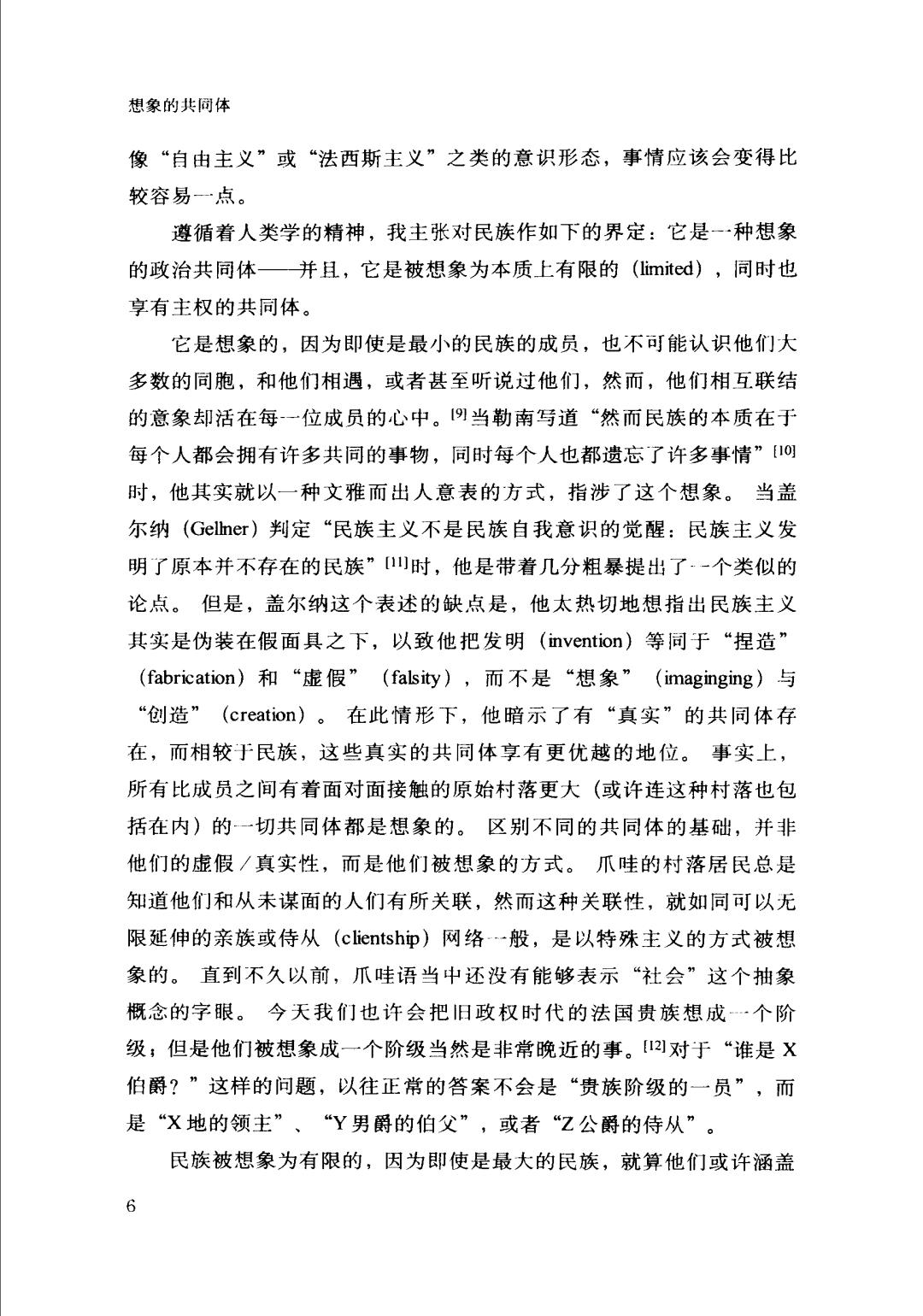
想象的共同体 像“自由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事情应该会变得比 较容易一点。 遵循着人类学的精神,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一种想象 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 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 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 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鬥当勒南写道“然而民族的本质在于 每个人都会拥有许多共同的事物,同时每个人也都遗忘了许多事情”o] 时,他其实就以一种文雅而出人意表的方式,指涉了这个想象。当盖 尔纳(Gellner)判定“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发 明了原本并不存在的民族”山时,他是带着几分粗暴提出了-个类似的 论点。但是,盖尔纳这个表述的缺点是,他太热切地想指出民族主义 其实是伪装在假面具之下,以致他把发明(invention)等同于“捏造” (fabrication)和“虚假”(falsity),而不是“想象”(imaginging)与 “创造”(creation)。在此情形下,他暗示了有“真实”的共同体存 在,而相较于民族,这些真实的共同体享有更优越的地位。事实上, 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 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 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爪哇的村落居民总是 知道他们和从未谋面的人们有所关联,然而这种关联性,就如同可以无 限延伸的亲族或侍从(clientship)网络-般,是以特殊主义的方式被想 象的。直到不久以前,爪哇语当中还没有能够表示“社会”这个抽象 概念的字眼。今天我们也许会把旧政权时代的法国贵族想成…个阶 级,但是他们被想象成一个阶级当然是非常晚近的事。2]对于“谁是X 伯爵?”这样的问题,以往正常的答案不会是“贵族阶级的一员”,而 是“X地的领主”、“Y男爵的伯父”,或者“Z公爵的侍从”。 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们或许涵盖 6

第·一章导论 了十亿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界,纵然是可变的,也还是有限的。 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虽然在某些时代, 基督徒确实有可能想象地球将成为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星球;然而,即使 最富于救世主精神的民族主义者也不会像这些基督徒一样地梦想有朝· 日,全人类都会成为他们民族的一员。 民族被想象为拥有主权,因为这个概念诞生时,启蒙运动与大革命 正在毁坏神谕的、阶层制的皇朝的合法性。民族发展臻于成熟之时, 人类史刚好步入…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即使是普遍宗教最虔诚的追 随者,也不可避免地被迫要面对生机勃勃的宗教多元主义,并且要面对 每一个信仰的本体论主张与它所支配和领土范围之间也有不一致的现 实。民族于是梦想着成为自由的,并且,如果是在上帝管辖下,直接 的自由。衡量这个自由的尺度与象征的就是主权国家。 最后,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 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 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 人们甘愿为民族一一这个有限的想象—一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猛然之间,这些死亡迫使我们直接面对民族主义提出来的核心问 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种只有短暂历史(不超过两个世纪)的,缩 小了的想象竟然能够激发起如此巨大的牺牲?我相信,只有探究民族 主义的文化根源,我们才有可能开始解答这个问题。 注释: [1]我选择用这个论述方式只是想强调战斗的规模和形态,而不是要追究罪责。为了 避免可能的误解,我们应该要说1978年12月的人侵源起,最早可以追湖到1971年的两个 革命运动党人之间的武装冲突。在1977年4月之后,最初由柬埔寨人发动,但越南人随 即跟进的边界突击行动的规模和范围逐步扩大,并在1977年12月升级成越南的大规模入 侵。然而这些突击行动的目的都不是要推翻敌方政权或占领大片领土,而且涉及的部队 人数也不能和198年12月所部署的部队相比。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的争论思虑最周详 的讨论,请参见斯蒂芬·黑德(Stephen P.Heder):《束埔寨一越南冲突》(The Kampu~ chean-Vietnamese Conflict),收于戴维·W.P.艾略特(David W.P.Elliot)编:《第三次中 南半岛冲突》(The Third Indo China Conflict),第21-67页,安东尼·巴纳特(Anthony Barnett):《共产:政权间之冲突与越南》(Inter-Communist conflicts and Vietnam),载于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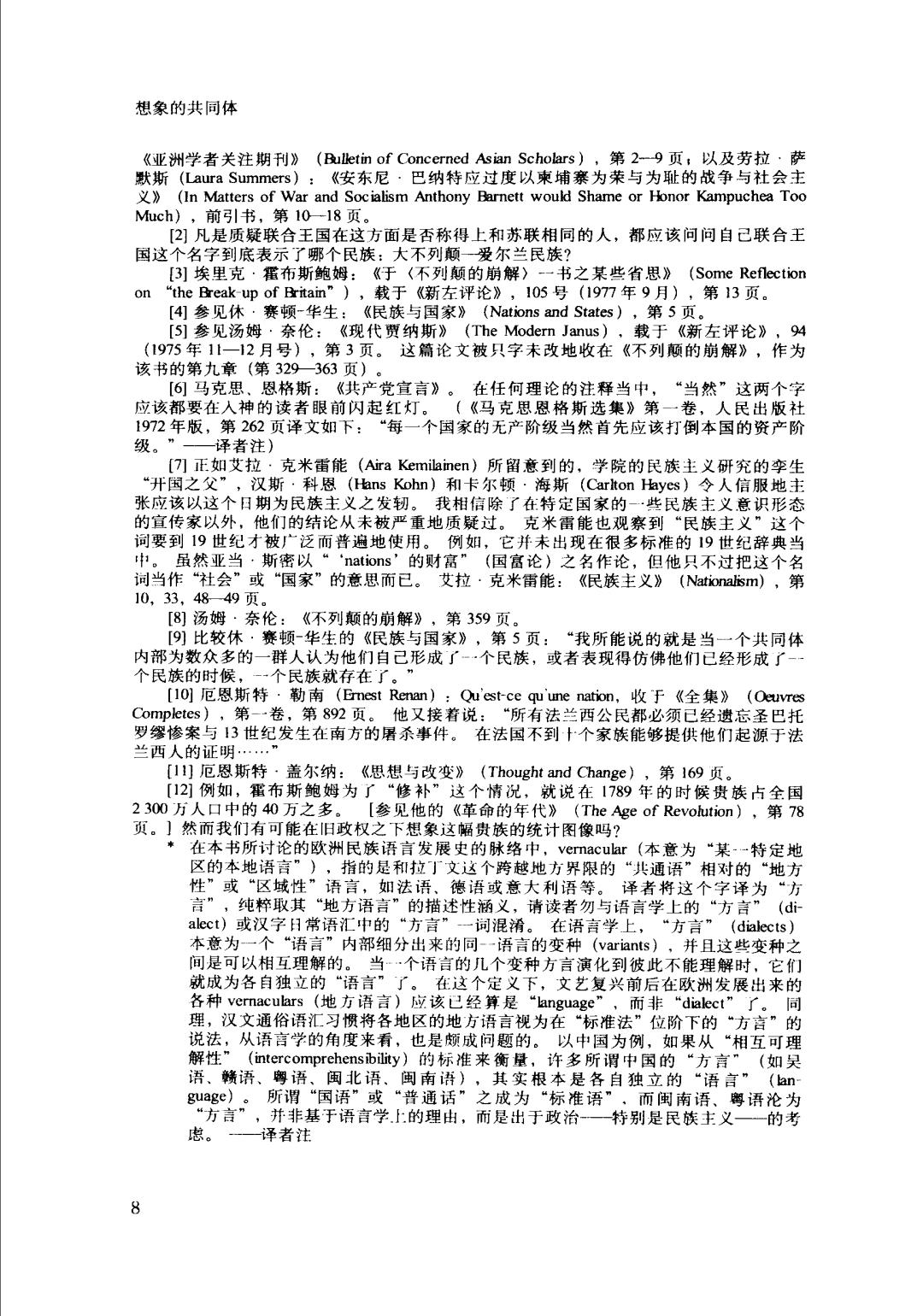
想象的共同体 《亚洲学者关注期刊》(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第2-9页,以及劳拉·萨 默斯(Laura Summers):《安东尼·巴纳特应过度以柬埔寨为荣与为耻的战争与社会主 (In Matters of War and Socialism Anthony Barnett would Shame or Honor Kampuchea Too Much),前引书,第10一18页。 [2]凡是质疑联合王国在这方面是否称得上和苏联相同的人,都应该问问自己联合王 国这个名字到底表示了哪个民族:大不列颠爱尔兰民族? [3]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于〈不列颠的崩解)-一书之某些省思》(Some Reflection on“the Break-up of Britain”),载于《新左评论》,10s号(1977年9月),第13页。 [4]参见休·赛顿-华生:《民族与国家》(Nations and States),第5页。 [S]参见汤姆·奈伦:《现代贾纳斯》(The Modern Janus),载于《新左评论》,94 (1975年11一12月号),第3页。这篇论文被只字未改地收在《不列颠的崩解》,作为 该书的第九章(第329一36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在任何理论的注释当中,“当然”这两个字 应该都要在入神的读者眼前闪起红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262页译文如下:“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 级。” —译者注) []正如艾拉·克米雷能(Aira Kemilainen)所留意到的,学院的民族主义研究的孪生 “开国之父”,汉斯·科恩(tans Kohn)和卡尔顿·海斯(Carlton Hayes)令人信服地主 张应该以这个日期为民族主义之发轫。我相信除了在特定国家的-·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的宣传家以外,他们的结论从未被严重地质疑过。克米雷能也观察到“民族主义”这个 词要到19世纪才被广泛而普遍地使用。例如,它并未出现在很多标准的19世纪辞典当 中。虽然亚当·斯密以“‘nations'的财富”(国富论)之名作论,但他只不过把这个名 词当作“社会”或“国家”的意思而已。艾拉·克米雷能:《民族主义》(Nationalism),第 10,33,48一49页。 [8]汤姆·奈伦:《不列颠的崩解》,第359页。 [9]比较休·赛顿-华生的《民族与国家》,第5页:“我所能说的就是当一个共同体 内部为数众多的一群人认为他们自己形成了-·个民族,或者表现得仿佛他们已经形成了- 个民族的时候,-一个民族就存在了。 [1O]厄恩斯特·勒南(Ernest Renan):Qu'est-cequ'une nation,收于《全集》(Oeuvres Completes),第-卷,第892页。他又接着说:“所有法兰西公民都必须已经遗忘圣巴托 罗缪惨案与I3世纪发生在南方的屠杀事件。在法国不到十个家族能够提供他们起源于法 兰西人的证明…” [11)厄恩斯特·盖尔纳:《思想与改变》(Thought and Change),第169页。 [12]例如,霜布斯鲍姆为了“修补”这个情况,就说在1789年的时候贵族占全国 2300万人口中的40万之多。[参见他的《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Revolution),第78 页。】然而我们有可能在旧政权之下想象这幅贵族的统计图像吗? 在本书所讨论的欧洲民族语言发展史的脉络中,vernacular(本意为“某-一特定地 区的本地语言”),指的是和拉丁文这个跨越地方界限的“共通语”相对的“地方 性”或“区域性”语言,如法语、德语或意大利语等。译者将这个字译为“方 言 ,纯粹取其“地方语言”的描述性涵义,请读者勿与语言学上的“方言”( alect)或汉字日常语汇中的“方言”一词混淆。在语言学上,“方言”(dialects) 本意为一个“语言”内部细分出来的同-语言的变种(variants),并且这些变种之 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当…个语言的几个变种方言演化到彼此不能理解时,它们 就成为各自独立的“语言”了。在这个定义下,文艺复兴前后在欧洲发展出来的 各种vernaculars(地方语言)应该已经算是“language”,而非“dialect”了。 同 理,汉文通俗语汇习惯将各地区的地方语言视为在“标准法”位阶下的“方言”的 说法,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也是颇成问题的。以中国为例,如果从“相互可理 解性”(intercomprehensibility)的标准来衡量,许多所谓中国的“方言”(如吴 语、赣语、粤语、闽北语、闽南语),其实根本是各自独立的“语言”(n guage)。所谓“国语”或“普通话”之成为“标准语”,而闽南语、爵语沦为 “方言”,并非基于语言学上的理由,而是出于政治—特别是民族主义一一的考 虑。 —译者注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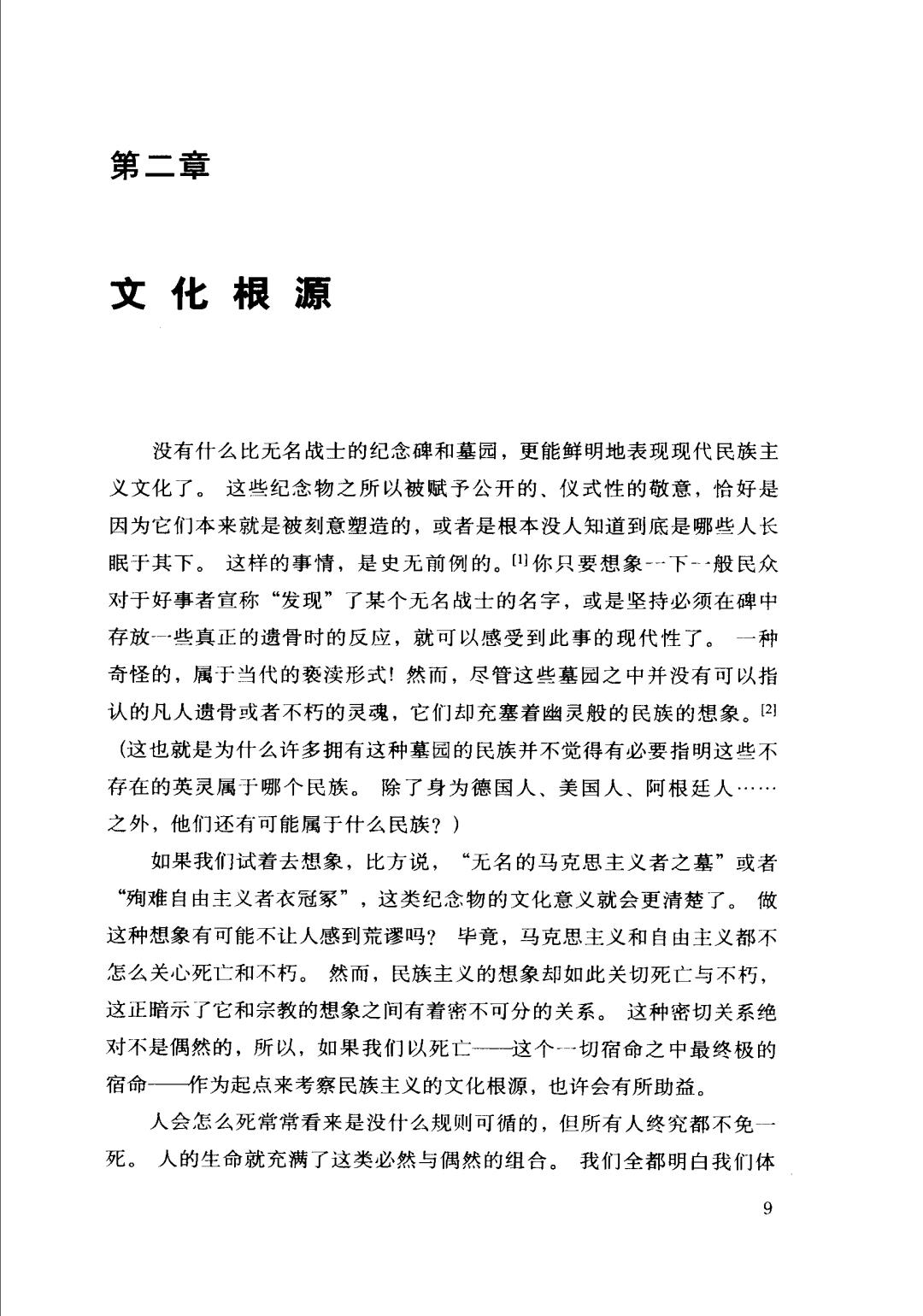
第二章 文化根源 没有什么比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和墓园,更能鲜明地表现现代民族主 义文化了。这些纪念物之所以被赋予公开的、仪式性的敬意,恰好是 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被刻意塑造的,或者是根本没人知道到底是哪些人长 眠于其下。这样的事情,是史无前例的。山你只要想象一下一般民众 对于好事者宣称“发现”了某个无名战士的名字,或是坚持必须在碑中 存放一些真正的遗骨时的反应,就可以感受到此事的现代性了。一种 奇怪的,属于当代的亵渎形式!然而,尽管这些墓园之中并没有可以指 认的凡人遗骨或者不朽的灵魂,它们却充塞着幽灵般的民族的想象。2! (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拥有这种墓园的民族并不觉得有必要指明这些不 存在的英灵属于哪个民族。除了身为德国人、美国人、阿根廷人… 之外,他们还有可能属于什么民族?) 如果我们试着去想象,比方说,“无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墓”或者 “殉难自由主义者衣冠冢”,这类纪念物的文化意义就会更清楚了。做 这种想象有可能不让人感到荒谬吗?毕竟,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不 怎么关心死亡和不朽。然而,民族主义的想象却如此关切死亡与不朽, 这正暗示了它和宗教的想象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绝 对不是偶然的,所以,如果我们以死亡一这个一切宿命之中最终极的 宿命作为起点来考察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也许会有所助益。 人会怎么死常常看来是没什么规则可循的,但所有人终究都不免一 死。人的生命就充满了这类必然与偶然的组合。我们全都明白我们体 9

想象的共同体 内特定的基因遗传,我们的性别,我们生存的时代,我们种种生理上的 能力,我们的母语等,虽是偶然的,却也是难以改变的。传统的宗教 世界观有·…个伟大的价值(我]自然不应将此处所谓的价值和他们在合 理化种种支配和剥削体系时所扮演的角色混为一谈),也就是他们对身 处宇宙之内的人、人类作为物种的存在以及生命之偶然性的关心。佛 教、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在许多不同的社会中存续了千年以上,这一惊 人的事实,证明了这些宗教对于人类苦难的重荷,如疾病、肢体残废、 悲伤、衰老和死亡,具有充满想象力的回应能力。为何我生而为盲 人?为何我的挚友不幸瘫痪?为何我的爱女智能不足?宗教企图作 出解释。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演化论进步论形态的思想体系的 -大弱点,就是对这些问题不耐烦地无言以对。刷同时,宗教思想也以种 种不同的方式通过将宿命转化成生命的连续性(如业报或原罪等观 念),隐讳模糊地暗示不朽的可能。经由此,宗教思想涉及了死者与未 降生者之间的联系,即关于重生的秘密。任何“个曾经经历过他们的子 女受孕与诞生的人,都会模糊地领会到“连续”这个字眼当中同时包含 的结合、偶然和宿命。[这里,演化论进步论思想又居于下风了,因为 它对任何连续性的观念抱着近乎赫拉克利特式(Herac litean)*的厌恶。] 我之所以提出这些似乎有点愚蠢的观点,主要是因为在西欧,18世 纪不只标志了民族主义的降生,也见证了宗教式思考模式的衰颓。这 个启蒙运动和理性世俗主义的世纪同时也带来了属于它自己特有的、现 代的黑暗。尽管宗教信仰逐渐退潮,人的受苦一有一部分乃因信仰 而生一一却并未随之消失。天堂解体了:所以有什么比命运更没道理 的呢?救赎是荒诞不经的:那又为什么非要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生命不 可呢?因而,这个时代所亟需的是,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 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会知道,很少有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希腊哲学家,主张斗争和不断的变 化是宇宙的自然状况。一译者注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