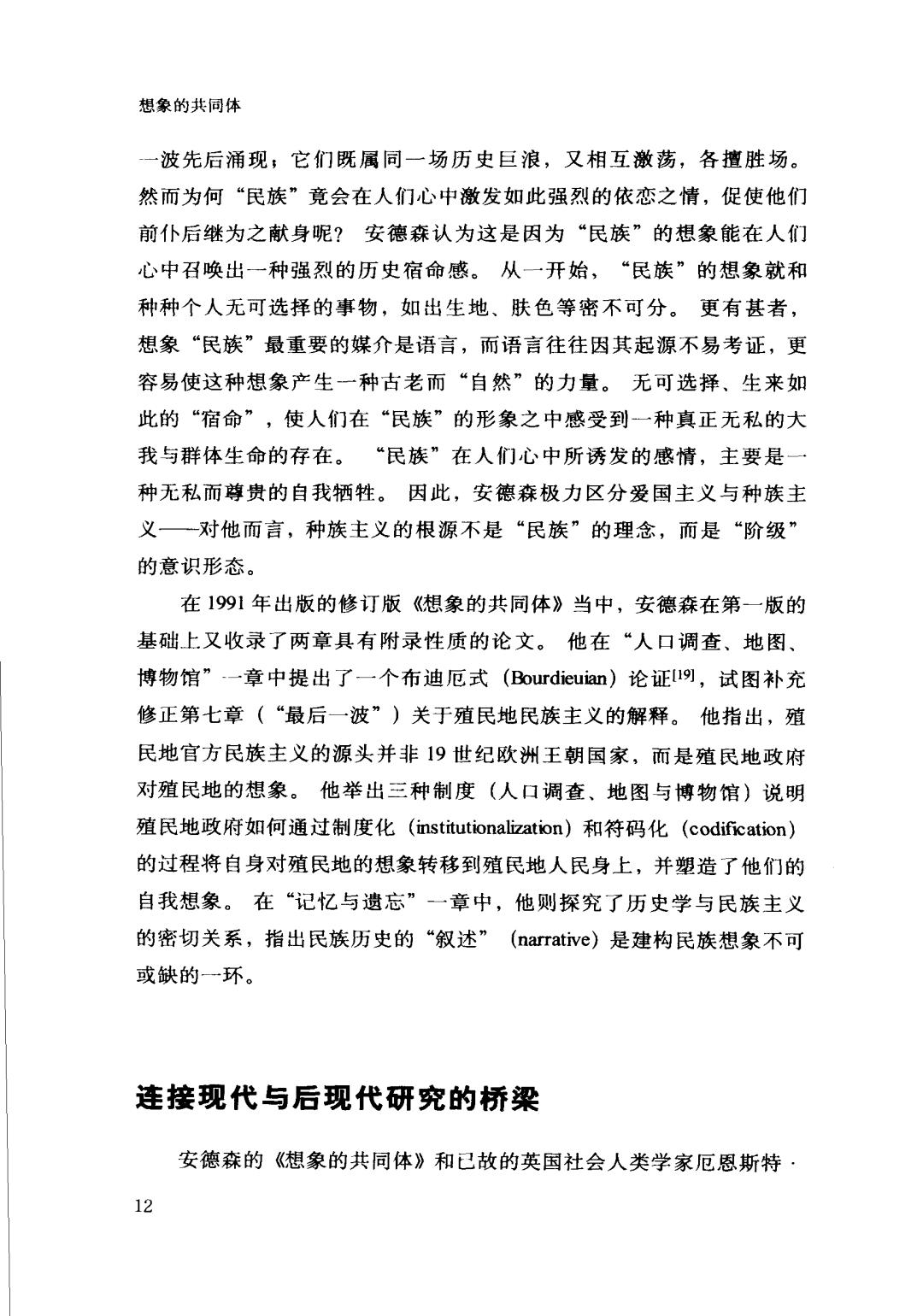
想象的共同体 一波先后涌现,它们既属同一场历史巨浪,又相互激荡,各擅胜场。 然而为何“民族”竟会在人们心中激发如此强烈的依恋之情,促使他们 前仆后继为之献身呢?安德森认为这是因为“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 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从一开始,“民族”的想象就和 种种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等密不可分。更有甚者, 想象“民族”最重要的媒介是语言,而语言往往因其起源不易考证,更 容易使这种想象产生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无可选择、生来如 此的“宿命”,使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 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民族”在人们心中所诱发的感情,主要是一 种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牲。因此,安德森极力区分爱国主义与种族主 义一对他而言,种族主义的根源不是“民族”的理念,而是“阶级” 的意识形态。 在1991年出版的修订版《想象的共同体》当中,安德森在第一版的 基础上又收录了两章具有附录性质的论文。他在“人口调查、地图、 博物馆”一章中提出了一个布迪厄式(Bourdieuian)论证l9,试图补充 修正第七章(“最后一波”)关于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解释。他指出,殖 民地官方民族主义的源头并非19世纪欧洲王朝国家,而是殖民地政府 对殖民地的想象。他举出三种制度(人口调查、地图与博物馆)说明 殖民地政府如何通过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和符码化(codification) 的过程将自身对殖民地的想象转移到殖民地人民身上,并塑造了他们的 自我想象。在“记忆与遗忘”一章中,他则探究了历史学与民族主义 的密切关系,指出民族历史的“叙述”(narrative)是建构民族想象不可 或缺的一环。 连接现代与后现代研究的桥梁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和己故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厄恩斯特·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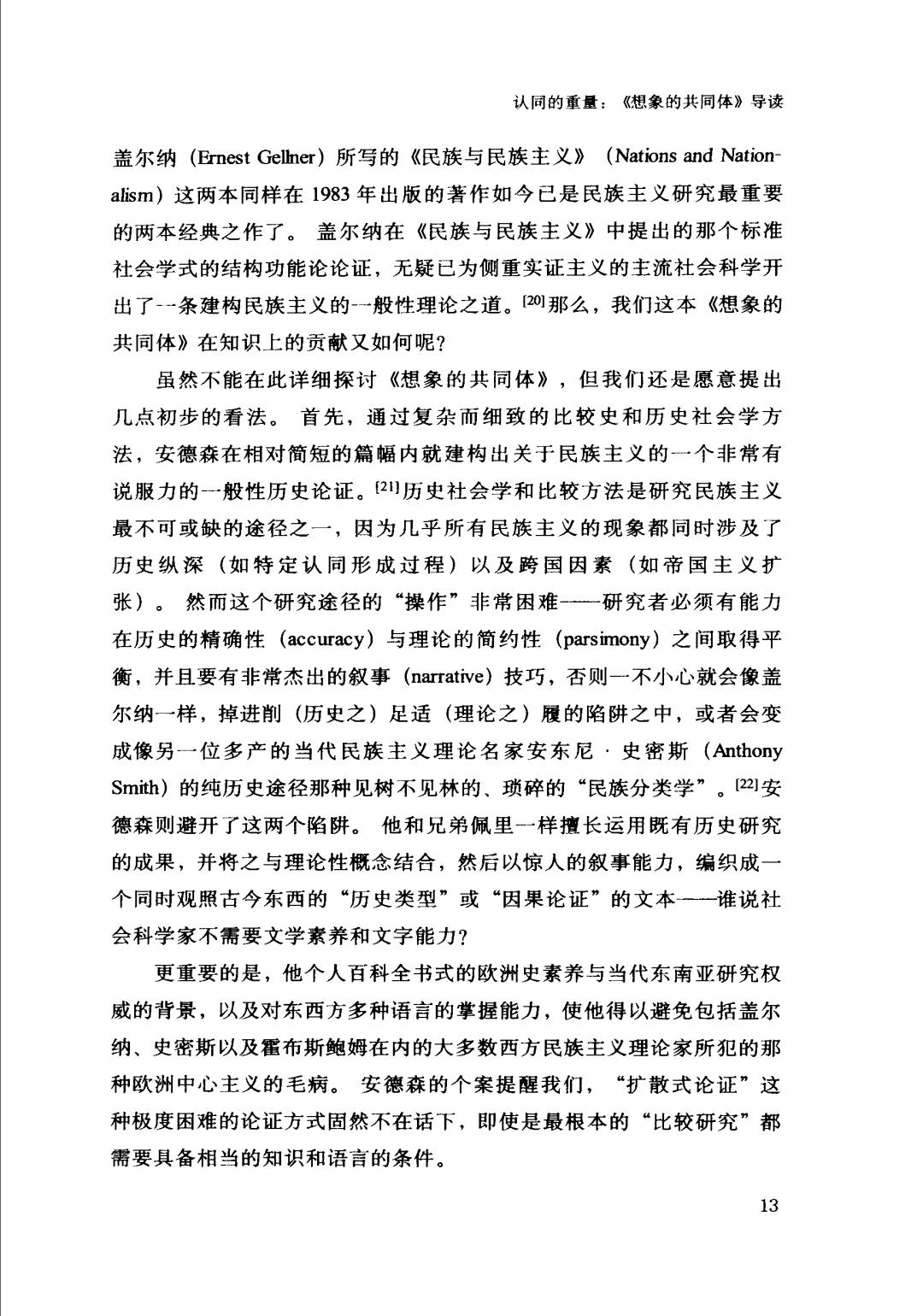
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 盖尔纳(Ernest Gellner)所写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 alism)这两本同样在1983年出版的著作如今已是民族主义研究最重要 的两本经典之作了。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提出的那个标准 社会学式的结构功能论论证,无疑已为侧重实证主义的主流社会科学开 出了一条建构民族主义的-一般性理论之道。[20]那么,我们这本《想象的 共同体》在知识上的贡献又如何呢? 虽然不能在此详细探讨《想象的共同体》,但我们还是愿意提出 几点初步的看法。首先,通过复杂而细致的比较史和历史社会学方 法,安德森在相对简短的篇幅内就建构出关于民族主义的一个非常有 说服力的一般性历史论证。2)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方法是研究民族主义 最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因为几乎所有民族主义的现象都同时涉及了 历史纵深(如特定认同形成过程)以及跨国因素(如帝国主义扩 张)。然而这个研究途径的“操作”非常困难-一研究者必须有能力 在历史的精确性(accuracy)与理论的简约性(parsimony)之间取得平 衡,并且要有非常杰出的叙事(narrative)技巧,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像盖 尔纳一样,掉进削(历史之)足适(理论之)履的陷阱之中,或者会变 成像另一位多产的当代民族主义理论名家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的纯历史途径那种见树不见林的、琐碎的“民族分类学”。[22]安 德森则避开了这两个陷阱。他和兄弟佩里一样擅长运用既有历史研究 的成果,并将之与理论性概念结合,然后以惊人的叙事能力,编织成一 个同时观照古今东西的“历史类型”或“因果论证”的文本一一谁说社 会科学家不需要文学素养和文字能力? 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百科全书式的欧洲史素养与当代东南亚研究权 威的背景,以及对东西方多种语言的掌握能力,使他得以避免包括盖尔 纳、史密斯以及霍布斯鲍姆在内的大多数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家所犯的那 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毛病。安德森的个案提醒我们,“扩散式论证”这 种极度困难的论证方式固然不在话下,即使是最根本的“比较研究”都 需要具备相当的知识和语言的条件。 13

想象的共同体 第二,安德森超越般将民族主义当作-一种单纯的政治现象的表 层观点,将它与人类深层的意识与世界观的变化结合起来。他将民族 主义放在比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更广阔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 脉络当中来理解一民族主义因此不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运 动,而是一种更复杂深刻的文化现象(或者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 种“文化的人造物”)。这种颇具人类学精神一或者有点接近法国 年鉴学派(Annales)史学所谓“心态史”(histoire des mentalites)、“历 史心理学”(psychologie historique)、“理念的社会史”(histoire sociale desidees)或“社会一文化史”(histoire socio-cukturelle)[23]一的途径将 我们对民族主义的认识从“社会基础”或“政治动员”的层面扩展到对 它的“文化根源”的探求之上。安德森不但没有像一般社会科学家那 样以实证主义式的傲慢(hubris)忽视人类追求“归属感”的需求(因为 “不够科学”,或者因为那是“虚假意识”或“病态”),反而直接面 对这个真实而深刻的存在性问题,并在他的架构中为之赋予适当的诠释 与意义。正因如此,他对民族主义的解释就更能掌握到人类行动的深 层动机。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个途径间接肯定了德国哲学家赫德 (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所说“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的箴言。[24] 第三,《想象的共同体》的论证结合了多重的研究途径,同时兼顾 文化与政治、意识与结构,开创了丰富的研究可能性,因此被北欧学者 斯坦·东尼生(Stein Tonnesson)和汉斯·安德洛夫(ams Antlov)称为 “连接现代与后现代研究途径的桥梁”2]。就传统比较政治学与历史 社会学的角度而言,这本书最重要的贡献可能是它关于民族主义的各种 “历史类型”以及“民族主义兴起的结构与制度条件”的论证。安德 森的“历史的”(historical)解释和盖尔纳所建构的“非历史的” (a-historical)结构功能论解释恰好成为当代民族主义理论的两个重要 而对立的典范。不过,相对于盖尔纳在主流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方面 的巨大影响,《想象的共同体》可能对以文化与“意识”(conscious- nss)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人文学科的影响更大。安德森对宗教、象征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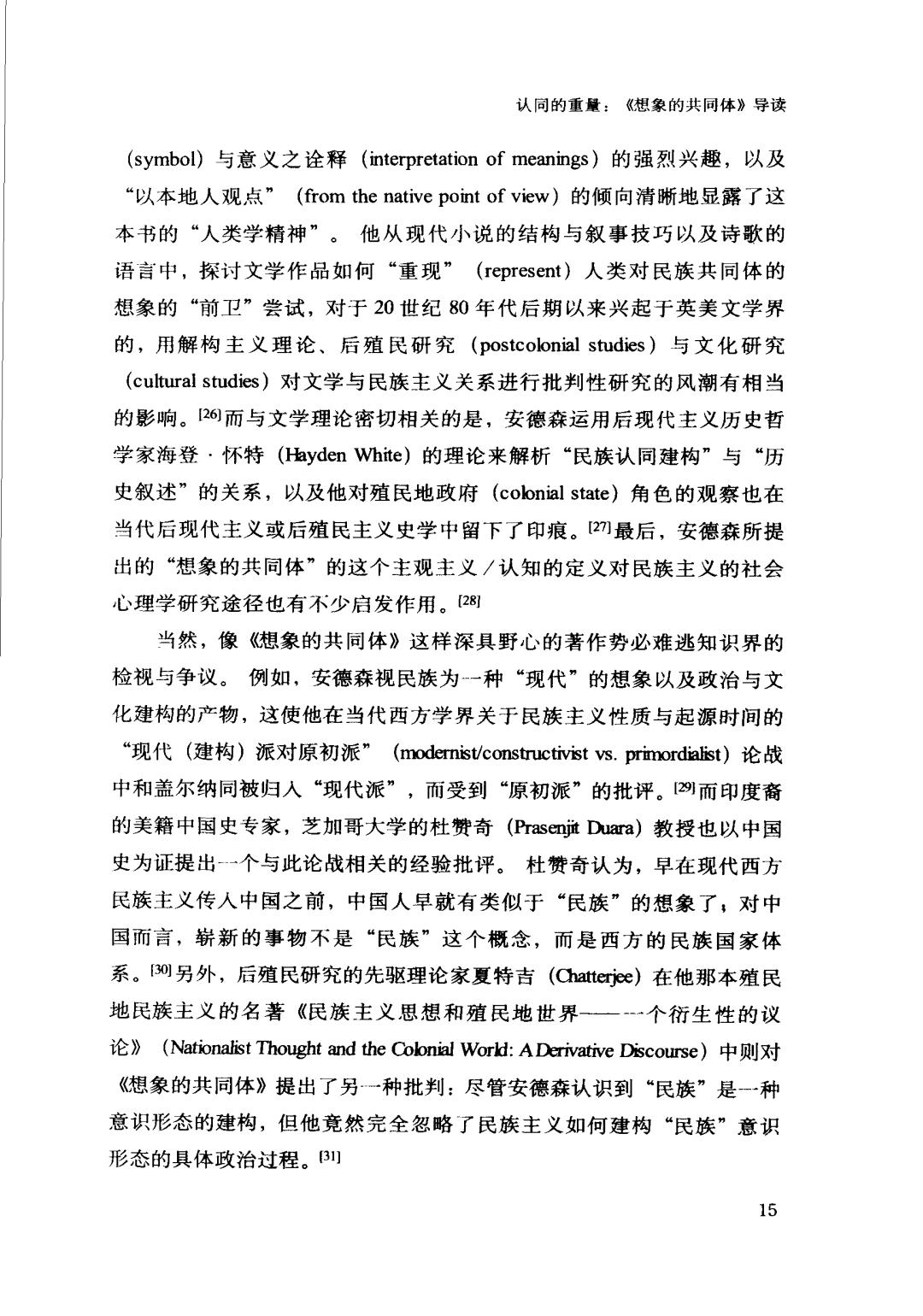
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 (symbol)与意义之诠释(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s)的强烈兴趣,以及 “以本地人观点”(from the native point of view)的倾向清晰地显露了这 本书的“人类学精神”。他从现代小说的结构与叙事技巧以及诗歌的 语言中,探讨文学作品如何“重现”(represent)人类对民族共同体的 想象的“前卫”尝试,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兴起于英美文学界 的,用解构主义理论、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与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对文学与民族主义关系进行批判性研究的风潮有相当 的影响。26而与文学理论密切相关的是,安德森运用后现代主义历史哲 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理论来解析“民族认同建构”与“历 史叙述”的关系,以及他对殖民地政府(colonial state)角色的观察也在 当代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史学中留下了印痕。2)最后,安德森所提 出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这个主观主义/认知的定义对民族主义的社会 心理学研究途径也有不少启发作用。[28] 当然,像《想象的共同体》这样深具野心的著作势必难逃知识界的 检视与争议。例如,安德森视民族为一种“现代”的想象以及政治与文 化建构的产物,这使他在当代西方学界关于民族主义性质与起源时间的 “现代(建构)派对原初派”(modernist/constructivist vs.primordialist)论战 中和盖尔纳同被归入“现代派”,而受到“原初派”的批评。2而印度裔 的美籍中国史专家,芝加哥大学的杜赞奇(Prasen啦Duara)教授也以中国 史为证提出一个与此论战相关的经验批评。杜赞奇认为,早在现代西方 民族主义传人中国之前,中国人早就有类似于“民族”的想象了,对中 国而言,崭新的事物不是“民族”这个概念,而是西方的民族国家体 系。[30另外,后殖民研究的先驱理论家夏特吉(Chatterjee)在他那本殖民 地民族主义的名著《民族主义思想和殖民地世界 一…个衍生性的议 论》(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ADerivative Discourse)中则对 《想象的共同体》提出了另一种批判:尽管安德森认识到“民族”是-一种 意识形态的建构,但他竟然完全忽略了民族主义如何建构“民族”意识 形态的具体政治过程。B]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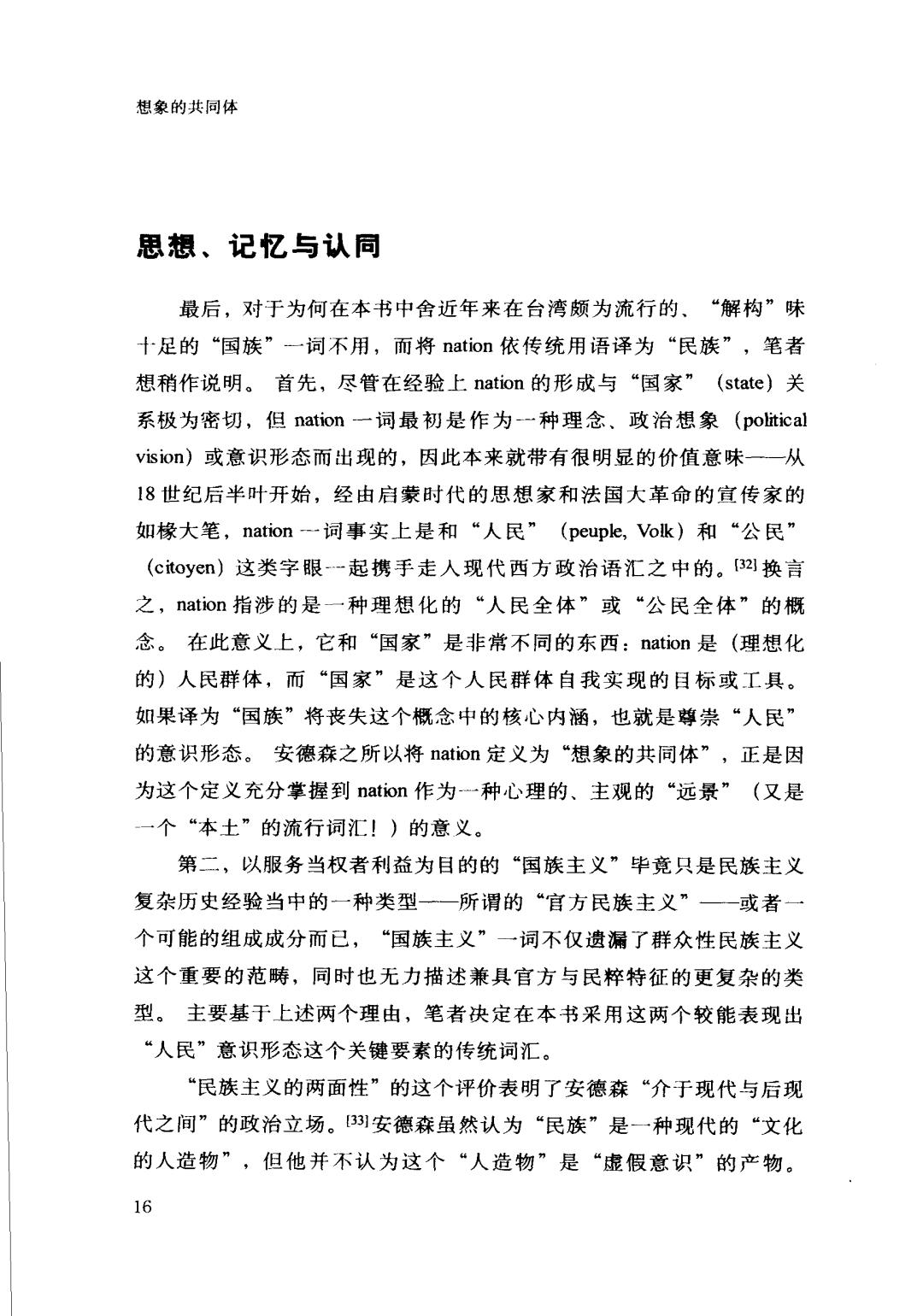
想象的共同体 思想、记忆与认同 最后,对于为何在本书中舍近年来在台湾颇为流行的、“解构”味 十足的“国族”一词不用,而将nation依传统用语译为“民族”,笔者 想稍作说明。首先,尽管在经验上nation的形成与“国家”(state)关 系极为密切,但nation一词最初是作为一种理念、政治想象(political vision)或意识形态而出现的,因此本来就带有很明显的价值意味一一从 18世纪后半叶开始,经由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和法国大革命的宣传家的 如椽大笔,nation一词事实上是和“人民”(peuple,Vo)和“公民” (citoyen)这类字眼-一起携手走人现代西方政治语汇之中的。[32]换言 之,nation指涉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民全体”或“公民全体”的概 念。在此意义上,它和“国家”是非常不同的东西:nation是(理想化 的)人民群体,而“国家”是这个人民群体自我实现的目标或工具。 如果译为“国族”将丧失这个概念中的核心内涵,也就是尊崇“人民” 的意识形态。安德森之所以将nation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正是因 为这个定义充分掌握到nation作为一种心理的、主规的“远景”(又是 一个“本土”的流行词汇!)的意义。 第二,以服务当权者利益为目的的“国族主义”毕竞只是民族主义 复杂历史经验当中的一种类型一所谓的“官方民族主义”—或者一 个可能的组成成分而已,“国族主义”一词不仅遗漏了群众性民族主义 这个重要的范畴,同时也无力描述兼具官方与民粹特征的更复杂的类 型。主要基于上述两个理由,笔者决定在本书采用这两个较能表现出 “人民”意识形态这个关键要素的传统词汇。 “民族主义的两面性”的这个评价表明了安德森“介于现代与后现 代之间”的政治立场。33]安德森虽然认为“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文化 的人造物”,但他并不认为这个“人造物”是“虚假意识”的产物。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