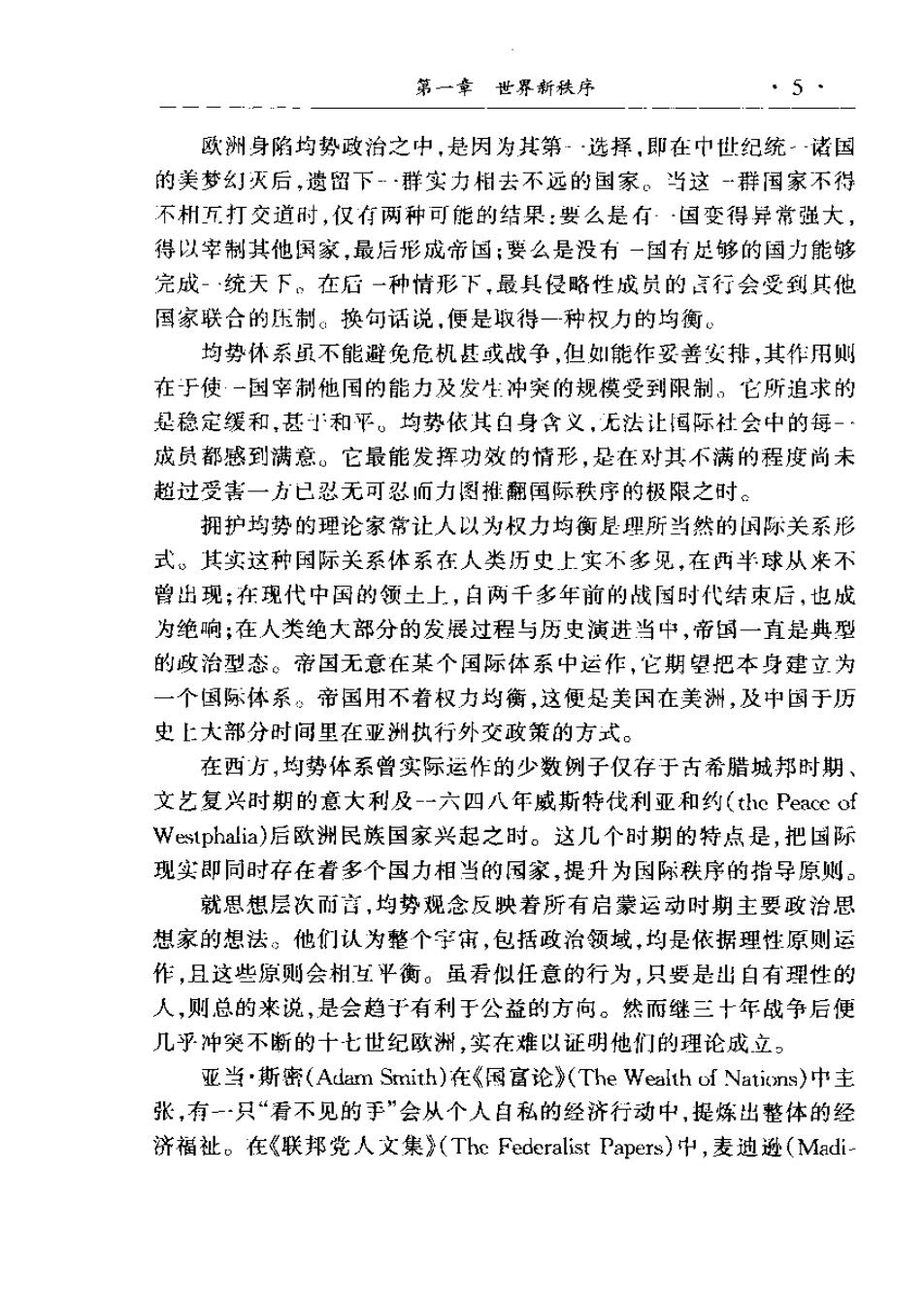
第一章世界新秩序 欧洲身陷均势政治之中,是因为其第·选择,即在巾世纪统·诸国 的美梦J灭后,遗留下-·群实力相去不远的国家。当这一群国家不得 不机万打交道时,仅有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是有··国变得异常强大, 得以宰制其他国家,最后形成帝国:要么是没有一国有足够的国力能够 完成-统天下。在后一种情形下,最具侵略性成员的言行会受到其他 国家联合的压制。换句话说,便是取得一种权力的均衡。 均势休系虽不能避免危机甚或战争,但如能作妥善安排,其作用则 在于使·一国宰制他国的能力及发生:冲突的规模受到限制。它听追求的 起稳定缓和,甚和平。均势依其自身含义,无法让国际社会中的每-· 成员都感到满意。它最能发挥功效的情形,是在对其不满的程度尚未 超过受害一方已忍无可忍而力图椎翻国际秩序的极限之时。 拥护均势的理论家常让人以为权力均衡是理所当然的国际关系形 式。其实这种国际关系体系在人类历史上实不多见,在西半球从来不 曾出现;在现代中国的领土上,自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结束后,也成 为绝响:在人类绝大部分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演进当中,帝国一直是典型 的政治型态。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为 一个国际体系帝国用不着权力均衡,这便是美国在美洲,及中国于历 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在亚洲执行外交政策的方式。 在西方,均势体系曾实际运作的少数例子仅存于古希猎城邦时期、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及-六四八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后欧洲民族国家兴起之时。这几个时期的特点是,把国际 现实即同时存在着多个国力相当的国家,提升为国际秩序的指导原则。 就思想层次而苦,均势规念反映着所有启蒙运动时期主要政治思 想家的想法。他们认为整个辛宙,包括政治领域,均是依据理性原则运 作,且这些原会相互平衡。虽看似任意的行为,只要是出自有理性的 人,则总的来说,是会趋于有利于公益的方向。然而继三十年战争后便 几乎冲突不断的十七世纪欧洲,实在雉以证明他们的理论成立。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主 张,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从个人自私的经济行动中,提烁出整体的经 济福祉。在《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中,麦迪逊(Mad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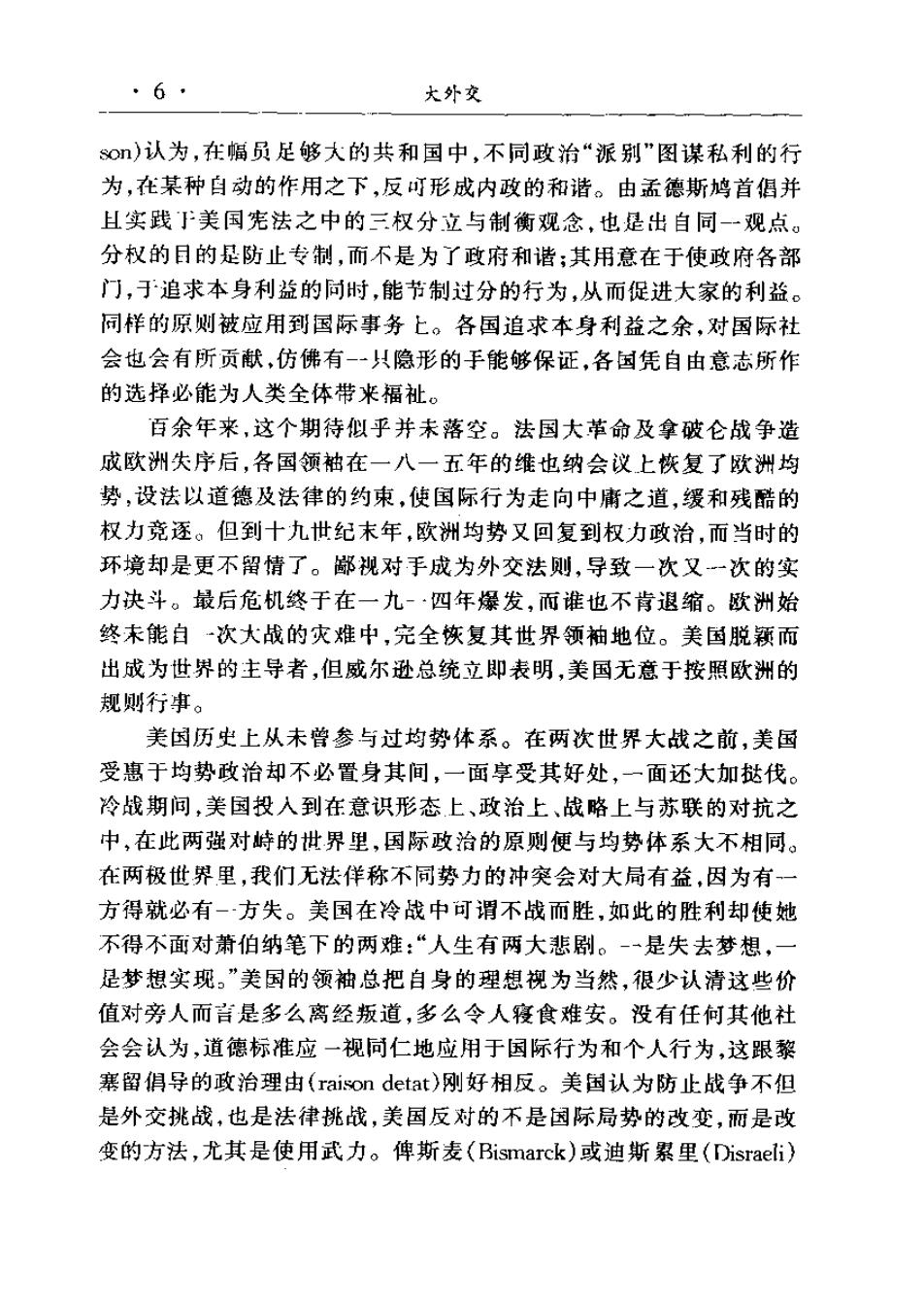
6 大外交 so)认为,在幅员足够大的共和国中,不同政治“派别”图谋私利的行 为,在某种自动的作用之下,反可形成内政的和谐。由孟德斯鸠首倡并 且实践美国宪法之中的三权分立与制衡观念,也是出自同-一观点。 分权的目的是防止专制,而不是为了政府和谐;其用意在于使政府各部 门,丁追求本身利益的同时,能节制过分的行为,从而促进大家的利益。 同样的原则被应用到国际事务上。各国追求本身利益之余,对国际社 会也会有所贡献,仿佛有-一只隐形的手能够保证,各国凭自由意志所作 的选择必能为人类全体带来福祉。 百余年来,这个期待似乎并未落空。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造 成欧洲失序后,各国领袖在一八一五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恢复了欧洲均 势,设法以道德及法律的约束,使国际行为走向中庸之道,缓和残酷的 权力竞逐。但到十九世纪末年,欧洲均势又回复到权力政治,而当时的 环境却是更不留情了。鄙视对手成为外交法则,导致一次又一次的实 力决斗。最后危机终于在一九-·四年爆发,而谁也不肯退缩。欧洲始 终未能自一次大战的灾难中,完全恢复其世界领袖地位。美国脱颖而 出成为世界的主导者,但威尔逊总统立即表明,美国无意于按照欧洲的 规则行事。 美国历史上从未曾参与过均势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 受惠于均势政治却不必置身其间,一面享受其好处,一面还大加挞伐。 冷战期间,美国投入到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战略上与苏联的对抗之 中,在此两强对峙的世界里,国际政治的原则便与均势体系大不相同。 在两极世界里,我们无法佯称不同势力的冲突会对大局有益,因为有一 方得就必有-方失。美国在冷战中可谓不战而胜,如此的胜利却使她 不得不面对萧伯纳笔下的两难:“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失去梦想,一 是梦想实现,”美国的领袖总把自身的理想视为当然,很少认清这些价 值对旁人而言是多么离经叛道,多么令人寝食难安。没有任何其他社 会会认为,道德标准应一视同仁地应用于国际行为和个人行为,这跟黎 塞留得导的政治理由(raison detat)刚好相反。美国认为防止战争不但 是外交挑战,也是法律挑战,美国反对的不是国际局势的改变,而是改 变的方法,尤其是使用武力。伸斯麦(Bismarck)或迪斯累里(Disrae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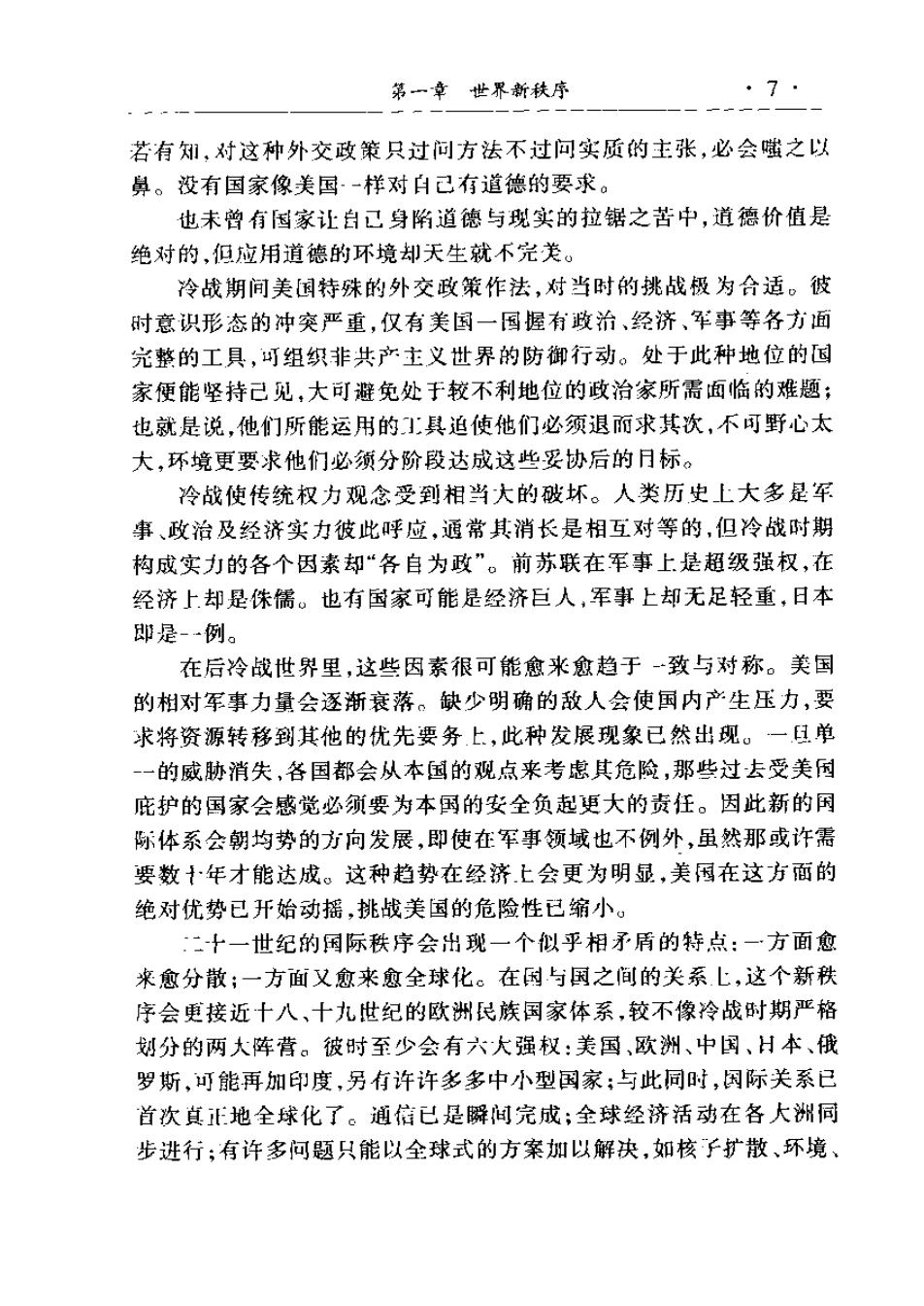
第一章世界新秩序 若有,对这种外交政策只过问方法不过问实质的主张,必会嗤之以 鼻。没有国家像美国一样对白己有道德的要求。 也末曾有国家让自己身陷道德与现实的拉锯之苦中,道德价值是 绝对的,但应用道德的环境却天生就不完关。 冷战期间美国特殊的外交政策作法,对当时的挑战极为合适。彼 时意识形态的冲突严重,仅有美国一国握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 完整的工具,可组织非共产主义世界的防御行动。处于此种地位的国 家便能坚持己见,大可避免处于较不利地位的政治家所需面临的难题; 也就是说,他们所能运用的具迫使他们必须退而求其次,不可野心太 大,环境更要求他们必须分阶段达成这些妥协后的月标。 冷战使传统权力观念受到相当大的破坏。人类历史上大多是军 事、政治及经济实力彼此呼应,通常其消长是相互对等的,但冷战时期 构成实力的各个因素却“各自为政”。前苏联在军事上.是超级强权,在 经济上却是侏儒。也有国家可能是经济巨人,军事上却无足轻重,日本 即是-一例。 在后冷战世界里,这些因素很可能愈来愈趋于致与对称。美国 的相对军事力量会逐渐衰落。缺少明确的敌人会使国内产生压力,要 求将资源转移到其他的优先要务上,此种发展现象已然出现。一且单 一的威胁消失,各国都会从本国的观点来考虑其危险,那些过去受美园 庇护的国家会感觉必须要为本国的安全负起更大的责任。因此新的国 际体系会朝均势的方向发展,即使在军事领域也不例外,虽然那或许需 要数十·年才能达成。这种趋势在经济上会更为明显,美国在这方面的 绝对优势已开始动摇,挑战美国的危险性已缩小。 :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秩序会出现一个似乎相矛屑的特点:一·方面愈 来愈分散;一方面又愈来愈全球化。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北,这个新秩 序会更接近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较不像冷战时期严格 划分的两大阵营。彼时至少会有六大强权:美国,欧洲、中国、H本、俄 罗斯,可能再加印度,另有许许多多中小型国家:与此同时,国际关系已 首次真地全球化了。通信已是瞬间完成;全球经济活动在各大洲同 步进行;有许多问题只能以全球式的方案珈以解决,如核子扩散、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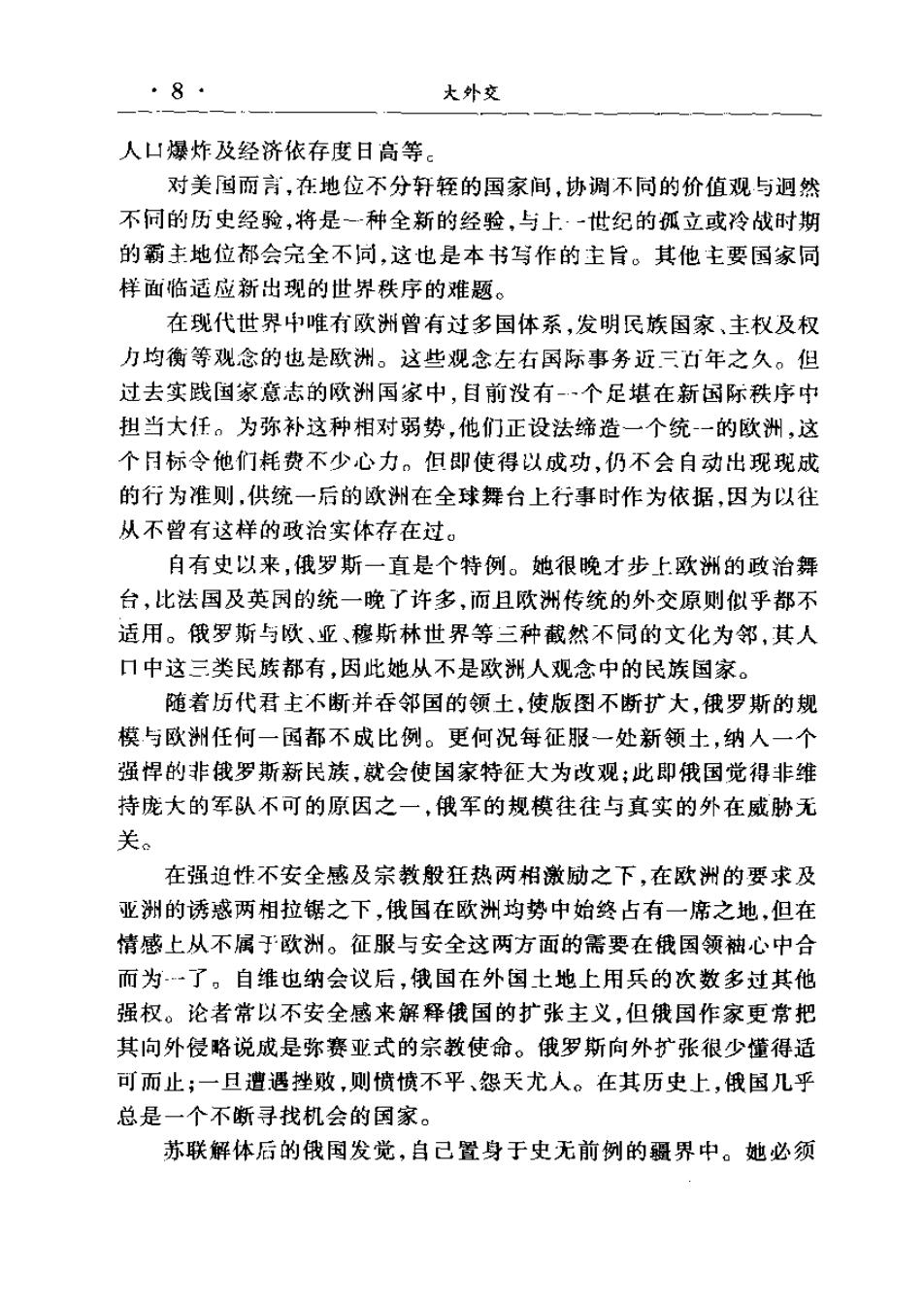
·8 大外交 人口爆炸及经济依存度日高等。 对美国而言,在地位不分轩轾的国家间,协调不同的价值观与迥然 不同的历史经验,将是一种全新的经验,与上.一世纪的孤立或冷战时期 的霸主地位都会完全不同,这也是本书写作的主旨。其他主要国家同 样面临适应新出现的世界秩序的难题。 在现代世界中唯有欧洲曾有过多国体系,发明民族国家、主权及权 力均衡等观念的也是欧洲。这些观念左右国际事务近三白年之久。但 过去实践国家意志的欧洲国家中,目前没有-个足堪在新国际秩序中 担当大任。为弥补这种相对弱势,他们正设法缔造一个统-一的欧洲,这 个目标令他们耗费不少心力。但即使得以成功,仍不会自动出现现成 的行为准则,供统一后的欧洲在全球舞台上行事时作为依据,因为以往 从不曾有这样的政治实体存在过。 自有史以来,俄罗斯一直是个特例。她很晚才步上欧洲的政治舞 台,比法国及英闲的统一晚了许多,而且欧洲传统的外交原则似乎都不 适用。俄罗斯与欧、亚、穆斯林世界等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为邻,其人 口中这三类民族都有,因此她从不是欧洲人观念中的民族国家。 随着历代君主不断并吞邻国的领土,使版图不断扩大,俄罗斯的规 模与欧洲任何一国都不成比例。更何况每征服一处新领土,纳人一个 强悍的非俄罗斯新民族,就会使国家特征大为改观;此即俄国觉得非维 持庞大的军队不可的原因之一,俄军的规模往往与真实的外在威胁无 关。 在强迫性不安全感及宗教般狂热两相激励之下,在欧洲的要求及 亚洲的诱惑两相拉锯之下,俄国在欧洲均势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但在 情感上从不属于欧洲。征服与安全这两方面的需要在俄国领袖心中合 而为一了。自维也纳会议后,俄国在外国土地上用兵的次数多过其他 强权。论者常以不安全感来解释俄国的扩张主义,但俄国作家更常把 其向外侵略说成是弥赛亚式的宗教使命。俄罗斯向外扩张很少懂得适 可而止;一且遭遇挫效,则愤愤不平、怨天尤人。在其历史上,俄国儿乎 总是一个不断寻找机会的国家。 苏联解体后的俄国发觉,自己置身于史无前例的疆界中。她必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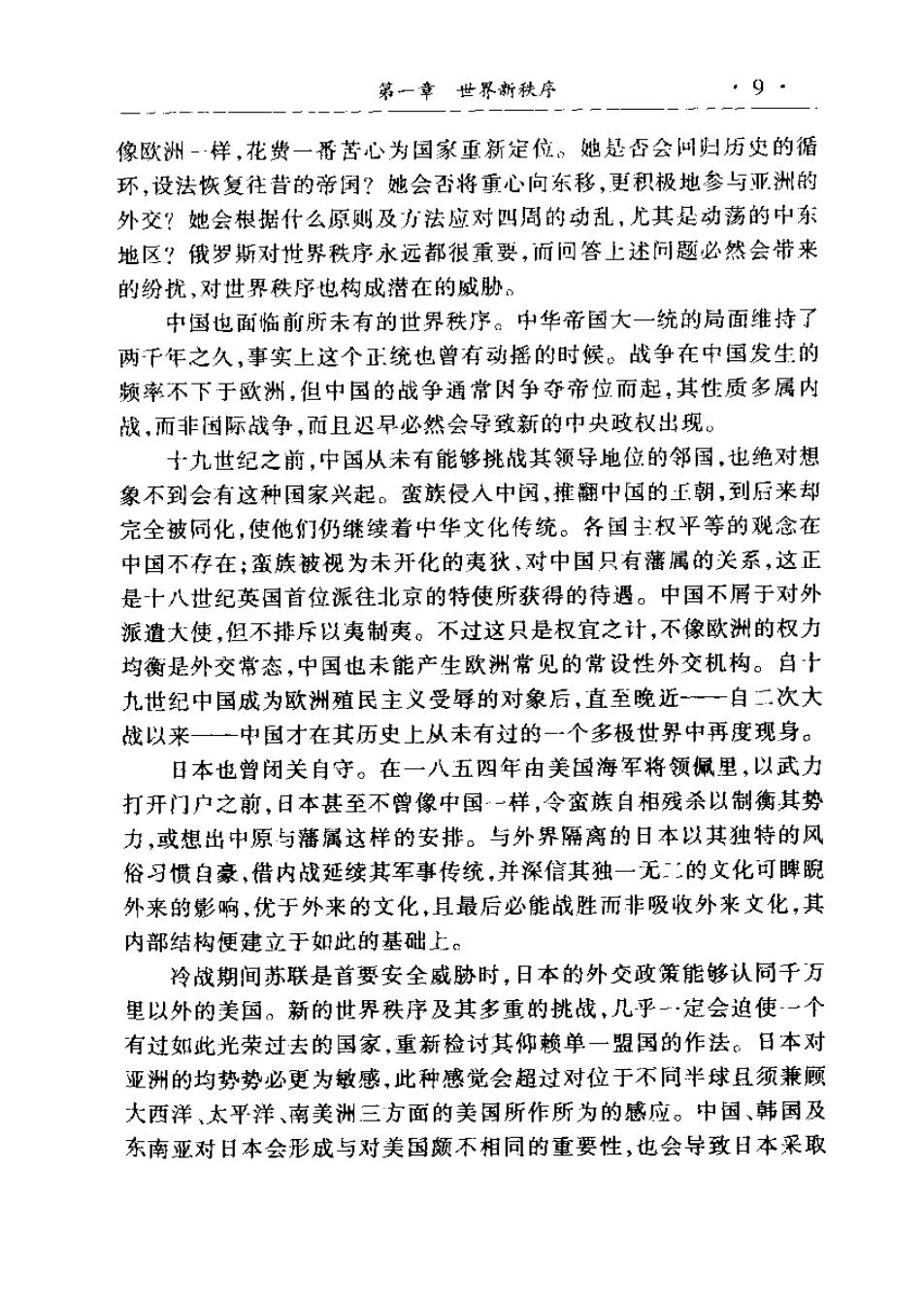
第一章世界新秩序 像欧洲-·样,花费一番苦心为国家重新定位。她是否会问归历史的循 环,设法恢复往昔的帝国?她会否将重心向东移,更积极地参与亚洲的 外交?她会根据什么原则及方法应对四周的动乱,尤其是动荡的中东 地区?俄罗斯对世界秩序永远都很重要,而问答上述问题必然会带来 的纷扰,对世界秩序也构成潜在的威胁。 中国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世界秩序。中华帝国大一统的局面维持了 两干年之久,事实上这个正统也曾有动摇的时候。战争在中国发生的 频率不下于欧洲,但中国的战争通常内争夺帝位而起,其性质多属内 战.而非国际战争,而且迟早必然会导致新的中央政权出现。 十九世纪之前,中国从未有能够挑战其领导地位的邻国,也绝对想 象不到会有这种国家兴起。蛮族侵入中国,推翻中国的上朝,到后来却 完全被同化,使他们仍继续着中华文化传统。各国主权平等的观念在 中国不存在;蛮族被视为未开化的夷狄,对中国只有藩属的关系,这正 是十八世纪英国首位派往北京的特使所获得的待遇。中国不屑于对外 派遣大使,但不排斥以夷制夷。不过这只是权宜之计,不像欧洲的权力 均衡是外交常态,中国也未能产生欧洲常见的常设性外交机构。自十 九世纪中国成为欧洲殖民主义受辱的对象后,直至晚近—自二次大 战以来一中国才在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多极世界中再度现身。 日本也曾闭关自守。在一八五四年由美国海军将领佩里,以武力 打开门户之前,日本甚至不曾像中国一样,令蛮族自相残杀以制衡其势 力,或想出中原与藩属这样的安排。与外界隔离的日本以其独特的风 俗习惯自豪,借内战延续其军事传统,并深信其独一无“的文化可脾睨 外来的影响,优于外来的文化,且最后必能战胜而非吸收外来文化,其 内部结构便建立于如此的基础上。 冷战期间苏联是首要安全威胁时,日本的外交政策能够认同千万 里以外的美国。新的世界秩序及其多重的挑战,几乎-…定会迫使.一个 有过如此光荣过去的国家,重新检讨其仰赖单一盟国的作法。日本对 亚洲的均势势必更为敏感,此种感觉会超过对位于不同半球且须兼顾 大西洋、太平洋、南美洲三方面的美国所作所为的感应。中国、韩国及 东南亚对日本会形成与对美国颇不相同的重要性,也会导致日本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