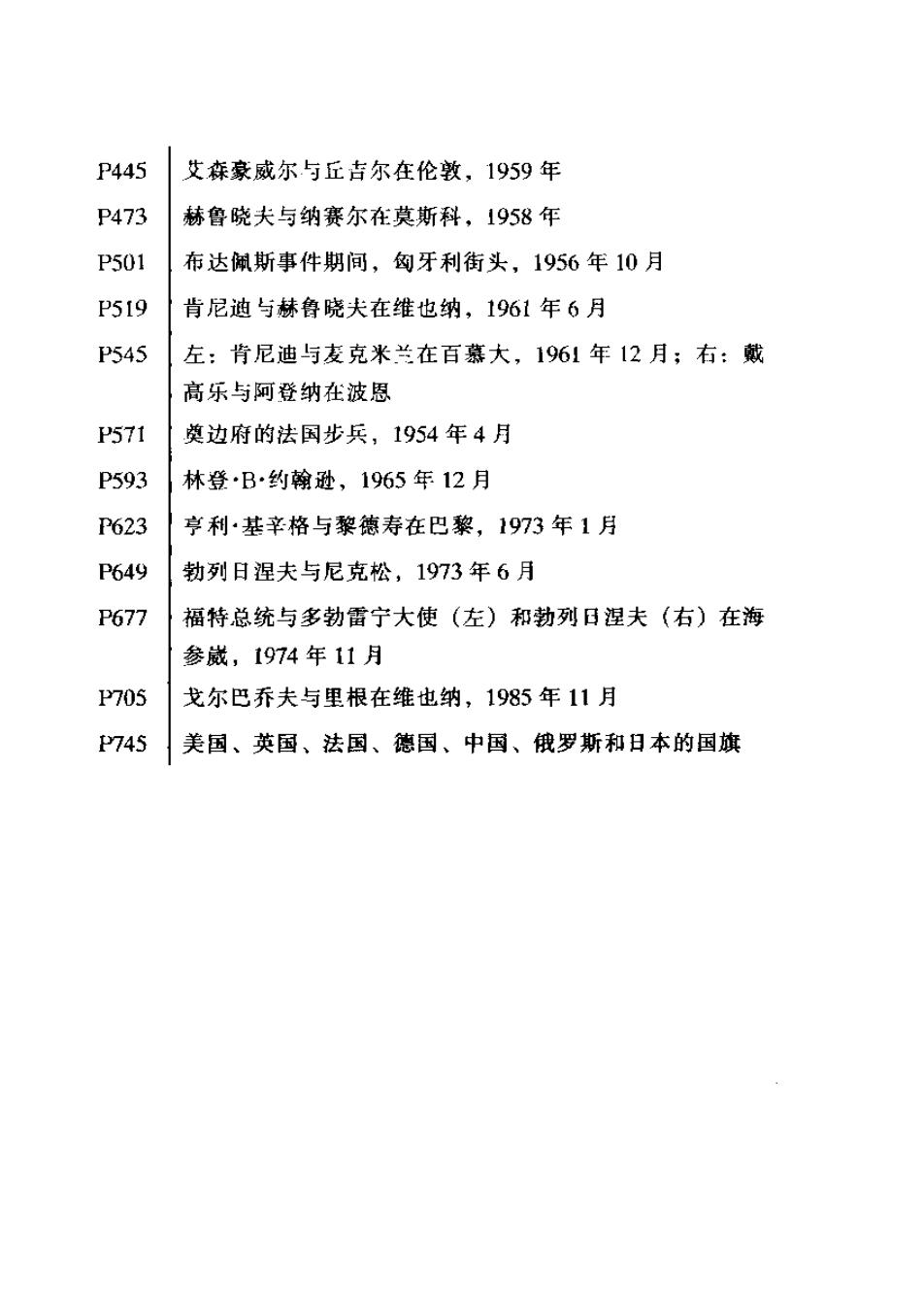
P445 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在伦敦,1959年 P473 赫鲁晓夫与纳赛尔在莫斯科,1958年 P501 布达佩斯事件期间,匈牙利街头,1956年10月 P519 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1961年6月 P545 左:肯尼迪与麦克米兰在百慕大,1961年12月;右:戴 高乐与阿登纳在波恩 P571 奠边府的法国步兵,1954年4月 P593 林登·B·约翰逊,1965年12月 P623 亭利·基辛格与黎德寿在巴黎,1973年1月 P649 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1973年6月 P677 福特总统与多勃雷宁大使(左)和勒列日涅夫(右)在海 参崴,1974年11月 P705 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维也纳,1985年11月 P745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的国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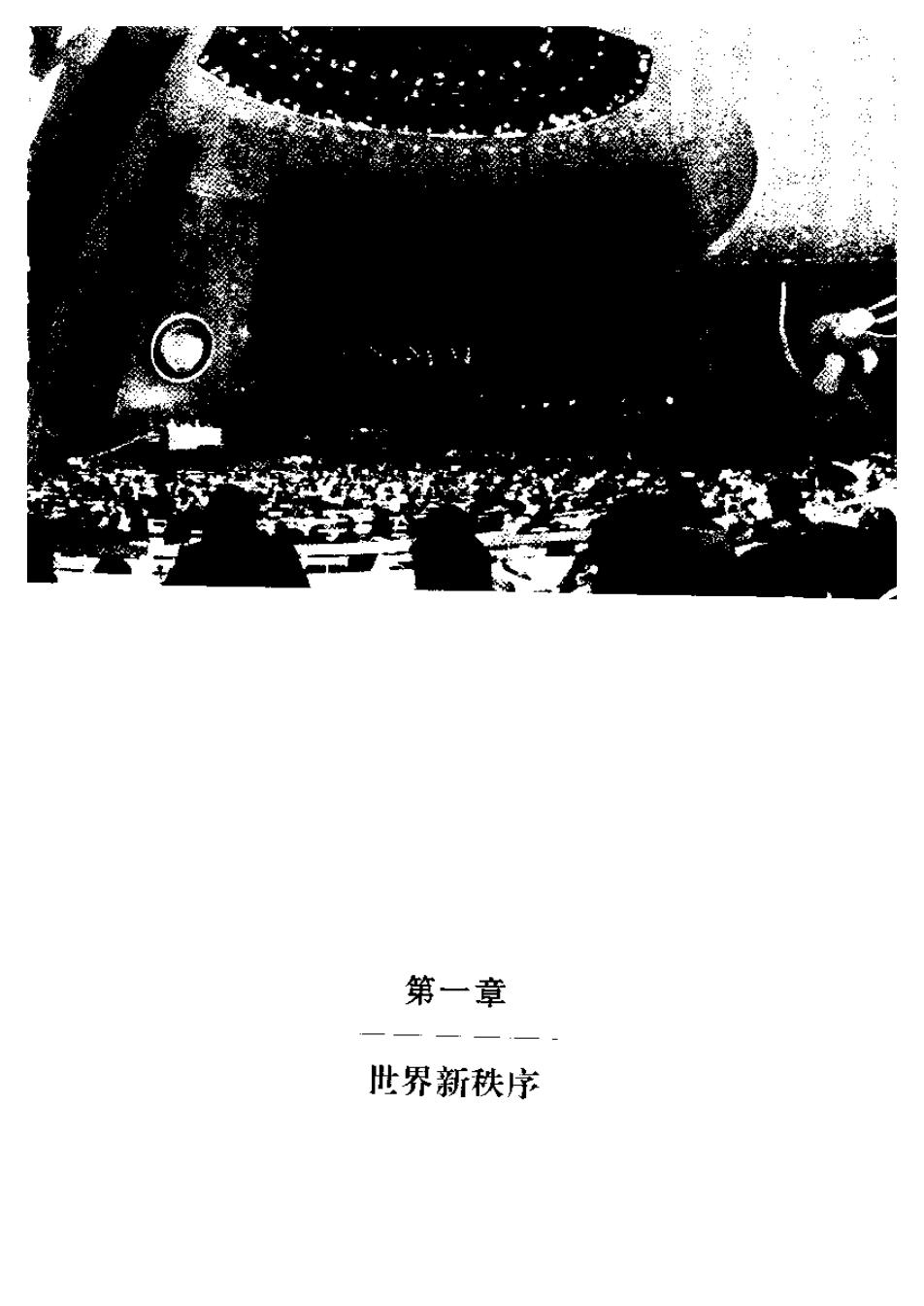
第一章 世界新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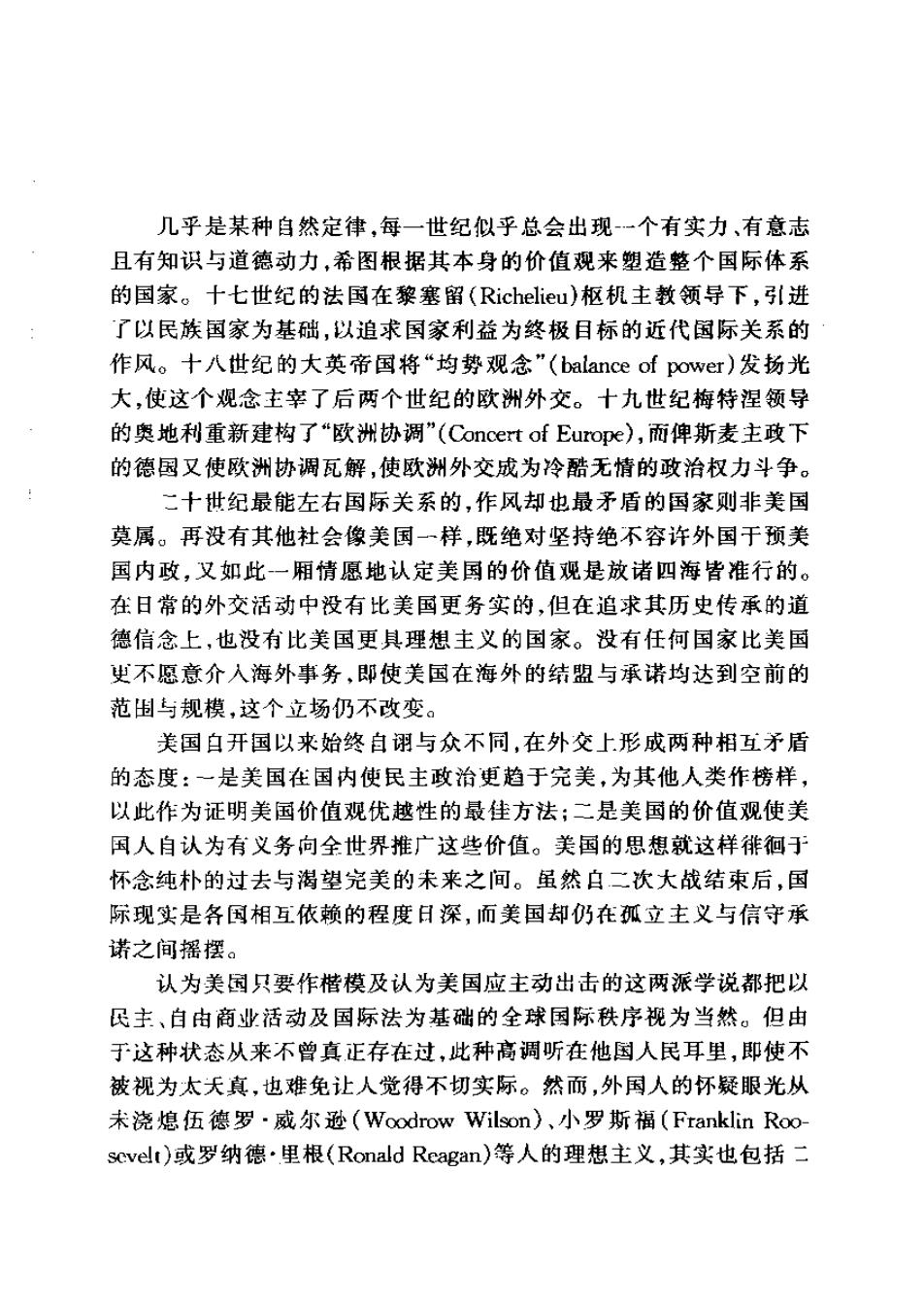
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 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希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规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 的国家。十七世纪的法国在黎塞留(Richelieu)枢机主教领导下,引进 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终极目标的近代国际关系的 作风。十八世纪的大英帝国将“均势观念”(balance of power)发扬光 大,使这个观念主宰了后两个世纪的欧洲外交。十九世纪梅特涅领导 的奥地利重新建构了“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而俾斯麦主政下 的德国又使欧洲协调瓦解,使欧洲外交成为冷酷无情的政治权力斗争。 二十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则非美国 莫属。再没有其他社会像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绝不容许外国于预美 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皆准行的。 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其历史传承的道 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没有任何国家比美国 史不愿意介入海外事务,即使美国在海外的结盟与承诺均达到空前的 范围与规模,这个立场仍不改变。 美国白开国以来始终自诩与众不同,在外交上形成两种相互矛盾 的态度: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政治更趋于完美,为其他人类作榜样, 以此作为证明美国价值观优越性的最佳方法: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美 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美国的思想就这样徘徊于于 怀念纯朴的过去与渴望完美的未来之间。虽然白二次大战结束后,国 际现实是各国相互依赖的程度日深,而美国却仍在孤立主义与信守承 诺之间摇摆。 认为美国只要作楷模及认为美国应主动出击的这两派学说都把以 民主、自由商业活动及国际法为基础的全球国际秩序视为当然。但由 于这种状态从来不曾真正存在过,此种高调听在他国人民耳里,即使不 被视为太天真,也难免让人觉得不切实际。然而,外国人的怀疑眼光从 未浇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小罗斯福(Franklin Roo- sevelt)或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等人的理想主义,其实也包括二

第一章世界新秩序 ·3 十世纪所有其他的美国总统在内。其结果是促使美国人相信,历史是 可以超越的,如果全世界真心想要和平,就需要接纳美国的道德处方。 这两派的:主张均是美国经验的产物。虽然共和国不止美国一国, 何其他共和国均非刻意为实现官由的理想而缔建。没有别的国家的人 芪是打着为全民自由与繁荣的旗帜,远走新大陆开天辟地。因此孤立 主义与传教士精神,这两个表面上如此相冲突的主张,正反映出美国人 共同的基本信念:美国拥有世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其他人类只要放弃传 统外交,跟美国-样信奉民主及倒际法,即可可获得和平与繁荣。 美因在国际上的经历一直是信仰胜过经验。自美国于一九一七年 进人世界政治舞台以来,依仗其强大的国力及对理想之自我肯定,以致 于本世纪主要的国际协议均是美国价值观的具体里现,从国际联盟及 凯洛格一白里安公约(Kellogg Briand Pact)到联合国宪章及赫尔辛基 最后文件(Helsinki Final Act),均是如此。前苏联的解体似乎证明了美 国理想的正确性,却也使美国无从逃避她始终不愿面对的世界局势。 在逐渐显现的国际新秩序中,民族主义又借尸还魂;各国亟于追求本身 利益远胜于坚持崇高的原则,而且竞争多过合作。我们找不到证据可 以证明此种历史悠久的行为模式已行改变,或是在未来数十年中会有 所变化。 在逐渐显现的世界秩序中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首 次面临的既不能退出又不能主宰世界舞台的困境。美国无法改变自有 史以来使深自期许的使命,也不应希望有所改变。美国刚走入国际社 会时,正值年轻力壮,也有实力让全世界顺从其对国际关系的理想。到 …九四五年次大战终了时,美国闲力之强(全世界的总产值中,美因 度便占了35%左右),仿佛注定她要根据自己的编好来啦造整个世 界。 约翰·肯尼迪总统(John F.Kennedy)在一九六-一年充满信心地宣 称,美国强大到足以“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重担”,以确保自由的胜 利成功。三十年后,美国已不县备坚持立即实现其所有愿望的实力,而 另-些国家已成长为强权大国。美国现在面临在不同阶段达成不同目 标的挑战,而每一目标均是美国价值及地缘政治需要相结合的产物

大外交 新出现的现实需要之~是:同时存在着儿个实力相近国家的世界,其秩 序必须建立在某种均衡(equilibrium)的观念上.,而这是美国向来雉以 接受的一种观念。 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与欧洲外交传统于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和会上交 手时,历史经验的差异便极为明显。欧洲领袖想根据他们熟悉的方式 调整既有的体系;美国的与会代表则认为,此次大战绝非起因于难以控 制的地缘政治冲突,面是欧洲人作法不当所造成的。域尔逊在著名的 “十四点原则”中告诉欧洲人,由此可知国际体系不应建立在均势上,而 应以民族月决为基础,欧洲的安全不应仰赖军事结盟,而应建立集体安 全,且其外交不应再由专家秘密进行,应“以公开达成的公开协议”为 准。显然,威尔逊来此主要不是为了讨论停战的条件,或恢复固有的国 际秩序,而是想要把行之已近三百年的国际关系体系加以重新建构。 美国人只要一想到外交政策,必定会认为欧洲的问题都是出在均 势体系上。而自从欧洲首度必须顾及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欧洲领袖便 对美国以全球改革为已任的想法不以为然。双方的态度仿佛都是认 为,对方的外交行为模式全是任性的抉择,如果更加明智或不是那么好 战,本应当会选择另外一种更能令人接受的模式。 事实上,美国与欧洲的外交政策模式都是其本身特殊环境的产物: 美国所处的近乎是真空的大陆,毗邻的是弱国,又有两大洋将虎视眈耽 的强权隔离在外。由于美国没有面临需要与之抗衡的对等势力,自然 不太可能全力投人应付平衡权力的挑战中,即使美国领袖曾有过“在背 离欧洲的美国”模仿欧洲的这种怪念头,也不可能做得到。 让欧洲国家深受其苦的国家安全困境,美国在近一百五十年后才 开始面临。美因面临这个难题时,便是参与了全是欧洲国家引起的两 次世界大战。每次美国参战,权力均势均已瓦解,这里显现出一个矛盾 现象:受大多数美国人排斥的均势观念事实上保障了美国的安全,只要 它运作良好;是均势遭到破坏才使美国涉人国际政治。 欧洲各国从未主动选择均势,来作为历来纷争不休、或旧大陆式喜 好谋略的国际关系的规范。若说强调民主及国际法是美国独特的安全 感所导致,则欧洲外交便是在严酷的打击下所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