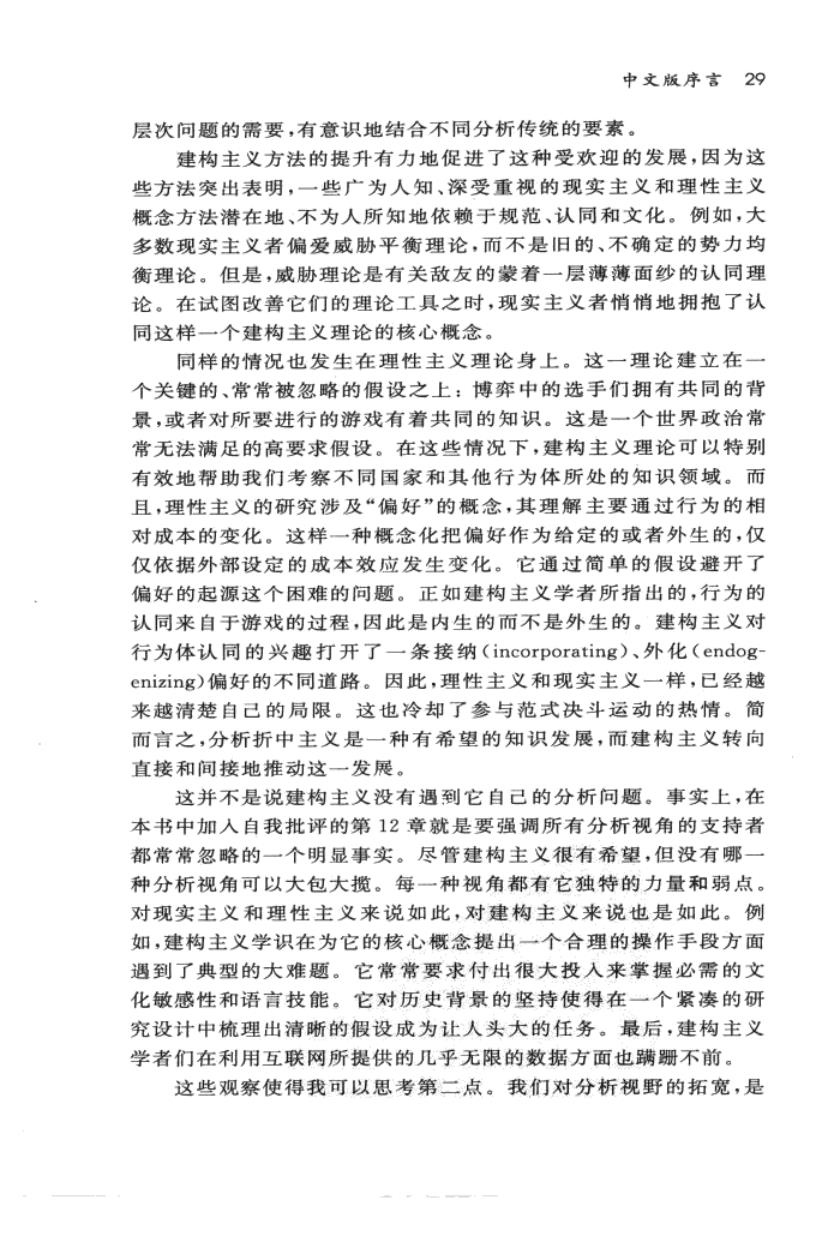
中文版序言29 层次问题的需要,有意识地结合不同分析传统的要素。 建构主义方法的提升有力地促进了这种受欢迎的发展,因为这 些方法突出表明,一些广为人知、深受重视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 概念方法潜在地、不为人所知地依赖于规范、认同和文化。例如,大 多数现实主义者偏爱威胁平衡理论,而不是旧的、不确定的势力均 衡理论。但是,威胁理论是有关敌友的蒙着一层薄薄面纱的认同理 论。在试图改善它们的理论工具之时,现实主义者悄悄地拥抱了认 同这样一个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理性主义理论身上。这一理论建立在一 个关键的、常常被忽略的假设之上:博弈中的选手们拥有共同的背 景,或者对所要进行的游戏有着共同的知识。这是一个世界政治常 常无法满足的高要求假设。在这些情况下,建构主义理论可以特别 有效地帮助我们考察不同国家和其他行为体所处的知识领域。而 且,理性主义的研究涉及“偏好”的概念,其理解主要通过行为的相 对成本的变化。这样一种概念化把偏好作为给定的或者外生的,仅 仅依据外部设定的成本效应发生变化。它通过简单的假设避开了 偏好的起源这个困难的问题。正如建构主义学者所指出的,行为的 认同来自于游戏的过程,因此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建构主义对 行为体认同的兴趣打开了一条接纳(incorporating)、外化(endog enizing)偏好的不同道路。因此,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样,已经越 来越清楚自己的局限。这也冷却了参与范式决斗运动的热情。简 而言之,分析折中主义是一种有希望的知识发展,而建构主义转向 直接和间接地推动这一发展。 这并不是说建构主义没有遇到它自己的分析问题。事实上,在 本书中加入自我批评的第12章就是要强调所有分析视角的支持者 都常常忽略的一个明显事实。尽管建构主义很有希望,但没有哪一 种分析视角可以大包大揽。每一种视角都有它独特的力量和弱点。 对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来说如此,对建构主义来说也是如此。例 如,建构主义学识在为它的核心概念提出一个合理的操作手段方面 遇到了典型的大难题。它常常要求付出很大投入来掌握必需的文 化敏感性和语言技能。它对历史背景的坚持使得在一个紧凑的研 究设计中梳理出清晰的假设成为让人头大的任务。最后,建构主义 学者们在利用互联网所提供的几乎无限的数据方面也蹒跚不前。 这些观察使得我可以思考第二点。我们对分析视野的拓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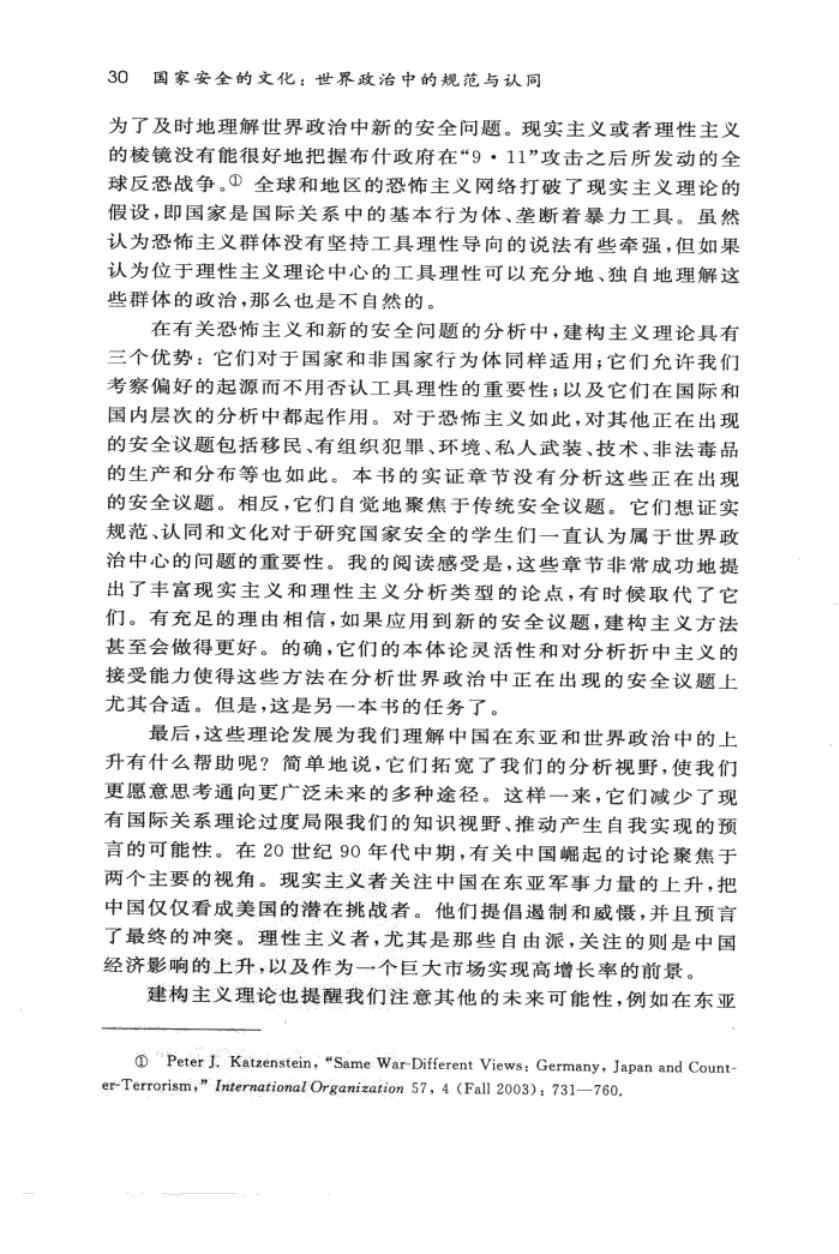
30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 为了及时地理解世界政治中新的安全问题。现实主义或者理性主义 的棱镜没有能很好地把握布什政府在“9·11”攻击之后所发动的全 球反恐战争。①全球和地区的恐怖主义网络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的 假设,即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行为体、垄断着暴力工具。虽然 认为恐怖主义群体没有坚持工具理性导向的说法有些牵强,但如果 认为位于理性主义理论中心的工具理性可以充分地、独自地理解这 些群体的政治,那么也是不自然的。 在有关恐怖主义和新的安全问题的分析中,建构主义理论具有 三个优势:它们对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同样适用,它们允许我们 考察偏好的起源而不用否认工具理性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国际和 国内层次的分析中都起作用。对于恐怖主义如此,对其他正在出现 的安全议题包括移民、有组织犯罪、环境、私人武装、技术、非法毒品 的生产和分布等也如此。本书的实证章节没有分析这些正在出现 的安全议题。相反,它们自觉地聚焦于传统安全议题。它们想证实 规范、认同和文化对于研究国家安全的学生们一直认为属于世界政 治中心的问题的重要性。我的阅读感受是,这些章节非常成功地提 出了丰富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分析类型的论点,有时候取代了它 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如果应用到新的安全议题,建构主义方法 甚至会做得更好。的确,它们的本体论灵活性和对分析折中主义的 接受能力使得这些方法在分析世界政治中正在出现的安全议题上 尤其合适。但是,这是另一本书的任务了。 最后,这些理论发展为我们理解中国在东亚和世界政治中的上 升有什么帮助呢?简单地说,它们拓宽了我们的分析视野,使我们 更愿意思考通向更广泛未来的多种途径。这样一来,它们减少了现 有国际关系理论过度局限我们的知识视野、推动产生自我实现的预 言的可能性。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关中国崛起的讨论聚焦于 两个主要的视角。现实主义者关注中国在东亚军事力量的上升,把 中国仅仅看成美国的潜在挑战者。他们提倡遏制和威慑,并且预言 了最终的冲突。理性主义者,尤其是那些自由派,关注的则是中国 经济影响的上升,以及作为一个巨大市场实现高增长率的前景。 建构主义理论也提醒我们注意其他的未来可能性,例如在东亚 D Peter J.Katzenstein,"Same War-Different Views:Germany,Japan and Count- er-Terror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7,4 (Fall 2003):731-7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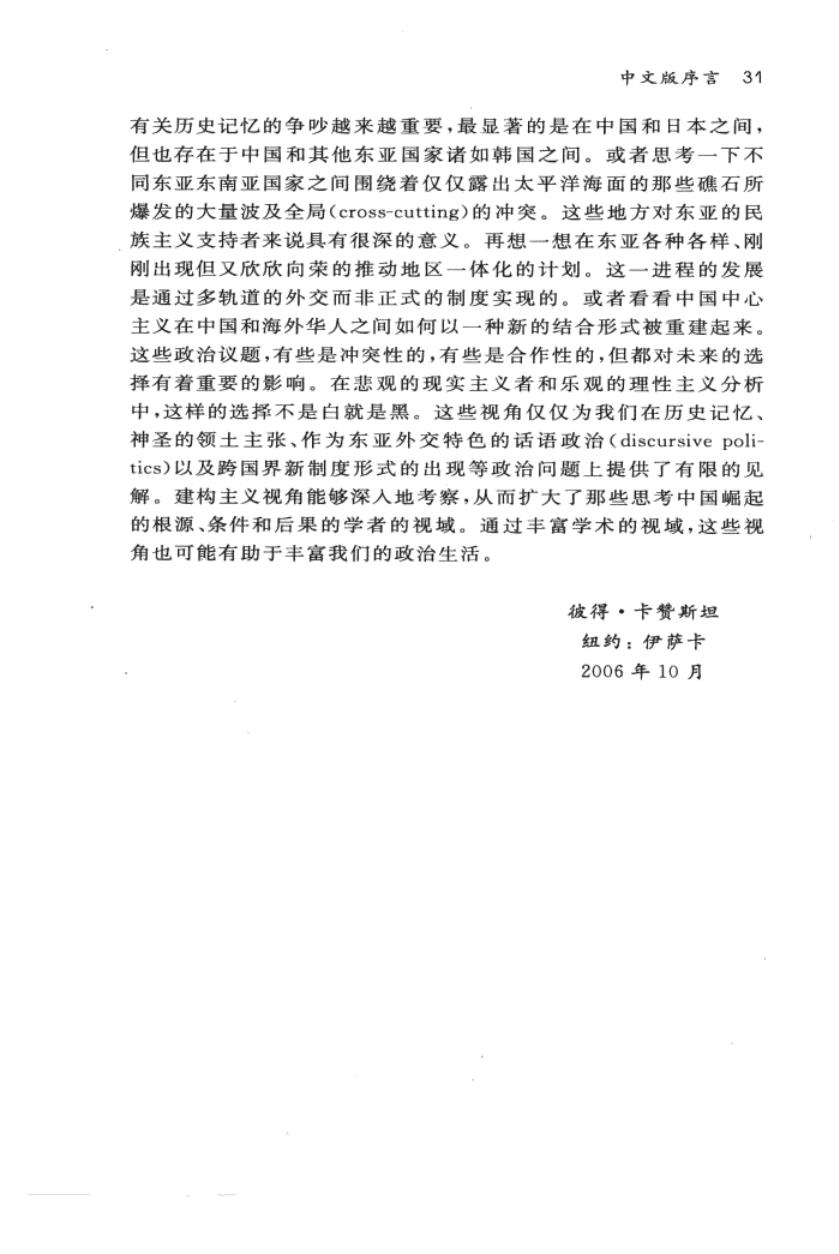
中文版序言31 有关历史记忆的争吵越来越重要,最显著的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 但也存在于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诸如韩国之间。或者思考一下不 同东亚东南亚国家之间围绕着仅仅露出太平洋海面的那些礁石所 爆发的大量波及全局(cross-cutting)的冲突。这些地方对东亚的民 族主义支持者来说具有很深的意义。再想一想在东亚各种各样、刚 刚出现但又欣欣向荣的推动地区一体化的计划。这一进程的发展 是通过多轨道的外交而非正式的制度实现的。或者看看中国中心 主义在中国和海外华人之间如何以一种新的结合形式被重建起来。 这些政治议题,有些是冲突性的,有些是合作性的,但都对未来的选 择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悲观的现实主义者和乐观的理性主义分析 中,这样的选择不是白就是黑。这些视角仅仅为我们在历史记忆、 神圣的领土主张、作为东亚外交特色的话语政治(discursive poli- tiCs)以及跨国界新制度形式的出现等政治问题上提供了有限的见 解。建构主义视角能够深入地考察,从而扩大了那些思考中国崛起 的根源、条件和后果的学者的视域。通过丰富学术的视域,这些视 角也可能有助于丰富我们的政治生活。 彼得·卡赞斯坦 纽约:伊萨卡 2006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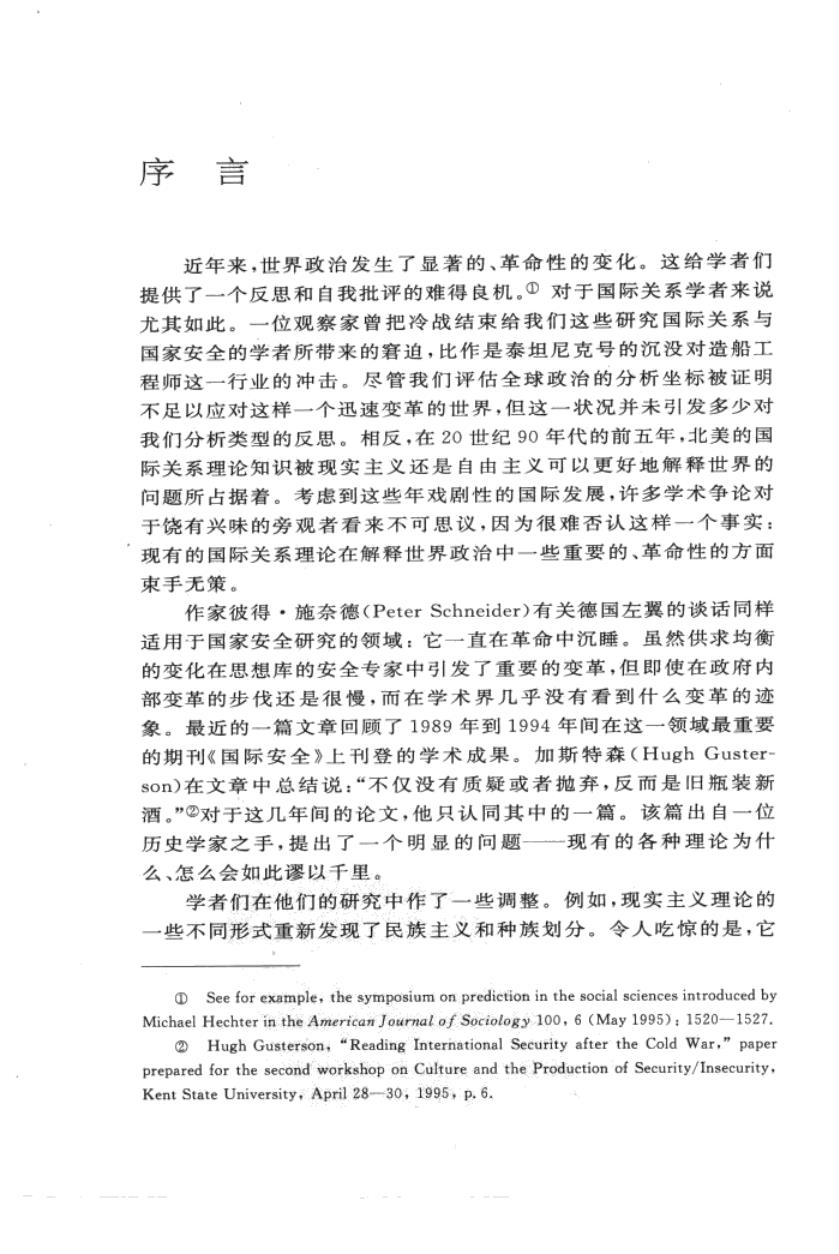
序言 近年来,世界政治发生了显著的、革命性的变化。这给学者们 提供了一个反思和自我批评的难得良机。①对于国际关系学者来说 尤其如此。一位观察家曾把冷战结束给我们这些研究国际关系与 国家安全的学者所带来的窘迫,比作是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对造船工 程师这一行业的冲击。尽管我们评估全球政治的分析坐标被证明 不足以应对这样一个迅速变革的世界,但这一状况并未引发多少对 我们分析类型的反思。相反,在20世纪90年代的前五年,北美的国 际关系理论知识被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可以更好地解释世界的 问题所占据着。考虑到这些年戏剧性的国际发展,许多学术争论对 于饶有兴味的旁观者看来不可思议,因为很难否认这样一个事实: 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世界政治中一些重要的、革命性的方面 束手无策。 作家彼得·施奈德(Peter Schneider.)有关德国左翼的谈话同样 适用于国家安全研究的领域:它一直在革命中沉睡。虽然供求均衡 的变化在思想库的安全专家中引发了重要的变革,但即使在政府内 部变革的步伐还是很慢,而在学术界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变革的迹 象。最近的一篇文章回顾了1989年到1994年间在这一领域最重要 的期刊《国际安全》上刊登的学术成果。加斯特森(Hugh Guster- so)在文章中总结说:“不仅没有质疑或者抛弃,反而是旧瓶装新 酒。”②对于这几年间的论文,他只认同其中的一篇。该篇出自一位 历史学家之手,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一现有的各种理论为什 么、怎么会如此谬以千里。 学者们在他们的研究中作了一些调整。例如,现实主义理论的 一些不同形式重新发现了民族主义和种族划分。令人吃惊的是,它 D See for example,the symposium on predic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troduced by Michael Hechter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6 (May 1995):1520-1527. 2Hugh Gusterson,"Read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paper prepared for the second workshop on Cultu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Security/Insecurity, Kent State University,April 28-30,1995,p.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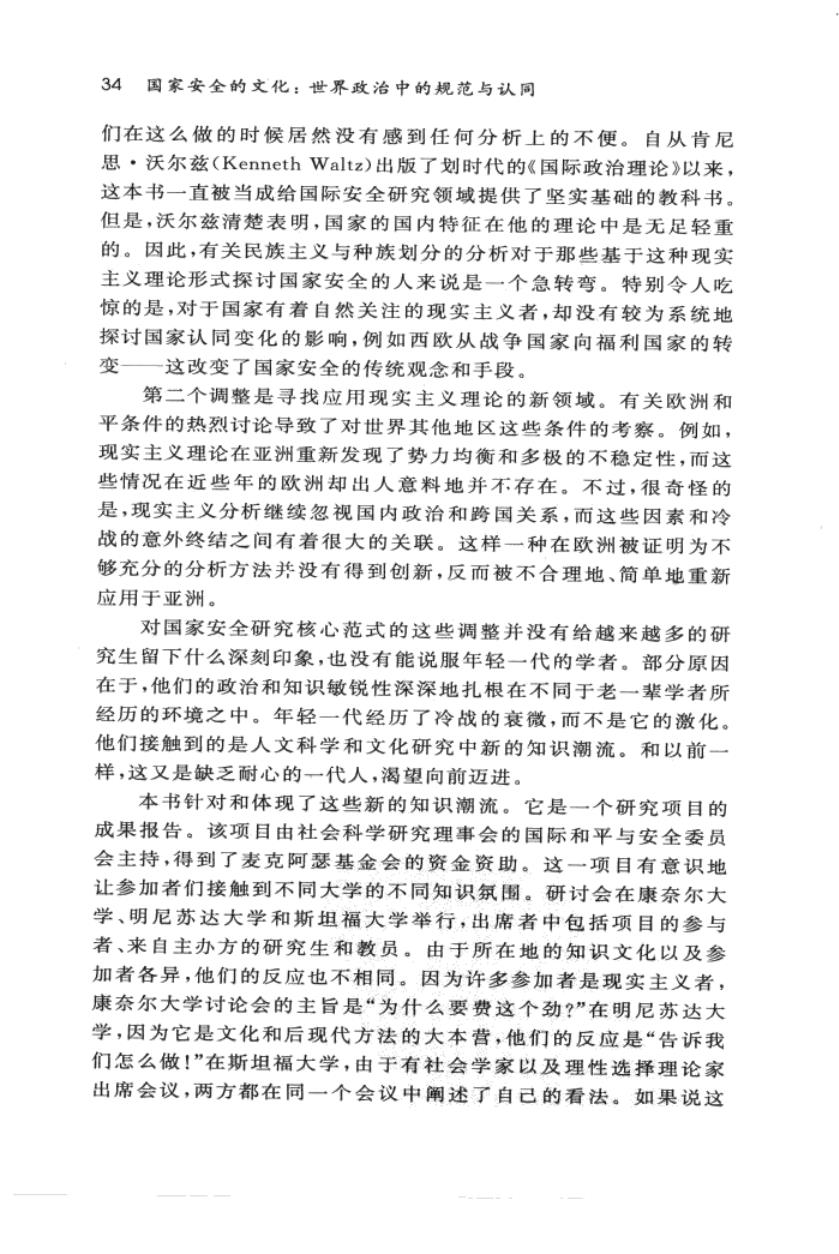
34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 们在这么做的时候居然没有感到任何分析上的不便。自从肯尼 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出版了划时代的《国际政治理论》以来, 这本书一直被当成给国际安全研究领域提供了坚实基础的教科书。 但是,沃尔兹清楚表明,国家的国内特征在他的理论中是无足轻重 的。因此,有关民族主义与种族划分的分析对于那些基于这种现实 主义理论形式探讨国家安全的人来说是一个急转弯。特别令人吃 惊的是,对于国家有着自然关注的现实主义者,却没有较为系统地 探讨国家认同变化的影响,例如西欧从战争国家向福利国家的转 变一这改变了国家安全的传统观念和手段。 第二个调整是寻找应用现实主义理论的新领域。有关欧洲和 平条件的热烈讨论导致了对世界其他地区这些条件的考察。例如, 现实主义理论在亚洲重新发现了势力均衡和多极的不稳定性,而这 些情况在近些年的欧洲却出人意料地并不存在。不过,很奇怪的 是,现实主义分析继续忽视国内政治和跨国关系,而这些因素和冷 战的意外终结之间有着很大的关联。这样一种在欧洲被证明为不 够充分的分析方法并没有得到创新,反而被不合理地、简单地重新 应用于亚洲。 对国家安全研究核心范式的这些调整并没有给越来越多的研 究生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也没有能说服年轻一代的学者。部分原因 在于,他们的政治和知识敏锐性深深地扎根在不同于老一辈学者所 经历的环境之中。年轻一代经历了冷战的衰微,而不是它的激化。 他们接触到的是人文科学和文化研究中新的知识潮流。和以前一 样,这又是缺乏耐心的一代人,渴望向前迈进。 本书针对和体现了这些新的知识潮流。它是一个研究项目的 成果报告。该项目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委员 会主持,得到了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金资助。这一项目有意识地 让参加者们接触到不同大学的不同知识氛围。研讨会在康奈尔大 学、明尼苏达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举行,出席者中包括项目的参与 者、来自主办方的研究生和教员。由于所在地的知识文化以及参 加者各异,他们的反应也不相同。因为许多参加者是现实主义者, 康奈尔大学讨论会的主旨是“为什么要费这个劲?”在明尼苏达大 学,因为它是文化和后现代方法的大本营,他们的反应是“告诉我 们怎么做!”在斯坦福大学,由于有社会学家以及理性选择理论家 出席会议,两方都在同一个会议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如果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