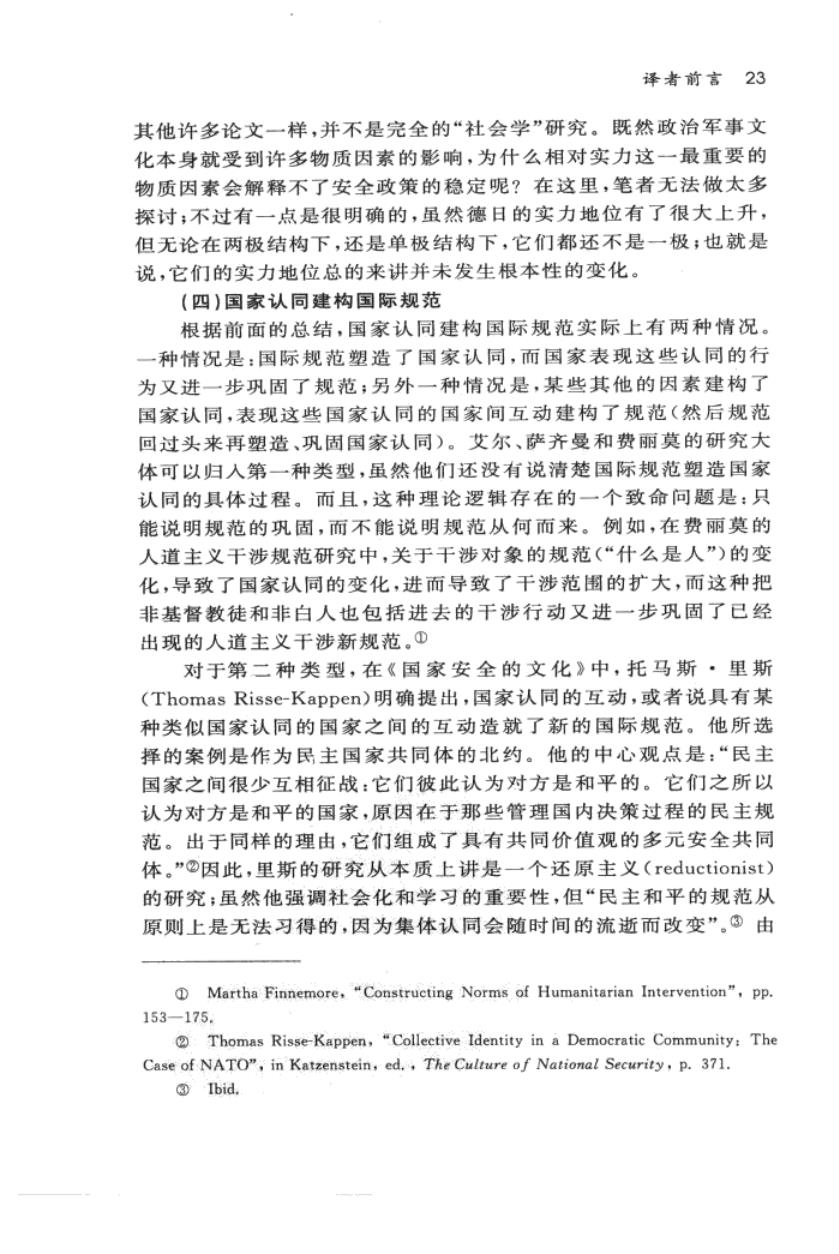
译者前言23 其他许多论文一样,并不是完全的“社会学”研究。既然政治军事文 化本身就受到许多物质因素的影响,为什么相对实力这一最重要的 物质因素会解释不了安全政策的稳定呢?在这里,笔者无法做太多 探讨:不过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虽然德日的实力地位有了很大上升, 但无论在两极结构下,还是单极结构下,它们都还不是一极;也就是 说,它们的实力地位总的来讲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四)国家认同建构国际规范 根据前面的总结,国家认同建构国际规范实际上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国际规范塑造了国家认同,而国家表现这些认同的行 为又进一步巩固了规范:另外一种情况是,某些其他的因素建构了 国家认同,表现这些国家认同的国家间互动建构了规范(然后规范 回过头来再塑造、巩固国家认同)。艾尔、萨齐曼和费丽莫的研究大 体可以归人第一种类型,虽然他们还没有说清楚国际规范塑造国家 认同的具体过程。而且,这种理论逻辑存在的一个致命问题是:只 能说明规范的巩固,而不能说明规范从何而来。例如,在费丽莫的 人道主义干涉规范研究中,关于干涉对象的规范(“什么是人”)的变 化,导致了国家认同的变化,进而导致了干涉范围的扩大,而这种把 非基督教徒和非白人也包括进去的干涉行动又进一步巩固了已经 出现的人道主义干涉新规范。① 对于第二种类型,在《国家安全的文化》中,托马斯·里斯 (Thomas Risse-Kappen)明确提出,国家认同的互动,或者说具有某 种类似国家认同的国家之间的互动造就了新的国际规范。他所选 择的案例是作为民主国家共同体的北约。他的中心观点是:“民主 国家之间很少互相征战:它们彼此认为对方是和平的。它们之所以 认为对方是和平的国家,原因在于那些管理国内决策过程的民主规 范。出于同样的理由,它们组成了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多元安全共同 体。”②因此,里斯的研究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还原主义(reductionist) 的研究;虽然他强调社会化和学习的重要性,但“民主和平的规范从 原则上是无法习得的,因为集体认同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改变”。③由 D Martha Finnemore,"Constructing Norm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pp. 153—175. 2 Thomas Risse-Kappen,"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The Case of NATO",in 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p.371. ③-Ib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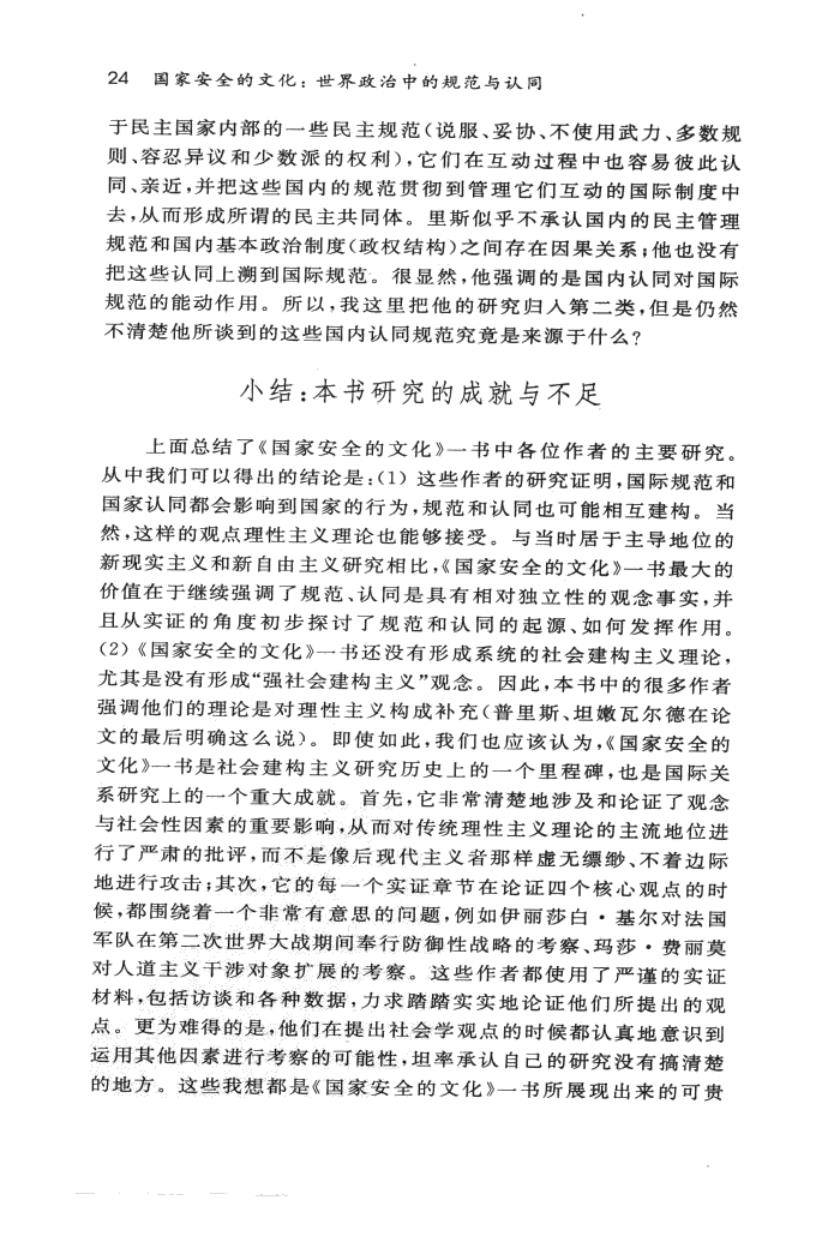
24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 于民主国家内部的一些民主规范(说服、妥协、不使用武力、多数规 则、容忍异议和少数派的权利),它们在互动过程中也容易彼此认 同、亲近,并把这些国内的规范贯彻到管理它们互动的国际制度中 去,从而形成所谓的民主共同体。里斯似乎不承认国内的民主管理 规范和国内基本政治制度(政权结构)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他也没有 把这些认同上溯到国际规范。很显然,他强调的是国内认同对国际 规范的能动作用。所以,我这里把他的研究归入第二类,但是仍然 不清楚他所谈到的这些国内认同规范究竟是来源于什么? 小结:本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上面总结了《国家安全的文化》一书中各位作者的主要研究。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1)这些作者的研究证明,国际规范和 国家认同都会影响到国家的行为,规范和认同也可能相互建构。当 然,这样的观点理性主义理论也能够接受。与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研究相比,《国家安全的文化》一书最大的 价值在于继续强调了规范、认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观念事实,并 且从实证的角度初步探讨了规范和认同的起源、如何发挥作用。 (2)《国家安全的文化》一书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 尤其是没有形成“强社会建构主义”观念。因此,本书中的很多作者 强调他们的理论是对理性主义构成补充(普里斯、坦嫩瓦尔德在论 文的最后明确这么说)。即使如此,我们也应该认为,《国家安全的 文化》一书是社会建构主义研究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国际关 系研究上的一个重大成就。首先,它非常清楚地涉及和论证了观念 与社会性因素的重要影响,从而对传统理性主义理论的主流地位进 行了严肃的批评,而不是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虚无缥缈、不着边际 地进行攻击;其次,它的每一个实证章节在论证四个核心观点的时 候,都围绕着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例如伊丽莎白·基尔对法国 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奉行防御性战略的考察、玛莎·费丽莫 对人道主义干涉对象扩展的考察。这些作者都使用了严谨的实证 材料,包括访谈和各种数据,力求踏踏实实地论证他们所提出的观 点。更为难得的是,他们在提出社会学观点的时候都认真地意识到 运用其他因素进行考察的可能性,坦率承认自己的研究没有搞清楚 的地方。这些我想都是《国家安全的文化》一书所展现出来的可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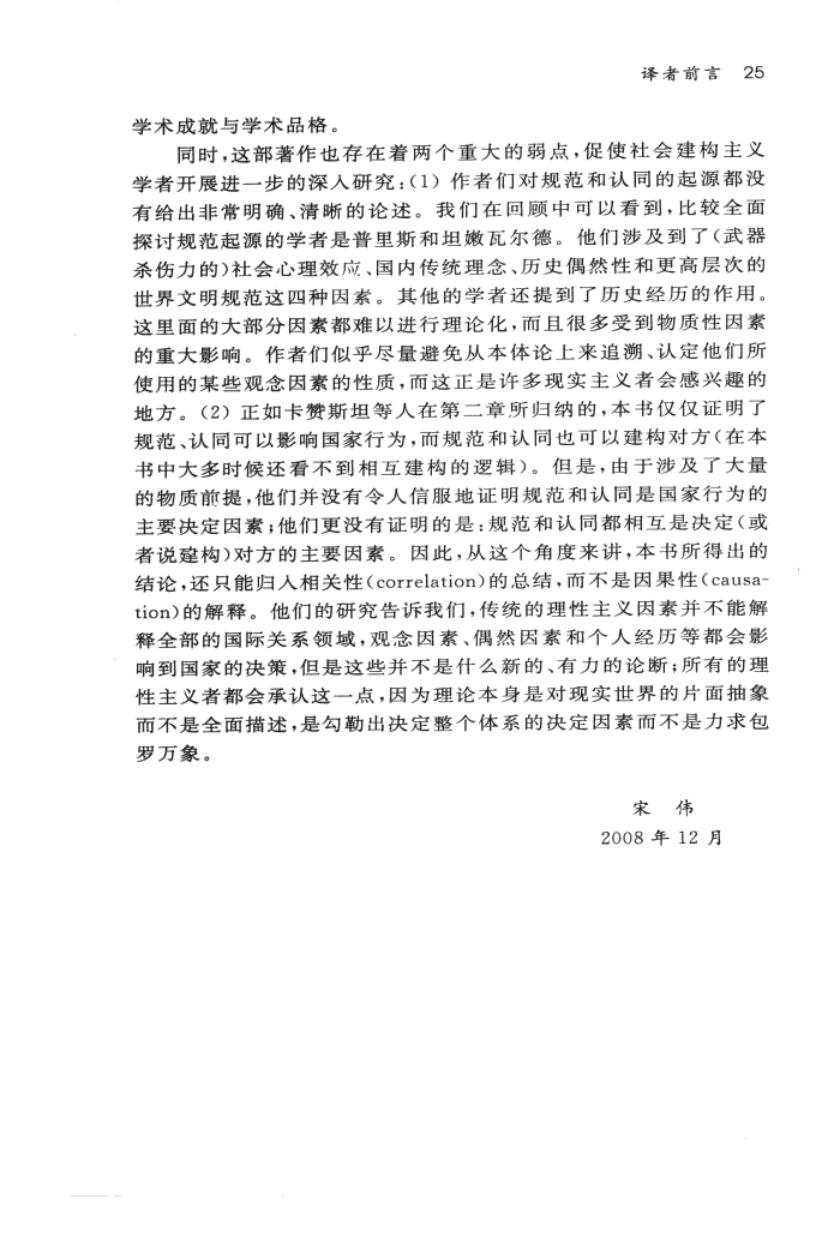
译者前言25 学术成就与学术品格。 同时,这部著作也存在着两个重大的弱点,促使社会建构主义 学者开展进一步的深人研究:(1)作者们对规范和认同的起源都没 有给出非常明确、清晰的论述。我们在回顾中可以看到,比较全面 探讨规范起源的学者是普里斯和坦嫩瓦尔德。他们涉及到了(武器 杀伤力的)社会心理效应、国内传统理念、历史偶然性和更高层次的 世界文明规范这四种因索。其他的学者还提到了历史经历的作用。 这里面的大部分因素都难以进行理论化,而且很多受到物质性因素 的重大影响。作者们似乎尽量避免从本体论上来追溯、认定他们所 使用的某些观念因素的性质,而这正是许多现实主义者会感兴趣的 地方。(2)正如卡赞斯坦等人在第二章所归纳的,本书仅仅证明了 规范、认同可以影响国家行为,而规范和认同也可以建构对方(在本 书中大多时候还看不到相互建构的逻辑)。但是,由于涉及了大量 的物质前提,他们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证明规范和认同是国家行为的 主要决定因素,他们更没有证明的是:规范和认同都相互是决定(或 者说建构)对方的主要因素。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本书所得出的 结论,还只能归入相关性(correlation)的总结,而不是因果性(causa tio)的解释。他们的研究告诉我们,传统的理性主义因素并不能解 释全部的国际关系领域,观念因素、偶然因素和个人经历等都会影 响到国家的决策,但是这些并不是什么新的、有力的论断:所有的理 性主义者都会承认这一点,因为理论本身是对现实世界的片面抽象 而不是全面描述,是勾勒出决定整个体系的决定因素而不是力求包 罗万象。 宋伟 2008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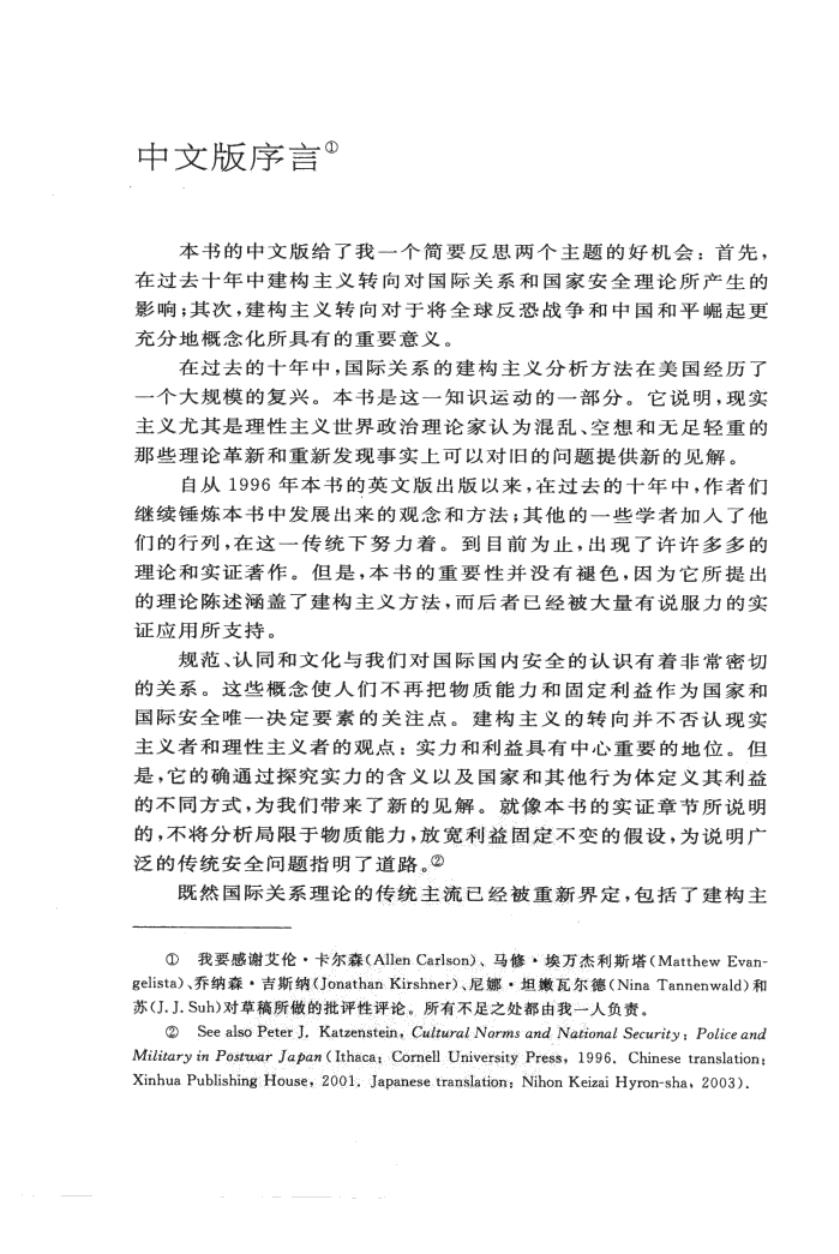
中文版序言① 本书的中文版给了我一个简要反思两个主题的好机会:首先, 在过去十年中建构主义转向对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理论所产生的 影响;其次,建构主义转向对于将全球反恐战争和中国和平崛起更 充分地概念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分析方法在美国经历了 一个大规模的复兴。本书是这一知识运动的一部分。它说明,现实 主义尤其是理性主义世界政治理论家认为混乱、空想和无足轻重的 那些理论革新和重新发现事实上可以对旧的问题提供新的见解。 自从1996年本书的英文版出版以来,在过去的十年中,作者们 继续锤炼本书中发展出来的观念和方法:其他的一些学者加入了他 们的行列,在这一传统下努力着。到目前为止,出现了许许多多的 理论和实证著作。但是,本书的重要性并没有褪色,因为它所提出 的理论陈述涵盖了建构主义方法,而后者已经被大量有说服力的实 证应用所支持。 规范、认同和文化与我们对国际国内安全的认识有着非常密切 的关系。这些概念使人们不再把物质能力和固定利益作为国家和 国际安全唯一决定要素的关注点。建构主义的转向并不否认现实 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实力和利益具有中心重要的地位。但 是,它的确通过探究实力的含义以及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定义其利益 的不同方式,为我们带来了新的见解。就像本书的实证章节所说明 的,不将分析局限于物质能力,放宽利益固定不变的假设,为说明广 泛的传统安全问题指明了道路。② 既然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主流已经被重新界定,包括了建构主 ①我要感谢艾伦·卡尔森(Allen Carlson).、马修·埃万杰利斯塔(Matthew Evan- gelista)、乔纳森·吉斯纳(Jonathan Kirshner)、尼娜·坦嫩瓦尔德(Nina Tannenwald)和 苏(J.J.Suh)对草稿所做的批评性评论,所有不足之处都由我一人负贵。 2 See also Peter J.Katzenstein,Cultural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Police and Military in Postwar Japan(Ithaca:Comell University Press,1996.Chinese translation: Xinhua Publishing House,2001.Japanese translation:Nihon Keizai Hyron-sha,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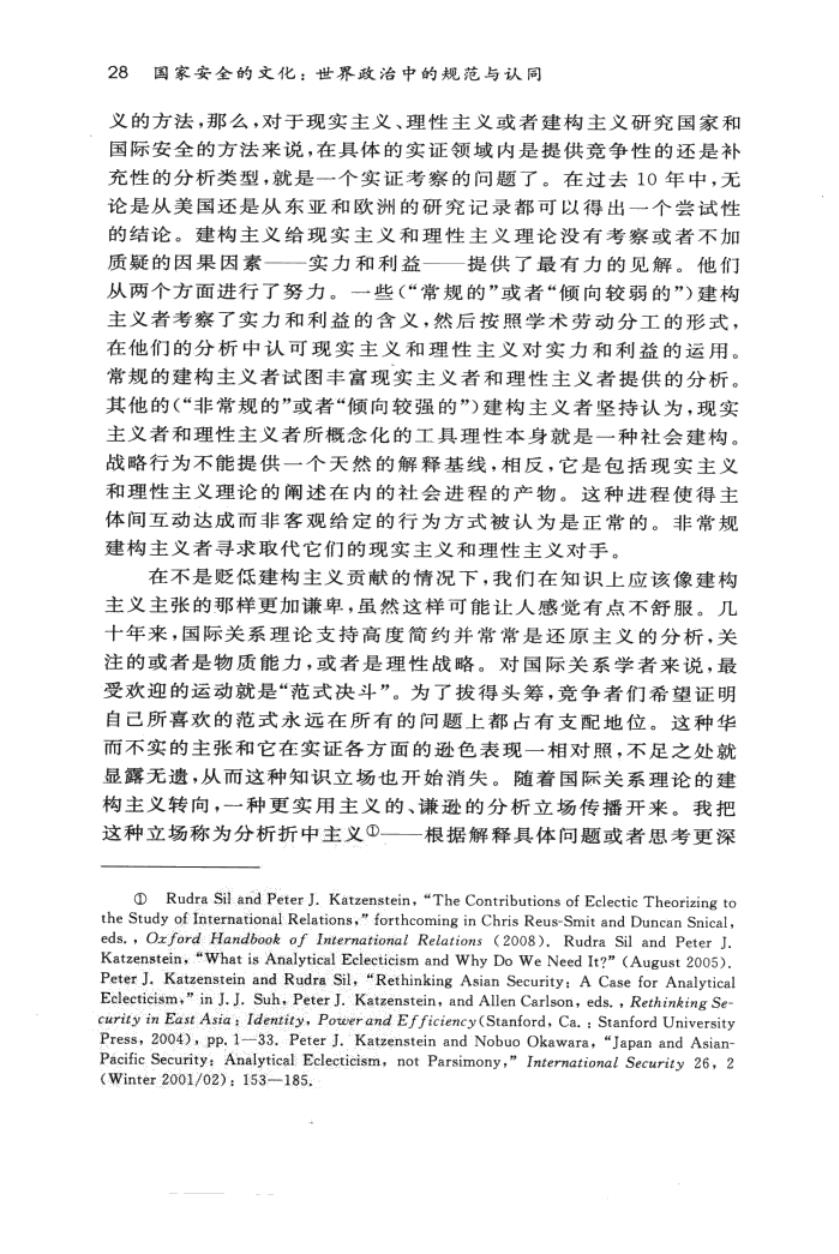
28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 义的方法,那么,对于现实主义、理性主义或者建构主义研究国家和 国际安全的方法来说,在具体的实证领域内是提供竞争性的还是补 充性的分析类型,就是一个实证考察的问题了。在过去10年中,无 论是从美国还是从东亚和欧洲的研究记录都可以得出一个尝试性 的结论。建构主义给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理论没有考察或者不加 质疑的因果因素一实力和利益一提供了最有力的见解。他们 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努力。一些(“常规的”或者“倾向较弱的”)建构 主义者考察了实力和利益的含义,然后按照学术劳动分工的形式, 在他们的分析中认可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对实力和利益的运用。 常规的建构主义者试图丰富现实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提供的分析。 其他的(“非常规的”或者“倾向较强的”)建构主义者坚持认为,现实 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所概念化的工具理性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构。 战略行为不能提供一个天然的解释基线,相反,它是包括现实主义 和理性主义理论的阐述在内的社会进程的产物。这种进程使得主 体间互动达成而非客观给定的行为方式被认为是正常的。非常规 建构主义者寻求取代它们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对手。 在不是贬低建构主义贡献的情况下,我们在知识上应该像建构 主义主张的那样更加谦卑,虽然这样可能让人感觉有点不舒服。几 十年来,国际关系理论支持高度简约并常常是还原主义的分析,关 注的或者是物质能力,或者是理性战略。对国际关系学者来说,最 受欢迎的运动就是“范式决斗”。为了拔得头筹,竞争者们希望证明 自己所喜欢的范式永远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占有支配地位。这种华 而不实的主张和它在实证各方面的逊色表现一相对照,不足之处就 显露无遗,从而这种知识立场也开始消失。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建 构主义转向,一种更实用主义的、谦逊的分析立场传播开来。我把 这种立场称为分析折中主义①一根据解释具体问题或者思考更深 D Rudra Sil and Peter J.Katzenstein,"The Contributions of Eclectic Theorizing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orthcoming in Chris Reus-Smit and Duncan Snical, eds.,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8).Rudra Sil and Peter J. Katzenstein,"What is Analytical Eclecticism and Why Do We Need It?"(August 2005). Peter J.Katzenstein and Rudra Sil,"Rethinking Asian Security:A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in J.J.Suh,Peter J.Katzenstein,and Allen Carlson,eds.,Rethinking Se- curity in East Asia:Identity,Power and Efficiency(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33.Peter J.Katzenstein and Nobuo Okawara,"Japan and Asian- Pacific Security:Analytical Eclecticism,not Parsimony,"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2 (Winter2001/02):153-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