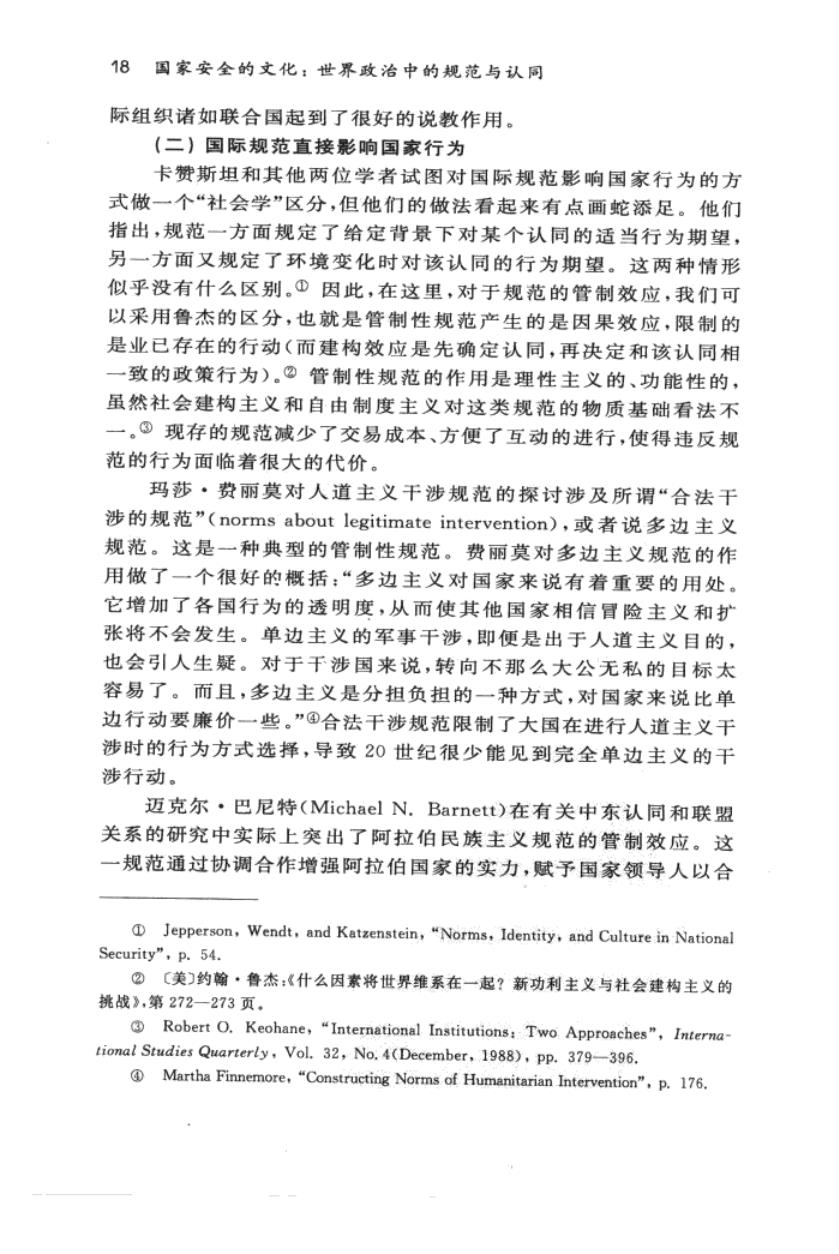
18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 际组织诸如联合国起到了很好的说教作用。 (二)国际规范直接影响国家行为 卡赞斯坦和其他两位学者试图对国际规范影响国家行为的方 式做一个“社会学”区分,但他们的做法看起来有点画蛇添足。他们 指出,规范一方面规定了给定背景下对某个认同的适当行为期望, 另一方面又规定了环境变化时对该认同的行为期望。这两种情形 似乎没有什么区别。①因此,在这里,对于规范的管制效应,我们可 以采用鲁杰的区分,也就是管制性规范产生的是因果效应,限制的 是业已存在的行动(而建构效应是先确定认同,再决定和该认同相 一致的政策行为)。②管制性规范的作用是理性主义的、功能性的, 虽然社会建构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对这类规范的物质基础看法不 一。③现存的规范减少了交易成本、方便了互动的进行,使得违反规 范的行为面临着很大的代价。 玛莎·费丽莫对人道主义干涉规范的探讨涉及所谓“合法干 涉的规范”(norms about legitimate intervention),或者说多边主义 规范。这是一种典型的管制性规范。费丽莫对多边主义规范的作 用做了一个很好的概括:“多边主义对国家来说有着重要的用处。 它增加了各国行为的透明度,从而使其他国家相信冒险主义和扩 张将不会发生。单边主义的军事干涉,即便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 也会引人生疑。对于干涉国来说,转向不那么大公无私的目标太 容易了。而且,多边主义是分担负担的一种方式,对国家来说比单 边行动要廉价一些。”④合法干涉规范限制了大国在进行人道主义干 涉时的行为方式选择,导致20世纪很少能见到完全单边主义的干 涉行动。 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N.Barnett)在有关中东认同和联盟 关系的研究中实际上突出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规范的管制效应。这 一规范通过协调合作增强阿拉伯国家的实力,赋予国家领导人以合 D Jepperson,Wendt,and Katzenstein,"Norms,Identity,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p.54. ②〔美〕约翰·鲁杰:《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 挑战》,第272一273页。 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Interna- 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2,No.4(December,1988),pp.379-396. Martha Finnemore,"Constructing Norm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p.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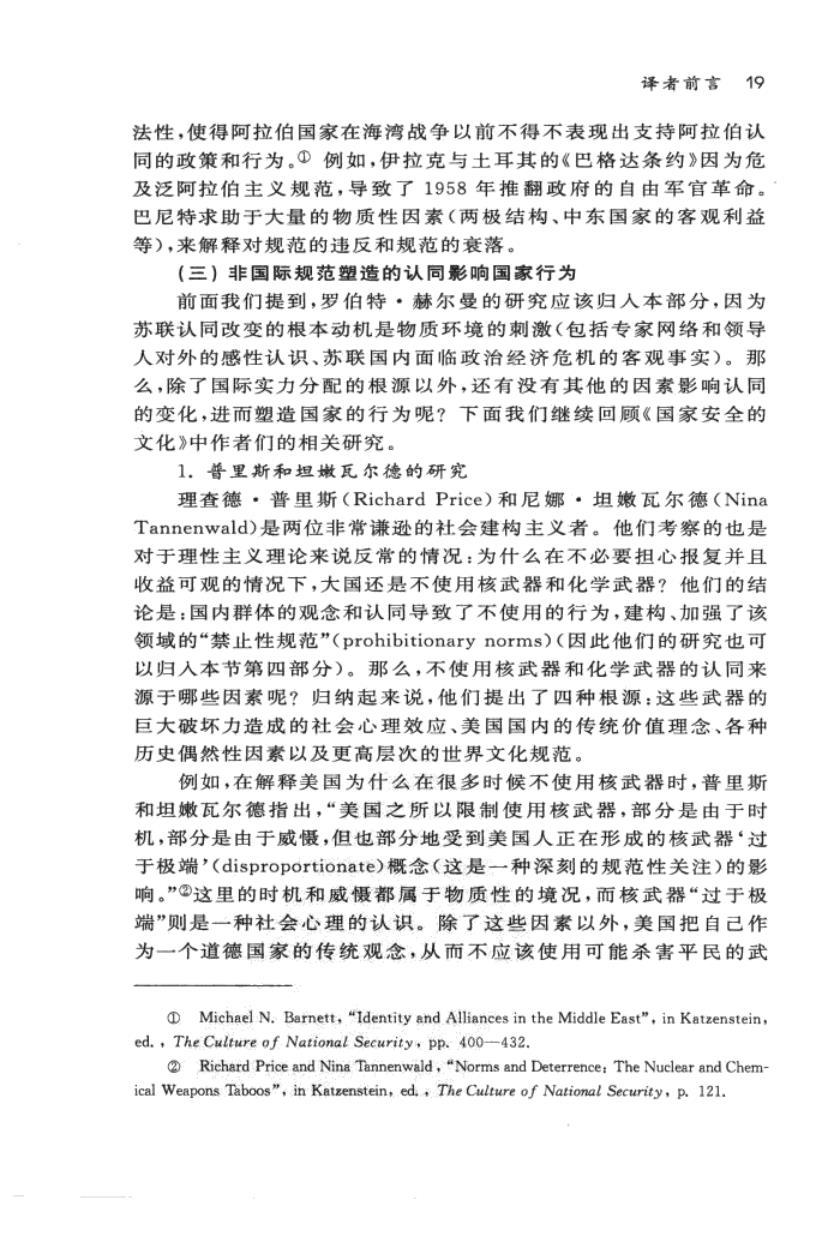
译者前言19 法性,使得阿拉伯国家在海湾战争以前不得不表现出支持阿拉伯认 同的政策和行为。①例如,伊拉克与土耳其的《巴格达条约》因为危 及泛阿拉伯主义规范,导致了1958年推翻政府的自由军官革命。 巴尼特求助于大量的物质性因素(两极结构、中东国家的客观利益 等),来解释对规范的违反和规范的衰落。 (三)非国际规范塑造的认同影响国家行为 前面我们提到,罗伯特·赫尔曼的研究应该归人本部分,因为 苏联认同改变的根本动机是物质环境的刺激(包括专家网络和领导 人对外的感性认识、苏联国内面临政治经济危机的客观事实)。那 么,除了国际实力分配的根源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影响认同 的变化,进而塑造国家的行为呢?下面我们继续回顾《国家安全的 文化》中作者们的相关研究。 1,普里斯和坦嫩瓦尔德的研究 理查德·普里斯(Richard Price)和尼娜·坦嫩瓦尔德(Nina Tannenwald)是两位非常谦逊的社会建构主义者。他们考察的也是 对于理性主义理论来说反常的情况:为什么在不必要担心报复并且 收益可观的情况下,大国还是不使用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他们的结 论是:国内群体的观念和认同导致了不使用的行为,建构、加强了该 领域的“禁止性规范”(prohibitionary norms)(因此他们的研究也可 以归入本节第四部分)。那么,不使用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认同来 源于哪些因素呢?归纳起来说,他们提出了四种根源:这些武器的 巨大破坏力造成的社会心理效应、美国国内的传统价值理念、各种 历史偶然性因素以及更高层次的世界文化规范。 例如,在解释美国为什么在很多时候不使用核武器时,普里斯 和坦嫩瓦尔德指出,“美国之所以限制使用核武器,部分是由于时 机,部分是由于威慑,但也部分地受到美国人正在形成的核武器‘过 于极端'(disproportionate)概念(这是一种深刻的规范性关注)的影 响。”②这里的时机和威慑都属于物质性的境况,而核武器“过于极 端”则是一种社会心理的认识。除了这些因素以外,美国把自己作 为一个道德国家的传统观念,从而不应该使用可能杀害平民的武 D Michael N.Barnett,"Identity and Alliances in the Middle East",in Katzenstein, 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pp.400-432. 2 Richard Price and Nina Tannenwald,"Norms and Deterrence:The Nuclear and Chem- ical Weapons Taboos",in 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p.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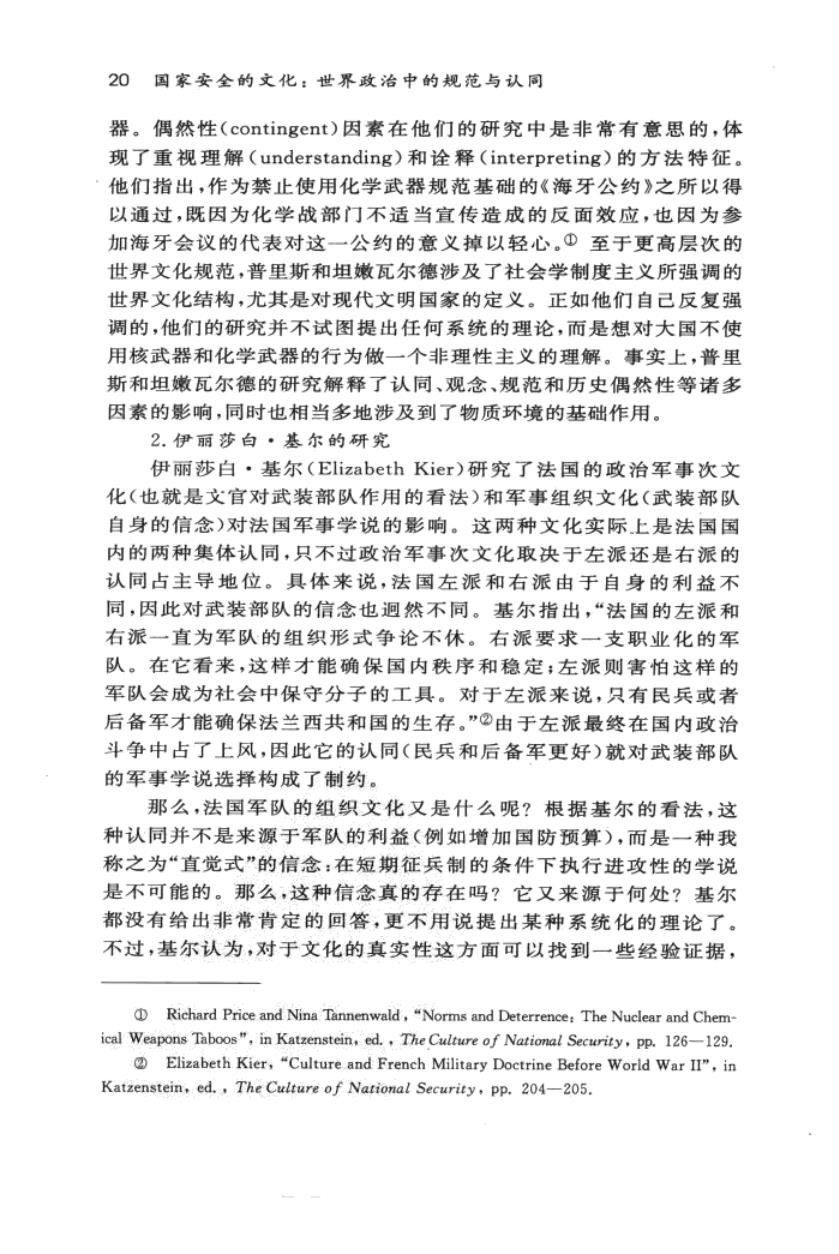
20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 器。偶然性(contingent)因素在他们的研究中是非常有意思的,体 现了重视理解(understanding)和诠释(interpreting)的方法特征。 他们指出,作为禁止使用化学武器规范基础的《海牙公约》之所以得 以通过,既因为化学战部门不适当宜传造成的反面效应,也因为参 加海牙会议的代表对这一公约的意义掉以轻心。①至于更高层次的 世界文化规范,普里斯和坦嫩瓦尔德涉及了社会学制度主义所强调的 世界文化结构,尤其是对现代文明国家的定义。正如他们自己反复强 调的,他们的研究并不试图提出任何系统的理论,而是想对大国不使 用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行为做一个非理性主义的理解。事实上,普里 斯和坦嫩瓦尔德的研究解释了认同、观念、规范和历史偶然性等诸多 因素的影响,同时也相当多地涉及到了物质环境的基础作用。 2.伊丽莎白·基尔的研究 伊丽莎白·基尔(Elizabeth Kier)研究了法国的政治军事次文 化(也就是文官对武装部队作用的看法)和军事组织文化(武装部队 自身的信念)对法国军事学说的影响。这两种文化实际上是法国国 内的两种集体认同,只不过政治军事次文化取决于左派还是右派的 认同占主导地位。具体来说,法国左派和右派由于自身的利益不 同,因此对武装部队的信念也迥然不同。基尔指出,“法国的左派和 右派一直为军队的组织形式争论不休。右派要求一支职业化的军 队。在它看来,这样才能确保国内秩序和稳定:左派则害怕这样的 军队会成为社会中保守分子的工具。对于左派来说,只有民兵或者 后备军才能确保法兰西共和国的生存。”②由于左派最终在国内政治 斗争中占了上风,因此它的认同(民兵和后备军更好)就对武装部队 的军事学说选择构成了制约。 那么,法国军队的组织文化又是什么呢?根据基尔的看法,这 种认同并不是来源于军队的利益(例如增加国防预算),而是一种我 称之为“直觉式”的信念:在短期征兵制的条件下执行进攻性的学说 是不可能的。那么,这种信念真的存在吗?它又来源于何处?基尔 都没有给出非常肯定的回答,更不用说提出某种系统化的理论了。 不过,基尔认为,对于文化的真实性这方面可以找到一些经验证据, D Richard Price and Nina Tannenwald,"Norms and Deterrence:The Nuclear and Chem- ical Weapons Taboos",in 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pp.126-129. Elizabeth Kier,"Culture and French Military Doctrine Before World War II",in 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pp.204-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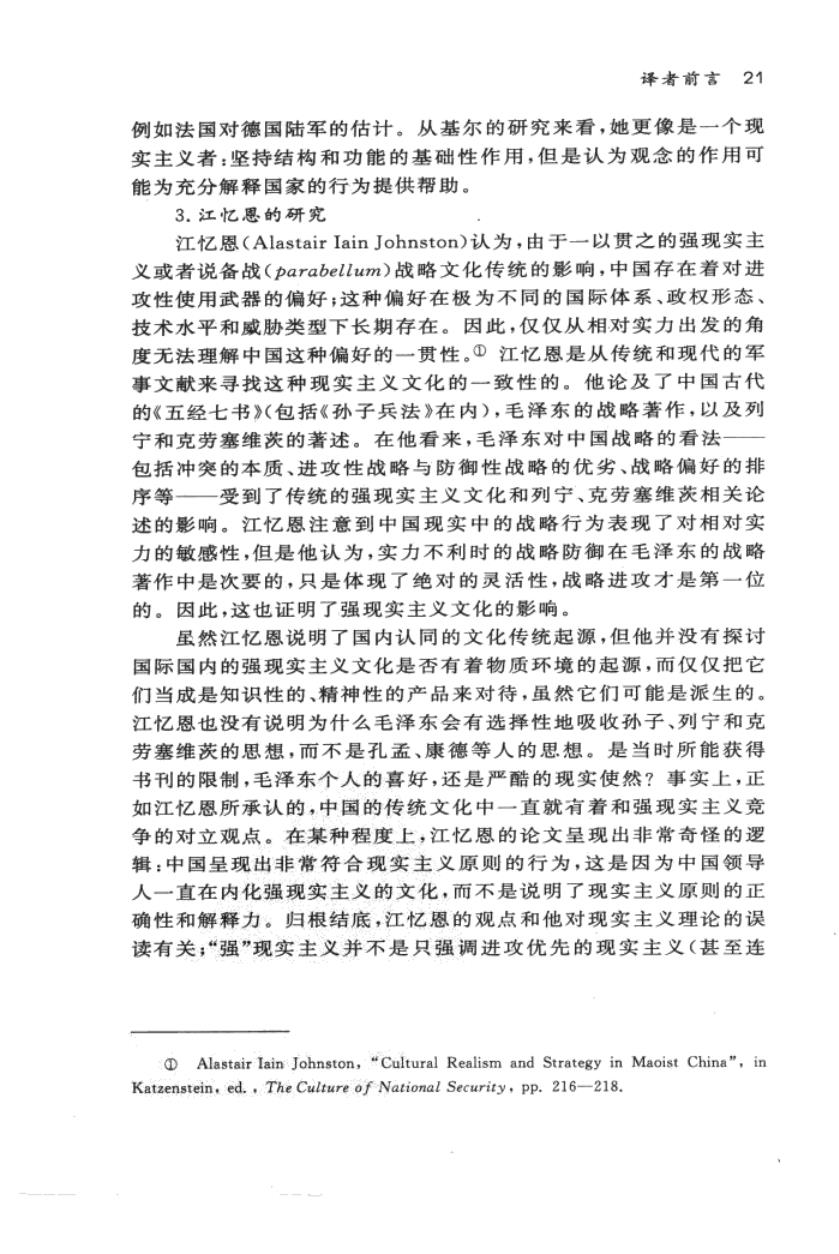
译者前言21 例如法国对德国陆军的估计。从基尔的研究来看,她更像是一个现 实主义者:坚持结构和功能的基础性作用,但是认为观念的作用可 能为充分解释国家的行为提供帮助。 3.江忆思的研究 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认为,由于一以贯之的强现实主 义或者说备战(parabellum)战略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存在着对进 攻性使用武器的偏好;这种偏好在极为不同的国际体系、政权形态、 技术水平和威胁类型下长期存在。因此,仅仅从相对实力出发的角 度无法理解中国这种偏好的一贯性。①江忆恩是从传统和现代的军 事文献来寻找这种现实主义文化的一致性的。他论及了中国古代 的《五经七书》(包括《孙子兵法》在内),毛泽东的战略著作,以及列 宁和克劳塞维茨的著述。在他看来,毛泽东对中国战略的看法 包括冲突的本质、进攻性战略与防御性战略的优劣、战略偏好的排 序等一受到了传统的强现实主义文化和列宁、克劳塞维茨相关论 述的影响。江忆恩注意到中国现实中的战略行为表现了对相对实 力的敏感性,但是他认为,实力不利时的战略防御在毛泽东的战略 著作中是次要的,只是体现了绝对的灵活性,战略进攻才是第一位 的。因此,这也证明了强现实主义文化的影响。 虽然江忆恩说明了国内认同的文化传统起源,但他并没有探讨 国际国内的强现实主义文化是否有着物质环境的起源,而仅仅把它 们当成是知识性的、精神性的产品来对待,虽然它们可能是派生的。 江忆恩也没有说明为什么毛泽东会有选择性地吸收孙子、列宁和克 劳塞维茨的思想,而不是孔孟、康德等人的思想。是当时所能获得 书刊的限制,毛泽东个人的喜好,还是严酷的现实使然?事实上,正 如江忆恩所承认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就有着和强现实主义竞 争的对立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江忆恩的论文呈现出非常奇怪的逻 辑:中国呈现出非常符合现实主义原则的行为,这是因为中国领导 人一直在内化强现实主义的文化,而不是说明了现实主义原则的正 确性和解释力。归根结底,江忆恩的观点和他对现实主义理论的误 读有关,“强”现实主义并不是只强调进攻优先的现实主义(甚至连 D 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in 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pp.216-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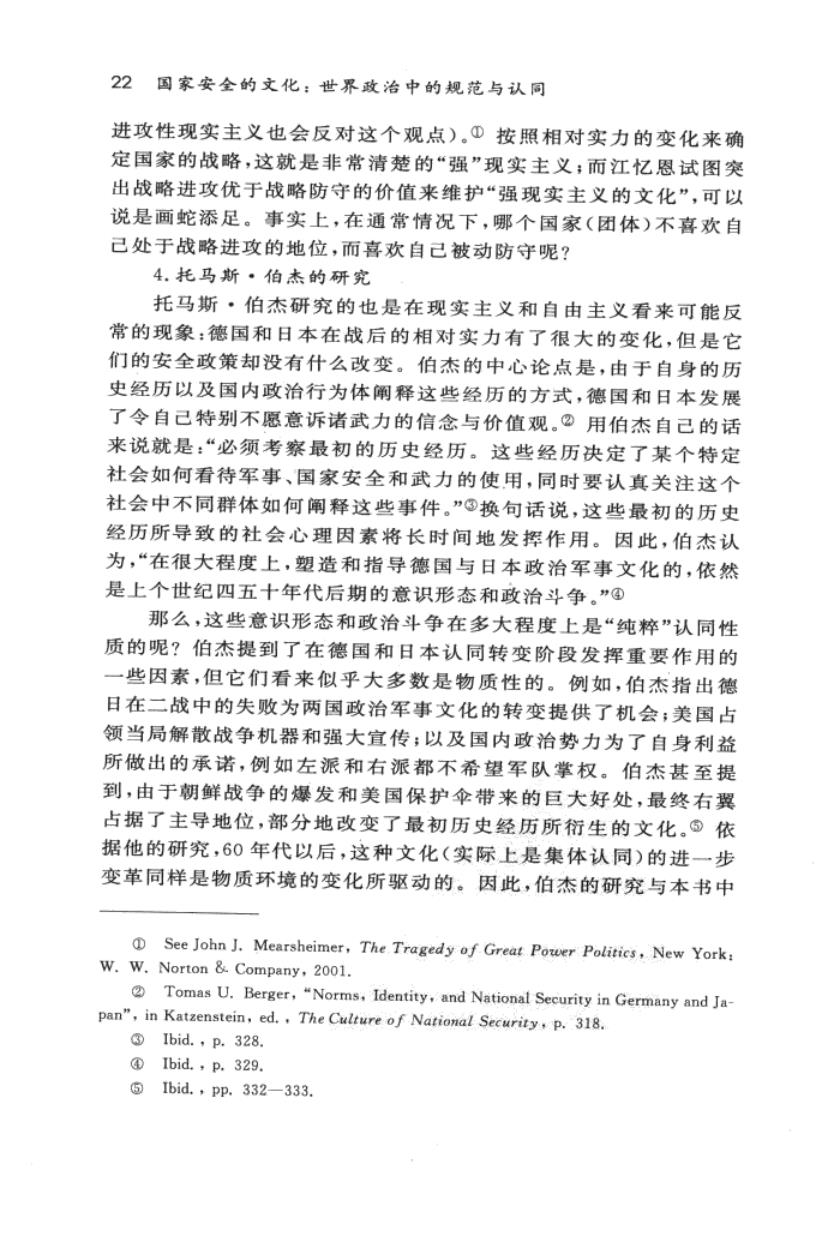
22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 进攻性现实主义也会反对这个观点)。①按照相对实力的变化来确 定国家的战略,这就是非常清楚的“强”现实主义:而江忆恩试图突 出战略进攻优于战略防守的价值来维护“强现实主义的文化”,可以 说是画蛇添足。事实上,在通常情况下,哪个国家(团体)不喜欢自 己处于战略进攻的地位,而喜欢自己被动防守呢? 4.托马斯·伯杰的研究 托马斯·伯杰研究的也是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看来可能反 常的现象: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的相对实力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它 们的安全政策却没有什么改变。伯杰的中心论点是,由于自身的历 史经历以及国内政治行为体阐释这些经历的方式,德国和日本发展 了令自己特别不愿意诉诸武力的信念与价值观。②用伯杰自己的话 来说就是:“必须考察最初的历史经历。这些经历决定了某个特定 社会如何看待军事、国家安全和武力的使用,同时要认真关注这个 社会中不同群体如何阐释这些事件。”③换句话说,这些最初的历史 经历所导致的社会心理因素将长时间地发挥作用。因此,伯杰认 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和指导德国与日本政治军事文化的,依然 是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后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④ 那么,这些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在多大程度上是“纯粹”认同性 质的呢?伯杰提到了在德国和日本认同转变阶段发挥重要作用的 一些因素,但它们看来似乎大多数是物质性的。例如,伯杰指出德 日在二战中的失败为两国政治军事文化的转变提供了机会;美国占 领当局解散战争机器和强大宣传;以及国内政治势力为了自身利益 所做出的承诺,例如左派和右派都不希望军队掌权。伯杰甚至提 到,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保护伞带来的巨大好处,最终右翼 占据了主导地位,部分地改变了最初历史经历所衍生的文化。⑤依 据他的研究,60年代以后,这种文化(实际上是集体认同)的进一步 变革同样是物质环境的变化所驱动的。因此,伯杰的研究与本书中 See 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 W.W.Norton Company,2001. 2 Tomas U.Berger,"Norms,Identity,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Germany and Ja- pan",in 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p.318. ③Ibid.,p.328. ④Ibid.,p.329. ⑤Ibid.,pp.332-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