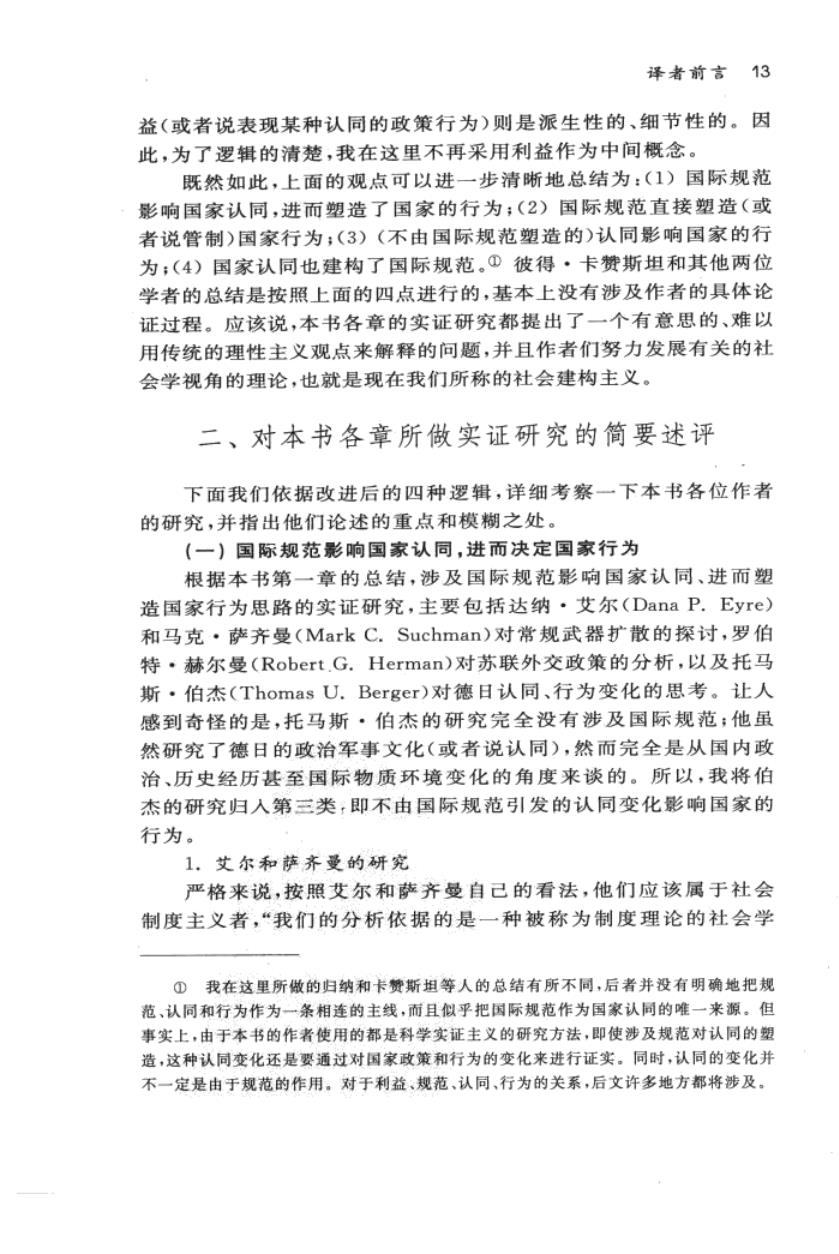
译者前言13 益(或者说表现某种认同的政策行为)则是派生性的、细节性的。因 此,为了逻辑的清楚,我在这里不再采用利益作为中间概念。 既然如此,上面的观点可以进一步清晰地总结为:(1)国际规范 影响国家认同,进而塑造了国家的行为:(2)国际规范直接塑造(或 者说管制)国家行为:(3)(不由国际规范塑造的)认同影响国家的行 为:(4)国家认同也建构了国际规范。①彼得·卡赞斯坦和其他两位 学者的总结是按照上面的四点进行的,基本上没有涉及作者的具体论 证过程。应该说,本书各章的实证研究都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难以 用传统的理性主义观点来解释的问题,并且作者们努力发展有关的社 会学视角的理论,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称的社会建构主义。 二、对本书各章所做实证研究的简要述评 下面我们依据改进后的四种逻辑,详细考察一下本书各位作者 的研究,并指出他们论述的重点和模糊之处。 (一)国际规范影响国家认同,进而决定国家行为 根据本书第一章的总结,涉及国际规范影响国家认同、进而塑 造国家行为思路的实证研究,主要包括达纳·艾尔(Dana P.Eyre) 和马克·萨齐曼(Mark C.Suchman)对常规武器扩散的探讨,罗伯 特·赫尔曼(Robert.G.Herman)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分析,以及托马 斯·伯杰(Thomas U.Berger)对德日认同、行为变化的思考。让人 感到奇怪的是,托马斯·伯杰的研究完全没有涉及国际规范:他虽 然研究了德日的政治军事文化(或者说认同),然而完全是从国内政 治、历史经历甚至国际物质环境变化的角度来谈的。所以,我将伯 杰的研究归入第三类,即不由国际规范引发的认同变化影响国家的 行为。 1,艾尔和萨齐曼的研究 严格来说,按照艾尔和萨齐曼自己的看法,他们应该属于社会 制度主义者,“我们的分析依据的是一种被称为制度理论的社会学 ①我在这里所做的归纳和卡赞斯坦等人的总结有所不同,后者并没有明确地把规 范、认同和行为作为一条相连的主线,而且似乎把国际规范作为国家认同的唯一来源。但 事实上,由于本书的作者使用的都是科学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即使涉及规范对认同的塑 造,这种认同变化还是要通过对国家政策和行为的变化来进行证实。同时,认同的变化并 不一定是由于规范的作用。对于利益、规范、认同,行为的关系,后文许多地方都将涉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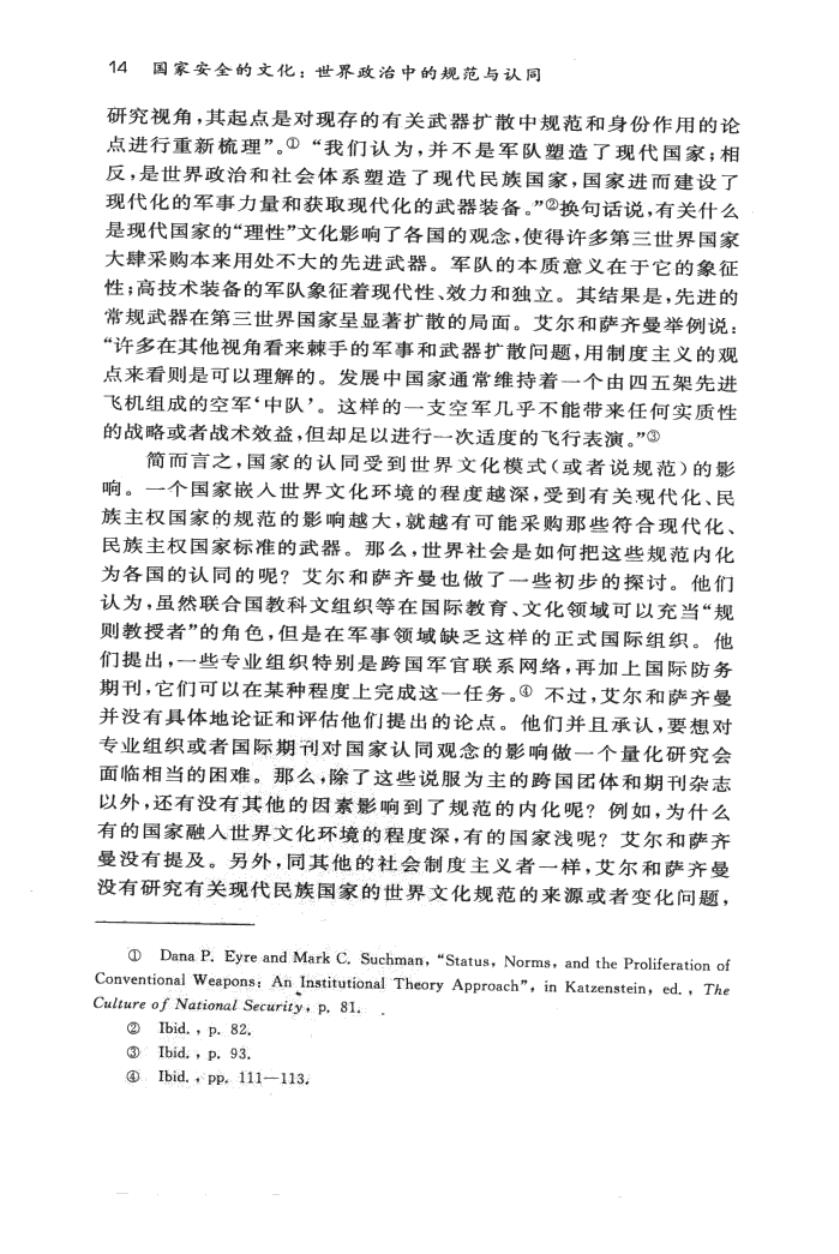
14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 研究视角,其起点是对现存的有关武器扩散中规范和身份作用的论 点进行重新梳理”。①“我们认为,并不是军队塑造了现代国家;相 反,是世界政治和社会体系塑造了现代民族国家,国家进而建设了 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和获取现代化的武器装备。”②换句话说,有关什么 是现代国家的“理性”文化影响了各国的观念,使得许多第三世界国家 大肆采购本来用处不大的先进武器。军队的本质意义在于它的象征 性;高技术装备的军队象征着现代性、效力和独立。其结果是,先进的 常规武器在第三世界国家呈显著扩散的局面。艾尔和萨齐曼举例说: “许多在其他视角看来棘手的军事和武器扩散问题,用制度主义的观 点来看则是可以理解的。发展中国家通常维持着一个由四五架先进 飞机组成的空军‘中队’。这样的一支空军几乎不能带来任何实质性 的战略或者战术效益,但却足以进行一次适度的飞行表演。”③ 简而言之,国家的认同受到世界文化模式(或者说规范)的影 响。一个国家嵌人世界文化环境的程度越深,受到有关现代化、民 族主权国家的规范的影响越大,就越有可能采购那些符合现代化、 民族主权国家标准的武器。那么,世界社会是如何把这些规范内化 为各国的认同的呢?艾尔和萨齐曼也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他们 认为,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在国际教育、文化领域可以充当“规 则教授者”的角色,但是在军事领域缺乏这样的正式国际组织。他 们提出,一些专业组织特别是跨国军官联系网络,再加上国际防务 期刊,它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完成这一任务。④不过,艾尔和萨齐曼 并没有具体地论证和评估他]提出的论点。他们并且承认,要想对 专业组织或者国际期刊对国家认同观念的影响做一个量化研究会 面临相当的困难。那么,除了这些说服为主的跨国团体和期刊杂志 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影响到了规范的内化呢?例如,为什么 有的国家融入世界文化环境的程度深,有的国家浅呢?艾尔和萨齐 曼没有提及。另外,同其他的社会制度主义者一样,艾尔和萨齐曼 没有研究有关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界文化规范的来源或者变化问题, ① Dana P.Eyre and Mark C.Suchman,"Status,Norms,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Conventional Weapons:An Institutional Theory Approach",in 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p.81. ②Ibid.,p.82. ③Ibid.,p.93. ④bid.,pp,111-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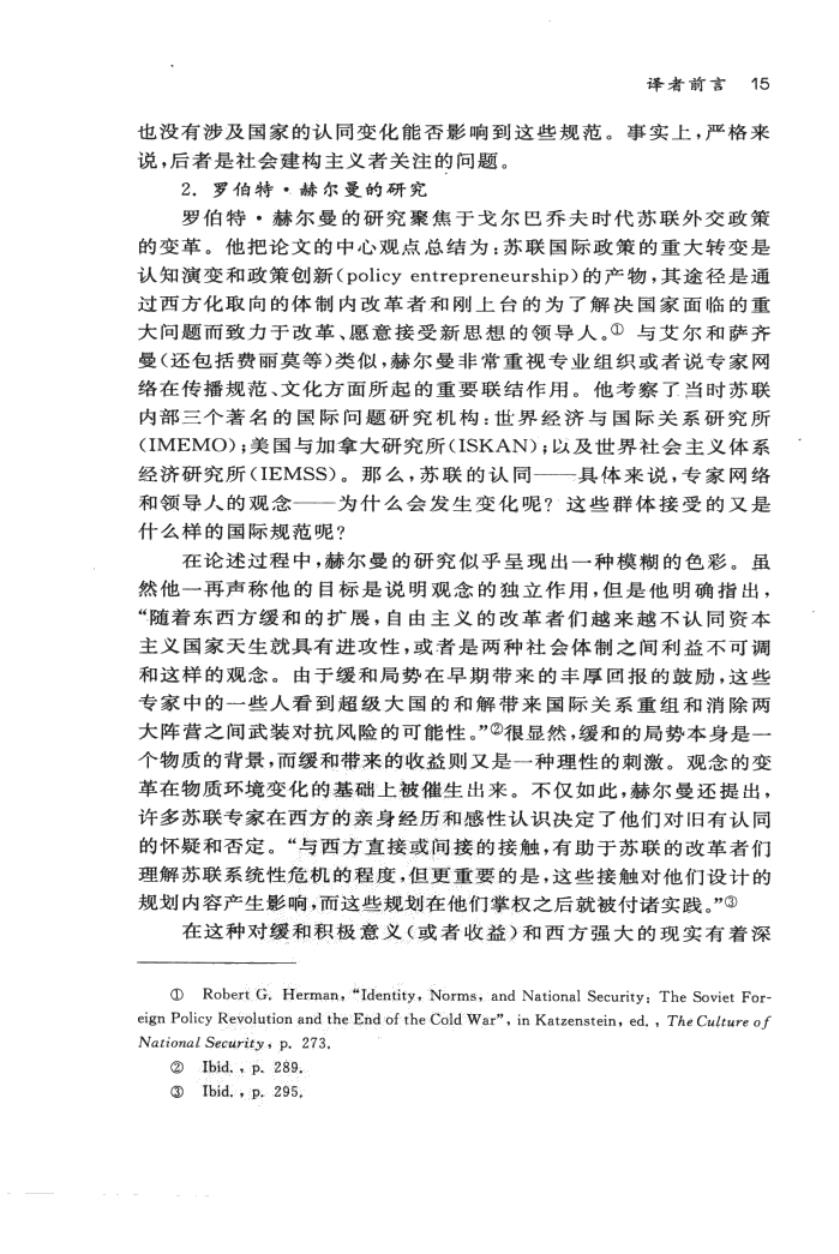
译者前言15 也没有涉及国家的认同变化能否影响到这些规范。事实上,严格来 说,后者是社会建构主义者关注的问题。 2。罗伯特·赫尔曼的研究 罗伯特·赫尔曼的研究聚焦于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外交政策 的变革。他把论文的中心观点总结为:苏联国际政策的重大转变是 认知演变和政策创新(policy entrepreneurship)的产物,其途径是通 过西方化取向的体制内改革者和刚上台的为了解决国家面临的重 大问题而致力于改革、愿意接受新思想的领导人。①与艾尔和萨齐 曼(还包括费丽莫等)类似,赫尔曼非常重视专业组织或者说专家网 络在传播规范、文化方面所起的重要联结作用。他考察了当时苏联 内部三个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 (IMEMO);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ISKAN):以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经济研究所(IEMSS)。那么,苏联的认同一具体来说,专家网络 和领导人的观念一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这些群体接受的又是 什么样的国际规范呢? 在论述过程中,赫尔曼的研究似乎呈现出一种模糊的色彩。虽 然他一再声称他的目标是说明观念的独立作用,但是他明确指出, “随着东西方缓和的扩展,自由主义的改革者们越来越不认同资本 主义国家天生就具有进攻性,或者是两种社会体制之间利益不可调 和这样的观念。由于缓和局势在早期带来的丰厚回报的鼓励,这些 专家中的一些人看到超级大国的和解带来国际关系重组和消除两 大阵营之间武装对抗风险的可能性。”②很显然,缓和的局势本身是一 个物质的背景,而缓和带来的收益则又是一种理性的刺激。观念的变 革在物质环境变化的基础上被催生出来。不仅如此,赫尔曼还提出, 许多苏联专家在西方的亲身经历和感性认识决定了他们对旧有认同 的怀疑和否定。“与西方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有助于苏联的改革者们 理解苏联系统性危机的程度,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接触对他们设计的 规划内容产生影响,而这些规划在他们掌权之后就被付诸实践。”③ 在这种对缓和积极意义(或者收益)和西方强大的现实有着深 D Robert G.Herman,"Identity,Norms,and National Security:The Soviet For- eign Policy Revolu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n 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p.273. ②Ibid.,p.289. ③Tbid,p.2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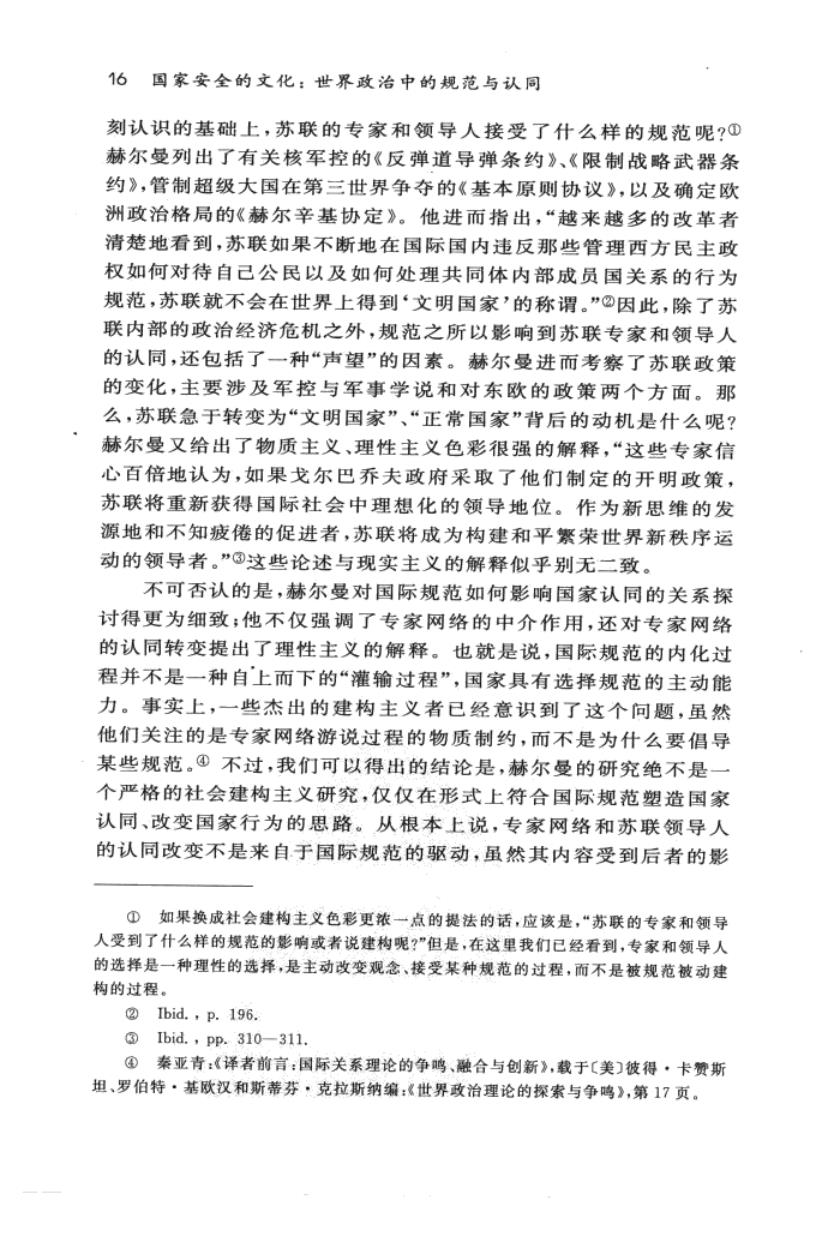
16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 刻认识的基础上,苏联的专家和领导人接受了什么样的规范呢?① 赫尔曼列出了有关核军控的《反弹道导弹条约》、《限制战略武器条 约》,管制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争夺的《基本原则协议》,以及确定欧 洲政治格局的《赫尔辛基协定》。他进而指出,“越来越多的改革者 清楚地看到,苏联如果不断地在国际国内违反那些管理西方民主政 权如何对待自己公民以及如何处理共同体内部成员国关系的行为 规范,苏联就不会在世界上得到‘文明国家’的称谓。”②因此,除了苏 联内部的政治经济危机之外,规范之所以影响到苏联专家和领导人 的认同,还包括了一种“声望”的因素。赫尔曼进而考察了苏联政策 的变化,主要涉及军控与军事学说和对东欧的政策两个方面。那 么,苏联急于转变为“文明国家”、“正常国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 赫尔曼又给出了物质主义、理性主义色彩很强的解释,“这些专家信 心百倍地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政府采取了他们制定的开明政策, 苏联将重新获得国际社会中理想化的领导地位。作为新思维的发 源地和不知疲倦的促进者,苏联将成为构建和平繁荣世界新秩序运 动的领导者。”③这些论述与现实主义的解释似乎别无二致。 不可否认的是,赫尔曼对国际规范如何影响国家认同的关系探 讨得更为细致:他不仅强调了专家网络的中介作用,还对专家网络 的认同转变提出了理性主义的解释。也就是说,国际规范的内化过 程并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灌输过程”,国家具有选择规范的主动能 力。事实上,一些杰出的建构主义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虽然 他们关注的是专家网络游说过程的物质制约,而不是为什么要倡导 某些规范。④不过,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赫尔曼的研究绝不是一 个严格的社会建构主义研究,仅仅在形式上符合国际规范塑造国家 认同、改变国家行为的思路。从根本上说,专家网络和苏联领导人 的认同改变不是来自于国际规范的驱动,虽然其内容受到后者的影 ①如果换成社会建构主义色彩更浓一点的提法的话,应该是,“苏联的专家和领导 人受到了什么样的规范的影响或者说建构呢?”但是,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专家和领导人 的选择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是主动改变观念、接受某种规范的过程,而不是被规范被动建 构的过程。 ②Ibid.,p.196. ③Ibid.,pp.310-311. ④秦亚青:《译者前言:国际关系理论的争鸣、融合与创新》,载于〔美彼得·卡赞斯 坦、罗伯特·基欧汉和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第1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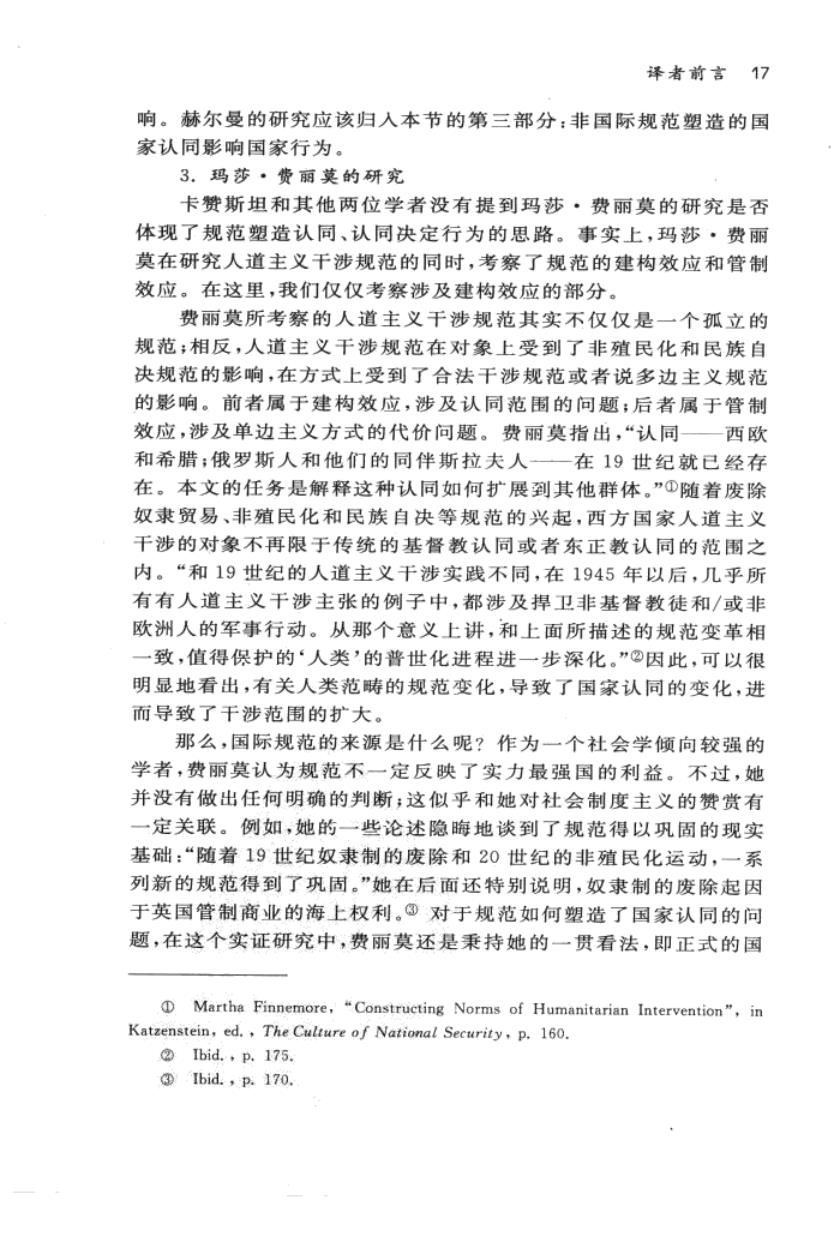
译者前言17 响。赫尔曼的研究应该归入本节的第三部分:非国际规范塑造的国 家认同影响国家行为。 3。玛莎·费丽莫的研究 卡赞斯坦和其他两位学者没有提到玛莎·费丽莫的研究是否 体现了规范塑造认同、认同决定行为的思路。事实上,玛莎·费丽 莫在研究人道主义干涉规范的同时,考察了规范的建构效应和管制 效应。在这里,我们仅仅考察涉及建构效应的部分。 费丽莫所考察的人道主义干涉规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 规范:相反,人道主义干涉规范在对象上受到了非殖民化和民族自 决规范的影响,在方式上受到了合法干涉规范或者说多边主义规范 的影响。前者属于建构效应,涉及认同范围的问题;后者属于管制 效应,涉及单边主义方式的代价问题。费丽莫指出,“认同一西欧 和希腊:俄罗斯人和他们的同伴斯拉夫人一在19世纪就已经存 在。本文的任务是解释这种认同如何扩展到其他群体。”①随着废除 奴隶贸易、非殖民化和民族自决等规范的兴起,西方国家人道主义 干涉的对象不再限于传统的基督教认同或者东正教认同的范围之 内。“和19世纪的人道主义干涉实践不同,在1945年以后,几乎所 有有人道主义干涉主张的例子中,都涉及捍卫非基督教徒和/或非 欧洲人的军事行动。从那个意义上讲,和上面所描述的规范变革相 一致,值得保护的‘人类'的普世化进程进一步深化。”②因此,可以很 明显地看出,有关人类范畴的规范变化,导致了国家认同的变化,进 而导致了干涉范围的扩大。 那么,国际规范的来源是什么呢?作为一个社会学倾向较强的 学者,费丽莫认为规范不一定反映了实力最强国的利益。不过,她 并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判断;这似乎和她对社会制度主义的赞赏有 一定关联。例如,她的一些论述隐晦地谈到了规范得以巩固的现实 基础:“随着19世纪奴隶制的废除和20世纪的非殖民化运动,一系 列新的规范得到了巩固。”她在后面还特别说明,奴隶制的废除起因 于英国管制商业的海上权利。③对于规范如何塑造了国家认同的问 题,在这个实证研究中,费丽莫还是秉持她的一贯看法,即正式的国 D Martha Finnemore,"Constructing Norm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in 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p.160. ②Ibid.,p.175. ③bid.,p.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