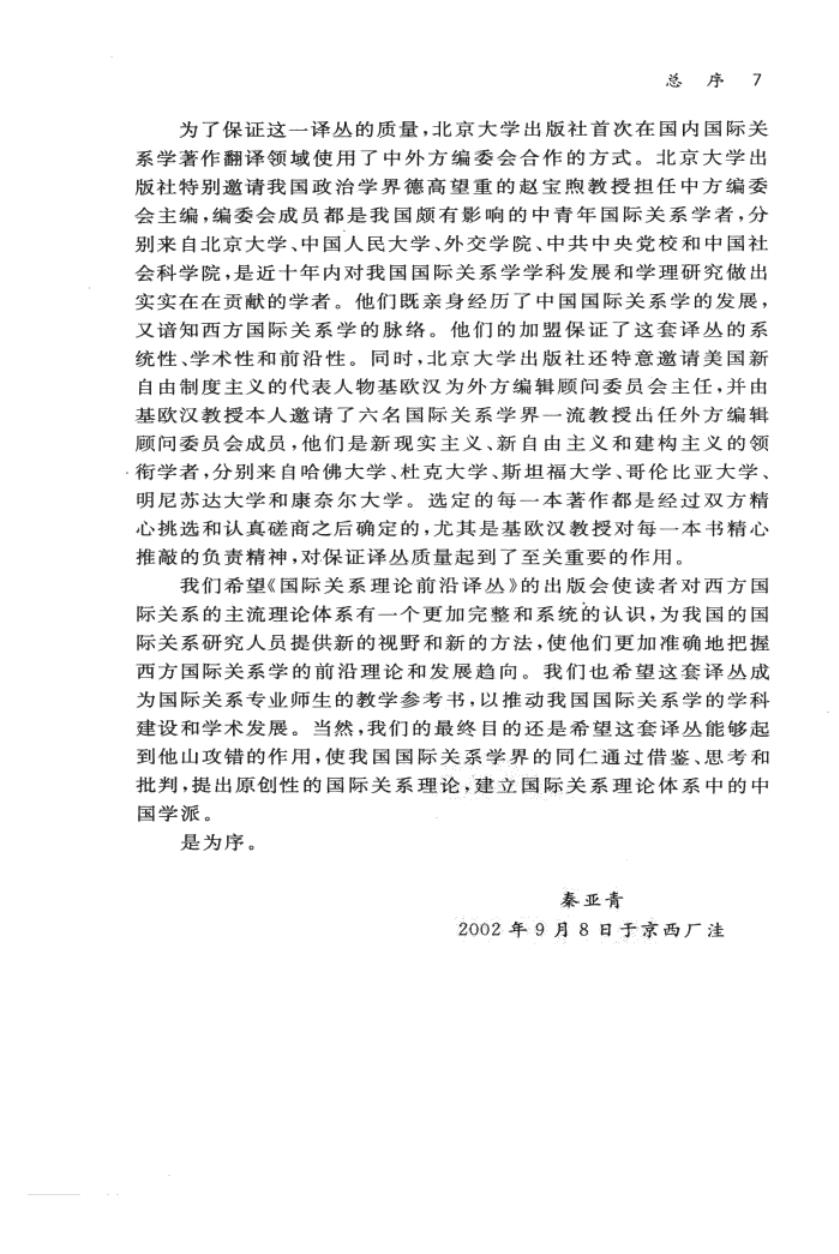
总序7 为了保证这一译丛的质量,北京大学出版社首次在国内国际关 系学著作翻译领域使用了中外方编委会合作的方式。北京大学出 版社特别邀请我国政治学界德高望重的赵宝煦教授担任中方编委 会主编,编委会成员都是我国颇有影响的中青年国际关系学者,分 别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社 会科学院,是近十年内对我国国际关系学学科发展和学理研究做出 实实在在贡献的学者。他们既亲身经历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 又谙知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脉络。他们的加盟保证了这套译丛的系 统性、学术性和前沿性。同时,北京大学出版社还特意邀请美国新 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基欧汉为外方编辑顾问委员会主任,并由 基欧汉教授本人邀请了六名国际关系学界一流教授出任外方编辑 顾问委员会成员,他们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领 衔学者,分别来自哈佛大学、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明尼苏达大学和康奈尔大学。选定的每一本著作都是经过双方精 心挑选和认真磋商之后确定的,尤其是基欧汉教授对每一本书精心 推敲的负责精神,对保证译丛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希望《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的出版会使读者对西方国 际关系的主流理论体系有一个更加完整和系统的认识,为我国的国 际关系研究人员提供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使他们更加准确地把握 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前沿理论和发展趋向。我们也希望这套译丛成 为国际关系专业师生的教学参考书,以推动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 建设和学术发展。当然,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这套译丛能够起 到他山攻错的作用,使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同仁通过借鉴、思考和 批判,提出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中 国学派。 是为序。 秦亚青 2002年9月8日于京西厂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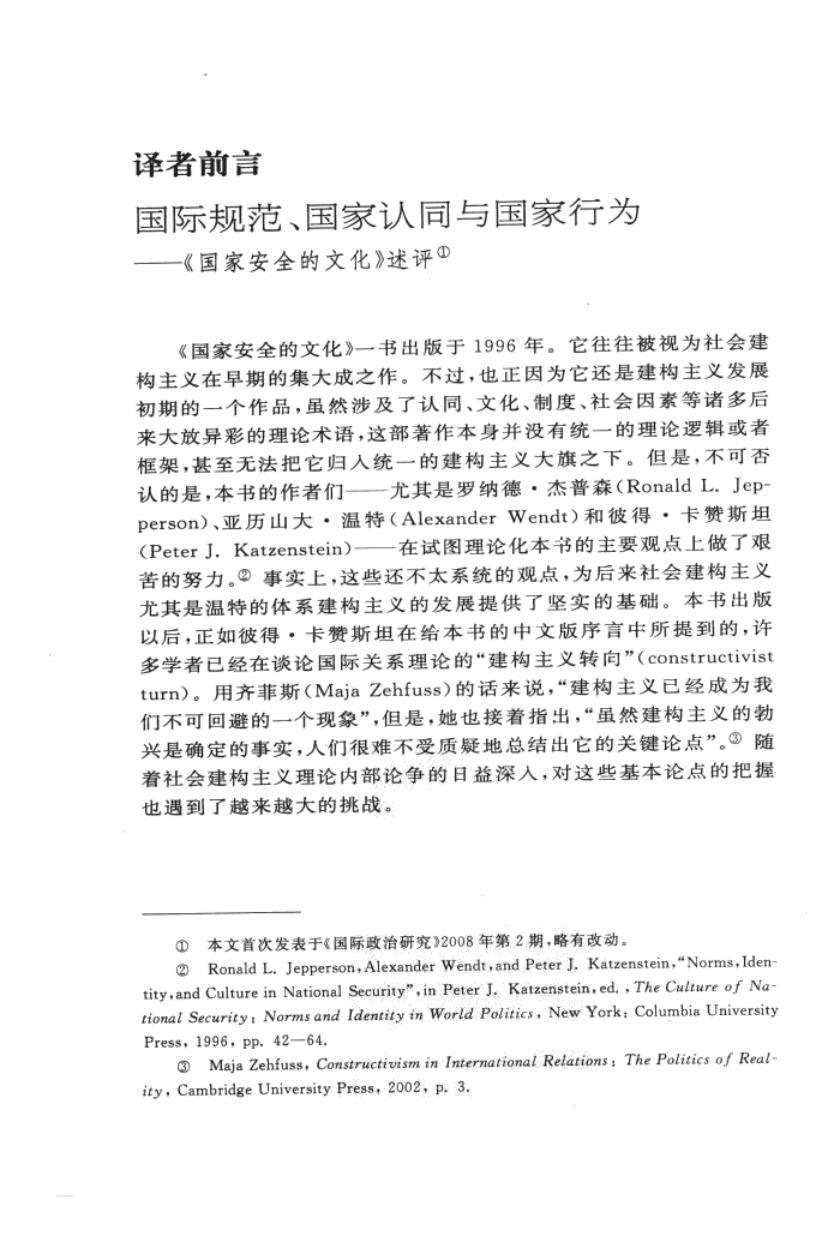
译者前言 国际规范、国家认同与国家行为 —《国家安全的文化》述评① 《国家安全的文化》一书出版于1996年。它往往被视为社会建 构主义在早期的集大成之作。不过,也正因为它还是建构主义发展 初期的一个作品,虽然涉及了认同、文化、制度、社会因素等诸多后 来大放异彩的理论术语,这部著作本身并没有统一的理论逻辑或者 框架,甚至无法把它归入统一的建构主义大旗之下。但是,不可否 认的是,本书的作者们一尤其是罗纳德·杰普森(Ronald L.Jep person)、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和彼得·卡赞斯坦 (Peter J.Katzenstein)一在试图理论化本书的主要观点上做了艰 苦的努力。③事实上,这些还不太系统的观点,为后来社会建构主义 尤其是温特的体系建构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本书出版 以后,正如彼得·卡赞斯坦在给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所提到的,许 多学者已经在谈论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主义转向”(constructivist turn)。用齐菲斯(Maja Zehfuss)的话来说,“建构主义已经成为我 们不可回避的一个现象”,但是,她也接着指出,“虽然建构主义的勃 兴是确定的事实,人们很难不受质疑地总结出它的关键论点”。③随 着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内部论争的日益深入,对这些基本论点的把握 也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 ① 本文首次发表于《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略有改动。 Ronald L.Jepperson,Alexander Wendt,and Peter J.Katzenstein,"Norms,Iden- tity,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in Peter J.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 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p.42-64, 3 Maja Zehfuss,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Politics of Real- 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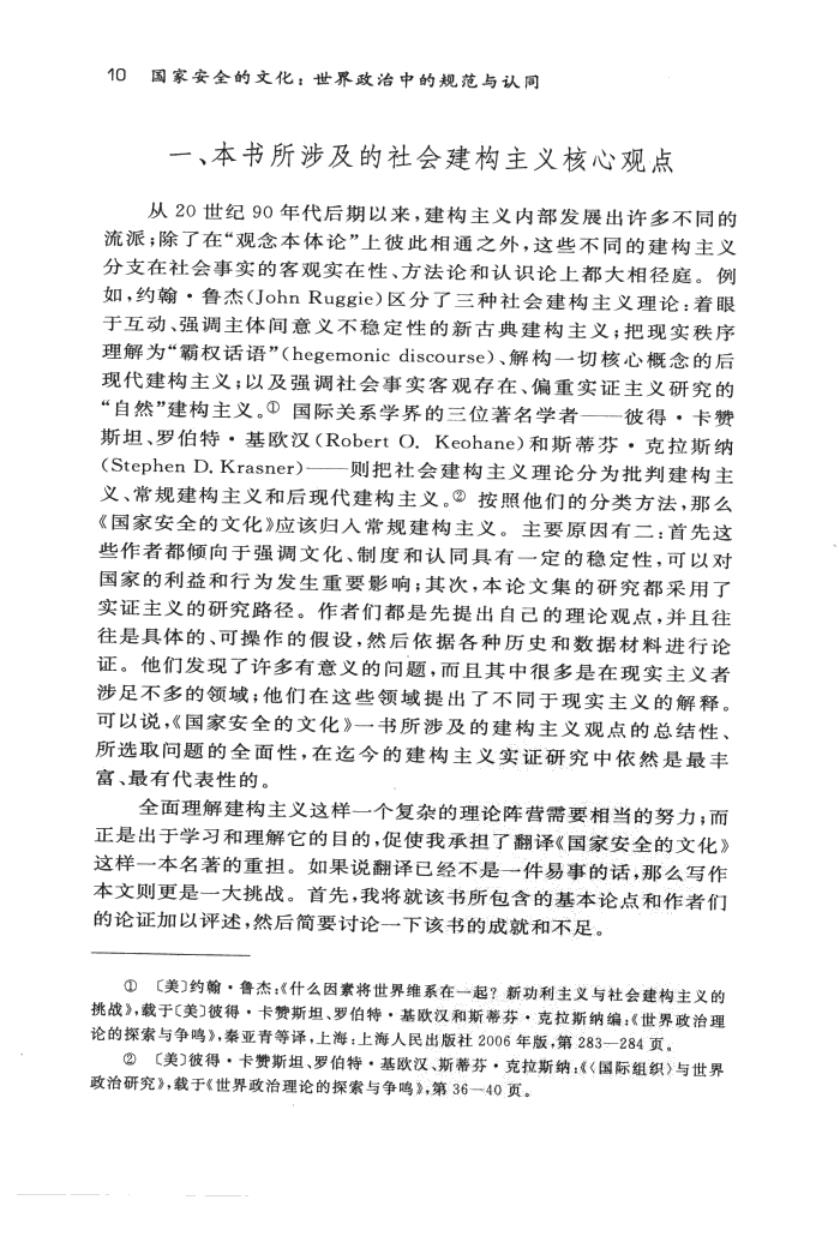
10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 一、本书所涉及的社会建构主义核心观点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建构主义内部发展出许多不同的 流派;除了在“观念本体论”上彼此相通之外,这些不同的建构主义 分支在社会事实的客观实在性、方法论和认识论上都大相径庭。例 如,约翰·鲁杰(John Ruggie)区分了三种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着眼 于互动、强调主体间意义不稳定性的新古典建构主义,把现实秩序 理解为“霸权话语”(hegemonic discourse)、解构一切核心概念的后 现代建构主义;以及强调社会事实客观存在、偏重实证主义研究的 “自然”建构主义。①国际关系学界的三位著名学者一彼得·卡赞 斯坦、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斯蒂芬·克拉斯纳 (Stephen D.Krasner)一则把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分为批判建构主 义、常规建构主义和后现代建构主义。②按照他们的分类方法,那么 《国家安全的文化》应该归入常规建构主义。主要原因有二:首先这 些作者都倾向于强调文化、制度和认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可以对 国家的利益和行为发生重要影响:其次,本论文集的研究都采用了 实证主义的研究路径。作者们都是先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并且往 往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假设,然后依据各种历史和数据材料进行论 证。他们发现了许多有意义的问题,而且其中很多是在现实主义者 涉足不多的领域;他们在这些领域提出了不同于现实主义的解释。 可以说,《国家安全的文化》一书所涉及的建构主义观点的总结性、 所选取问题的全面性,在迄今的建构主义实证研究中依然是最丰 富、最有代表性的。 全面理解建构主义这样一个复杂的理论阵营需要相当的努力:而 正是出于学习和理解它的目的,促使我承担了翻译《国家安全的文化》 这样一本名著的重担。如果说翻译已经不是一件易事的话,那么写作 本文则更是一大挑战。首先,我将就该书所包含的基本论点和作者们 的论证加以评述,然后简要讨论一下该书的成就和不足。 ①〔美〕约翰·鲁杰:《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 挑战》,载于〔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恭欧汉和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 论的探素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一284页, ②〔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国际组织)与世界 政治研究》,载于《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紫与争鸣》,第36一4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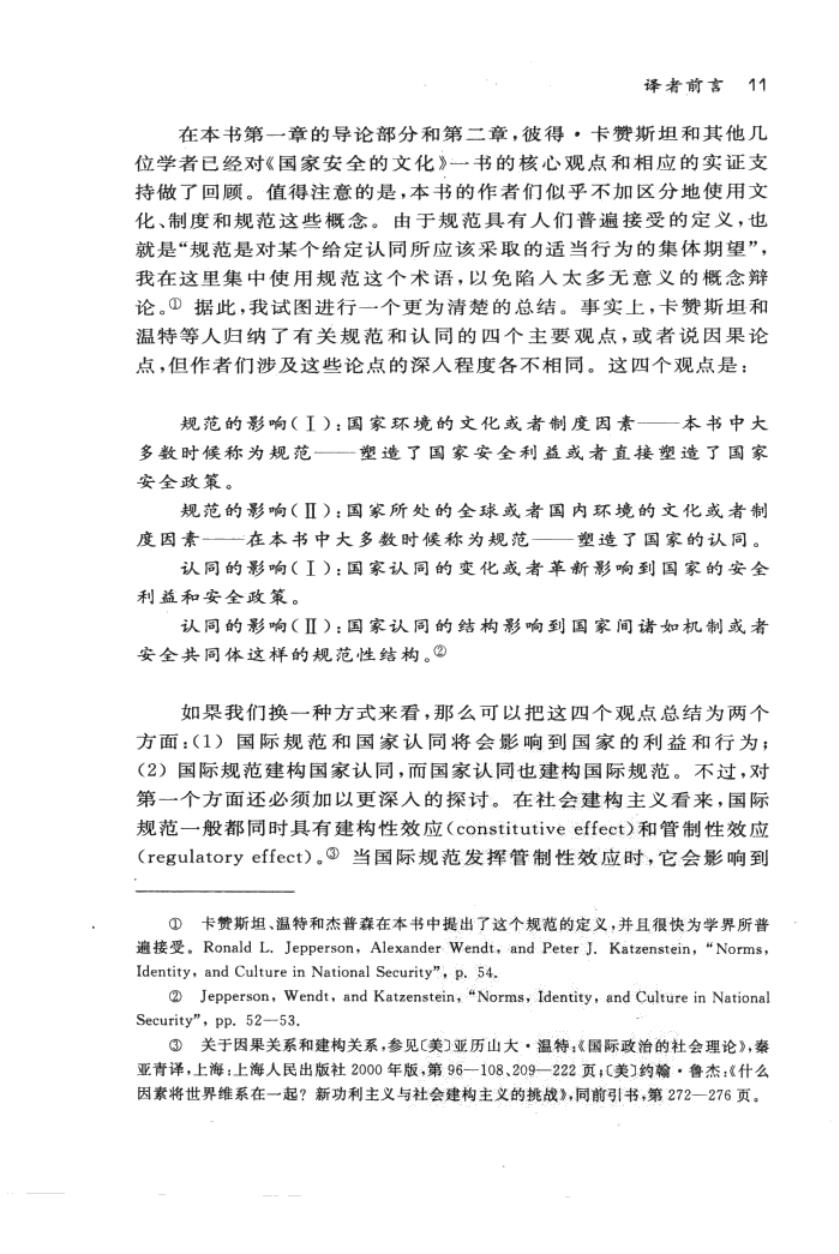
译者前言11 在本书第一章的导论部分和第二章,彼得·卡赞斯坦和其他几 位学者已经对《国家安全的文化》一书的核心观点和相应的实证支 持做了回顾。值得注意的是,本书的作者们似乎不加区分地使用文 化、制度和规范这些概念。由于规范具有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也 就是“规范是对某个给定认同所应该采取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 我在这里集中使用规范这个术语,以免陷人太多无意义的概念辩 论。①据此,我试图进行一个更为清楚的总结。事实上,卡赞斯坦和 温特等人归纳了有关规范和认同的四个主要观点,或者说因果论 点,但作者们涉及这些论点的深入程度各不相同。这四个观点是: 规范的影响(I):国家环境的文化或者制度因素一本书中大 多数时候称为规范一塑造了国家安全利益或者直接塑造了国家 安全政策。 规范的影响(Ⅱ):国家所处的全球或者国内环境的文化或者制 度因素一在本书中大多数时候称为规范—塑造了国家的认同。 认同的影响(I):国家认同的变化或者革斯影响到国家的安全 利益和安全政策。 认同的影响(Ⅱ):国家认同的结构影响到国家间诸如机制或者 安全共同体这样的规范性结构。② 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来看,那么可以把这四个观点总结为两个 方面:(1)国际规范和国家认同将会影响到国家的利益和行为; (2)国际规范建构国家认同,而国家认同也建构国际规范。不过,对 第一个方面还必须加以更深入的探讨。在社会建构主义看来,国际 规范一般都同时具有建构性效应(constitutive effect)和管制性效应 (regulatory effect).③当国际规范发挥管制性效应时,它会影响到 ①卡赞斯坦、温特和杰普森在本书中提出了这个规范的定义,并且很快为学界所普 ǜ接受,Ronald L.Jepperson,Alexander Wendt,and Peter J.Katzenstein,“Norms, Identity,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p.54. 2Jepperson,Wendt,and Katzenstein,"Norms,Identity,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pp.52-53. )关于因果关系和建构关系,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 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6一108、209一222页,〔美〕约瀚·鲁杰:《什么 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同前引书,第272一27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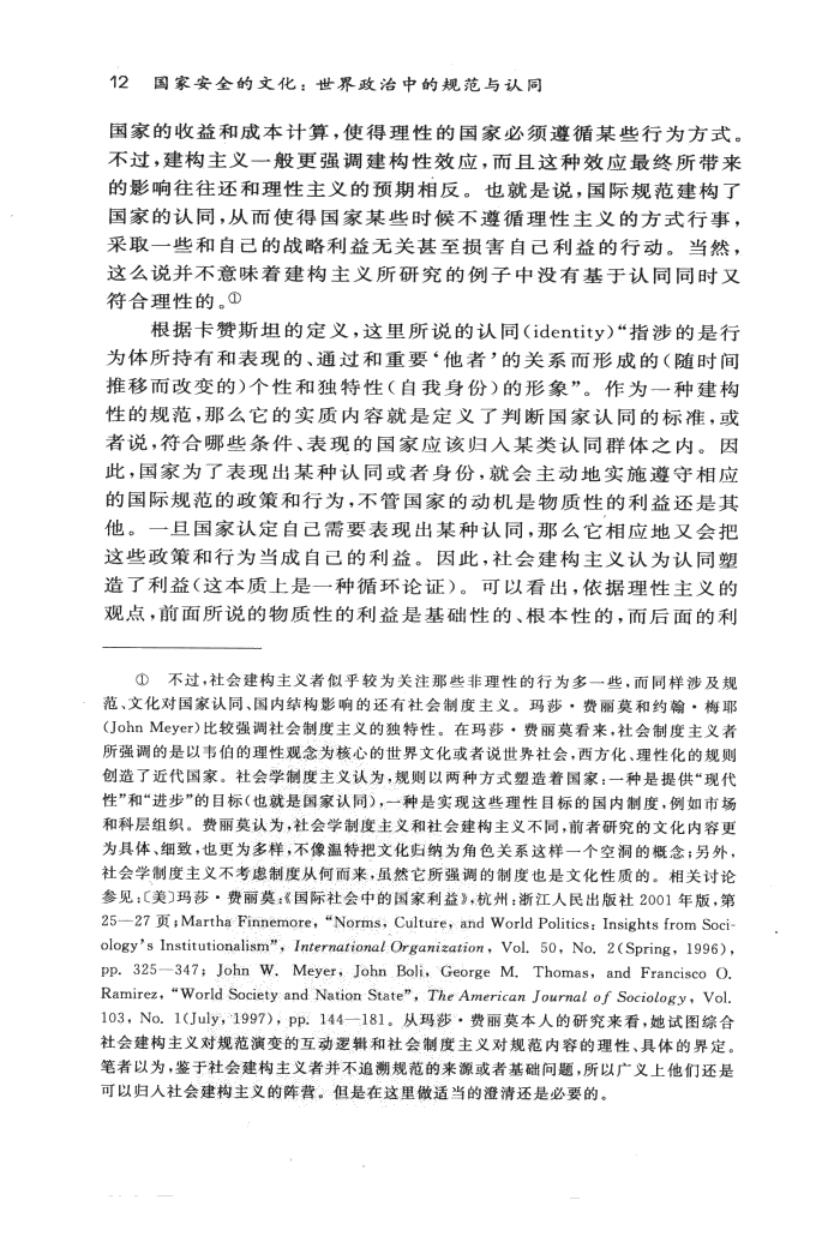
12 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 国家的收益和成本计算,使得理性的国家必须遵循某些行为方式。 不过,建构主义一般更强调建构性效应,而且这种效应最终所带来 的影响往往还和理性主义的预期相反。也就是说,国际规范建构了 国家的认同,从而使得国家某些时候不遵循理性主义的方式行事, 采取一些和自己的战略利益无关甚至损害自己利益的行动。当然,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建构主义所研究的例子中没有基于认同同时又 符合理性的。① 根据卡赞斯坦的定义,这里所说的认同(identity)“指涉的是行 为体所持有和表现的、通过和重要‘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随时间 推移而改变的)个性和独特性(自我身份)的形象”。作为一种建构 性的规范,那么它的实质内容就是定义了判断国家认同的标准,或 者说,符合哪些条件、表现的国家应该归人某类认同群体之内。因 此,国家为了表现出某种认同或者身份,就会主动地实施遵守相应 的国际规范的政策和行为,不管国家的动机是物质性的利益还是其 他。一旦国家认定自己需要表现出某种认同,那么它相应地又会把 这些政策和行为当成自己的利益。因此,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认同塑 造了利益(这本质上是一种循环论证)。可以看出,依据理性主义的 观点,前面所说的物质性的利益是基础性的、根本性的,而后面的利 ①不过,社会建构主义者似乎较为关注那些非理性的行为多一些,而同样涉及规 范、文化对国家认同、国内结构影响的还有社会制度主义。玛莎·费丽莫和约翰·梅耶 (John Meyer)比较强调社会制度主义的独特性。在玛莎·费丽莫看来,社会制度主义者 所强调的是以韦伯的理性观念为核心的世界文化或者说世界社会,西方化、理性化的规则 创造了近代国家。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规则以两种方式塑造着国家:一种是提供“现代 性”和“进步”的目标(也就是国家认同),一种是实现这些理性目标的国内制度,例如市场 和科层组织。费丽莫认为,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不同,前者研究的文化内容更 为具体、细致,也更为多样,不像温特把文化归纳为角色关系这样一个空洞的概念:另外, 社会学制度主义不考虑制度从何而来,虽然它所强调的制度也是文化性质的。相关讨论 参见:〔美)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25-27:Martha Finnemore,"Norms,Culture,and World Politics:Insights from Soci- ology's Institution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0,No.2(Spring,1996), pp.325-347;John W.Meyer,John Boli.George M.Thomas,and Francisco O. Ramirez,"World Society and Nation Stat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103,No.1(July,1997),pp.144一181。从玛莎·费丽莫本人的研究来看,她试图综合 社会建构主义对规范演变的互动逻辑和社会制度主义对规范内容的理性,具体的界定。 笔者以为,鉴于社会建构主义者并不追测规范的来源或者基础问题,所以广义上他们还是 可以归人社会建构主义的阵营。但是在这里做适当的澄清还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