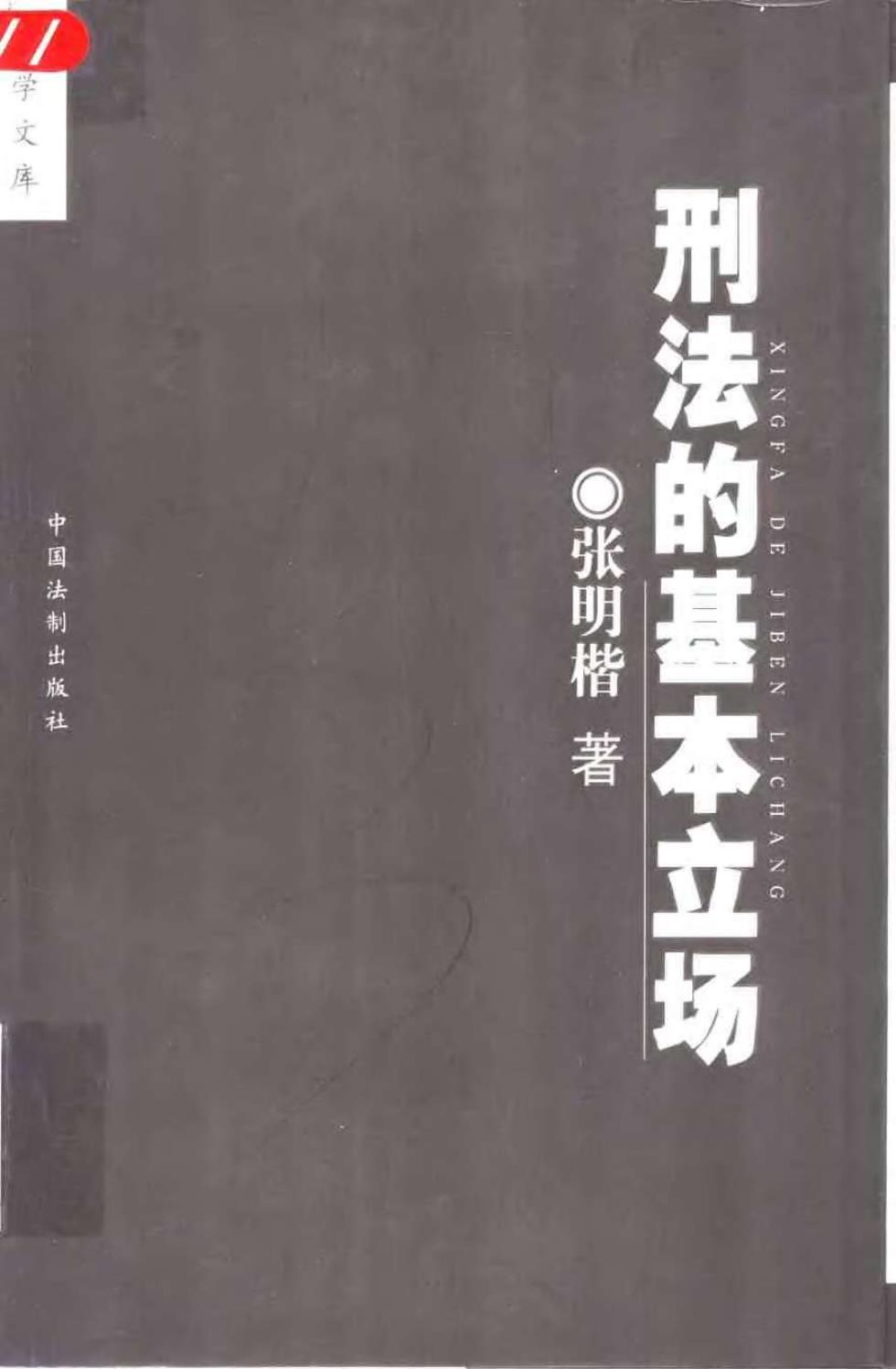
学文库 中国法制出版社 张明楷著 刑法的基本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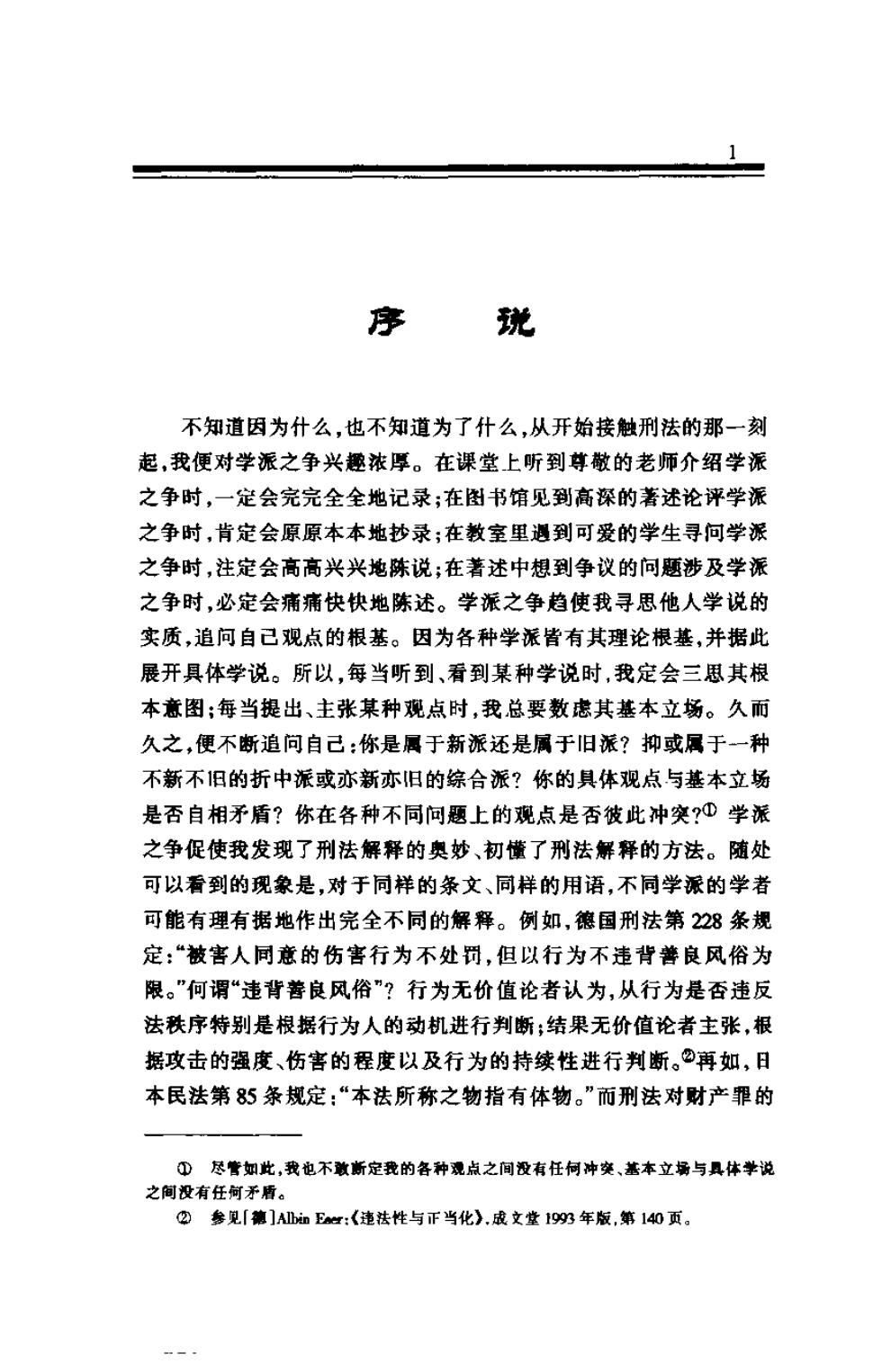
序 锐 不知道因为什么,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从开始接触刑法的那一刻 起,我便对学派之争兴趣浓厚。在课堂上听到尊敬的老师介绍学派 之争时,一定会完完全全地记录;在图书馆见到高深的著述论评学派 之争时,肯定会原原本本地抄录;在教室里遇到可爱的学生寻问学派 之争时,注定会高高兴兴地陈说:在著述中想到争议的问题涉及学派 之争时,必定会痛浦快快地陈述。学派之争趋使我寻思他人学说的 实质,追问自己观点的根基。因为各种学派皆有其理论根基,并据此 展开具体学说。所以,每当听到、看到某种学说时,我定会三思其根 本意图;每当提出、主张某种观点时,我总要数虑其基本立场。久而 久之,便不断追问自己:你是属于新派还是属于旧派?抑或属于一种 不新不旧的折中派或亦新亦旧的综合派?你的具体观点与基本立场 是否自相矛盾?你在各种不同问题上的观点是否彼此冲突?心学派 之争促使我发现了刑法解释的奥妙、初懂了刑法解释的方法。随处 可以看到的现象是,对于同样的条文、同样的用语,不同学派的学者 可能有理有据地作出完全不同的解释。例如,银国刑法第228条规 定:“被害人同意的伤害行为不处罚,但以行为不违背善良风俗为 限。”何谓“违背善良风俗”?行为无价值论者认为,从行为是否违反 法秩序特别是根据行为人的动机进行判断;结果无价值论者主张,根 据攻击的强度、伤害的程度以及行为的持续性进行判断。②再如,日 本民法第85条规定:“本法所称之物指有体物。”而刑法对财产罪的 ①尽管如此,我也不敢断定我的各种观点之间没有任何冲突、基本立场与具体学说 之间没有任阿矛盾。 ②参见「幕]AbEa:《违法性与正当化》.成文堂993年版,第14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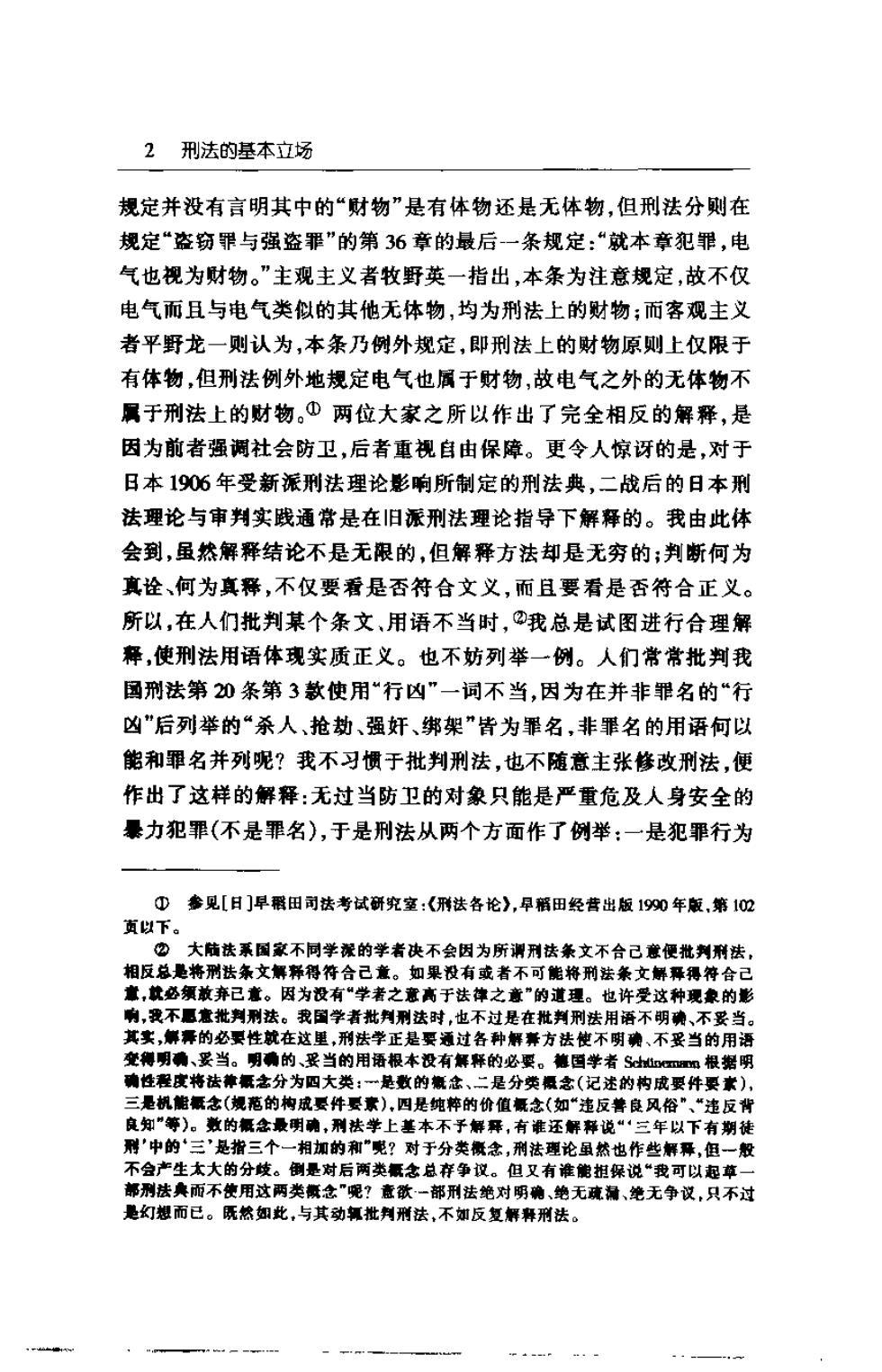
2刑法的基本立场 规定并没有言明其中的“财物”是有体物还是无体物,但刑法分则在 规定“盗窃罪与强盗罪”的第36章的最后一条规定:“就本章犯罪,电 气也视为财物。”主观主义者牧野英一指出,本条为注意规定,故不仅 电气而且与电气类似的其他无体物,均为刑法上的财物:而客观主义 者平野龙一则认为,本条乃例外规定,即刑法上的财物原则上仅限于 有体物,但刑法例外地规定电气也属于财物,故电气之外的无体物不 属于刑法上的财物。①两位大家之所以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是 因为前者强调社会防卫,后者重视自由保障。更令人惊讶的是,对于 日本1906年受新派刑法理论影响所制定的刑法典,二战后的日本刑 法理论与审判实践通常是在旧派刑法理论指导下解释的。我由此体 会到,虽然解释结论不是无限的,但解释方法却是无穷的;判断何为 真诠、何为真释,不仅要看是否符合文义,而且要看是否符合正义。 所以,在人们批判某个条文、用语不当时,②我总是试图进行合理解 释,使刑法用语体现实质正义。也不妨列举一例。人们常常批判我 国刑法第20条第3款使用“行凶”一词不当,因为在并非罪名的“行 凶”后列举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皆为罪名,非罪名的用语何以 能和罪名并列呢?我不习惯于批判刑法,也不随意主张修改刑法,便 作出了这样的解释:无过当防卫的对象只能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 暴力犯罪(不是罪名),于是刑法从两个方面作了例举:一是犯罪行为 ①参见[日]早稻田司法考试研究室:《形法各论》,早稻田经营出版1990年版,第102 页以下。 ②大陆法系国家不同学深的学者决不会因为所调刑法条文不合己意便批判刑法, 相反总是将刑齿条文解释得符合己意。如果没有或者不可能将刑法条文解释得符合己 靠,款必须敢弃已意。因为没有“学者之意高于法律之意”的道理。也许受这种现象的影 响,我不惠意批判刑法。我的学者批判刑法时,也不过是在批判刑法用语不明确、不妥当。 其实,解弄的必要性就在这里,刑法学正是要通过各种解膏方法使不明确、不妥当的用语 变得明确、妥当。明确的、妥当的用语根本没有解释的必要。德酉学者Schuinemamn根据明 确性程度将祛棒概念分为四大类:一是数的撕念、二是分类概念(记迷的构成要件要素)、 三是机能氯念(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因是纯粹的价值概念(如“违反善良风俗”、“违反背 良知”等)。数的幅念最明确,刑法学上基本不子解舞,有谁还解释说“‘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中的‘三'是指三个一相加的和”呢?对于分类衡念,刑法理论虽然也作些解得,但一般 不会产生太大的分歧。倒是对后两类氟念总存争议。但又有谁能担保说“我可以起草一 部刑法典而不使用这两类撕念”呢?意欲一部刑法绝对明确、绝无疏漏、绝无争议,只不过 是幻想而已。既然如此,与其动氧批判刑法,不如反复解春刑法

序说3 的方式:行凶:①二是犯罪行为的性质: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 通过行为方式与行为性质的例举,可以使司法机关更加明确“严重危 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范围。而且,“行凶”一词还可以涵盖那些 性质不明、界限不清,但又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这样解释 似乎不致于将刑法第20条第3款大骂一通、猛批一顿。我一直认 为,刑法典是正义的文字表述(其他成文法也是如此)。我不敢定义 正义是什么,但我知道什么是正义的:所以,我习惯于尽量以善意将 条文、用语(不管有无争议)朝着正义的方向解释(当然必须说明解释 过程,并且不得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不得损害国民的预测 可能性):②我不喜欢夸大实然(现行刑法条文)与应然之间的距离, 而是愿意使实然接近、贴近应然(当然不是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也 不是说不追求应然,而是通过解释实然来追求、实现应然),试图采用 各种适当方法将刑法解释为良法、正义之法。 显然,对刑法学派之争的兴趣并不能成为我主张中国应有刑法 学派之争的重要理由,更不能成为这一主张的惟一理由。 学派之争可以将理论研究引向深人。刑法理论对诸具体问题的 不同看法,源于对刑法性质、机能的不同认识。但是,如果一位研究 者没有学派意识,③便可能忽视自己的具体观点与基本立场的关 系,进而导致具体观点与基本立场相冲突;或者所提出的各种具体学 说表面上相一致,但各自的基本立场相冲突。学派的形成会追使研 究者思考自已采取了何种立场、属于哪种学派,从而保持理论的一致 性、协调性。学术需要批判。对一种观点的批判无疑是对该观点的 ①至于应否将“行凶”限定为使用凶器的暴力行为,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②后面将会看到,我认为新刑法向客魂主义领斜,采取了结果无价值论、并合主义。 读者很可能认为我的理由并不充分:事实上,我也有能力找出新刑法向主观主义领斜、采 取了行为无价值论、目的刑论的某些理由或根据。但是,由于我认为客观主义、结果无价 值,并合主义更为科学、合理,也符合中国的国情、人心,便得出了这种结论。可见,这里并 不只是各种主义、学说能否在刑法上找到充分根据的问题。 ③所谓学派煮识,不单是指学者们应当促进学派的形成,更重要的是指清楚地意 识到自已理论的核心;不要轻易动据自已的基本立场;对具体何糖的看法与处理应当与基 本立场相一致:面对他人的学说时应当审视其背后的根基:如此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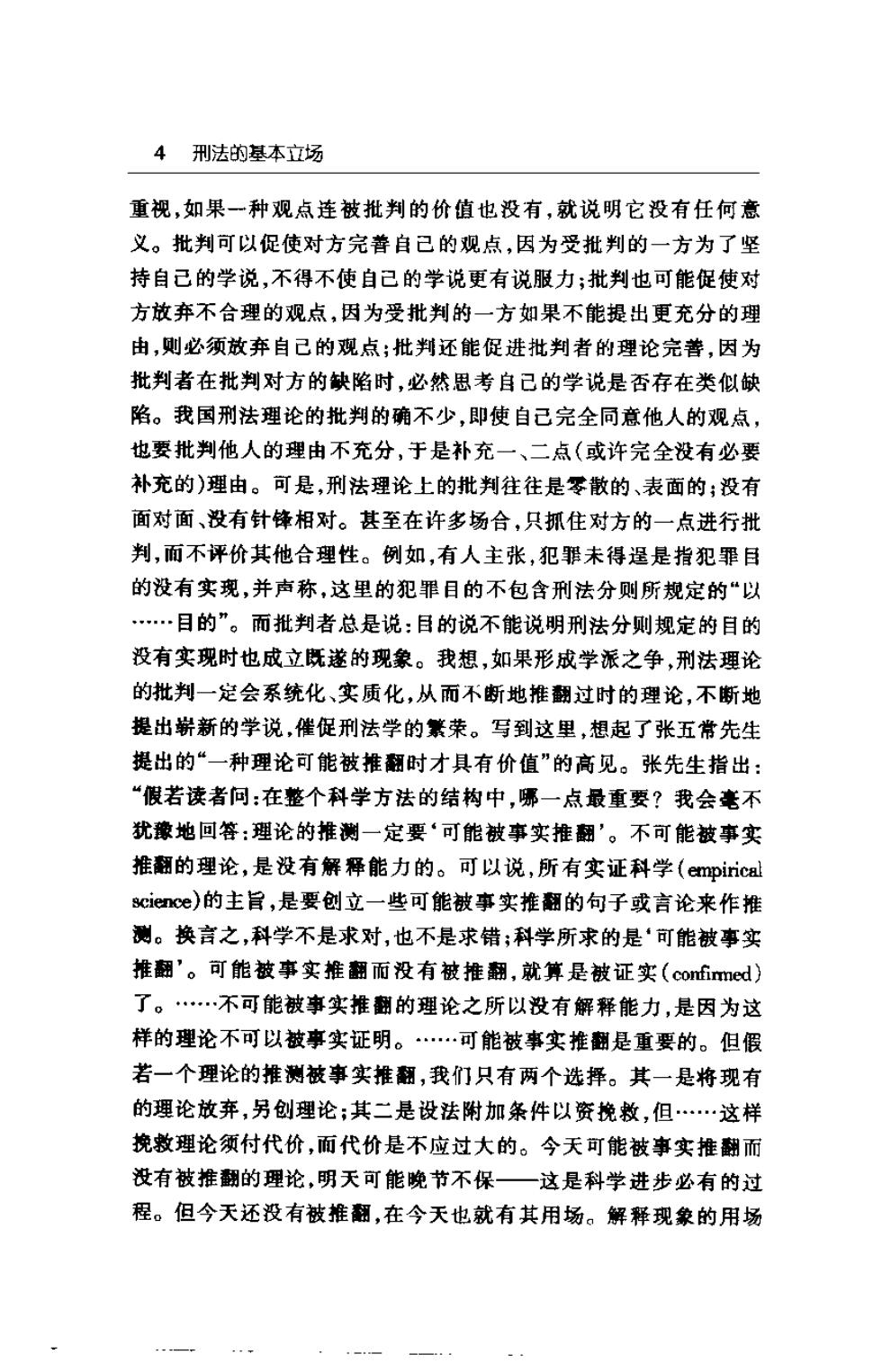
4刑法的基本立场 重视,如果一种观点连被批判的价值也没有,就说明它没有任何意 义。批判可以促使对方完善自己的观点,因为受批判的一方为了坚 持自己的学说,不得不使自己的学说更有说服力:批判也可能促使对 方放弃不合理的观点,因为受批判的一方如果不能提出更充分的理 由,则必须放弃自己的观点;批判还能促进批判者的理论完善,因为 批判者在批判对方的缺陷时,必然思考自己的学说是否存在类似缺 陷。我国刑法理论的批判的确不少,即使自己完全同意他人的观点, 也要批判他人的理由不充分,于是补充一、二点(或许完全没有必要 补充的)理由。可是,刑法理论上的批判往往是零散的、表面的;没有 面对面、没有针锋相对。甚至在许多场合,只抓住对方的一点进行批 判,而不评价其他合理性。例如,有人主张,犯罪未得逞是指犯罪目 的没有实现,并声称,这里的犯罪目的不包含刑法分则所规定的“以 .目的”。而批判者总是说:目的说不能说明刑法分则规定的目的 没有实现时也成立既遂的现象。我想,如果形成学派之争,刑法理论 的批判一定会系统化、实质化,从而不断地推翻过时的理论,不断地 提出崭新的学说,催促刑法学的繁荣。写到这里,想起了张五常先生 提出的“一种理论可能被推翻时才具有价值”的高见。张先生指出: “假若读者问:在整个科学方法的结构中,哪一点最重要?我会毫不 犹豫地回答:理论的推测一定要‘可能被事实推翻'。不可能被事实 推翻的理论,是没有解释能力的。可以说,所有实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的主旨,是要创立一些可能被事实推翻的句子或言论来作推 测。换言之,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 推翻'。可能被事实推翻而没有被推翻,就算是被证实(confimmed) 了。.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之所以没有解释能力,是因为这 样的理论不可以被事实证明。.可能被事实推翻是重要的。但假 若一个理论的推测被事实推翻,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其一是将现有 的理论放弃,另创理论;其二是设法附加条件以资挽救,但.这样 挽救理论须付代价,而代价是不应过大的。今天可能被事实推翻而 没有被推翻的理论,明天可能晚节不保一这是科学进步必有的过 程。但今天还没有被推翻,在今天也就有其用场。解释现象的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