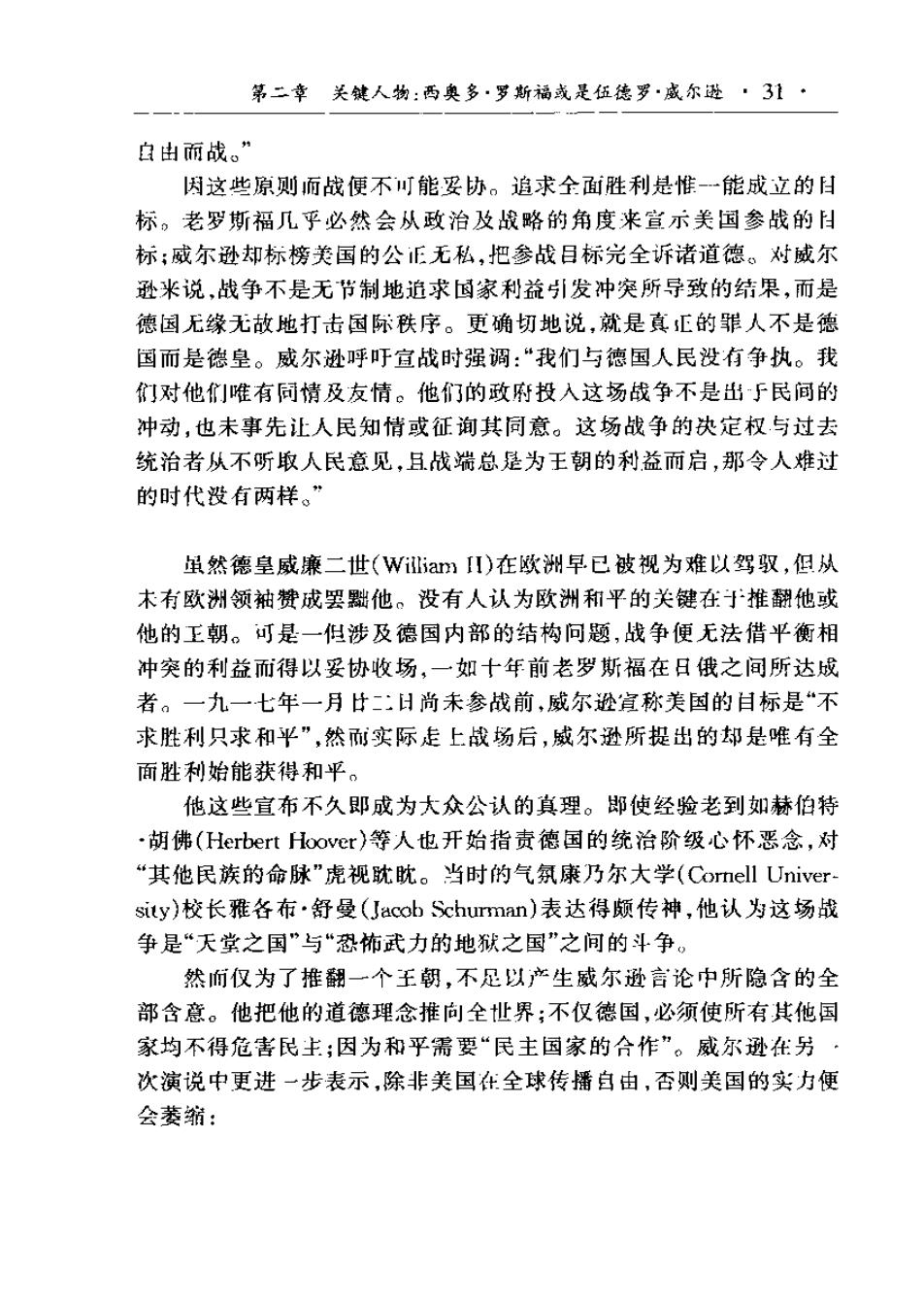
第二章关键人物:西奥多·罗斯福或是伍德罗·威尔逊·31 自由而战。” 因这些原则而战便不叮能妥协。追求全面胜利是惟-一能成立的目 标。老罗撕福几乎必然会从政治及战略的角度来宣示美国参战的」 标;威尔逊却标榜美国的公正无私,把参战目标完全诉诸道德。对威尔 逊来说,战争不是无节制地追求国家利益引发冲突所导致的结果,而是 德国无缘无故地打击国际秩序。更确切地说,就是真正的罪人不是德 国而是德皇。威尔逊呼吁宜战时强调:“我们与德国人民没有争执。我 们对他们唯有同情及友情。他们的政附投入这场战争不是出民间的 冲动,也未事先让人民知情或征询其同意。这场战争的决定权与过去 统治者从不所取人民意见,且战端总是为王朝的利益而启,那令人雉过 的时代没有两样。” 虽然德皇威廉二世(William I)在欧洲早已被视为难以驾驭,但从 未有欧洲领袖赞成罢黜他。没有人认为欧洲和平的关键在推翻他或 他的王朝。可是一但涉及德国内部的结构问题,战争便无法猎平衡相 冲突的利益耐得以妥协收场,一如十年前老罗斯福在日俄之间所达城 者。一九一七年一月廿二:日尚未参战前,威尔逊宣称国的甘标是“不 求胜利只求和平”,然实际走上战场后,威尔逊所提出的却是唯有全 面胜利始能获得和平。 他这些宣布不久即成为大众公认的真理。即使经验老到如赫伯特 ·胡佛(Herbert Hoover)等人也开始指责德国的统治阶级心怀恶念,对 “其他民族的命脉”虎视眈眈。当时的气氛康乃尔大学(Cornell Univer- sity)校长雅各布·舒曼(Jacob Schurman)表达得颇传神,他认为这场战 争是“天堂之国”与“恐怖武力的地狱之国”之间的斗争。 然而仅为了推翻一个王朝,不足以产生威尔逊言论中所隐含的全 部含意。他把他的道德理念推向全世界;不仅德国,必须使所有其他国 家均不得危害民主;因为和平需要“民主国家的合作”。威尔逊在另· 次演说中更进一步表示,除非美国在全球传播自由,否则美国的实力便 会萎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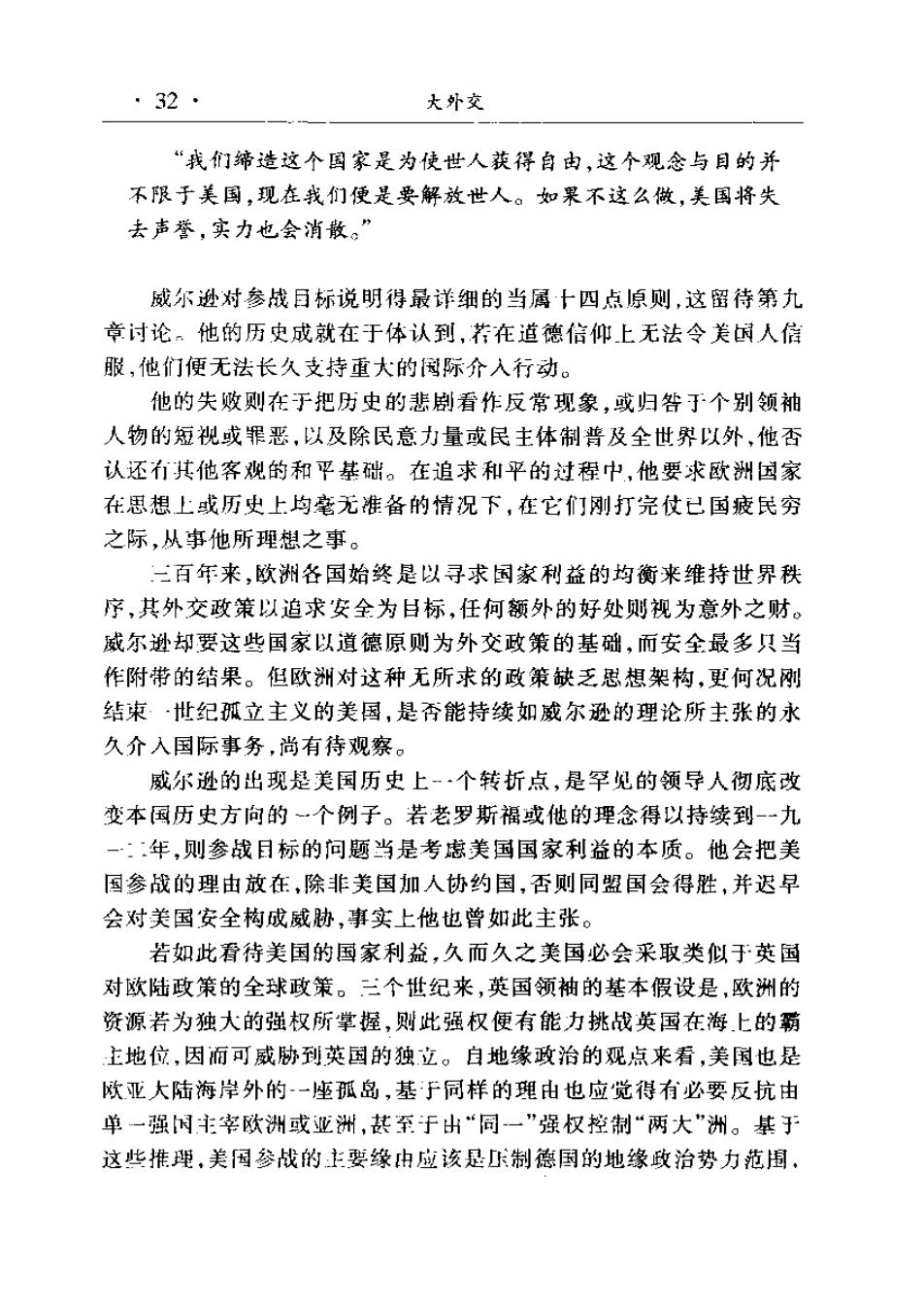
·32· 大外交 “我们缔造这个国家是为使世人获得自由,这个观念与目的并 不限于美国,现在我们便是要解放世人。如果不这么做,美国将失 去声誉,实力也会消散。” 威尔逊对参战目标说明得最详细的当属十四点原则,这留待第九 章讨论。他的历史成就在于体认到,若在道德信仰上无法令美闲人信 服,他们便无法长久支持重大的倒际介入行动。 他的失败则在于把历史的悲脚看作反常现象,或归咎于个别领袖 人物的短视或罪恶,以及除民意力量或民主体制普及全世界以外,他否 认还其他客观的和平基础。在追求和平的过程中,他要求欧洲国家 在思想上或历史上均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在它们刚打完仗已国疲民穷 之际,从事他所理想之事。 :二百年来,欧洲各国始终是以寻求国家利益的均衡来维持世界秩 序,其外交政策以追求安全为目标,任何额外的好处则视为意外之财。 威尔逊却要这些国家以道德原则为外交政策的基础,而安全最多只当 作附带的结果。但欧洲对这种无所求的政策缺乏思想架构,更何况刚 结束·世纪孤立主义的美国,是否能持续如威尔逊的理论所主张的永 久介人国际事务,尚有待观察。 威尔逊的出现是美国历史上·个转折点,是罕见的领导人彻底改 变本国历史方向的一个例子。若老罗斯福或他的理念得以持续到-一九 -:年,则参战目标的问题当是考虑美国国家利益的本质。他会把美 国参战的理由放在,除非美国加人协约国,否则同盟国会得胜,并迟早 会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事实上他也曾如此主张。 若如此看待美国的国家利益,久而久之美国必会采取类似于英国 对欧陆政策的全球政策。三个世纪来,英国领袖的基本假设是,欧洲的 资源若为独大的强权所掌握,则此强权便有能力挑战英国在海上的霸 主地位,因而可威胁到英国的独立。自地缘政治的观点来看,美国也是 炊亚大陆海岸外的一座孤岛,基于同样的理由也应觉得有必要反抗由 单一强闲主宰欧洲或亚洲,甚至于出“同一”强权控制“两大”洲。基于 这些推理,美国参战的上要缘由应该是制德国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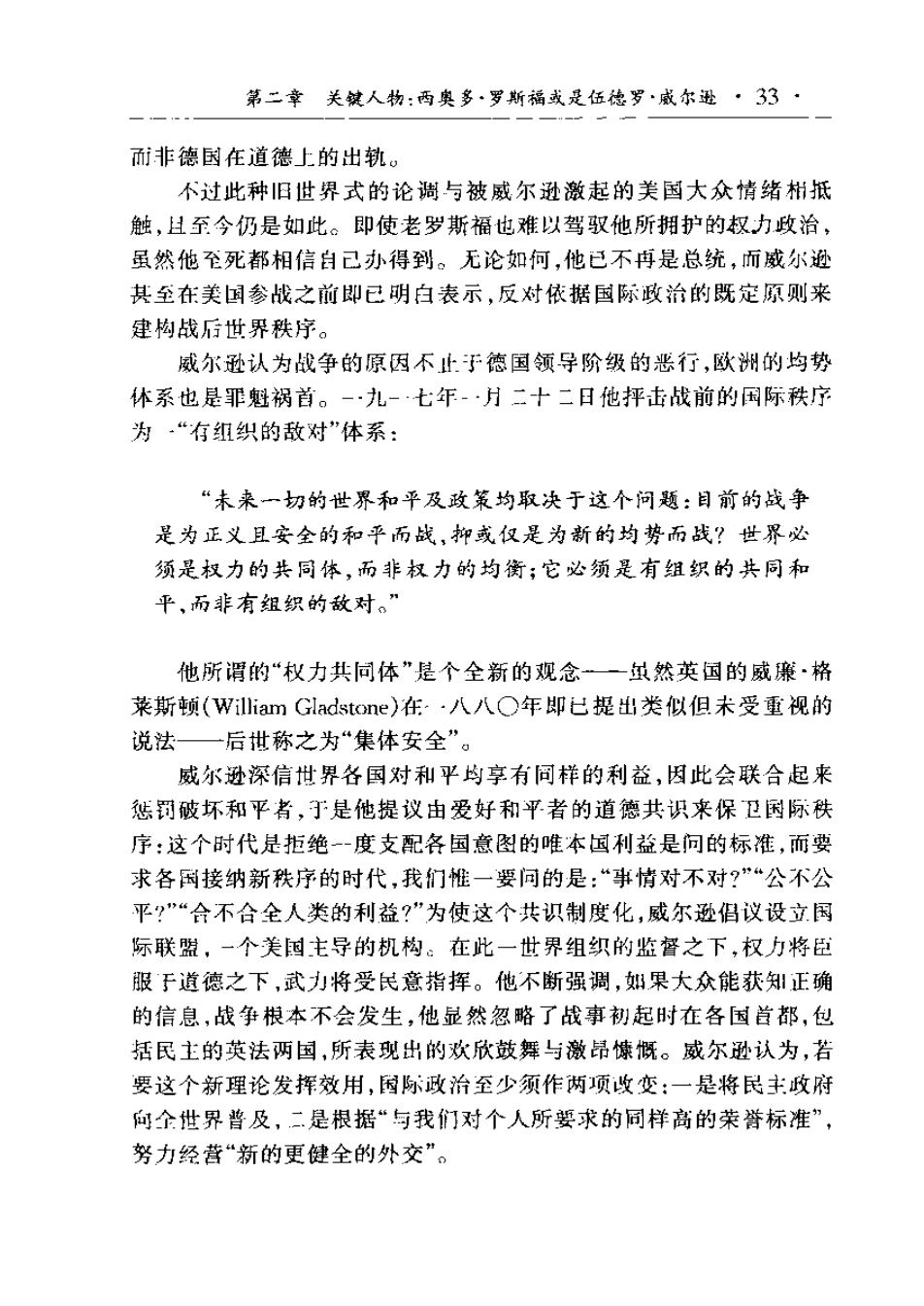
第二章关键人物:西奥多·罗斯福或是伍德罗·成尔逊·33· 非德国國在道德上的出轨。 不过此种旧世界式的论调与被威尔逊激起的美国大众情绪相抵 触,且至今仍是如此。即使老罗斯福也难以驾驭他所拥护的权力政治, 虽然他至死都相信自己办得到。无论如何,他已不再是总统,而威尔逊 其至在美国参战之前即已明白表示,反对依据国际政治的既定原则来 建构战后世界秩序。 威尔逊认为战争的原因不止子德国领导阶级的恶行,欧洲的均势 体系也是罪魁祸首。一·儿-·七年-·月二十二日他抨击战前的国际秩序 为“有组织的敌对”体系: “未来一切的世界和平及政策均取决于这个问题:目前的战争 是为正义且安全的和平而战,抑或仅是为新的均势而战?世界必 须是权力的共同体,而非权力的均衡;它必须是有组织的共同和 平,而非有组织的敌对。” 他所谓的“权力共同体”是个全新的规念一虫然英国的威廉·格 菜斯顿(William Gladstone)在,·八八○年即已提出类似但未受重视的 说法一后世称之为“集体安全”。 威尔逊深信世界各国对和平均享有同样的利益,因此会联合起来 惩罚破坏和平者,于是他提议由爱好和平者的道德共识来保卫国际秩 序:这个时代是拒绝一-度支配各国意图的唯本国利益是问的标准,而要 求各国接纳新秩序的时代,我们惟一要问的是:“事情对不对?”“公不公 平?”“合不合全人类的利益?”为使这个共识制度化,威尔逊倡议设立国 际联盟,一个美国主导的机构。在此一世界组织的监督之下,权力将臣 服于道德之下,武力将受民意指挥。他不断强调,如果大众能获知正确 的信息,战争根本不会发生,他显然忽略了战事初起时在各国首都,包 括民主的英法两国,所表现出的欢欣鼓舞与激昂慷慨。威尔逊认为,若 要这个新理论发挥效用,国你政治至少须作两项收变:一是将民主:政府 向金世界普及,二是根据“与我们对个人所要求的同样高的荣誉标准”, 努力经营“新的更键全的外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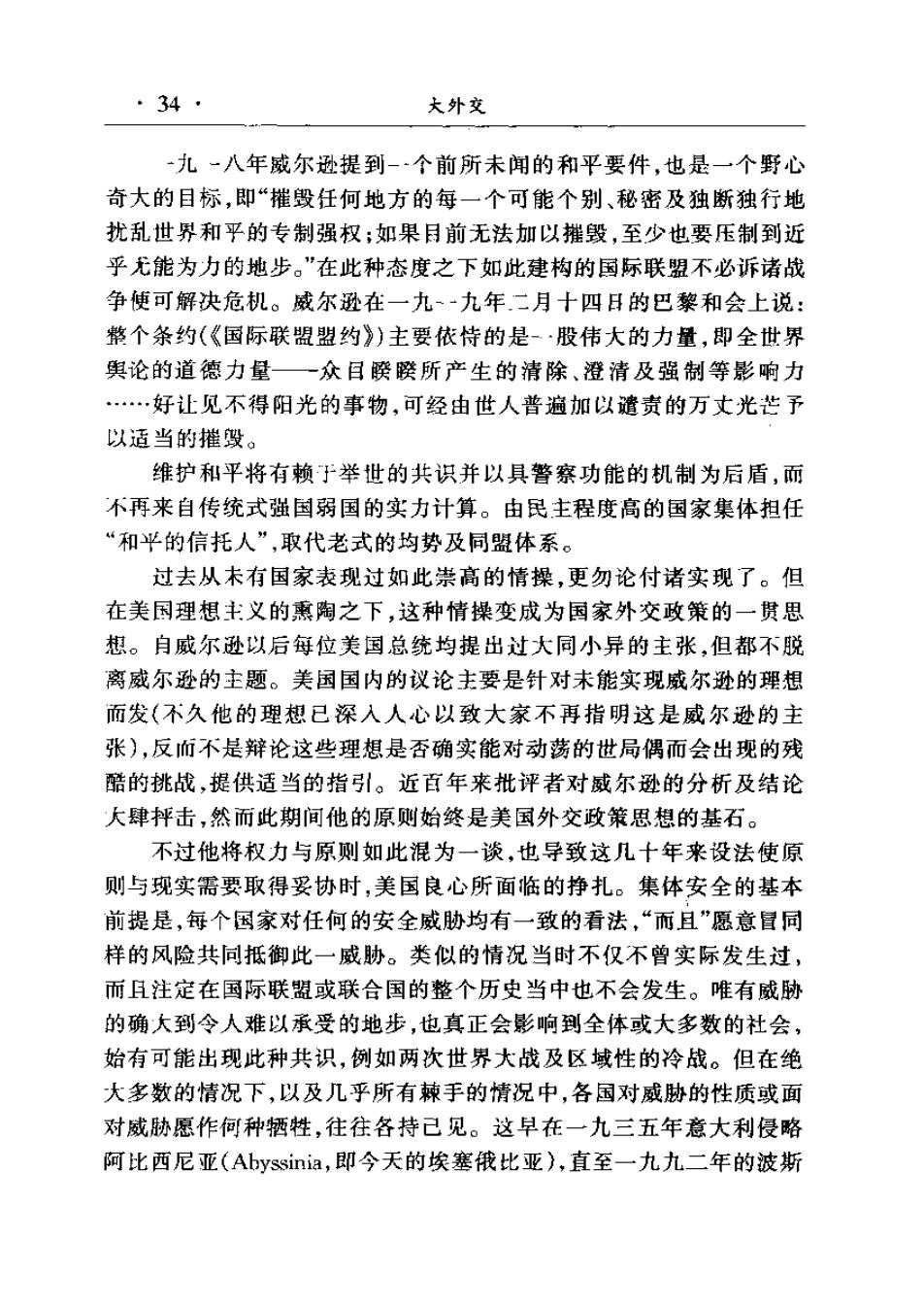
34· 大外交 一九~八年威尔逊提到-·个前所未闻的和平要件,也是一个野心 奇大的目标,即“摧毁任何地方的每一个可能个别、秘密及独断独行地 扰乱世界和平的专制强权:如果目前无法加以摧毁,至少也要压制到近 乎尤能为力的地步。”在此种态度之下如此建构的国际联盟不必诉诸战 争便可解决危机。威尔逊在一九~-九年.二月十四日的巴黎和会上说: 整个条约(《国际联盟盟约》)主要依恃的是-·股伟大的力量,即全世界 舆论的道德力量一众目睽睽所产生的清除、澄清及强制等影响力 …好让见不得阳光的事物,可经由世人普遍加以谴责的万丈光芒予 以适当的摧毁。 维护和平将有赖于举世的共识并以具警察功能的机制为后盾,而 不再来自传统式强国弱国的实力计算。由民主程度高的国家集体担任 “和平的信托人”,取代老式的均势及同盟体系。 过去从卡有国家表现过如此崇高的情操,更勿论付诸实现了。但 在美国理想主:义的熏陶之下,这种情操变成为国家外交政策的一贯思 想。自威尔逊以后每位美国总统均提出过大同小异的主张,但都不脱 离威尔逊的主题。美国国内的议论主要是针对未能实现威尔逊的理想 而发(不久他的理想已深入人心以致大家不再指明这是威尔逊的主 张),反而不是辩论这些理想是否确实能对动荡的世局偶而会出现的残 酷的挑战,提供适当的指引。近百年来批评者对威尔逊的分析及结论 人肆抨击,然而此期间他的原则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的基石。 不过他将权力与原则如此混为一谈,也导致这几十年来设法使原 则与现实需要取得妥协时,美国良心所面临的挣扎。集体安全的基本 前提是,每个国家对任何的安全威胁均有一致的看法,“而且”愿意冒同 样的风险共同抵御此一威胁。类似的情祝当时不仅不曾实际发生过, 而且注定在国际联盟或联合国的整个历史当中也不会发生。唯有威胁 的确大到令人雉以承受的地步,也真正会影响到全体或大多数的社会, 始有可能出现此种共识,例如两次世界大战及区域性的冷战。但在绝 大多数的情况下,以及几乎所有棘手的情况中,各国对威胁的性质或面 对威胁愿作何种牺牲,往往各持己见。这早在一九三五年意大利侵略 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即今天的埃塞俄比亚),直至一九九二年的波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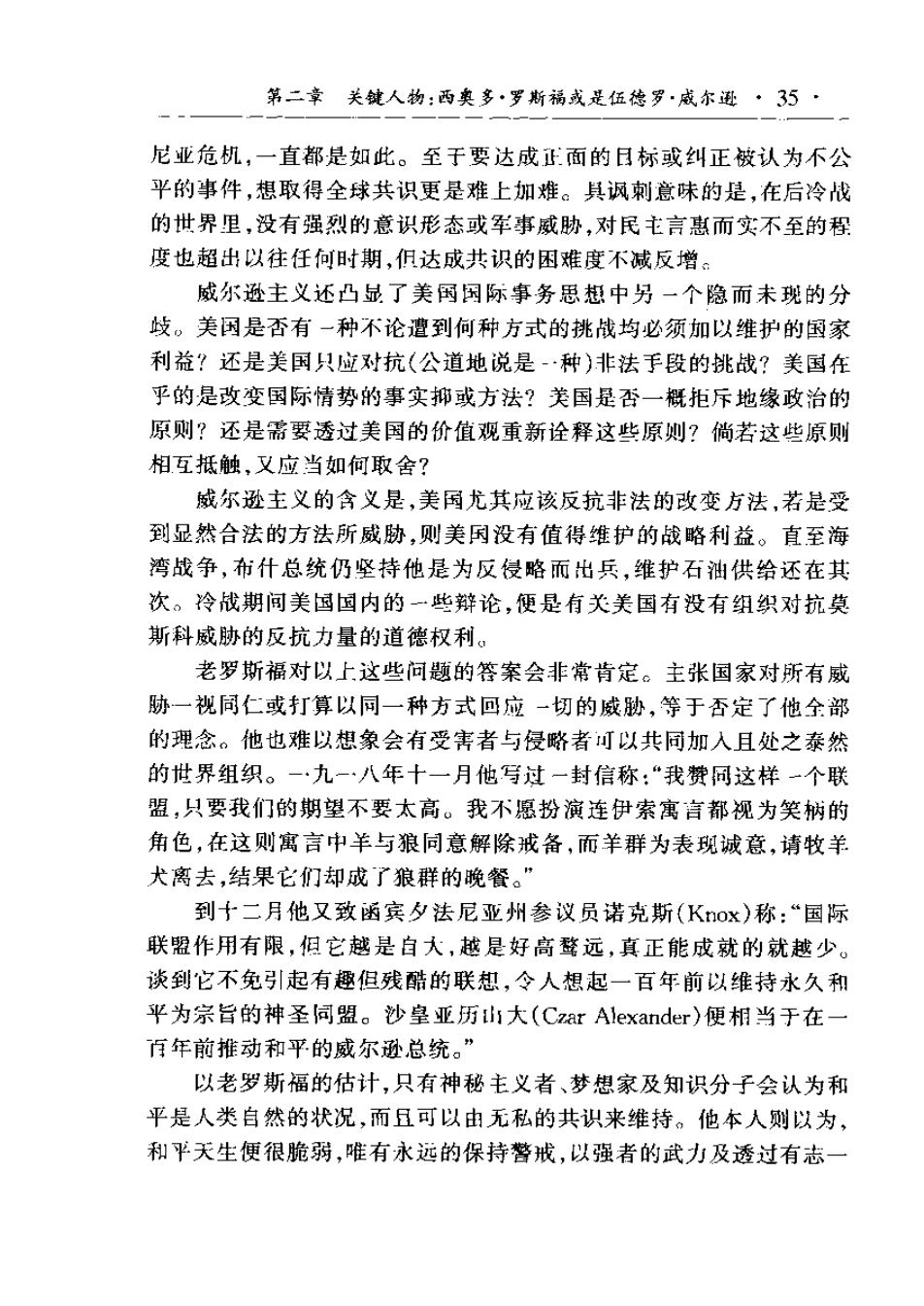
第二章关键人物:西奥多·罗斯福或是伍德罗·咸尔逊·35· 尼亚危机,一直都是如此。至于要达成正面的且标或纠正被认为不公 平的事件,想取得全球共识更是难上加难。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后冷战 的世界里,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或军事威胁,对民主言惠而实不至的程 度也超出以往任向时期,但达成共识的困难度不减反增。 威尔逊主义还凸显了美国国际事务思想中另一个隐而未现的分 歧。美国是否有一种不论遭到何种方式的挑战均必须加以维护的国家 利益?还是美国只应对抗(公道地说是·种)非法手段的挑战?美国在 乎的是改变国际情势的事实抑或方法?美国是否一概拒斥地缘政治的 原则?还是需要透过美国的价值观重新诠释这些原则?倘若这些原则 相互抵触,又应当如何取舍? 威尔逊主义的含义是,美国尤其应该反抗非法的改变方法,若是受 到显然合法的方法所威胁,则美国没有值得维护的战略利益。直至海 湾战争,布什总统仍坚持他是为反侵略而出兵,维护石油供给还在其 次。冷战期间美国国内的一些辩论,便是有关美国有没有组织对抗莫 斯科威胁的反抗力量的道德权利, 老罗斯福对以上这些问题的答案会非常肯定。主张国家对所有威 胁一视同仁或打算以同一种方式回应一切的威胁,等于否定了他全部 的理念。他也难以想象会有受害者与侵略者可以共同加入且处之泰然 的世界组织。一·九-·八年十一月他写过一封信称:“我赞同这样一个联 盟,只要我们的期望不要太高。我不愿扮演连伊索寓言都视为笑枘的 角色,在这则寓言中羊与狼同意解除戒备,而羊群为表现城意,请牧羊 犬离去,结果它们却成了狼群的晚餐。” 到十二月他又致函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诺克斯(Kox)称:“国际 联盟作用有限,但它越是自大,越是好高鹜远,真正能成就的就越少。 谈到它不免引起有趣但残酷的联想,令人想起一百年前以维持永久和 平为宗旨的神圣同盟。沙皇亚历大(Czar Alexander)便相当于在一 厅年前推动和平的威尔逊总统。” 以老罗斯福的估计,只有神秘主义者、梦想家及知识分子会认为和 平是人类自然的状况,而且可以由无私的共识来维持。他本人则以为, 和平天生便很脆弱,唯有永远的保持警戒,以强者的武力及透过有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