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学中的解释
地理学中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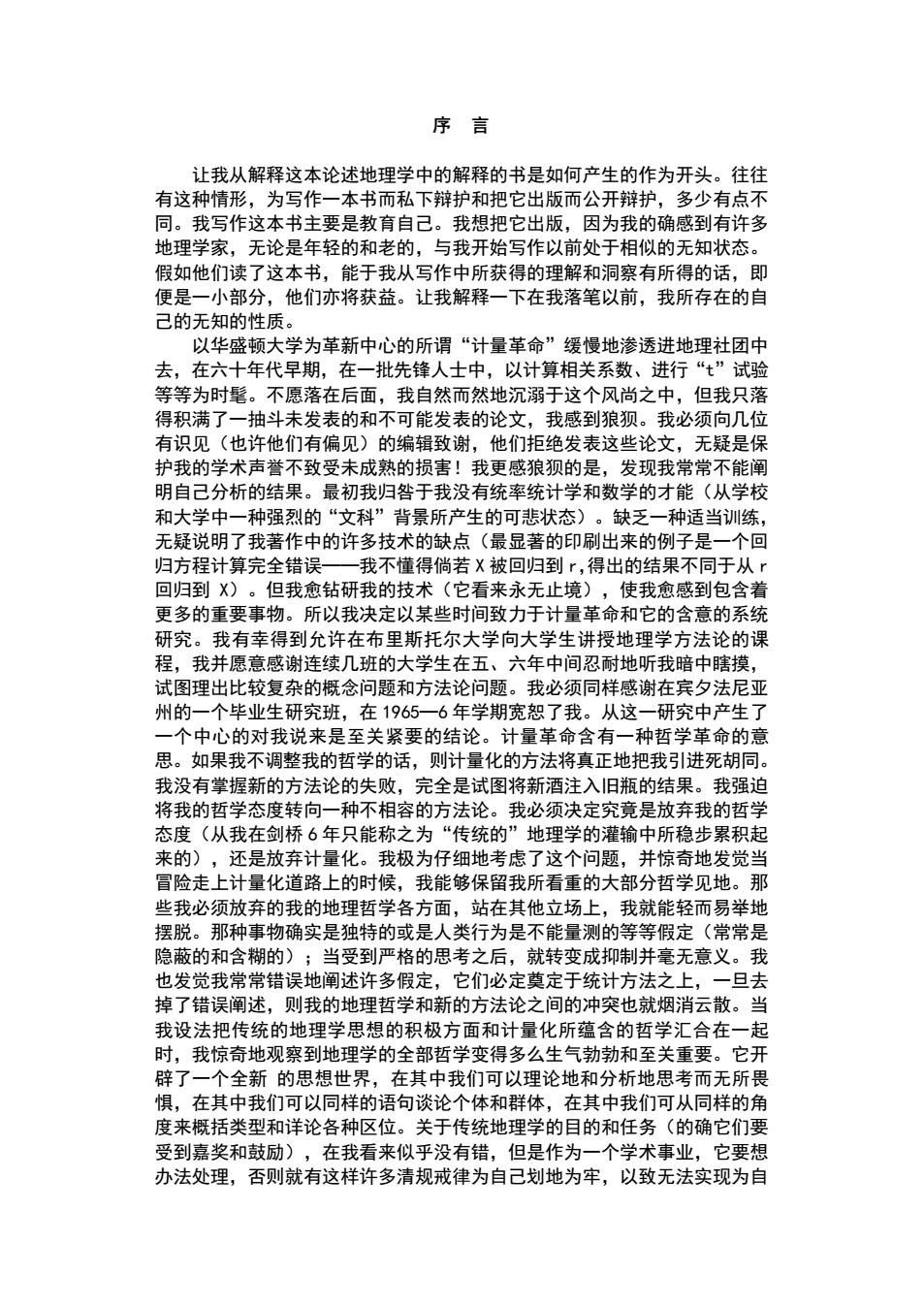
序言 让我从解释这本论述地理学中的解释的书是如何产生的作为开头。往往 有这种情形,为写作一本书而私下辩护和把它出版而公开辩护,多少有点不 同。我写作这本书主要是教育自己。我想把它出版,因为我的确感到有许多 地理学家,无论是年轻的和老的,与我开始写作以前处于相似的无知状态。 假如他们读了这本书, 能于我从写作中所获得的理解和洞察有所得的话 便是 小部分,他们亦将获益。让我解释一下在我落笔以前,我所存在的自 己的无知的性质 以华盛顿大学为革新中心的所谓“计量革命”缓慢地渗透进地理社团中 去,在六十年代早期.在一壮先锋人十中,以计算相关系数、讲行“t”试验 等等为时髦。 不愿落在后面 我自然而然地沉溺于这个风 尚之中 但我只落 得积满了 抽斗未发表的和不可能发表的论文,我感到狼狈。我必须向几位 有识见(也许他们有偏见)的编辑致谢,他们拒绝发表这些论文,无疑是保 护我的学术声誉不致受未成熟的损害!我更感狼狈的是,发现我常常不能阐 明自己分析的结果。最初我归咎于我没有统率统计学和数学的才能(从学校 种强烈的 背景所 的可悲状态 种适当训练 无疑说明了我著作中的许多技术的缺点(最显著的印刷出来的例子是 归方程计算完全错误 我不董得倘若X被回归到r,得出的结果不同于从 回归到X)。但我愈钻研我的技术(它看来永无止境),使我愈感到包含着 更多的重要事物。所以我决定以某些时间致力于计量革命和它的含意的系统 研究。 我有幸得 到允许在布里斯托分 大学向大学生讲授地理学方法论的 程,我并愿意感谢连续几班的大学生在五、 六年中间忍时地听我暗中瞎摸 试图理出比较复杂的概念问题和方法论问题。我必须同样感谢在宾夕法尼亚 州的一个毕业生研究班.在1965一6年学期宽恕了我。从这一研究中产生了 个中心的对我说来是至关竖要的结论 计量革命含有 种哲学革命的老 思。 如果我不调整我的哲学的话, 则计量化的方法将真正此 巴我引进死胡后 我没有掌握新的方法论的失败,完全是试图将新酒注入旧瓶的结果。 我强迫 将我的哲学态度转向一种不相容的方法论。我必须决定究竞是放弃我的哲学 态度(从我在制桥6年只能称之为“传统的”地理学的灌输中所稳步累积起 来的) 还是放弃计量化。我极为仔细地考虑了这个问题,并惊奇地发觉当 冒险走上计量化道路】 仁的时候 我能够 看重的大部分哲学见地 些我必须放弃的我的地理哲学各方面,站在其他立场上,我就能轻而易举地 摆脱。那种事物确实是独特的或是人类行为是不能量测的等等假定(常常是 隐蔽的和含湖的):当受到严格的思老之后,就转变成柳制并嘉无意义。我 也发觉我常常错误地阐述许多假定, 它们必定奠定于统计方法之上 日士 掉了错误阐述, 找的地埋哲字和 新的方法论之间的冲突也就烟消云散。 我设法把传统的地理学思想的积极方面和计量化所蕴含的哲学汇合在 时,我惊奇地观察到地理学的全部哲学变得多么生气勃勃和至关重要。它开 辟了一个全新的思想世界,在其中我们可以理论地和分析地思考而无所畏 惧,在其中我们可以同样的语句谈论个体和群体 在其中我们可从同样的角 度来概括类型和详论各种区位。关于传统地理学的目的和任务(的确它们要 受到嘉奖和鼓励),在我看来似乎没有错,但是作为 个学术事业,它要想 办法处理,否则就有这样许多清规戒律为自己划地为牢,以致无法实现为自
序 言 让我从解释这本论述地理学中的解释的书是如何产生的作为开头。往往 有这种情形,为写作一本书而私下辩护和把它出版而公开辩护,多少有点不 同。我写作这本书主要是教育自己。我想把它出版,因为我的确感到有许多 地理学家,无论是年轻的和老的,与我开始写作以前处于相似的无知状态。 假如他们读了这本书,能于我从写作中所获得的理解和洞察有所得的话,即 便是一小部分,他们亦将获益。让我解释一下在我落笔以前,我所存在的自 己的无知的性质。 以华盛顿大学为革新中心的所谓“计量革命”缓慢地渗透进地理社团中 去,在六十年代早期,在一批先锋人士中,以计算相关系数、进行“t”试验 等等为时髦。不愿落在后面,我自然而然地沉溺于这个风尚之中,但我只落 得积满了一抽斗未发表的和不可能发表的论文,我感到狼狈。我必须向几位 有识见(也许他们有偏见)的编辑致谢,他们拒绝发表这些论文,无疑是保 护我的学术声誉不致受未成熟的损害!我更感狼狈的是,发现我常常不能阐 明自己分析的结果。最初我归咎于我没有统率统计学和数学的才能(从学校 和大学中一种强烈的“文科”背景所产生的可悲状态)。缺乏一种适当训练, 无疑说明了我著作中的许多技术的缺点(最显著的印刷出来的例子是一个回 归方程计算完全错误——我不懂得倘若 X 被回归到 r,得出的结果不同于从 r 回归到 X)。但我愈钻研我的技术(它看来永无止境),使我愈感到包含着 更多的重要事物。所以我决定以某些时间致力于计量革命和它的含意的系统 研究。我有幸得到允许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向大学生讲授地理学方法论的课 程,我并愿意感谢连续几班的大学生在五、六年中间忍耐地听我暗中瞎摸, 试图理出比较复杂的概念问题和方法论问题。我必须同样感谢在宾夕法尼亚 州的一个毕业生研究班,在 1965—6 年学期宽恕了我。从这一研究中产生了 一个中心的对我说来是至关紧要的结论。计量革命含有一种哲学革命的意 思。如果我不调整我的哲学的话,则计量化的方法将真正地把我引进死胡同。 我没有掌握新的方法论的失败,完全是试图将新酒注入旧瓶的结果。我强迫 将我的哲学态度转向一种不相容的方法论。我必须决定究竟是放弃我的哲学 态度(从我在剑桥 6 年只能称之为“传统的”地理学的灌输中所稳步累积起 来的),还是放弃计量化。我极为仔细地考虑了这个问题,并惊奇地发觉当 冒险走上计量化道路上的时候,我能够保留我所看重的大部分哲学见地。那 些我必须放弃的我的地理哲学各方面,站在其他立场上,我就能轻而易举地 摆脱。那种事物确实是独特的或是人类行为是不能量测的等等假定(常常是 隐蔽的和含糊的);当受到严格的思考之后,就转变成抑制并毫无意义。我 也发觉我常常错误地阐述许多假定,它们必定奠定于统计方法之上,一旦去 掉了错误阐述,则我的地理哲学和新的方法论之间的冲突也就烟消云散。当 我设法把传统的地理学思想的积极方面和计量化所蕴含的哲学汇合在一起 时,我惊奇地观察到地理学的全部哲学变得多么生气勃勃和至关重要。它开 辟了一个全新 的思想世界,在其中我们可以理论地和分析地思考而无所畏 惧,在其中我们可以同样的语句谈论个体和群体,在其中我们可从同样的角 度来概括类型和详论各种区位。关于传统地理学的目的和任务(的确它们要 受到嘉奖和鼓励),在我看来似乎没有错,但是作为一个学术事业,它要想 办法处理,否则就有这样许多清规戒律为自己划地为牢,以致无法实现为自

己设置的目的和任务。特别是,就总的说来,地理学家们不善于利用科学方 法的神奇力量 这就是科学方法的哲学 它蕴含在计量化。 有些人对 “科学方法 这术语可能畏缩不前,所以我得声明, 我以一种 极为宽广的意义来阐明它,即为了合理的论证而树立并加以遵守的合宜的智 力标准。现在这点很明显,我们能遵守这些标准而无需耽溺于计量化之中。 高明的地理学家始终遵守着它们。但奇怪的是计量化向我指明了我自己的标 准是多么马 因此有那些不可能发表的论文。 我以为计量化最重要的效 果是强迫我们逻辑地和前后一贯地去思维,然而在以前,我们不是那样做的, 这个结论引导我去改变我的方法的重点。虽然这并不是偶然的,计量化正在 迫使我们去提高论证的标准,但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提高标准而无 需再提计量化。所以计量化的问题本身逐渐显现于背景之中。我对逻辑论证 和推论中的标准和规范的一 般性问题愈来愈感 这些 为地理学家有 研究过程中应当接受的。这些标准和科学作为整体不能相分离 总之 我对 地理学中的科学方法(不管怎么想法)的作用感到兴趣。现在有许多人在科 学的道路上已训练有素,以致看来在它的方法上无需再受正规的教导。向这 非人施教似平是他们对正化是怎么, 。但有许多地 理学家需要1 E规施教, 因为他们像我 样没有上升到科学的道路 即便是 已相当直觉地掌握科学方法的地理学家,也不能不注意它的形式分析 一 直觉的掌握来自知觉对象和实例的传授。这样 类掌握常足以驾驭例行工作 (大部分科学是例行的)。但它常常不能抓住新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没有 前例的。在这点上, 常常必需懂得科学方法作为整体的哲学支撑 科学方法提供我们锋利的工具。但任何工匠将会告诉你滥用锋利的工具 时,它能够造成很大的危害。最锋利的工具是数学和统计学所提供的。前者 向我们提供了用公式表示论点的严密而又简单的方法,而后者向我们提供了 数据分析和以有关数据来试验假说的工具」 我相信在地理学中 这些工具常 被滥用或误解。 我断然控诉有关这方面的罪过 如果我们在研究中控制地利 用这些锋利的工具,我们必须理解运用它们哲学的和方法论的假说 目然 通过科学方法的分析,这些假说明确地建立起来。但是我们必须保证所接受 的有关科学的特殊工具的假说,并不与为了合理论证和推论所树立的标准而 使用的更为宽广的假说发生冲突。所以在计量技术和平常的合理论证及推论 扫的占 方法就见得加倍重要 因此计 量化的重要就在于山 所以我们必须将假说顾及地理研究中的所有层 我从探讨理解科学的某些 有效工具的性质开始,而以理解时程的完整性结束,文些时程导致地理理解 的获得和总其成。 所以本书讲的是获得地理理解和知识的各种方法与合理论证及推论的种 种标 为了 证程导 直理的, 它们是必 可少的。 对于判断 证是否有力,使用的技术是否得当,或者解释是否合理的指标,我想作些系 统的讲述。我并不以为我详细讲述的这些指标是正确无误的。无知是相对的。 和我五年以前的情况相比,现在我感觉更为精通和聪明,但是对我仍须学习 相对说来,我感觉到比以前更为无知。的确, 白1968年6月结束这个手稿 我已改变了几处观点 并能识别在分析 中的错误和 足 所以这是 个人在特定时刻的观点。我不指望它成为某些新的正 统观念的基础,就一个人的意志说来,我肯定不会用这些名词来保卫它。我 的目的是开放竞技的场所,而不是关闭它,使之脱离将来的发展
己设置的目的和任务。特别是,就总的说来,地理学家们不善于利用科学方 法的神奇力量。这就是科学方法的哲学,它蕴含在计量化之中。 有些人对“科学方法”这术语可能畏缩不前,所以我得声明,我以一种 极为宽广的意义来阐明它,即为了合理的论证而树立并加以遵守的合宜的智 力标准。现在这点很明显,我们能遵守这些标准而无需耽溺于计量化之中。 高明的地理学家始终遵守着它们。但奇怪的是计量化向我指明了我自己的标 准是多么马虎——因此有那些不可能发表的论文。我以为计量化最重要的效 果是强迫我们逻辑地和前后一贯地去思维,然而在以前,我们不是那样做的。 这个结论引导我去改变我的方法的重点。虽然这并不是偶然的,计量化正在 迫使我们去提高论证的标准,但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提高标准而无 需再提计量化。所以计量化的问题本身逐渐显现于背景之中。我对逻辑论证 和推论中的标准和规范的一般性问题愈来愈感兴趣,这些问题为地理学家在 研究过程中应当接受的。这些标准和科学作为整体不能相分离。总之,我对 地理学中的科学方法(不管怎么想法)的作用感到兴趣。现在有许多人在科 学的道路上已训练有素,以致看来在它的方法上无需再受正规的教导。向这 辈人施教,似乎是他们对正规化是怎么一回事早已直觉地懂得。但有许多地 理学家需要正规施教,因为他们像我一样没有上升到科学的道路上。即便是 已相当直觉地掌握科学方法的地理学家,也不能不注意它的形式分析。一种 直觉的掌握来自知觉对象和实例的传授。这样一类掌握常足以驾驭例行工作 (大部分科学是例行的)。但它常常不能抓住新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没有 前例的。在这点上,常常必需懂得科学方法作为整体的哲学支撑。 科学方法提供我们锋利的工具。但任何工匠将会告诉你滥用锋利的工具 时,它能够造成很大的危害。最锋利的工具是数学和统计学所提供的。前者 向我们提供了用公式表示论点的严密而又简单的方法,而后者向我们提供了 数据分析和以有关数据来试验假说的工具。我相信在地理学中,这些工具常 被滥用或误解。我断然控诉有关这方面的罪过。如果我们在研究中控制地利 用这些锋利的工具,我们必须理解运用它们哲学的和方法论的假说。自然, 通过科学方法的分析,这些假说明确地建立起来。但是我们必须保证所接受 的有关科学的特殊工具的假说,并不与为了合理论证和推论所树立的标准而 使用的更为宽广的假说发生冲突。所以在计量技术和平常的合理论证及推论 碰在一起的点上,合适的方法就见得加倍重要。因此计量化的重要就在于此。 所以我们必须将假说顾及地理研究中的所有层次。我从探讨理解科学的某些 有效工具的性质开始,而以理解过程的完整性结束,这些过程导致地理理解 的获得和总其成。 所以本书讲的是获得地理理解和知识的各种方法与合理论证及推论的种 种标准,为了保证过程是合乎道理的,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判断一个论 证是否有力,使用的技术是否得当,或者解释是否合理的指标,我想作些系 统的讲述。我并不以为我详细讲述的这些指标是正确无误的。无知是相对的。 和我五年以前的情况相比,现在我感觉更为精通和聪明,但是对我仍须学习, 相对说来,我感觉到比以前更为无知。的确,自 1968 年 6 月结束这个手稿以 来,我已改变了几处观点,并能识别在分析中的错误和不足。所以这是一个 极为临时的报告———个人在特定时刻的观点。我不指望它成为某些新的正 统观念的基础,就一个人的意志说来,我肯定不会用这些名词来保卫它。我 的目的是开放竞技的场所,而不是关闭它,使之脱离将来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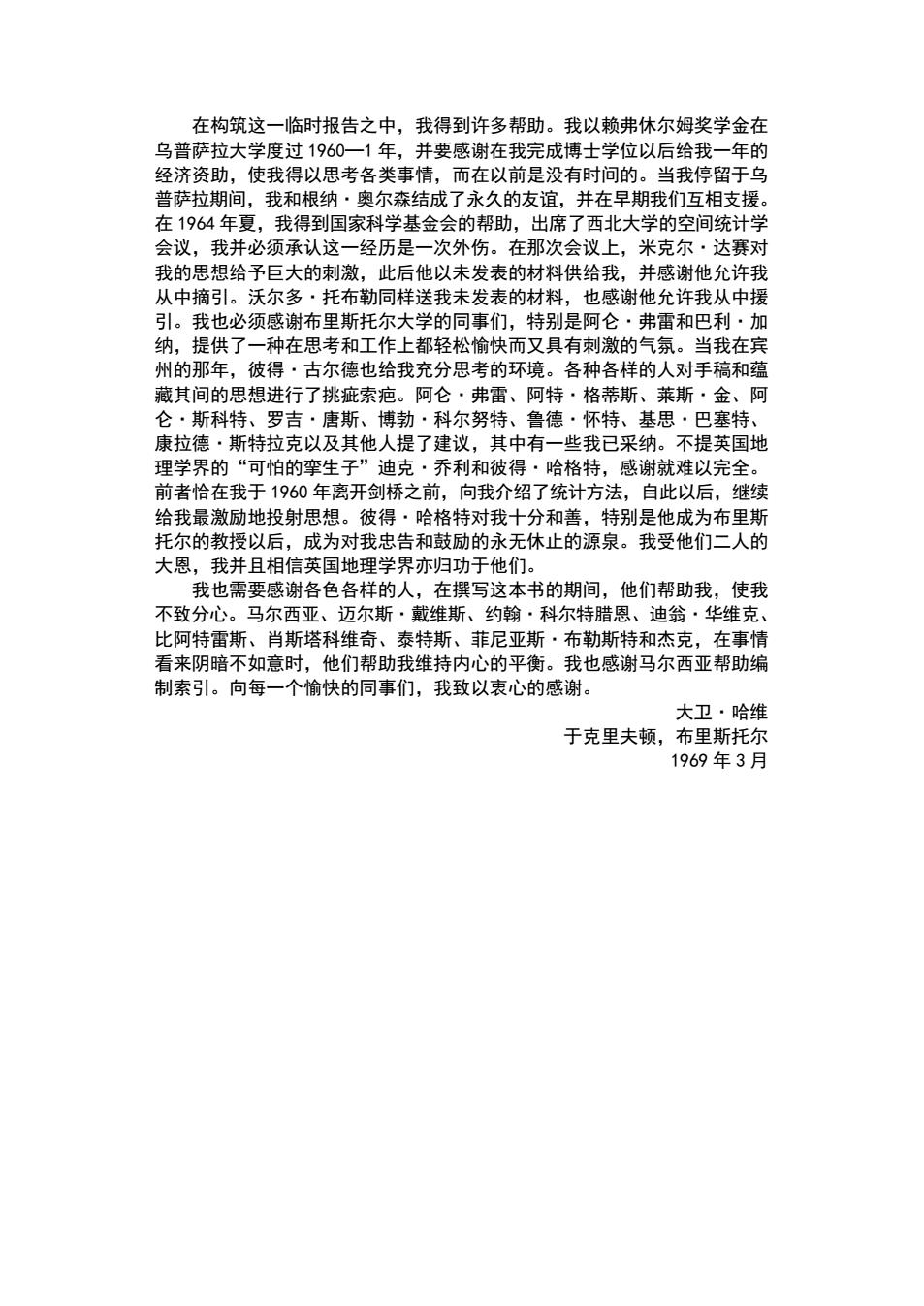
在构筑这一临时报告之中,我得到许多帮助。我以赖弗休尔姆奖学金在 乌普萨拉大学度过1960 并要感谢在我完成博士学位以后给我 的 经济资助,使我得以思考各类事情,而在以前是没有时间的。当我停留于鸟 普萨拉期间,我和根纳·奥尔森结成了永久的友谊,并在早期我们互相支援。 在1964年夏,我得到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帮助,出席了西北大学的空间统计学 会议,我并必须承认这一经历是一次外伤。在那次会议上,米克尔·达赛对 我的思想给予巨大的刺激 此后他以未发表的材料供给我。 并感谢他允许我 从中摘引。沃尔多·托布勒同样送我未发表的材料,也感谢他允许我从中援 引。我也必须感谢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同事们,特别是阿仑·弗雷和巴利·加 纳,提供了一种在思考和工作上都轻松愉快而又具有刺激的气氛。当我在宾 州的那年,彼得·古尔德也给我充分思考的环境。各种各样的人对手稿和蕴 藏其间的思想进行了挑疵索疤 阿仑 弗雷、阿特 ·格蒂斯 莱斯 阿 仑·斯科特、罗吉·唐斯、博勃·科尔努特、鲁德·怀特、基思·巴塞特 康拉德·斯特拉克以及其他人提了建议,其中有一些我已采纳。不提英国地 理学界的“可怕的挛生子”迪克·乔利和彼得·哈格特,感谢就难以完全。 前者恰在我于1960年离开剑桥之前,向我介绍了统计方法,自此以后,继续 给我最激励 投射思想。 彼得 哈格特对我十分和 特别是他 成头 布里斯 托尔的教授以后,成为对我忠告和鼓励的永无休止的源泉。我受他们二人的 大恩,我并且相信英国地理学界亦归功于他们。 我也需要感谢各色各样的人,在撰写这本书的期间,他们帮助我,使我 不致分心。马尔西亚、迈尔斯·戴维斯、约翰·科尔特腊恩、迪翁·华维克 比阿特雷斯、肖斯塔科维奇、泰特斯、 菲尼亚斯 布勒斯特和杰克,在事情 看来阴暗不如意时,他们帮助我维持内心的平衡。我也感谢马尔西亚帮助编 制索引。向每一个愉快的同事们,我致以衷心的感谢。 大卫·哈维 于克里夫顿,布里斯托尔 1969年3月
在构筑这一临时报告之中,我得到许多帮助。我以赖弗休尔姆奖学金在 乌普萨拉大学度过 1960—1 年,并要感谢在我完成博士学位以后给我一年的 经济资助,使我得以思考各类事情,而在以前是没有时间的。当我停留于乌 普萨拉期间,我和根纳·奥尔森结成了永久的友谊,并在早期我们互相支援。 在 1964 年夏,我得到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帮助,出席了西北大学的空间统计学 会议,我并必须承认这一经历是一次外伤。在那次会议上,米克尔·达赛对 我的思想给予巨大的刺激,此后他以未发表的材料供给我,并感谢他允许我 从中摘引。沃尔多·托布勒同样送我未发表的材料,也感谢他允许我从中援 引。我也必须感谢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同事们,特别是阿仑·弗雷和巴利·加 纳,提供了一种在思考和工作上都轻松愉快而又具有刺激的气氛。当我在宾 州的那年,彼得·古尔德也给我充分思考的环境。各种各样的人对手稿和蕴 藏其间的思想进行了挑疵索疤。阿仑·弗雷、阿特·格蒂斯、莱斯·金、阿 仑·斯科特、罗吉·唐斯、博勃·科尔努特、鲁德·怀特、基思·巴塞特、 康拉德·斯特拉克以及其他人提了建议,其中有一些我已采纳。不提英国地 理学界的“可怕的挛生子”迪克·乔利和彼得·哈格特,感谢就难以完全。 前者恰在我于 1960 年离开剑桥之前,向我介绍了统计方法,自此以后,继续 给我最激励地投射思想。彼得·哈格特对我十分和善,特别是他成为布里斯 托尔的教授以后,成为对我忠告和鼓励的永无休止的源泉。我受他们二人的 大恩,我并且相信英国地理学界亦归功于他们。 我也需要感谢各色各样的人,在撰写这本书的期间,他们帮助我,使我 不致分心。马尔西亚、迈尔斯·戴维斯、约翰·科尔特腊恩、迪翁·华维克、 比阿特雷斯、肖斯塔科维奇、泰特斯、菲尼亚斯·布勒斯特和杰克,在事情 看来阴暗不如意时,他们帮助我维持内心的平衡。我也感谢马尔西亚帮助编 制索引。向每一个愉快的同事们,我致以衷心的感谢。 大卫·哈维 于克里夫顿,布里斯托尔 1969 年 3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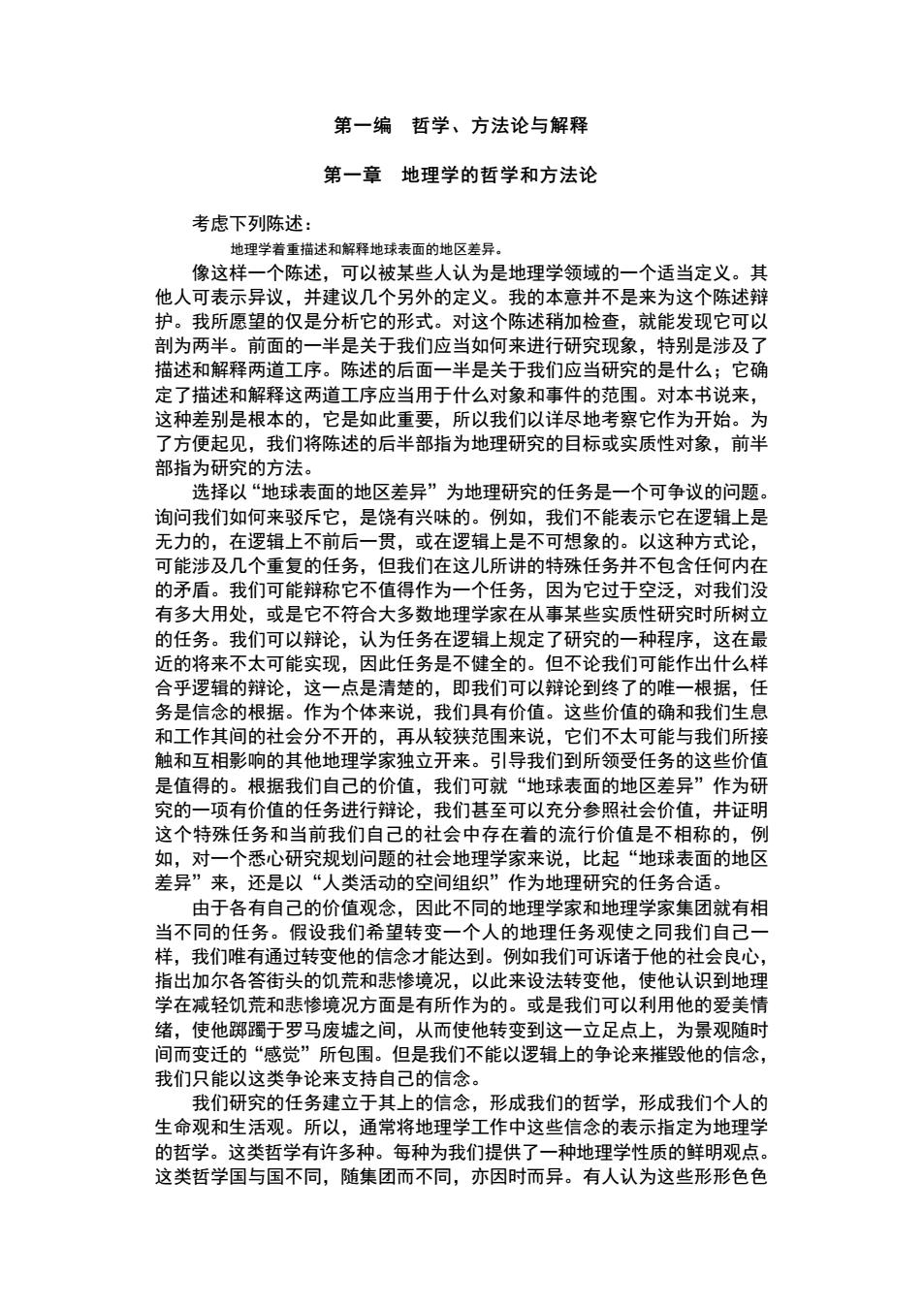
第一编哲学、方法论与解释 第一章地理学的哲学和方法论 考虑下列陈述: 地理学着重描述和解释地球表面的地区差异】 像这 个陈述, 可以被某些人认为是地理学领域 一个适当定义。其 他人可表示异议,并建议几个另外的定义。我的本意并不是来为这个陈述辩 护。我所愿望的仅是分析它的形式。对这个陈述稍加检查,就能发现它可以 剖为两半。前面的一半是关于我们应当如何来进行研究现象,特别是涉及了 描述和解释两道工序。陈述的后面一半是关于我们应当研究的是什么:它确 定了描述和解释这两道工序应当用于什么对象和事件的范围。 对本书说来, 这种差别是根本的,它是如此重要,所以我们以详尽地考察它作为开始。为 了方便起见,我们将陈述的后半部指为地理研究的目标或实质性对象,前半 部指为研究的方法。 洗择以“地球去面的地区芜导”为地理研密的年多是一个可角议的题 询问我们如何来驳斥它,是饶有兴味的。例如,我们不能表示它在逻辑上是 无力的,在逻辑上不前后一贯,或在逻辑上是不可想象的。以这种方式论, 可能涉及几个重复的任务,但我们在这儿所讲的特殊任务并不包含任何内在 的矛盾。我们可能辩称它不值得作为一个任务,因为它过于空泛,对我们没 有多大用外 式是不合大多勒地理受家在从些空质性开密所对 的任务。我们可以辩论,认为任务在逻辑上规定了研究的 种程序 这在最 近的将来不太可能实现,因此任务是不健全的。但不论我们可能作出什么样 合乎逻辑的辩论,这一点是清楚的,即我们可以辩论到终了的唯一根据,任 条是信念的根据。作为个体来说,我们具有价值。这些价值的确和我们生息 和工作其间的社会分 不开的 再从较狭范围来说 它们不太可能与我们所接 触和互相影响的其他地理学家独立开来。引导我们到所领受任务的这些价值 是值得的。根据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可就“地球表面的地区差异”作为研 究的一项有价值的任务进行辩论,我们甚至可以充分参照社会价值,井证明 这个特殊任务和当前我们自己的社会中存在着的流行价值是不相称的,例 时. 个悉心研究规划问题的社会地 比起“地球表面的地区 来,还是以 “人类活动的空间组织”作为地理研究的任务合适。 由于各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因此不同的地理学家和地理学家集团就有相 当不同的任务。假设我们希望转变一个人的地理任务观使之同我们自己 样,我们唯有通过转变他的信念才能达到。例如我们可诉诸于他的社会良心 指出加尔各 街头 的9 荒和悲 境况 以此来设 变他 使他认识到地理 学在减轻饥荒和悲惨境况方面是有所作为的。或是我们可以利用他的爱美情 绪,使他踯躅于罗马废墟之间,从而使他转变到这一立足点上,为景观随时 间而变迁的“感觉”所包围。但是我们不能以逻辑上的争论来摧毁他的信念, 我们只能以这类争论来支持自己的信念 我们研究的任务建立于其上的信 形成我们的哲学,形成我们个人的 生命观和生活观。所以,通常将地理学工作中这些信念的表示指定为地理学 的哲学。这类哲学有许多种。每种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地理学性质的鲜明观点。 这类哲学国与国不同,随集团而不同,亦因时而异。有人认为这些形形色色
第一编 哲学、方法论与解释 第一章 地理学的哲学和方法论 考虑下列陈述: 地理学着重描述和解释地球表面的地区差异。 像这样一个陈述,可以被某些人认为是地理学领域的一个适当定义。其 他人可表示异议,并建议几个另外的定义。我的本意并不是来为这个陈述辩 护。我所愿望的仅是分析它的形式。对这个陈述稍加检查,就能发现它可以 剖为两半。前面的一半是关于我们应当如何来进行研究现象,特别是涉及了 描述和解释两道工序。陈述的后面一半是关于我们应当研究的是什么;它确 定了描述和解释这两道工序应当用于什么对象和事件的范围。对本书说来, 这种差别是根本的,它是如此重要,所以我们以详尽地考察它作为开始。为 了方便起见,我们将陈述的后半部指为地理研究的目标或实质性对象,前半 部指为研究的方法。 选择以“地球表面的地区差异”为地理研究的任务是一个可争议的问题。 询问我们如何来驳斥它,是饶有兴味的。例如,我们不能表示它在逻辑上是 无力的,在逻辑上不前后一贯,或在逻辑上是不可想象的。以这种方式论, 可能涉及几个重复的任务,但我们在这儿所讲的特殊任务并不包含任何内在 的矛盾。我们可能辩称它不值得作为一个任务,因为它过于空泛,对我们没 有多大用处,或是它不符合大多数地理学家在从事某些实质性研究时所树立 的任务。我们可以辩论,认为任务在逻辑上规定了研究的一种程序,这在最 近的将来不太可能实现,因此任务是不健全的。但不论我们可能作出什么样 合乎逻辑的辩论,这一点是清楚的,即我们可以辩论到终了的唯一根据,任 务是信念的根据。作为个体来说,我们具有价值。这些价值的确和我们生息 和工作其间的社会分不开的,再从较狭范围来说,它们不太可能与我们所接 触和互相影响的其他地理学家独立开来。引导我们到所领受任务的这些价值 是值得的。根据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可就“地球表面的地区差异”作为研 究的一项有价值的任务进行辩论,我们甚至可以充分参照社会价值,井证明 这个特殊任务和当前我们自己的社会中存在着的流行价值是不相称的,例 如,对一个悉心研究规划问题的社会地理学家来说,比起“地球表面的地区 差异”来,还是以“人类活动的空间组织”作为地理研究的任务合适。 由于各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因此不同的地理学家和地理学家集团就有相 当不同的任务。假设我们希望转变一个人的地理任务观使之同我们自己一 样,我们唯有通过转变他的信念才能达到。例如我们可诉诸于他的社会良心, 指出加尔各答街头的饥荒和悲惨境况,以此来设法转变他,使他认识到地理 学在减轻饥荒和悲惨境况方面是有所作为的。或是我们可以利用他的爱美情 绪,使他踯躅于罗马废墟之间,从而使他转变到这一立足点上,为景观随时 间而变迁的“感觉”所包围。但是我们不能以逻辑上的争论来摧毁他的信念, 我们只能以这类争论来支持自己的信念。 我们研究的任务建立于其上的信念,形成我们的哲学,形成我们个人的 生命观和生活观。所以,通常将地理学工作中这些信念的表示指定为地理学 的哲学。这类哲学有许多种。每种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地理学性质的鲜明观点。 这类哲学国与国不同,随集团而不同,亦因时而异。有人认为这些形形色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