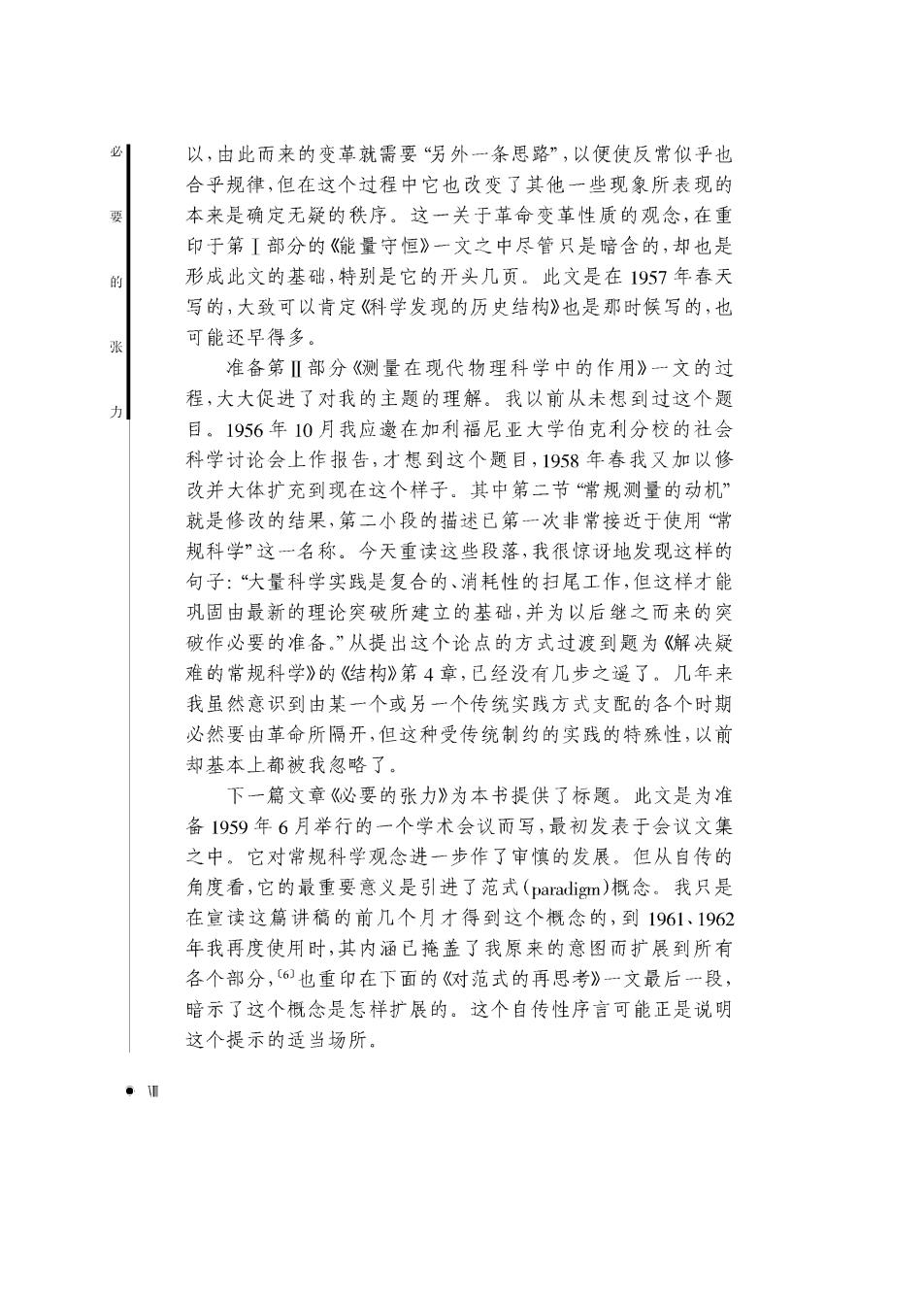
必 以,由此而来的变革就需要“另外一条思路”,以便使反常似乎也 合乎规律,但在这个过程中它也改变了其他一些现象所表现的 要 本来是确定无疑的秩序。这一关于革命变革性质的观念,在重 印于第I部分的《能量守恒》一文之中尽管只是暗含的,却也是 9 形成此文的基础,特别是它的开头几页。此文是在1957年春天 写的,大致可以肯定《科学发现的历史结构》也是那时候写的,也 张 可能还早得多。 准备第Ⅱ部分《测量在现代物理科学中的作用》一文的过 程,大大促进了对我的主题的理解。我以前从未想到过这个题 力 目。1956年10月我应邀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 科学讨论会上作报告,才想到这个题目,1958年春我又加以修 改并大体扩充到现在这个样子。其中第二节“常规测量的动机” 就是修改的结果,第二小段的描述已第一次非常接近于使用“常 规科学”这一名称。今天重读这些段落,我很惊讶地发现这样的 句子:“大量科学实践是复合的、消耗性的扫尾工作,但这样才能 巩固由最新的理论突破所建立的基础,并为以后继之而来的突 破作必要的准备.”从提出这个论点的方式过渡到题为《解决疑 难的常规科学》的《结构》第4章,已经没有几步之遥了。几年来 我虽然意识到由某一个或另一个传统实践方式支配的各个时期 必然要由革命所隔开,但这种受传统制约的实践的特殊性,以前 却基本上都被我忽略了。 下一篇文章《必要的张力》为本书提供了标题。此文是为准 备1959年6月举行的一个学术会议而写,最初发表于会议文集 之中。它对常规科学观念进一步作了审慎的发展。但从自传的 角度看,它的最重要意义是引进了范式(paradigm)概念。我只是 在宣读这篇讲稿的前几个月才得到这个概念的,到1961、1962 年我再度使用时,其内涵已掩盖了我原来的意图而扩展到所有 各个部分,〔6也重印在下面的《对范式的再思考》一文最后一段, 暗示了这个概念是怎样扩展的。这个自传性序言可能正是说明 这个提示的适当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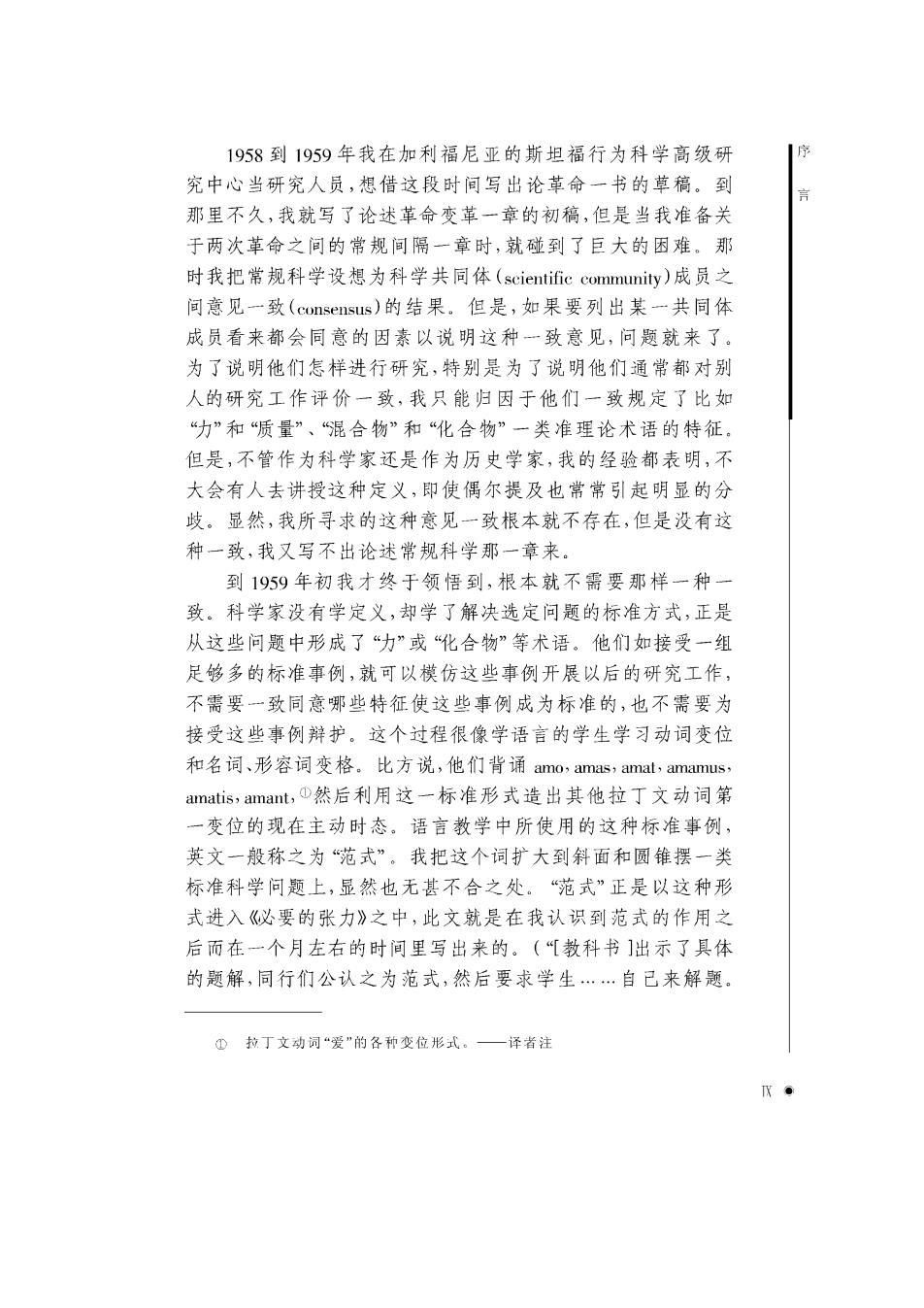
1958到1959年我在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级研 序 究中心当研究人员,想借这段时间写出论革命一书的草稿。到 言 那里不久,我就写了论述革命变革一章的初稿,但是当我准备关 于两次革命之间的常规间隔一章时,就碰到了巨大的困难。那 时我把常规科学设想为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成员之 间意见一致(consensus).的结果。但是,如果要列出某一共同体 成员看来都会同意的因素以说明这种一致意见,问题就来了。 为了说明他们怎样进行研究,特别是为了说明他们通常都对别 人的研究工作评价一致,我只能归因于他们一致规定了比如 “力”和“质量”、混合物”和“化合物”一类准理论术语的特征。 但是,不管作为科学家还是作为历史学家,我的经验都表明,不 大会有人去讲授这种定义,即使偶尔提及也常常引起明显的分 歧。显然,我所寻求的这种意见一致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没有这 种一致,我又写不出论述常规科学那一章来。 到1959年初我才终于领悟到,根本就不需要那样一种一 致。科学家没有学定义,却学了解决选定问题的标准方式,正是 从这些问题中形成了“力”或“化合物”等术语。他们如接受一组 足够多的标准事例,就可以模仿这些事例开展以后的研究工作, 不需要一致同意哪些特征使这些事例成为标准的,也不需要为 接受这些事例辩护。这个过程很像学语言的学生学习动词变位 和名词、形容词变格。比方说,他们背诵amo,amas,amat,amamus, amatis,amant,①然后利用这一标准形式造出其他拉丁文动词第 一变位的现在主动时态。语言教学中所使用的这种标准事例, 英文一般称之为“范式”。我把这个词扩大到斜面和圆锥摆一类 标准科学问题上,显然也无甚不合之处。“苑式”正是以这种形 式进入《必要的张力》之中,此文就是在我认识到范式的作用之 后而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写出来的。(“[教科书]出示了具体 的题解,同行们公认之为范式,然后要求学生…自已来解题。 ①拉丁文动词“爱”的各种变位形式。一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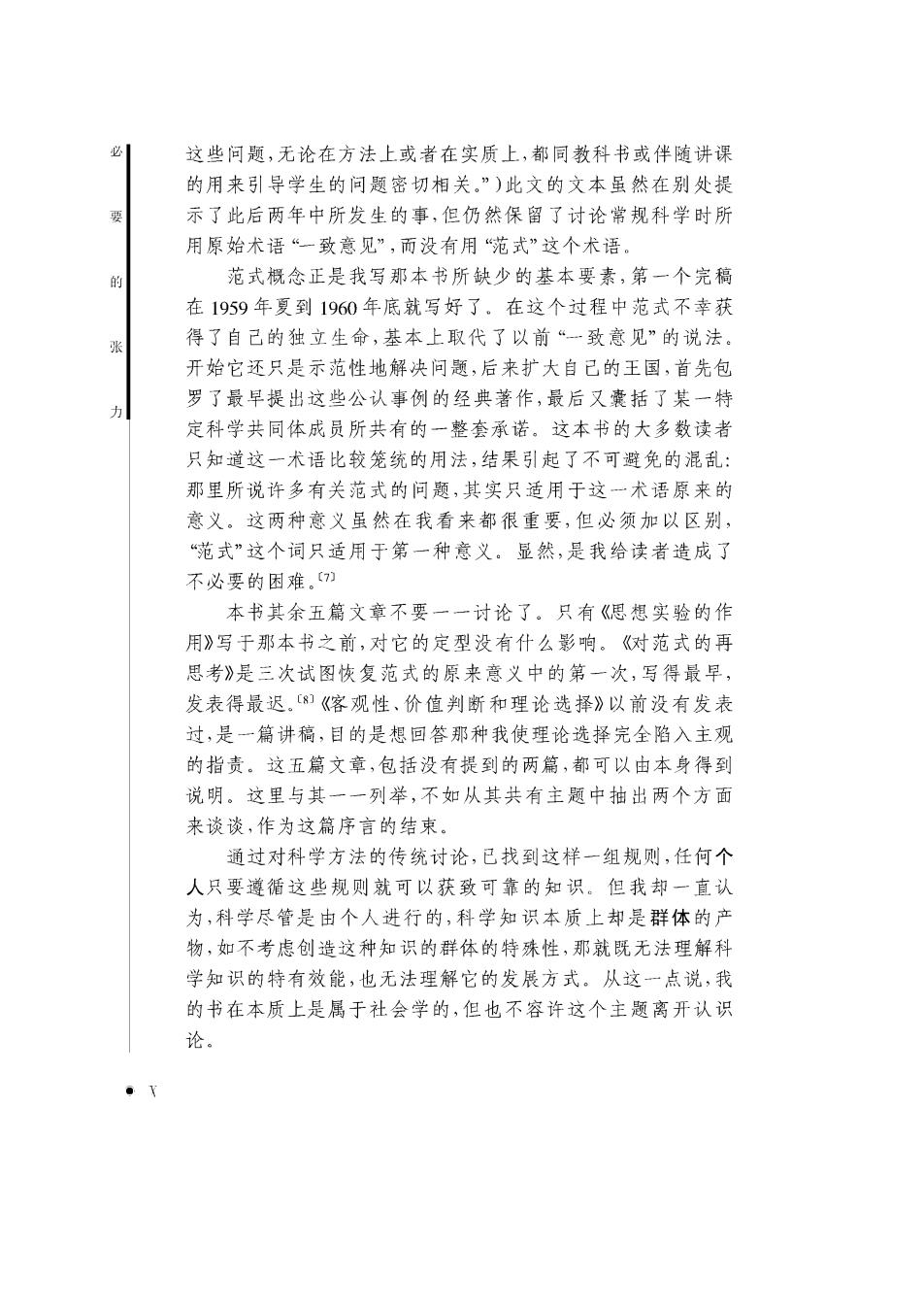
必 这些问题,无论在方法上或者在实质上,都同教科书或伴随讲课 的用来引导学生的问题密切相关。”)此文的文本虽然在别处提 要 示了此后两年中所发生的事,但仍然保留了讨论常规科学时所 用原始术语“一致意见”,而没有用“范式”这个术语。 9 范式概念正是我写那本书所缺少的基本要素,第一个完稿 在1959年夏到1960年底就写好了。在这个过程中范式不幸获 张 得了自己的独立生命,基本上取代了以前“一致意见”的说法。 开始它还只是示范性地解决问题,后来扩大自已的王国,首先包 罗了最早提出这些公认事例的经典著作,最后又囊括了某一特 力 定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一整套承诺。这本书的大多数读者 只知道这一术语比较笼统的用法,结果引起了不可避免的混乱: 那里所说许多有关范式的问题,其实只适用于这一术语原来的 意义。这两种意义虽然在我看来都很重要,但必须加以区别, “苑式”这个词只适用于第一种意义。显然,是我给读者造成了 不必要的困难。〔) 本书其余五篇文章不要一一讨论了。只有《思想实验的作 用》写于那本书之前,对它的定型没有什么影响。《对范式的再 思考》是三次试图恢复范式的原来意义中的第一次,写得最早, 发表得最迟。[]《客观性、价值判断和理论选择》以前没有发表 过,是一篇讲稿,目的是想回答那种我使理论选择完全陷入主观 的指责。这五篇文章,包括没有提到的两篇,都可以由本身得到 说明。这里与其一一列举,不如从其共有主题中抽出两个方面 来谈谈,作为这篇序言的结束。 通过对科学方法的传统讨论,已找到这样一组规则,任何个 人只要遵循这些规则就可以获致可靠的知识。但我却一直认 为,科学尽管是由个人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却是群体的产 物,如不考虑创造这种知识的群体的特殊性,那就既无法理解科 学知识的特有效能,也无法理解它的发展方式。从这一点说,我 的书在本质上是属于社会学的,但也不容许这个主题离开认识 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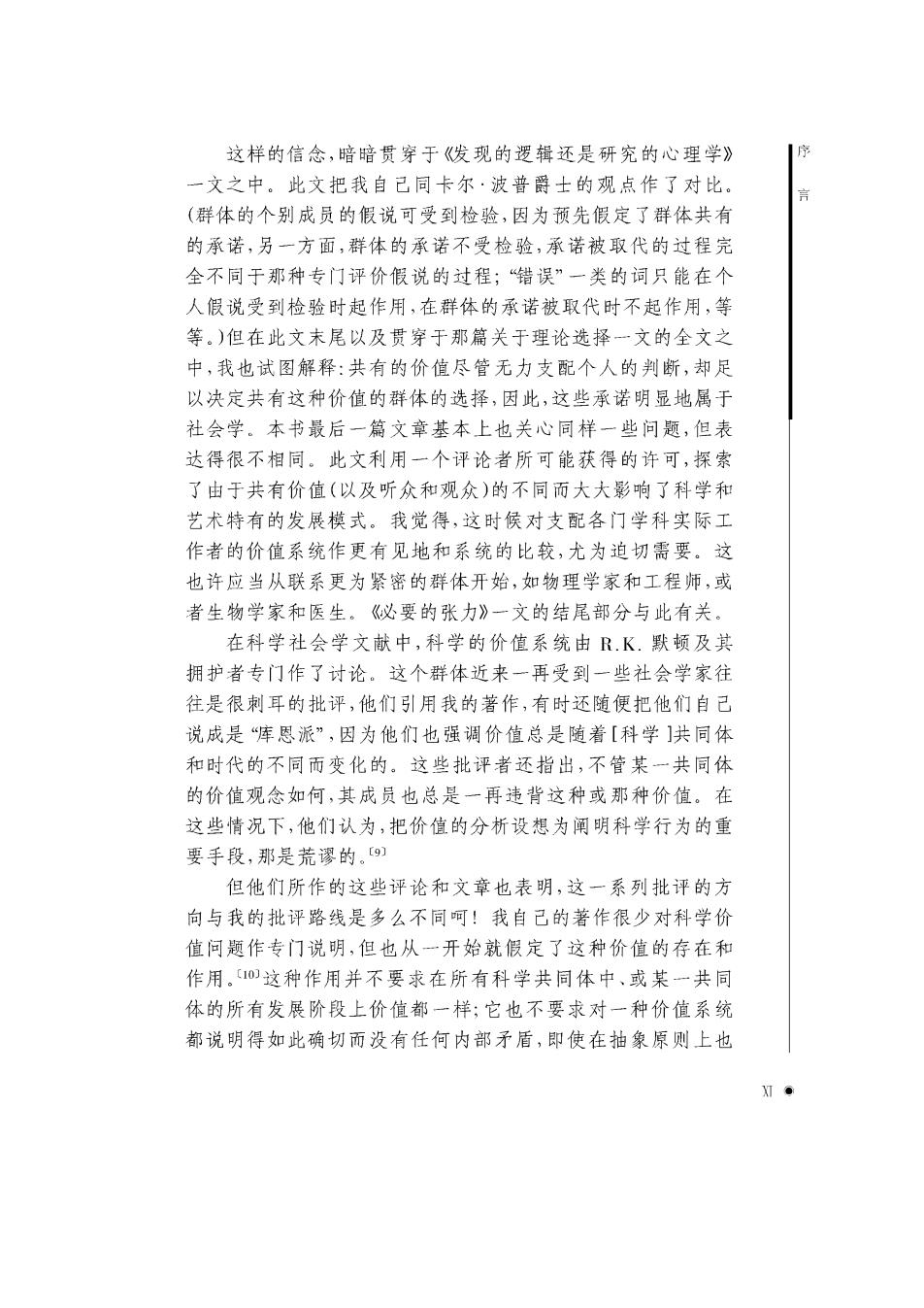
这样的信念,暗暗贯穿于《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 序 一文之中。此文把我自己同卡尔·波普爵士的观点作了对比。 (群体的个别成员的假说可受到检验,因为预先假定了群体共有 的承诺,另一方面,群体的承诺不受检验,承诺被取代的过程完 全不同于那种专门评价假说的过程;“错误”一类的词只能在个 人假说受到检验时起作用,在群体的承诺被取代时不起作用,等 等。)但在此文末尾以及贯穿于那篇关于理论选择一文的全文之 中,我也试图解释:共有的价值尽管无力支配个人的判断,却足 以决定共有这种价值的群体的选择,因此,这些承诺明显地属于 社会学。本书最后一篇文章基本上也关心同样一些问题,但表 达得很不相同。此文利用一个评论者所可能获得的许可,探索 了由于共有价值(以及听众和观众)的不同而大大影响了科学和 艺术特有的发展模式。我觉得,这时候对支配各门学科实际工 作者的价值系统作更有见地和系统的比较,尤为迫切需要。这 也许应当从联系更为紧密的群体开始,如物理学家和工程师,或 者生物学家和医生。《必要的张力》一文的结尾部分与此有关。 在科学社会学文献中,科学的价值系统由R.K.默顿及其 拥护者专门作了讨论。这个群体近来一再受到一些社会学家往 往是很刺耳的批评,他们引用我的著作,有时还随便把他们自己 说成是“库恩派”,因为他们也强调价值总是随着[科学]共同体 和时代的不同而变化的。这些批评者还指出,不管某一共同体 的价值观念如何,其成员也总是一再违背这种或那种价值。在 这些情况下,他们认为,把价值的分析设想为阐明科学行为的重 要手段,那是荒谬的。[9) 但他们所作的这些评论和文章也表明,这一系列批评的方 向与我的批评路线是多么不同呵!我自己的著作很少对科学价 值问题作专门说明,但也从一开始就假定了这种价值的存在和 作用。「1这种作用并不要求在所有科学共同体中、或某一共同 体的所有发展阶段上价值都一样;它也不要求对一种价值系统 都说明得如此确切而设有任何内部矛盾,即使在抽象原则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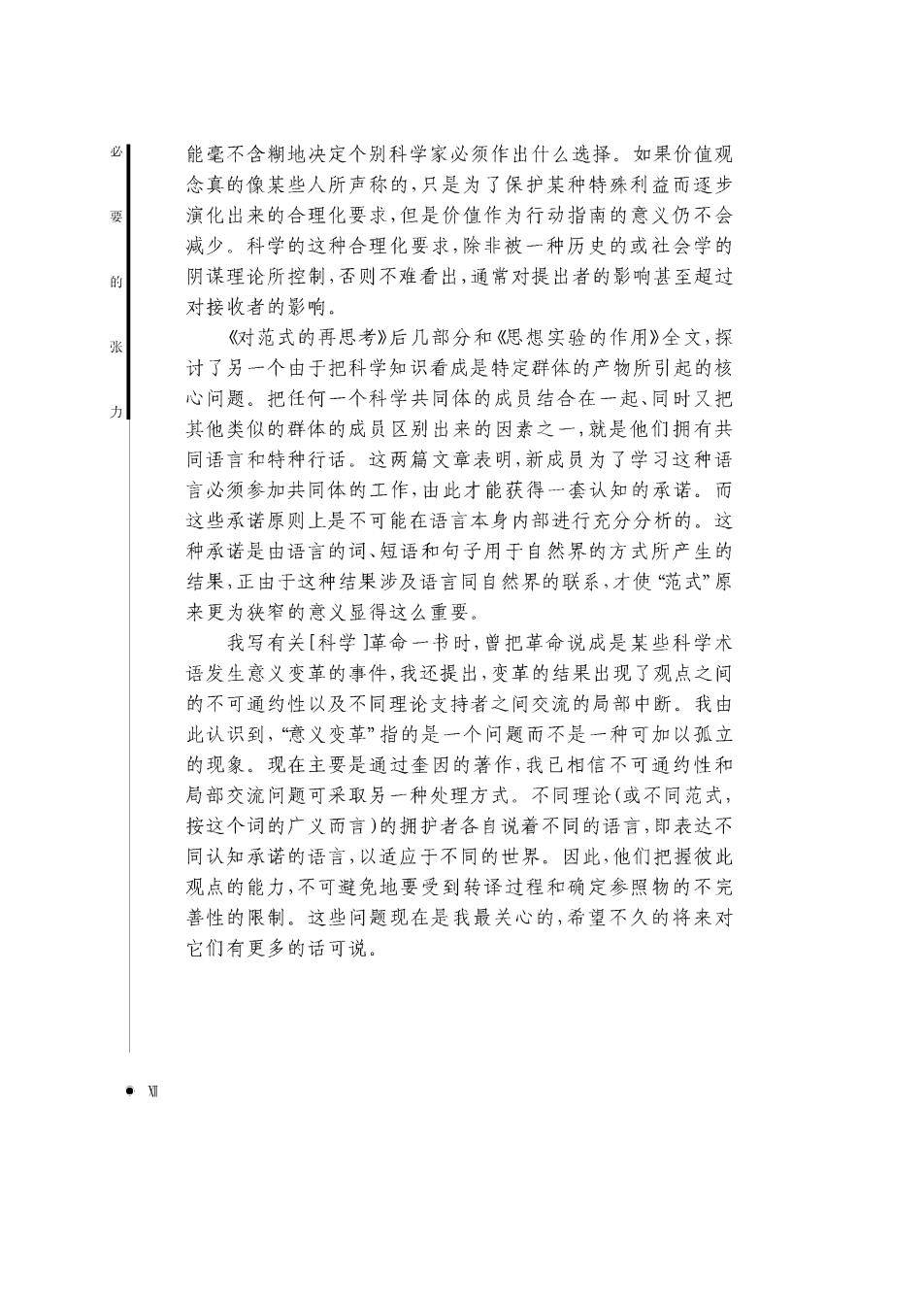
必 能毫不含糊地决定个别科学家必须作出什么选择。如果价值观 念真的像某些人所声称的,只是为了保护某种特殊利益而逐步 要 演化出来的合理化要求,但是价值作为行动指南的意义仍不会 减少。科学的这种合理化要求,除非被一种历史的或社会学的 9 阴谋理论所控制,否则不难看出,通常对提出者的影响甚至超过 对接收者的影响。 张 《对范式的再思考》后几部分和《思想实验的作用》全文,探 讨了另一个由于把科学知识看成是特定群体的产物所引起的核 心问题。把任何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结合在一起、同时又把 力 其他类似的群体的成员区别出来的因素之一,就是他们拥有共 同语言和特种行话。这两篇文章表明,新成员为了学习这种语 言必须参加共同体的工作,由此才能获得一套认知的承诺。而 这些承诺原则上是不可能在语言本身内部进行充分分析的。这 种承诺是由语言的词、短语和句子用于自然界的方式所产生的 结果,正由于这种结果涉及语言同自然界的联系,才使“范式”原 来更为狭窄的意义显得这么重要。 我写有关[科学]革命一书时,曾把革命说成是某些科学术 语发生意义变革的事件,我还提出,变革的结果出现了观点之间 的不可通约性以及不同理论支持者之间交流的局部中断。我由 此认识到,“意义变革”指的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种可加以孤立 的现象。现在主要是通过奎因的著作,我已相信不可通约性和 局部交流问题可采取另一种处理方式。不同理论(或不同范式, 按这个词的广义而言)的拥护者各自说着不同的语言,即表达不 同认知承诺的语言,以适应于不同的世界。因此,他们把握彼此 观点的能力,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转译过程和确定参照物的不完 善性的限制。这些问题现在是我最关心的,希望不久的将来对 它们有更多的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