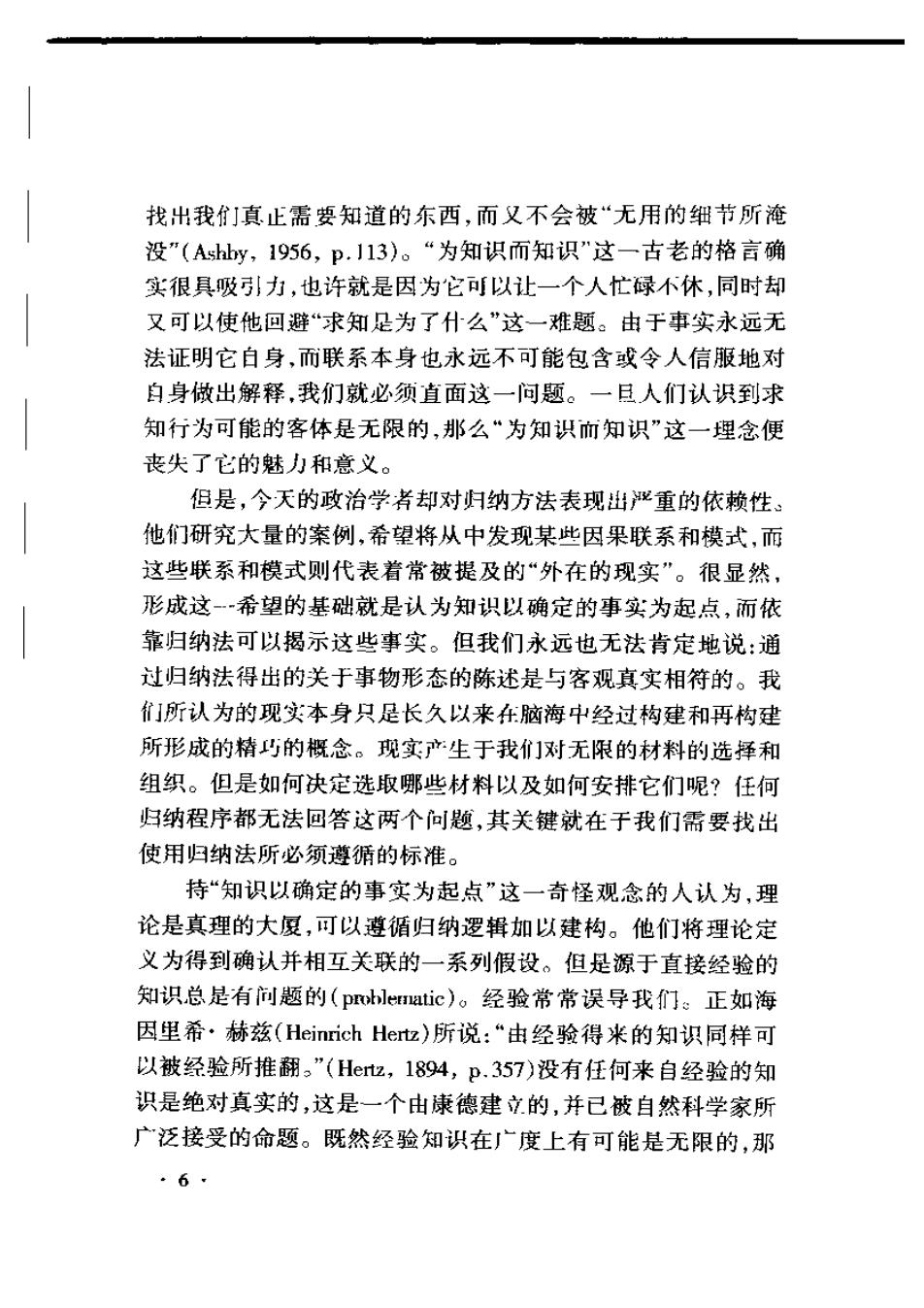
找出我们真止需要知道的东西,而义不会被“无用的细节所淹 没”(Ashby,1956,P.J13)。“为知识而知识"这一古老的格言确 实很具吸引力,也许就是因为它可以让一个人忙碌不休,同时却 又可以使他回避“求知是为了什么”这一雄题。由于事实永远无 法证明它自身,而联系本身也永远不可能包含或令人信服地对 自身做出解释,我们就必须直面这一问题。一且人们认识到求 知行为可能的客体是无限的,那么“为知识而知识”这一理念便 丧失了它的魅力和意义。 但是,今天的政治学者却对归纳方法表现出严重的依赖性 他们研究大量的案例,希望将从中发现某些因果联系和模式,而 这些联系和模式则代表着常被提及的“外在的现实”。很显然, 形成这-希望的基础就是认为知识以确定的事实为起点,而依 靠归纳法可以揭示这些事实。但我们永远也无法肯定地说:通 过归纳法得出的关于事物形态的陈述是与客观真实相符的。我 ]所认为的现实本身只是长久以来在脑海中经过构建和再构建 所形成的精巧的概念。现实产生于我]对无限的材料的选择和 组织。但是如何决定选取哪些材料以及如何安排它们呢?任何 归纳程序都无法回答这两个向问题,其关键就在于我们需要找出 使用归纳法所必须遵循的标准。 持“知识以确定的事实为起点”这一奇怪观念的人认为,理 论是真理的大厦,可以遵循归纳逻辑加以建构。他们将理论定 义为得到确认并相互关联的一系列假设。但是源于直接经验的 知识总是有问题的(problematic)。经验常常误导我们。正如海 因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所说:“由经验得米的知识同样可 以被经验所推翻,”(Het也,1894,p.357)没有任何来自经验的知 识是绝对真实的,这是一个由康德建立的,并已被自然科学家所 广泛接受的命题。既然经验知识在广度上有可能是无限的,那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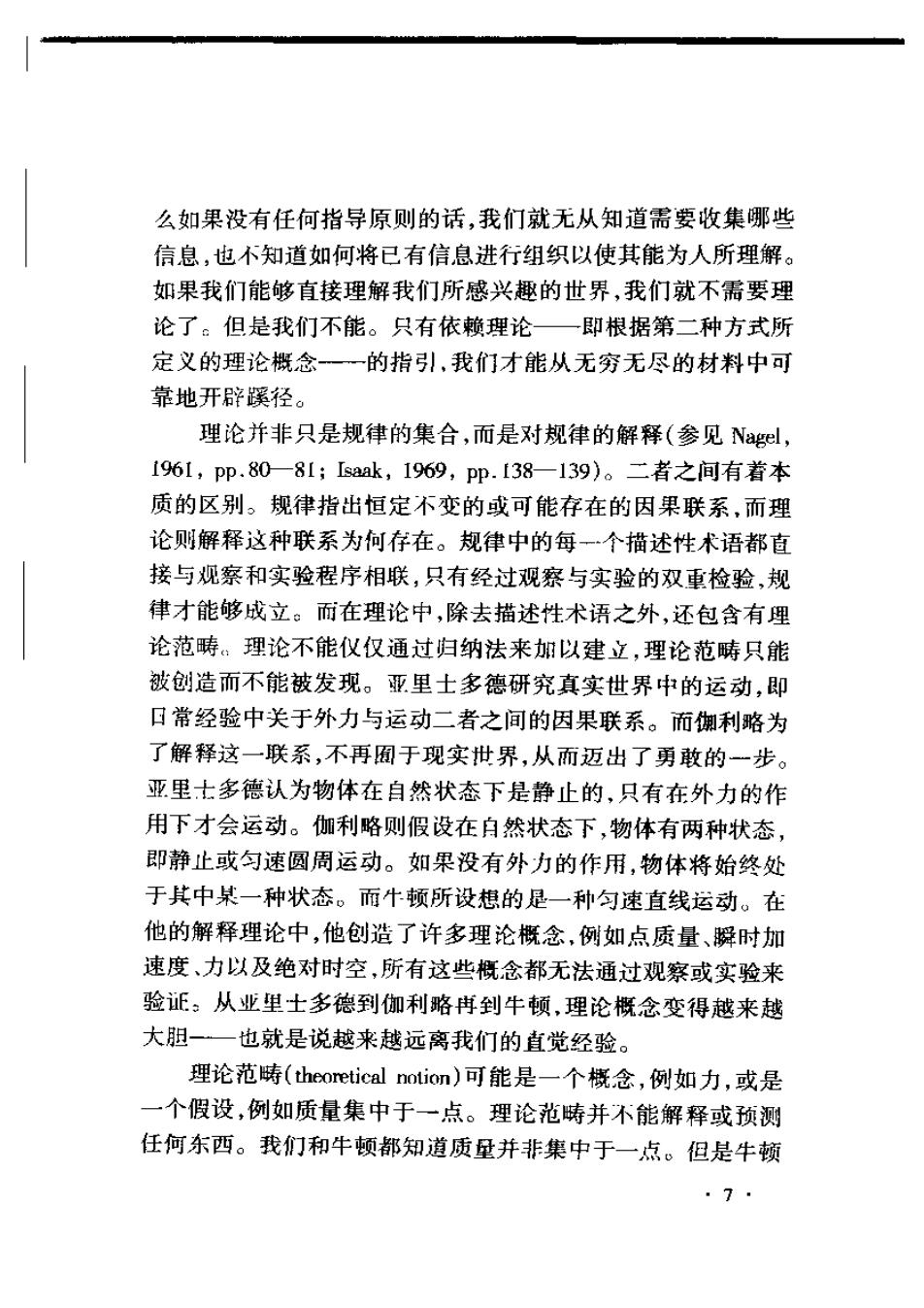
么如果没有任何指导原则的话,我们就无从知道需要收集哪些 信息,也不知道如何将已有信息进行组织以使其能为人所理解。 如果我们能够直接理解我们所感兴趣的世界,我们就不需要理 论了。但是我们不能。只有依赖理论一即根据第二种方式所 定义的理论概念一一的指引,我们才能从无穷无尽的材料中可 靠地开辟溪径。 理论并非只是规律的集合,而是对规律的解释(参见Nagel, 1961,pp.80-81;saak,1969,pp.138-139)。二者之间有着本 质的区别。规律指出恒定不变的或可能存在的因果联系,而理 论则解释这种联系为何存在。规律中的每一个描述性术语都直 接与规察和实验程序相联,只有经过观察与实验的双重检验,规 律才能够成立。而在理论中,除去描述性术语之外,还包含有理 论范畴。:理论不能仪仅通过归纳法来加以建立,理论范畴只能 被创造而不能被发现。亚里士多德研究真实世界中的运动,即 口常经验中关于外力与运动二者之间的因果联系。而御利略为 了解释这一联系,不再囿于现实世界,从而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在自然状态下是静止的,只有在外力的作 用下才会运动。伽利略则假设在自然状态下,物体有两种状态, 即静止或匀速圆周运动。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物体将始终处 于其中某一种状态。而牛顿所设想的是一种匀速直线运动。在 他的解释理论中,他创造了许多理论概念,例如点质量、瞬时加 速度、力以及绝对时空,所有这些概念都无法通过观察或实验来 验证。从亚里土多德到伽利略再到牛顿,理论概念变得越来越 大胆一一也就是说越来越远离我们的直觉经验。 理论范畴(theoretical notion.)可能是一个椽,念,例如力,或是 一个假设,例如质量集中于一点。理论范畴并不能解释或预测 任何东西。我们和牛顿都知道质量并非集中于一点。但是牛顿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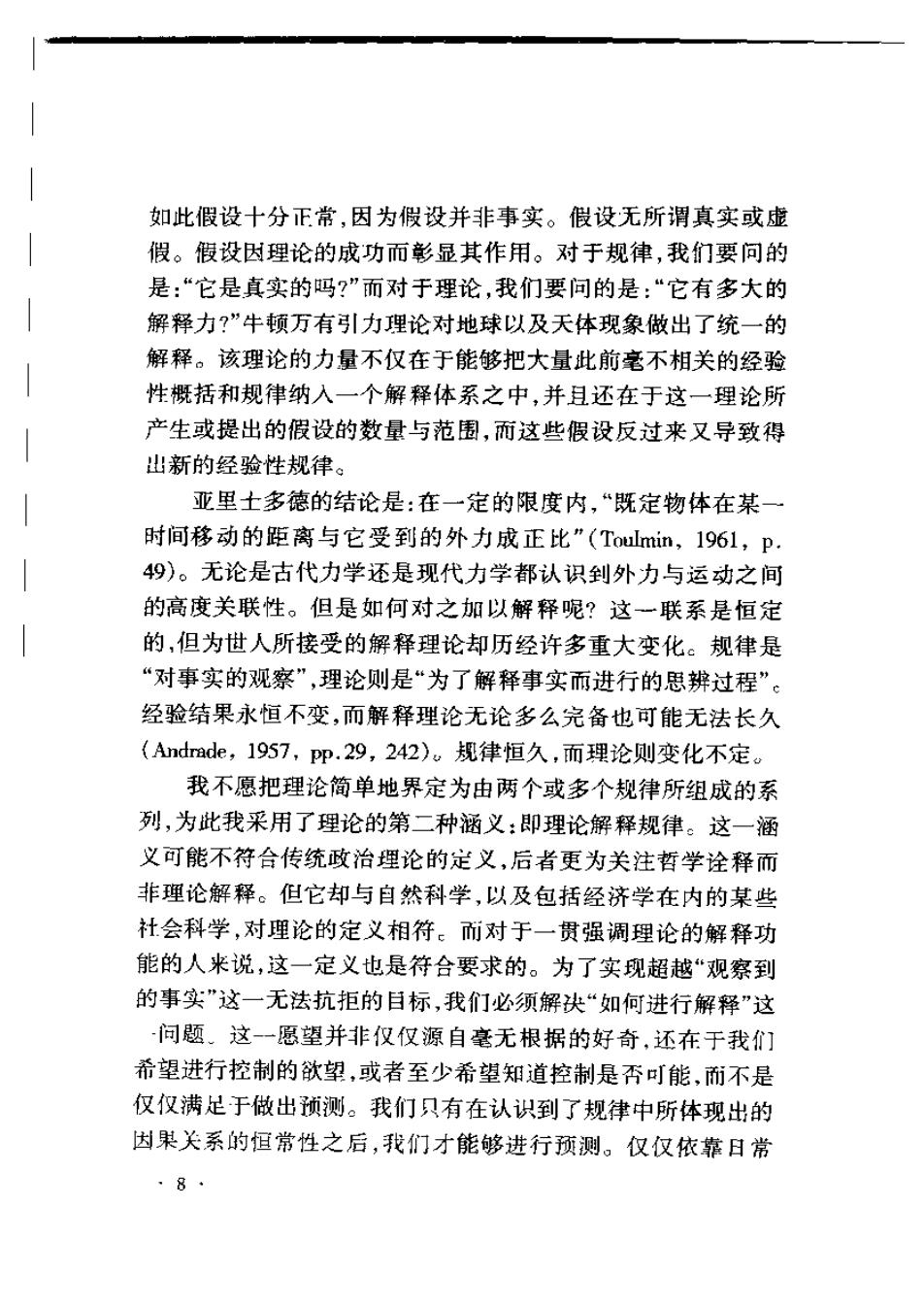
如此假设十分正常,因为假设并非事实。假设无所谓真实或虚 假。假设因理论的成功而彰显其作用。对于规律,我们要问的 是:“它是真实的吗?”而对于理论,我们要问的是:“它有多大的 解释力?”牛顿万有引力理论对地球以及天体现象做出了统一的 解释。该理论的力量不仅在于能够把大量此前毫不相关的经跑 性概括和规律纳入一个解释体系之中,并且还在于这一理论所 产生或提出的假设的数量与范围,而这些假设反过来又导致得 出新的经验性规律。 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在一定的限度内,“既定物体在某一 时间移动的距离与它受到的外力成正比”(Toulmin,1961,p. 49)。无论是古代力学还是现代力学都认识到外力与运动之间 的高度关联性。但是如何对之加以解释呢?这一联系是恒定 的,但为世人所接受的解释理论却历经许多重大变化。规律是 “对事实的观察”,理论则是“为了解释事实而进行的思辨过程”。 经验结果永恒不变,而解释理论无论多么完备也可能无法长久 (Andrade,1957,p.29,242)。规律恒久,而理论则变化不定。 我不愿把理论简单地界定为由两个或多个规律所组成的系 列,为此我采用了理论的第二种涵义:即理论解释规律。这一涵 义可能不符合传统政治理论的定义,后者更为关注哲学诠释而 非理论解释。但它却与自然科学,以及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某些 社会科学,对理论的定义相符。而对于一贯强调理论的解释功 能的人来说,这一定义也是符合要求的。为了实现超越“观察到 的事实”这一无法抗拒的目标,我们必须解决“如何进行解释”这 问题。这一愿望并非仅仅源自毫无根据的好奇,还在于我们 希望进行控制的欲望,或者至少希望知道控制是否可能,而不是 仅仅满足于做出预测。我们只有在认识到了规律中所体现出的 因果关系的恒常性之后,我们才能够进行预测。仅仅依靠日常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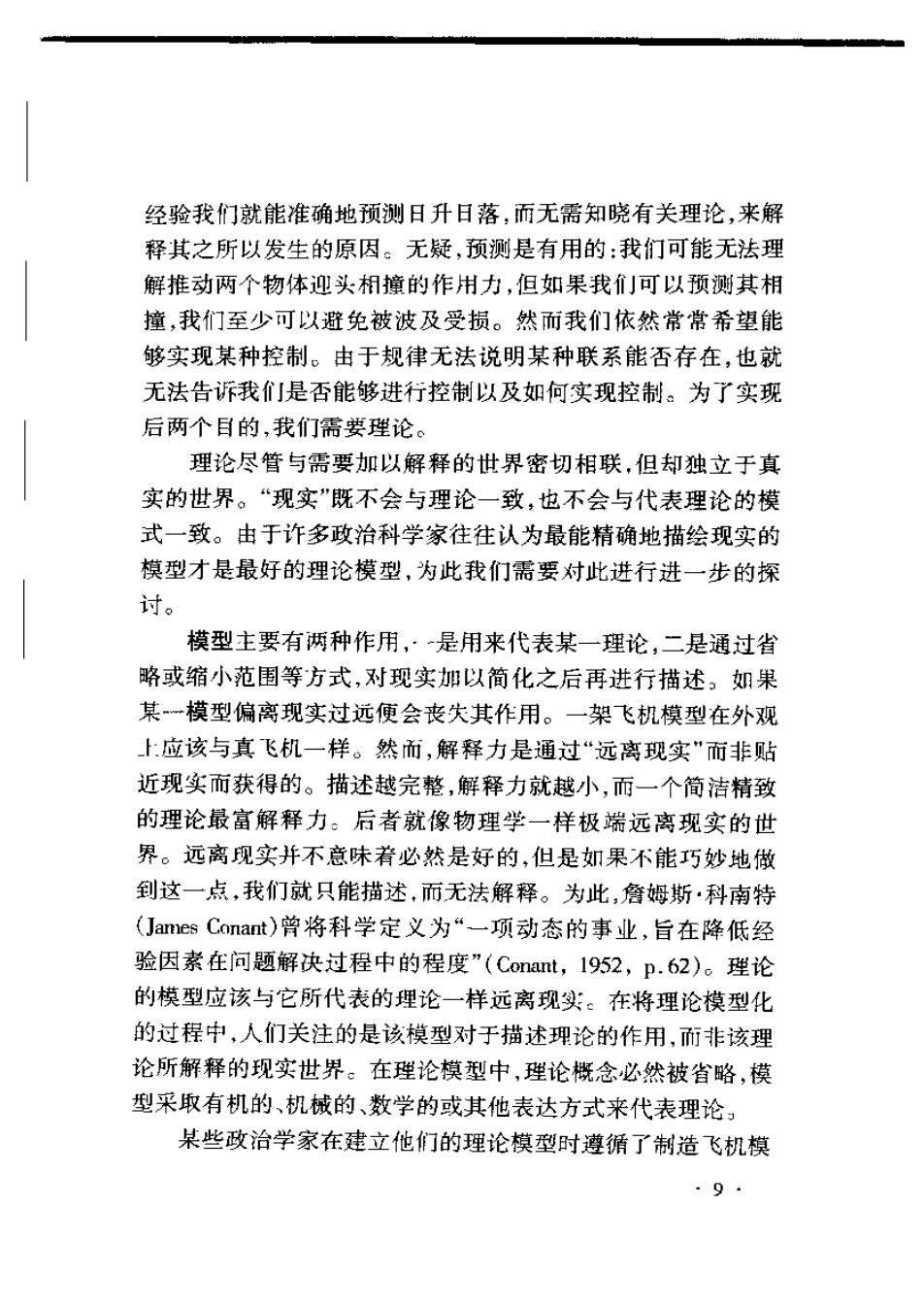
经验我们就能准确地预测日升日落,而无需知晓有关理论,来解 释其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无疑,预测是有用的:我们可能无法理 解推动两个物体迎头相撞的作用力,但如果我可以预满其相 撞,我们至少可以避免被波及受损。然而我们依然常常希望能 够实现某种控制。由于规律无法说明某种联系能否存在,也就 无法告诉我创是否能够进行控制以及如何实现控制。为了实现 后两个目的,我们需要理论。 理论尽管与需要加以解释的世界密切相联,但却独立于真 实的世界。“现实”既不会与理论一致,也不会与代表理论的模 式一致。由于许多政治科学家往往认为最能精确地描绘现实的 模型才是最好的理论模型,为此我们需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的探 讨。 模型主要有两种作用,·一是用来代表某一理论,二是通过省 略或缩小范围等方式,对现实加以简化之后再进行描述。如果 某一模型偏离现实过远便会丧失其作用。一架飞机模型在外观 上应该与真飞机一样。然而,解释力是通过“远离现实”而非贴 近现实而获得的。描述越完整,解释力就越小,而一个简洁精致 的理论最富解释力。后者就像物理学一样极端远离现实的世 界。远离现实并不意味着必然是好的,但是如果不能巧妙地做 到这一点,我们就只能描述,而无法解释。为此,詹姆斯·科南特 (James Conant)曾将科学定义为“一项动态的事业,旨在降低经 验因素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程度”(Conant,1952,p.62)。理论 的模型应该与它所代表的理论一样远离现实。在将理论模型化 的过程中,人们关注的是该模型对于描述理论的作用,而非该理 论所解释的现实世界。在理论模型中,理论概念必然被省略,模 型采取有机的、机械的、数学的或其他表达方式来代表理论, 某些政治学家在建立他们的理论模型时遵循了制造飞机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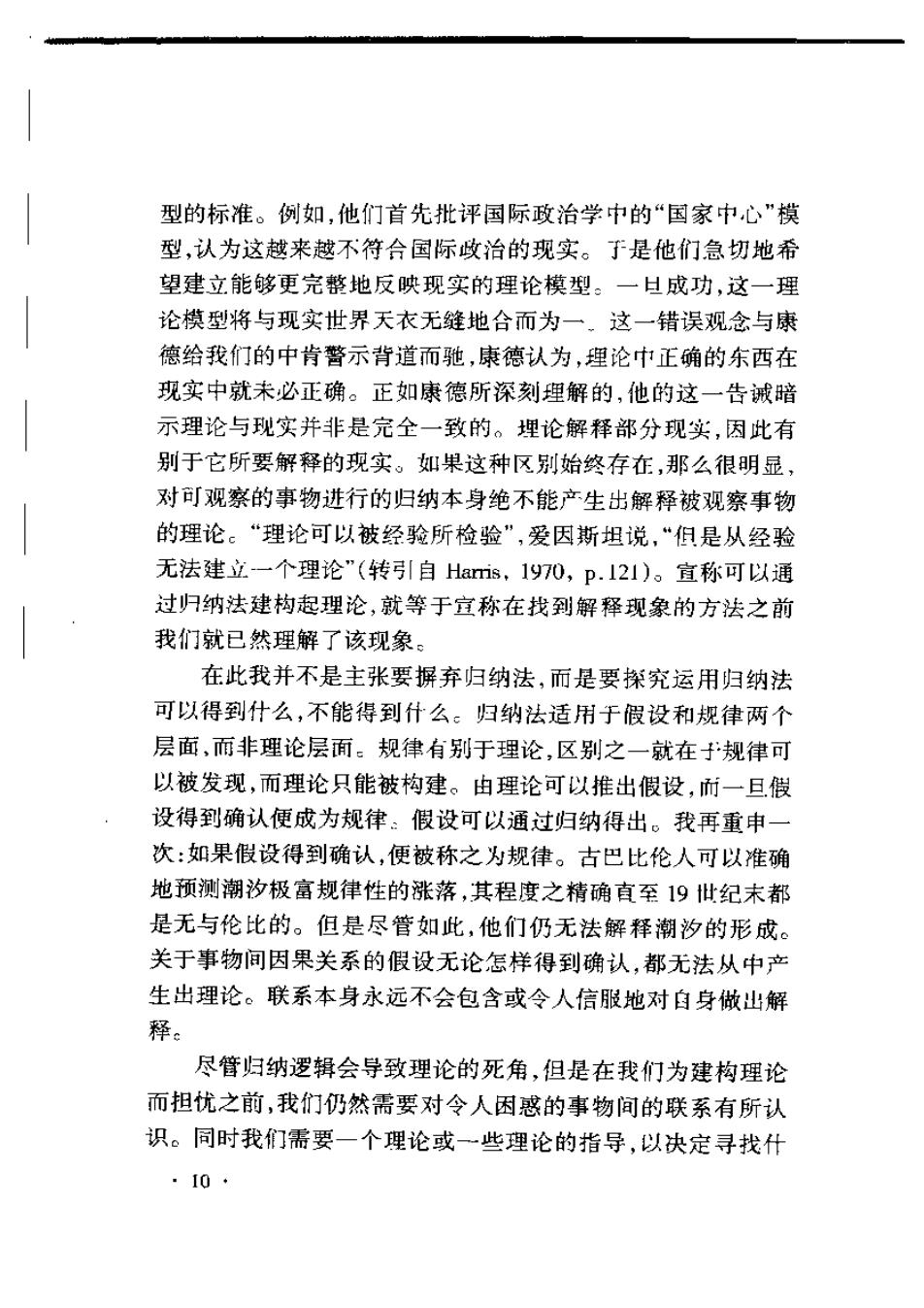
型的标准。例如,他们首先批评国际政治学中的“国家中心”模 型,认为这越来越不符合国际政治的现实。于是他们急切地希 望建立能够更完整地反映现实的理论模型。一旦成功,这一理 论模型将与现实世界天衣无缝地合而为一.这一错误观念与康 德给我们的中肯警示背道而驰,康德认为,理论中正确的东西在 现实中就未必正确。正如康德所深刻理解的,他的这一告诫暗 示理论与现实并非是完全一致的。埋论解释部分现实,因此有 别于它所要解释的现实。如果这种区别始终存在,那么很明显, 对可观察的事物进行的归纳本身绝不能产生出解释被观察事物 的理论。“理论可以被经验所检验”,爱因斯坦说,“但是从经验 无法建立一个理论”(转引自Hams,1970,P.121)。宜称可以通 过归纳法建构起理论,就等于宜称在找到解释现象的方法之前 我们就已然理解了该现象 在此我并不是主张要摒弃归纳法,而是要探究运用归纳法 可以得到什么,不能得到什么。归纳法适用于假设和规律两个 层面,而非理论层而。规律有别于理论,区别之一就在规律可 以被发现,而理论只能被构建。由理论可以推出假设,而一旦假 设得到确认便成为规律。假设可以通过归纳得出。我再重申一 次:如果假设得到确认,便被称之为规律。古巴比伦人可以准确 地预测潮汐极富规律性的涨落,其程度之精确直至19世纪未都 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仍无法解释潮汐的形成 关于事物间因果关系的假设无论怎样得到确认,都无法从中产 生出理论。联系本身永远不会包含或令人信服地对自身做出解 释e 尽管归纳逻辑会导致理论的死角,但是在我们为建构理论 而担忧之前,我们仍然需要对令人困惑的事物间的联系有所认 识。同时我们需要一个理论或一些理论的指导,以决定寻找什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