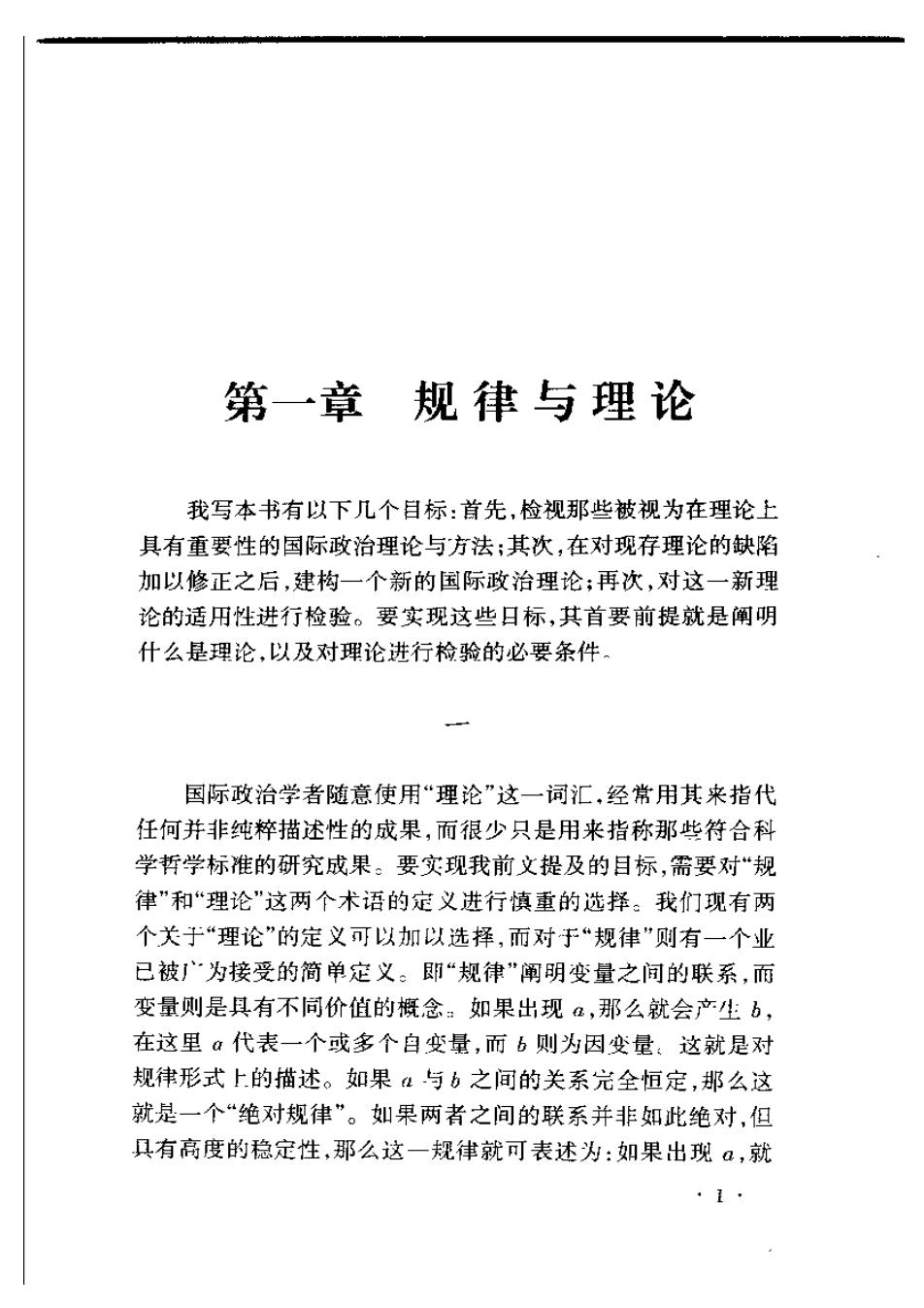
第一章规律与理论 我写本书有以下几个目标:首先,检视那些被视为在理论土 具有重要性的国际政治理论与方法:其次,在对现存理论的缺陷 加以修正之后,建构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理论:再次,对这一新理 论的适円性进行检验。要实现这些日标,其首要前提就是阐明 什么是理论,以及对理论进行检验的必要条件 国际政治学者随意使用“理论”这一词汇,经常用其来指代 任何并非纯粹描述性的成果,而很少只是用来指称那些符合科 学哲学标准的研究成果。要实现我前文提及的目标,需要对“规 律”和“理论”这两个术语的定义进行慎重的选择。我们现有两 个关于“理论”的定义可以加以选择,而对于“规律”则有一个业 已被广为接受的简单定义。即“规律”阐明变量之间的联系,而 变量则是具有不同价值的概念:如果出现a,那么就会产生b, 在这里a代表一个或多个自变量,而b则为因变量:这就是对 规律形式上的描述。如果a与6之间的关系完全恒定,郑么这 就是一个“绝对规律”。如果两者之间的联系并非如此绝对,但 具有高度的稳定性,那么这一规律就可表述为:如果出现α,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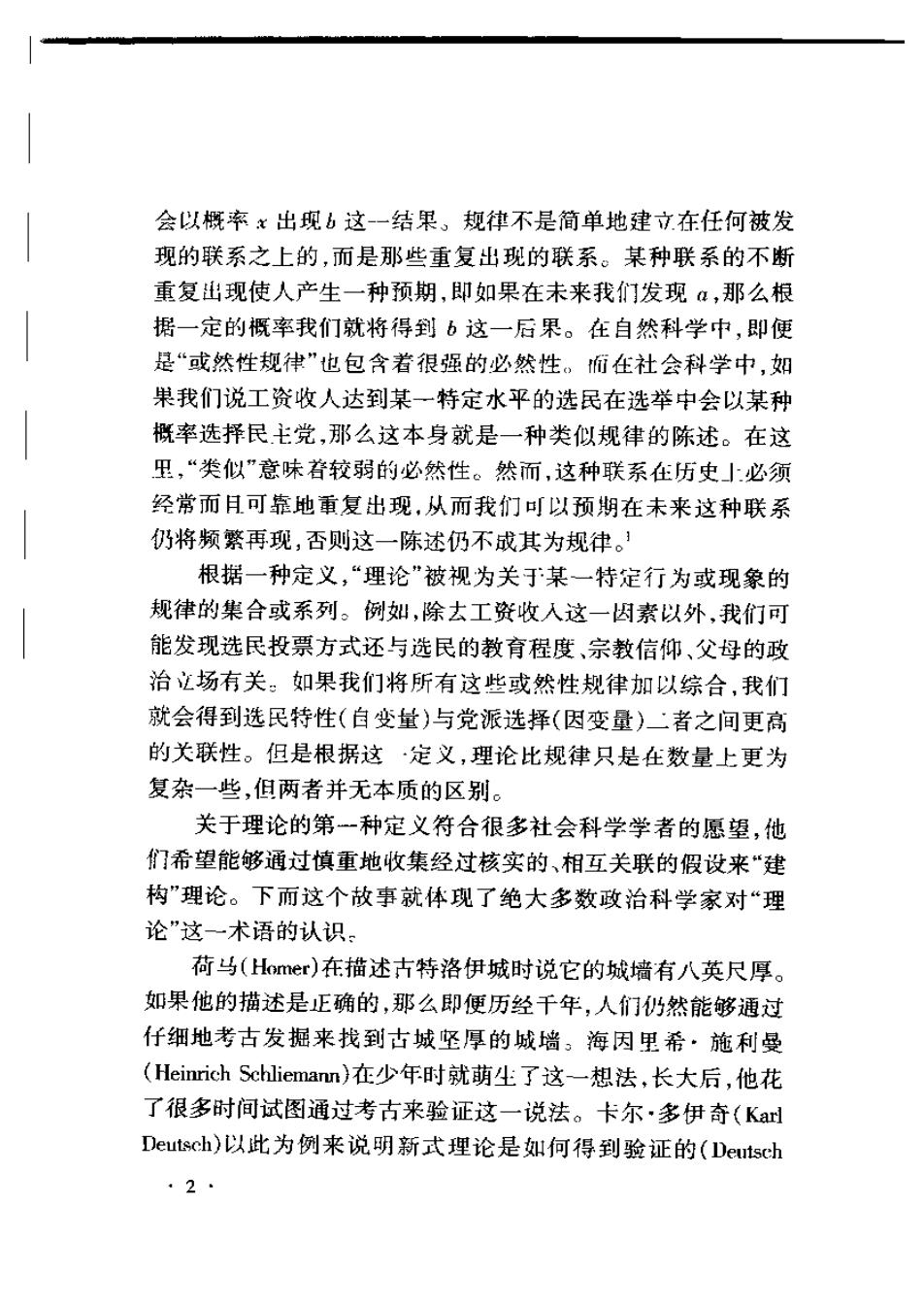
会以概率x出现b这-一结果、规律不是简单地建立在任何被发 现的联系之上的,而是那些重复出现的联系。某种联系的不断 重复出现使人产生一种预期,即如果在未来我们发现a,那么根 据一定的概率我们就将得到b这一后果。在自然科学中,即便 是“或然性规律”也包含者很强的必然性。而在社会科学中,如 果我们说工资收人达到某一特定水平的选民在选举中会以某种 概率选择民主党,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类似规律的陈述。在这 里,“类似”意味着较弱的必然性。然而,这种联系在历史」必须 经常而月可靠地重复出现,从而我们可以预期在未来这种联系 仍将频繁再现,否则这一陈述仍不成其为规律。! 根据一种定义,“理论”被视为关于某一特定行为或现象的 规律的集合或系列。例如,除去工资收入这一因素以外,我们可 能发现选民投票方式还与选民的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父母的政 治立场有关。如果我们将所有这些或然性规律加以综合,我们 就会得到选民特性(自变量)与党派选择(因变量)二者之间更高 的关联性。但是根据这·定义,理论比规律只是在数量上更为 复杂一些,但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 关于理论的第一种定义符合很多社会科学学者的愿望,他 们希望能够通过慎重地收集经过核实的、相互关联的假设来“建 构”理论。下而这个故事就体现了绝大多数政治科学家对“理 论”这一术语的认识, 荷马(Homer)在描述古特洛伊城时说它的城墙有八英尺厚。 如果他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即便历经千年,人们仍然能够通过 仟细地考古发掘来找到古城坚厚的城墙。海因里希·施利曼 (Heinrich Schliemann)在少年时就萌生了这一想法,长大后,他花 了很多时间试图通过考古来验证这一说法。卡尔·多伊奇(Ka Deutsch)以此为例来说明新式理论是如何得到验证的(Deutsch ·2

1966,p.168一169)。理论产生于推测,如果这一推测得到证 实,那么理论便因之而成立。多伊奇将简单的“如果一那么”模 式的理论视为“特殊理论”,有可能“在以后被植人某一宏大理论 之中”。为此,他又给出了另一些例证,从而由原本的“‘是/否 问题转变成‘程度'问题”。我们应该试图发现“不同的变量”会 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既定的结果(Deutsch,【966,pp.29一221)e 那么在这种思考方式屮,什么可能是有用的,什么又是没用 的呢?我们知道,即便是一个很高的相关系数,也并不能保证有 在某种恒定的因果关系。然而,如果将这一系数开方,从技术上 我们可以说已经解释了一定比例的方差。这易于导致我们相信 已经发现了一个其正的因果联系并进行了估算,认为已经确立 了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问的关系,却忘记了其实我们所指山的只 不过类似于指出一张纸上有几个点以及穿过这些点形成的一条 回归线,此外毫无意义。这一相关性(correlation)是虚假的吗? 这里提出了一个切中要害的问题,却没有深入地加以探究。相 关性无所谓真实还是虚假:它们只不过是人]通过简单的数学 运算而得到的数据而已:然而我们从这些数据屮所推论出的相 关性则既有可能是真实的,又有可能是虚假的。假设某人通过 仔细地计量加于小车的推力以及小车的运动距离二者之间的关 系,从而提出了某种规律。如果条件始终保持恒定,测量也始终 精准,那么这种关联的建立也不过是对事实的一种观察,是一个 恒久成立的规律。但是对外力与运动二者之间联系的解释则由 于我是选择亚里士多德、伽利略还是牛顿的学说而大相径庭。 对数据不加批判的接受,并认为该数据显示了某种联系,是我们 首先需要戒除的危险习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而下面我们 将讨论的则是一个更为重要、也更雅解决的问题。 即便我们通过各种方式的验证,认为关于桌种因果联系的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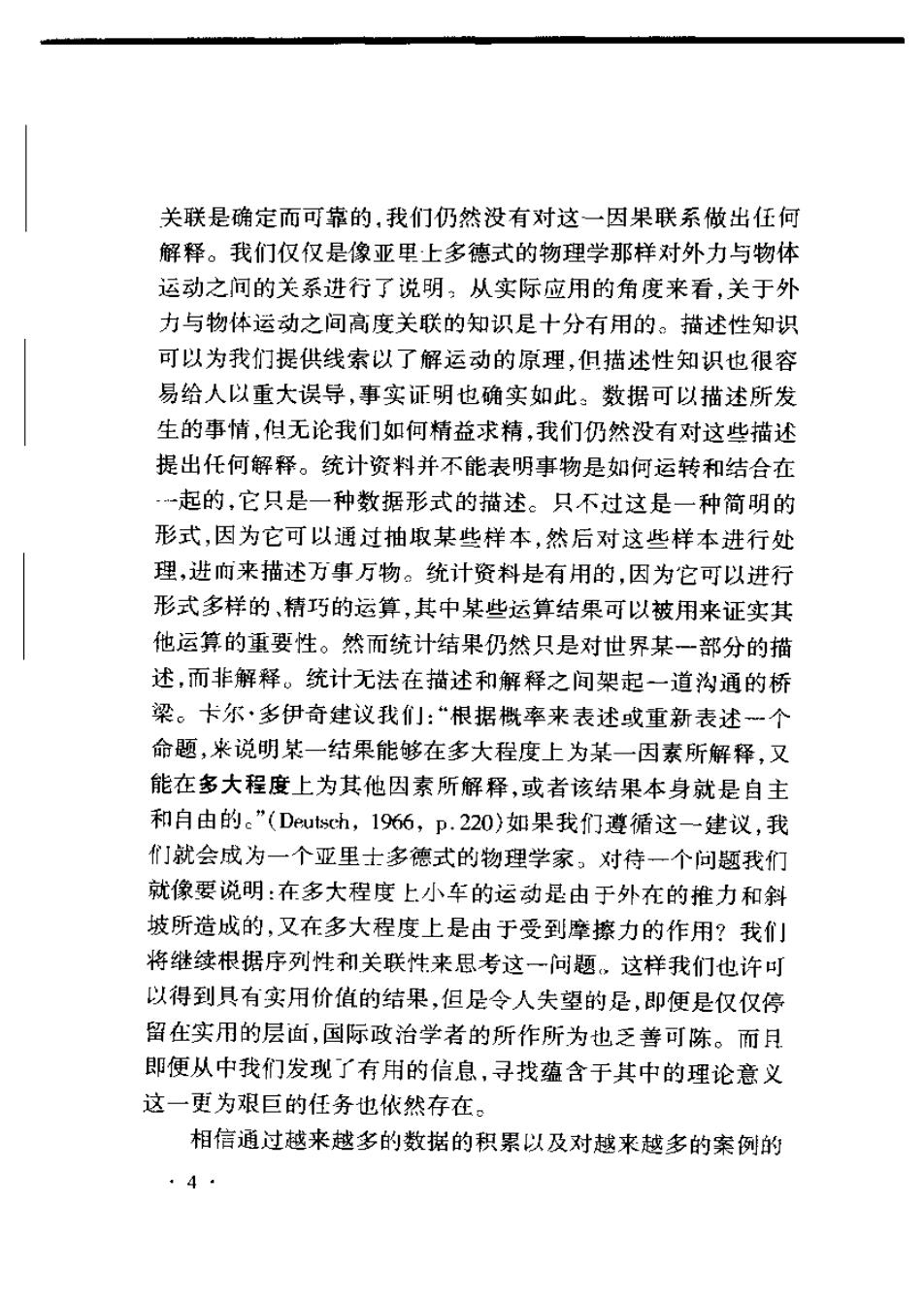
关联是确定而可靠的,我们仍然没有对这一因果联系做出任何 解释。我们仅仅是像亚里上多德式的物理学那样对外力与物体 运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说明,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关于外 力与物体运动之间高度关联的知识是十分有用的。描述性知识 可以为我们提供线索以了解运动的原理,但描述性知识也很容 易给人以重大误导,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数据可以描述所发 生的事情,但无论我们如何精益求精,我们仍然没有对这些描述 提出任何解释。统计资料并不能表明事物是如何运转和结合在 一起的,它只是一种数据形式的描述。只不过这是一种简明的 形式,因为它可以通过抽取某些样本,然后对这些样本进行处 理,进而来描述万事万物。统计资料是有用的,因为它可以进行 形式多样的,精巧的运算,其中某些运算结果可以被用来证实其 他运算的重要性。然而统计结果仍然只是对世界某一部分的描 述,而非解释。统计无法在描述和解释之间架起一道沟通的桥 梁。卡尔·多伊奇建议我们:“根据概率来表述或重新表述一个 命题,来说明某一结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某一因素所解释,又 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其他因素所解释,或者该结果本身就是自主 和自由的e”(Deutsch,1966,p.220)如果我们遵循这一建议,我 ]就会成为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物理学家,对待一个问题我们 就像要说明:在多大程度上小车的运动是由于外在的推力和斜 坡所造成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摩擦力的作用?我」 将继续根据序列性和关联性来思考这一问题。,这样我们也许可 以得到具有实用价值的结果,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即便是仅仅停 留在实用的层面,国际政治学者的所作所为也乏善可陈。而月 即便从中我们发现了有用的信息,寻找蕴含于其中的理论意义 这一更为艰巨的任务也依然存在。 相信通过越来越多的数据的积累以及对越来越多的案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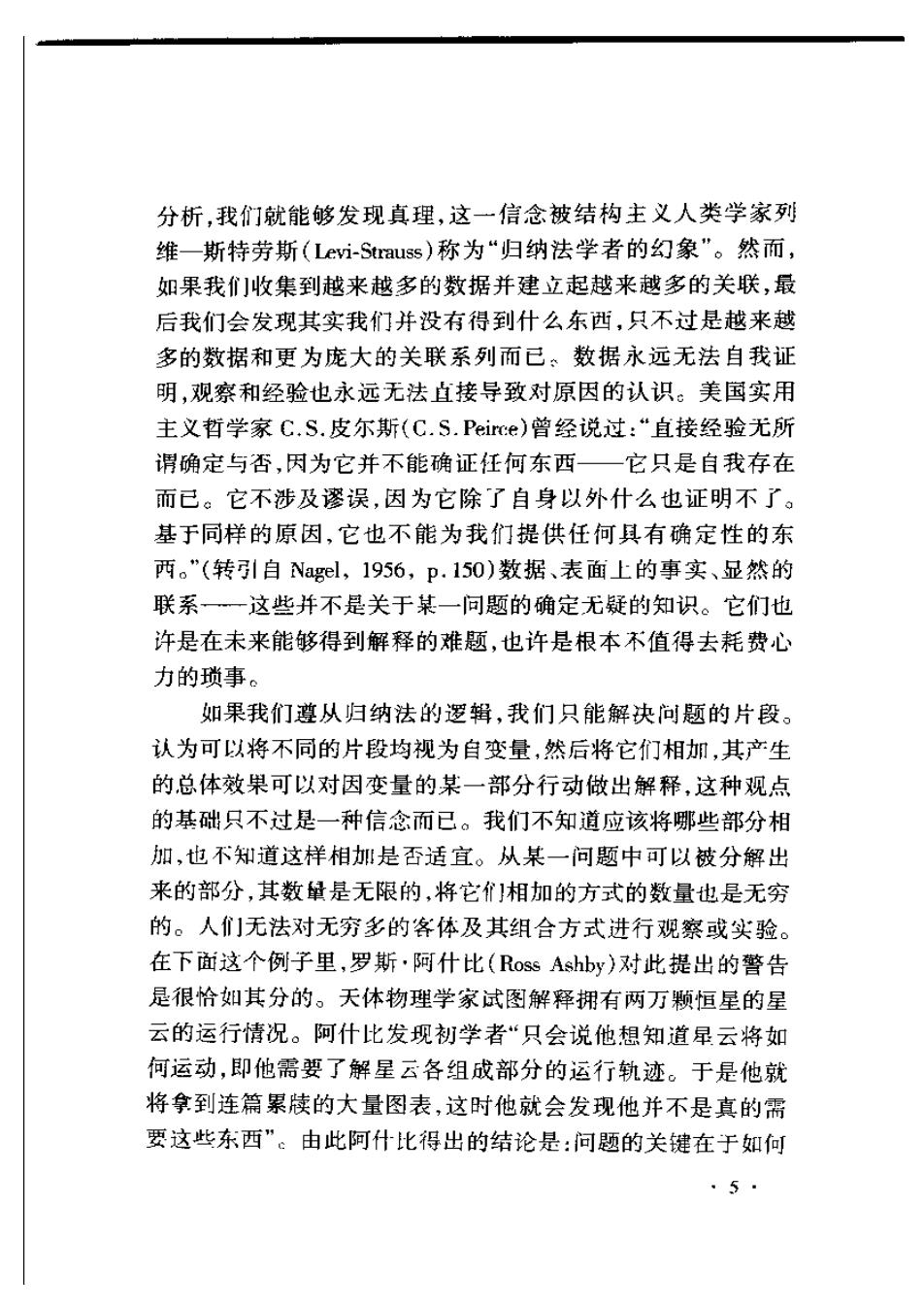
分析,我们就能够发现真理,这一信念被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 维一斯特劳斯(Lei-Strauss)称为“归纳法学者的幻象”。然而, 如果我]收集到越来越多的数据并建立起越来越多的关联,最 后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并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只不过是越来越 多的数据和更为庞大的关联系列而已。数据永远无法自我证 明,观察和经验也永远无法直接导致对原因的认识。美国实用 主义哲学家C.S.皮尔斯(C.S.Peirce)曾经说过:“直接经验无所 谓确定与否,因为它并不能确证任何东西一它只是自我存在 而已。它不涉及谬误,因为它除了自身以外什么也证明不了。 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具有确定性的东 西。”(转引自Nag©l,1956,P.150)数据、表面上的事实、显然的 联系一这些并不是关于某一问题的确定无疑的知识。它们也 许是在未来能够得到解释的难题,也许是根本不值得去耗费心 力的琐事。 如果我们遵从归纳法的逻辑,我们只能解决问题的片段 认为可以将不同的片段均视为自变量,然后将它们相加,其产生 的总体效果可以对因变量的某一部分行动做出解释,这种观,点 的基础只不过是一种信念而已。我们不知道应该将哪些部分相 加,也不知道这样相加是否适宜。从某一问题中可以被分解出 来的部分,其数量是无限的,将它]相加的方式的数量也是无穷 的。人们无法对无穷多的客体及其组合方式进行观察或实验。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罗斯·阿什比(Ross Ashby)对此提出的警告 是很恰如其分的。天体物理学家试图解释拥有两万颗恒星的星 云的运行情祝。阿什比发现初学者“只会说他想知道星云将如 何运动,即他需要了解星云各组成部分的运行轨迹。于是他就 将拿到连篇累牍的大量图表,这时他就会发现他并不是真的需 要这些东西”。由此阿什比得出的结论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