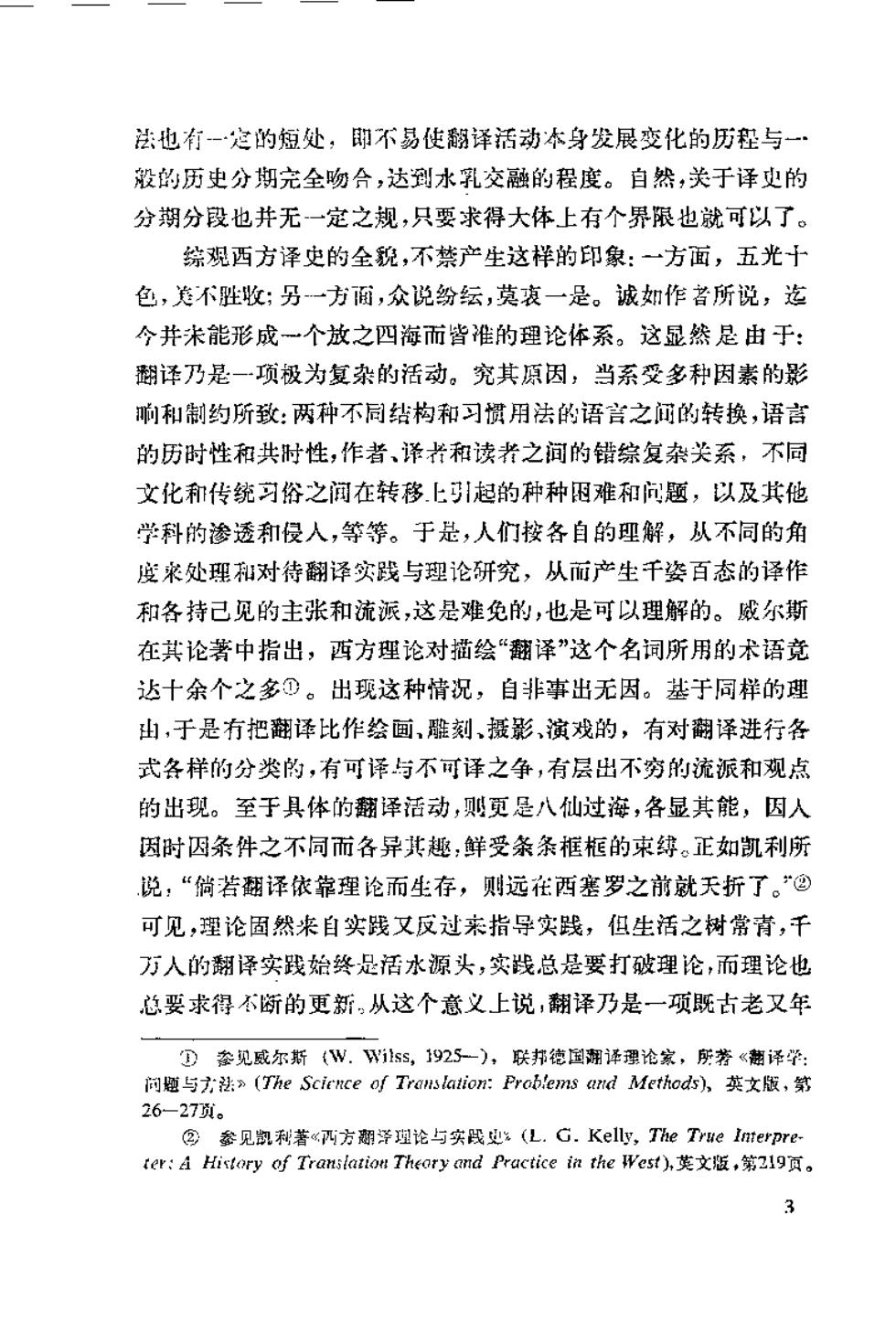
法也有-定的短处,即不易使翻译活动本身发展变化的历程与一· 般的历史分期完全吻合,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自然关于译更的 分期分段也并无一定之规,只要求得大体上有个界限也就可以了。 综观西方译史的全貌,不禁产生这样的印象:一方面,五光十 色,迄不胜收;另一方面,众说纷纭,莫哀一是。诚如作者所说,迄 今并未能形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这显然是由于: 翻译乃是一一项极为复杂的活动。究其原因,当系受多种因素的影 响和制约听致:两种不同钻构和习惯用法的语音之间的转换,语言 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作者、译者和读者之涧的错综复杂关系,不同 文化和传统习俗之润在转移上引起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以及其他 学科的渗透和侵人,等等。于是,人们按各自的理解,从不同的角 度来处理和对待翻译实践与迎论研究,从而产生千姿百态的译作 和各持己见的主张和流派,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威尔斯 在其论著中指出,西方理论对描绘“翻译”这个名词所用的术语竞 达十余个之多①。出现这种情祝,自非事出无因。基于同样的理 山,于是行把翻译比作绘画,雕刻、摄影,演戏的,有对翻译进行各 式各样的分类的,有可译与不可译之争,有层出不穷的流派和观点 的出现。至于具体的翻译活动,则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因人 因时因条件之不同而各异其趣,鲜受条条框框的束缚。正如凯利所 说,“徜若翻译依靠理论而生存,则远在西塞罗之前就天折了。② 可见,理论固然来自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但生活之树常青,千 万人的翻译实践始终是活水源头,实浅总是要打破理论,而理论也 总要求得不断的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乃是一项既古老又年 ①参见威尔斯(W.ss,92S-),联邦德国棚译理论家,所若《翻译学: 问题与方法>(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Prablems and Methods),英文版,第 26-27页。 ②畚见凯利著g西i方翻泽理论与实践%(L.G.Kelly,The True Interpre te: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West),英文版,第2l9页。 3

轻的事业。 如此说来,翻译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这是一个长期难以定 论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对翻译的前景作何种预测的问题,这个 问题在西方的翻译研究与现代科学和技术攀了亲,形成多边缘交 叉的现状,特别是在电了计算机的发明与研制进入模拟人脑活动 阶段之后的今天,人们(主要是语言学派的理论家)对翻译的看法 便越来越倾向于认定它是一门科学了。奈达有题为《翻译科学探 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之作,巴尔胡达罗夫在其著 心语言与翻译一书也中提出“翻译学”这个术语,并认为“从各个不 同角度研究翻译的各门学科,可以总称之为翻译学。翻译学的核心 部分是翻译的语言理论,围绕这一理论还有翻译研究中的其他流 派,如文艺学派、心理学派,数控论派等等。”①然而,浅见以为,翻译 这门事业是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看来还有进一步探时和商 榷之余地。理油简述多次,翻译同语言和数学近似,它既不隶属于 经济基础,也不隶属子层建筑,既非自然科学,也作社会科学,而 是入类用以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的工具。把一些学科中研究翻译的 各个边缘交叉部分统统都加起来,也并不足以成为认定这门学问 本身就是一门独立科学的充足理由。威尔斯对“翻译学”一词加了 许多限定语。巴尔胡达罗夫也指出,翻译理论“甚至主要并不是规 定性科学”,而主要是-一门描写性学科”,尽管前者“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②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看来乃是由于人类对白身脑千 的知识还非常贫泛之故。正如斯坦纳在其论著中所指出,“我们并 不了解人类的言语在脑子里的活动情况.假使有几种语言在同 一入脑中同时并存,它们是怎样安排、怎样储存的,我们几乎一无 ①套见苏联巴尔胡达罗夫著、恭毅等译《语言与翻译,第29页。中国对外翻 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 ②同上书,第25一28页。 4

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有象样的翻译理论呢?”①又说,“翻译究 凳是什么7”“人的脑子究竟怎样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的? 人们对这些情祝也是“含糊不清”。②“语言怎样使用,怎祥理解,在 关键的地方因人而异。.我们所研究的不是一门科学,而完全是 .门艺术。”③奈达殊途同归,近年来他改变原先关于翻译“既是科 学,又是艺术”的观点,拾前者而取后者,并声称翻译才能是“天赋” 的,从另一·个侧面肯定翻译是艺术或技能。但是,问题并未因此获 得圆满的解答。近年来,西方进行人工智能的研究,正在力图通过计 算机实现“人一机对话”,以期使计算机“懂得”人类社会所使用 的语言、达到不同语言之间转换自如的目的。西方翻译界还致力于 将符号学应月于翻译研究,是否意在使语言学按数学的模式,使语 音摆脱过去长期采用“定性”和“归纳”的方法,转为采月“定量”和 “演绎”的方法,以期有朝.日使·种语言顺利绝转换为另一种语 言,达到用机器代替人工从事翻译的理想目标呢?不久前偶然看到 -·侧电讯,说美国一家杂志预言,到本世纪末全世界就可以普遍使 用电脑近行翻译了。果然如此,那真要谢天谢地,数以万千计翻译 工作者便可以从“一名之立,句月蜘蹰”(严复语)的窘境中解脱出 来了。而翻译这门学询便终将成为一门独立的(应用)科学,这个理 想极富魅力!是否能实现呢?限下实在无法作绝对的肯定或否 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人类的语言体系具有极为复杂 的性质。有“科学的语言”,有“艺术的语言”①(可以说,还有“说理 的语言”),前者或许有可能使之全部数学符号化,以纳入计算机的 软件,后者有无这样的可能呢?何祝还有许许多多的模糊语言。即 使计算机不断升级换代,数学计算的程度日益精密,是否能处理大 ①②习分别参见斯坦纳著&语言与翻译面面观》(G.Steiner,fter Babel: A5- 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英文版,第294,278和295页。 ④)参见金克木尝心诗知时传达位息》一文,我《读书1986年第5,6两期。 5

量的模糊语言也还在木定之天。而且,即使所有的问题都能获得 解决,生产出来的译品想必会是于篇一律,人世间也就不免要失去 你有的生机和光泽: 另·方矿,还可以从文艺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以加切 奇拉泽为例,这一派并不否认语言在翻译中的重要作川。相反,他 主张文艺翻译“应当千方百计地开展各种语言层次的对比工作,包 括修辞对比,以选择最恰当的语言手段,充分表达原作的思想或形 象”但他强调文艺翻译的“美学价值”和“创造性原则。”@显易 见,任何文体和题材的翻译都离不开语言符号这个信总载体,文艺 翻译自不能例外。可是,正如带通语言的语言学家并不一定能城 为文学家一样,掌握两种语言的人也不一定能成为合格的文“艺作 品翻译者。因为还需要具备其他的条件,如还必须有较高的文化 修养和广博的知识、创作才能以至“天赋”, 现在让我们肴-看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之争的趋向。在西方 学术界处于现代综合思潮迭起的冲击下,翻译研究自六十年代以 来也进入了要求综合或统一的新阶段,②以往尖锐对峙的苏联两 大学派之一的代表人物费得罗夫也曾表示:“当代是各门科学空前 协作的时代”,“现在仍然坚持在文艺翻译的理论中只有走文艺学 的路子或只有走语言学的路子才是拾当的,这种提法已经过时了, 落后了。”据此,巴尔胡达罗夫认为,这两派的理论“应当在共同的 综合性的学科一翻译学的范用内逃行协作。”③他在书的结尾处 还引用奈达的话强调指出,我们应当永远牢记:“翻译一'它的含 义比科学要广泛得多,它也是一种技能,而高质量的翻译,归根结 )加红奇拉泽,苏联文艺菠陶译理论家,著灯代表作%文艺翻译和文学交诚。 中译本已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187),茶毅等译, )参见斯迎纳同上书,第238页, ②参见巴尔胡达罗尖同上书中译本,第30页。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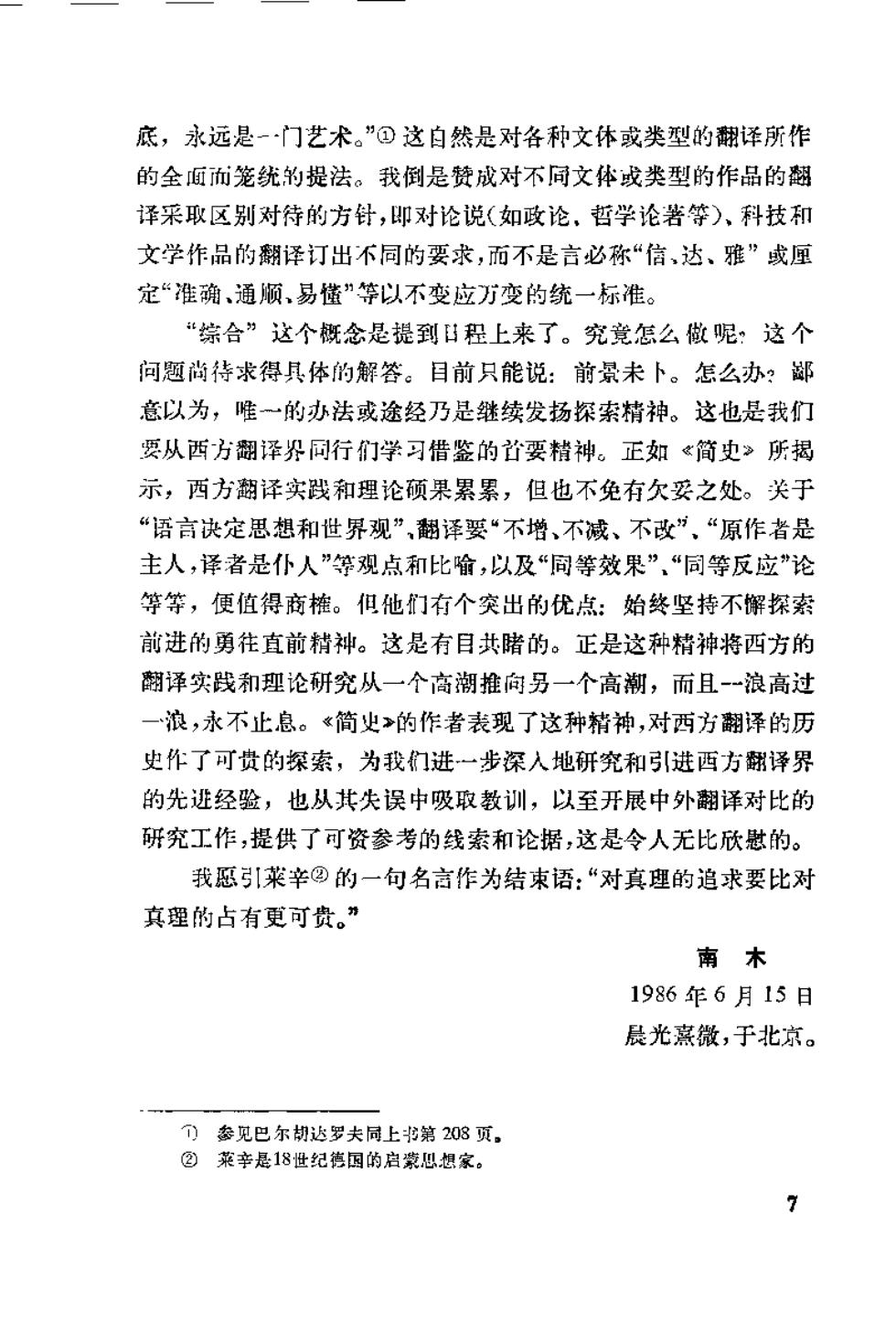
底,永远是一门艺术。”回这自然是对各种文休或类型的翻译所作 的全面而笼统的提法。我倒是赞成对不同文体或类型的作品的翻 译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即对论说(如政论、哲学论著等)、科技和 文学作品的翻译订出不同的要求,而不是言必称“信,达、雅”或厘 定“准确、通顺,易懂”等以不变应方变的统一标准。 “综合”这个概念是提到程上来了。究凳怎么做呢:这个 问题尚待求得具体的解答。目前只能说:前景未卜。怎么办?部 意以为,唯一的办法或途经乃是继续发扬探索精神。这也是我们 要从西方翻译界同行们学习借鉴的首要精神。正如心简更》所揭 示,西方翻译实践和理论硕果累累,但也不免有欠妥之处。关于 “语言决定思想和世界观”,翻译要“不增、不减、不改”、“原作者是 主人,译者是仆人”等观点和比喻,以及“同等效果”.“同等反应”论 等等,便值得商榷。但他们有个突出的优点:始终坚持不懈探索 前进的勇往直前精神。这是有目共睹的。正是这种精神将西方的 翻译实践和迎论研究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而且-一浪高过 一浪,永不止息。简史的作者表现了这种精神,对西方翻译的历 史作了可贵的探索,为我门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和进西方翻译界 的光进经验,也从其失误中吸取教训,以至开展中外翻译对比的 研究工作,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线索和论据,这是令人无比欣慰的。 我愿引莱辛②的一句名言作为结束语:“对真理的追求要比对 真避的占有更可贵。” 南木 1986年6月15日 晨光熹微,于北京。 ①参见巴尔胡达罗夫同上第208页, ②菜辛是18世纪德国的启蒙思想家。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