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为之奋斗终生的崇高目标是人类自身的解放,他们所创建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 人类解放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崇高目标及其所创建的学说,是人类文明史 的必然产物,也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19世纪4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已进人了成熟阶段,并以其成熟的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而孕育了成熟的无产阶级,因而为人类追求和实现自身解放提供了现实 条件。与此同时,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自然科学已经从分们别类地“搜集材 料”的科学而发展为系统地“整理材料”的科学,从而为证地理解自然、历史 和思维的运动过程提供了科学前提。而且,当时已获得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又 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前提。作为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的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两国思想家所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尤其是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 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通常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予以 表述,并在通常的誓学原理教科书中把它叙述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 观四个方面的理论内容。在这种表述中,主要包含两层含义:其一,马克思主义 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既不是唯心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心主义哲学),也不 是旧唯物主义哲学。在这种理解中,既是从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来界说马克思主 义哲学,也是从辩证法的历史发展来界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唯物主义的历史发 展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超越了古代的素朴的唯物主义和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 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就辩证法的历史发展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超越了古代 的素朴辩证法和近代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辩证唯物主义”。其二,“历史唯物主 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也就是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去解释和说明社会历史。在这种理解中,既要求人们以唯物主 义的观点去解释历史,也就是以社会存在去解释社会意识;又要求人们用辩证法 的观点去解释历史,也就是辩证地看待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历史发展过程与人 的创造活动等等的相互关系。 近些年来,哲学界又提出以“实践唯物主义”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 提法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论述:对实践的唯物主义 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 事物的现状。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 把他们所创立的哲学概括为“实践唯物主义”;另一种理解则认为,马克思恩格 斯在这里所讲的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而不是“实践唯物主义”:还有一种理 解认为,用“实践唯物主义”来概括和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马克思恩格斯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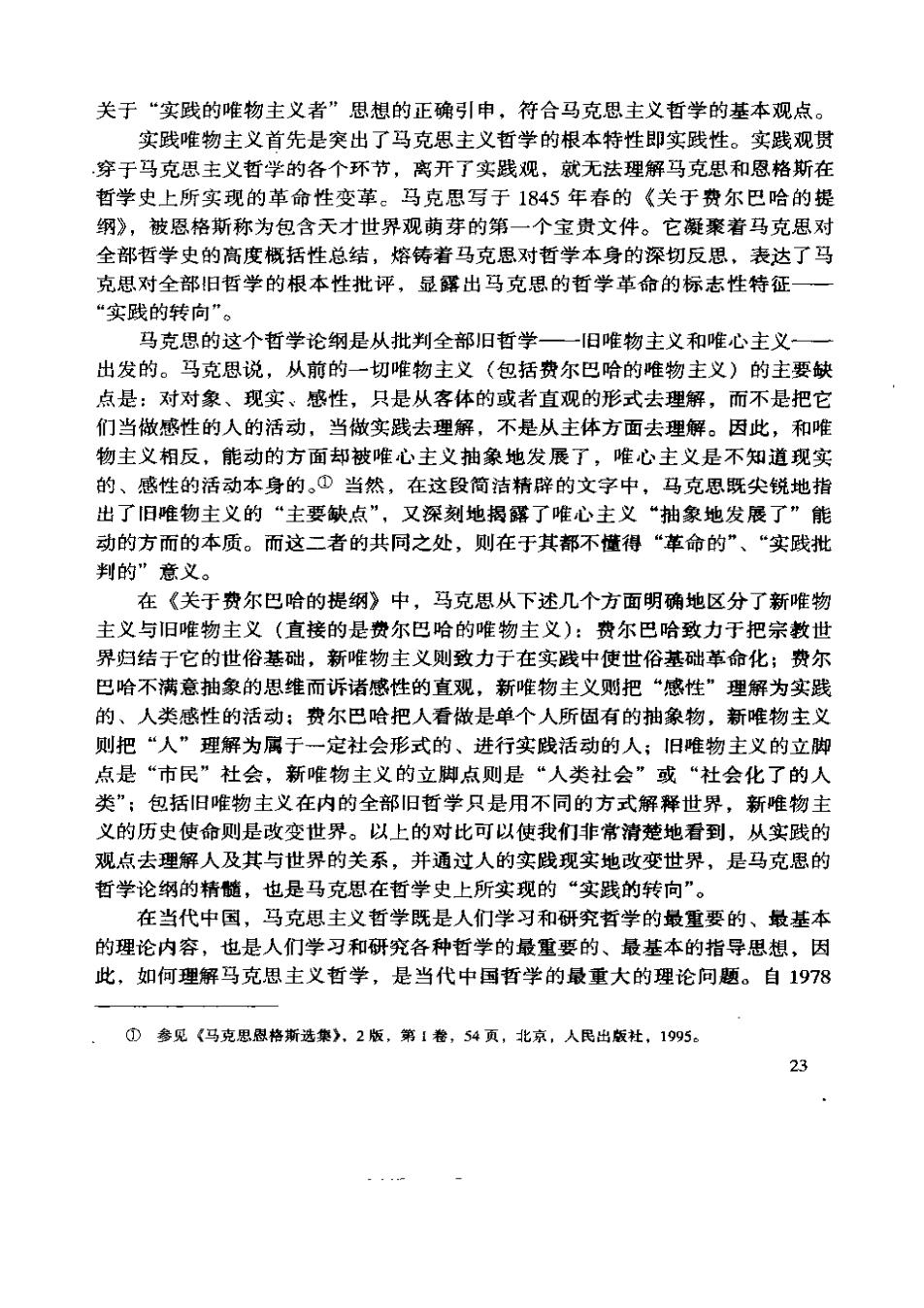
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思想的正确引申,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实践唯物主义首先是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性即实践性。实践观贯 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环节,离开了实践观,就无法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鸟克思写于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被恩格斯称为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宝贵文件。它凝聚着马克思对 全部哲学史的高度概括性总结,熔铸着马克思对哲学本身的深切反思,表达了马 克思对全部旧哲学的根本性批评,显露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标志性特征一 “实践的转向”。 马克思的这个哲学论纲是从批判全部旧哲学一一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一 出发的。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 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 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 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 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①当然,在这段简洁精辟的文字中,马克思既尖锐地指 出了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又深刻地揭露了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能 动的方而的本质。而这二者的共同之处,则在于其都不懂得“革命的”、“实践批 判的”意义。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从下述几个方面明确地区分了新唯物 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直接的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致力于把宗教世 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新唯物主义则致力于在实践中使世俗基础革命化;费尔 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新唯物主义则把“感性”理解为实践 的、人类感性的活动:费尔巴哈把人看做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新唯物主义 则把“人”理解为属于一定社会形式的、进行实践活动的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 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 类”;包括旧唯物主义在内的全部旧哲学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新唯物主 义的历史使命则是改变世界。以上的对比可以使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从实践的 观点去理解人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并通过人的实践现实地改变世界,是马克思的 哲学论纲的精髓,也是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实践的转向”。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人们学习和研究哲学的最重要的、最基本 的理论内容,也是人们学习和研究各种哲学的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因 此,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最重大的理论问题。自1978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54页,化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

年以来,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整个社 会生活,发生了举世漏目的重大变革。作为这种重大变革的理论表征,当代中国 的哲学承担起推进社会的解放思想和实现自身的思想解放的双重使命,已经和正 在经历着自身的变革。 当代中国的哲学改革,首先是在哲学原理内部形成了以变革通行几十年的哲 学教科书体系为基本指向和主要任务的哲学改革的潮流。这场哲学改革的出发点 和归宿点,是重新理解和重新建构马克恩主义哲学体系。这场哲学改革的理论重 点,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 性与客观性、自由与必然、历史规律与人的历史活动等哲学所探索的一系列重大 的关系问题,并以这些重新理解的重大问题为基础去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这场哲学改革的现实基础,在于当代人类的社会实践、特别是当代中国改革开 放的社会实践,已经和正在变革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它要求 哲学理论地表征这种时代性的变革,并理想性地塑造和引导这种时代性的变 革。 在哲学原理方面实现教科书体系改革的同时,包括中外哲学史在内的各个哲 学分支学科也出现了自身的改革,并从而深化了哲学原理的教科书改革。西方哲 学领域在翻译和评述现代西方哲学论著的基础上,逐步地从研究对象自身出发, 把一系列新的哲学范畴、新的哲学问题和新的哲学提问方式渗透到哲学理论探索 之中,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中国哲学领域以介绍和评 论现代新儒学为突破口,对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利弊得失进行反 思,探索“返本开新”、“融会中西”的途径与意义,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 国传统哲学的对话。 80年代的哲学改革,从其根本的指向性上看,是以新的教科书体系取代旧 的教科书体系,也就是重构教科书体系。进人9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则在理论 探索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转向。这突出地表现在,不是以争论教科书的利弊得失 和如何重构教科书体系为研究的出发点,而是把教科书作为某种退人背景的理论 框架,从现实生活或现代哲学中提出问题,形成了由“体系意识”到“问题意 识”的转换,“元哲学问题”、“人的存在方式问题”、“社会发展问题”、“两大思 潮问题”、“中西文化问题”成为90年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这些源于现 代社会生活的哲学问题,不断地开拓了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新领域,从而为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研究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在80年代以前,哲学的各个学科处于界限分明、壁垒森严、互不介人的状 态,在80年代反思教科书的哲学改革过程中,这种状况虽有所改变,但仍然是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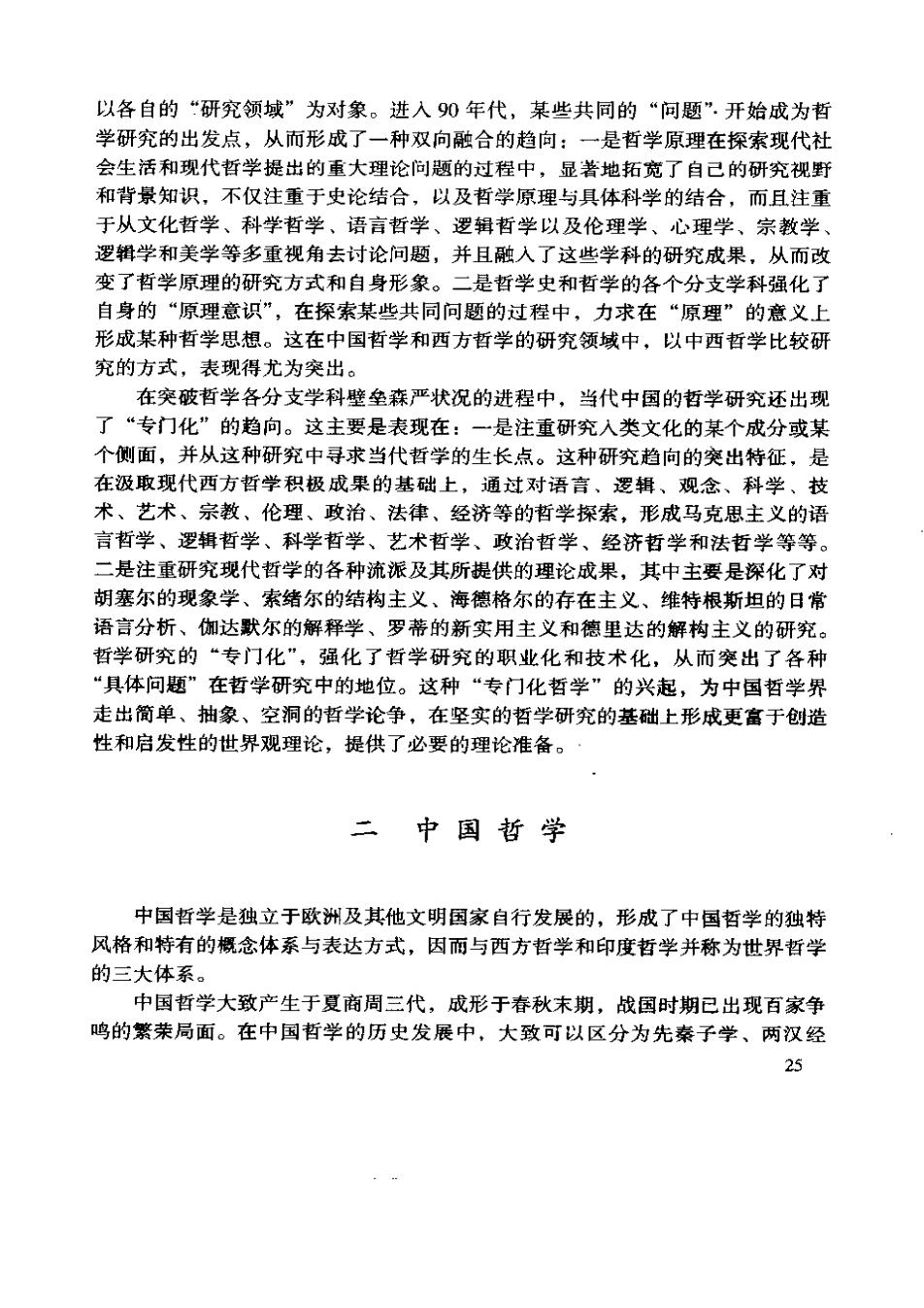
以各自的“研究领域”为对象。进入0年代,某些共同的“问题”.开始成为哲 学研究的出发点,从而形成了一种双向融合的趋向:一是哲学原理在探索现代社 会生活和现代哲学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的过程中,显著地拓宽了自己的研究视野 和背景知识,不仅注重于史论结合,以及哲学原理与具体科学的结合,而且注重 于从文化哲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以及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学、 逻辑学和美学等多重视角去讨论问题,并且融入了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从而改 变了哲学原理的研究方式和自身形象。二是哲学史和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强化了 自身的“原理意识”,在探索某些共同问题的过程中,力求在“原理”的意义上 形成某种哲学思想。这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中,以中西哲学比较研 究的方式,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突破哲学各分支学科壁垒森严状况的进程中,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还出现 了“专门化”的趋向。这主要是表现在:一是注重研究入类文化的某个成分或某 个侧面,并从这种研究中寻求当代哲学的生长点。这种研究趋向的突出特征,是 在汲取现代西方哲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语言、逻辑、观念、科学、技 术、艺术、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经济等的哲学探索,形成马克思主义的语 言哲学、逻辑哲学、科学哲学、艺术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和法哲学等等。 二是注重研究现代哲学的各种流派及其所提供的理论成果,其中主要是深化了对 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日常 语言分析、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研究。 哲学研究的“专门化”,强化了哲学研究的职业化和技术化,从而突出了各种 “具体问题”在哲学研究中的地位。这种“专门化哲学”的兴起,为中国哲学界 走出简单、抽象、空洞的哲学论争,在坚实的哲学研究的基础土形成更富于创造 性和启发性的世界观理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是独立于欧洲及其他文明国家自行发展的,形成了中国哲学的独特 风格和特有的概念体系与表达方式,因而与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并称为世界哲学 的三大体系。 中国哲学大致产生于夏商周三代,成形于春秋末期,战国时期已出现百家争 鸣的繁荣局面。在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中,大致可以区分为先秦子学、两汉经 25

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近代新学等主要阶段。“五四” 运动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不可遏止的生机而传播于中国,形形色色 的西方哲学思潮如放闸之水而流行于学界,中国传统哲学则在时代的巨变中而被 重新阐释、提倡。社会生活的空前震荡,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中西文化的猛烈 撞击,新旧学术的砥砺契合,由此便构成了思路各异、学派纷呈、各具规模、论 战迭起的现代中国哲学。80年代以来,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当代中国哲学承担起了推进社会的解放思想与实 现哲学的思想解放的双重使命,实现了当代中国哲学的繁荣与发展。 中华民族是富于哲学智慧的民族。日本学者西周译西名“爱智” (philosophia)为“哲学”,显然是利用了中国表达智慧的“哲”字。然而,“哲 学”虽为“爱智”之学的译名,“中国哲学”的“哲学”却不能完全从西方的 “爱智”的原义上去理解。中国哲学亦称形而上学,“形而上学”语出《易·系辞》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由此区分了形上与形下,道与器。就《易 传》而言,形而上学乃天地、阴阳、动静之学,亦即宇宙万物之道。道是中国哲 学的终极性范畴,也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终极境界。中国哲学以“究天人之际”为 要务,是以天人关系来表达思存、主客这一哲学主题的。但天人问题并不等同于 思存、主客问题,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理论意义,因而没有造成思存、主 客的分裂与对峙。哲学以字宙人生为主要对象,中外哲学概莫能外。而中国哲学 却着力于人生的探索。但中国哲学不是弧立地研究人,而是在天人之际追寻人之 为人的根据,所以人孤立起来看并不是哲学范畴,要想使人进人哲学的思考系, 必须使之升华,追寻人人之人,非个人之人。中国哲学讲求“身以载道”,他自 身就是他的哲学的实践者,不论儒、道、释所追求的仁、道、真如有何不同,皆 能与道同体,达一最高境界。因而中国哲学之本体,不是脱离人生的孤立自存的 轴象物,乃人生道德修炼之所得。① 关于中国哲学,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有过多方面的系统论述。探索这些论 述,可以帮助我们体会“中国哲学的精神”。 冯友兰认为,“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 中的地位相比”②,因而哲学一直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他具体地指出, 中国人“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 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欣赏了超道德价值,而按照哲学去生活,也 ①参见陈庆坤主编:《中国哲学史通》,1~2、14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2版,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