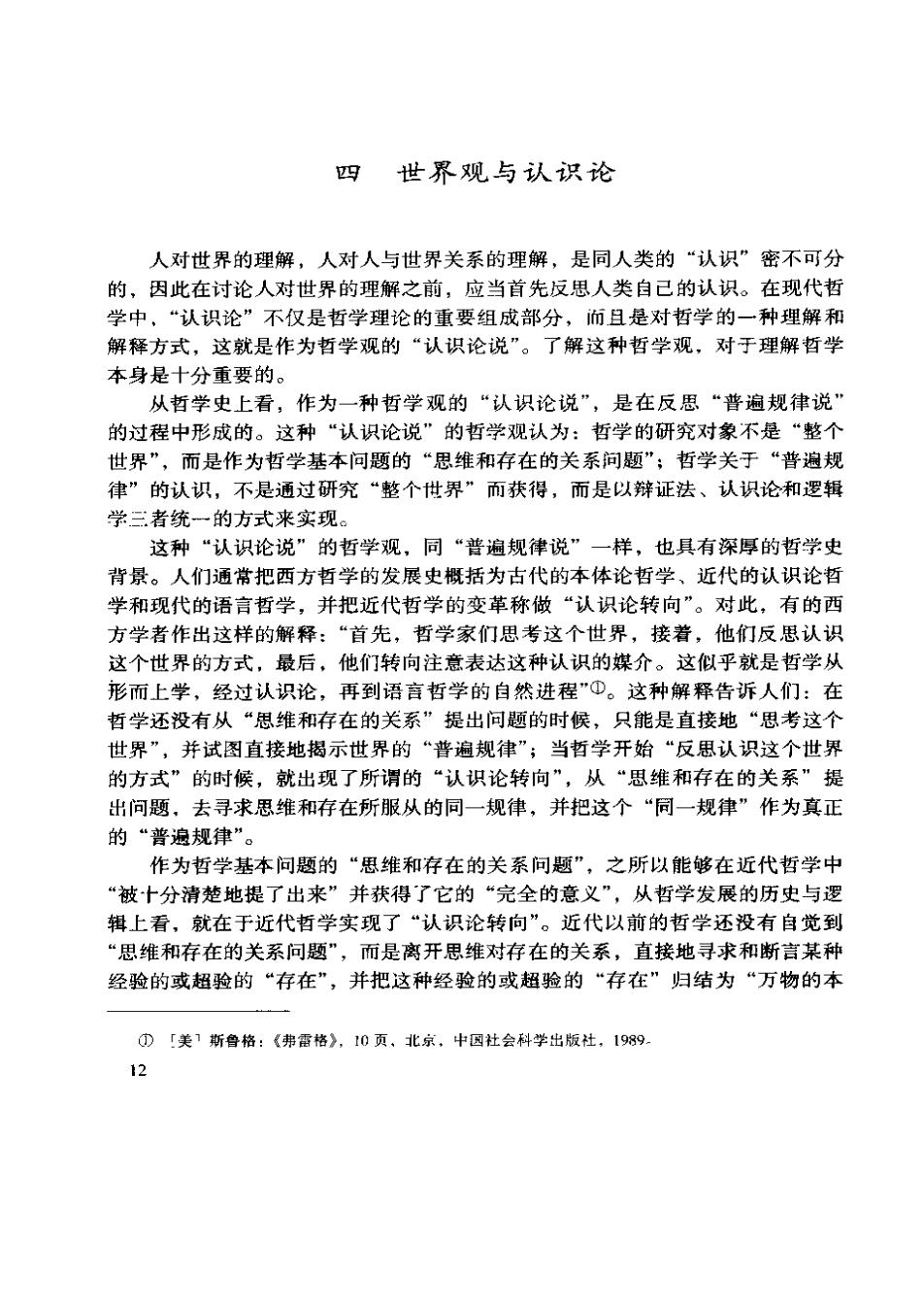
四 世界观与认识论 人对世界的理解,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是同人类的“认识”密不可分 的,因此在讨论人对世界的理解之前,应当首先反思人类自己的认识。在现代哲 学中,“认识论”不仅是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对哲学的一种理解和 解释方式,这就是作为哲学观的“认识论说”。了解这种哲学观,对于理解哲学 本身是十分重要的。 从哲学史上看,作为一种哲学观的“认识论说”,是在反思“普遍规律说” 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认识论说”的哲学观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整个 世界”,而是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关于“普遍规 律”的认识,不是通过研究“整个世界”而获得,而是以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 学二三者统一的方式来实现。 这种“认识论说”的哲学观,同“普遍规律说”一样,也具有深厚的哲学史 背景。人们通常把西方哲学的发展史概括为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近代的认识论哲 学和现代的语言哲学,并把近代哲学的变革称做“认识论转向”。对此,有的西 方学者作出这样的解释:“首先,哲学家们思考这个世界,接着,他们反思认识 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这似乎就是哲学从 形而上学,经过认识论,再到语哲学的自然进程”①。这种解释告诉人们:在 哲学还没有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提出问题的时候,只能是直接地“思考这个 世界”,并试图直接地揭示世界的“普遍规律”;当哲学开始“反思认识这个世界 的方式”的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认识论转向”,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提 出问题,去寻求思维和存在所服从的同一规律,并把这个“同一规律”作为真正 的“普遍规律”。 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能够在近代哲学中 “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并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从哲学发展的历史与逻 辑上看,就在于近代哲学实现了“认识论转向”。近代以前的哲学还没有自觉到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离开思维对存在的关系,直接地寻求和断言某种 经验的或超验的“存在”,并把这种经验的或超验的“存在”归结为“万物的本 ①「美1斯鲁格:《弗雷格》,1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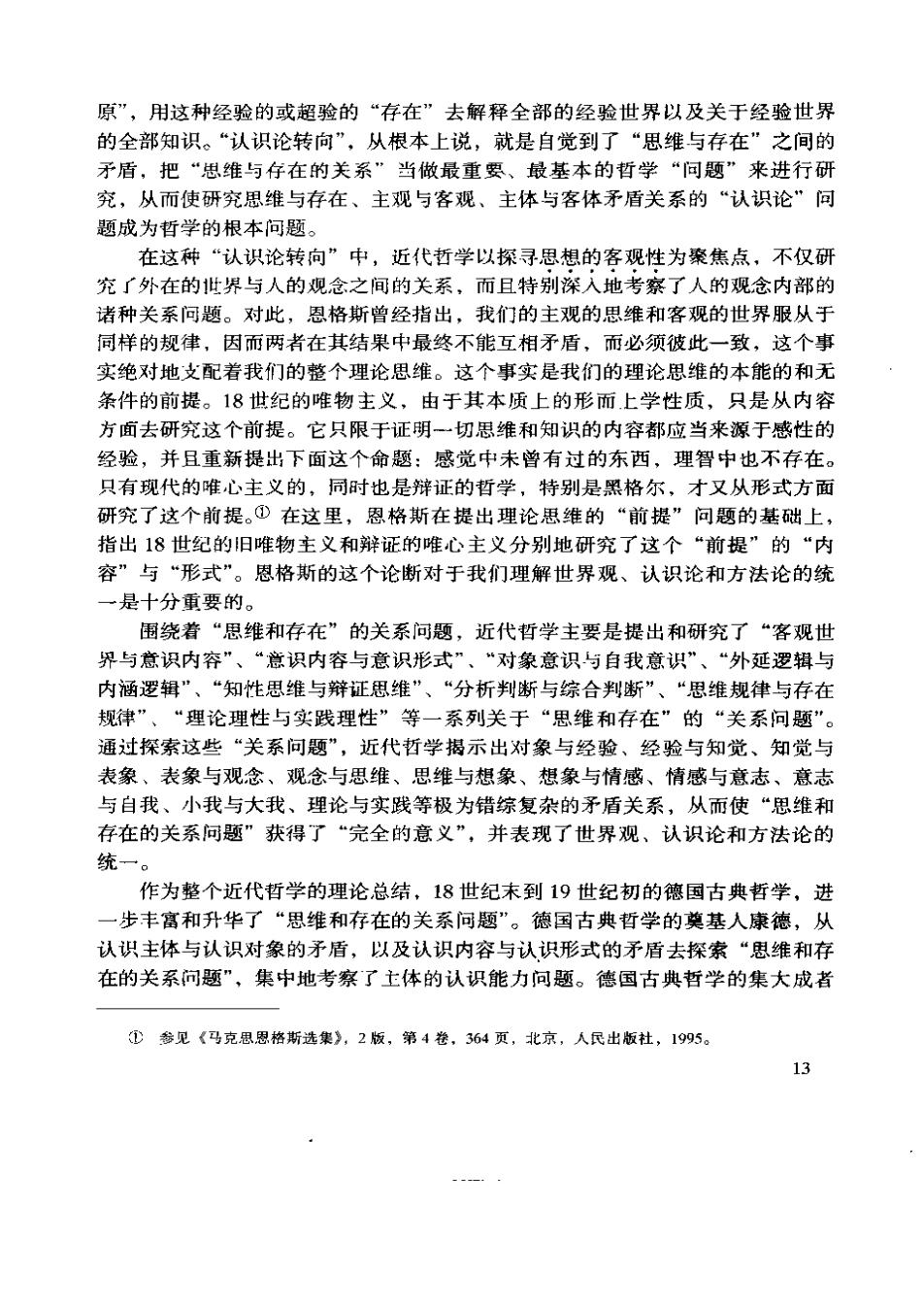
原”,用这种经验的或超验的“存在”去解释全部的经验世界以及关于经验世界 的全部知识。“认识论转向”,从根本上说,就是自觉到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 矛盾,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当做最重要、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来进行研 究,从而使研究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矛盾关系的“认识论”问 题成为哲学的根本问题。 在这种“认识论转向”中,近代哲学以探寻思想的客观性为聚焦点,不仅研 究了外在的世界与人的观念之间的关系,而且特别深入地考察了人的观念内部的 诸种关系问题。对此,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 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其结果中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 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 条件的前提。18世纪的唯物主义,由于其本质上的形而上学性质,只是从内容 方面去研究这个前提。它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来源于感性的 经验,并且重新提出下面这个命题: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理智中也不存在。 只有现代的唯心主义的,同时也是辩证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才又从形式方面 研究了这个前提。①在这里,恩格斯在提出理论思维的“前提”问题的基础上, 指出18世纪的旧唯物主义和辩证的唯心主义分别地研究了这个“前提”的“内 容”与“形式”。恩格斯的这个论断对于我们理解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 一是十分重要的。 围绕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近代哲学主要是提出和研究了“客观世 界与意识内容”、“意识内容与意识形式”、“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外延逻辑与 内涵逻辑”、“知性思维与辩证思维”、“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思维规律与存在 规律”、“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等一系列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通过探索这些“关系问题”,近代哲学揭示出对象与经验、经验与知觉、知觉与 表象、表象与观念、观念与思维、思维与想象、想象与情感、情感与意志、意志 与自我、小我与大我、理论与实践等极为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从而使“思维和 存在的关系问题”获得了“完全的意义”,并表现了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 统一。 作为整个近代哲学的理论总结,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进 一步丰富和升华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从 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矛盾,以及认识内容与认识形式的矛盾去探索“思维和存 在的关系问题”,集中地考察了主体的认识能力问题。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 ①参见《马克思思格斯选集》,2版,第4卷,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黑格尔,则从思维的矛盾运动中去论证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又从思维的建构与 反思的对立统一中去展现思维的矛盾运动,力图在辩证法的“本体论”、“认识 论”和“逻辑学”的统一中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费尔巴哈在批判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过程中,则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归结为思维与“感性存 在”的关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些方近代哲学所达到的关于哲学基本 问题的认识水平,也就是西方近代哲学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使哲学基本问题获 得的“完全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现实 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以实践论的思维方式去回答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 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实现了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对此,我】在这 里可以简要地作出这样的概括: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思维自觉反映存在 运动的规律凝聚着、积淀着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所创建的全部科学反映世界的 认识成果,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因此,在其客观内 容和普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 的理论,即哲学世界观: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认识和实践的主体与客体交互作 用的丰富关系及其历史发展来研究思维自觉反映存在运动的规律,为人类的全部 历史活动提供认识基础,因此,就其研究对象和理论性质上看,它就是关于思维 与存在统一规律的理论,即哲学认识论;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思维自觉 反映存在运动的规律,既是对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总结,又是思维自觉地向存在 接近和通近的方法,因此,就其理论价值和社会功能上看,它又是人类认识世界 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即哲学方法论。这就是我们从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的统一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解释。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苏联的凯德洛夫、柯普宁和伊里因科夫等哲学家, 以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和列宁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一致 的观点为出发点,以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为背景,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认 识论说”的哲学观,并以这种哲学观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自80年代以 来,“认识论说”的哲学观在我国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学者试图以列宁 《哲学笔记》中关于辩证法就是认识论,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一致, 哲学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哲学与哲学史的统一,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基本 知识领域等重要论述,去反思“普遍规律说”的哲学观。从总体上说,人们已经 认识到,需要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中去理解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 学。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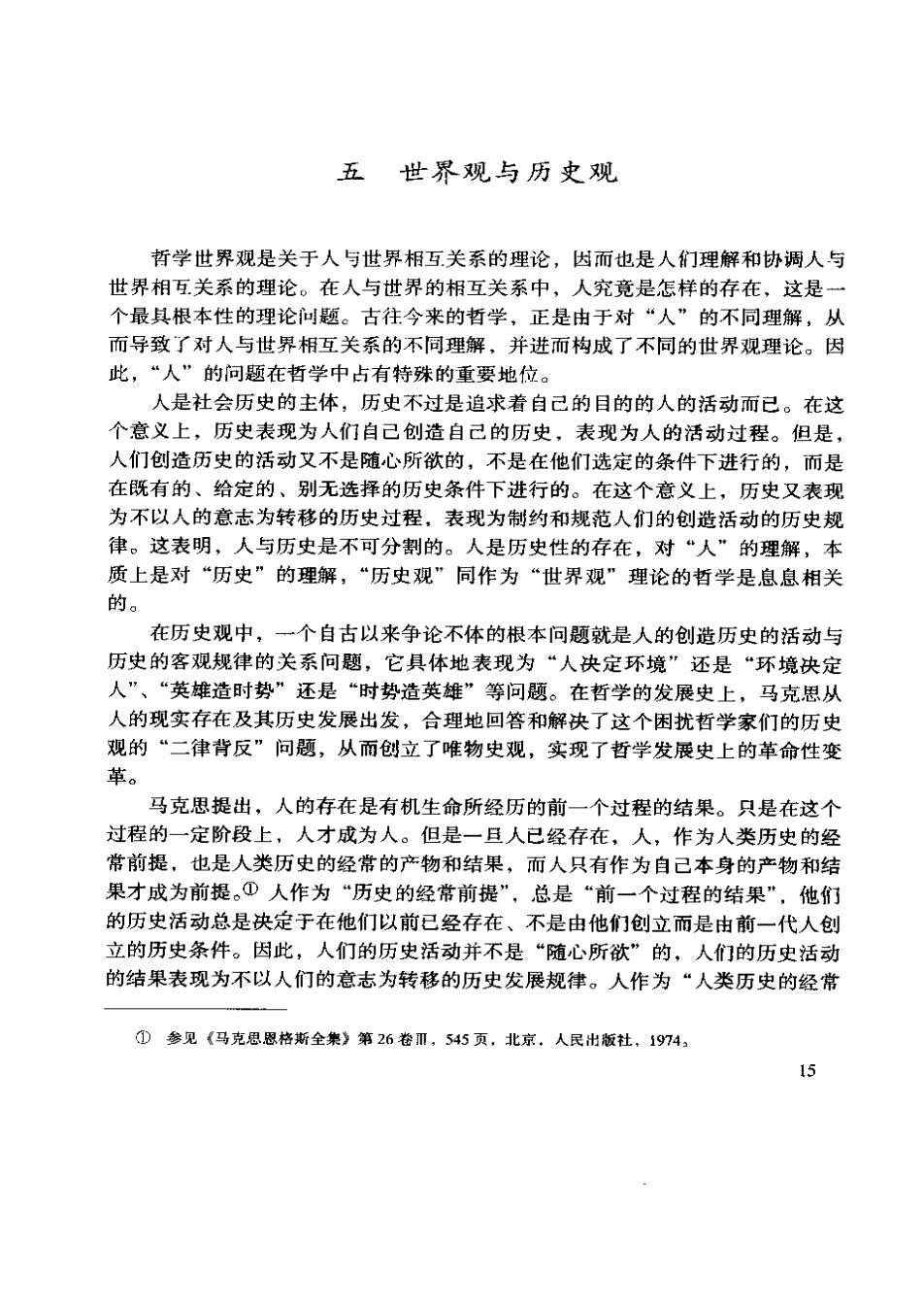
五世界观与历史观 哲学世界观是关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理论,因而也是人们理解和协调人与 世界相互关系的理论。在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人究竟是怎样的存在,这是一 个最具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古往今来的哲学,正是由于对“人”的不同理解,从 而导致了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并进而构成了不同的世界观理论。因 此,“人”的问题在哲学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这 个意义上,历史表现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表现为人的活动过程。但是, 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又不是随心所欲的,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进行的,而是 在既有的、给定的、别无选择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又表现 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过程,表现为制约和规范人们的创造活动的历史规 律。这表明,人与历史是不可分割的。人是历史性的存在,对“人”的理解,本 质上是对“历史”的理解,“历史观”同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是息息相关 的。 在历史观中,一个自古以来争论不体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的创造历史的活动与 历史的客观规律的关系问题,它具体地表现为“人决定环境”还是“环境决定 人”、“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等问题。在哲学的发展史上,马克思从 人的现实存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合理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个困忧哲学家们的历史 观的“二律背反”问题,从雨创立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哲学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 革。 马克思提出,人的存在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只是在这个 过程的一定阶段上,人才成为人。但是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 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 果才成为前提。①人作为“历史的经常前提”,总是“前一个过程的结果”,他们 的历史活动总是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 立的历史条件。因此,人们的历史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人们的历史活动 的结果表现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5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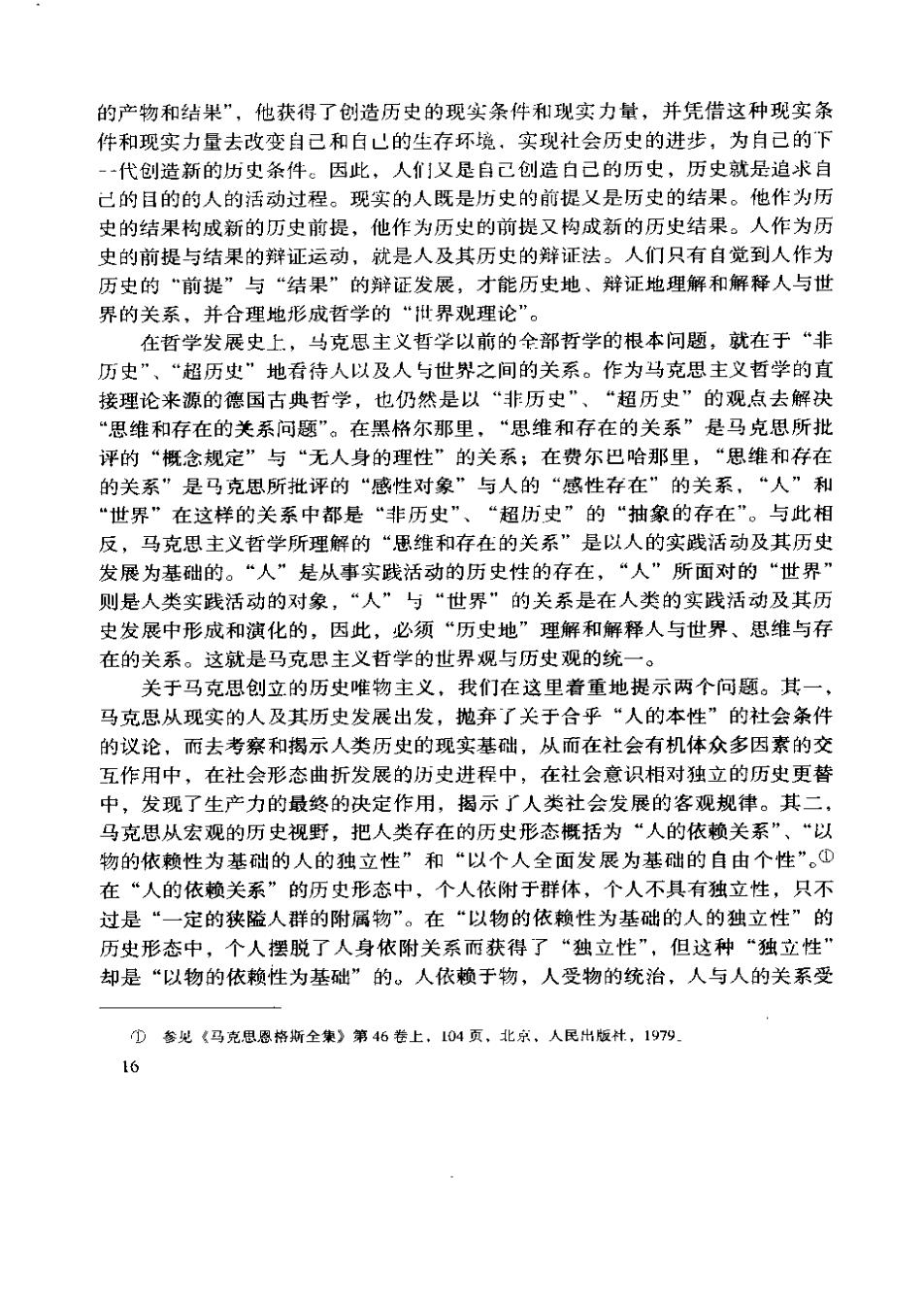
的产物和结果”,他获得了创造历史的现实条件和现实力量,并凭借这种现实条 件和现实力量去改变自已和白心的生存环境,实现社会历史的进步,为自已的下 -·代创造新的历史条件。因此,人又是自己创造白已的历史,历史就是追求自 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现实的人既是历史的前提又是历史的结果。他作为历 史的结果构成新的历史前提,他作为历史的前提又构成新的历史结果。人作为历 史的前提与结果的辩证运动,就是人及其历史的辩证法。人们只有自觉到人作为 历史的“前提”与“结果”的辩证发展,才能历史地、辩证地理解和解释人与世 界的关系,并合理地形成哲学的“世界观理论”。 在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全部哲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非 历史”、“超历史”地看待人以及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 接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也仍然是以“非历史”、“超历史”的观点去解决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黑格尔那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马克思所批 评的“概念规定”与“无人身的理性”的关系;在费尔巴哈那里,“思维和存在 的关系”是马克思所批评的“感性对象”与人的“感性存在”的关系,“人”和 “世界”在这样的关系中都是“非历史”、“超历史”的“抽象的存在”。与此相 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理解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以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 发展为基础的。“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的历史性的存在,“人”所面对的“世界” 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历 史发展中形成和演化的,因此,必须“历史地”理解和解释人与世界、思维与存 在的关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统一。 关于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在这里着重地提示两个问题。其一, 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 的议论,而去考察和揭示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从而在社会有机体众多因素的交 互作用中,在社会形态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社会意识相对独立的历史更替 中,发现了生产力的最终的决定作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二 马克思从宏观的历史视野,把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概括为“人的依赖关系”、“以 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① 在“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形态中,个人依附于群体,个人不具有独立性,只不 过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 历史形态中,个人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获得了“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 却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依赖于物,人受物的统治,人与人的关系受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