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而在近代哲学中,则不仅“十分清楚”地提出 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且使之获得了“完全的意义”。 “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何者为“本原”、何者为“派 生”、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时间先在性”问题。在“时间先 在性”的意义上.,精神和物质的对立是僵硬的,其先后顺序是不能颠倒的,即: 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是精神的“本 原”,精神则是物质的“派生物”。 应当看到,强调“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中的重 大意义,是十分重要的。这有助于人们鲜明地区分哲学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但是,简单地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归结为“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却会导 致对哲学的简单化、经验化的理解,以至于丢弃哲学的“反思”的思维方式。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较之“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其重要特征在于,其不 仅具有“精神和物质”关系的“时间先在性”问题,而且具有超越“精神和物 质”关系的“逻辑先在性”问题。这是二者的重大区别。在“精神和物质”的 “时间先在性”问题中,精神和物质二者的关系是不可变易的,即“物质”是 “本原性”的存在。而在“思维和存在”的“逻辑”关系中,则表现出极为丰富 和极为复杂的矛盾关系。 显而易见,“存在”这个范畴不等同于“物质”这个范畴,它不仅包括“物 质”的存在,也包括“精神”的存在。用近代哲学的方式说,“存在”不仅是 “意识外的存在”,而且是“意识界的存在”。与这种“存在”范畴相对应,“思维 和存在”的关系,至少就应当包括“精神和物质(意识外的存在)”的关系,也 包括“精神和精神(意识界的存在)”的关系。 同样,“思维”这个范畴也不等同于“精神”或“意识”。从狭义上看,“思 维”似乎只是“精神”或“意识”的一部分,但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意 义上,“思维”就不仅是指“意识的内容”,而且也指“意识的形式”;不仅是指 关于思维对象的“对象意识”,而且也指构成、把握、统摄和反省“对象意识” 的“自我意识”;不仅是指“思想的内容”,而且也指“思想的活动”。 这表明,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所自觉到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 题”中,不仅“存在”范畴具有相对性和多义性,与之相对应的“思维”范畴也 具有相对性和多义性。正是这种“思维和存在”的相对性和多义性,构成了“思 维和存在”之间的极为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并从而形成了哲学的极其丰富多彩 的理论内容。如果把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简单地、直 接地归结为和等同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就会忽视甚至无视“思维和存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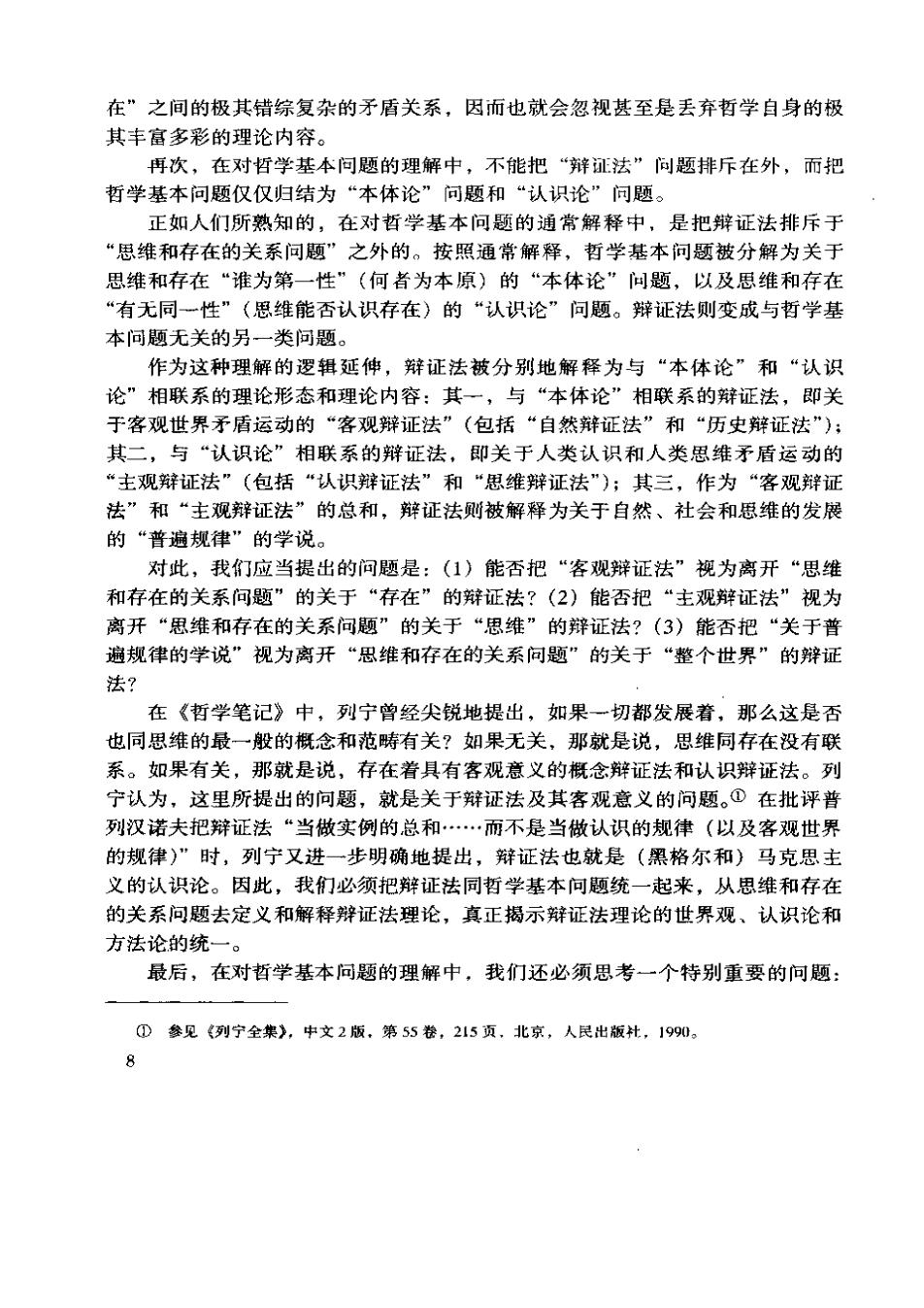
在”之间的极其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因而也就会忽视甚至是丢弃哲学自身的极 其丰富多彩的理论内容。 再次,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中,不能把“辩证法”问题排斥在外,而把 哲学基本问题仅仅归结为“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通常解释中,是把辩证法排斥于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外的。按照通常解释,哲学基本问题被分解为关于 思维和存在“谁为第一性”(何者为本原)的“本体论”问题,以及思维和存在 “有无同一性”(思维能否认识存在)的“认识论”问题。辩证法则变成与哲学基 本问题无关的另一类问题。 作为这种理解的逻辑延伸,辩证法被分别地解释为与“本体论”和“认识 论”相联系的理论形态和理论内容:其一,与“本体论”相联系的辩证法,即关 于客观世界矛盾运动的“客观辩证法”(包括“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 其二,与“认识论”相联系的辩证法,即关于人类认识和人类思维矛盾运动的 “主观辩证法”(包括“认识辩证法”和“思维辩证法”);其三,作为“客观辩证 法”和“主观辩证法”的总和,辩证法则被解释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发展 的“普遍规律”的学说。 对此,我们应当提出的问题是:(1)能否把“客观辩证法”视为离开“思维 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关于“存在”的辩证法?(2)能否把“主观辩证法”视为 离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关于“思维”的辩证法?(3)能否把“关于普 遍规律的学说”视为离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关于“整个世界”的辩证 法? 在《哲学笔记》中,列宁曾经尖锐地提出,如果一切都发展着,那么这是否 也同思维的最一般的概念和范畴有关?如果无关,那就是说,思维同存在没有联 系。如果有关,那就是说,存在着具有客观意义的概念辩证法和认识辩证法。列 宁认为,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就是关于辩证法及其客观意义的问题。①在批评普 列汉诺夫把辩证法“当做实例的总和…而不是当做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 的规律)”时,列宁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 义的认识论。因此,我们必须把辩证法同哲学基本问题统一起来,从思维和存在 的关系问题去定义和解释辩证法理论,真正揭示辩证法理论的世界观、认识论和 方法论的统一。 最后,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中,我们还必须思考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①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55卷,2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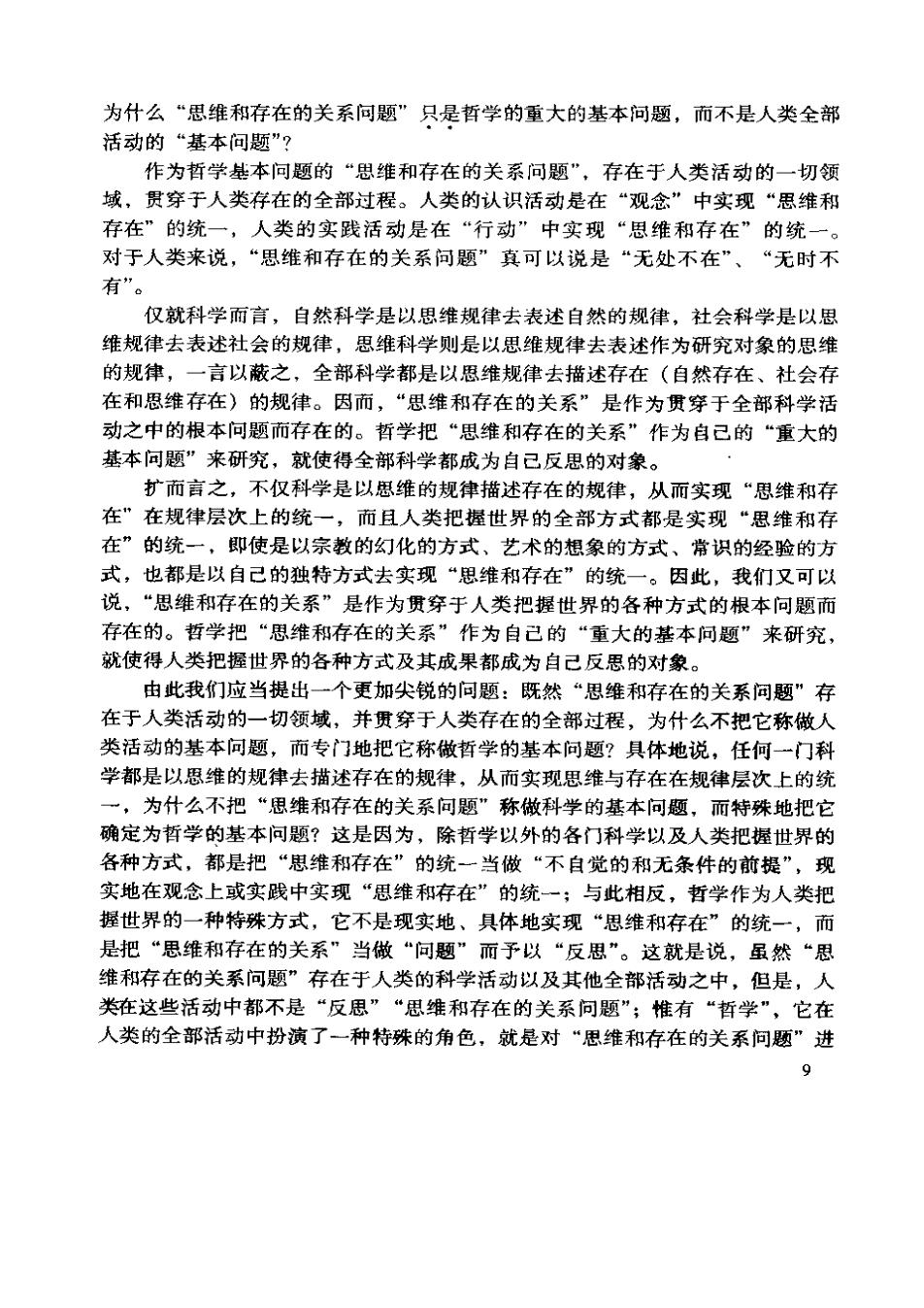
为什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而不是人类全部 活动的“基本问题”? 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存在于人类活动的一切领 域,贯穿于人类存在的全部过程。人类的认识活动是在“观念”中实现“思维和 存在”的统一,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在“行动”中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 对于人类来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真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 有”。 仅就科学而言,自然科学是以思维规律去表述自然的规律,社会科学是以思 维规律去表述社会的规律,思维科学则是以思维规律去表述作为研究对象的思维 的规律,一言以蔽之,全部科学都是以恩维规律去描述存在(自然存在、社会存 在和思维存在)的规律。因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作为贯穿于全部科学活 动之中的根本问题而存在的。哲学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自己的“重大的 基本问题”来研究,就使得全部科学都成为自己反思的对象。 扩而言之,不仅科学是以思维的规律描述存在的规律,从而实现“思维和存 在”在规律层次上的统一,而且人类把握世界的全部方式都是实现“思维和存 在”的统一,即使是以宗教的幻化的方式、艺术的想象的方式、常识的经验的方 式,也都是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去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因此,我们又可以 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作为贯穿于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的根本问题而 存在的。哲学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自已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来研究, 就使得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及其成果都成为自己反思的对象。 由此我们应当提出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既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存 在于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并贯穿于人类存在的全部过程,为什么不把它称做人 类活动的基本问题,而专门地把它称做哲学的基本问题?具体地说,任何一门科 学都是以恩维的规律去描述存在的规律,从而实现思维与存在在规律层次上的统 一,为什么不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称做科学的基本问题,而特殊地把它 确定为哲学的基本问题?这是因为,除哲学以外的各门科学以及人类把握世界的 各种方式,都是把“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当做“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现 实地在观念上或实践中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与此相反,哲学作为人类把 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它不是现实地、具体地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而 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做“问题”而予以“反思”。这就是说,虽然“思 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存在于人类的科学活动以及其他全部活动之中,但是,人 类在这些活动中都不是“反思”“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惟有“哲学”,它在 人类的全部活动中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就是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进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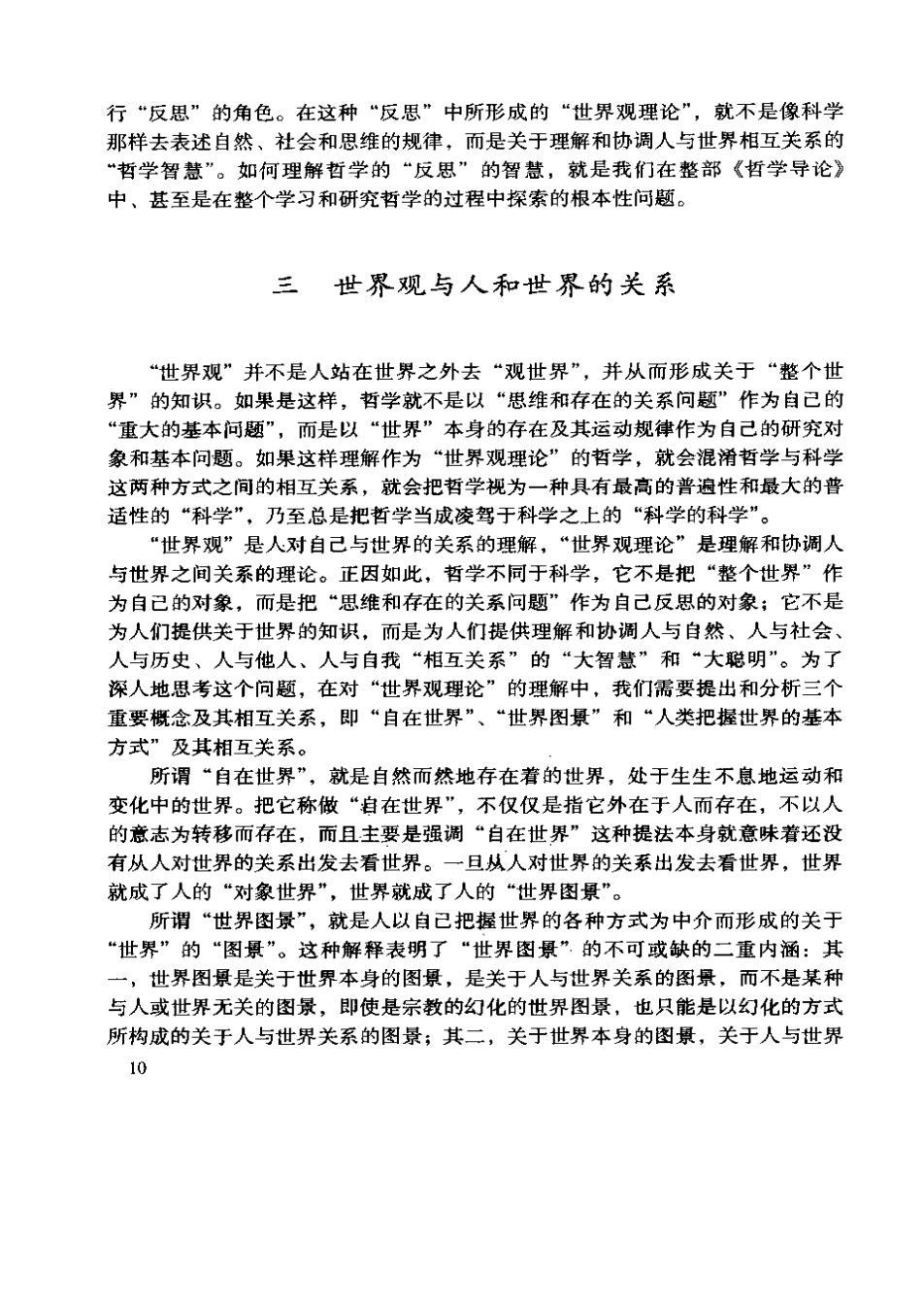
行“反思”的角色。在这种“反思”中所形成的“世界观理论”,就不是像科学 那样去表述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规律,而是关于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 “哲学智慧”。如何理解哲学的“反思”的智慧,就是我们在整部《哲学导论》 中、甚至是在整个学习和研究哲学的过程中探素的根本性问题。 三世界观与人和世界的关系 “世界观”并不是人站在世界之外去“观世界”,并从而形成关于“整个世 界”的知识。如果是这样,哲学就不是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已的 “重大的基本问题”,而是以“世界”本身的存在及其运动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 象和基本问题。如果这样理解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就会混淆哲学与科学 这两种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会把哲学视为一种具有最高的普遍性和最大的普 适性的“科学”,乃至总是把哲学当成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 “世界观”是人对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世界观理论”是理解和协调人 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理论。正因如此,哲学不同于科学,它不是把“整个世界”作 为自已的对象,而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反思的对象;它不是 为人们提供关于世界的知识,而是为人们提供理解和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人与历史、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相互关系”的“大智慧”和“大聪明”。为了 深人地思考这个问题,在对“世界观理论”的理解中,我们需要提出和分析三个 重要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即“自在世界”、“世界图景”和“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 方式”及其相互关系。 所谓“自在世界”,就是自然而然地存在着的世界,处于生生不息地运动和 变化中的世界。把它称做“自在世界”,不仅仅是指它外在于人而存在,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而且主要是强调“自在世界”这种提法本身就意味着还没 有从人对世界的关系出发去看世界。一旦从人对世界的关系出发去看世界,世界 就成了人的“对象世界”,世界就成了人的“世界图景”。 所谓“世界图景”,就是人以自已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为中介而形成的关于 “世界”的“图景”。这种解释表明了“世界图景”的不可或缺的二重内涵:其 一,世界图景是关于世界本身的图景,是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图景,而不是某种 与人或世界无关的图景,即使是宗教的幻化的世界图景,也只能是以幻化的方式 所构成的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图景;其二,关于世界本身的图景,关于人与世界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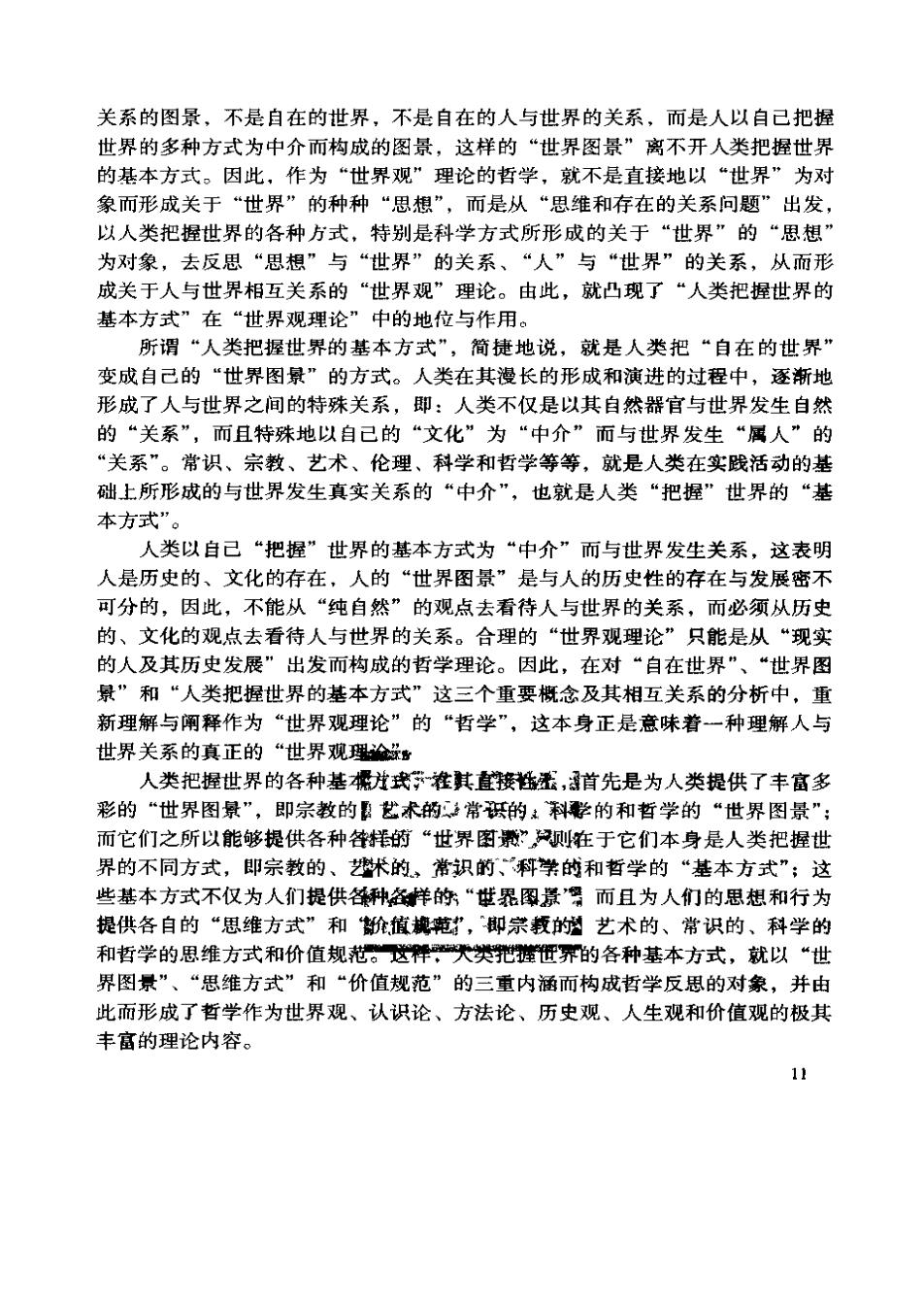
关系的图景,不是自在的世界,不是自在的人与世界的关系,而是人以自己把握 世界的多种方式为中介而构成的图景,这样的“世界图景”离不开人类把握世界 的基本方式。因此,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就不是直接地以“世界”为对 象而形成关于“世界”的种种“思想”,而是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出发, 以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特别是科学方式所形成的关于“世界”的“思想” 为对象,去反思“思想”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形 成关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世界观”理论。由此,就凸现了“人类把握世界的 基本方式”在“世界观理论”中的地位与作用。 所谓“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简捷地说,就是人类把“自在的世界” 变成自己的“世界图景”的方式。人类在其漫长的形成和演进的过程中,逐渐地 形成了人与世界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人类不仅是以其自然器官与世界发生自然 的“关系”,而且特殊地以自己的“文化”为“中介”而与世界发生“属人”的 “关系”。常识、宗教、艺术、伦理、科学和哲学等等,就是人类在实践活动的基 础上所形成的与世界发生真实关系的“中介”,也就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 本方式”。 人类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为“中介”而与世界发生关系,这表明 人是历史的、文化的存在,人的“世界图景”是与人的历史性的存在与发展密不 可分的,因此,不能从“纯自然”的观点去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而必须从历史 的、文化的观点去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合理的“世界观理论”只能是从“现实 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而构成的哲学理论。因此,在对“自在世界”、“世界图 景”和“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这三个重要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中,重 新理解与阐释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这本身正是意味着一种理解人与 世界关系的真正的“世界观理冷好 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进武节稚其鞍进,通首先是为人类提供了丰富多 彩的“世界图景”,即宗教的芯术的常的利科学的和哲学的“世界图景”; 而它们之所以能够提供各种样的“世界菌素”在于它们本身是人类把握世 界的不同方式,即宗教的、术的,常识的、科学的和哲学的“基本方式”;这 些基本方式不仅为人们提供种样的“苹界军景'而且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提供各自的“思维方式”和值规范,即宗教的的艺术的、常识的、科学的 和哲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必释,犬类把征界的各种基本方式,就以“世 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三重内涵而构成哲学反思的对象,并由 此而形成了哲学作为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极其 丰富的理论内容。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