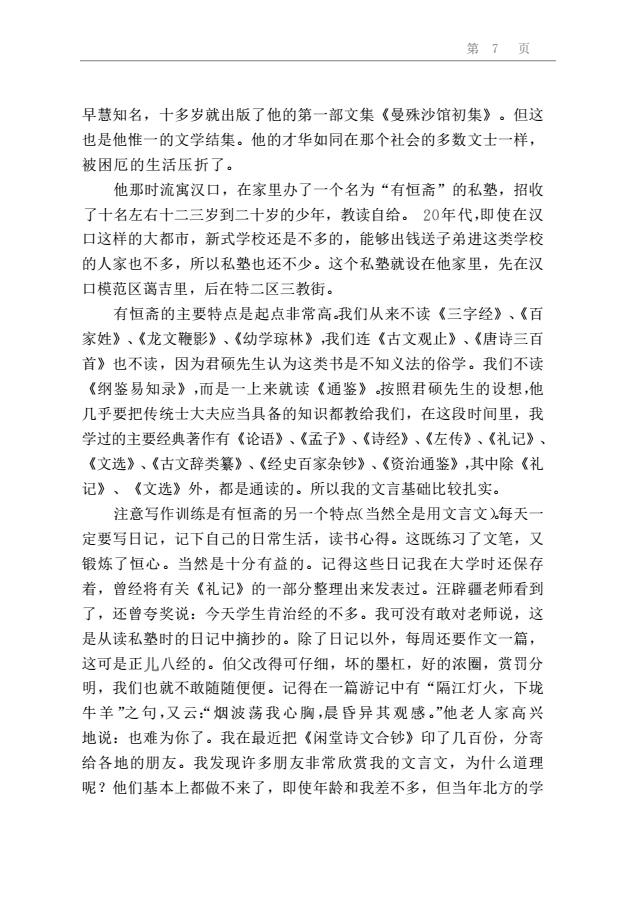
第7页 早慧知名,十多岁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集《曼殊沙馆初集》。但这 也是他惟一的文学结集。他的才华如同在那个社会的多数文士一样, 被困厄的生活压折了。 他那时流寓汉口,在家里办了一个名为“有恒斋”的私塾,招收 了十名左右十二三岁到二十岁的少年,教读自给。20年代,即使在汉 口这样的大都市,新式学校还是不多的,能够出钱送子弟进这类学校 的人家也不多,所以私塾也还不少。这个私塾就设在他家里,先在汉 口模范区蔼吉里,后在特二区三教街。 有恒斋的主要特点是起点非常高我们从来不读《三字经》、《百 家姓》、《龙文鞭影》、《幼学琼林》,我们连《古文观止》、《唐诗三百 首》也不读,因为君硕先生认为这类书是不知义法的俗学。我们不读 《纲鉴易知录》,而是一上来就读《通鉴》按照君硕先生的设想,他 几乎要把传统士大夫应当具备的知识都教给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我 学过的主要经典著作有《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礼记》、 《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资治通鉴》,其中除《礼 记》、《文选》外,都是通读的。所以我的文言基础比较扎实。 注意写作训练是有恒斋的另一个特点(当然全是用文言文每天 定要写日记,记下自己的日常生活,读书心得。这既练习了文笔,又 锻炼了恒心。当然是十分有益的。记得这些日记我在大学时还保存 着,曾经将有关《礼记》的一部分整理出来发表过。汪辟疆老师看到 了,还曾夸奖说:今天学生肯治经的不多。我可没有敢对老师说,这 是从读私塾时的日记中摘抄的。除了日记以外,每周还要作文一篇,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伯父改得可仔细,坏的墨杠,好的浓圈,赏罚分 明,我们也就不敢随随便便。记得在一篇游记中有“隔江灯火,下垅 牛羊”之句,又云:“烟波荡我心胸,晨昏异其观感。”他老人家高兴 地说:也难为你了。我在最近把《闲堂诗文合钞》印了几百份,分寄 给各地的朋友。我发现许多朋友非常欣赏我的文言文,为什么道理 呢?他们基本上都做不来了,即使年龄和我差不多,但当年北方的学
早慧知名,十多岁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集《曼殊沙馆初集》。但这 也是他惟一的文学结集。他的才华如同在那个社会的多数文士一样, 被困厄的生活压折了。 他那时流寓汉口,在家里办了一个名为“有恒斋”的私塾,招收 了十名左右十二三岁到二十岁的少年,教读自给。 年代,即使在汉 口这样的大都市,新式学校还是不多的,能够出钱送子弟进这类学校 的人家也不多,所以私塾也还不少。这个私塾就设在他家里,先在汉 口模范区蔼吉里,后在特二区三教街。 有恒斋的主要特点是起点非常高。我们从来不读《三字经》、《百 家姓》、《龙文鞭影》、《幼学琼林》,我们连《古文观止》、《唐诗三百 首》也不读,因为君硕先生认为这类书是不知义法的俗学。我们不读 《纲鉴易知录》,而是一上来就读《通鉴》。按照君硕先生的设想,他 几乎要把传统士大夫应当具备的知识都教给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我 学过的主要经典著作有《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礼记》、 《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资治通鉴》,其中除《礼 记》、《文选》外,都是通读的。所以我的文言基础比较扎实。 注意写作训练是有恒斋的另一个特点(当然全是用文言文)。每天一 定要写日记,记下自己的日常生活,读书心得。这既练习了文笔,又 锻炼了恒心。当然是十分有益的。记得这些日记我在大学时还保存 着,曾经将有关《礼记》的一部分整理出来发表过。汪辟疆老师看到 了,还曾夸奖说:今天学生肯治经的不多。我可没有敢对老师说,这 是从读私塾时的日记中摘抄的。除了日记以外,每周还要作文一篇, 这可是正 八经的。伯父改得可仔细,坏的墨杠,好的浓圈,赏罚分 明,我们也就不敢随随便便。记得在一篇游记中有“隔江灯火,下垅 牛羊”之句,又云“:烟波荡我心胸,晨昏异其观感。”他老人家高兴 地说:也难为你了。我在最近把《闲堂诗文合钞》印了几百份,分寄 给各地的朋友。我发现许多朋友非常欣赏我的文言文,为什么道理 呢?他们基本上都做不来了,即使年龄和我差不多,但当年北方的学 第 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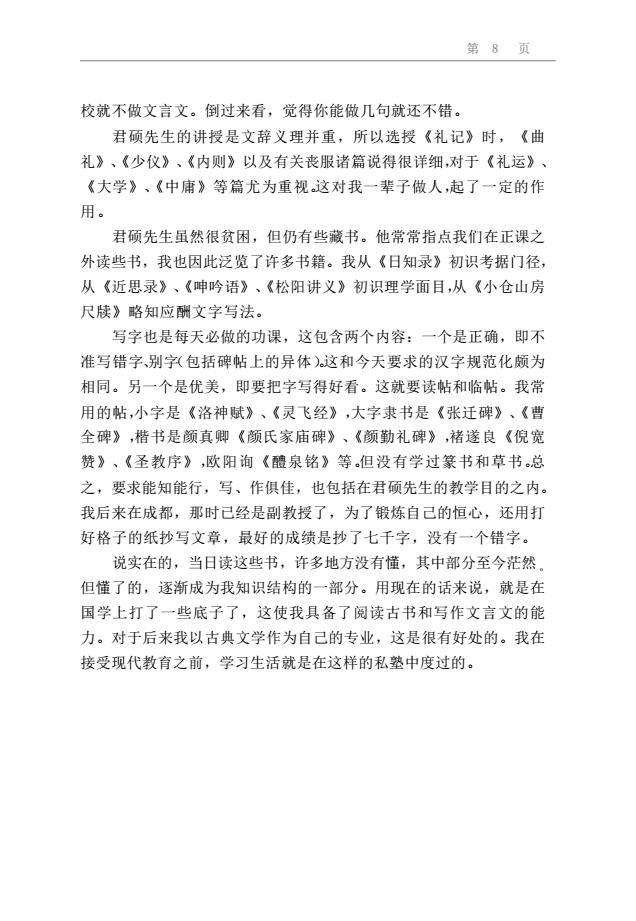
第8页 校就不做文言文。倒过来看,觉得你能做几句就还不错。 君硕先生的讲授是文辞义理并重,所以选授《礼记》时,《曲 礼》、《少仪》、《内则》以及有关丧服诸篇说得很详细,对于《礼运》、 《大学》、《中庸》等篇尤为重视这对我一辈子做人,起了一定的作 用。 君硕先生虽然很贫困,但仍有些藏书。他常常指点我们在正课之 外读些书,我也因此泛览了许多书籍。我从《日知录》初识考据门径, 从《近思录》、《呻吟语》、《松阳讲义》初识理学面目,从《小仓山房 尺牍》略知应酬文字写法。 写字也是每天必做的功课,这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正确,即不 准写错字,别字包括碑帖上的异体)。这和今天要求的汉字规范化颇为 相同。另一个是优美,即要把字写得好看。这就要读帖和临帖。我常 用的帖,小字是《洛神赋》、《灵飞经》,大字隶书是《张迁碑》、《曹 全碑》,楷书是颜真卿《颜氏家庙碑》、《颜勤礼碑》,褚遂良《倪宽 赞》、《圣教序》,欧阳询《醴泉铭》等但没有学过篆书和草书。总 之,要求能知能行,写、作俱佳,也包括在君硕先生的教学目的之内。 我后来在成都,那时已经是副教授了,为了锻炼自己的恒心,还用打 好格子的纸抄写文章,最好的成绩是抄了七千字,没有一个错字。 说实在的,当日读这些书,许多地方没有懂,其中部分至今茫然 但懂了的,逐渐成为我知识结构的一部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 国学上打了一些底子了,这使我具备了阅读古书和写作文言文的能 力。对于后来我以古典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这是很有好处的。我在 接受现代教育之前,学习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私塾中度过的
校就不做文言文。倒过来看,觉得你能做几句就还不错。 君硕先生的讲授是文辞义理并重,所以选授《礼记》时,《曲 礼》、《少仪》、《内则》以及有关丧服诸篇说得很详细,对于《礼运》、 《大学》、《中庸》等篇尤为重视。这对我一辈子做人,起了一定的作 用。 君硕先生虽然很贫困,但仍有些藏书。他常常指点我们在正课之 外读些书,我也因此泛览了许多书籍。我从《日知录》初识考据门径, 从《近思录》、《呻吟语》、《松阳讲义》初识理学面目,从《小仓山房 尺牍》略知应酬文字写法。 写字也是每天必做的功课,这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正确,即不 准写错字、别字(包括碑帖上的异体)。这和今天要求的汉字规范化颇为 相同。另一个是优美,即要把字写得好看。这就要读帖和临帖。我常 用的帖,小字是《洛神赋》、《灵飞经》,大字隶书是《张迁碑》、《曹 全碑》,楷书是颜真卿《颜氏家庙碑》、《颜勤礼碑》,褚遂良《倪宽 赞》、《圣教序》,欧阳询《醴泉铭》等。但没有学过篆书和草书。总 之,要求能知能行,写、作俱佳,也包括在君硕先生的教学目的之内。 我后来在成都,那时已经是副教授了,为了锻炼自己的恒心,还用打 好格子的纸抄写文章,最好的成绩是抄了七千字,没有一个错字。 说实在的,当日读这些书,许多地方没有懂,其中部分至今茫然 但懂了的,逐渐成为我知识结构的一部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 国学上打了一些底子了,这使我具备了阅读古书和写作文言文的能 力。对于后来我以古典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这是很有好处的。我在 接受现代教育之前,学习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私塾中度过的。 第 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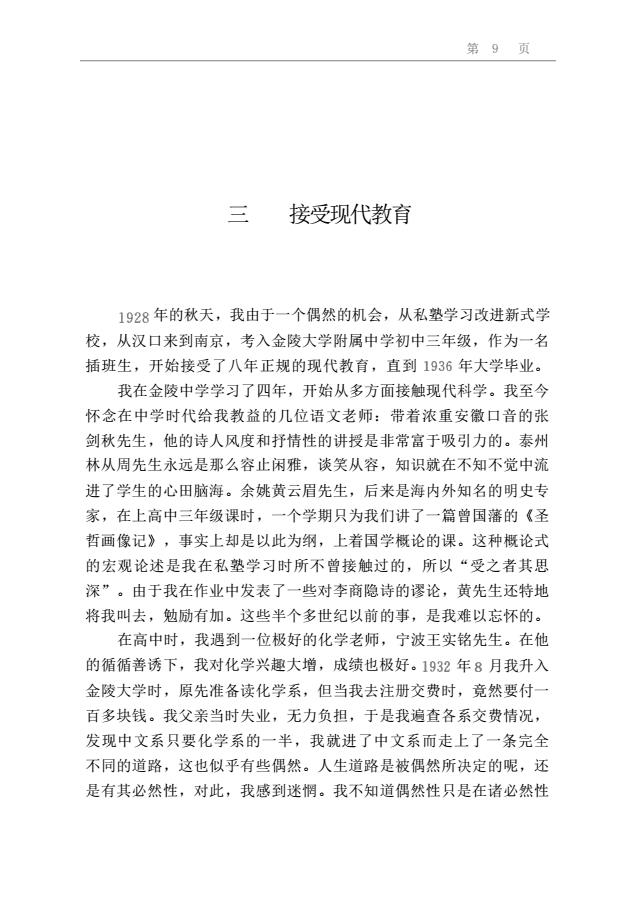
第9页 三 接受现代教育 1928年的秋天,我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从私塾学习改进新式学 校,从汉口来到南京,考入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三年级,作为一名 插班生,开始接受了八年正规的现代教育,直到1936年大学毕业。 我在金陵中学学习了四年,开始从多方面接触现代科学。我至今 怀念在中学时代给我教益的几位语文老师:带着浓重安徽口音的张 剑秋先生,他的诗人风度和抒情性的讲授是非常富于吸引力的。泰州 林从周先生永远是那么容止闲雅,谈笑从容,知识就在不知不觉中流 进了学生的心田脑海。余姚黄云眉先生,后来是海内外知名的明史专 家,在上高中三年级课时,一个学期只为我们讲了一篇曾国藩的《圣 哲画像记》,事实上却是以此为纲,上着国学概论的课。这种概论式 的宏观论述是我在私塾学习时所不曾接触过的,所以“受之者其思 深”。由于我在作业中发表了一些对李商隐诗的谬论,黄先生还特地 将我叫去,勉励有加。这些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是我难以忘怀的。 在高中时,我遇到一位极好的化学老师,宁波王实铭先生。在他 的循循善诱下,我对化学兴趣大增,成绩也极好。1932年8月我升入 金陵大学时,原先准备读化学系,但当我去注册交费时,竞然要付 百多块钱。我父亲当时失业,无力负担,于是我遍查各系交费情况, 发现中文系只要化学系的一半,我就进了中文系而走上了一条完全 不同的道路,这也似乎有些偶然。人生道路是被偶然所决定的呢,还 是有其必然性,对此,我感到迷惘。我不知道偶然性只是在诸必然性
三 接受现代教育 年的秋天,我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从私塾学习改进新式学 校,从汉口来到南京,考入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三年级,作为一名 插班生,开始接受了八年正规的现代教育,直到 年大学毕业。 我在金陵中学学习了四年,开始从多方面接触现代科学。我至今 怀念在中学时代给我教益的几位语文老师:带着浓重安徽口音的张 剑秋先生,他的诗人风度和抒情性的讲授是非常富于吸引力的。泰州 林从周先生永远是那么容止闲雅,谈笑从容,知识就在不知不觉中流 进了学生的心田脑海。余姚黄云眉先生,后来是海内外知名的明史专 家,在上高中三年级课时,一个学期只为我们讲了一篇曾国藩的《圣 哲画像记》,事实上却是以此为纲,上着国学概论的课。这种概论式 的宏观论述是我在私塾学习时所不曾接触过的,所以“受之者其思 深”。由于我在作业中发表了一些对李商隐诗的谬论,黄先生还特地 将我叫去,勉励有加。这些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是我难以忘怀的。 在高中时,我遇到一位极好的化学老师,宁波王实铭先生。在他 的循循善诱下,我对化学兴趣大增,成绩也极好。 年 月我升入 金陵大学时,原先准备读化学系,但当我去注册交费时,竟然要付一 百多块钱。我父亲当时失业,无力负担,于是我遍查各系交费情况, 发现中文系只要化学系的一半,我就进了中文系而走上了一条完全 不同的道路,这也似乎有些偶然。人生道路是被偶然所决定的呢,还 是有其必然性,对此,我感到迷惘。我不知道偶然性只是在诸必然性 第 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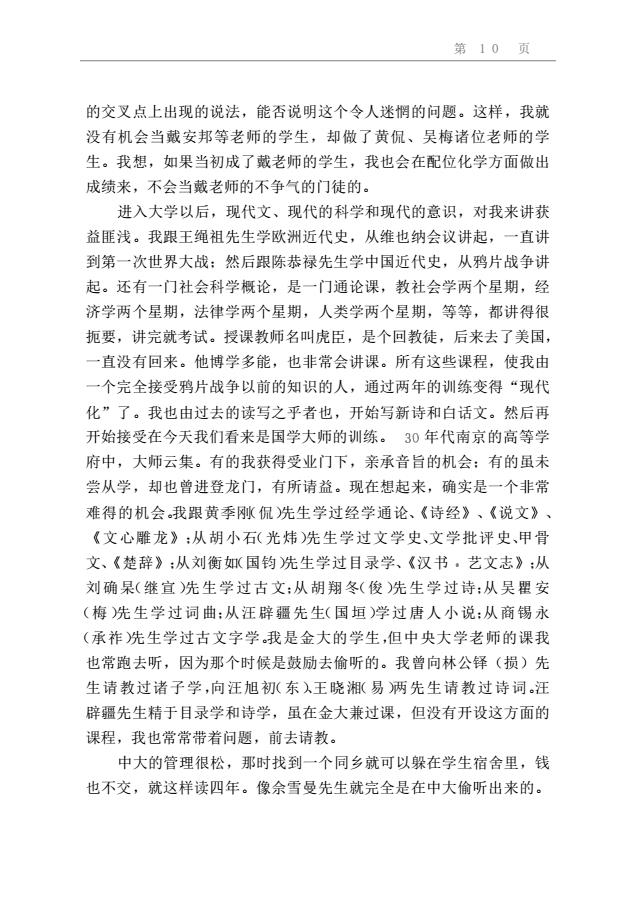
第10币 的交叉点上出现的说法,能否说明这个令人迷惘的问题。这样,我就 没有机会当戴安邦等老师的学生,却做了黄侃、吴梅诸位老师的学 生。我想,如果当初成了戴老师的学生,我也会在配位化学方面做出 成绩来,不会当戴老师的不争气的门徒的。 进入大学以后,现代文、现代的科学和现代的意识,对我来讲获 益匪浅。我跟王绳祖先生学欧洲近代史,从维也纳会议讲起,一直讲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跟陈恭禄先生学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讲 起。还有一门社会科学概论,是一门通论课,教社会学两个星期,经 济学两个星期,法律学两个星期,人类学两个星期,等等,都讲得很 扼要,讲完就考试。授课教师名叫虎臣,是个回教徒,后来去了美国, 一直没有回来。他博学多能,也非常会讲课。所有这些课程,使我由 一个完全接受鸦片战争以前的知识的人,通过两年的训练变得“现代 化”了。我也由过去的读写之乎者也,开始写新诗和白话文。然后再 开始接受在今天我们看来是国学大师的训练。30年代南京的高等学 府中,大师云集。有的我获得受业门下,亲承音旨的机会:有的虽未 尝从学,却也曾进登龙门,有所请益。现在想起来,确实是一个非常 难得的机会我跟黄季刚侃)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说文》、 《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 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冼生学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 刘确杲(继宜)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过诗:从吴瞿安 (梅)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先生(国垣)学过唐人小说:从商锡永 (承祚先生学过古文字学我是金大的学生,但中央大学老师的课我 也常跑去听,因为那个时候是鼓励去偷听的。我曾向林公铎(损)先 生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东入王晓湘(易两先生请教过诗词.汪 辟疆先生精于目录学和诗学,虽在金大兼过课,但没有开设这方面的 课程,我也常常带着问题,前去请教。 中大的管理很松,那时找到一个同乡就可以躲在学生宿舍里,钱 也不交,就这样读四年。像佘雪曼先生就完全是在中大偷听出来的
的交叉点上出现的说法,能否说明这个令人迷惘的问题。这样,我就 没有机会当戴安邦等老师的学生,却做了黄侃、吴梅诸位老师的学 生。我想,如果当初成了戴老师的学生,我也会在配位化学方面做出 成绩来,不会当戴老师的不争气的门徒的。 进入大学以后,现代文、现代的科学和现代的意识,对我来讲获 益匪浅。我跟王绳祖先生学欧洲近代史,从维也纳会议讲起,一直讲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跟陈恭禄先生学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讲 起。还有一门社会科学概论,是一门通论课,教社会学两个星期,经 济学两个星期,法律学两个星期,人类学两个星期,等等,都讲得很 扼要,讲完就考试。授课教师名叫虎臣,是个回教徒,后来去了美国, 一直没有回来。他博学多能,也非常会讲课。所有这些课程,使我由 一个完全接受鸦片战争以前的知识的人,通过两年的训练变得“现代 化”了。我也由过去的读写之乎者也,开始写新诗和白话文。然后再 开始接受在今天我们看来是国学大师的训练。 年代南京的高等学 府中,大师云集。有的我获得受业门下,亲承音旨的机会;有的虽未 尝从学,却也曾进登龙门,有所请益。现在想起来,确实是一个非常 难得的机会。我跟黄季刚(侃)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说文》、 《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 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过目录学、《汉书 艺文志》;从 刘确杲(继宣)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过诗;从吴瞿安 (梅)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先生(国垣)学过唐人小说;从商锡永 (承祚)先生学过古文字学。我是金大的学生,但中央大学老师的课我 也常跑去听,因为那个时候是鼓励去偷听的。我曾向林公铎(损)先 生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东)、王晓湘(易)两先生请教过诗词。汪 辟疆先生精于目录学和诗学,虽在金大兼过课,但没有开设这方面的 课程,我也常常带着问题,前去请教。 中大的管理很松,那时找到一个同乡就可以躲在学生宿舍里,钱 也不交,就这样读四年。像佘雪曼先生就完全是在中大偷听出来的。 第 1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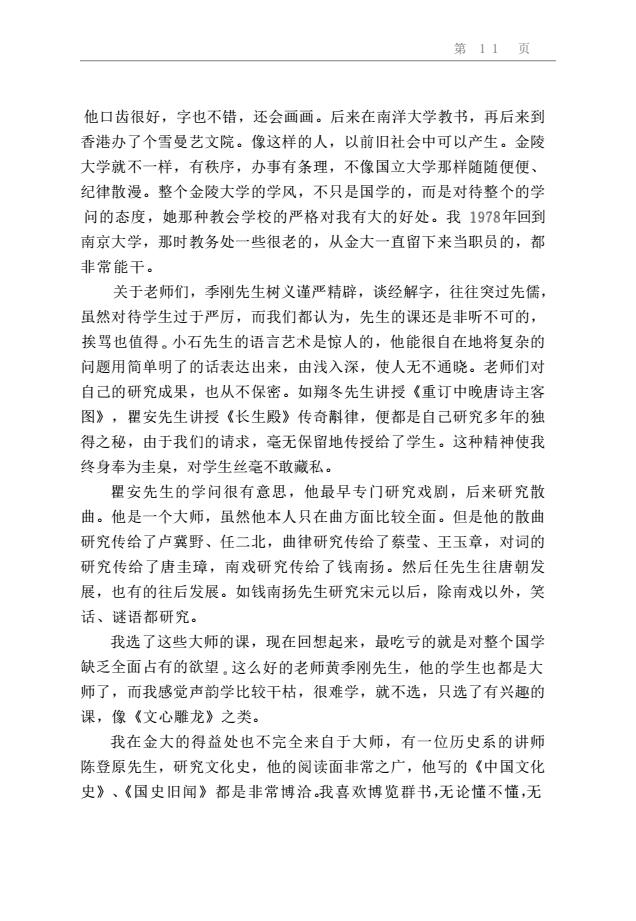
第11页 他口齿很好,字也不错,还会画画。后来在南洋大学教书,再后来到 香港办了个雪曼艺文院。像这样的人,以前旧社会中可以产生。金陵 大学就不一样,有秩序,办事有条理,不像国立大学那样随随便便、 纪律散漫。整个金陵大学的学风,不只是国学的,而是对待整个的学 问的态度,她那种教会学校的严格对我有大的好处。我1978年回到 南京大学,那时教务处一些很老的,从金大一直留下来当职员的,都 非常能干。 关于老师们,季刚先生树义谨严精辟,谈经解字,往往突过先儒, 虽然对待学生过于严厉,而我们都认为,先生的课还是非听不可的, 挨骂也值得。小石先生的语言艺术是惊人的,他能很自在地将复杂的 问题用简单明了的话表达出来,由浅入深,使人无不通晓。老师们对 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从不保密。如翔冬先生讲授《重订中晚唐诗主客 图》,瞿安先生讲授《长生殿》传奇制律,便都是自己研究多年的独 得之秘,由于我们的请求,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学生。这种精神使我 终身奉为圭臬,对学生丝毫不敢藏私。 瞿安先生的学问很有意思,他最早专门研究戏剧,后来研究散 曲。他是一个大师,虽然他本人只在曲方面比较全面。但是他的散曲 研究传给了卢冀野、任二北,曲律研究传给了蔡莹、王玉章,对词的 研究传给了唐圭璋,南戏研究传给了钱南扬。然后任先生往唐朝发 展,也有的往后发展。如钱南扬先生研究宋元以后,除南戏以外,笑 话、谜语都研究。 我选了这些大师的课,现在回想起来,最吃亏的就是对整个国学 缺乏全面占有的欲望。这么好的老师黄季刚先生,他的学生也都是大 师了,而我感觉声韵学比较干枯,很难学,就不选,只选了有兴趣的 课,像《文心雕龙》之类。 我在金大的得益处也不完全来自于大师,有一位历史系的讲师 陈登原先生,研究文化史,他的阅读面非常之广,他写的《中国文化 史》、《国史旧闻》都是非常博洽我喜欢博览群书,无论懂不懂,无
他口齿很好,字也不错,还会画画。后来在南洋大学教书,再后来到 香港办了个雪曼艺文院。像这样的人,以前旧社会中可以产生。金陵 大学就不一样,有秩序,办事有条理,不像国立大学那样随随便便、 纪律散漫。整个金陵大学的学风,不只是国学的,而是对待整个的学 问的态度,她那种教会学校的严格对我有大的好处。我 年回到 南京大学,那时教务处一些很老的,从金大一直留下来当职员的,都 非常能干。 关于老师们,季刚先生树义谨严精辟,谈经解字,往往突过先儒, 虽然对待学生过于严厉,而我们都认为,先生的课还是非听不可的, 挨骂也值得 小石先生的语言艺术是惊人的,他能很自在地将复杂的 问题用简单明了的话表达出来,由浅入深,使人无不通晓。老师们对 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从不保密。如翔冬先生讲授《重订中晚唐诗主客 图》,瞿安先生讲授《长生殿》传奇斠律,便都是自己研究多年的独 得之秘,由于我们的请求,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学生。这种精神使我 终身奉为圭臬,对学生丝毫不敢藏私。 瞿安先生的学问很有意思,他最早专门研究戏剧,后来研究散 曲。他是一个大师,虽然他本人只在曲方面比较全面。但是他的散曲 研究传给了卢冀野、任二北,曲律研究传给了蔡莹、王玉章,对词的 研究传给了唐圭璋,南戏研究传给了钱南扬。然后任先生往唐朝发 展,也有的往后发展。如钱南扬先生研究宋元以后,除南戏以外,笑 话、谜语都研究。 我选了这些大师的课,现在回想起来,最吃亏的就是对整个国学 缺乏全面占有的欲望 这么好的老师黄季刚先生,他的学生也都是大 师了,而我感觉声韵学比较干枯,很难学,就不选,只选了有兴趣的 课,像《文心雕龙》之类。 我在金大的得益处也不完全来自于大师,有一位历史系的讲师 陈登原先生,研究文化史,他的阅读面非常之广,他写的《中国文化 史》、《国史旧闻》都是非常博洽。我喜欢博览群书,无论懂不懂,无 第 1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