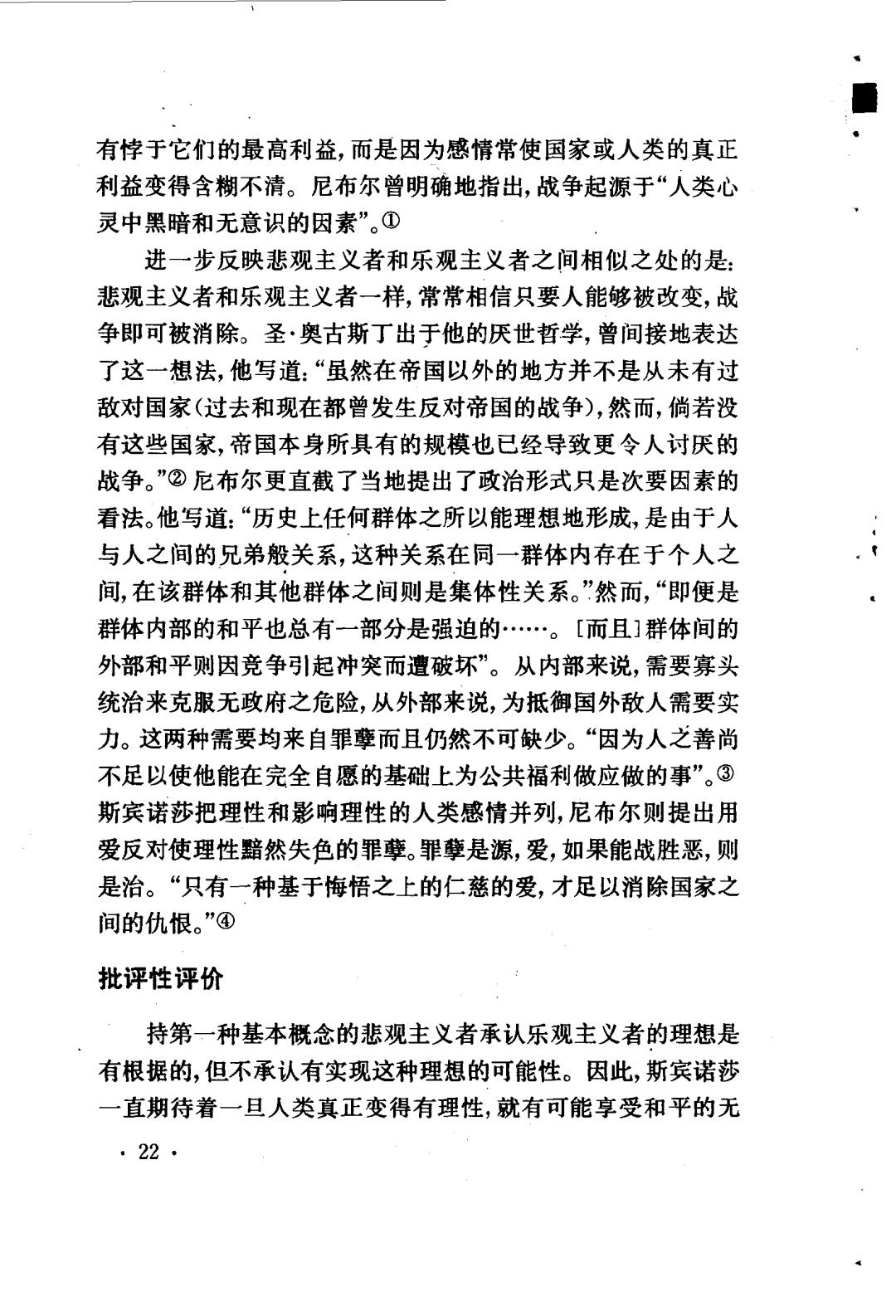
有悖于它们的最高利益,而是因为感情常使国家或人类的真正 利益变得含糊不清。尼布尔曾明确地指出,战争起源于“人类心 灵中黑暗和无意识的因素”。① 进一步反映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之间相似之处的是: 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一样,常常相信只要人能够被改变,战 争即可被消除。圣·奥古斯丁出于他的厌世哲学,曾间接地表达 了这一想法,他写道:“虽然在帝国以外的地方并不是从未有过 敌对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曾发生反对帝国的战争),然而,徜若没 有这些国家,帝国本身所具有的规模也已经导致更令人讨厌的 战争。”②尼布尔更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政治形式只是次要因素的 看法。他写道:“历史上任何群体之所以能理想地形成,是由于人 与人之间的兄弟般关系,这种关系在同一群体内存在于个人之 间,在该群体和其他群体之间则是集体性关系。”然而,“即便是 群体内部的和平也总有一部分是强迫的…。[而且]群体间的 外部和平则因竞争引起冲突而遭破坏”。从内部来说,需要寡头 统治来克服无政府之危险,从外部来说,为抵御国外敌人需要实 力。这两种需要均来自罪孽而且仍然不可缺少。“因为人之善尚 不足以使他能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为公共福利做应做的事”。③ 斯宾诺莎把理性和影响理性的人类感情并列,尼布尔则提出用 爱反对使理性黯然失色的罪孽。罪孽是源,爱,如果能战胜恶,则 是治。“只有一种基于悔悟之上的仁慈的爱,才足以消除国家之 间的仇恨。”④ 批评性评价 持第一种基本概念的悲观主义者承认乐观主义者的理想是 有根据的,但不承认有实现这种理想的可能性。因此,斯宾诺莎 一直期待着一旦人类真正变得有理性,就有可能享受和平的无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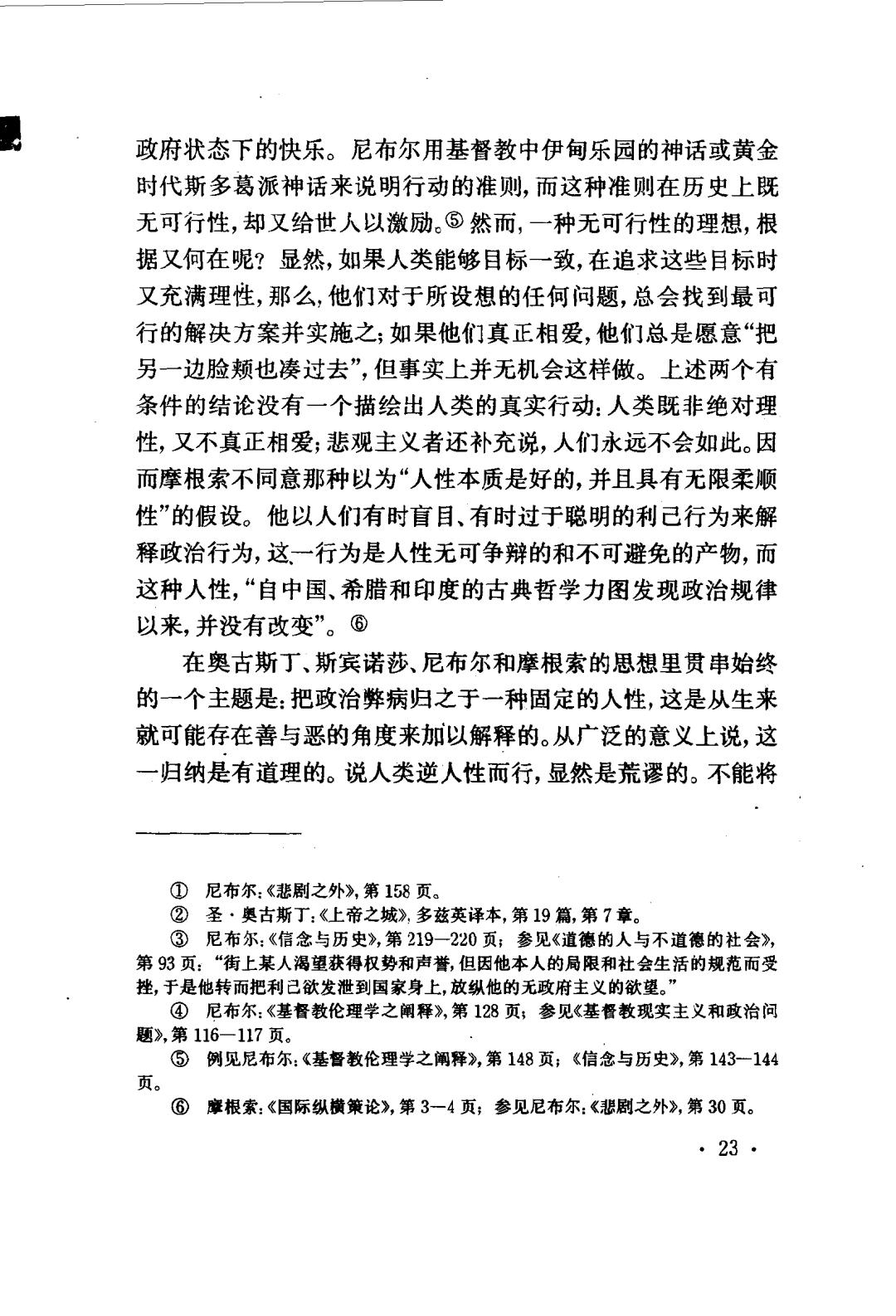
政府状态下的快乐。尼布尔用基督教中伊甸乐园的神话或黄金 时代斯多葛派神话来说明行动的准则,而这种准则在历史上既 无可行性,却又给世人以激励.⑤然而,一种无可行性的理想,根 据又何在呢?显然,如果人类能够目标一致,在追求这些目标时 又充满理性,那么,他们对于所设想的任何问题,总会找到最可 行的解决方案并实施之;如果他们真正相爱,他们总是愿意“把 另一边脸颊也凑过去”,但事实上并无机会这样做。上述两个有 条件的结论没有一个描绘出人类的真实行动:人类既非绝对理 性,又不真正相爱;悲观主义者还补充说,人们永远不会如此。因 而摩根索不同意那种以为“人性本质是好的,并且具有无限柔顺 性”的假设。他以人们有时盲目、有时过于聪明的利己行为来解 释政治行为,这.一行为是人性无可争辩的和不可避免的产物,而 这种人性,“自中国、希腊和印度的古典哲学力图发现政治规律 以来,并没有改变”。⑥ 在奥古斯丁、斯宾诺莎、尼布尔和摩根索的思想里贯串始终 的一个主题是:把政治弊病归之于一种固定的人性,这是从生来 就可能存在善与恶的角度来加以解释的。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这 一归纳是有道理的。说人类逆人性而行,显然是荒谬的。不能将 ①尼布尔:《悲剧之外》,第158页。 ②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多兹英译本,第19篇,第7章。 ③尼布尔:《信念与历史》,第219一220页;参见《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 第93页:“街上某人渴望获得权势和声誉,但因他本人的局限和社会生活的规范而受 挫,于是他转而把利己欲发泄到国家身上,放纵他的无政府主义的欲望。” ④尼布尔:《基督教伦理学之阐释》,第128页;参见《基督教现实主义和政治问 题》,第116一117页。 ⑤例见尼布尔:《基督教伦理学之阐释》,第148页;《信念与历史》,第143一144 页。 ⑥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第3一4页;参见尼布尔:《悲剧之外》,第30页。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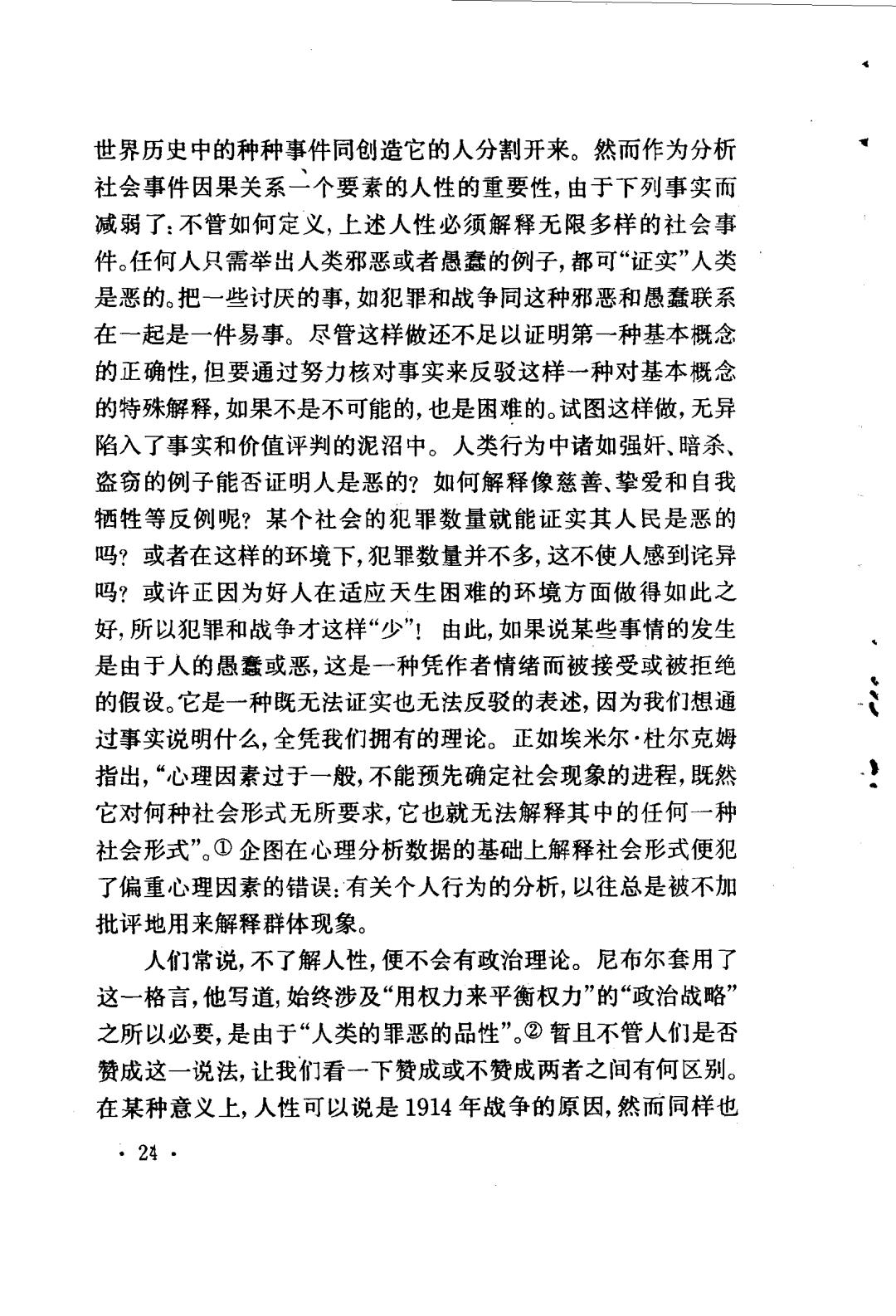
世界历史中的种种事件同创造它的人分割开来。然而作为分析 社会事件因果关系一个要素的人性的重要性,由于下列事实而 减弱了:不管如何定义,上述人性必须解释无限多样的社会事 件。任何人只需举出人类邪恶或者愚蠢的例子,都可“证实”人类 是恶的。把一些讨厌的事,如犯罪和战争同这种邪恶和愚蠢联系 在一起是一件易事。尽管这样做还不足以证明第一种基本概念 的正确性,但要通过努力核对事实来反驳这样一种对基本概念 的特殊解释,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困难的。试图这样做,无异 陷入了事实和价值评判的泥沼中。人类行为中诸如强奸、暗杀、 盗窃的例子能否证明人是恶的?如何解释像慈善、挚爱和自我 牺性等反例呢?某个社会的犯罪数量就能证实其人民是恶的 吗?或者在这样的环境下,犯罪数量并不多,这不使人感到诧异 吗?或许正因为好人在适应天生困难的环境方面做得如此之 好,所以犯罪和战争才这样“少”!由此,如果说某些事情的发生 是由于人的愚蠢或恶,这是一种凭作者情绪而被接受或被拒绝 的假设。它是一种既无法证实也无法反驳的表述,因为我们想通 过事实说明什么,全凭我们拥有的理论。正如埃米尔·杜尔克姆 指出,“心理因素过于一般,不能预先确定社会现象的进程,既然 它对何种社会形式无所要求,它也就无法解释其中的任何一种 社会形式”。①企图在心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解释社会形式便犯 了偏重心理因素的错误:有关个人行为的分析,以往总是被不加 批评地用来解释群体现象。 人们常说,不了解人性,便不会有政治理论。尼布尔套用了 这一格言,他写道,始终涉及“用权力来平衡权力”的“政治战略” 之所以必要,是由于“人类的罪恶的品性”。②暂且不管人们是否 赞成这一说法,让我们看一下赞成或不赞成两者之间有何区别。 在某种意义上,人性可以说是1914年战争的原因,然而同样也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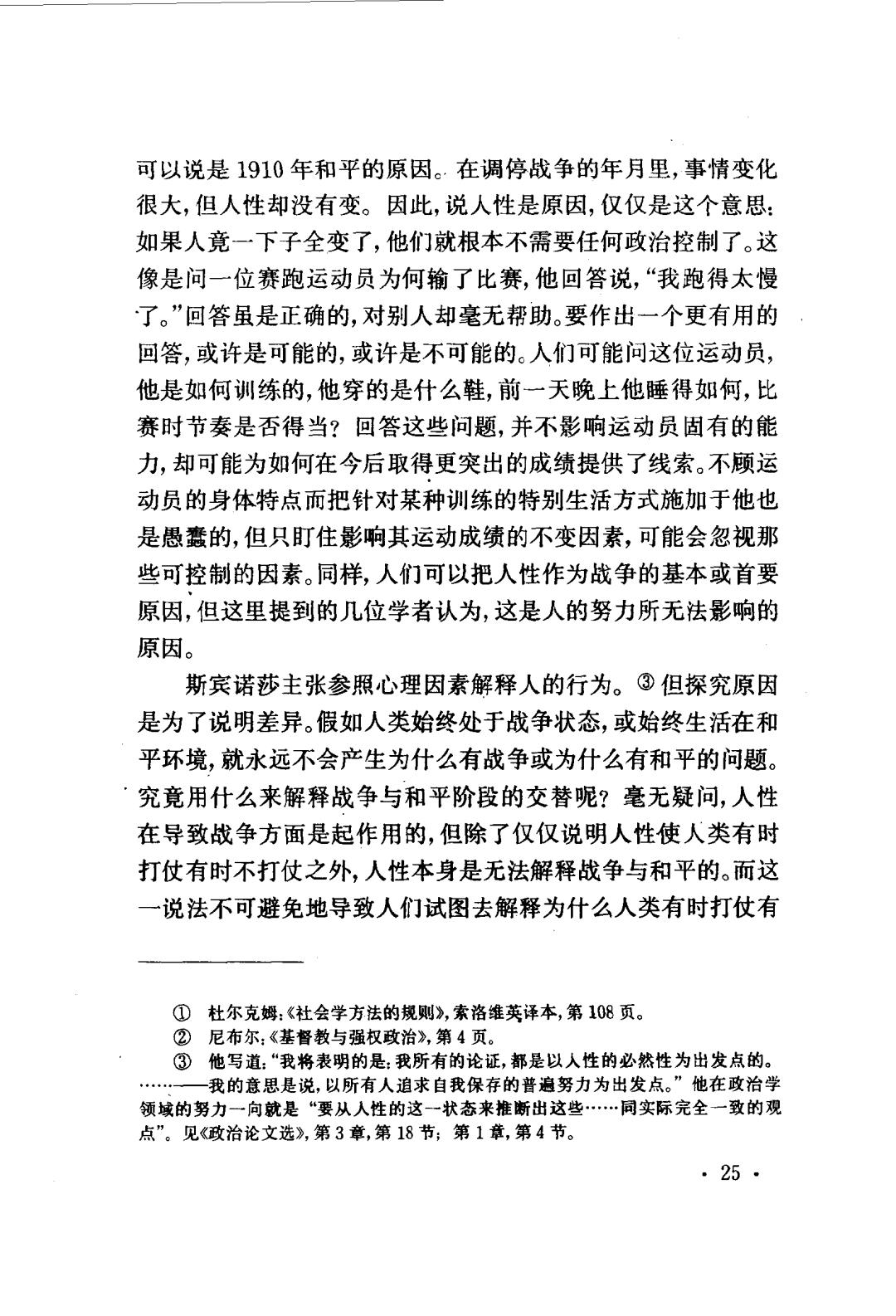
可以说是1910年和平的原因。·在调停战争的年月里,事情变化 很大,但人性却没有变。因此,说人性是原因,仅仅是这个意思: 如果人竟一下子全变了,他们就根本不需要任何政治控制了。这 像是问一位赛跑运动员为何输了比赛,他回答说,“我跑得太慢 ·了。”回答虽是正确的,对别人却毫无帮助。要作出一个更有用的 回答,或许是可能的,或许是不可能的。人们可能问这位运动员, 他是如何训练的,他穿的是什么鞋,前一天晚上他睡得如何,比 赛时节奏是否得当?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影响运动员固有的能 力,却可能为如何在今后取得更突出的成绩提供了线索。不顾运 动员的身体特点而把针对某种训练的特别生活方式施加于他也 是愚蠢的,但只盯住影响其运动成绩的不变因素,可能会忽视那 些可控制的因素。同样,人们可以把人性作为战争的基本或首要 原因,但这里提到的几位学者认为,这是人的努力所无法影响的 原因。 斯宾诺莎主张参照心理因素解释人的行为。③但探究原因 是为了说明差异。假如人类始终处于战争状态,或始终生活在和 平环境,就永远不会产生为什么有战争或为什么有和平的问题。 究竟用什么来解释战争与和平阶段的交替呢?毫无疑问,人性 在导致战争方面是起作用的,但除了仅仅说明人性使人类有时 打仗有时不打仗之外,人性本身是无法解释战争与和平的。而这 一说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试图去解释为什么人类有时打仗有 ①杜尔克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索洛维英译本,第108页。 ②尼布尔:《基督教与强权政治》,第4页。 ③他写道:“我将表明的是:我所有的论证,都是以人性的必然性为出发点的。 …一我的意思是说,以所有人追求自我保存的普遍努力为出发点。”他在政治学 领域的努力一向就是“要从人性的这-一状态来椎断出这些…同实际完全一致的观 点”。见《政治论文选》,第3章,第18节;第1草,第4节。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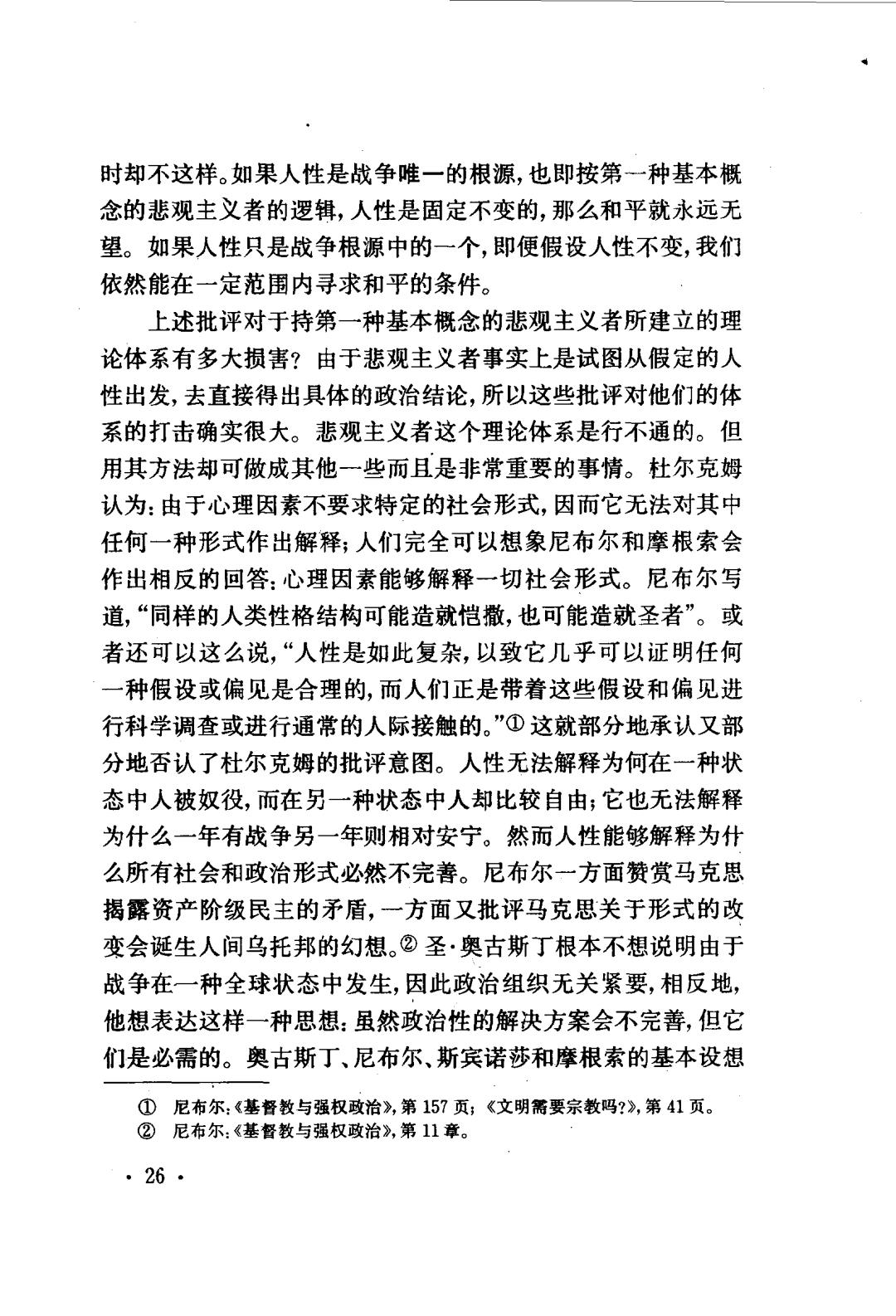
时却不这样。如果人性是战争唯一的根源,也即按第一种基本概 念的悲观主义者的逻辑,人性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和平就永远无 望。如果人性只是战争根源中的一个,即便假设人性不变,我们 依然能在一定范围内寻求和平的条件。 上述批评对于持第一种基本概念的悲观主义者所建立的理 论体系有多大损害?由于悲观主义者事实上是试图从假定的人 性出发,去直接得出具体的政治结论,所以这些批评对他们的体 系的打击确实很大。悲观主义者这个理论体系是行不通的。但 用其方法却可做成其他一些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杜尔克姆 认为:由于心理因素不要求特定的社会形式,因而它无法对其中 任何一种形式作出解释;人们完全可以想象尼布尔和摩根索会 作出相反的回答:心理因素能够解释一切社会形式。尼布尔写 道,“同样的人类性格结构可能造就恺撒,也可能造就圣者”。或 者还可以这么说,“人性是如此复杂,以致它几乎可以证明任何 一种假设或偏见是合理的,而人们正是带着这些假设和偏见进 行科学调查或进行通常的人际接触的。”①这就部分地承认又部 分地否认了杜尔克姆的批评意图。人性无法解释为何在一种状 态中人被奴役,而在另一种状态中人却比较自由;它也无法解释 为什么一年有战争另一年则相对安宁。然而人性能够解释为什 么所有社会和政治形式必然不完善。尼布尔一方面赞赏马克思 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矛盾,一方面又批评马克思关于形式的改 变会诞生人间乌托邦的幻想。②圣·奥古斯丁根本不想说明由于 战争在一种全球状态中发生,因此政治组织无关紧要,相反地, 他想表达这样一种思想:虽然政治性的解决方案会不完善,但它 们是必需的。奥古斯丁、尼布尔、斯宾诺莎和摩根索的基本设想 ①尼布尔:《基督教与强权政治》,第157页;《文明需要宗教吗?》,第41页。 ②尼布尔:《基督教与强权政治》,第11章。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