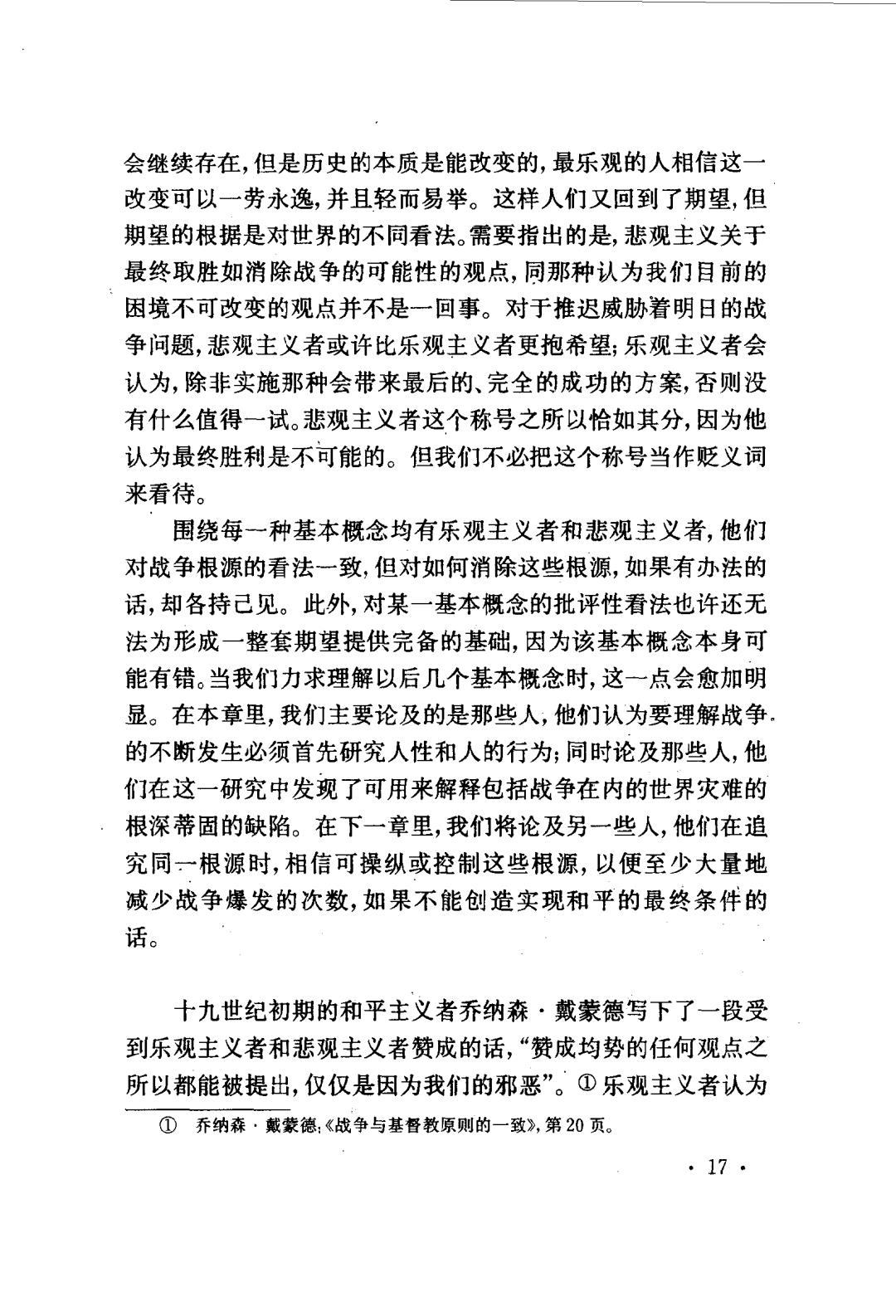
会继续存在,但是历史的本质是能改变的,最乐观的人相信这一 改变可以一劳永逸,并且轻而易举。这样人们又回到了期望,但 期望的根据是对世界的不同看法。需要指出的是,悲观主义关于 最终取胜如消除战争的可能性的观点,同那种认为我们目前的 困境不可改变的观点并不是一回事。对于推迟威胁着明日的战 争问题,悲观主义者或许比乐观主义者更抱希望;乐观主义者会 认为,除非实施那种会带来最后的、完全的成功的方案,否则没 有什么值得一试。悲观主义者这个称号之所以恰如其分,因为他 认为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不必把这个称号当作贬义词 来看待。 围绕每一种基本概念均有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他们 对战争根源的看法一致,但对如何消除这些根源,如果有办法的 话,却各持己见。此外,对某一基本概念的批评性看法也许还无 法为形成一整套期望提供完备的基础,因为该基本概念本身可 能有错。当我们力求理解以后几个基本概念时,这一点会愈加明 显。在本章里,我们主要论及的是那些人,他们认为要理解战争 的不断发生必须首先研究人性和人的行为;同时论及那些人,他 们在这一研究中发现了可用来解释包括战争在内的世界灾难的 根深蒂固的缺陷。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论及另一些人,他们在追 究同一根源时,相信可操纵或控制这些根源,以便至少大量地 减少战争爆发的次数,如果不能创造实现和平的最终条件的 话。 十九世纪初期的和平主义者乔纳森·戴蒙德写下了一段受 到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赞成的话,“赞成均势的任何观点之 所以都能被提出,仅仅是因为我们的邪恶”。①乐观主义者认为 ①乔纳森·戴蒙德,《战争与基督教原则的一致》,第20页。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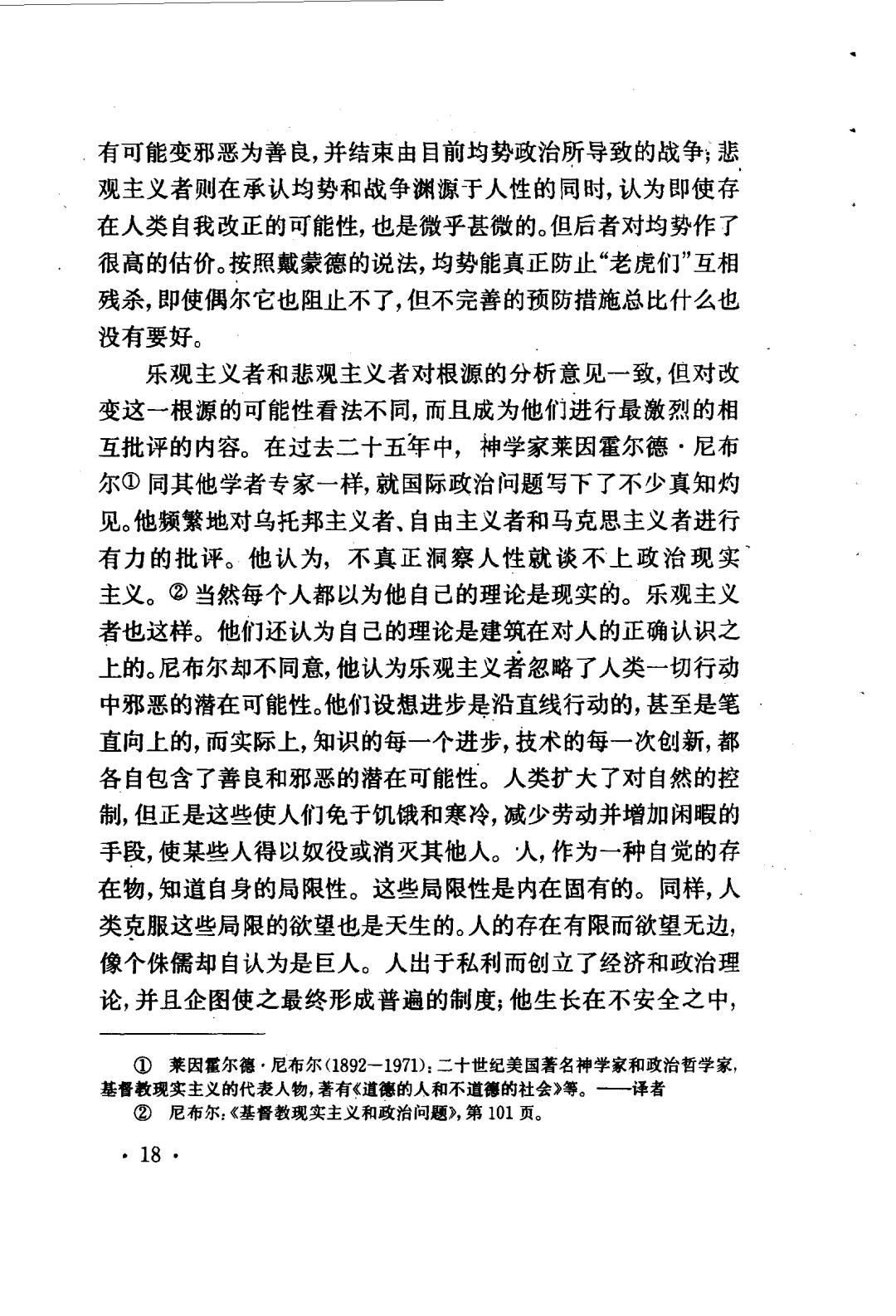
有可能变邪恶为善良,并结束由目前均势政治所导致的战争;悲 观主义者则在承认均势和战争渊源于人性的同时,认为即使存 在人类自我改正的可能性,也是微乎甚微的。但后者对均势作了 很高的估价。按照戴蒙德的说法,均势能真正防止“老虎们”互相 残杀,即使偶尔它也阻止不了,但不完善的预防措施总比什么也 没有要好。 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对根源的分析意见一致,但对改 变这一根源的可能性看法不同,而且成为他们进行最激烈的相 互批评的内容。在过去二十五年中,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 尔①同其他学者专家一样,就国际政治问题写下了不少真知灼 见。他频繁地对鸟托邦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 有力的批评。他认为,不真正洞察人性就谈不上政治现实 主义。②当然每个人都以为他自己的理论是现实的。乐观主义 者也这样。他们还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建筑在对人的正确认识之 上的。尼布尔却不同意,他认为乐观主义者忽略了人类一切行动 中邪恶的潜在可能性。他们设想进步是沿直线行动的,甚至是笔 直向上的,而实际上,知识的每一个进步,技术的每一次创新,都 各自包含了善良和邪恶的潜在可能性。人类扩大了对自然的控 制,但正是这些使人们免于饥饿和寒冷,减少劳动并增加闲暇的 手段,使某些人得以奴役或消灭其他人。人,作为一种自觉的存 在物,知道自身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是内在固有的。同样,人 类克服这些局限的欲望也是天生的。人的存在有限而欲望无边, 像个侏儒却自认为是巨人。人出于私利而创立了经济和政治理 论,并且企图使之最终形成普遍的度;他生长在不安全之中, ①莱因霍尔德·尼布尔(1892一1971):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神学家和政治哲学家, 基督教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著有《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等。一译者 ②尼布尔:《基督教现实主义和政治问题》,第101页。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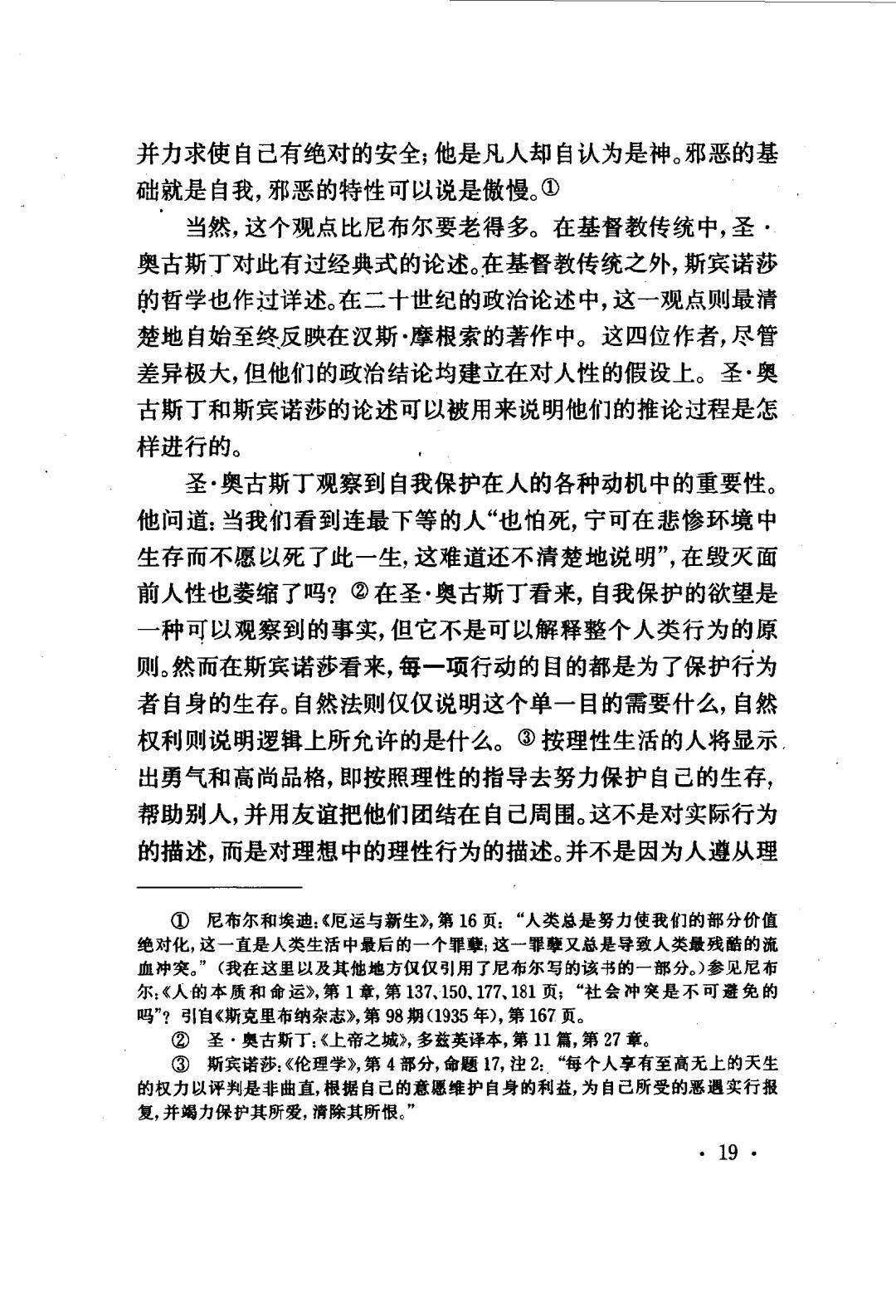
并力求使自己有绝对的安全;他是凡人却自认为是神。邪恶的基 础就是自我,邪恶的特性可以说是傲慢。① 当然,这个观点比尼布尔要老得多。在基督教传统中,圣 奥古斯丁对此有过经典式的论述。在基督教传统之外,斯宾诺莎 的哲学也作过详述。在二十世纪的政治论述中,这一观点则最清 楚地自始至终反映在汉斯·摩根索的著作中。这四位作者,尽管 差异极大,但他们的政治结论均建立在对人性的假设上。圣·奥 古斯丁和斯宾诺莎的论述可以被用来说明他们的推论过程是怎 样进行的。 圣·奥古斯丁观察到自我保护在人的各种动机中的重要性。 他问道:当我们看到连最下等的人“也怕死,宁可在悲惨环境中 生存而不愿以死了此一生,这难道还不清楚地说明”,在毁灭面 前人性也萎缩了吗?②在圣·奥古斯丁看来,自我保护的欲望是 一种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但它不是可以解释整个人类行为的原 则。然而在斯宾诺莎看来,每一项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行为 者自身的生存。自然法则仅仅说明这个单一目的需要什么,自然 权利则说明逻辑上所允许的是什么。③按理性生活的人将显示 出勇气和高尚品格,即按照理性的指导去努力保护自己的生存, 帮助别人,并用友谊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这不是对实际行为 的描述,而是对理想中的理性行为的描述。并不是因为人遵从理 ①尼布尔和埃迪:《厄运与新生》,第16页:“人类总是努力使我们的部分价值 绝对化,这一直是人类生活中最后的一个罪孽;这一罪孽又总是导致人类最残酷的流 血冲突。”(我在这里以及其他地方仅仅引用了尼布尔写的该书的一部分。)参见尼布 尔:《人的本质和命运》,第1章,第137、150、177、181页;“杜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吗”?引自《斯克里布纳杂志》,第98期(1935年),第167页。 ②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多兹英译本,第11篇,第27章。 ③斯宾诺莎:《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17,注2:“每个人享有至高无上的天生 的权力以评判是非曲直,根据自己的意愿维护自身的利益,为自己所受的恶遇实行报 复,并竭力保护其所爱,清除其所恨。”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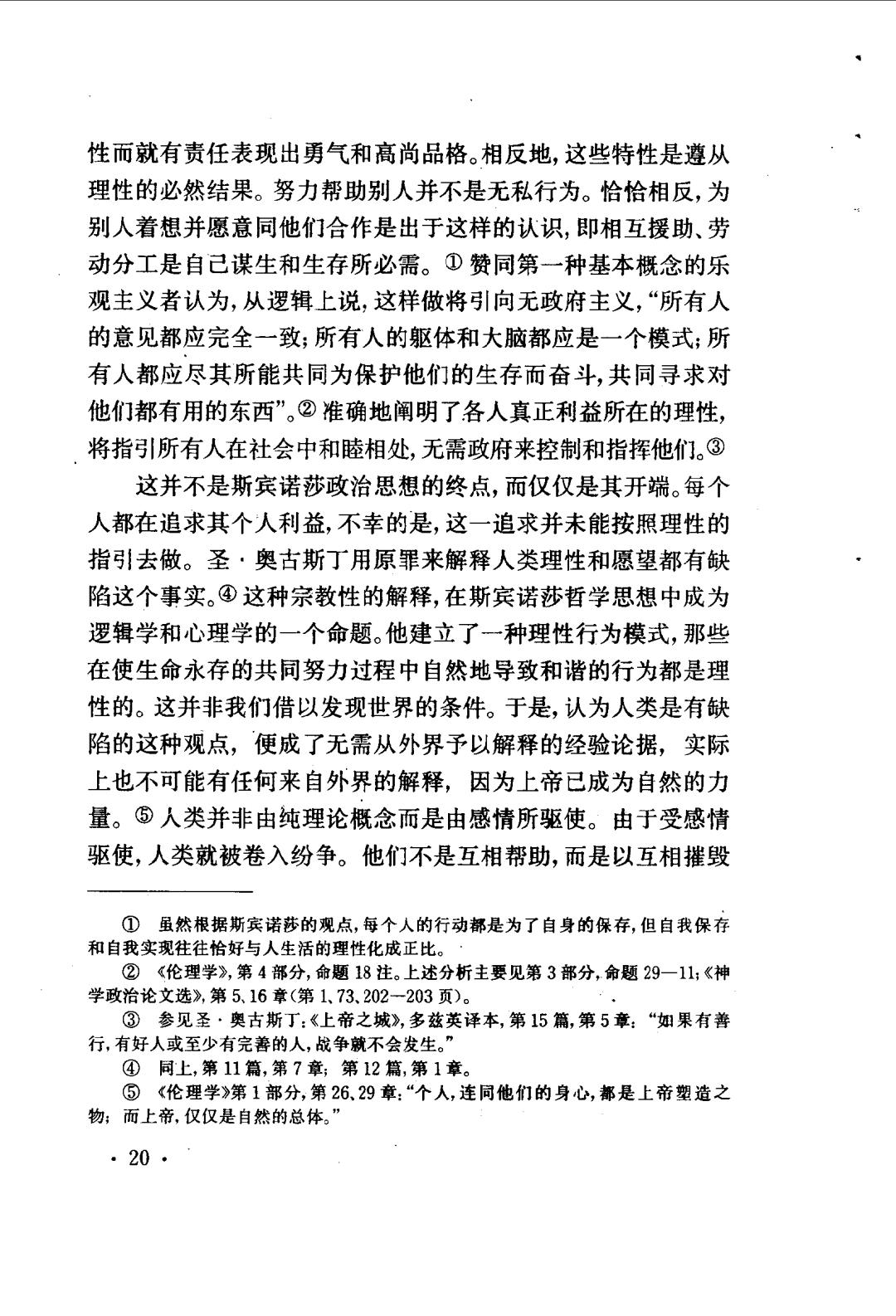
性而就有责任表现出勇气和高尚品格。相反地,这些特性是遵从 理性的必然结果。努力帮助别人并不是无私行为。恰恰相反,为 别人着想并愿意同他们合作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即相互援助、劳 动分工是自己谋生和生存所必需。①赞同第一种基本概念的乐 观主义者认为,从逻辑上说,这样做将引向无政府主义,“所有人 的意见都应完全一致;所有人的躯体和大脑都应是一个模式;所 有人都应尽其所能共同为保护他们的生存而奋斗,共同寻求对 他们都有用的东西”。②准确地阐明了各人真正利益所在的理性, 将指引所有人在社会中和睦相处,无需政府来控制和指挥他们,③ 这并不是斯宾诺莎政治思想的终点,而仅仅是其开端。每个 人都在追求其个人利益,不幸的是,这一追求并未能按照理性的 指引去做。圣·奥古斯丁用原罪来解释人类理性和愿望都有缺 陷这个事实。④这种宗教性的解释,在斯宾诺莎哲学思想中成为 逻辑学和心理学的一个命题。他建立了一种理性行为模式,那些 在使生命永存的共同努力过程中自然地导致和谐的行为都是理 性的。这并非我们借以发现世界的条件。于是,认为人类是有缺 陷的这种观点,便成了无需从外界予以解释的经验论据,实际 上也不可能有任何来自外界的解释,因为上帝已成为自然的力 量。⑤人类并非由纯理论概念而是由感情所驱使。由于受感情 驱使,人类就被卷入纷争。他们不是互相帮助,而是以互相摧毁 ①虽然根据斯宾诺莎的观点,每个人的行动都是为了自身的保存,但自我保存 和自我实现往往恰好与人生活的理性化成正比。 ②《伦理学》,第4部分,命题18注。上述分析主要见第3部分,命题29一11;《神 学政治论文选》,第5、16章(第1、73、202一203页)。 ③参见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多兹英译本,第15篇,第5章:“如果有善 行,有好人或至少有完善的人,战争就不会发生。” ④同上,第11篇,第7章;第12篇,第1章。 ⑤《伦理学》第1部分,第26、29章:“个人,连同他们的身心,都是上帝塑造之 物;而上帝,仅仅是自然的总体。”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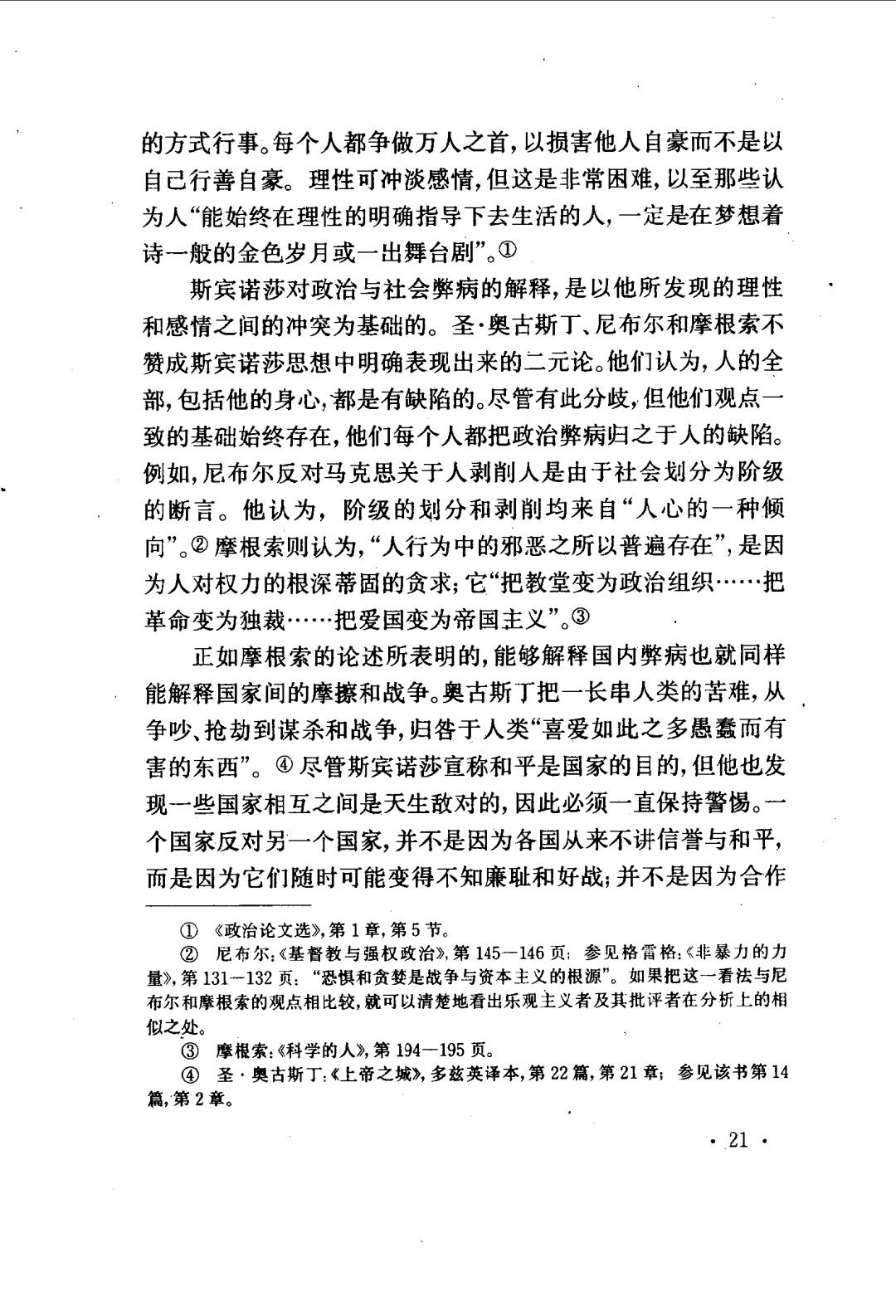
的方式行事。每个人都争做万人之首,以损害他人自豪而不是以 自己行善自豪。理性可冲淡感情,但这是非常困难,以至那些认 为人“能始终在理性的明确指导下去生活的人,一定是在梦想着 诗一般的金色岁月或一出舞台剧”。① 斯宾诺莎对政治与社会弊病的解释,是以他所发现的理性 和感情之间的冲突为基础的。圣·奥古斯丁、尼布尔和摩根索不 赞成斯宾诺莎思想中明确表现出来的二元论。他们认为,人的全 部,包括他的身心,都是有缺陷的。尽管有此分歧,但他们观点一 致的基础始终存在,他们每个人都把政治弊病归之于人的缺陷。 例如,尼布尔反对马克思关于人剥削人是由于社会划分为阶级 的断言。他认为,阶级的划分和剥削均来自“人心的一种倾 向”。②摩根索则认为,“人行为中的邪恶之所以普遍存在”,是因 为人对权力的根深蒂固的贪求;它“把教堂变为政治组织…把 革命变为独裁…把爱国变为帝国主义”。③ 正如摩根索的论述所表明的,能够解释国内弊病也就同样 能解释国家间的摩擦和战争。奥古斯丁把一长串人类的苦难,从 争吵、抢劫到谋杀和战争,归咎于人类“喜爱如此之多愚蠢而有 害的东西”。④尽管斯宾诺莎宣称和平是国家的目的,但他也发 现一些国家相互之间是天生敌对的,因此必须一直保持警惕。一 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并不是因为各国从来不讲信誉与和平, 而是因为它们随时可能变得不知廉耻和好战:并不是因为合作 ①《政治论文选》,第1章,第5节。 ②尼布尔:《基督教与强权政治》,第145一146页;参见格雷格:《非暴力的力 量》,第131一132页:“恐惧和贪婪是战争与资本主义的根源”。如果把这一看法与尼 布尔和摩根索的观点相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乐观主义者及其批评者在分析上的相 似之处。 ③摩根索:《科学的人》,第194一195页。 ④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多兹英译本,第22篇,第21章;参见该书第14 篇,第2章。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