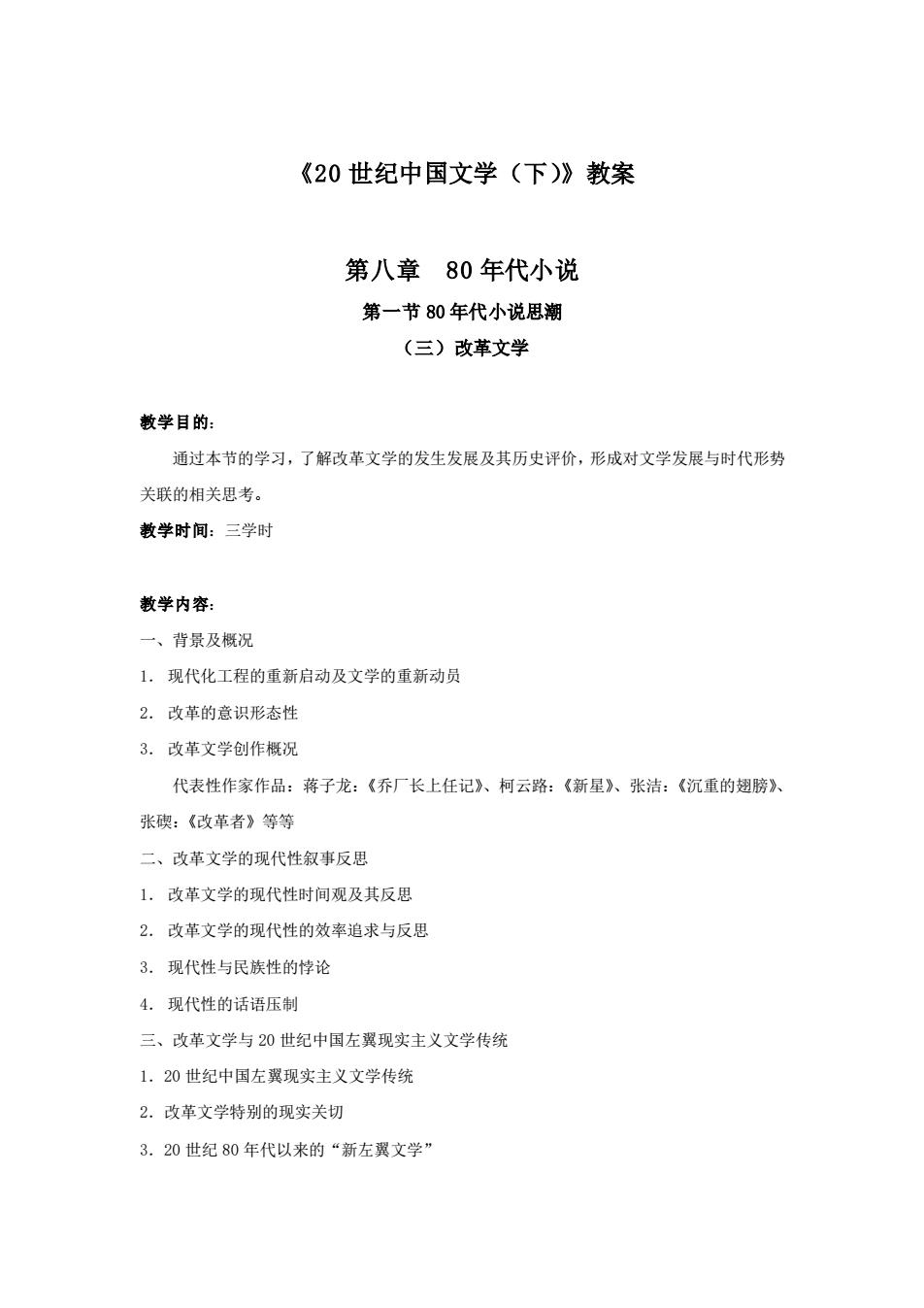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文学(下)》教案 第八章80年代小说 第一节80年代小说思潮 (三)改革文学 教学目的: 通过本节的学习,了解改革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历史评价,形成对文学发展与时代形势 关联的相关思考。 教学时间:三学时 教学内容 一、背景及概况 1.现代化工程的重新启动及文学的重新动员 2.改革的意识形态性 3.改革文学创作概况 代表性作家作品: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新星》、张洁:《沉重的翅膀》、 张奥:《改革者》等等 二、改革文学的现代性叙事反思 1.改革文学的现代性时间观及其反思 2。改革文学的现代性的效率追求与反思 3.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悖论 4.现代性的话语压制 三、改革文学与20世纪中国左翼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1.20世纪中国左翼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2.改革文学特别的现实关切 3.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左翼文学
《20 世纪中国文学(下)》教案 第八章 80 年代小说 第一节 80 年代小说思潮 (三)改革文学 教学目的: 通过本节的学习,了解改革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历史评价,形成对文学发展与时代形势 关联的相关思考。 教学时间:三学时 教学内容: 一、背景及概况 1. 现代化工程的重新启动及文学的重新动员 2. 改革的意识形态性 3. 改革文学创作概况 代表性作家作品: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新星》、张洁:《沉重的翅膀》、 张碶:《改革者》等等 二、改革文学的现代性叙事反思 1. 改革文学的现代性时间观及其反思 2. 改革文学的现代性的效率追求与反思 3. 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悖论 4. 现代性的话语压制 三、改革文学与 20 世纪中国左翼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1.20 世纪中国左翼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2.改革文学特别的现实关切 3.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新左翼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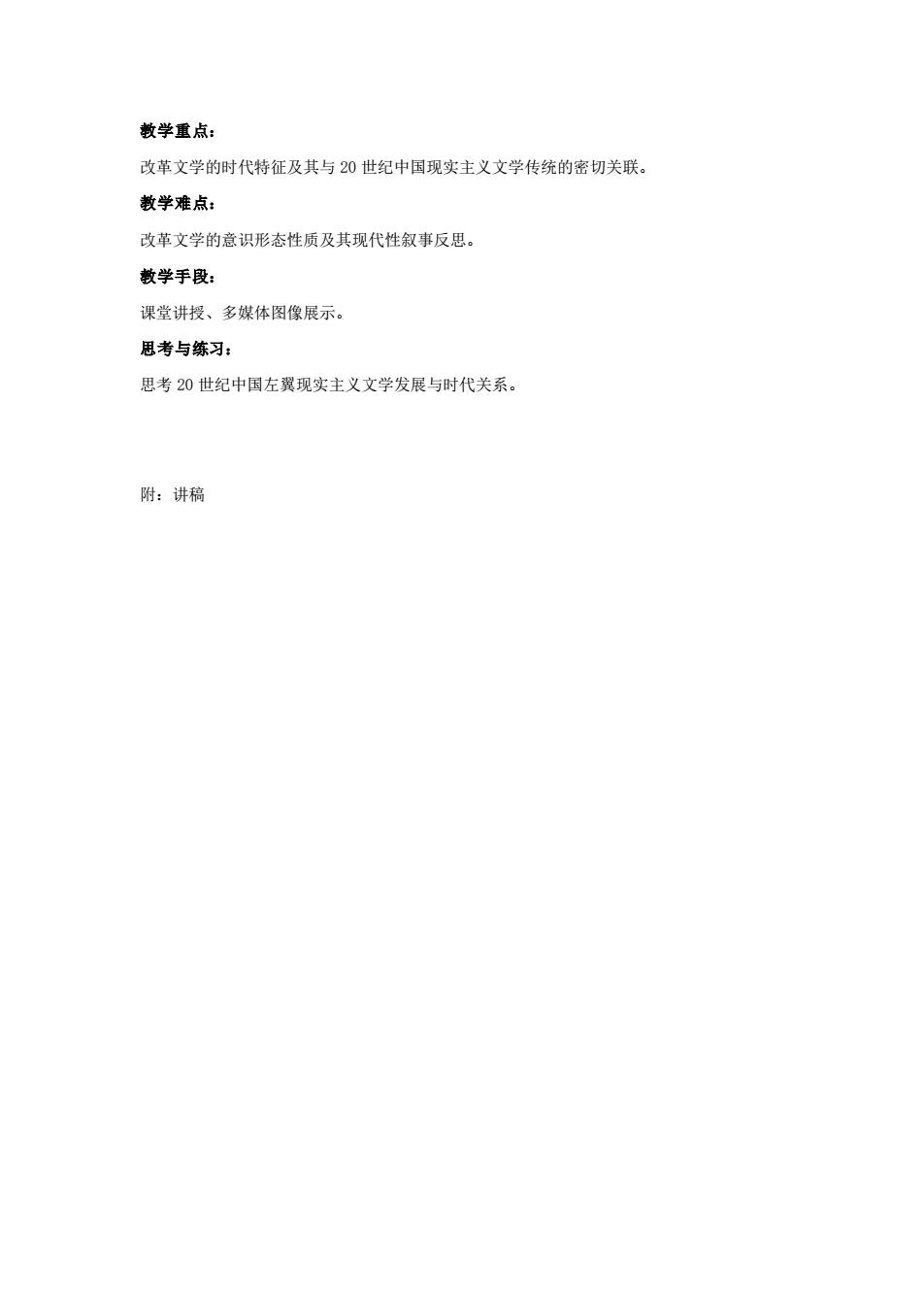
敕学重点: 改革文学的时代特征及其与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密切关联。 教学难点: 改革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及其现代性叙事反思, 敦学手段: 课堂讲投、多媒体图像展示 思考与练习: 思考20世纪中国左翼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与时代关系。 附:讲稿
教学重点: 改革文学的时代特征及其与 20 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密切关联。 教学难点: 改革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及其现代性叙事反思。 教学手段: 课堂讲授、多媒体图像展示。 思考与练习: 思考 20 世纪中国左翼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与时代关系。 附:讲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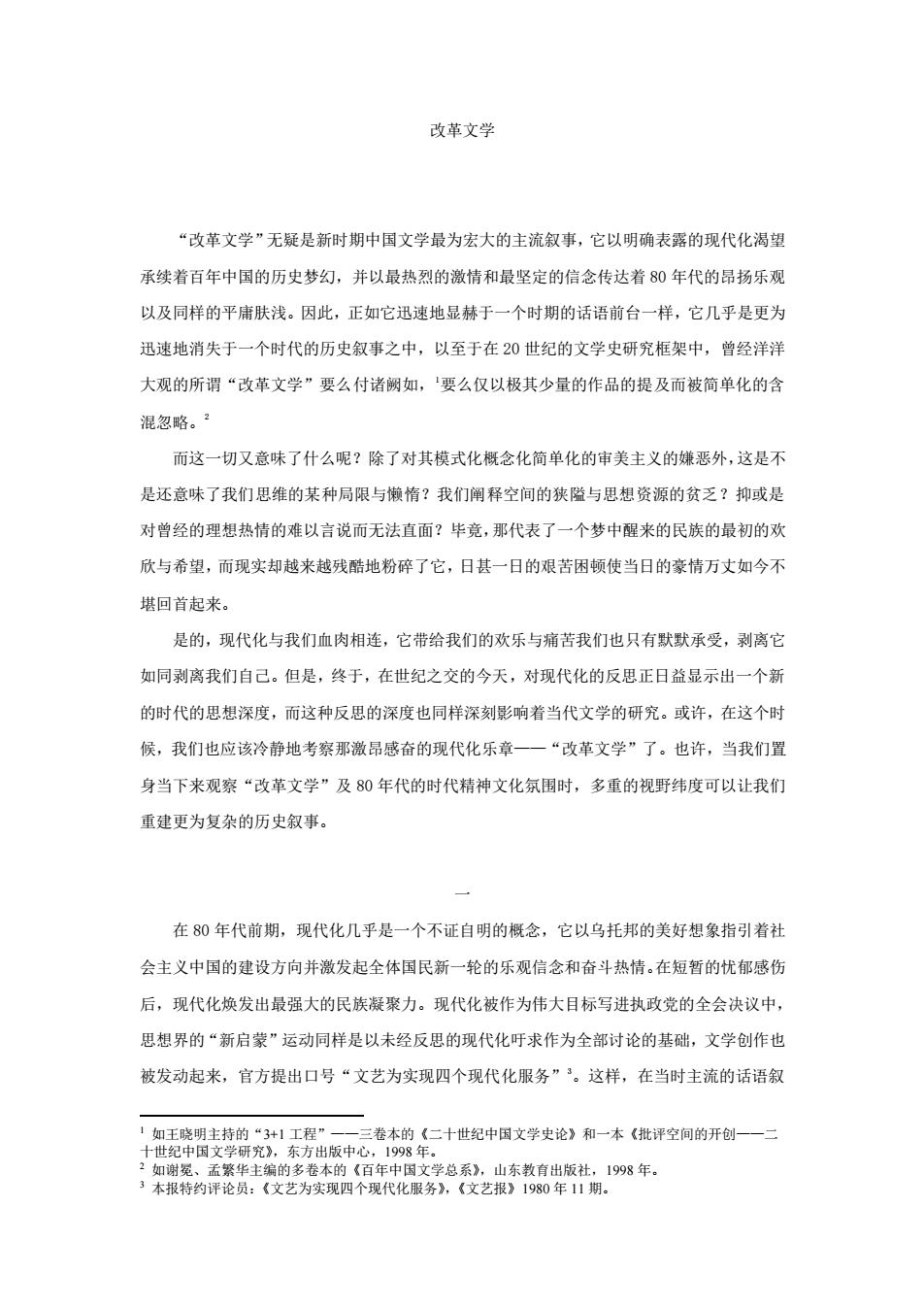
改革文学 “改革文学”无疑是新时期中国文学最为宏大的主流叙事,它以明确表露的现代化渴望 承续着百年中国的历史梦幻,并以最热烈的激情和最坚定的信念传达着80年代的昂扬乐观 以及同样的平庸肤浅。因此,正如它迅速地显赫于一个时期的话语前台一样,它几乎是更为 迅速地消失于一个时代的历史叙事之中,以至于在20世纪的文学史研究框架中,曾经洋洋 大观的所谓“改革文学”要么付诸阙如,'要么仅以极其少量的作品的提及而被简单化的含 混忽路。 而这一切又意味了什么呢?除了对其模式化概念化简单化的审美主义的嫌恶外,这是不 是还意味了我们思维的某种局限与懒惰?我们阐释空间的狭隘与思想资源的贫乏?抑或是 对曾经的理想热情的难以言说而无法直面?毕竟,那代表了一个梦中醒来的民族的最初的欢 欣与希望,而现实却越来越残酷地粉碎了它,日甚一日的艰苦困倾使当日的豪情万丈如今不 堪回首起来。 是的,现代化与我们血肉相连,它带给我们的欢乐与痛苦我们也只有默默承受,剥离它 如同剥离我们自己。但是,终于,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对现代化的反思正日益显示出一个新 的时代的思想深度,而这种反思的深度也同样深刻影响着当代文学的研究。或许,在这个时 候,我们也应该冷静地考察那激昂感奋的现代化乐章一一“改革文学”了。也许,当我们置 身当下来观察“改革文学”及80年代的时代精神文化氛围时,多重的视野纬度可以让我们 重建更为复杂的历史叙事。 在80年代前期,现代化几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它以乌托邦的美好想象指引者社 会主义中国的建设方向并激发起全体国民新一轮的乐观信念和奋斗热情,在短暂的忧郁感伤 后,现代化焕发出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现代化被作为伟大目标写进执政党的全会决议中, 思想界的“新启蒙”运动同样是以未经反思的现代化吁求作为全部讨论的基础,文学创作也 被发动起来,官方提出口号“文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这样,在当时主流的话语叙 如王晓明主持的“3+1工程 三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和一本《批评空间的开创一一二 十谢实 方出的百年 的秋之高华什咖年
改革文学 “改革文学”无疑是新时期中国文学最为宏大的主流叙事,它以明确表露的现代化渴望 承续着百年中国的历史梦幻,并以最热烈的激情和最坚定的信念传达着 80 年代的昂扬乐观 以及同样的平庸肤浅。因此,正如它迅速地显赫于一个时期的话语前台一样,它几乎是更为 迅速地消失于一个时代的历史叙事之中,以至于在 20 世纪的文学史研究框架中,曾经洋洋 大观的所谓“改革文学”要么付诸阙如,1要么仅以极其少量的作品的提及而被简单化的含 混忽略。2 而这一切又意味了什么呢?除了对其模式化概念化简单化的审美主义的嫌恶外,这是不 是还意味了我们思维的某种局限与懒惰?我们阐释空间的狭隘与思想资源的贫乏?抑或是 对曾经的理想热情的难以言说而无法直面?毕竟,那代表了一个梦中醒来的民族的最初的欢 欣与希望,而现实却越来越残酷地粉碎了它,日甚一日的艰苦困顿使当日的豪情万丈如今不 堪回首起来。 是的,现代化与我们血肉相连,它带给我们的欢乐与痛苦我们也只有默默承受,剥离它 如同剥离我们自己。但是,终于,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对现代化的反思正日益显示出一个新 的时代的思想深度,而这种反思的深度也同样深刻影响着当代文学的研究。或许,在这个时 候,我们也应该冷静地考察那激昂感奋的现代化乐章——“改革文学”了。也许,当我们置 身当下来观察“改革文学”及 80 年代的时代精神文化氛围时,多重的视野纬度可以让我们 重建更为复杂的历史叙事。 一 在 80 年代前期,现代化几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它以乌托邦的美好想象指引着社 会主义中国的建设方向并激发起全体国民新一轮的乐观信念和奋斗热情。在短暂的忧郁感伤 后,现代化焕发出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现代化被作为伟大目标写进执政党的全会决议中, 思想界的“新启蒙”运动同样是以未经反思的现代化吁求作为全部讨论的基础,文学创作也 被发动起来,官方提出口号“文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3。这样,在当时主流的话语叙 1 如王晓明主持的“3+1 工程”——三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和一本《批评空间的开创——二 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 年。 2 如谢冕、孟繁华主编的多卷本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年。 3 本报特约评论员:《文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文艺报》1980 年 1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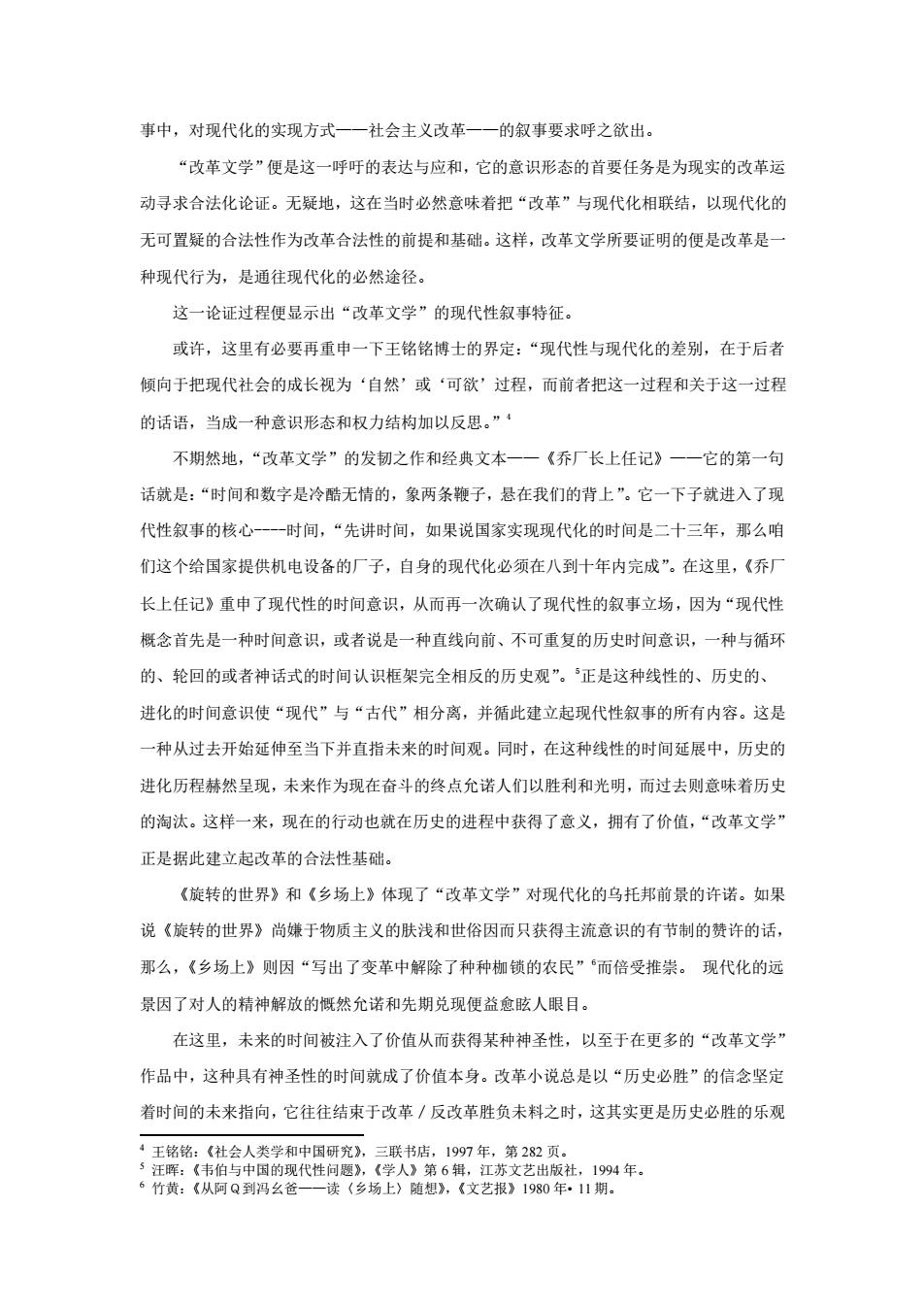
事中,对现代化的实现方式一一社会主义改革一一的叙事要求呼之欲出。 “改革文学”便是这一呼吁的表达与应和,它的意识形态的首要任务是为现实的改革运 动寻求合法化论证。无疑地,这在当时必然意味着把“改革”与现代化相联结,以现代化的 无可置疑的合法性作为改革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础。这样,改革文学所要证明的便是改革是 种现代行为,是通往现代化的必然途径。 这一论证过程便显示出“改革文学”的现代性叙事特征。 或许,这里有必要再重申一下王铭铭博士的界定:“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差别,在于后者 倾向于把现代社会的成长视为‘自然'或‘可欲'过程,而前者把这一过程和关于这一过程 的话语,当成一种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加以反思。”‘ 不期然地,“改革文学”的发韧之作和经典文本一一《乔厂长上任记》一一它的第一句 话就是:“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象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它一下子就进入了现 代性叙事的核心一时间,“先讲时间,如果说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那么咱 们这个给国家提供机电设备的厂子,自身的现代化必须在八到十年内完成”。在这里,《乔厂 长上任记》重申了现代性的时间意识,从而再一次确认了现代性的叙事立场,因为“现代性 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 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正是这种线性的、历史的、 进化的时间意识使“现代”与“古代”相分离,并循此建立起现代性叙事的所有内容。这是 一种从过去开始延伸至当下并直指未来的时间观。同时,在这种线性的时间延展中,历史的 进化历程赫然呈现,未来作为现在奋斗的终点允诺人们以胜利和光明,而过去则意味着历史 的淘汰。这样一来,现在的行动也就在历史的进程中获得了意义,拥有了价值,“改革文学" 正是据此建立起改革的合法性基础。 《旋转的世界》和《乡场上》体现了“改革文学”对现代化的乌托邦前景的许诺。如果 说《旋转的世界》尚嫌于物质主义的肤浅和世俗因而只获得主流意识的有节制的赞许的话, 那么,《乡场上》则因“写出了变革中解除了种种枷锁的农民”而倍受推崇。现代化的远 景因了对人的精神解放的概然允诺和先期兑现便益愈眩人眼目。 在这里,未来的时间被注入了价值从而获得某种神圣性,以至于在更多的“改革文学” 作品中,这种具有神圣性的时间就成了价值本身。改革小说总是以“历史必胜”的信念坚定 若时间的未来指向,它往往结束于改革/反改革胜负未料之时,这其实更是历史必胜的乐观 。行黄:《从同到3么爸读《乡场随想,《文艺报)1980年·1期
事中,对现代化的实现方式——社会主义改革——的叙事要求呼之欲出。 “改革文学”便是这一呼吁的表达与应和,它的意识形态的首要任务是为现实的改革运 动寻求合法化论证。无疑地,这在当时必然意味着把“改革”与现代化相联结,以现代化的 无可置疑的合法性作为改革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础。这样,改革文学所要证明的便是改革是一 种现代行为,是通往现代化的必然途径。 这一论证过程便显示出“改革文学”的现代性叙事特征。 或许,这里有必要再重申一下王铭铭博士的界定:“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差别,在于后者 倾向于把现代社会的成长视为‘自然’或‘可欲’过程,而前者把这一过程和关于这一过程 的话语,当成一种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加以反思。”4 不期然地,“改革文学”的发韧之作和经典文本——《乔厂长上任记》——它的第一句 话就是:“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象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它一下子就进入了现 代性叙事的核心-时间,“先讲时间,如果说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那么咱 们这个给国家提供机电设备的厂子,自身的现代化必须在八到十年内完成”。在这里,《乔厂 长上任记》重申了现代性的时间意识,从而再一次确认了现代性的叙事立场,因为“现代性 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 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5正是这种线性的、历史的、 进化的时间意识使“现代”与“古代”相分离,并循此建立起现代性叙事的所有内容。这是 一种从过去开始延伸至当下并直指未来的时间观。同时,在这种线性的时间延展中,历史的 进化历程赫然呈现,未来作为现在奋斗的终点允诺人们以胜利和光明,而过去则意味着历史 的淘汰。这样一来,现在的行动也就在历史的进程中获得了意义,拥有了价值,“改革文学” 正是据此建立起改革的合法性基础。 《旋转的世界》和《乡场上》体现了“改革文学”对现代化的乌托邦前景的许诺。如果 说《旋转的世界》尚嫌于物质主义的肤浅和世俗因而只获得主流意识的有节制的赞许的话, 那么,《乡场上》则因“写出了变革中解除了种种枷锁的农民”6而倍受推崇。 现代化的远 景因了对人的精神解放的慨然允诺和先期兑现便益愈眩人眼目。 在这里,未来的时间被注入了价值从而获得某种神圣性,以至于在更多的“改革文学” 作品中,这种具有神圣性的时间就成了价值本身。改革小说总是以“历史必胜”的信念坚定 着时间的未来指向,它往往结束于改革/反改革胜负未料之时,这其实更是历史必胜的乐观 4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和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 年,第 282 页。 5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学人》第 6 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年。 6 竹黄:《从阿Q到冯幺爸——读〈乡场上〉随想》,《文艺报》1980 年• 1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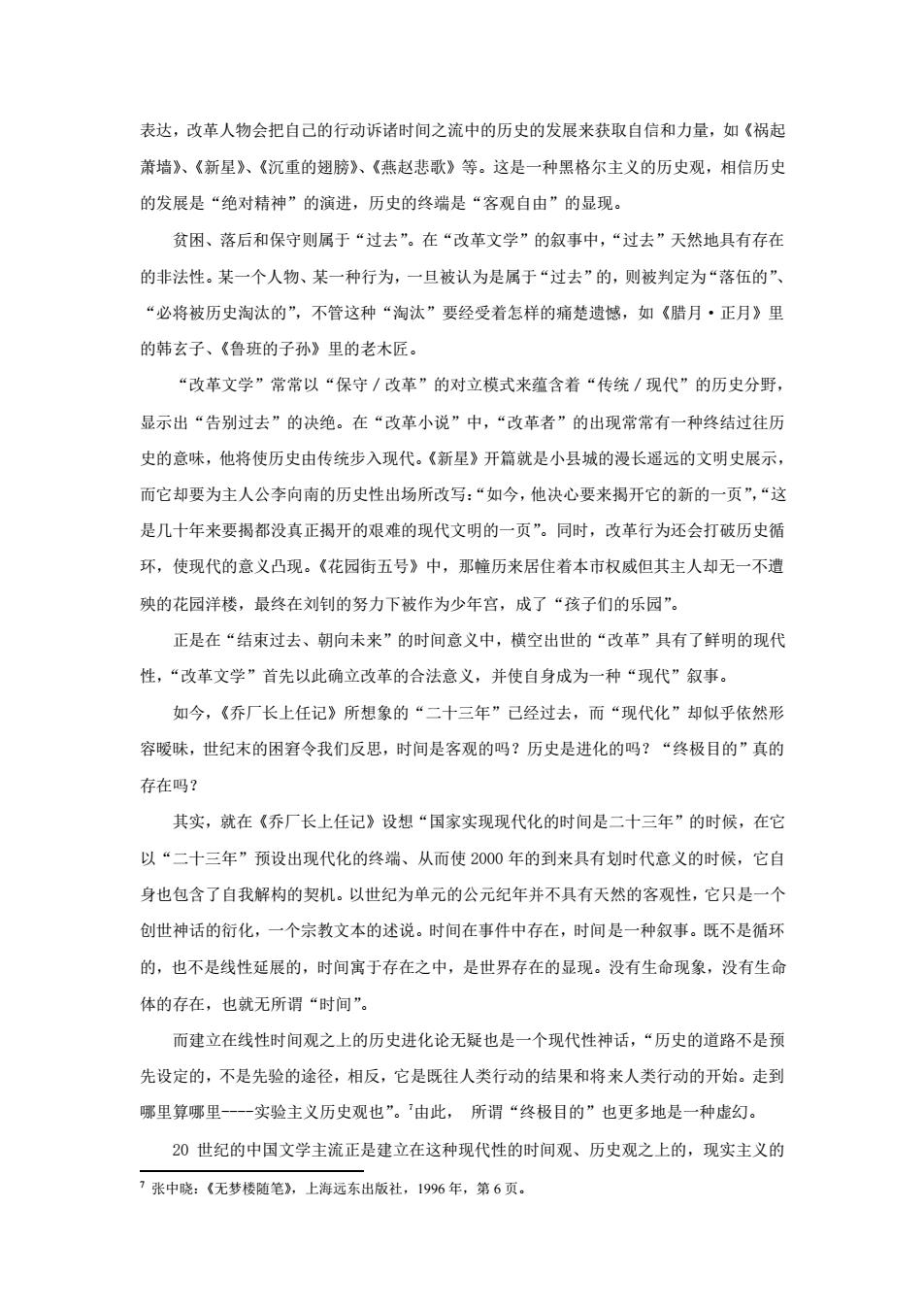
表达,改革人物会把自己的行动诉诸时间之流中的历史的发展来获取自信和力量,如《祸起 萧培》、《新星》、《沉重的翅膀》、《燕赵悲歌》等。这是一种黑格尔主义的历史观,相信历史 的发展是“绝对精神”的演进,历史的终端是“客观自由”的显现。 贫困、落后和保守则属于“过去”。在“改革文学”的叙事中,“过去”天然地具有存在 的非法性。某一个人物、某一种行为,一旦被认为是属于“过去”的,则被判定为“落伍的”、 “必将被历史淘汰的”,不管这种“淘汰”要经受着怎样的痛楚遗憾,如《腊月·正月》里 的韩玄子、《鲁班的子孙》里的老木匠。 “改革文学”常常以“保守/改革”的对立模式来蕴含着“传统/现代”的历史分野。 显示出“告别过去”的决绝。在“改革小说”中,“改革者”的出现常常有一种终结过往历 史的意味,他将使历史由传统步入现代。《新星》开篇就是小县城的漫长遥远的文明史展示, 而它却要为主人公李向南的历史性出场所改写:“如今,他决心要来揭开它的新的一页”,“这 是几十年来要揭都没真正揭开的艰难的现代文明的一页”。同时,改革行为还会打破历史循 环,使现代的意义凸现。《花园街五号》中,那幢历来居住着本市权威但其主人却无一不遭 殃的花园洋楼,最终在刘钊的努力下被作为少年宫,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正是在“结束过去、朝向未来”的时间意义中,横空出世的“改革”具有了鲜明的现代 性,“改革文学”首先以此确立改革的合法意义,并使自身成为一种“现代”叙事。 如今,《乔厂长上任记》所想象的“二十三年”已经过去,而“现代化”却似乎依然形 容暖味,世纪末的困窘令我们反思,时间是客观的吗?历史是进化的吗?“终极目的”真的 存在吗? 其实,就在《乔厂长上任记》设想“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的时候,在它 以“二十三年”预设出现代化的终端、从而使2000年的到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候,它自 身也包含了自我解构的契机。以世纪为单元的公元纪年并不具有天然的客观性,它只是一个 创世神话的衍化,一个宗教文本的述说。时间在事件中存在,时间是一种叙事。既不是循环 的,也不是线性延展的,时间寓于存在之中,是世界存在的显现。没有生命现象,没有生命 体的存在,也就无所谓“时间”。 而建立在线性时间观之上的历史进化论无疑也是一个现代性神话,“历史的道路不是预 先设定的,不是先验的途径,相反,它是既往人类行动的结果和将来人类行动的开始。走到 哪里算哪里一实验主义历史观也”。由此,所谓“终极目的”也更多地是一种虚幻。 0世纪的中国文学主流正是建立在这种现代性的时间观、历史观之上的,现实主义的 7张中晓:(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6页
表达,改革人物会把自己的行动诉诸时间之流中的历史的发展来获取自信和力量,如《祸起 萧墙》、《新星》、《沉重的翅膀》、《燕赵悲歌》等。这是一种黑格尔主义的历史观,相信历史 的发展是“绝对精神”的演进,历史的终端是“客观自由”的显现。 贫困、落后和保守则属于“过去”。在“改革文学”的叙事中,“过去”天然地具有存在 的非法性。某一个人物、某一种行为,一旦被认为是属于“过去”的,则被判定为“落伍的”、 “必将被历史淘汰的”,不管这种“淘汰”要经受着怎样的痛楚遗憾,如《腊月·正月》里 的韩玄子、《鲁班的子孙》里的老木匠。 “改革文学”常常以“保守/改革”的对立模式来蕴含着“传统/现代”的历史分野, 显示出“告别过去”的决绝。在“改革小说”中,“改革者”的出现常常有一种终结过往历 史的意味,他将使历史由传统步入现代。《新星》开篇就是小县城的漫长遥远的文明史展示, 而它却要为主人公李向南的历史性出场所改写:“如今,他决心要来揭开它的新的一页”,“这 是几十年来要揭都没真正揭开的艰难的现代文明的一页”。同时,改革行为还会打破历史循 环,使现代的意义凸现。《花园街五号》中,那幢历来居住着本市权威但其主人却无一不遭 殃的花园洋楼,最终在刘钊的努力下被作为少年宫,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正是在“结束过去、朝向未来”的时间意义中,横空出世的“改革”具有了鲜明的现代 性,“改革文学”首先以此确立改革的合法意义,并使自身成为一种“现代”叙事。 如今,《乔厂长上任记》所想象的“二十三年”已经过去,而“现代化”却似乎依然形 容暧昧,世纪末的困窘令我们反思,时间是客观的吗?历史是进化的吗?“终极目的”真的 存在吗? 其实,就在《乔厂长上任记》设想“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的时候,在它 以“二十三年”预设出现代化的终端、从而使 2000 年的到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候,它自 身也包含了自我解构的契机。以世纪为单元的公元纪年并不具有天然的客观性,它只是一个 创世神话的衍化,一个宗教文本的述说。时间在事件中存在,时间是一种叙事。既不是循环 的,也不是线性延展的,时间寓于存在之中,是世界存在的显现。没有生命现象,没有生命 体的存在,也就无所谓“时间”。 而建立在线性时间观之上的历史进化论无疑也是一个现代性神话,“历史的道路不是预 先设定的,不是先验的途径,相反,它是既往人类行动的结果和将来人类行动的开始。走到 哪里算哪里-实验主义历史观也”。7由此, 所谓“终极目的”也更多地是一种虚幻。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主流正是建立在这种现代性的时间观、历史观之上的,现实主义的 7 张中晓:《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第 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