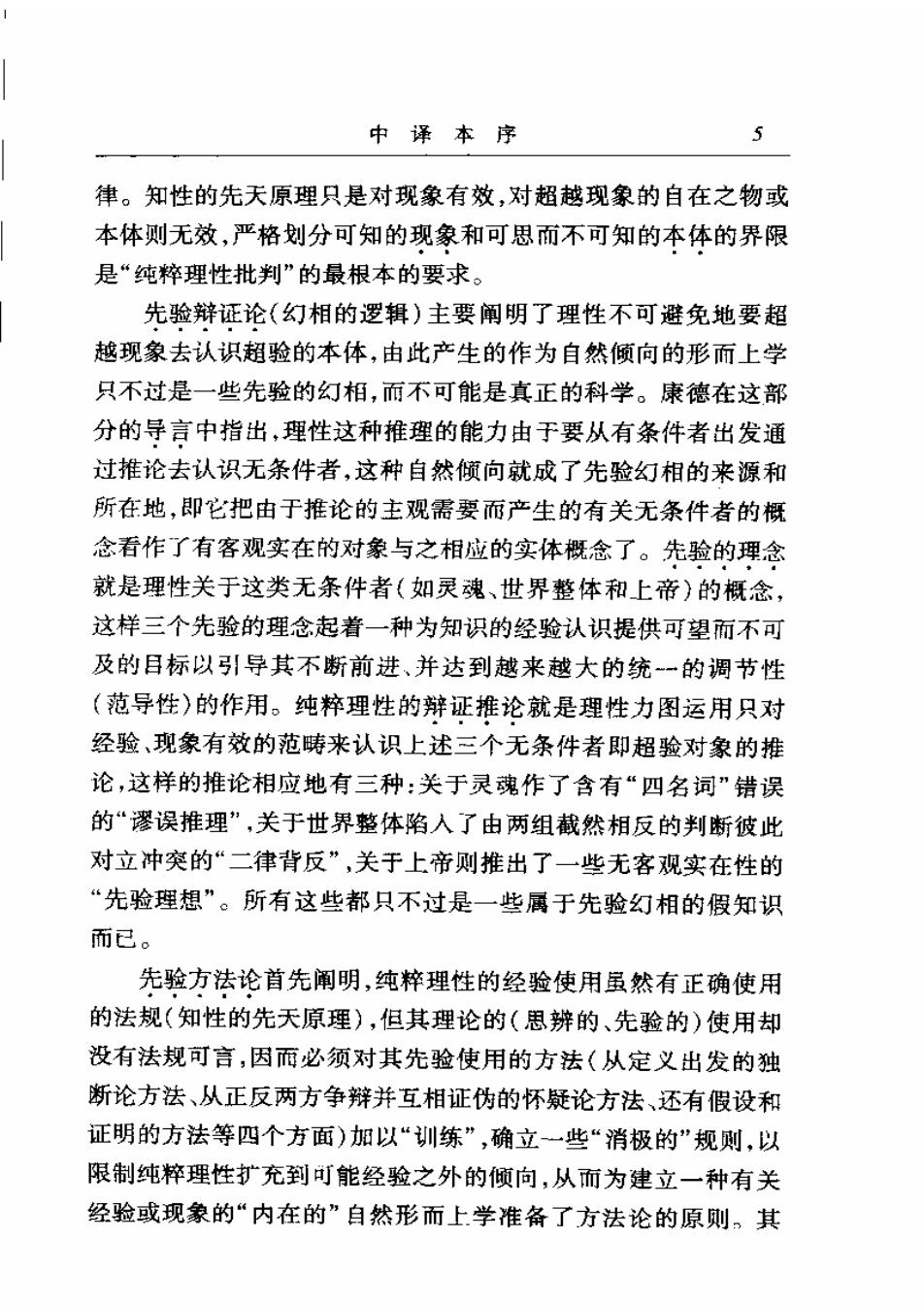
中译本序 5 律。知性的先天原理只是对现象有效,对超越现象的自在之物或 本体则无效,严格划分可知的现象和可思而不可知的本体的界限 是“纯粹理性批判”的最根本的要求。 先验辩证论(幻相的逻辑)主要阐明了理性不可避免地要超 越现象去认识超验的本体,由此产生的作为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 只不过是一些先验的幻相,而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康德在这部 分的导言中指出,理性这种推理的能力由于要从有条件者出发通 过推论去认识无条件者,这种自然倾向就成了先验幻相的来源和 所在地,即它把由于推论的主观需要而产生的有关无条件者的概 念看作了有客观实在的对象与之相应的实体概念了。先验的理念 就是理性关于这类无条件者(如灵魂、世界整体和上帝)的概念, 这样三个先验的理念起着一种为知识的经验认识提供可望而不可 及的目标以引导其不断前进、并达到越来越大的统一的调节性 (范导性)的作用。纯粹理性的辩证推论就是理性力图运用只对 经验、现象有效的范畴来认识上述三个无条件者即超验对象的推 论,这样的推论相应地有三种:关于灵魂作了含有“四名词”错误 的“谬误推理”,关于世界整体陷入了由两组截然相反的判断彼此 对立冲突的“二律背反”,关于上帝则推出了一些无客观实在性的 “先验理想”。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些属于先验幻相的假知识 而已。 先验方法论首先阐明,纯粹理性的经验使用虽然有正确使用 的法规(知性的先天原理),但其理论的(思辨的、先验的)使用却 没有法规可言,因而必须对其先验使用的方法(从定义出发的独 断论方法、从正反两方争辩并互相证伪的怀疑论方法、还有假设和 证明的方法等四个方面)加以“圳练”,确立一些“消极的”规则,以 限制纯粹理性扩充到可能经验之外的倾向,从而为建立一种有关 经验或现象的“内在的”自然形而上学准备了方法论的原则,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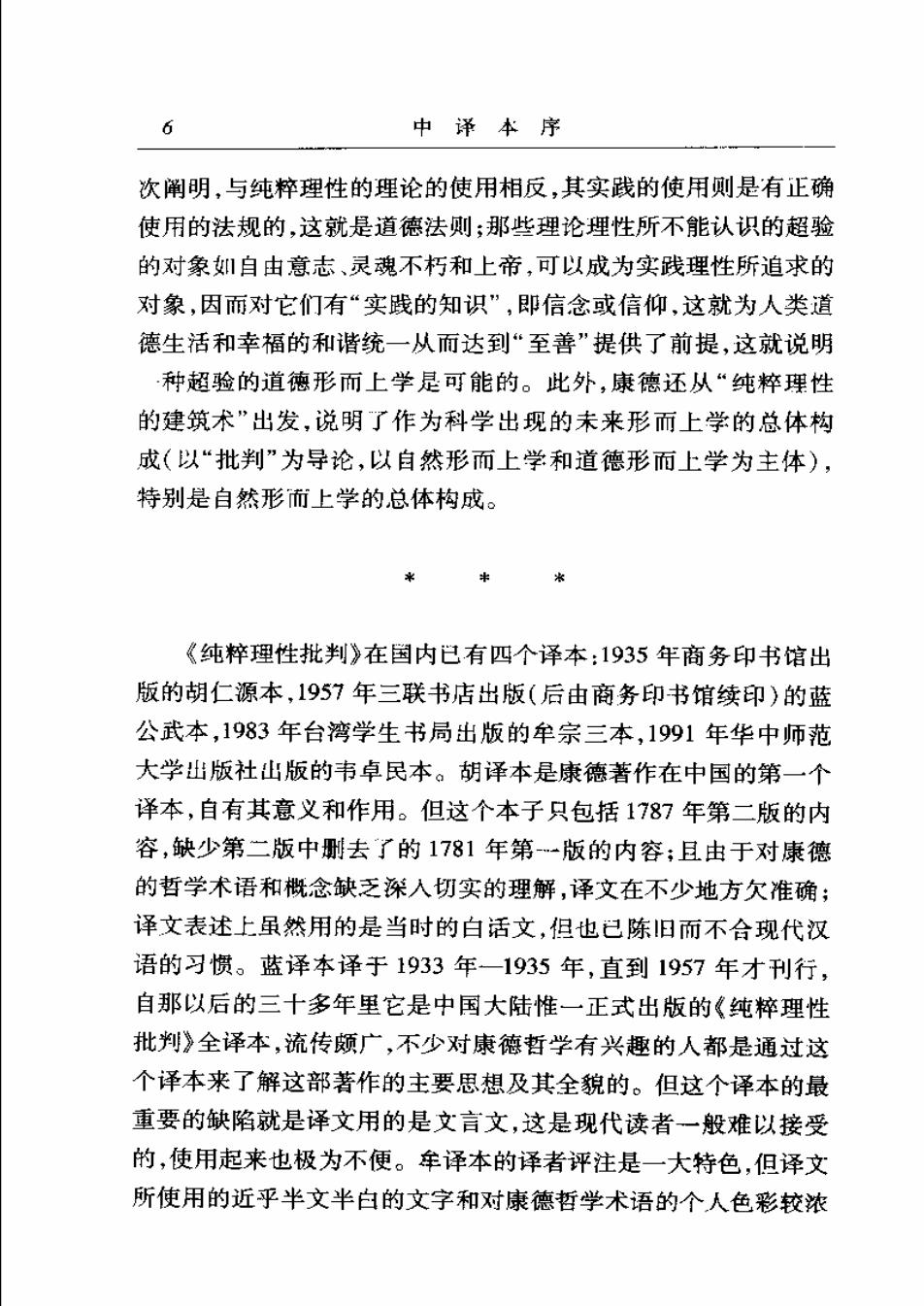
6 中译本序 次阐明,与纯粹理性的理论的使用相反,其实践的使用则是有正确 使用的法规的,这就是道德法则;那些理论理性所不能认识的超验 的对象自由意志、灵魂不朽和上帝,可以成为实践理性所追求的 对象,因而对它们有“实践的知识”,即信念或信仰,这就为人类道 德生活和幸福的和谐统一从而达到“至善”提供了前提,这就说明 种超验的道德形而上学是可能的。此外,康德还从“纯粹理性 的建筑术”出发,说明了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的总体构 成(以“批判”为导论,以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为主体), 特别是自然形而上学的总体构成。 《纯粹理性批判》在国内已有四个译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 版的胡仁源本,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后由商务印书馆续印)的蓝 公武本,1983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牟宗三本,1991年华中师范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韦卓民本。胡译本是康德著作在中国的第一个 译本,自有其意义和作用。但这个本子只包括1787年第二版的内 容,缺少第二版中删去了的1781年第一版的内容:且由于对康德 的哲学术语和概念缺乏深入切实的理解,译文在不少地方欠准确; 译文表述上虽然用的是当时的白话文,但也已陈旧而不合现代汉 语的习惯。蓝译本译于1933年一1935年,直到1957年才刊行, 自那以后的三十多年里它是中国大陆惟一正式出版的《纯粹理性 批判》全译本,流传颇广,不少对康德哲学有兴趣的人都是通过这 个译本来了解这部著作的主要思想及其全貌的。但这个译本的最 重要的缺陷就是译文用的是文言文,这是现代读者一般难以接受 的,使用起来也极为不便。牟译本的译者评注是一大特色,但译文 所使用的近乎半文半白的文字和对康德哲学术语的个人色彩较浓

中译本序 的译法也偏离了一般读者(特别是大陆读者)的习惯。韦译本的 初稿于1962年译出,直到1991年才经曹方久教授等人校整埋 出版。这个本子是用现代汉语译出的,对康德的某些术语、概念虽 有泽者异于通常的译法,但仍明白易懂,所馆注释也有益于增进理 解,从而使康德这部艰深难读的著作对于中国读者初次有了可读 性,这是我国康德译事中明显的进展。但是,包括韦译本在内的所 有这些译本的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它们都不是从德文原本而是 从英译本转译的,最多仅以德文版本作参考,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受 到英译本的限制,难以摆脱英译本的种种缺陷,如行文与德文原本 出入较大,错漏较多,译意不明确和欠准确,甚或与德文的原意相 左之处也不鲜见。显然,从英译本转译而来的译本很难令有志于 进一步学习和了解康德哲学的中国读者们满意,更不用说满足对 康德这部苣著作深入研究的人的迫切需要了。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个译本是《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五个中译 本,它不同于前面四个译本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从德文 原本直接移译过来的。这个译本从最初的尝试到最终的脱稿经历 了差不多近十年的时间, 1993年到1995年,我和邓晓芒教授计划共同撰写一部逐章 逐节解说康德这部巨著的书一《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①。 这样性质的著作不可避免地要有大量的原文引述。鉴于《纯粹理 性批判》一书现有几个中译本的情况,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 “引文均须从德文原本重新译出”。这个决定是有基础的,因为负 责提供《指要》初稿的邓晓芒当时已经翻译出版了康德的《实用人 类学》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两部著作,具有这方面的翻 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杨祖陶、邓晓芒著,湖南教育出版杜 1996年初版,人民出版社2002年再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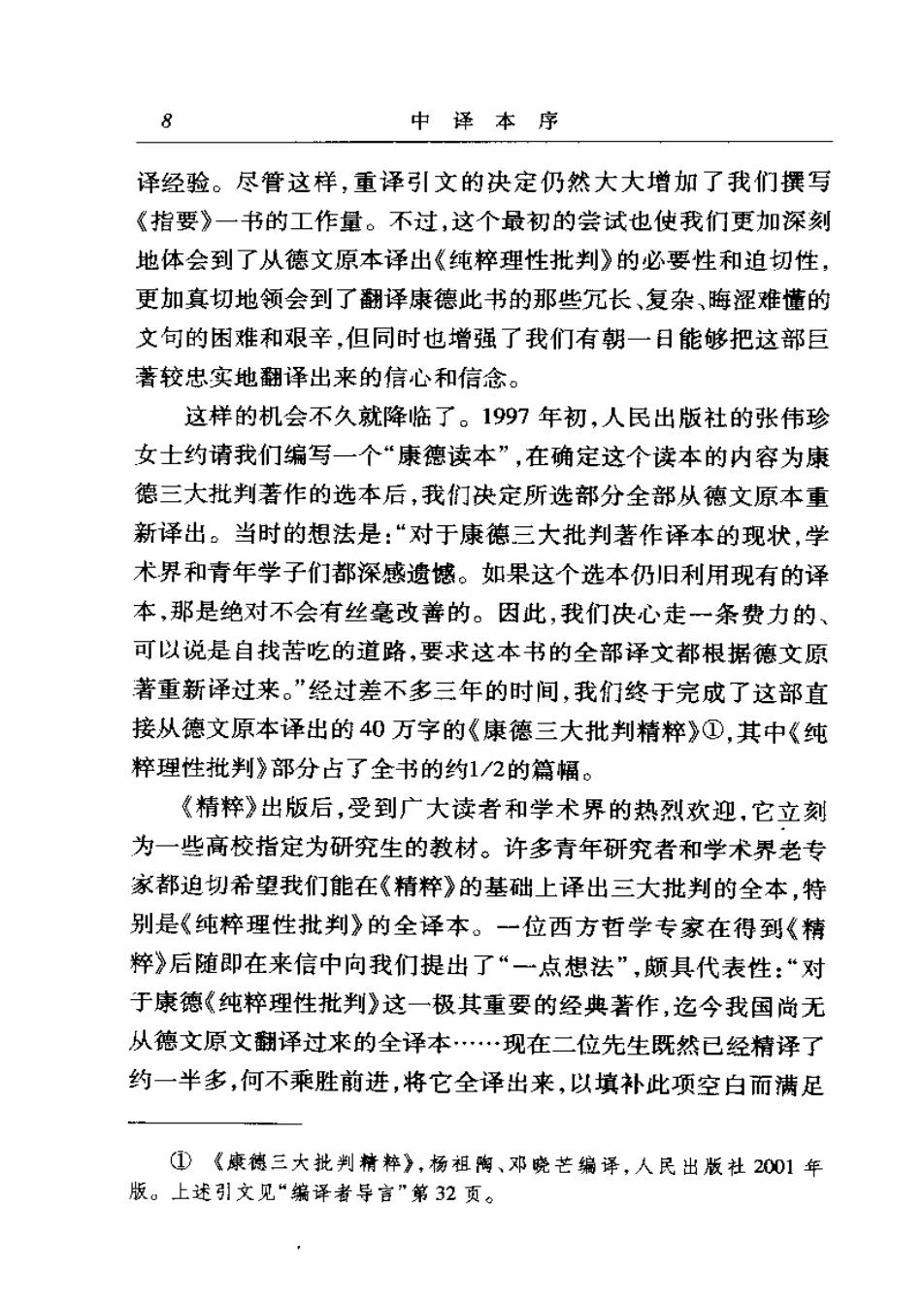
8 中译本序 译经验。尽管这样,重译引文的决定仍然大大增加了我们撰写 《指要》一书的工作量。不过,这个最初的尝试也使我们更加深刻 地体会到了从德文原本译出《纯粹理性批判》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更加真切地领会到了翻译康德此书的那些冗长、复杂、晦涩摊懂的 文句的困难和艰辛,但同时也增强了我们有朝一日能够把这部巨 著较忠实地翻译出来的信心和信念。 这样的机会不久就降临了。1997年初,人民出版社的张伟珍 女士约请我们编写一个“康德读本”,在确定这个读本的内容为康 德三大批判著作的选本后,我们决定所选部分全部从德文原本重 新译出。当时的想法是:“对于康德三大批判著作译本的现状,学 术界和青年学子们都深感遗憾。如果这个选本仍旧利用现有的译 本,那是绝对不会有丝毫改善的。因此,我们决心走一条费力的、 可以说是自找苦吃的道路,要求这本书的全部译文都根据德文原 著重新译过来。”经过差不多三年的时间,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部直 接从德文原本译出的40万字的《康德三大批判精粹》①,其中《纯 粹理性批判》部分占了全书的约1/2的篇幅。 《精粹》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和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它立刻 为一些高校指定为研究生的教材。许多青年研究者和学术界老专 家都迫切希望我们能在《精粹》的基础上译出三大批判的全本,特 别是《纯粹理性批判》的全译本。一位西方哲学专家在得到《精 粹》后随即在来信中向我们提出了“一点想法”,颇具代表性:“对 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这一极其重要的经典著作,迄今我国尚无 从德文原文翻译过来的全译本…现在二位先生既然已经精译了 约一半多,何不乘胜前进,将它全译出来,以填补此项空白而满足 (①《康德三大批判精粹》,杨祖陶、邓晓芒编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 版。上述引文见“编译者导言”第3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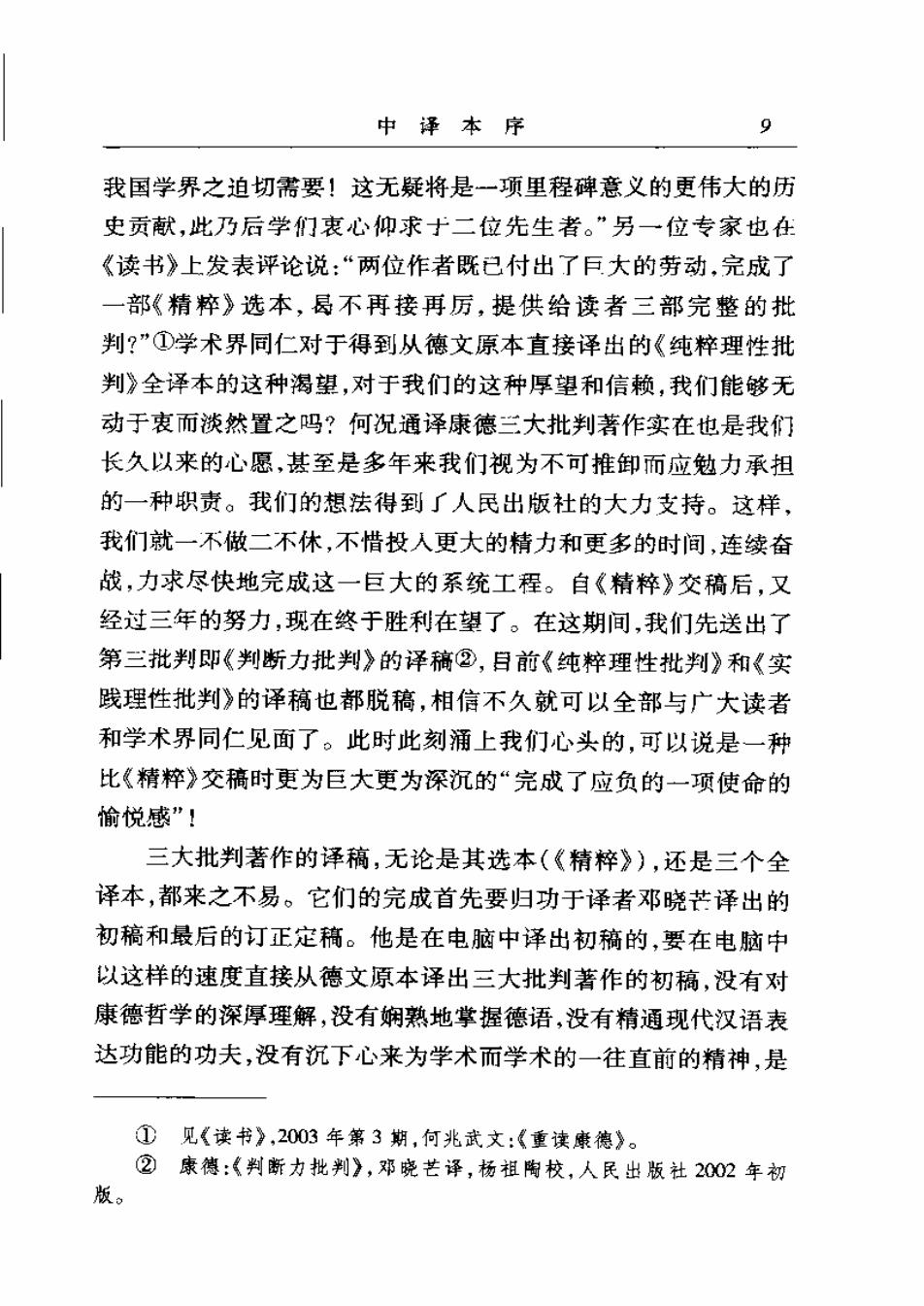
中译本序 9 我国学界之迫切需要!这无疑将是一项里程碑意义的更伟大的历 史贡献,此乃后学们衷心仰求于二位先生者。”另一位专家也在 《读书》上发表评论说:“两位作者既已付出了戶大的劳动,完成了 一部《精粹》选本,曷不再接再厉,提供给读者三部完整的批 判?”①学术界同仁对于得到从德文原本直接译出的《纯粹理性批 判》全译本的这种渴望,对于我们的这种厚望和信赖,我们能够无 动于衷而淡然置之吗?何况通译康德三大批判著作实在也是我们 长久以来的心愿,甚至是多年来我们视为不可推卸而应勉力承担 的一种职责。我们的想法得到了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这样, 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不惜投人更大的精力和更多的时间,连续奋 战,力求尽快地完成这一巨大的系统工程。自《精粹》交稿后,又 经过三年的努力,现在终于胜利在望了。在这期间,我们先送出了 第三批判即《判断力批判》的译稿②,目前《纯粹理性批判》和《实 践理性批判》的译稿也都脱稿,相信不久就可以全部与广大读者 和学术界同仁见面了。此时此刻涌上我们心头的,可以说是一种 比《精粹》交稿时更为巨大更为深沉的“完成了应负的一项使命的 愉悦感”! 三大批判著作的译稿,无论是其选本(《精粹》),还是三个全 译本,都来之不易。它们的完成首先要归功于译者邓晓芒译出的 初稿和最后的订正定稿。他是在电脑中译出初稿的,要在电脑中 以这样的速度直接从德文原本译出三大批判著作的初稿,没有对 康德哲学的深厚理解,没有娴熟地掌握德语,没有精通现代汉语表 达功能的功夫,没有沉下心来为学术而学术的一往直前的精神,是 ① 见《读书》,2003年第3期,何兆武文:《重读康德》。 ②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C02年初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