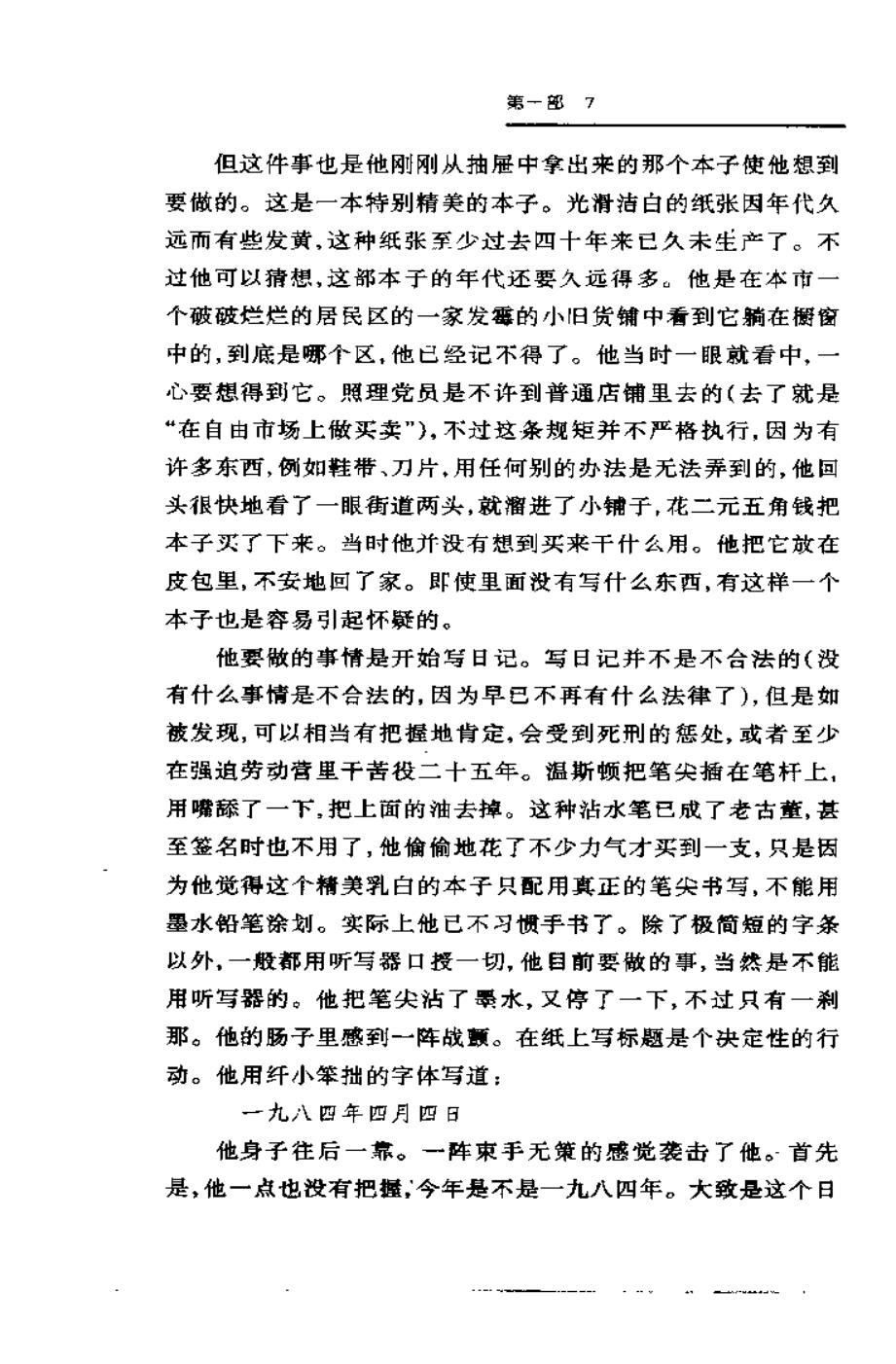
第一部7 但这件事也是他刚刚从抽屉中拿出来的那个本子使他想到 要做的。这是一本特别精美的本子。光滑洁白的纸张因年代久 远而有些发黄,这种纸张至少过去四十年来已久未生产了。不 过他可以猜想,这部本子的年代还要久远得多。他是在本市一 个破破烂烂的居民区的一家发霉的小旧货辅中看到它躺在橱窗 中的,到底是哪个区,他已经记不得了。他当时一眼就看中,一 心要想得到它。照理党员是不许到普通店铺里去的(去了就是 “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不过这条规矩并不严格执行,因为有 许多东西,例如鞋带、刀片,用任何别的办法是无法弄到的,他回 头很快地看了一眼街道两头,就溜进了小辅子,花二元五角钱把 本子买了下来。当时他并没有想到买来干什么用。他把它放在 皮包里,不安地回了家。即使里面没有写什么东西,有这样一个 本子也是容易引起怀疑的。 他要做的事情是开始写日记。写日记并不是不合法的(没 有什么事情是不合法的,因为早巴不再有什么法律了),但是如 被发现,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肯定,会受到死刑的惩处,或者至少 在强迫劳动营里干苦役二十五年。温斯顿把笔尖插在笔杆上, 用嘴舔了一下,把上面的油去掉。这种沾水笔已成了老古堇,甚 至签名时也不用了,他偷偷地花了不少力气才买到一支,只是因 为他觉得这个精美乳白的本子只配用真正的笔尖书写,不能用 墨水铅笔涂划。实际上他已不习惯手书了。除了极简短的字条 以外,一般都用听写器口授一切,他目前要做的事,当然是不能 用听写器的。他把笔尖沾了墨水,又停了一下,不过只有一刹 那。他的肠子里感到一阵战颤。在纸上写标题是个决定性的行 动。他用纤小笨拙的字体写道: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身子往后一靠。一阵束手无策的感觉袭击了他。首先 是,他一点也没有把握,今年是不是一九八四年。大致是这个日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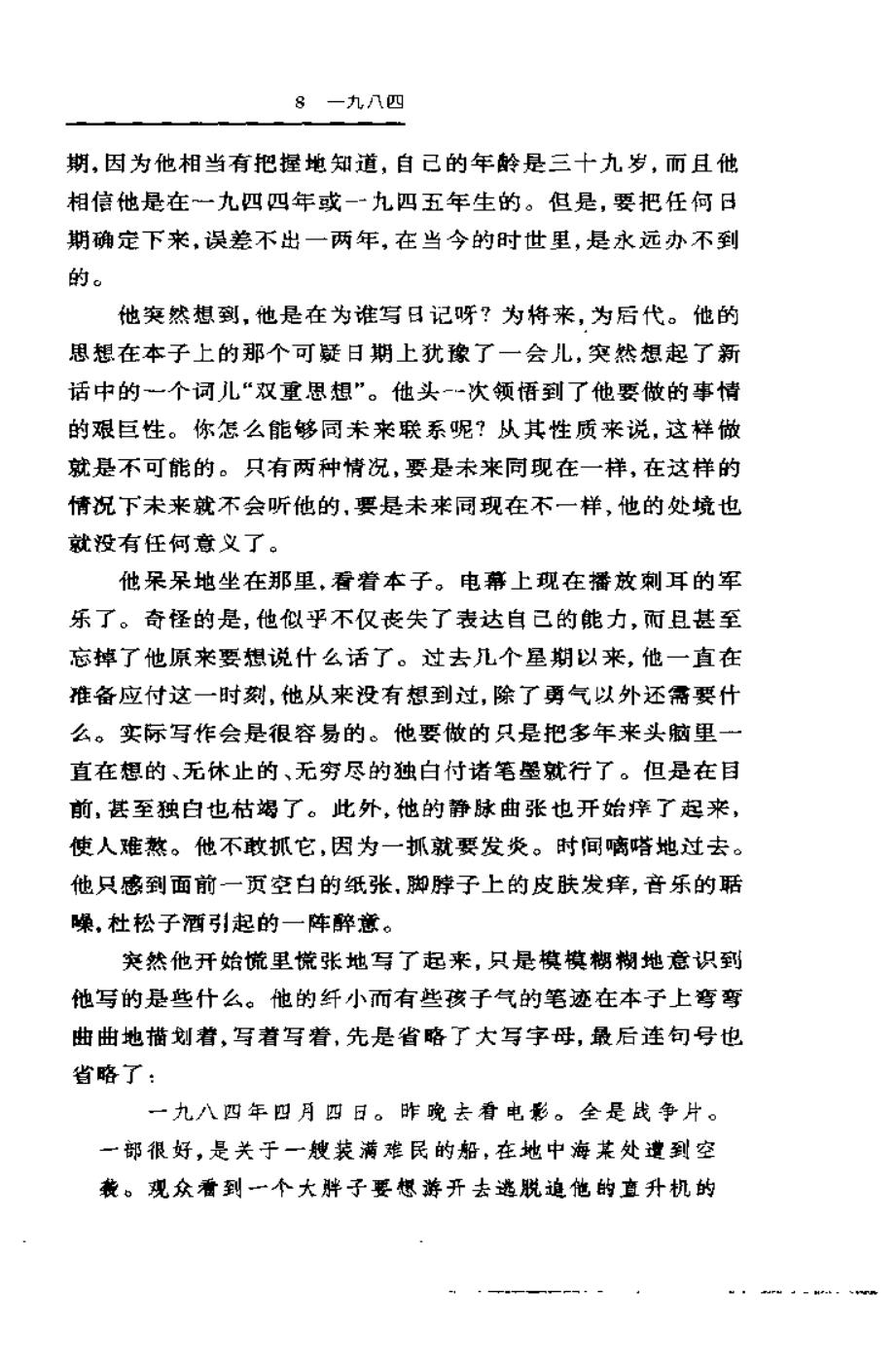
8一九几四 期,因为他相当有把握地知道,自已的年龄是三十九岁,而且他 相信他是在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生的。但是,要把任何日 期确定下来,误差不出一两年,在当今的时世里,是永远办不到 的。 他突然想到,他是在为谁写日记呀?为将来,为后代。他的 思想在本子上的那个可疑日期上犹豫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新 话中的一个词儿“双重思想”。他头一次领悟到了他要做的事情 的艰巨性。你怎么能够同米来联系呢?从其性质来说,这样做 就是不可能的。只有两种情况,要是未来同现在一样,在这样的 情况下未来就不会听他的,要是未来同现在不一样,他的处境也 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他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本子。电幕上现在播效刺耳的军 乐了。奇怪的是,他似平不仅丧失了表达自已的能力,而且甚至 忘掉了他原来要想说什么话了。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 准备应付这一时刻,他从来没有想到过,除了勇气以外还幂要什 么。实际写作会是很容易的。他要做的只是把多年来头脑里一 直在想的、无休止的、无穷尽的独白付诸笔墨就行了。但是在目 前,甚至独白也枯竭了。此外,他的静脉曲张也开始猝了起来, 使人难熬。他不敢抓它,因为一抓就要发炎。时闻嘀嗒地过去。 他只感到面前一贡空白的纸张,脚脖子上的皮肤发痒,音乐的聒 噪,社松子酒1起的一阵醉意。 突然他开始慌里慌张地写了起来,只是模摸糊糊地意识到 他写的是些什么。他的纤小而有些孩子气的笔迹在本子上弯弯 曲曲地描划着,写着写着,先是省略了大写字母,最后连句号也 省略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昨晚去看电彩。全是战争片。 一部很好,是关于一艘装满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遭到空 栽。观众看到一个大胖子要想游开去逃脱迫他的直升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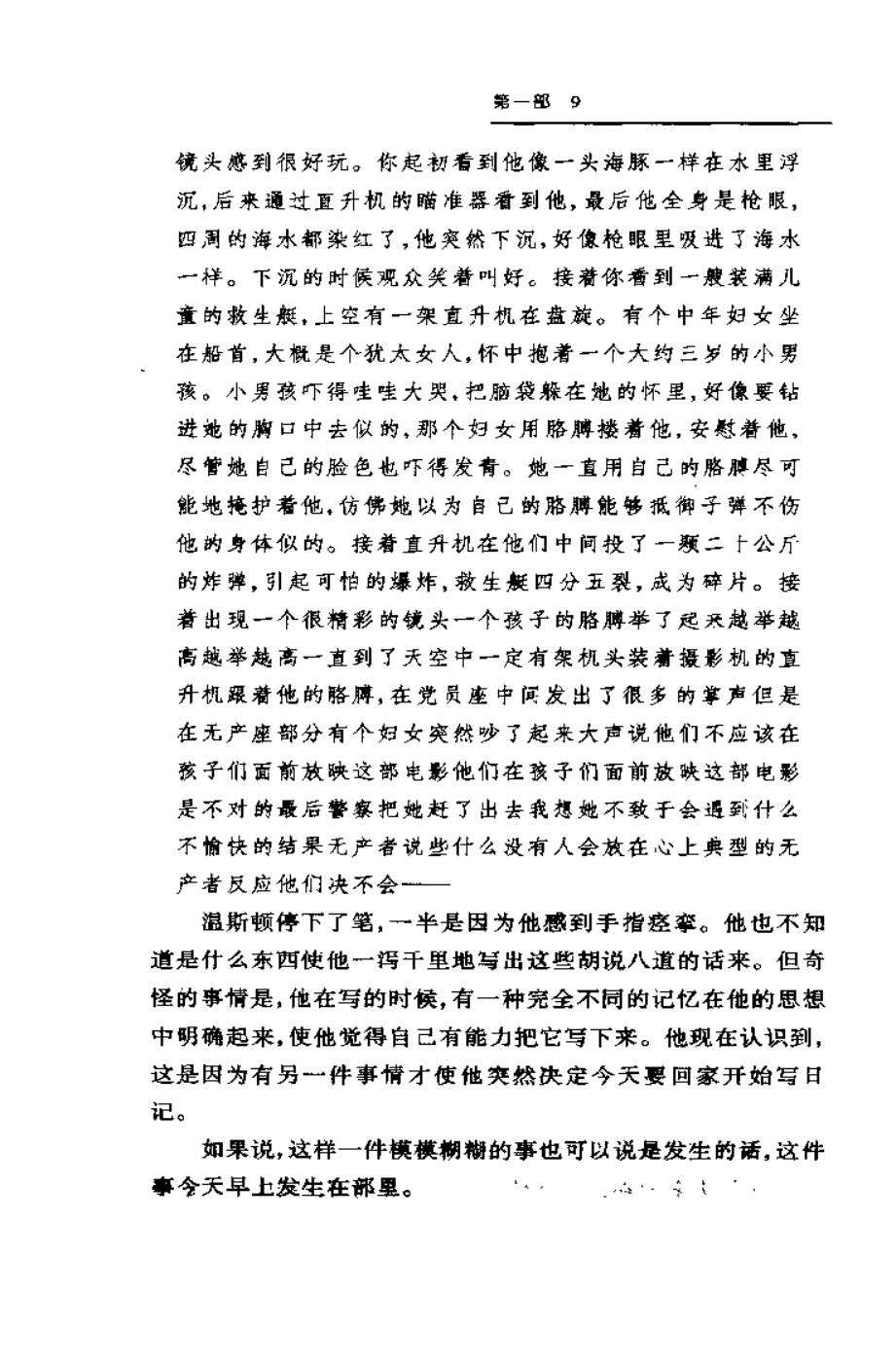
第一部9 镜头感到很好玩。你起初看到他像一头海豚一样在水里浮 沉,后来通过直升机的瞄准器香到他,最后他全身是枪眼, 四周的海水都染红了,他突然下沉,好像枪眼里吸进了海水 一样。下沉的时候观众笑着叫好。接着你香到一艘装满儿 童的救生艇,上空有一架直升机在盘旋。有个中年妇女坐 在船首,大概是个犹太女人,怀中抱着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 孩。小男孩吓得哇哇大哭,把脑袋躲在她的怀里,好像要钻 进地的胸口中去似的,那个妇女用胳膊楼着他,安慰着他, 尽管她自己的脸色也吓得发青。她一直用自己的胳膜尽可 能地掩护着他,仿佛她以为自已的胳膊能够抵御子弹不伤 他的身体似的。接着直升机在他们中间投了一颗二公 的炸弹,引起可怕的爆炸,救生艇四分五裂,成为碎片。接 着出现一个很精彩的镜头一个孩子的胳膊举了起采越举越 高越举越高一直到了天空中一定有架机头装著摄影机的直 升机跟着他的胳膊,在党员座中闻发出了很多的掌声但是 在无产座部分有个妇女突然妙了起来大声说他们不应该在 孩子们面前放映这部电影他们在孩子们面前放映这部电彩 是不对的最后警察把她赶了出去我想她不致于会设到什么 不愉快的结果无产者说些什么没有人会放在心上典型的无 产者反应他们决不会一 温斯顿停下了笔,一半是因为他感到手指痉李。他也不知 道是付么东西使他一泻千里地写出这些胡说八道的话来。但奇 怪的事情是,他在写的时候,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记忆在他的思想 中明确起来,使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把它写下来。他现在认识到, 这是因为有另一件事情才使他突然决定今天要回家开始写日 记。 如果说,这样一件模模湖糊的事也可以说是发生的话,这件 事全天早上发生在部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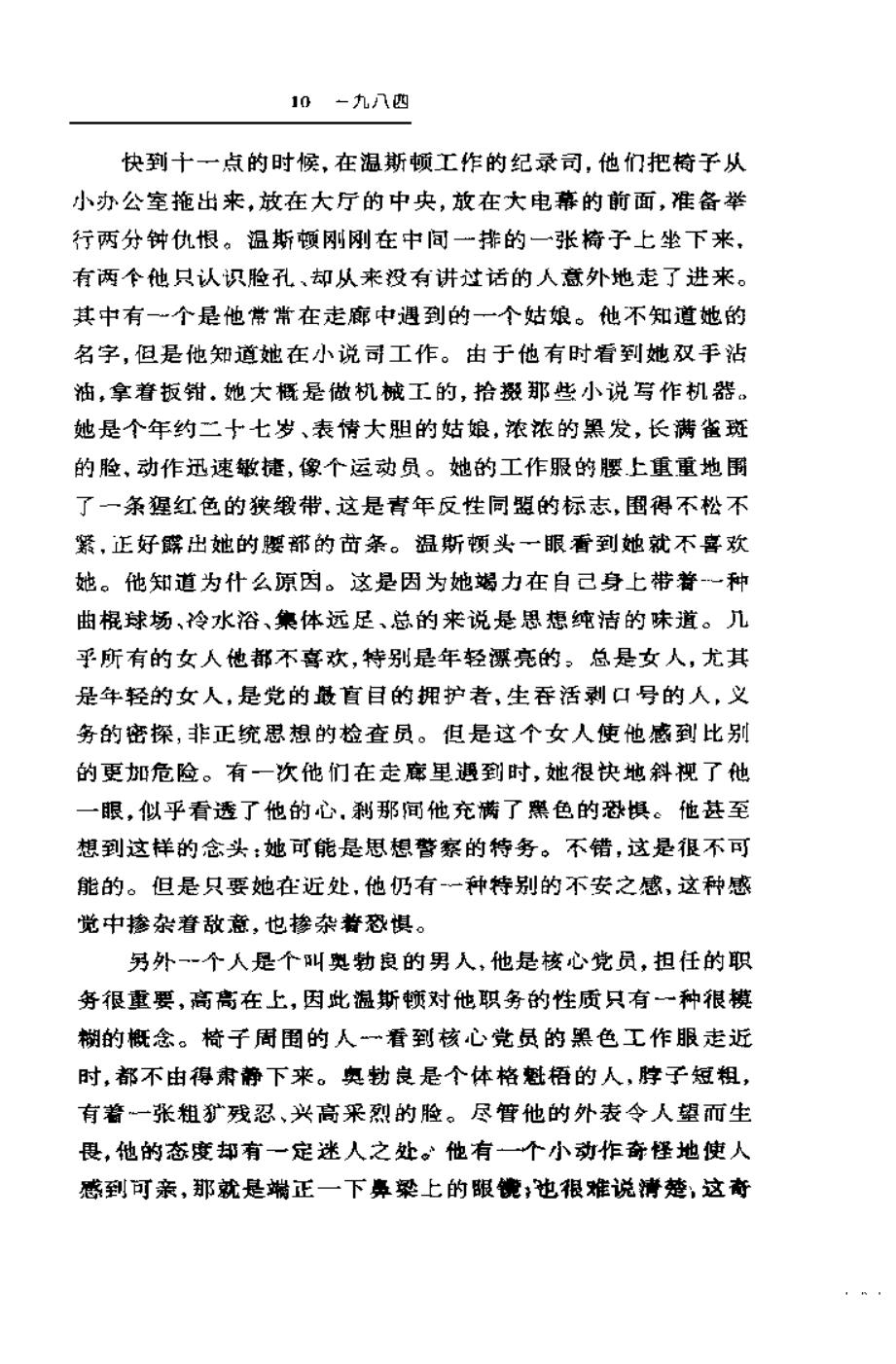
10-九几四 快到干一点的时候,在温斯顿工作的纪录司,他们把椅子从 小办公室拖出来,放在大厅的中央,放在大电幕的前面,推备举 行两分钟仇恨。温斯顿刚刚在中间一#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 有两个他只认识脸孔、却从来没有讲过话的人意外地走了进来。 其中有一个是他常常在走廊中週到的一个姑娘。他不知道她的 名字,但是他知道她在小说司工作。由于他有时看到她双手沾 油,拿着扳钳,她大概是做机械工的,拾掇那些小说写作机器。 她是个年约二七岁、表情大胆的姑娘,浓浓的黑发,长满雀斑 的脸,动作迅速敏捷,像个运动员。她的工作服的腰上重重地围 了一条猩红色的狭缎带,这是青年反性同盟的标志,围得不松不 繁,正好解出她的腰部的苗条。温斯顿头一眼看到她就不喜欢 她。他知道为什么原因。这是因为她竭力在自己身上带着一种 曲棍球场、冷水浴、集体远足、总的来说是思想纯洁的味道。几 乎所有的女人德都不喜欢,特别是年轻漂亮的,总是女人,尤其 是年轻的女人,是党的最直目的拥护者,生吞活剥口号的人,义 务的密探,非正统思想的检查员。但是这个女人使他感到比别 的更加危险。有一次他们在走廊里通到时,她很快地斜视了他 一眼,似乎看透了他的心,刹那间他充满了黑色的恐惧。他甚至 想到这样的念头:她可能是思想营察的特务。不错,这是很不可 能的。但是只要她在近处,他仍有一种特别的不安之感,这种感 觉中糁杂着敌意,也糁杂普惧。 另外一一个人是个叫與勃良的男人,他是核心党员,担任的职 务很重要,高高在上,因此温斯顿对他职务的性质只有一种很模 糊的概念。椅子周围的人一看到核心党员的黑色工作服走近 时,都不由得肃静下来。奥勃良是个体格魁梧的人,脖子短粗, 有着一张粗犷矿残忍、兴高采烈的脸。尽管他的外表令人望而生 畏,他的态度却有一定迷人之处。他有个小动作奇怪地使人 感到可亲,那就是端正一下鼻梁上的眼恍;池很难说清楚,这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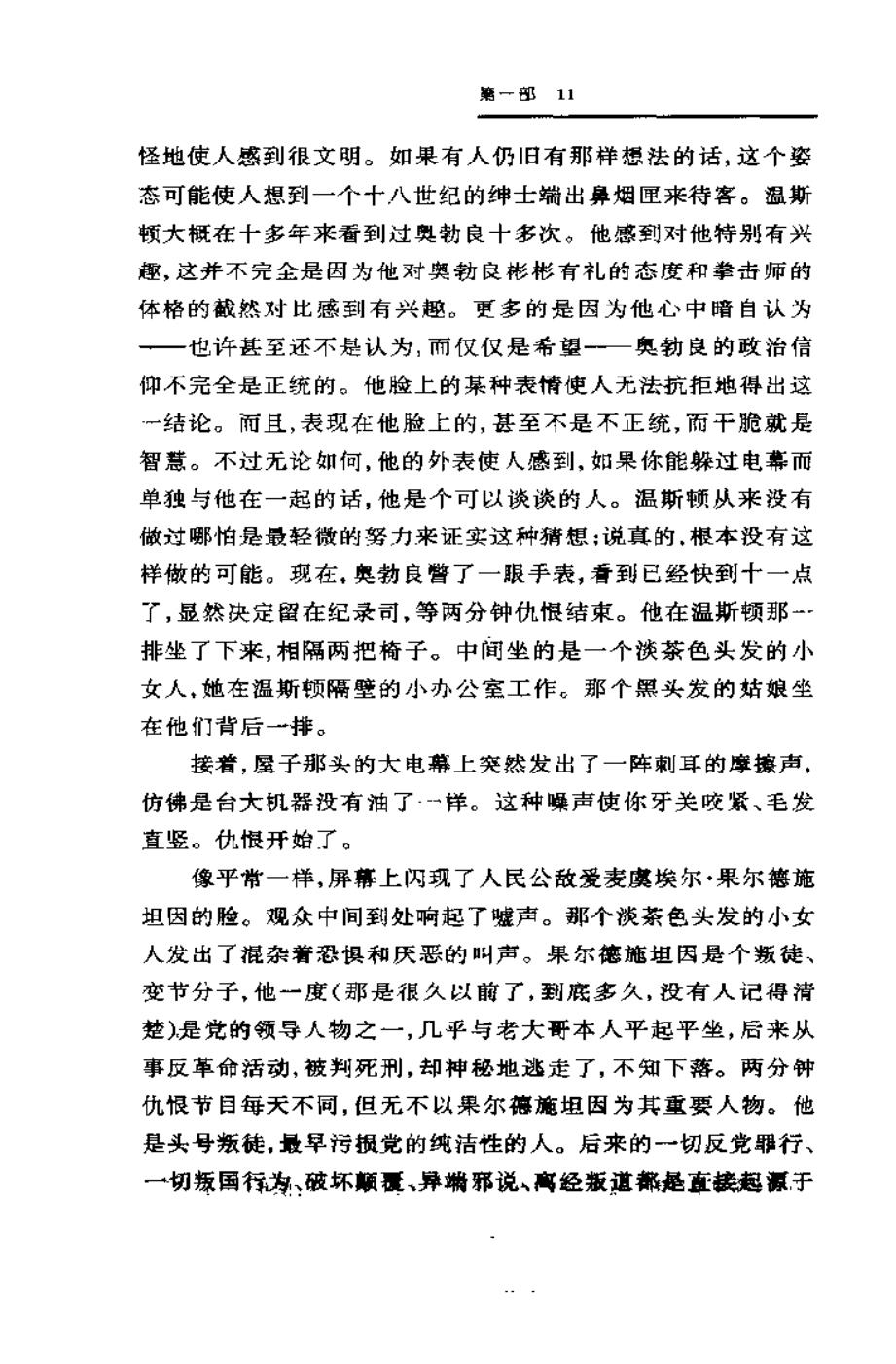
籍一部11 怪地使人感到很文明。如果有人仍旧有那样想法的话,这个姿 态可能使人想到一个十八世纪的绅士端出鼻烟匣来待客。温斯 顿大概在十多年来看到过奥勃良十多次。他感到对他特别有兴 趣,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对奥勃良彬彬有礼的态度和拳击师的 体格的截然对比感到有兴趣。更多的是因为他心中暗自认为 一也许甚至还不是认为,而仅仅是希望一奥勃良的政治信 仰不完全是正统的。他脸上的某种表情使人无法抗拒地得出这 一结论。而且,表现在他脸上的,甚至不是不正统,而干脆就是 智惹。不过无论如何,他的外表使人感到,如果你能躲过电幕而 单独与他在一起的话,他是个可以谈谈的人。温斯顿从来没有 做过哪怕是最轻微的努力来证实这种猜想:说真的,根本没有这 样做的可能。现在,奥勃良警了一眼手表,看到已经快到十一点 了,显然决定留在纪录司,等两分钟仇恨结束。他在温斯顿那· 排坐了下来,相隔两把椅子。中间坐的是一个淡茶色头发的小 女人,她在温斯领隔壁的小办公室工作。那个黑头发的姑娘坐 在他们背后一排。 接着,屋子那头的大电幕上突然发出了一阵刺耳的摩擦声, 仿佛是台大机器没有油了·一样。这种噪声使你牙关咬紧、毛发 直竖。仇恨开始了。 像平常一样,屏幕上闪现了人民公敌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 坦因的脸。观众中间到处响起了嘘声。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 人发出了混杂着恐惧和厌恶的叫声。果尔德施坦因是个叛徒、 变节分子,他一度(那是很久以前了,到底多久,没有人记得清 楚)是党的领导人物之一,几平与老大哥本人平起平坐,后来从 事反革命活动,被判死刑,却神秘地逃走了,不知下落。两分钟 仇恨节目每天不同,但无不以果尔德施坦因为其重要人物。他 是头号叛徒,最早污损党的纯洁性的人。后来的一切反党罪行、 一切叛国行为、破坏顺覆、异懒邪说、高经叛道都起直接起源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