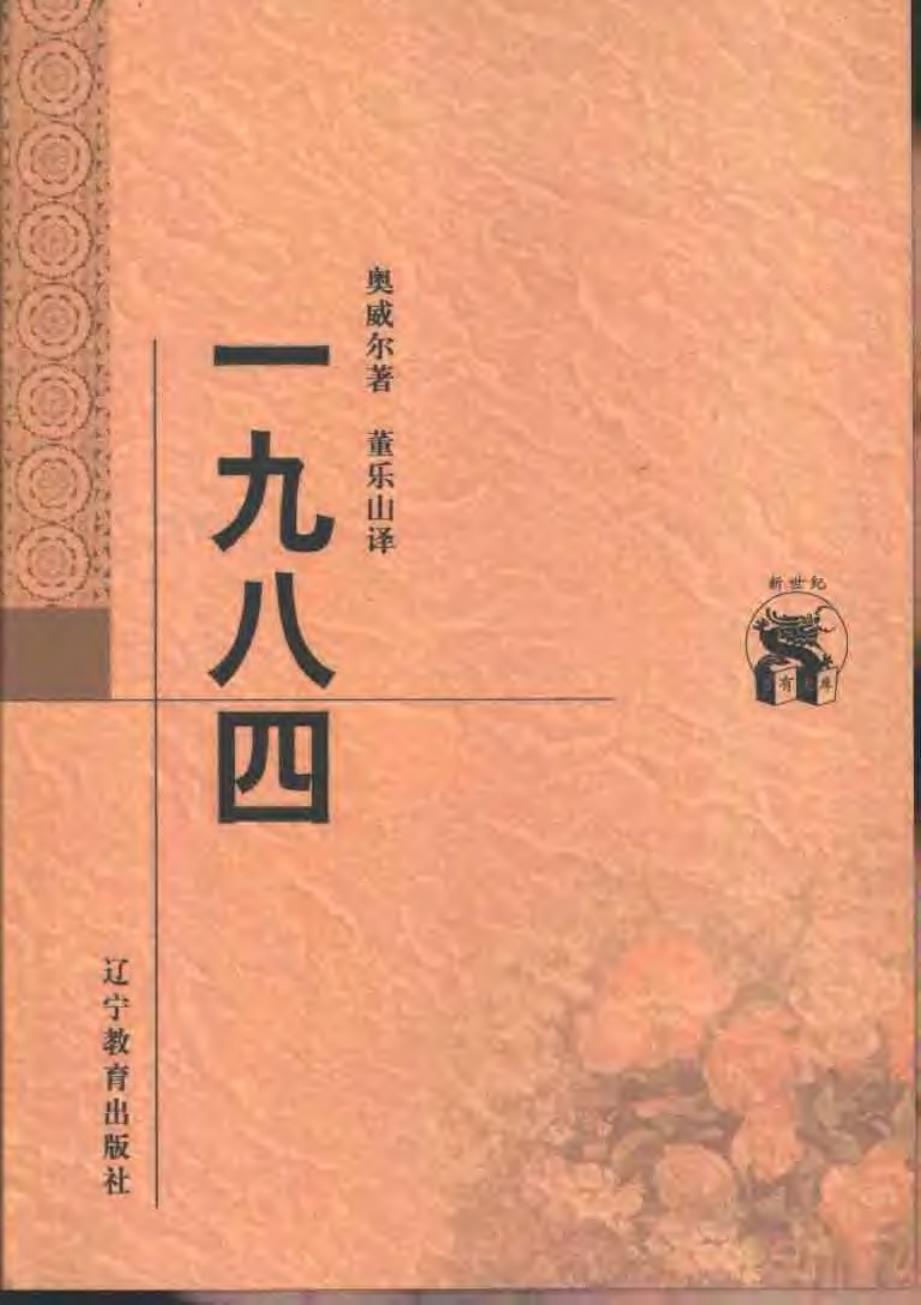
一九八四 奥威尔著董乐山译 析些纪 辽宁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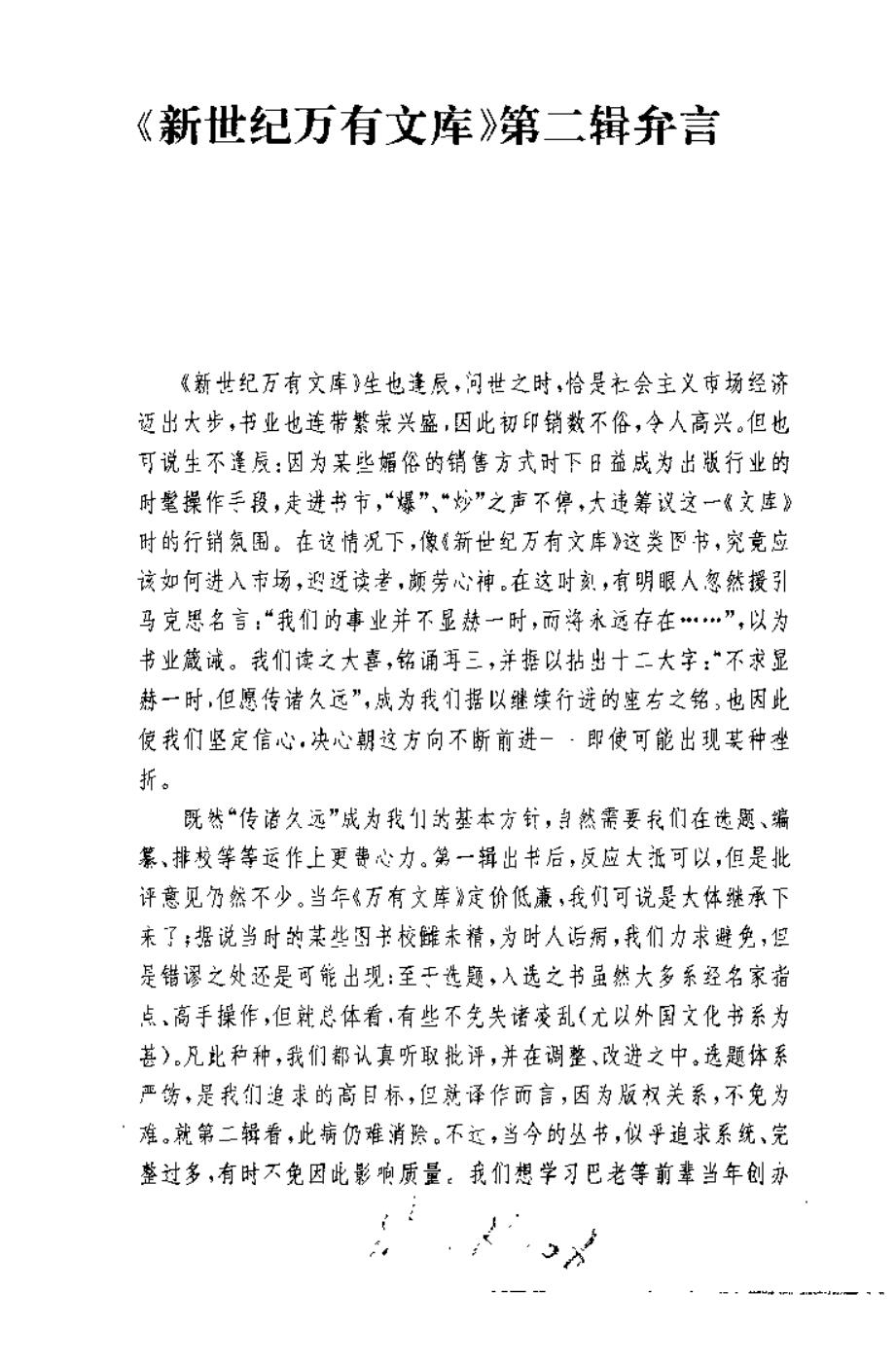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弁言 《新世纪万有文库》生也逢辰,问世之时,恰是在会主义市场经济 迈出大步,书业也连带繁荣兴盛,因此初印销数不俗,令人高兴。但也 可说生不逢辰:因为某些媚俗的销售方式时下日益成为出版行业的 时髦操作手段,走进书市,“爆”、“妙”之声不停,大违筹议这一《文库》 时的行销氛围。在这情况下,像新世纪万有文库》这类图书,究竞应 该如何进入市场,识迓读老,颜劳心神。在这时刻,有明眼人忽然援引 马克思名言:“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而游永英存在…”,以为 书业箴诫。我们读之大喜,铭诵再三,并拒以拈出十二大字:“不求显 赫一时,但愿传诸久运”,成为我们据以继续行进的座方之铭,也因此 使我们坚定信心,决心朝这方向不断前进-·即使可能出现某种坐 折。 既然“传诸久远”成为我]的基本方针,自然需要我们在选题、编 慕、排校等等运作上更费心力。第一辑出书后,反应大派可以,但是批 评意见乃然不少。当年《万有文库》定价低燾,我们可说是大体继承下 来了;据说当时的某些图书校雠未精,为时人近病,我们力求避免,但 是错谬之处还是可能出现:至工选题,入选之书虽然大多系经名家指 点,高手操作,但就总体看,有些不先失诸凌乱(元以外国文化书系为 葚)。凡此和种,我们都认真听取批评,并在调整、改进之中。选题体系 严筋,是我们追求的高目标,但斑译作而言,因为版权关系,不免为 难。就第二辑着,此病仍难消脍。不这,当今的丛书,似乎追求系统、完 整过多,有时天免因此影响质量:我们想学习巴老等前辈当年创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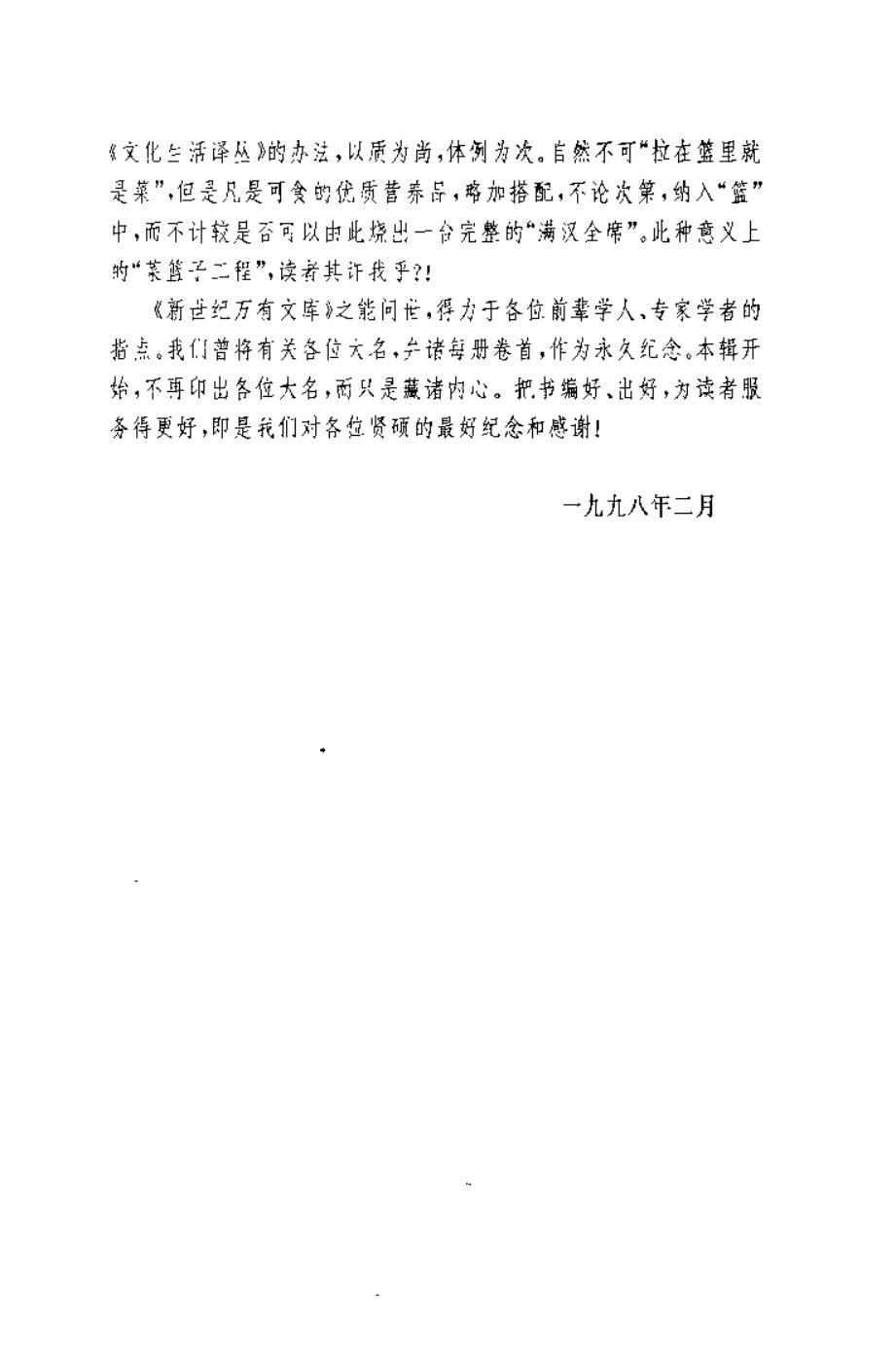
象文化三活译丛》的办法,以质为尚,体列为次。自然不可“拉在篮里就 是菜”,但是凡是可食的优质营养于,路加搭配,不论次第,纳入“篮” 中,而不计较是石可以由此烧出!一合完整的“满汉全席”。此种意义上 的“菜篮工二程”,读者其许我乎?! 《新过纪万有文库》之能问龙,得力于各位前辈学人、专家学者的 指点。我们曾将有关各位六名,台诸每册卷首,作为永久纪念。本辑开 给,不再印出各位大名,而只是燕诸内心。把书编好、出好,为读者服 务得更好,即是我们对各位贤硕的最好纪念和感谢! 一九九八年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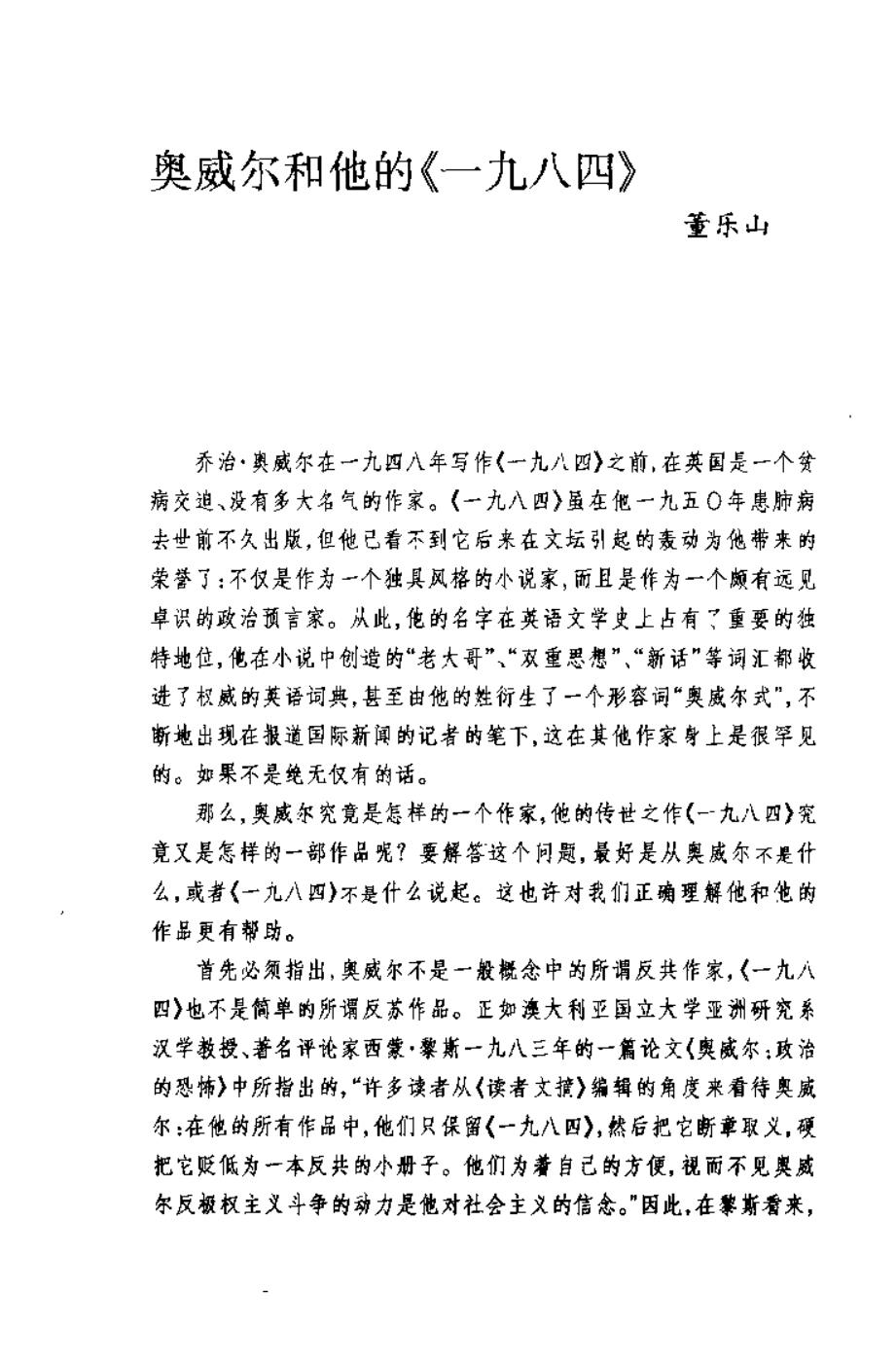
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 董乐山 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四八年写作(一九八四》之前,在英国是一个贫 病交迫、没有多大名气的作家。《一九八四》虽在他一九五0年患肺病 去世前不久出版,但他已着不到它后来在文坛引起的麦动为他带来的 荣誉了:不仅是作为一个独具风格的小说家,而且是作为一个颇有远见 卓识的政治预言家。从此,他的名字在英语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独 特地位,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都收 进了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了一个形容词“奥威尔式”,不 断地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的笔下,这在其他作家身上是很罕见 的。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 那么,奥威尔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作家,他的传世之作(-九八四》究 竟又是怎样的一部作品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最好是从奥威尔不是什 么,或者《一九八四)不是什么说起。这也许对我们正确理解他和他的 作品更有帮助。 首先必须指出,奥威尔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谓反共作家,《一九八 四》也不是简单的所谓反苏作品。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系 汉学教授、著名评论家西蒙·黎斯一九八三年的一篇论文《奥威尔:政治 的恐怖》中所指出的,“许多读者从《读者文镀》编辑的角度来看待奥威 尔: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们只保留《一九八四》,然后把它断章取义,硬 把它贬低为一本反共的小册子。他们为着自己的方便,视而不见奥威 尔反极权主义斗争的动力是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因此,在攀斯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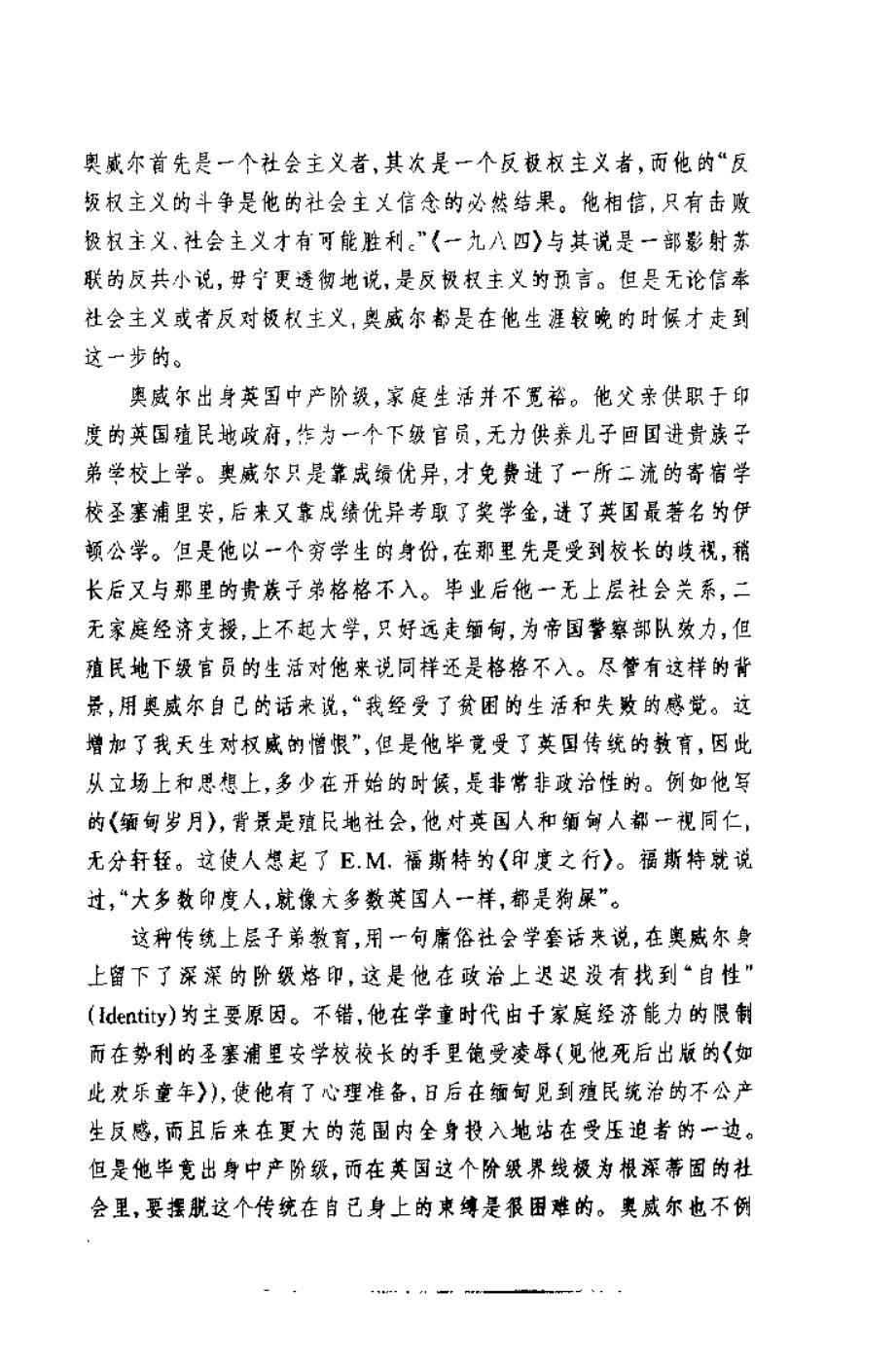
奥威尔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其次是一个反极权主义者,而他的“反 顿权主义的斗争是他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必然结果。他相信,只有击败 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胜利”《一九八四〉与其说是一部影射苏 联的反共小说,毋宁更透彻地说,是反极权主义的预言。但是无论信奉 社会主义或者反对极权主义,奥威尔都是在他生涯较晚的时候才走到 这一步的。 奥威尔出身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并不置裕。他父亲供职于印 度的英国殖民地政府,炸为一个下级官员,无力供养儿子回国进贵族子 弟学校上学。奥威尔只是靠成簽优异,才免费进了一所二流的寄宿学 校圣塞浦里安,后来又靠成绩优异考取了奖学金,进了英国最著名的伊 顿公学。但是他以一个穷学生的身份,在那里先是受到校长的歧视,稍 长后又与那里的贵族手弟格格不入。毕业后他一无上层社会关系,二 无家庭经济支援,上不起大学,只好远走缅句,为帝国警察部以效力,但 殖民地下级官员的生活对他来说同样还是格格不入。尽管有这样的背 景,用奥威尔自己的话来说,“我经受了贫困的生活和失敦的感觉。这 增加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但是他毕竟受了英国传统的教育,因此 从立场上和思想上,多少在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非政治性的。例如他写 的《缅甸岁月),背景是殖民地社会,他对英国人和缅剑人都一视同仁, 无分轩轾。这使人想起了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福斯特就说 过,“大多数印度人,就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都是狗屎”。 这种传统上层子弟教育,用一句庸俗社会学套话夹说,在奥威尔身 上留下了深深的阶级烙印,这是他在政治上迟迟没有找到“自性” (dentity)钓主要原因。不错,他在学童时代由于家庭经济能力的限制 而在势利的圣塞浦里安学校校长的手里饱受凌辱(见他死后出版的〈如 此欢乐童年》),使他有了心理准备,日后在缅甸见到殖民统治的不公产 生反感,而且后来在更大的范围内全身投入地站在受压追者的一边。 但是他毕竟出身中产阶级,而在英国这个阶级界线极为根深蒂固的社 会里,要摆脱这个传统在自已身上的束缚是很困难的。奥威尔也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