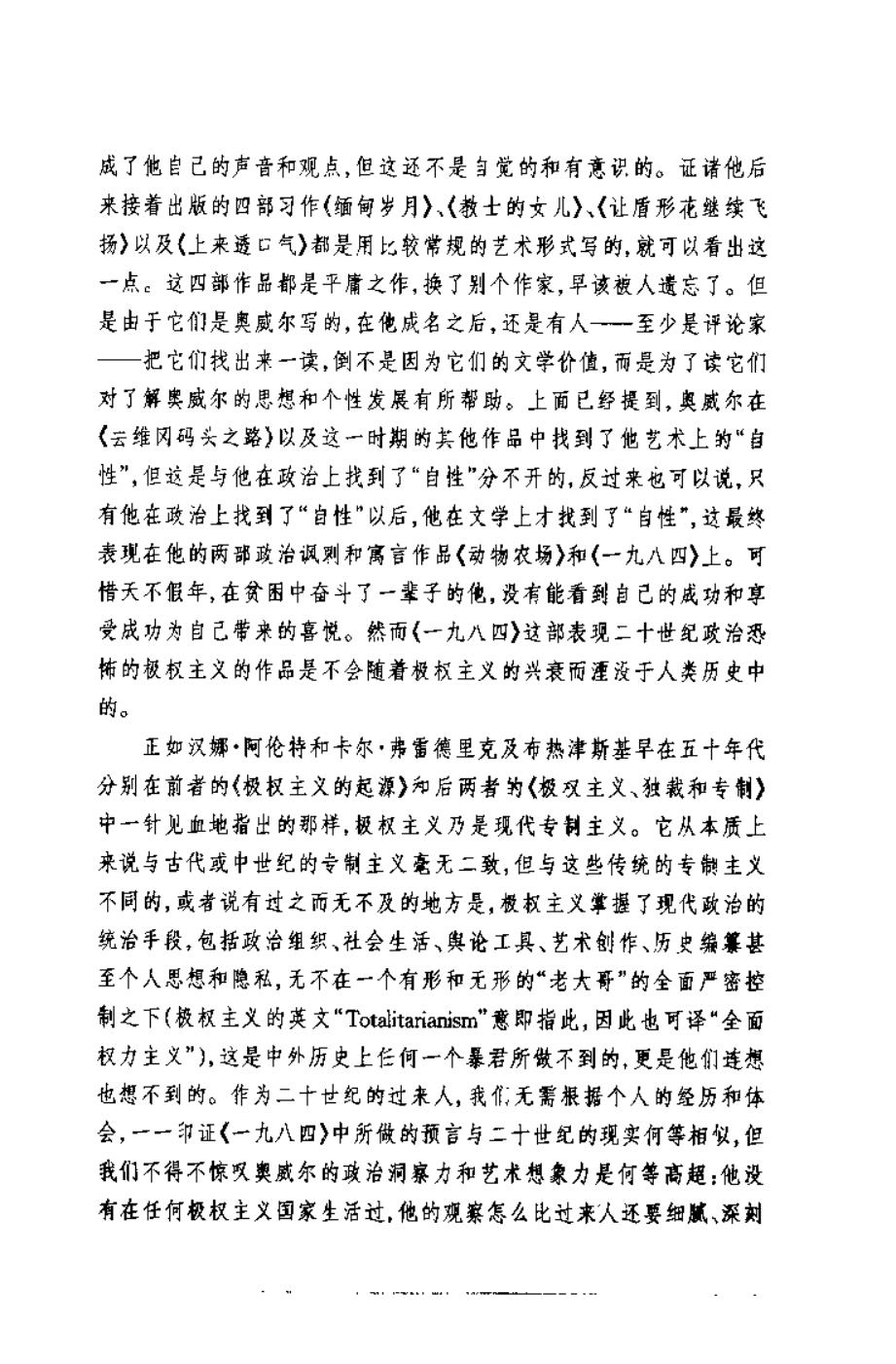
成了他自己的声音和观点,但这还不是自觉的和有意识,的。证诸他后 来接着出版的四部习作(缅甸岁月》、《教士的女儿》、《让盾形花继续飞 扬》以及《上来透口气)都是用比较常规的艺术形式写的,就可以看出这 一点。这四部作品都是平庸之作,换了别个作家,早该板人遗忘了。但 是由于它们是奥威尔写的,在他成名之后,还是有人一至少是评论家 一把它们找出来一读,倒不是因为它们的文学价值,而是为了读它们 对了解奥威尔的思想和个性发展有所帮助。上面已经提到,奥威尔在 (云维冈码关之路)以及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品中找到了他艺术上的“自 性”,但这是与他在政治上找到了“自性”分不开的,反过来也可以说,只 有他在政治上找到了“自性”以后,他在文学上才找到了“自性”,这最终 表现在他的两部政治讽和高言作品(《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上。可 惜天不假年,在贫困中奋斗了一辈子的他,没有能看到自己的成功和享 受成功为自己带来的喜悦。然而《一九八四》这部表现二十世纪政治恐 怖的极权主义的作品是不会随着极权主义的兴衰而湩液于人类历史中 的。 正如汉娜·阿伦特和卡尔·弗雷德里克及布热津斯基早在五十年代 分别在前者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知后两者钓《校双主义、独裁和专制》 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极权主义乃是现代专制主义。它从本质上 来说与古代或中世纪的专制主义毫无二致,但与这些传统的专制主义 不同的,或者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方是,极权主义掌握了现代政治的 统治手段,包括政治组织、社会生活、舆论工具、艺术创作、历史编纂甚 至个人思想和隐私,无不在一个有形和无形的“老大哥”的全面严密控 制之下(校权主义的英文“Totalitarianism”意即指此,因此也可译“全面 权力主义”),这是中外历史上仁何一个暴君所做不到的,更是他们连想 也想不到的。作为二十世纪的过来人,我:无需根据个人的经历和体 会,一一印证《一九八四》中所做的预言与二十世纪的现实何等相以,但 我们不得不惊叹奥威尔的政治洞察力和艺术想象力是何等高超:他没 有在任何校权主义国家生活过,他的观寒怎么此过来人还要细腻、深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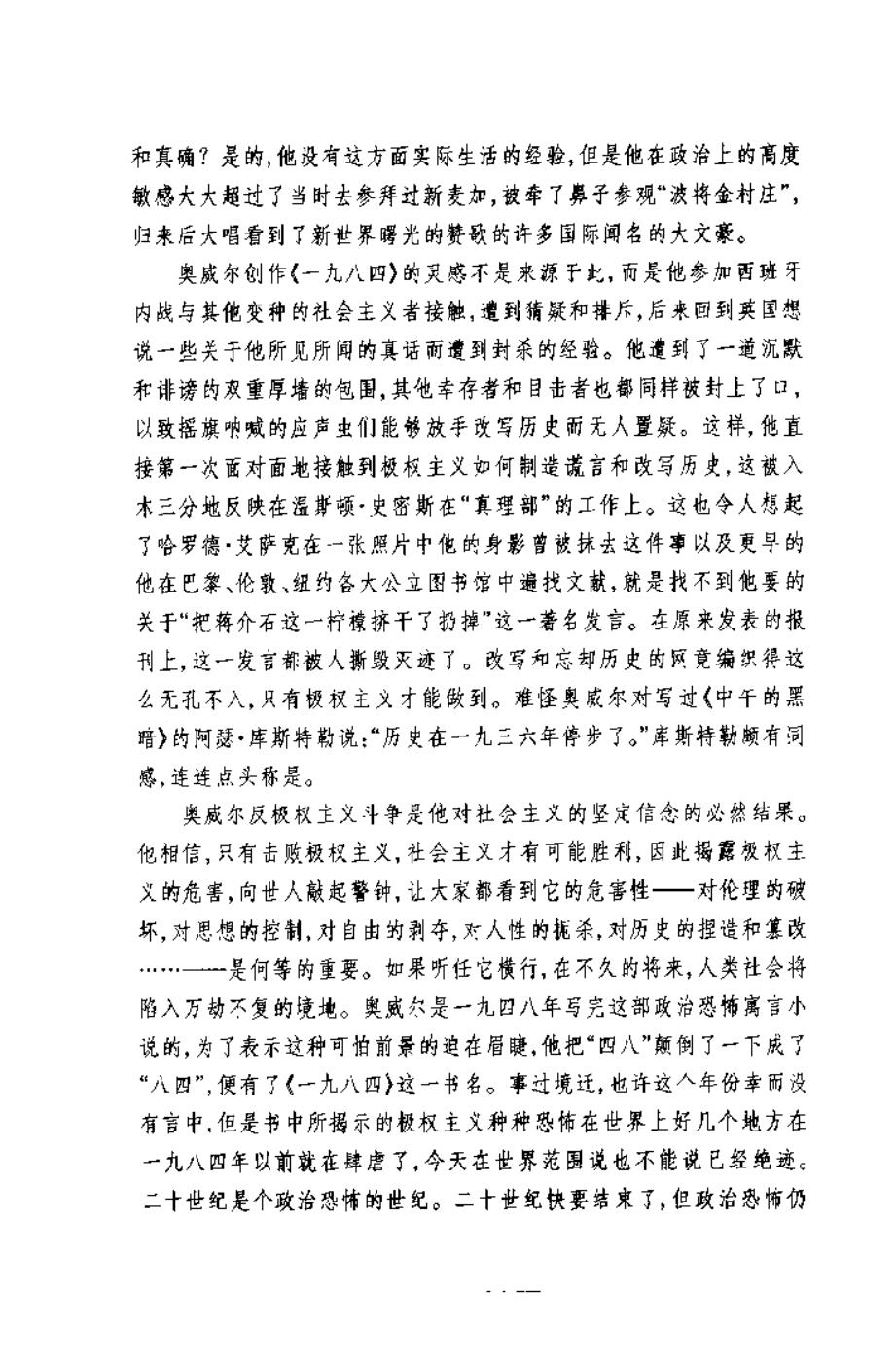
和真确?是的,他没有这方面实际生活的经验,但是他在政治上的高度 敏感大大超过了当时去参拜过新麦加,被牵了鼻子参观“波将金村注”, 归来后大唱看到了新世界曙光的赞欧的许多国际闻名的大文豪。 奥威尔创作《一九八四〉的灵感不是来源于北,而是他参加西班牙 内战与其他变种的社会主义者接触,遭到猜疑和排斥,后来回到英国想 说一些关于他所见所闻的真话而遭到封杀的经验。他遭到了一道沉默 和诽谤的效重厚堵的包围,其他幸存者和目击者也都同样被封上了口, 以致摇旗呐减的应声虫们能够放手改写历史而无人置疑。这样,他直 接第一次面对面地接触到极校主义如何制造荒言和改写历史,这被入 木三分地反陕在温斯顿·史密斯在“真理部”的工作上。这也令人想起 了哈罗德·艾萨克在一张照片中他的身影曾被抹去这件事以及更早的 他在巴黎、伦敦、纽约各大公立图书馆中遍找文献,就是找不到他要的 关于“把蒋介石这一柠撩挤干了扔掉”这一著名发言。在原来发表的报 刊上,这一发言都被人新毁灭迹了。改写和忘却历史的网竟编织得这 么无孔不入,只有极权主义才能做到。难怪奥威尔对写过《中午的黑 暗》的阿瑟·库斯特勒说:“历史在一九三六年停步了。”库斯特勒颇有词 感,连连点头称是。 奥威尔反极权主义斗争是他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的必然结果。 他相信,只有击败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胜利,因此揭露极权主 义的危害,向世人敲起警钟,让大家都看到它的危害性一对伦理的破 坏,对思想的控制,对自由的剥夺,为人性的拢杀,对历史的捏造和篡改 …一是何等的重要。如果听任它横行,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社会将 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奥威尔是一九四八年写完这部政治恐怖寓言小 说的,为了表示这种可怕前景的迫在眉睫,他把“四八”颠倒了一下成了 “八四”,便有了《一九八四)这一书名。事过境迁,也许这人年份幸而没 有言中,但是书中所揭示的极权主义种种恐怖在世界上好几个地方在 一九八四年以前就在肆唐了,今天在世界范围说也不能说已经绝迹 二十世纪是个政治恐怖的世纪。二十世纪快要结束了,但政治恐怖仍

然阴魂不散,因此《一九八四)在今天仍有价值。是否可以说,对我们来 说,只有彻底否定了诸如“文化大革命”这类恐怖的校权主义,才给我们 这些多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带来了真正值得向往的社会主义! 一九九七年七月酷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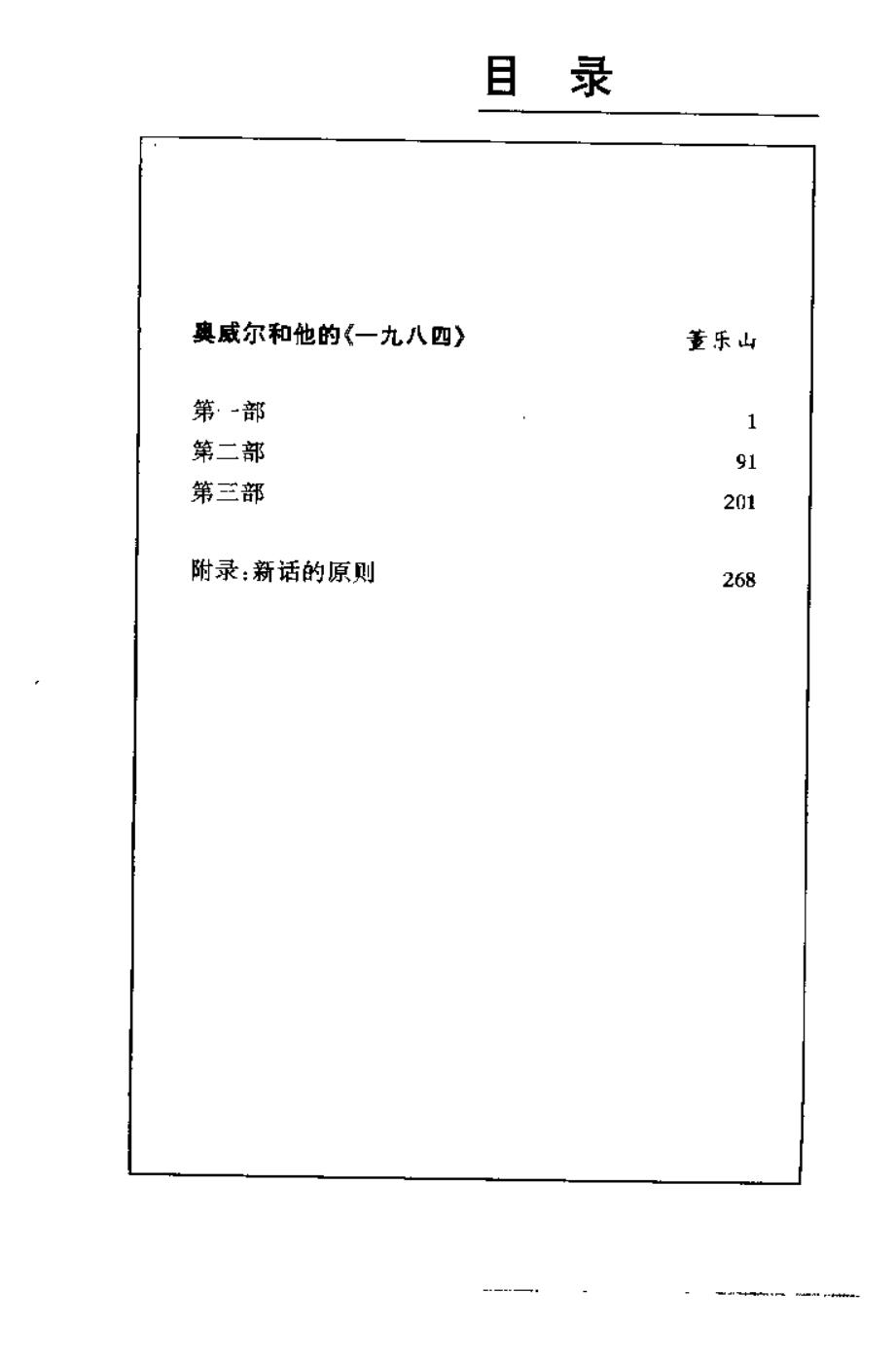
目录 奥咸尔和他的《一九八四》 董乐山 第一部 1 第二部 91 第三部 201 附录:新话的原则 268 :-P4

第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