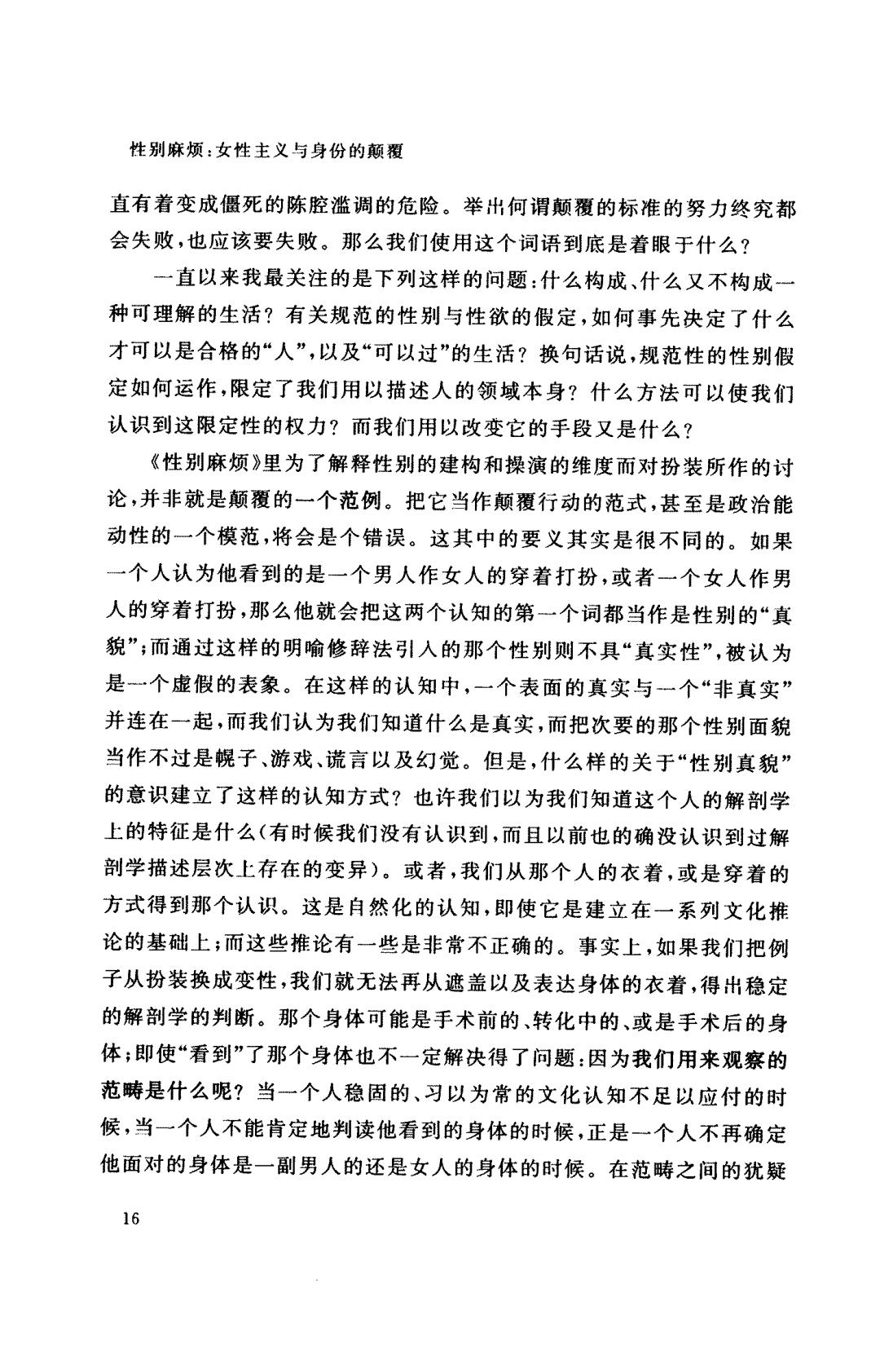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直有着变成僵死的陈腔滥调的危险。举出何谓颠覆的标准的努力终究都 会失败,也应该要失败。那么我们使用这个词语到底是着眼于什么? 一直以来我最关注的是下列这样的问题:什么构成、什么又不构成一 种可理解的生活?有关规范的性别与性欲的假定,如何事先决定了什么 才可以是合格的“人”,以及“可以过”的生活?换句话说,规范性的性别假 定如何运作,限定了我们用以描述人的领域本身?什么方法可以使我们 认识到这限定性的权力?面我们用以改变它的手段又是什么? 《性别麻烦》里为了解释性别的建构和操演的维度而对扮装所作的讨 论,并非就是颠覆的一个范例。把它当作颠覆行动的范式,甚至是政治能 动性的一个模范,将会是个错误。这其中的要义其实是很不同的。如果 一个人认为他看到的是一个男人作女人的穿着打扮,或者一个女人作男 人的穿着打扮,那么他就会把这两个认知的第一个词都当作是性别的“真 貌”;而通过这样的明喻修辞法引入的那个性别测不具“真实性”,被认为 是…个虚假的表象。在这样的认知中,一个表面的真实与一个“非真实” 并连在一起,而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什么是真实,而把次要的那个性别面貌 当作不过是幌子、游戏、谎言以及幻觉。但是,什么样的关于“性别真貌” 的意识建立了这样的认知方式?也许我们以为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解剖学 上的特征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没有认识到,而且以前也的确没认识到过解 剖学描述层次上存在的变异)。或者,我们从那个人的衣着,或是穿着的 方式得到那个认识。这是自然化的认知,即使它是建立在一系列文化推 论的基础上;而这些推论有一些是非常不正确的。事实上,如果我们把例 子从扮装换成变性,我们就无法再从遮盖以及表达身体的衣着,得出稳定 的解剖学的判断。那个身体可能是手术前的、转化中的、或是手术后的身 体;即使“看到”了那个身体也不一定解决得了问题:因为我们用来观察的 范畴是什么呢?当一个人稳固的、习以为常的文化认知不足以应付的时 候,当一个人不能肯定地判读他看到的身体的时候,正是一个人不再确定 他面对的身体是一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身体的时候。在范畴之间的犹疑 16

序(1999) 难决,正是我们所讨论的身体所经历的经验。 当这样的范畴成为讨论的问题的时候,性别的真实也陷入了危机:如 何区别真实与非真实变得不再清晰。这也是一个契机,使我们得以了解 那些我们以为是“真实”者、我们援引为自然化的性别知识者,实际上是-· 种可变的、可修改的真实。管它叫颠覆还是其他的什么!虽然这个洞见 本身并不构成一种政治革命,但是如果对于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真实 的,人的观念上没有一个根本的改变的话,是不可能有政治革命的。而有 时候这样的改变的发生,来自某些还没有在理论上得到清楚论述的实践, 它们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些基本的范畴:性别是什么,它如何被生产、被 复制,它的可能性是什么?在此,对积淀、物化的性别“真实”领域的理解 是:它也许可以改头换面,而且还是以较不暴力的方式被改变。 本书的重点不在颂扬扮装,把它当作一种正确的、模范的性别表达 (即使对不时发生的贬低扮装的情形予以反抗是很重要的),而在说明自 然化的性别认识对真实构成了一种先发制人的、暴力的限制。就性别规 范(理想的二元形态、身体的异性恋互补性、有关正确的和不正确的男性 特质和女性特质的理想和规则等,许多都得到种族纯粹的法规以及反对 异族通婚的禁忌的支持)确立什么会是、什么不会是可理解的人的特质, 而什么会、什么不会被认为是“真实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建立了使身 体可以得到合法表达的本体领域。如果《性别麻烦》有一个积极的规范性 任务的话,那就是坚持把这个合法性拓展到那些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错误 的、不真实的、以及无法理解的身体上。扮装是一个例子,意在证明“真 实”并不像我们一般所认定的那样一成不变。这个例子的目的在于揭露 性别“真实”的脆弱本质,以对抗性别规范所施行的暴力。 在本书以及其他地方我试图了解:假如不能跟它由以形成的那个权 力动能(the dynamics of power)分离的话,那么政治能动性可能会是什 么?操演的重复性是一种能动理论,而这理论不能否认权力是构成它的 可能性的条件。本书并没有从社会、心理、物质、以及时间性等方面对操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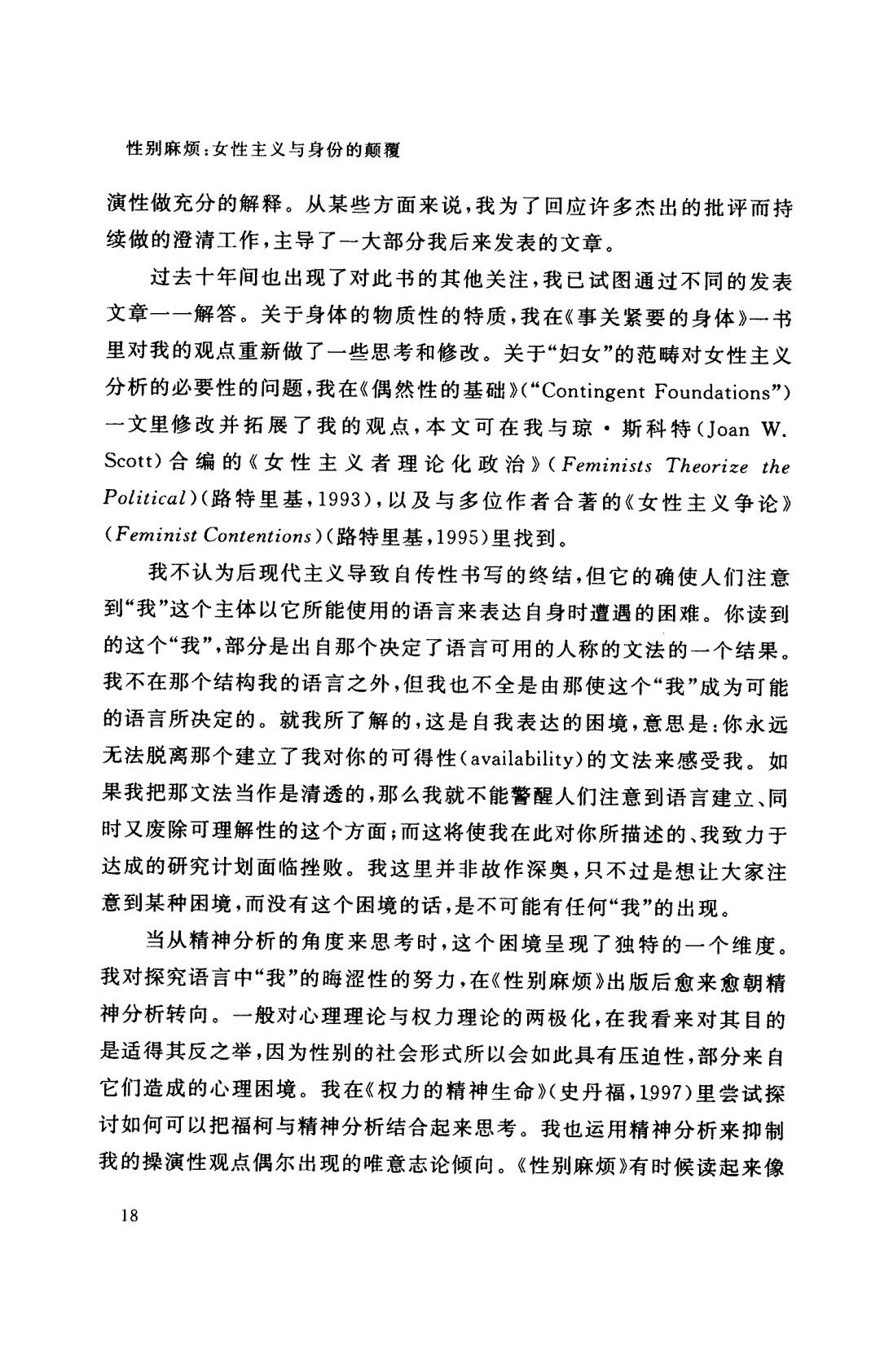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演性做充分的解释。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为了回应许多杰出的批评而持 续做的澄清工作,主导了一大部分我后来发表的文章。 过去十年间也出现了对此书的其他关注,我已试图通过不同的发表 文章一一解答。关于身体的物质性的特质,我在《事关紧要的身体》一书 里对我的观点重新做了一些思考和修改。关于“妇女”的范畴对女性主义 分析的必要性的问题,我在《偶然性的基础》(“Contingent Foundations'”) 一文里修改并拓展了我的观点,本文可在我与琼·斯科特(Joan W. Scott)合编的《女性主义者理论化政治》(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路特里基,1993),以及与多位作者合著的《女性主义争论》 (Feminist Contentions)(路特里基,l995)里找到。 我不认为后现代主义导致自传性书写的终结,但它的确使人们注意 到“我”这个主体以它所能使用的语言来表达自身时遭遇的困难。你读到 的这个“我”,部分是出自那个决定了语言可用的人称的文法的一个结果。 我不在那个结构我的语言之外,但我也不全是由那使这个“我”成为可能 的语言所决定的。就我所了解的,这是自我表达的困境,意思是:你永远 无法脱离那个建立了我对你的可得性(availability)的文法来感受我。如 果我把那文法当作是清透的,那么我就不能警醒人们注意到语言建立、同 时又废除可理解性的这个方面;而这将使我在此对你所描述的、我致力于 达成的研究计划面临挫败。我这里并非故作深奥,只不过是想让大家注 意到某种困境,而没有这个困境的话,是不可能有任何“我”的出现。 当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思考时,这个困境呈现了独特的一个维度。 我对探究语言中“我”的晦涩性的努力,在《性别麻烦》出版后愈来愈朝精 神分析转向。一般对心理理论与权力理论的两极化,在我看来对其目的 是适得其反之举,因为性别的社会形式所以会如此具有压迫性,部分来自 它们造成的心理困境。我在《权力的精神生命》(史丹福,1997)里尝试探 讨如何可以把福柯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思考。我也运用精神分析来抑制 我的操演性观点偶尔出现的唯意志论倾向。《性别麻烦》有时候读起来像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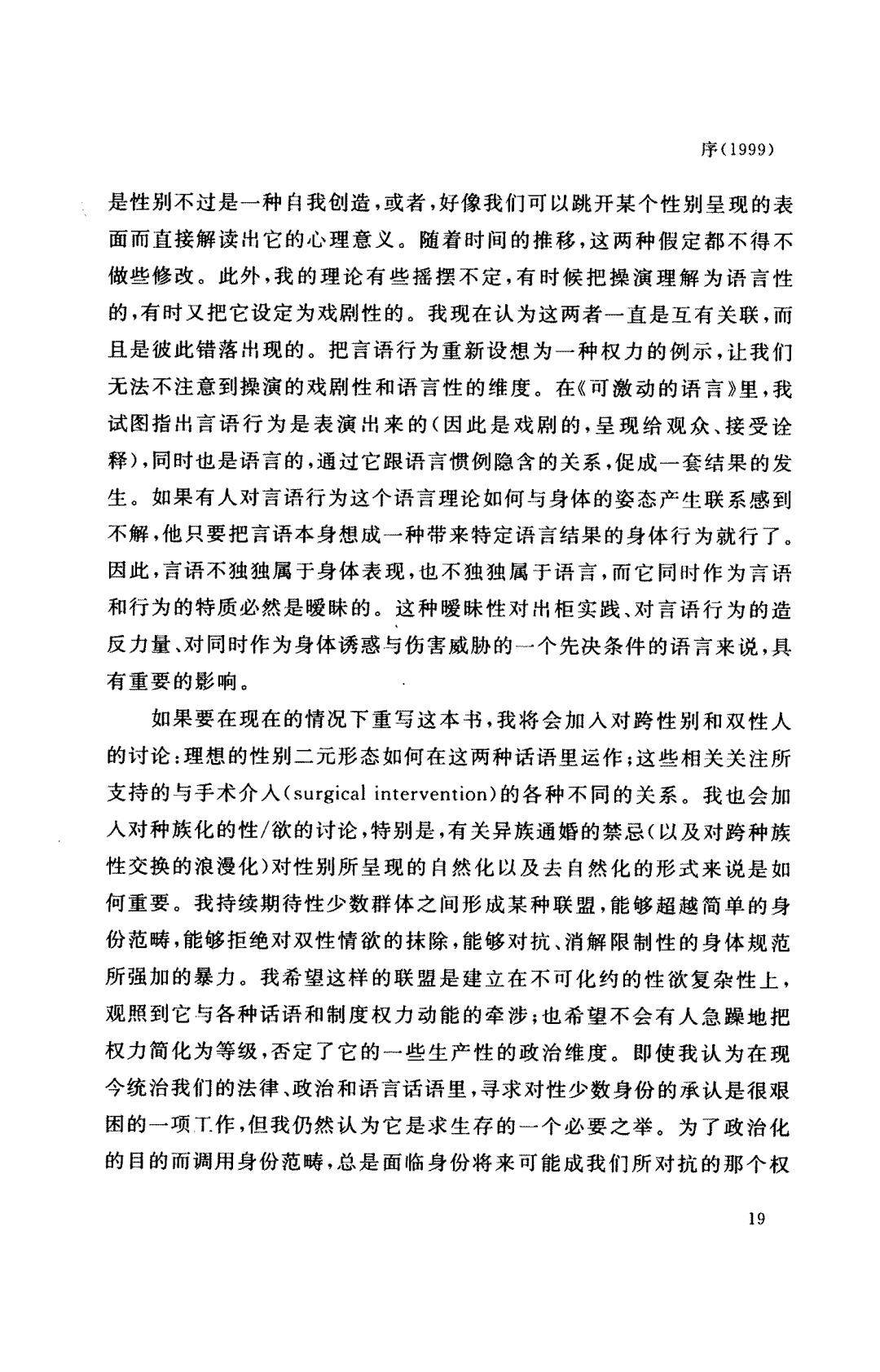
序(1999) 是性别不过是一种自我创造,或者,好像我们可以跳开某个性别呈现的表 面而直接解读出它的心理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假定都不得不 做些修改。此外,我的理论有些摇摆不定,有时候把操演理解为语言性 的,有时又把它设定为戏剧性的。我现在认为这两者一直是互有关联,而 且是彼此错落出现的。把言语行为重新设想为一种权力的例示,让我们 无法不注意到操演的戏剧性和语言性的维度。在《可激动的语言》里,我 试图指出言语行为是表演出来的(因此是戏剧的,呈现给观众、接受诠 释),同时也是语言的,通过它跟语言惯例隐含的关系,促成一套结果的发 生。如果有人对言语行为这个语言理论如何与身体的姿态产生联系感到 不解,他只要把言语本身想成一种带来特定语言结果的身体行为就行了。 因此,言语不独独属于身体表现,也不独独属于语言,而它同时作为言语 和行为的特质必然是暧昧的。这种暖昧性对出柜实践、对言语行为的造 反力量、对同时作为身体诱惑与伤害威胁的一个先决条件的语言来说,具 有重要的影响。 如果要在现在的情况下重写这本书,我将会加入对跨性别和双性人 的讨论:理想的性别二元形态如何在这两种话语里运作;这些相关关注所 支持的与手术介入(surgical intervention)的各种不同的关系。我也会加 人对种族化的性/欲的讨论,特别是,有关异族通婚的禁忌(以及对跨种族 性交换的浪漫化)对性别所呈现的自然化以及去自然化的形式来说是如 何重要。我持续期待性少数群体之间形成某种联盟,能够超越简单的身 份范畴,能够拒绝对双性情欲的抹除,能够对抗、消解限制性的身体规范 所强加的暴力。我希望这样的联盟是建立在不可化约的性欲复杂性上, 观照到它与各种话语和制度权力动能的牵涉;也希望不会有人急躁地把 权力简化为等级,否定了它的一些生产性的政治维度。即使我认为在现 今统治我们的法律、政治和语言话语里,寻求对性少数身份的承认是很艰 困的一项工作,但我仍然认为它是求生存的一个必要之举。为了政治化 的目的而调用身份范畴,总是面临身份将来可能成我们所对抗的那个权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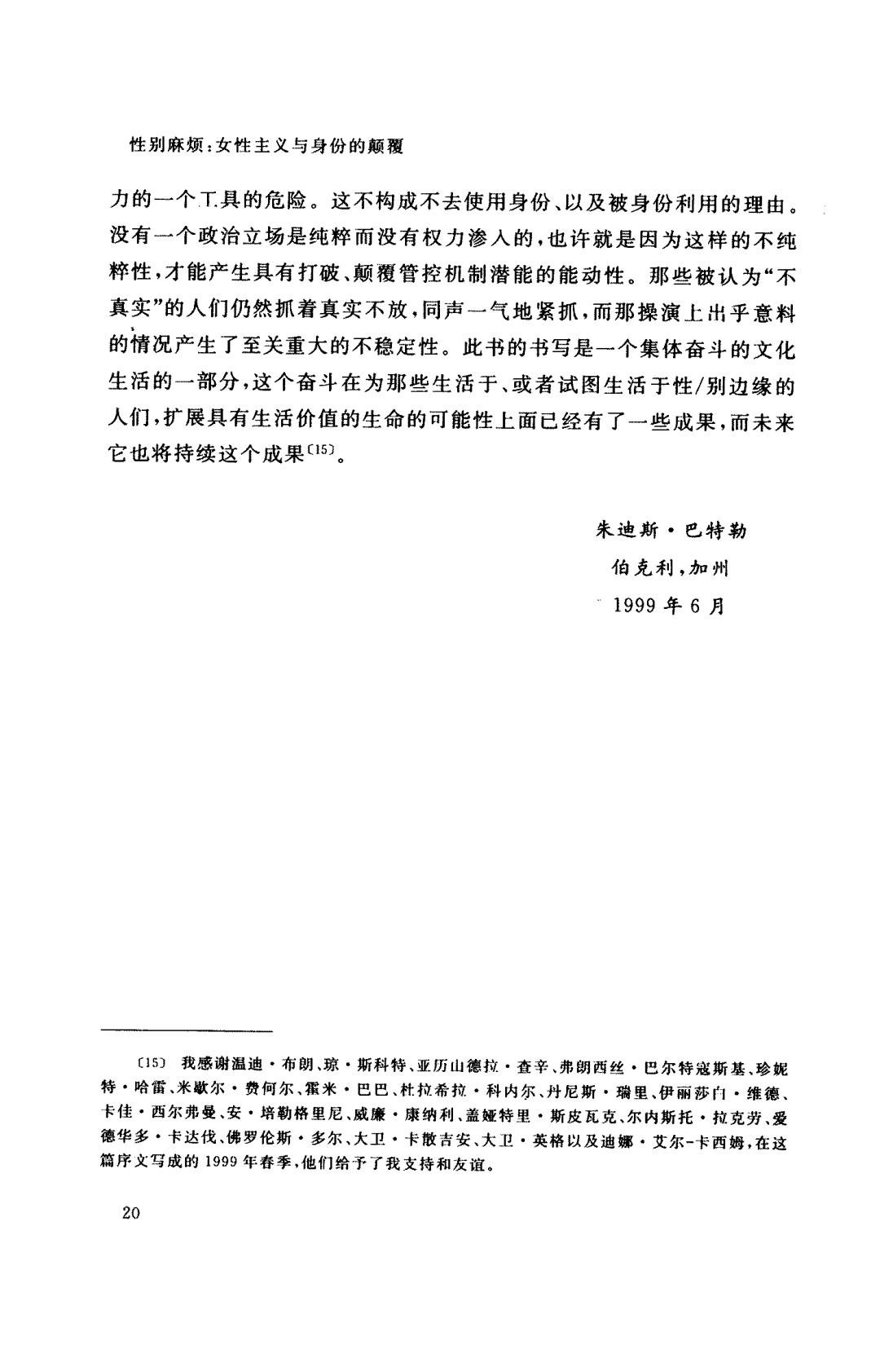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力的一个工具的危险。这不构成不去使用身份、以及被身份利用的理由。 没有一个政治立场是纯粹而没有权力渗入的,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不纯 粹性,才能产生具有打破、颠覆管控机制潜能的能动性。那些被认为“不 真实”的人们仍然抓着真实不放,同声一气地紧抓,而那操演上出乎意料 的情况产生了至关重大的不稳定性。此书的书写是一个集体奋斗的文化 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奋斗在为那些生活于、或者试图生活于性/别边缘的 人们,扩展具有生活价值的生命的可能性上面已经有了一些成果,而未来 它也将持续这个成果〔15)。 朱迪斯·巴特勒 伯克利,加州 ~1999年6月 〔15)我感谢温迪·布朗、琼·斯科特、亚历山德拉·查辛、弗朗西丝·巴尔特寇斯基、珍妮 特·哈街、米歇尔·费何尔、霍米·巴巴、杜拉希拉·科内尔、丹尼斯·瑞里、伊丽莎白·维德、 卡佳·西尔弗曼、安·培勒格里尼、威廉·康纳利、盖娅特里·斯皮瓦克、尔内斯托·拉克劳、爱 德华多·卡达伐、佛罗伦斯·多尔、大卫·卡散吉安、大卫·英格以及迪娜·艾尔-卡西姆,在这 篇序文写成的1999年春季,他们给予了我支持和友谊。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