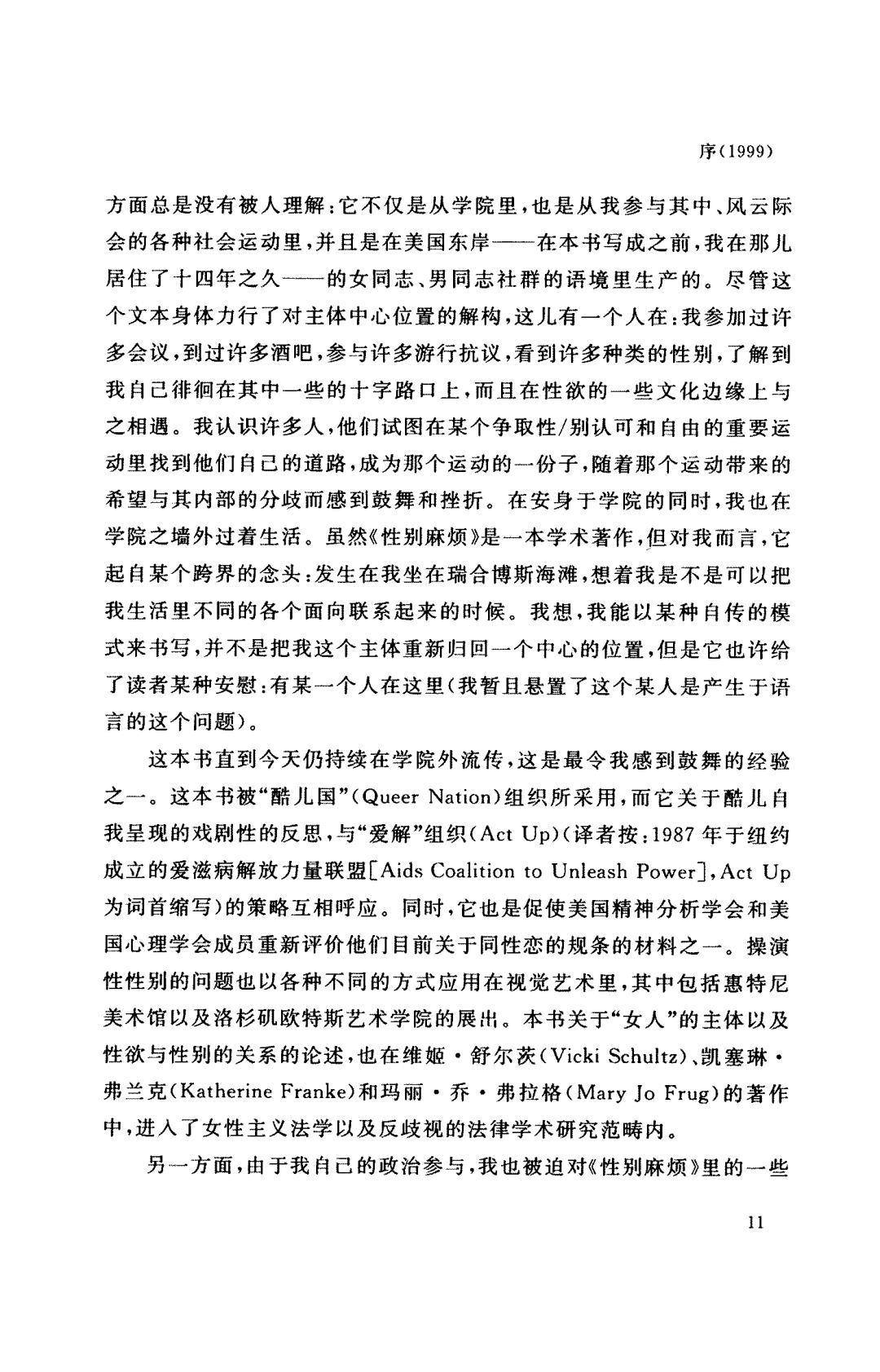
序(1999) 方面总是没有被人理解:它不仅是从学院里,也是从我参与其中、风云际 会的各种社会运动里,并且是在美国东岸一在本书写成之前,我在那儿 居住了十四年之久一的女同志、男同志社群的语境里生产的。尽管这 个文本身体力行了对主体中心位置的解构,这儿有一个人在:我参加过许 多会议,到过许多酒吧,参与许多游行抗议,看到许多种类的性别,了解到 我自己徘徊在其中一些的十字路口上,而且在性欲的一些文化边缘上与 之相遇。我认识许多人,他们试图在某个争取性/别认可和自由的重要运 动里找到他们自己的道路,成为那个运动的一一份子,随着那个运动带来的 希望与其内部的分歧而感到鼓舞和挫折。在安身于学院的同时,我也在 学院之墙外过着生活。虽然《性别麻烦》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对我面言,它 起自某个跨界的念头:发生在我坐在瑞合博斯海滩,想着我是不是可以把 我生活里不同的各个面向联系起来的时候。我想,我能以某种自传的模 式来书写,并不是把我这个主体重新归回一个中心的位置,但是它也许给 了读者某种安慰:有某一个人在这里(我暂且悬置了这个某人是产生于语 言的这个问题)。 这本书直到今天仍持续在学院外流传,这是最令我感到鼓舞的经验 之一。这本书被“酷儿国”(Queer Nation)组织所采用,而它关于酷儿自 我呈现的戏剧性的反思,与“爱解”组织(Act Up)(译者按:1987年于纽约 成立的爱滋病解放力量联盟[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Act Up 为词首缩写)的策略互相呼应。同时,它也是促使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和美 国心理学会成员重新评价他们目前关于同性恋的规条的材料之一。操演 性性别的问题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应用在视觉艺术里,其中包括惠特尼 美术馆以及洛杉矶欧特斯艺术学院的展出。本书关于“女人”的主体以及 性欲与性别的关系的论述,也在维姬·舒尔茨(Vicki Schultz)、凯塞琳· 弗兰克(Katherine Franke)和玛丽·乔·弗拉格(Mary Jo Frug)的著作 中,进入了女性主义法学以及反歧视的法律学术研究范畴内。 另一方面,由于我自己的政治参与,我也被迫对《性别麻烦》里的一些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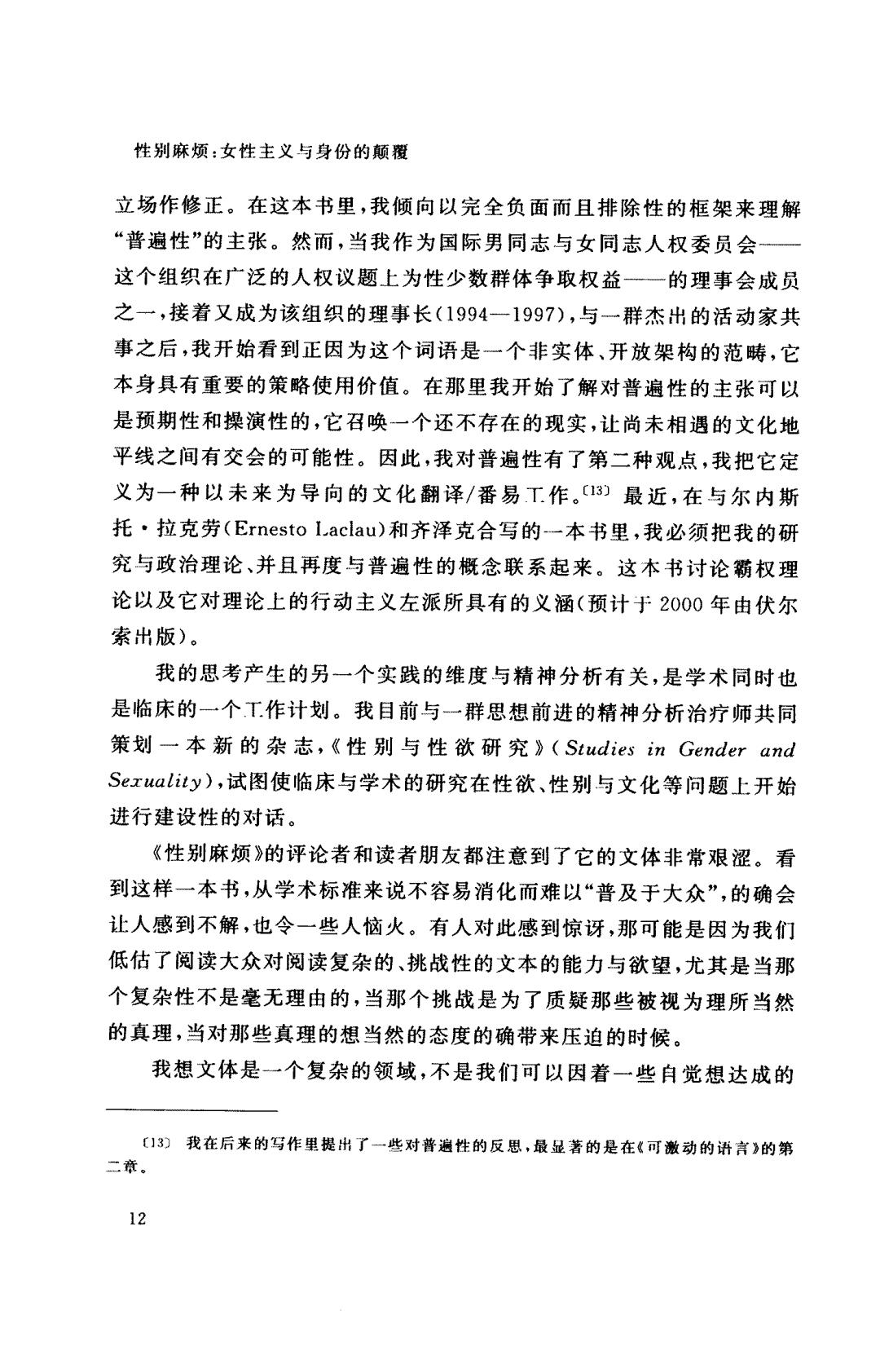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立场作修正。在这本书里,我倾向以完全负面而且排除性的框架来理解 “普遍性”的主张。然面,当我作为国际男同志与女同志人权委员会 这个组织在广泛的人权议题上为性少数群体争取权益一的理事会成员 之一,接着又成为该组织的理事长(1994一1997),与一群杰出的活动家共 事之后,我开始看到正因为这个词语是一个非实体、开放架构的范畴,它 本身具有重要的策略使用价值。在那里我开始了解对普遍性的主张可以 是预期性和操演性的,它召唤一个还不存在的现实,让尚未相遇的文化地 平线之间有交会的可能性。因此,我对普遍性有了第二种观点,我把它定 义为一种以未来为导向的文化翻译/番易.工作。13)最近,在与尔内斯 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齐泽克合写的一本书里,我必须把我的研 究与政治理论、并且再度与普遍性的概念联系起来。这本书讨论额权理 论以及它对理论上的行动主义左派所具有的义涵(预计于2000年由伏尔 索出版)。 我的思考产生的另一个实践的维度与精神分析有关,是学术同时也 是临床的一个工作计划。我目前与一群思想前进的精神分析治疗师共同 策划一本新的杂志,《性别与性欲研究》(Studies in Gender and Sexuality),试图使临床与学术的研究在性欲、性别与文化等问题上开始 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性别麻烦》的评论者和读者朋友都注意到了它的文体非常艰涩。看 到这样一本书,从学术标准来说不容易消化而难以“普及于大众”,的确会 让人感到不解,也令一些人恼火。有人对此感到惊讶,那可能是因为我们 低估了阅读大众对阅读复杂的、挑战性的文本的能力与欲望,尤其是当那 个复杂性不是毫无理由的,当那个挑战是为了质疑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 的真理,当对那些真理的想当然的态度的确带来压迫的时候。 我想文体是一个复杂的领域,不是我们可以因着一些自觉想达成的 〔13)我在后来的写作里提出了一些对普遍性的反思,最显著的是在《可激动的语言》的第 二章。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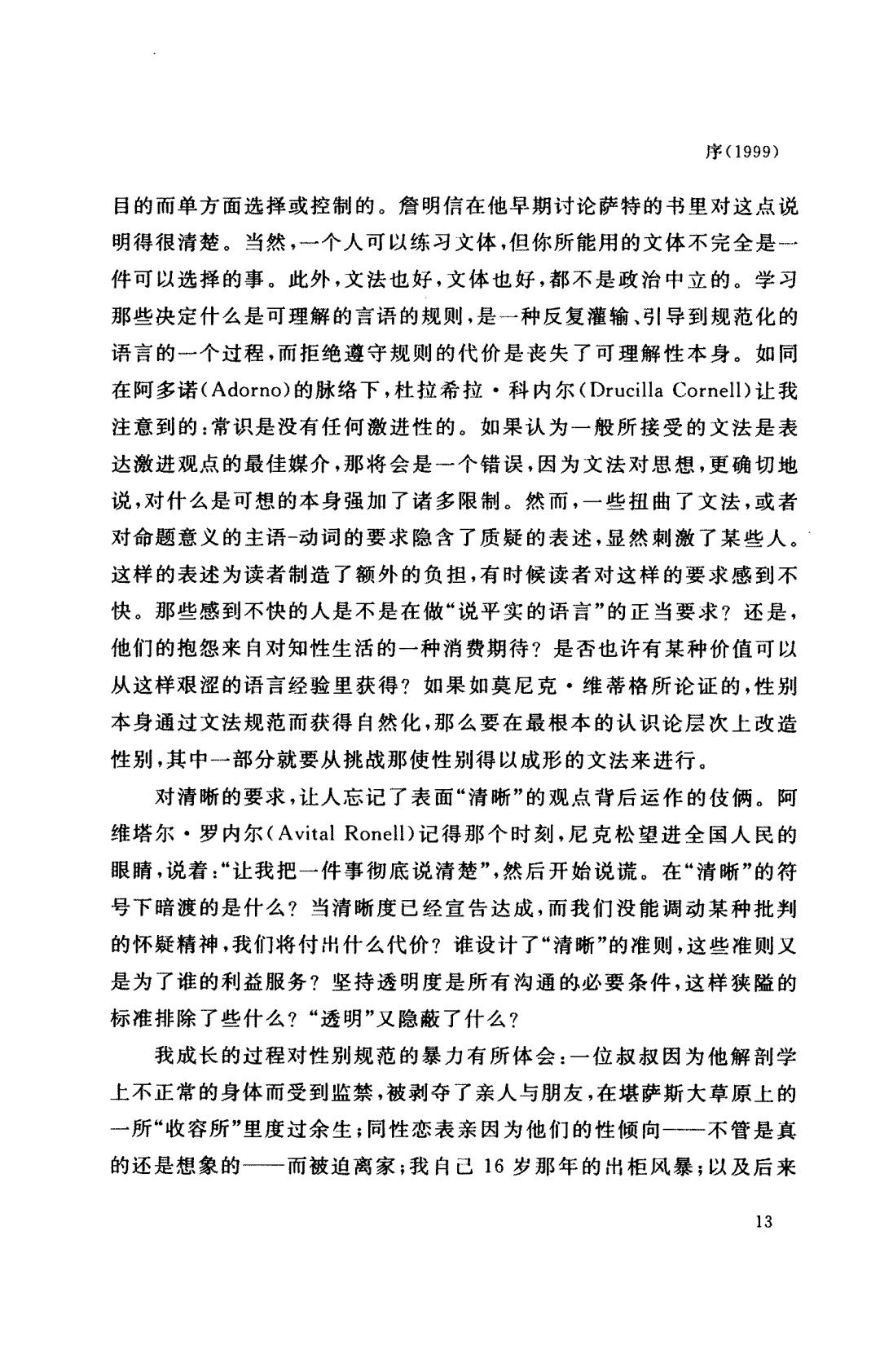
序(1999) 目的而单方面选择或控制的。詹明信在他早期讨论萨特的书里对这点说 明得很清楚。当然,一个人可以练习文体,但你所能用的文体不完全是… 件可以选择的事。此外,文法也好,文体也好,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学习 那些决定什么是可理解的言语的规则,是一种反复灌输、引导到规范化的 语言的一个过程,而拒绝遵守规则的代价是丧失了可理解性本身。如同 在阿多诺(Adorno)的脉络下,杜拉希拉·科内尔(Drucilla Cornell)让我 注意到的:常识是没有任何激进性的。如果认为一般所接受的文法是表 达激进观点的最佳媒介,那将会是一个错误,因为文法对思想,更确切地 说,对什么是可想的本身强加了诸多限制。然而,一些扭曲了文法,或者 对命题意义的主语-动词的要求隐含了质疑的表述,显然刺激了某些人。 这样的表述为读者制造了额外的负担,有时候读者对这样的要求感到不 快。那些感到不快的人是不是在做“说平实的语言”的正当要求?还是, 他们的抱怨来自对知性生活的一种消费期待?是否也许有某种价值可以 从这样艰涩的语言经验里获得?如果如莫尼克·维蒂格所论证的,性别 本身通过文法规范而获得自然化,那么要在最根本的认识论层次上改造 性别,其中一部分就要从挑战那使性别得以成形的文法来进行。 对清晰的要求,让人忘记了表面“清晰”的观点背后运作的伎俩。阿 维塔尔·罗内尔(Avital Ronell)记得那个时刻,尼克松望进全国人民的 眼睛,说着:“让我把一件事彻底说清楚”,然后开始说谎。在“清晰”的符 号下暗渡的是什么?当清晰度已经宣告达成,而我们没能调动某种批判 的怀疑精神,我们将付出什么代价?谁设计了“清晰”的准则,这些准则又 是为了谁的利益服务?坚持透明度是所有沟通的必要条件,这样狭隘的 标准排除了些什么?“透明”又隐蔽了什么? 我成长的过程对性别规范的暴力有所体会:一位叔叔因为他解剖学 上不正常的身体而受到监禁,被剥夺了亲人与朋友,在堪萨斯大草原上的 一所“收容所”里度过余生;同性恋表亲因为他们的性倾向一一不管是真 的还是想象的一而被迫离家;我白己16岁那年的出柜风暴;以及后来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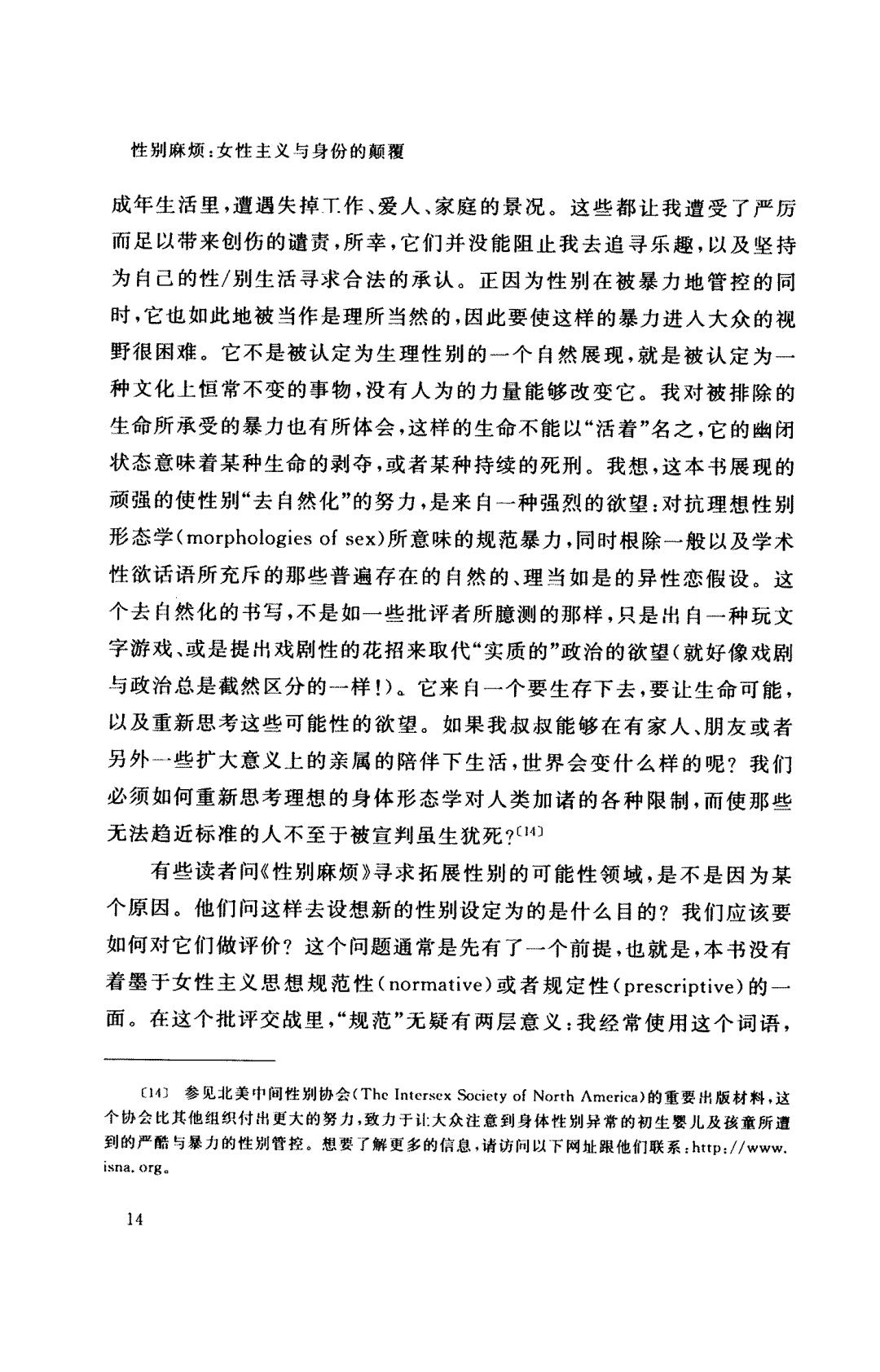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成年生活里,遭遇失掉工作、爱人、家庭的景况。这些都让我遭受了严厉 而足以带来创伤的谴责,所幸,它们并没能阻止我去追寻乐趣,以及坚持 为自己的性/别生活寻求合法的承认。正因为性别在被暴力地管控的同 时,它也如此地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要使这样的暴力进入大众的视 野很困难。它不是被认定为生理性别的一个自然展现,就是被认定为一 种文化上恒常不变的事物,没有人为的力量能够改变它。我对被排除的 生命所承受的暴力也有所体会,这样的生命不能以“活着”名之,它的幽闭 状态意味着某种生命的剥夺,或者某种持续的死刑。我想,这本书展现的 顽强的使性别“去自然化”的努力,是来自一种强烈的欲望:对抗理想性别 形态学(morphologies of sex)所意味的规范暴力,同时根除一般以及学术 性欲话语所充斥的那些普遍存在的自然的、理当如是的异性恋假设。这 个去自然化的书写,不是如一些批评者所臆测的那样,只是出自一种玩文 字游戏、或是提出戏剧性的花招来取代“实质的”政治的欲望(就好像戏剧 与政治总是截然区分的一样!)。它来自一个要生存下去,要让生命可能, 以及重新思考这些可能性的欲望。如果我叔叔能够在有家人、朋友或者 另外一些扩大意义上的亲属的陪伴下生活,世界会变什么样的呢?我们 必须如何重新思考理想的身体形态学对人类加诸的各种限制,而使那些 无法趋近标准的人不至于被宣判虽生犹死?(4们 有些读者问《性别麻烦》寻求拓展性别的可能性领域,是不是因为某 个原因。他们问这样去设想新的性别设定为的是什么目的?我们应该要 如何对它们做评价?这个问题通常是先有了一个前提,也就是,本书没有 着墨于女性主义思想规范性(normative)或者规定性(prescriptive)的一 面。在这个批评交战里,“规范”无疑有两层意义:我经常使用这个词语, I4)参见北美中间性别协会(The Intersex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的重要出版材料,这 个协会比其他组织付出更大的努力,致力于计:大众注意到身体性别异常的初生婴儿及孩童所遭 到的严酷与暴力的性别管控。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以下网址跟他们联系:http://www. isna.org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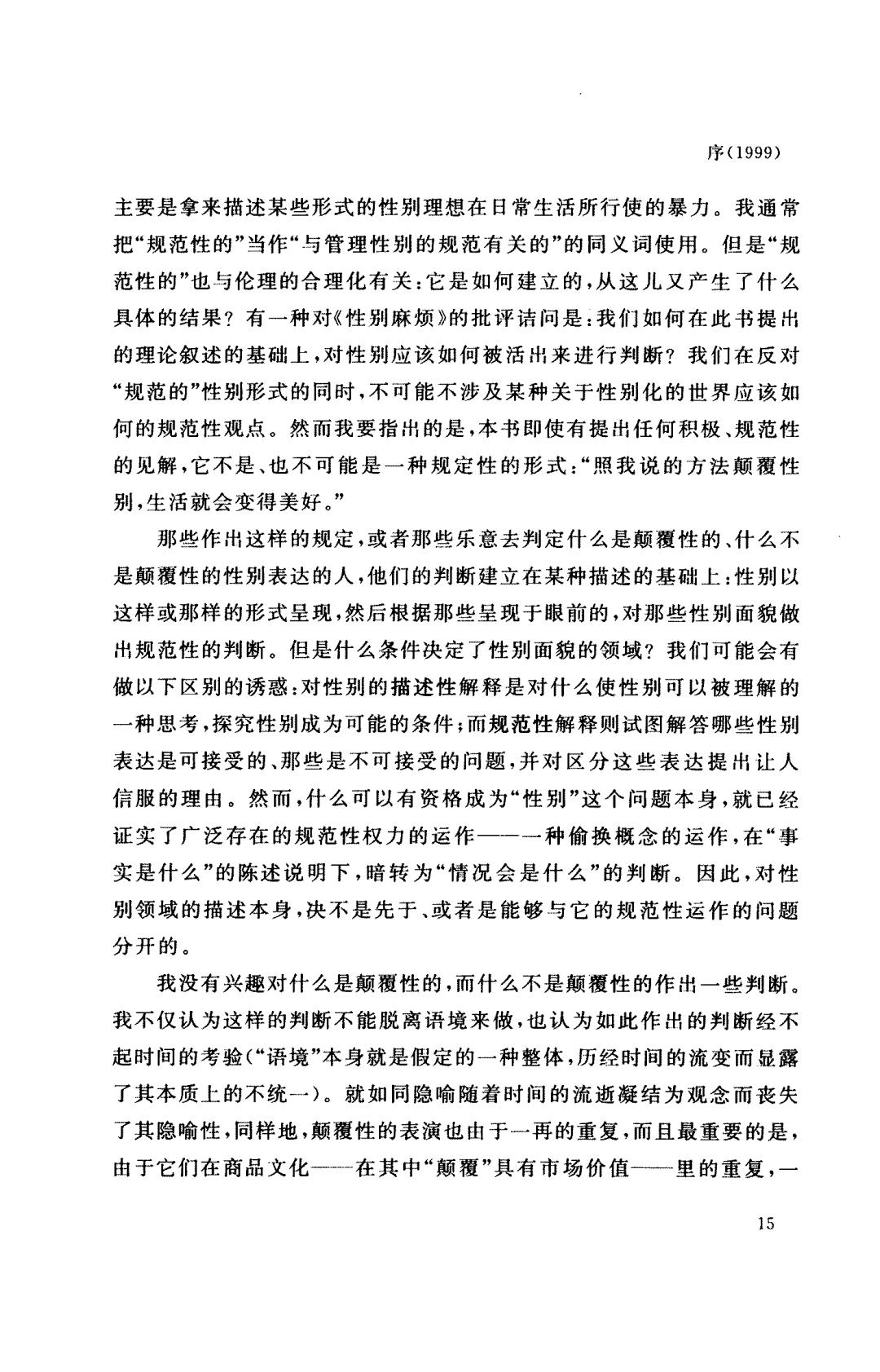
序(1999) 主要是拿来描述某些形式的性别理想在日常生活所行使的暴力。我通常 把“规范性的”当作“与管理性别的规范有关的”的同义词使用。但是“规 范性的”也与伦理的合理化有关:它是如何建立的,从这儿又产生了什么 具体的结果?有一种对《性别麻烦》的批评诘问是:我们如何在此书提出 的理论叙述的基础上,对性别应该如何被活出来进行判断?我们在反对 “规范的”性别形式的同时,不可能不涉及某种关于性别化的世界应该如 何的规范性观点。然而我要指出的是,本书即使有提出任何积极、规范性 的见解,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规定性的形式:“照我说的方法颠覆性 别,生活就会变得美好。” 那些作出这样的规定,或者那些乐意去判定什么是颠覆性的、什么不 是颠覆性的性别表达的人,他们的判断建立在某种描述的基础上:性别以 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呈现,然后根据那些呈现于跟前的,对那些性别面貌做 出规范性的判断。但是什么条件决定了性别面貌的领域?我们可能会有 做以下区别的诱惑:对性别的描述性解释是对什么使性别可以被理解的 一种思考,探究性别成为可能的条件;而规范性解释则试图解答哪些性别 表达是可接受的、那些是不可接受的问题,并对区分这些表达提出让人 信服的理由。然而,什么可以有资格成为“性别”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 证实了广泛存在的规范性权力的运作 一一一种偷换概念的运作,在“事 实是什么”的陈述说明下,暗转为“情况会是什么”的判断。因此,对性 别领域的描述本身,决不是先于、或者是能够与它的规范性运作的问题 分开的。 我没有兴趣对什么是颠覆性的,而什么不是颠覆性的作出一些判断。 我不仅认为这样的判断不能脱离语境来做,也认为如此作出的判断经不 起时间的考验(“语境”本身就是假定的一种整体,历经时间的流变而显露 了其本质上的不统一)。就如同隐喻随着时间的流逝凝结为观念而丧失 了其隐喻性,同样地,颠覆性的表演也由于一再的重复,而且最重要的是, 由于它们在商品文化一一在其中“颠覆”具有市场价值一里的重复,一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