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理论的范畴。因此化学家詹姆斯·科南特曾说:“理论只能被 另一理论推翻。”(Conant,947,p.48)而物理学家约翰·瑞德·普 拉特(John Rader Platt)也认为:“当我们接近巨大的、单一的综合 体(syntheses)时,科学决定论的压力就变得微弱而散乱,因为这 些综合体不仅是一种发现,而且是由人的品位和风格形塑出来 的艺术创造。”(Plat,1956,p.75)这些论述为数学家亨利·普恩 加莱(Henri Poincare)的著名论证作了注解,他曾说道:如果对某 种现象可以根据力学做出解释,那么我们也可以根据无数个其 他理由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2理论的确建构起某种现实,但永 远不能说这就是“现实”。我们面临着无穷的数据以及无限多的 可能的解释。这是一个双重问题。事实不能决定理论,而对于 一组事实则能有多个理论适用。理论无法确定无疑地解释事 实,我们也无法保证一个好的理论有朝一日不会被另一个更好 的理论所代替。 我已经阐述了理论是什么,但尚未说明理论是如何形成的。 那么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呢?最好的、也是最简短的回答就是理 论是被“创造性地”(creatively)创立起来的,不过这一答案却毫 尤助益。“创造性地”这个词提出了问题,但却没有说明如何解 决问题,如何从观察和经验过渡到解释性理论呢?最漫长而痛 苦的不断探索与错误并不能导致理论的创立,除非在某一时刻 智慧的灵光闪现,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观点在脑海中浮现。你无 法说明灵感从何而来,观点又是如何诞生的,但你知道它们是与 什么有关的。它们涉及研究主题的组织问题,向你传达事物间 不可观察到的联系,以及赋予所观察事物以不同意义的因果联 系与原因。理论并非所见的事物或记录来的联系,而是对它 们的解释。关于自由落体加速度的公式解释物体是如何下 落的,人们必须到经典物理学中去寻找答,而它则属于牛顿学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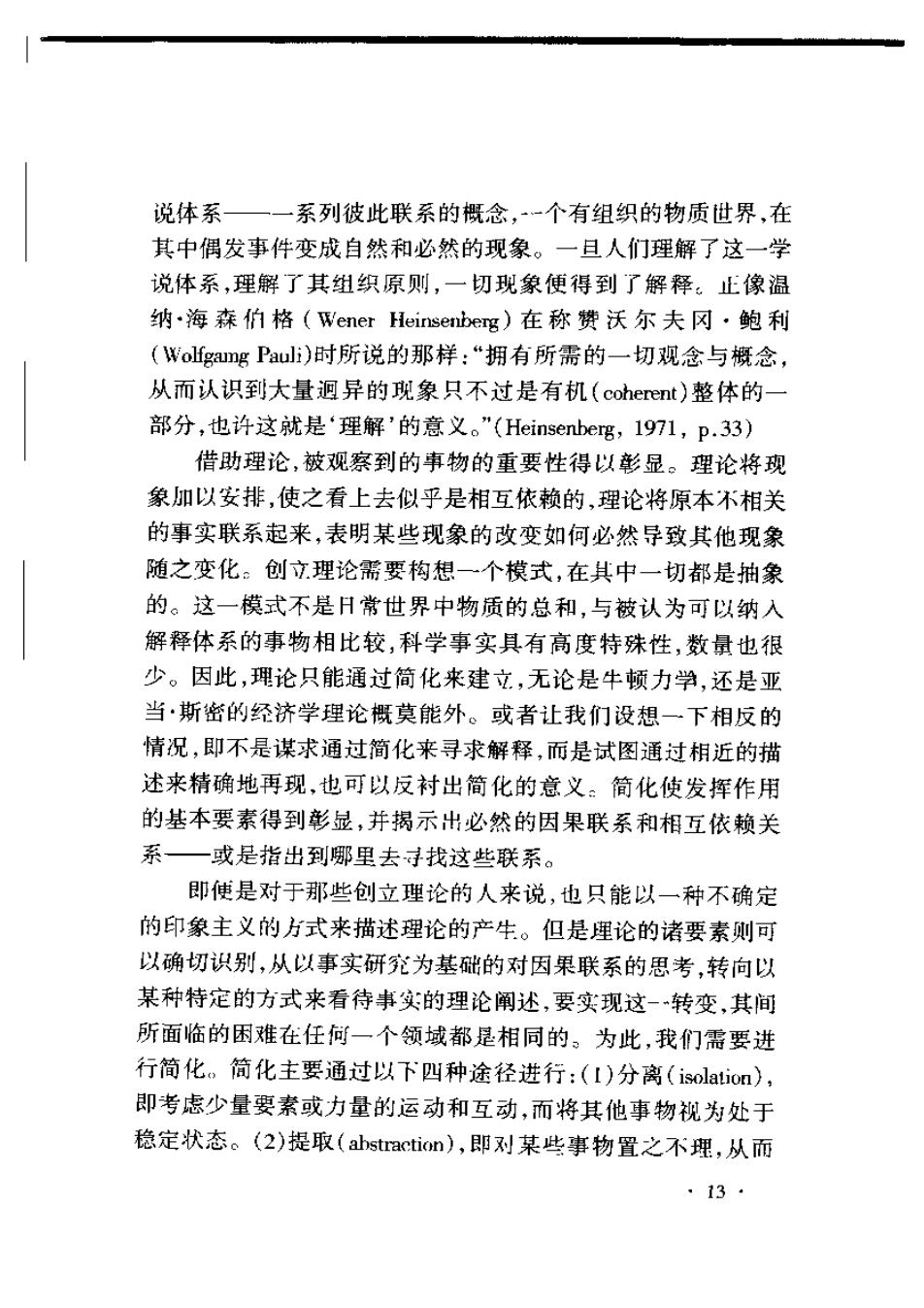
说体系一一系列彼此联系的概念,一个有组织的物质世界,在 其中偶发事件变成自然和必然的现象。一旦人们理解了这一学 说体系,理解了其组织原则,一切现象便得到了解释。止像温 纳·海森伯格(Wener Heinsenberg)在称赞沃尔夫冈·鲍利 (Wolfgag Pauli)时所说的那样:“拥有所需的一切观念与概念, 从而认识到大量迥异的现象只不过是有机(coherent)整体的一 部分,也许这就是‘理解'的意义。”(Heinsenberg,l971,p.33) 借助理论,被观察到的事物的重要性得以彰显。理论将现 象加以安排,使之看上去似乎是相互依赖的,理论将原本不相关 的事实联系起来,表明某些现象的改变如何必然导致其他现象 随之变化。创立理论需要构想一个模式,在其中一切都是抽象 的。这一模式不是H常世界中物质的总和,与被认为可以纳入 解释体系的事物相比较,科学事实具有高度特殊性,数量也很 少。因此,理论只能通过简化来建立,无论是牛顿力学,还是亚 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概莫能外。或者让我们设想一下相反的 情况,即不是谋求通过简化来寻求解释,而是试图通过相近的描 述来精确地再现,也可以反衬出简化的意义。简化使发挥作用 的基本要素得到彰显,并揭示出必然的因果联系和相互依赖关 系一或是指出到哪里去找这些联系。 即使是对于那些创立理论的人来说,也只能以一种不确定 的印象主义的方式来描述理论的产生。但是理论的诸要素则可 以确切识别,从以事实研究为基础的对因果联系的思考,转向以 某种特定的方式来看待事实的理论阐述,要实现这-转变,其间 所面临的困难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相同的、为此,我们需要进 行简化,简化主要通过以下四种途径进行:(I)分离(isolation), 即考虑少量要素或力量的运动和互动,而将其他事物视为处于 稳定状态。(2)提取(abstraction),即对某些事物置之不理,从而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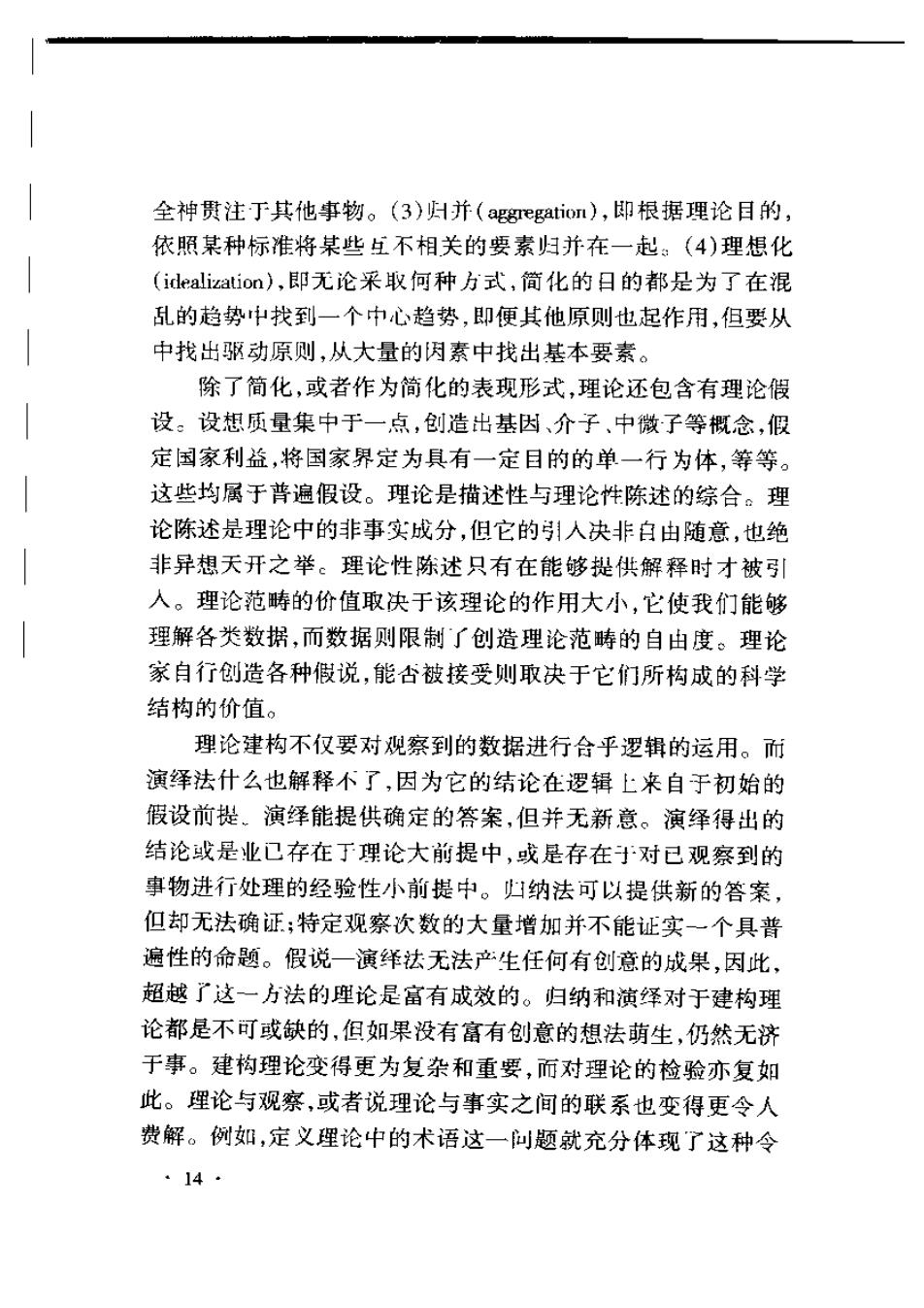
全神贯注于其他事物。(3)H并(aggregation),即根据理论目的, 依照某种标准将某些生不相关的要素归并在一起。(4)理想化 (idealization),即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简化的日的都是为了在混 乱的趋势中找到一个中心趋势,即便其他原则也起作用,但要从 中找出驱动原则,从大量的因素中找出基本要素。 除了简化,或者作为简化的表现形式,理论还包含有理论假 设。设想质量集中于一点,创造出基因、介子、中微子等概念,假 定国家利益,将国家界定为具有一定目的的单一行为体,等等。 这些均属于普遍假设。理论是描述性与理论性陈述的综合。理 论陈述是理论中的非事实成分,但它的引人决非自由随意,也绝 非异想天开之举。理论性陈述只有在能够提供解释时才被引 人。理论范畴的价值取决于该理论的作用大小,它使我们能够 理解各类数据,而数据则限制了创造理论范畴的自由度。理论 家自行创造各种假说,能否被接受则取决于它们所构成的科学 结构的价值。 理论建构不仅要对观察到的数据进行合乎逻辑的运用。而耐 演绎法什么也解释不了,因为它的结论在逻辑上来自于初始的 假设前提、演绎能提供确定的答案,但并无新意。演绎得出的 结论或是业已存在于理论大前提中,或是存在于对已观察到的 事物进行处理的经验性小前提中。归纳法可以提供新的答案, 但却无法确证:特定观察次数的大量增加并不能证实一个具普 遍性的命题。假说一演绎法无法产生任何有创意的成果,因此, 超越了这一方法的理论是富有成效的。归纳和演绎对于建构理 论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如果没有富有创意的想法萌生,仍然无济 于事。建构理论变得更为复杂和重要,而对理论的检验亦复如 此。理论与观察,或者说理论与事实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更令人 费解。例如,定义理论中的术语这一问题就充分体现了这种令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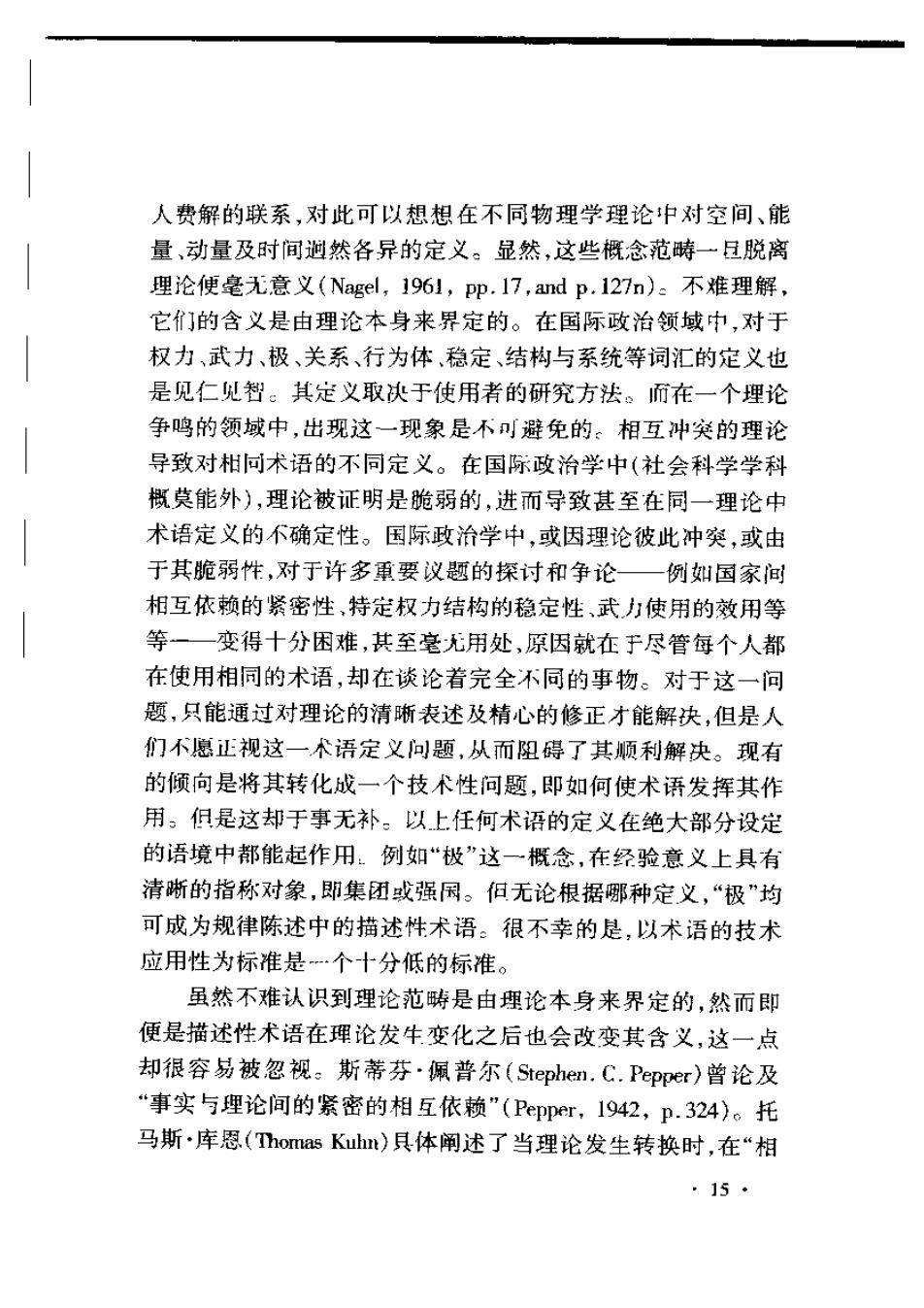
人费解的联系,对此可以想想在不同物理学理论中对空间、能 量、动量及时间迥然各异的定义。显然,这些概念范畴一且脱离 理论便毫无意义(Nagel,16l,Pp.17,andp.127n)。不难理解, 它们的含义是由理论本身来界定的。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对于 权力、武力、极、关系、行为体、稳定、结构与系统等词汇的定义也 是见仁见智。其定义取决于使用者的研究方法。而在一个理论 争鸣的领域中,出现这一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相互冲突的理论 导致对柑问术语的不同定义。在国际政治学中(社会科学学科 概莫能外),理论被证明是脆弱的,进而导致甚至在同一理论中 术语定义的不确定性。国际政治学中,或因理论彼此冲突,或由 于其脆弱性,对于许多重要议题的探讨和争论一例如国家间 相互依赖的紧密性,持定权力结构的稳定性、武力使用的效用等 等一变得十分困稚,其至毫无用处,原因就在于尽管每个人都 在使用相同的术语,却在谈论着完全不同的事物。对于这一问 题,只能通过对理论的清晰表述及精心的修正才能解决,但是人 们不愿正视这一术语定义问题,从而阻碍了其顺利解决。现有 的倾向是将其转化成一个技术性问题,即如何使术语发挥其作 用。但是这却于事无补。以上任何术语的定义在绝大部分设定 的语境中都能起作用.例如“极”这一概念,在经验意义上具有 清晰的指称对象,即集团或强闲。旧无论根据哪种定义,“极”均 可成为规律陈述中的描述性术语。很不幸的是,以术语的技术 应用性为标准是…个十分低的标准。 虽然不难认识到理论范畴是由理论本身来界定的,然而即 便是描述性术语在理论发牛变化之后也会改变其含义,这一点 却很容易被忽视。斯蒂芬·佩普尔(Stephen.C.Pepper)曾论及 “事实与理论间的紧密的相互依赖”(Pepper,1942,p.324)。托 马斯·库恩(Thomas Kuhn)具体阐述了当理论发生转换时,在“相 ·15

似关系”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某一理论中,属于相同或相异系 列中的客体,在另一理论中可能会被归人完全不同的系列中,就 像太阳、月球、火星与地球的排列顺序在哥白尼日心说创立前后 就截然不同一样。就像库恩所说,如果两个人遵从不同的理论, “我们不能保证他们所看到的是同样的事物,所掌握的是同样的 数据,只不过认识和解释的方法不同而已”(Khn,1970,p. 266一276),我们是否只是认识我们所见到的,抑或我们只能见 到我们所认识的东西?我们的头脑无法记录并了解我们所有所 见所闻。因此我们倾向于看到我们希望看到的,根据我们对事 物原因的感觉去发现我认为重要的事物。 理论的变化导致术语含义的变化,理论不仅界定术语,而且 指明术语如何得到正确应用。前文刚刚提及,应用问题只是一 个次要或者说实用问题,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又是个具有 根本重要性的问题。理论解释什么与什么相联系,这些联系又 是如何形成的。理论指出事物是如何运作的,如何联系在一起, 或者研究领域的结构是什么?如果某一领域内的组织对其内部 各变量的相互作用具有影响,那么在弄清变量是如何彼此联系 的之前,对数据进行处理便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在某些人看来, 正如在国际领域内一样,似乎这些变量都是彼此直接相联,而不 存在结构的限制,即仿佛我们所研究的现象都存在于同一层次 上。他们只是味积累相关系数的数据,却从不过问哪些理论 导致入们预期在哪些变量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 在开始研究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弄清二个常常被忽视的问 题,而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忽视才导致大量的工作不得要领。这 三个问题是: ●研究对象是否允许采用实验经典物理学的分析方法一 即在其他变量保持恒定的情况下检验(exam)两个变量的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