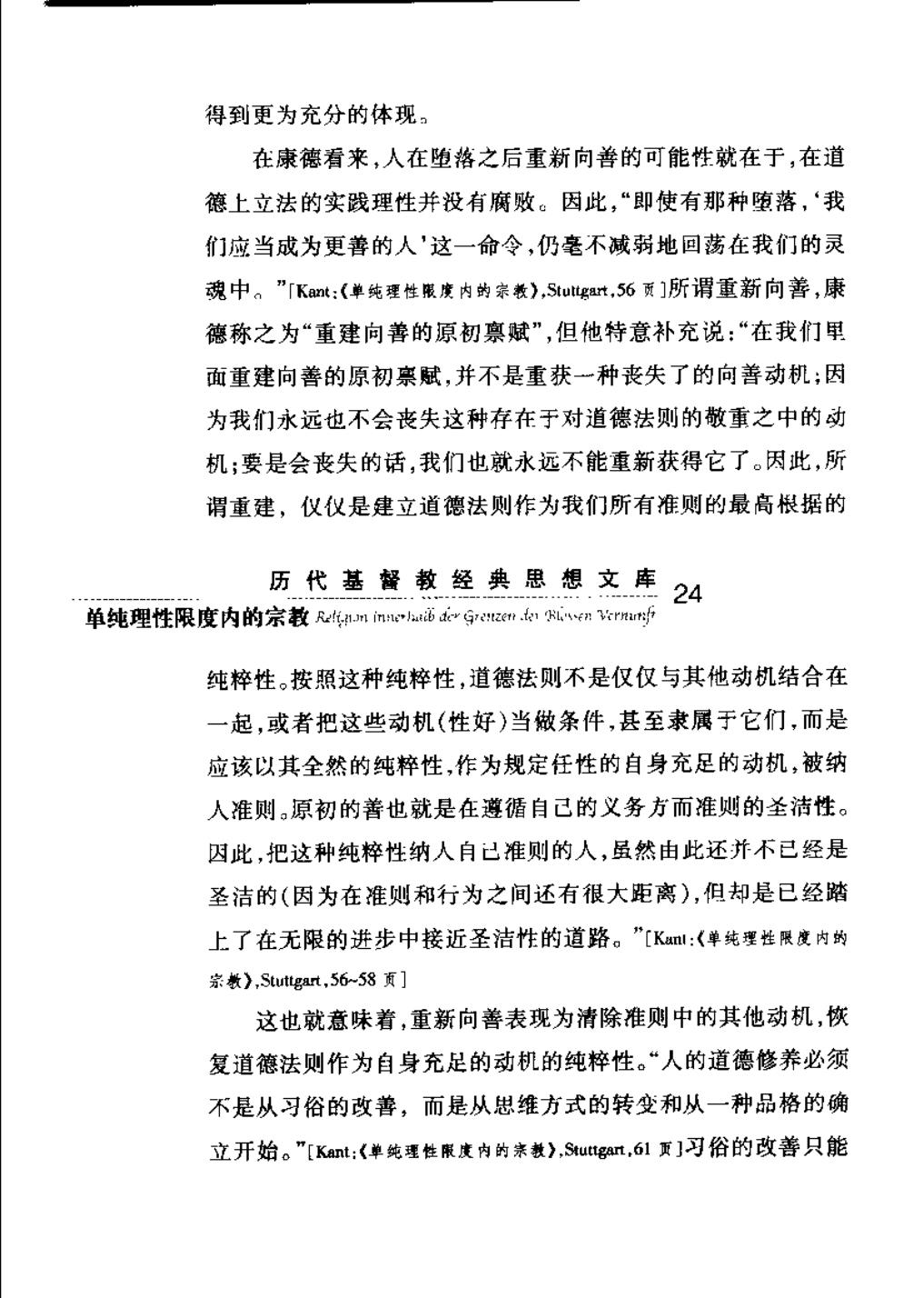
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 在康德看来,人在堕格之后重新向善的可能性就在于,在道 德上立法的实践理性并没有腐败。因此,“即使有那种堕落,‘我 们应当成为更善的人'这一命令,仍毫不减弱地回荡在我们的灵 魂中。”「Kamt:(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Stuligart,56页]所谓重新向善,康 德称之为“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但他特意补充说:“在我们里 面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并不是重获一种丧失了的向善动机:因 为我们永远也不会丧失这种存在于对道德法则的敬重之中的动 机;要是会丧失的话,我们也就永远不能重新获得它了。因此,所 谓重建,仪仪是建立道德法则作为我们所有准则的最高根据的 历代基餐教经典思想文库 24 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R兵,n inneh话dev Grez?.1nrr 纯粹性。按照这种纯粹性,道德法则不是仅仅与其他动机结合在 一起,或者把这些动机(性好)当做条件,甚至隶属于它们,而是 应该以其全然的纯粹性,作为规定任性的自身充足的动机,被纳 人准则,原初的善也就是在遵循自己的义务方而准则的圣洁性。 囚此,把这种纯粹性纳人自已准则的人,虽然由此还并不已经是 圣洁的(因为在准则和行为之间还有很大距离),但却是已经踏 上了在无限的进步中接近圣洁性的道路。”[Ka:《单纯理性限度内的 宗教),Stuttgart,5658页] 这也就意味着,重新向善表现为清除雅则中的其他动机,恢 复道德法则作为自身充足的动机的纯粹性。“人的道德修养必须 不是从习俗的改善,而是从忠维方式的转变和从一种品格的确 立开始。”[Kant:《单纯理性限度内的条教》,Stutigart,61页]习俗的改善只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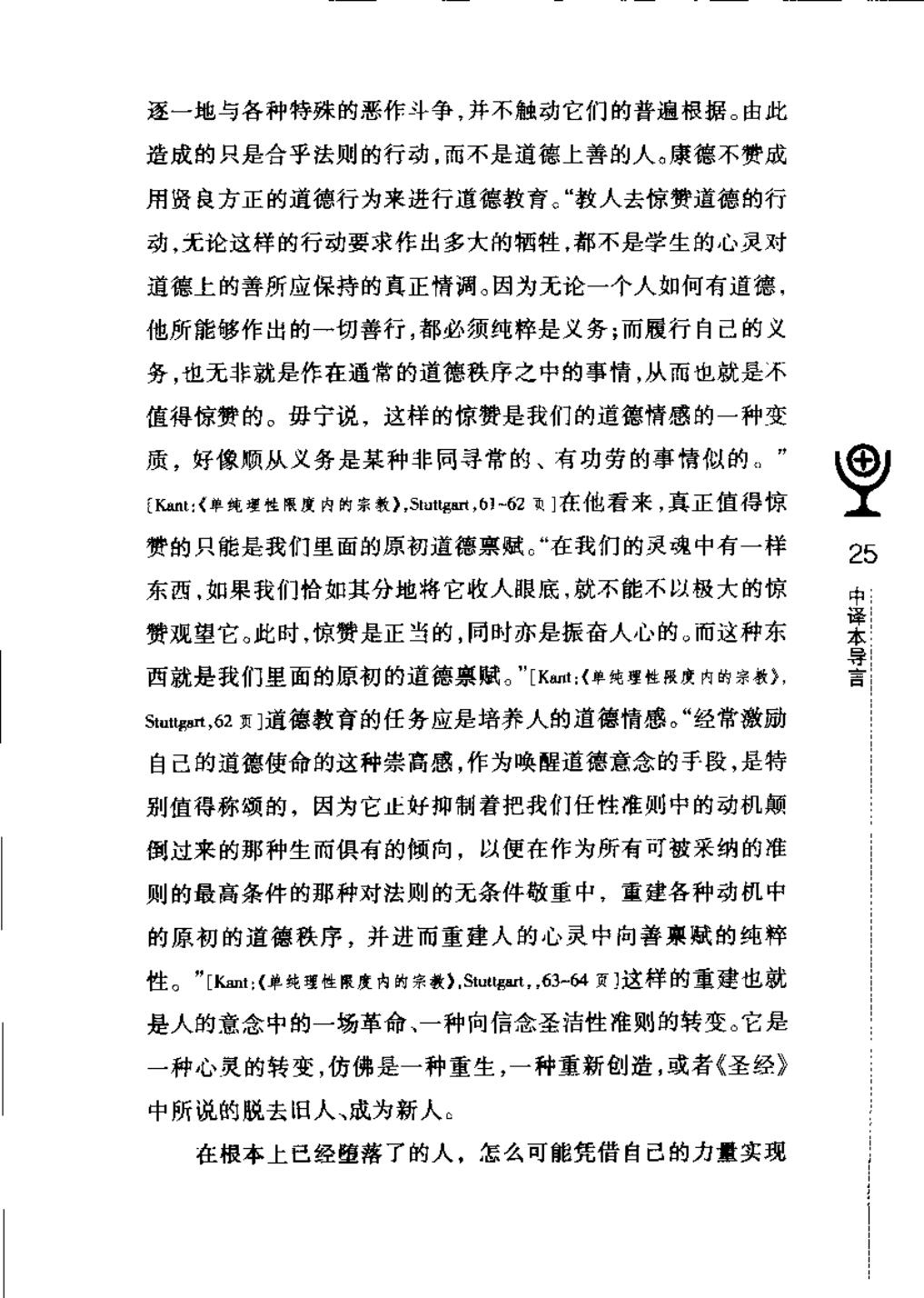
逐一地与各种特殊的恶作斗争,并不触动它们的普遍根据。由此 造成的只是合乎法则的行动,而不是道德上善的人。康德不赞成 用贤良方正的道德行为来进行道德教育。“教人去惊赞道德的行 动,无论这样的行动要求作出多大的牺牲,都不是学生的心灵对 道德上的善所应保持的真正情调。因为无论一个人如何有道德, 他所能够作出的一切善行,都必须纯粹是义务;而履行自己的义 务,也无非就是作在通常的道德秩序之中的事情,从而也就是不 值得惊赞的。毋宁说,这样的惊赞是我们的道德情感的一种变 质,好像顺从义务是某种非同寻常的、有功劳的事情似的。” {Kant:《单纯埋性限度内的宗教),Stuttgart,b1-62更]在他看来,真正值得惊 赞的只能是我们里面的原初道德禀赋。“在我们的灵魂中有一样 25 东西,如果我们恰如其分地将它收人眼底,就不能不以极大的惊 译 赞观望它。此时,惊赞是正当的,同时亦是振奋人心的。而这种东 西就是我们里面的原初的道德禀赋。”[Kat:《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 导言 Stutlgart,62页]道德教育的任务应是培养人的道德情感。“经常激励 自己的道德使命的这种崇高感,作为唤醒道德意念的手段,是特 别值得称颂的,因为它止好抑制着把我们任性准则中的动机颠 倒过来的那种生而俱有的倾向,以便在作为所有可被采纳的准 则的最高条件的那种对法则的无条件敬重中,重建各种动机中 的原初的道德秩序,并进而重建人的心灵中向善禀赋的纯粹 性。”[Kamt:(单纯理性假度内的宗表).Stutlgart,63-64页]这样的重建也就 是人的意念中的一场革命、一种向信念圣洁性准则的转变。它是 一种心灵的转变,仿佛是一种重生,一种重新创造,或者《圣经》 中所说的脱去旧人、成为新人 在根本上已经堕落了的人,怎么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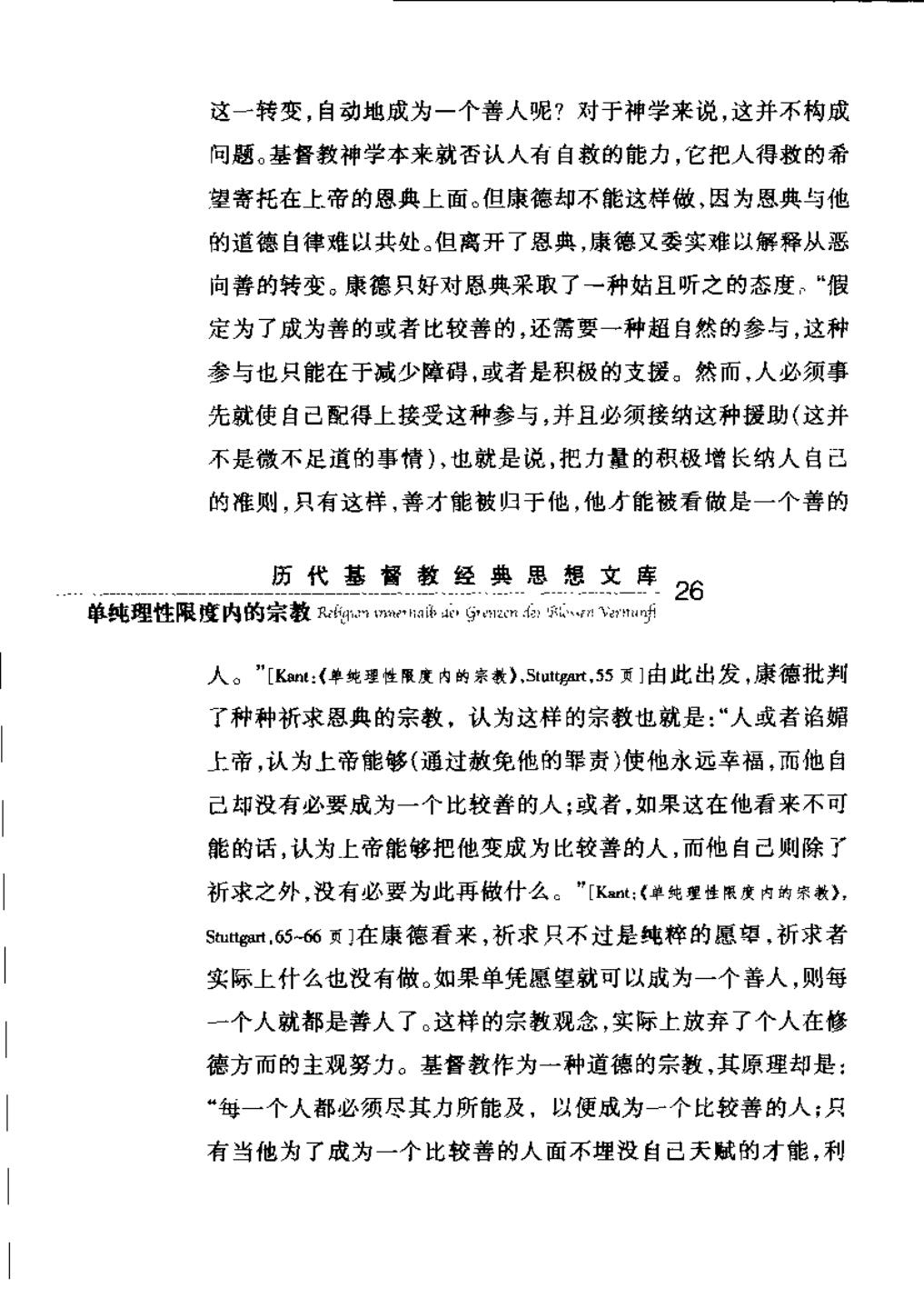
这一转变,自动地成为一个善人呢?对于神学来说,这并不构成 问题。基督教神学本来就否认人有自救的能力,它把人得救的希 望寄托在上帝的恩典上面。但康德却不能这样做,因为恩典与他 的道德自律难以共处。但离开了恩典,康德又委实难以解释从恶 向善的转变。康德只好对恩典采取了一种姑且听之的态度、“假 定为了成为善的或者比较善的,还需要一种超自然的参与,这种 参与也只能在于减少障碍,或者是积极的支援。然而,人必须事 先就使自已配得上接受这种参与,并且必须接纳这种援助(这并 不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也就是说,把力量的积极增长纳人自己 的准则,只有这样,善才能被归于他,他才能被看做是一个善的 历代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 26 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Riig menai语r12cn,wn2Tn呼 人。”[Kan:(单纯理性假度内的桌载),Stuttgart,55页]由此出发,康德批判 了种种析求恩典的宗教,认为这样的宗教也就是:“人或者谄媚 上帝,认为上帝能够(通过赦免他的罪责)使他永远幸福,而他自 己却没有必要成为一个比较善的人;或者,如果这在他看来不可 能的话,认为上帝能够把他变成为比较善的人,而他自己则除了 祈求之外,没有必要为此再做什么。”[Kat:《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宋教》, Stuttgart,65-66页]在康德看来,祈求只不过是纯粹的愿望,祈求者 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如果单凭愿望就可以成为一个善人,则每 一个人就都是善人了。这样的宗教观念,实际上放弃了个人在修 德方而的主观努力。基督教祚为一种道德的宗教,其原理却是: “每一个人都必须尽其力所能及,以便成为一个比较善的人;只 有当他为了成为一个比较善的人面不埋没自已天赋的才能,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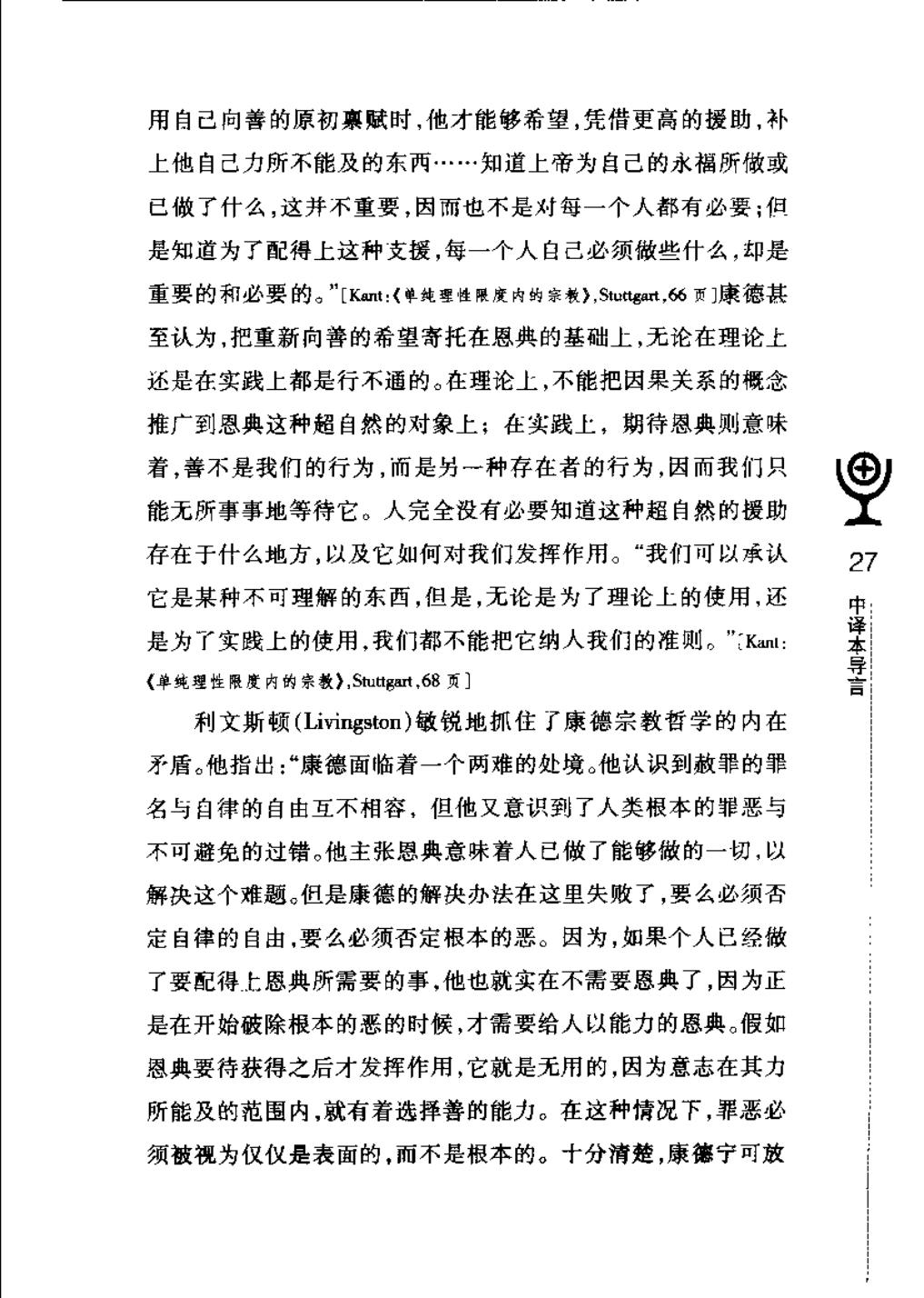
用自己向善的原初禀赋时,他才能够希望,凭猎更高的援助,补 上他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东两…知道上帝为自己的永福所做或 已做了什么,这并不重要,因而也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有必要:何 是知道为了配得上这种支援,每一个人自己必须做些什么,却是 重要的和必要的。”[Kant:《单纯零性限度内的宗栽》,Sttgart,.66页]康德甚 至认为,把重新向善的希望寄托在恩典的基础上,无论在理论上 还是在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在理论上,不能把因果关系的概念 推广到恩典这种超自然的对象上;在实践上,期待恩典则意味 着,善不是我们的行为,而是另一种存在者的行为,因而我们只 能无所事事地等待它。人完全没有必要知道这种超自然的援助 存在于什么地方,以及它如何对我们发挥作用。“我们可以承认 27 它是某种不可理解的东西,但是,无论是为了理论上的使用,还 是为了实践上的使用,我们都不能把它纳人我们的准则。”K: 《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崇教》,Stuttgart,68页] 译本导言 利文斯顿(Livingston)敏锐地抓住了康德宗教哲学的内在 矛盾。他指出:“康德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处境。他认识到赦罪的罪 名与自律的自由互不相容,但他又意识到了人类根本的罪恶与 不可避免的过错。他主张恩典意味着人已做了能够做的一切,以 解决这个难题。但是康德的解决办法在这里失败了,要么必须否 定自律的自由,要么必须否定根本的恶。因为,如果个人已经做 了要配得上恩典所需要的事,他也就实在不需要恩典了,因为正 是在开始破除根本的恶的时候,才需要给人以能力的恩典。假如 恩典要待获得之后才发挥作用,它就是无用的,因为意志在其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就有着选择善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罪恶必 须被视为仅仪是表面的,而不是根本的。十分清楚,康德宁可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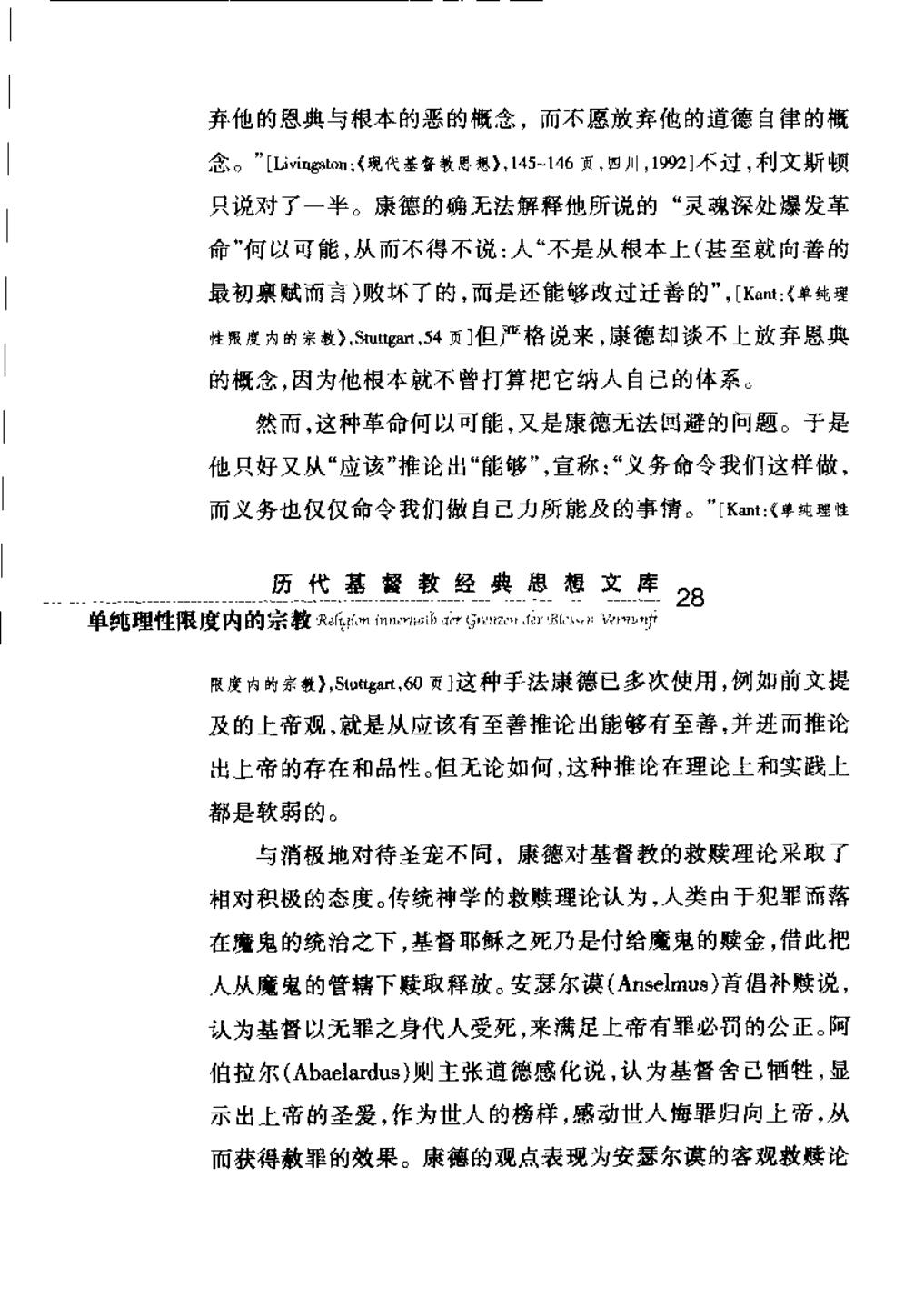
弃他的恩典与根本的恶的概念,而不愿放弃他的道德自律的概 念。”[Livingston:《魂代萎督教思想》,145-146页,四川,1992]不过,利文斯顿 只说对了一半。康德的确无法解释他所说的“灵魂深处爆发革 命”何以可能,从而不得不说:人“不是从根本上(甚至就向善的 最初禀赋而言)败坏了的,而是还能够改过迁善的”,[Kat:《单纯理 性限度为的宗教).Stuttgart,54页]但严格说来,康德却谈不上放弃恩典 的概念,因为他根本就不曾打算把它纳人自已的体系。 然而,这种革命何以可能,又是康德无法何避的问题。于是 他只好又从“应该”推论出“能够”,宣称:“义务命令我们这样做, 而义务也仅仅命令我们椒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Kamt:《单纯理性 历代基餐教经典思框文库 28 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Religiom in市r Grzo fir Blsa:u中 限度内的宗数》,Stutigart,.60页]这种手法康德已多次使用,例如前文提 及的上帝观,就是从应该有至善推论出能够有至善,并进而推论 出上帝的存在和品性。但无论如何,这种推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 都是软弱的。 与消极地对待圣宠不同,康德对基督教的救赎理论采取了 相对积极的态度。传统神学的救赎理论认为,人类由于犯罪而落 在魔鬼的统治之下,基督耶酥之死乃是付给魔鬼的赎金,借此把 人从魔鬼的管辖下赎取释放。安瑟尔谟(Anselmus)首得补赎说, 认为基督以无罪之身代人受死,来满足上帝有罪必罚的公正。阿 伯拉尔(Abaelardus))则主张道德感化说,认为基督舍已牺牲,显 示出上帝的圣爱,作为世人的榜样,感动世人悔罪归向上帝,从 而获得赦罪的效果。康德的观点表现为安瑟尔谟的客观救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