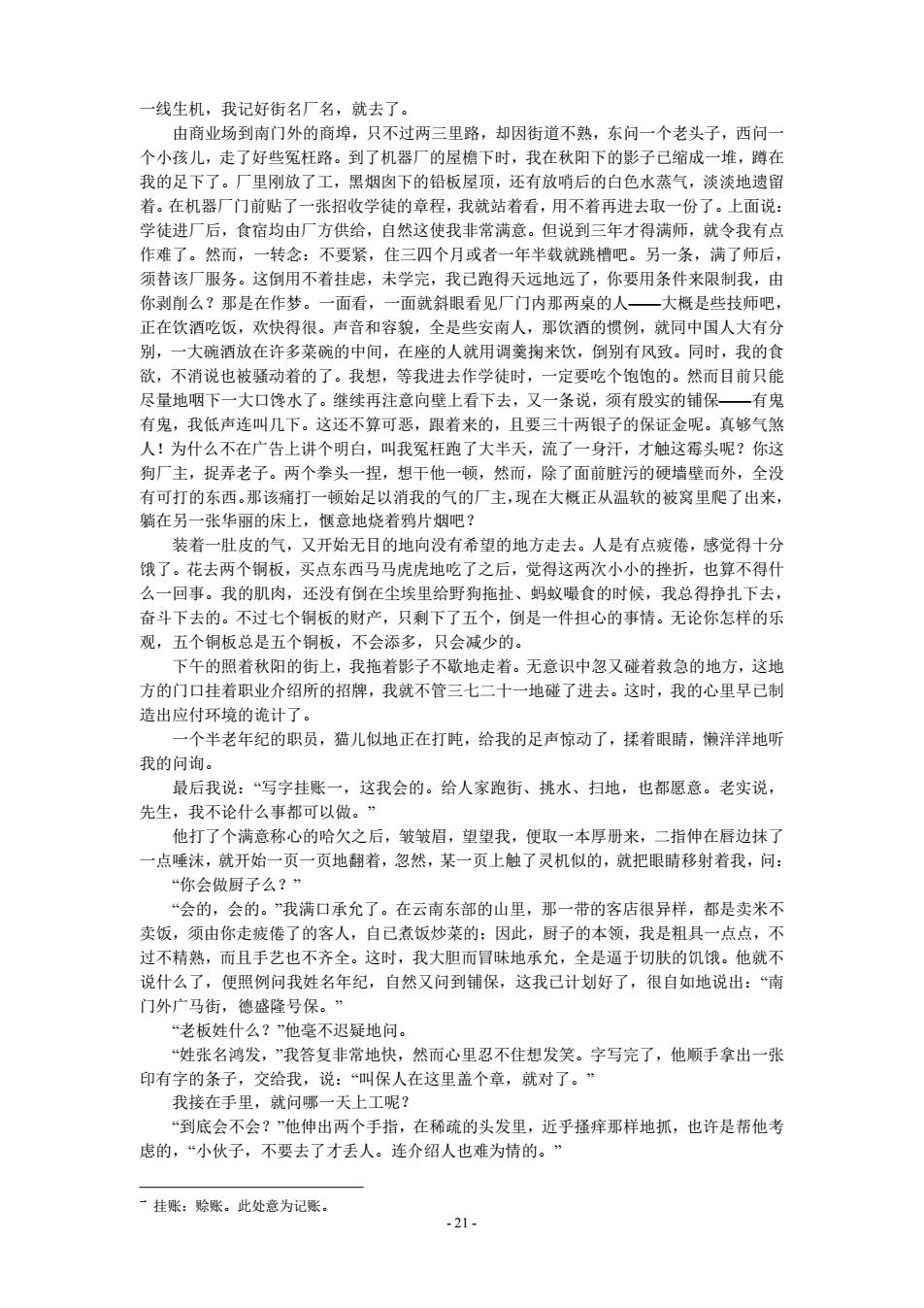
一线生机,我记好街名厂名,就去了。 由商业场到南门外的商埠,只不过两三里路,却因街道不熟,东问一个老头子,西问一 个小孩儿,走了好些冤枉路。到了机器厂的屋檐下时,我在秋阳下的影子己缩成一堆,蹲在 我的足下了。厂里刚放了工,黑烟囱下的铅板屋顶,还有放哨后的白色水蒸气,淡淡地遗留 着。在机器厂门前贴了一张招收学徒的章程,我就站着看,用不着再进去取一份了。上面说: 学徒进厂后,食宿均由厂方供给,自然这使我非常满意。但说到三年才得满师,就令我有点 作难了。然而,一转念:不要紧,住三四个月或者一年半载就跳槽吧。另一条,满了师后, 须替该厂服务。这倒用不着挂虑,未学完,我已跑得天远地远了,你要用条件来限制我,由 你剥削么?那是在作梦。一面看,一面就斜眼看见厂门内那两桌的人一大概是些技师吧, 正在饮酒吃饭,欢快得很。声音和容貌,全是些安南人,那饮酒的惯例,就同中国人大有分 别,一大碗酒放在许多菜碗的中间,在座的人就用调羹掬来饮,倒别有风致。同时,我的食 欲,不消说也被骚动着的了。我想,等我进去作学徒时,一定要吃个饱饱的。然而目前只能 尽量地咽下一大口馋水了。继续再注意向壁上看下去,又一条说,须有殷实的铺保一有鬼 有鬼,我低声连叫几下。这还不算可恶,跟着来的,且要三十两银子的保证金呢。真够气煞 人!为什么不在广告上讲个明白,叫我冤枉跑了大半天,流了一身汗,才触这霉头呢?你这 狗厂主,捉弄老子。两个拳头一捏,想干他一顿,然而,除了面前脏污的硬墙壁而外,全没 有可打的东西。那该痛打一顿始足以消我的气的厂主,现在大概正从温软的被窝里爬了出来, 躺在另一张华丽的床上,惬意地烧着鸦片烟吧? 装着一肚皮的气,又开始无目的地向没有希望的地方走去。人是有点疲倦,感觉得十分 饿了。花去两个铜板,买点东西马马虎虎地吃了之后,觉得这两次小小的挫折,也算不得什 么一回事。我的肌肉,还没有倒在尘埃里给野狗拖扯、蚂蚁嘬食的时候,我总得挣扎下去, 奋斗下去的。不过七个铜板的财产,只剩下了五个,倒是一件担心的事情。无论你怎样的乐 观,五个铜板总是五个铜板,不会添多,只会减少的。 下午的照着秋阳的街上,我拖着影子不歇地走着。无意识中忽又碰着救急的地方,这地 方的门口挂着职业介绍所的招牌,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碰了进去。这时,我的心里早己制 造出应付环境的诡计了。 一个半老年纪的职员,猫儿似地正在打盹,给我的足声惊动了,揉着眼晴,懒洋洋地听 我的问询。 最后我说:“写字挂账一,这我会的。给人家跑街、挑水、扫地,也都愿意。老实说, 先生,我不论什么事都可以做。” 他打了个满意称心的哈欠之后,皱皱眉,望望我,便取一本厚册来,二指伸在唇边抹了 一点唾沫,就开始一页一页地翻着,忽然,某一页上触了灵机似的,就把眼睛移射着我,问: “你会做厨子么?” “会的,会的。”我满口承允了。在云南东部的山里,那一带的客店很异样,都是卖米不 卖饭,须由你走疲倦了的客人,自己煮饭炒菜的:因此,厨子的本领,我是粗具一点点,不 过不精熟,而且手艺也不齐全。这时,我大胆而冒味地承允,全是逼于切肤的饥饿。他就不 说什么了,便照例问我姓名年纪,自然又问到铺保,这我已计划好了,很自如地说出:“南 门外广马街,德盛隆号保。” “老板姓什么?”他毫不迟疑地问。 “姓张名鸿发,”我答复非常地快,然而心里忍不住想发笑。字写完了,他顺手拿出一张 印有字的条子,交给我,说:“叫保人在这里盖个章,就对了。” 我接在手里,就问哪一天上工呢? “到底会不会?”他伸出两个手指,在稀疏的头发里,近乎搔痒那样地抓,也许是帮他考 虑的,“小伙子,不要去了才丢人。连介绍人也难为情的。” 一挂账:赊账。此处意为记账。 -21-
- 21 - 一线生机,我记好街名厂名,就去了。 由商业场到南门外的商埠,只不过两三里路,却因街道不熟,东问一个老头子,西问一 个小孩儿,走了好些冤枉路。到了机器厂的屋檐下时,我在秋阳下的影子已缩成一堆,蹲在 我的足下了。厂里刚放了工,黑烟囱下的铅板屋顶,还有放哨后的白色水蒸气,淡淡地遗留 着。在机器厂门前贴了一张招收学徒的章程,我就站着看,用不着再进去取一份了。上面说: 学徒进厂后,食宿均由厂方供给,自然这使我非常满意。但说到三年才得满师,就令我有点 作难了。然而,一转念:不要紧,住三四个月或者一年半载就跳槽吧。另一条,满了师后, 须替该厂服务。这倒用不着挂虑,未学完,我已跑得天远地远了,你要用条件来限制我,由 你剥削么?那是在作梦。一面看,一面就斜眼看见厂门内那两桌的人——大概是些技师吧, 正在饮酒吃饭,欢快得很。声音和容貌,全是些安南人,那饮酒的惯例,就同中国人大有分 别,一大碗酒放在许多菜碗的中间,在座的人就用调羹掬来饮,倒别有风致。同时,我的食 欲,不消说也被骚动着的了。我想,等我进去作学徒时,一定要吃个饱饱的。然而目前只能 尽量地咽下一大口馋水了。继续再注意向壁上看下去,又一条说,须有殷实的铺保——有鬼 有鬼,我低声连叫几下。这还不算可恶,跟着来的,且要三十两银子的保证金呢。真够气煞 人!为什么不在广告上讲个明白,叫我冤枉跑了大半天,流了一身汗,才触这霉头呢?你这 狗厂主,捉弄老子。两个拳头一捏,想干他一顿,然而,除了面前脏污的硬墙壁而外,全没 有可打的东西。那该痛打一顿始足以消我的气的厂主,现在大概正从温软的被窝里爬了出来, 躺在另一张华丽的床上,惬意地烧着鸦片烟吧? 装着一肚皮的气,又开始无目的地向没有希望的地方走去。人是有点疲倦,感觉得十分 饿了。花去两个铜板,买点东西马马虎虎地吃了之后,觉得这两次小小的挫折,也算不得什 么一回事。我的肌肉,还没有倒在尘埃里给野狗拖扯、蚂蚁嘬食的时候,我总得挣扎下去, 奋斗下去的。不过七个铜板的财产,只剩下了五个,倒是一件担心的事情。无论你怎样的乐 观,五个铜板总是五个铜板,不会添多,只会减少的。 下午的照着秋阳的街上,我拖着影子不歇地走着。无意识中忽又碰着救急的地方,这地 方的门口挂着职业介绍所的招牌,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碰了进去。这时,我的心里早已制 造出应付环境的诡计了。 一个半老年纪的职员,猫儿似地正在打盹,给我的足声惊动了,揉着眼睛,懒洋洋地听 我的问询。 最后我说:“写字挂账一,这我会的。给人家跑街、挑水、扫地,也都愿意。老实说, 先生,我不论什么事都可以做。” 他打了个满意称心的哈欠之后,皱皱眉,望望我,便取一本厚册来,二指伸在唇边抹了 一点唾沫,就开始一页一页地翻着,忽然,某一页上触了灵机似的,就把眼睛移射着我,问: “你会做厨子么?” “会的,会的。”我满口承允了。在云南东部的山里,那一带的客店很异样,都是卖米不 卖饭,须由你走疲倦了的客人,自已煮饭炒菜的;因此,厨子的本领,我是粗具一点点,不 过不精熟,而且手艺也不齐全。这时,我大胆而冒昧地承允,全是逼于切肤的饥饿。他就不 说什么了,便照例问我姓名年纪,自然又问到铺保,这我已计划好了,很自如地说出:“南 门外广马街,德盛隆号保。” “老板姓什么?”他毫不迟疑地问。 “姓张名鸿发,”我答复非常地快,然而心里忍不住想发笑。字写完了,他顺手拿出一张 印有字的条子,交给我,说:“叫保人在这里盖个章,就对了。” 我接在手里,就问哪一天上工呢? “到底会不会?”他伸出两个手指,在稀疏的头发里,近乎搔痒那样地抓,也许是帮他考 虑的,“小伙子,不要去了才丢人。连介绍人也难为情的。” 一 挂账:赊账。此处意为记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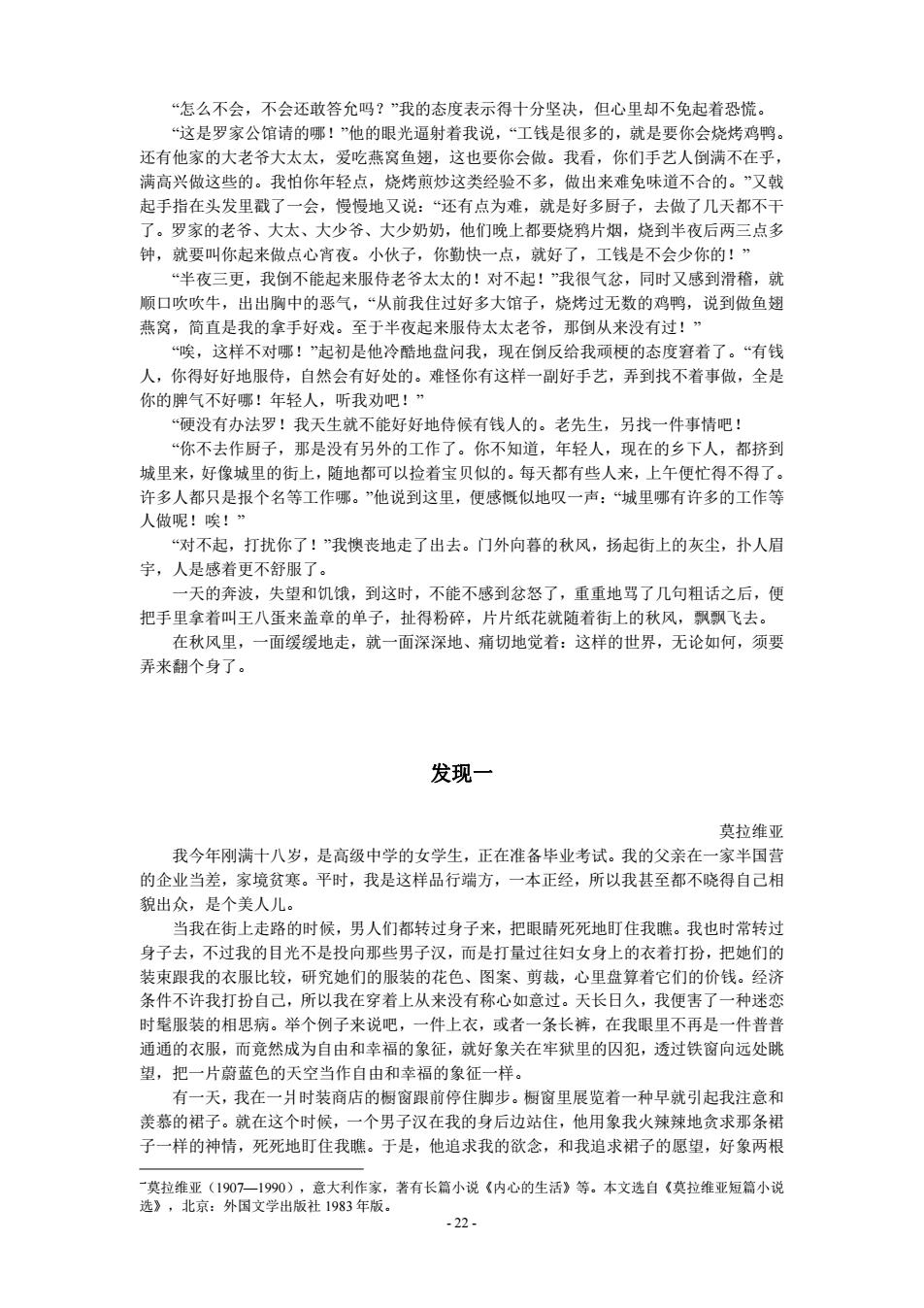
“怎么不会,不会还敢答允吗?”我的态度表示得十分坚决,但心里却不免起着恐慌。 “这是罗家公馆请的哪!”他的眼光逼射着我说,“工钱是很多的,就是要你会烧烤鸡鸭。 还有他家的大老爷大太太,爱吃燕窝鱼翅,这也要你会做。我看,你们手艺人倒满不在乎, 满高兴做这些的。我怕你年轻点,烧烤煎炒这类经验不多,做出来难免味道不合的。”又戟 起手指在头发里戳了一会,慢慢地又说:“还有点为难,就是好多厨子,去做了几天都不干 了。罗家的老爷、大太、大少爷、大少奶奶,他们晚上都要烧鸦片烟,烧到半夜后两三点多 钟,就要叫你起来做点心宵夜。小伙子,你勤快一点,就好了,工钱是不会少你的!” “半夜三更,我倒不能起来服侍老爷太太的!对不起!”我很气忿,同时又感到滑稽,就 顺口吹吹牛,出出胸中的恶气,“从前我住过好多大馆子,烧烤过无数的鸡鸭,说到做鱼翅 燕窝,简直是我的拿手好戏。至于半夜起来服侍太太老爷,那倒从来没有过!” “唉,这样不对哪!”起初是他冷酷地盘问我,现在倒反给我顽梗的态度窘着了。“有钱 人,你得好好地服侍,自然会有好处的。难怪你有这样一副好手艺,弄到找不着事做,全是 你的脾气不好哪!年轻人,听我劝吧!” “硬没有办法罗!我天生就不能好好地侍候有钱人的。老先生,另找一件事情吧! “你不去作厨子,那是没有另外的工作了。你不知道,年轻人,现在的乡下人,都挤到 城里来,好像城里的街上,随地都可以捡着宝贝似的。每天都有些人来,上午便忙得不得了。 许多人都只是报个名等工作哪。”他说到这里,便感慨似地叹一声:“城里哪有许多的工作等 人做呢!唉!” “对不起,打扰你了!”我懊丧地走了出去。门外向暮的秋风,扬起街上的灰尘,扑人眉 宇,人是感着更不舒服了。 一天的奔波,失望和饥饿,到这时,不能不感到忿怒了,重重地骂了几句粗话之后,便 把手里拿着叫王八蛋来盖章的单子,扯得粉碎,片片纸花就随着街上的秋风,飘飘飞去。 在秋风里,一面缓缓地走,就一面深深地、痛切地觉着:这样的世界,无论如何,须要 弄来翻个身了。 发现一 莫拉维亚 我今年刚满十八岁,是高级中学的女学生,正在准备毕业考试。我的父亲在一家半国营 的企业当差,家境贫寒。平时,我是这样品行端方,一本正经,所以我甚至都不晓得自己相 貌出众,是个美人儿。 当我在街上走路的时候,男人们都转过身子来,把眼晴死死地盯住我瞧。我也时常转过 身子去,不过我的目光不是投向那些男子汉,而是打量过往妇女身上的衣着打扮,把她们的 装束跟我的衣服比较,研究她们的服装的花色、图案、剪裁,心里盘算着它们的价钱。经济 条件不许我打扮自己,所以我在穿着上从来没有称心如意过。天长日久,我便害了一种迷恋 时髦服装的相思病。举个例子来说吧,一件上衣,或者一条长裤,在我眼里不再是一件普普 通通的衣服,而竞然成为自由和幸福的象征,就好象关在牢狱里的囚犯,透过铁窗向远处跳 望,把一片蔚蓝色的天空当作自由和幸福的象征一样。 有一天,我在一爿时装商店的橱窗跟前停住脚步。橱窗里展览着一种早就引起我注意和 羡慕的裙子。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男子汉在我的身后边站住,他用象我火辣辣地贪求那条裙 子一样的神情,死死地盯住我瞧。于是,他追求我的欲念,和我追求裙子的愿望,好象两根 莫拉维亚(1907一1990),意大利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内心的生活》等。本文选自《莫拉维亚短篇小说 选》,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2-
- 22 - “怎么不会,不会还敢答允吗?”我的态度表示得十分坚决,但心里却不免起着恐慌。 “这是罗家公馆请的哪!”他的眼光逼射着我说,“工钱是很多的,就是要你会烧烤鸡鸭。 还有他家的大老爷大太太,爱吃燕窝鱼翅,这也要你会做。我看,你们手艺人倒满不在乎, 满高兴做这些的。我怕你年轻点,烧烤煎炒这类经验不多,做出来难免味道不合的。”又戟 起手指在头发里戳了一会,慢慢地又说:“还有点为难,就是好多厨子,去做了几天都不干 了。罗家的老爷、大太、大少爷、大少奶奶,他们晚上都要烧鸦片烟,烧到半夜后两三点多 钟,就要叫你起来做点心宵夜。小伙子,你勤快一点,就好了,工钱是不会少你的!” “半夜三更,我倒不能起来服侍老爷太太的!对不起!”我很气忿,同时又感到滑稽,就 顺口吹吹牛,出出胸中的恶气,“从前我住过好多大馆子,烧烤过无数的鸡鸭,说到做鱼翅 燕窝,简直是我的拿手好戏。至于半夜起来服侍太太老爷,那倒从来没有过!” “唉,这样不对哪!”起初是他冷酷地盘问我,现在倒反给我顽梗的态度窘着了。“有钱 人,你得好好地服侍,自然会有好处的。难怪你有这样一副好手艺,弄到找不着事做,全是 你的脾气不好哪!年轻人,听我劝吧!” “硬没有办法罗!我天生就不能好好地侍候有钱人的。老先生,另找一件事情吧! “你不去作厨子,那是没有另外的工作了。你不知道,年轻人,现在的乡下人,都挤到 城里来,好像城里的街上,随地都可以捡着宝贝似的。每天都有些人来,上午便忙得不得了。 许多人都只是报个名等工作哪。”他说到这里,便感慨似地叹一声:“城里哪有许多的工作等 人做呢!唉!” “对不起,打扰你了!”我懊丧地走了出去。门外向暮的秋风,扬起街上的灰尘,扑人眉 宇,人是感着更不舒服了。 一天的奔波,失望和饥饿,到这时,不能不感到忿怒了,重重地骂了几句粗话之后,便 把手里拿着叫王八蛋来盖章的单子,扯得粉碎,片片纸花就随着街上的秋风,飘飘飞去。 在秋风里,一面缓缓地走,就一面深深地、痛切地觉着:这样的世界,无论如何,须要 弄来翻个身了。 发现一 莫拉维亚 我今年刚满十八岁,是高级中学的女学生,正在准备毕业考试。我的父亲在一家半国营 的企业当差,家境贫寒。平时,我是这样品行端方,一本正经,所以我甚至都不晓得自己相 貌出众,是个美人儿。 当我在街上走路的时候,男人们都转过身子来,把眼睛死死地盯住我瞧。我也时常转过 身子去,不过我的目光不是投向那些男子汉,而是打量过往妇女身上的衣着打扮,把她们的 装束跟我的衣服比较,研究她们的服装的花色、图案、剪裁,心里盘算着它们的价钱。经济 条件不许我打扮自己,所以我在穿着上从来没有称心如意过。天长日久,我便害了一种迷恋 时髦服装的相思病。举个例子来说吧,一件上衣,或者一条长裤,在我眼里不再是一件普普 通通的衣服,而竟然成为自由和幸福的象征,就好象关在牢狱里的囚犯,透过铁窗向远处眺 望,把一片蔚蓝色的天空当作自由和幸福的象征一样。 有一天,我在一爿时装商店的橱窗跟前停住脚步。橱窗里展览着一种早就引起我注意和 羡慕的裙子。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男子汉在我的身后边站住,他用象我火辣辣地贪求那条裙 子一样的神情,死死地盯住我瞧。于是,他追求我的欲念,和我追求裙子的愿望,好象两根 一莫拉维亚(1907—1990),意大利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内心的生活》等。本文选自《莫拉维亚短篇小说 选》,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裸露的电线发生接触,突然走电了,刹那间迸发的火花照亮了我的思路。突然间,一个连我 自己都大吃一惊的念头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我喜欢那条裙子,他喜欢我。那末,他应当 把我买下,这样我随之也就能够买下这条裙子。” 我正这么暗自思付,那男子贴近我的身边,不动声色地对我说: “真漂亮!一不,是那条裙子真漂亮!如果你愿意,我们到里面去,我把它买下来送 给你。” 两个站在那里的行人听到这番话,扭过身子来瞧我们。我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站在我 面前的是一个年轻的男子,身躯有点儿肥胖臃肿,神情矫揉造作,但从容不迫。我不加思索 地回答他,嗓门扯得很高,故意让站在那里的行人能够听得见: “一言为定:咱们进去吧。” 我们走进了时装店,我向女售货员指点了那条裙子。女售货员把裙子放在盒子里,细心 包扎好:他就象一个善良的父亲或者体贴的丈夫,到交款处付了钱。他办公的地方就在时装 店附近。在电梯里,后来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的举止行动仍然象一个邂逅相遇,多少有点儿 漫不经心的老朋友。我把装裙子的盆子放在写字桌上,毫不迟疑地开始脱衣服,他却显出一 种不可捉摸的神情,从容不迫地走来走去,忙着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末了,他把一条红绿格 子的苏格兰毛毯扔到黑皮沙发上,朝我扑过来,一把搂住了我。后来,隔壁房间里传来一连 串急促的电话铃声,他顾不得穿上衣服,赤身裸体急急忙忙走出去,把我独个儿撇在办公室 里。 我感到一阵激动的,同时又是惶乱的,几乎是不可置信的战栗,通常只是作出了重大发 现的人才能体味到这种感觉。请你们不要发笑,也不要挖苦我:我从来不曾想到,我方年满 十八岁,天真未泯,尚未走完以家庭和学校为全部内容的人生道路,却发现了一件极其古老、 普通,而又众所周知的东西一卖淫。是的,我发现,我掌握了某种东西,它对于我来说, 纵然是毫无价值的,而男人们却甘心情愿为它支付应有的代价。不过,我尤其注意到,这种 行为—也无妨把它称作买卖—的全过程,完全可以象履行合同似的平心静气地进行,因 此我可以绝对无忧无虑地从事这一活动。这个想法使我欣喜不己。我只穿了一件衬裙,情不 自禁地在房间里跳起舞来,嘴里象咏唱歌曲的叠句似地不断重复:“一切称心如意,一切称 心如意,果真如此吗?一一切称心如意?” 这时,我的主顾一他是我的裙子的买主?还是我身子的买主呢?或者,是这两者的买主? 一走了进来,他瞧见我这副兴高采烈的样子,不禁吃了一惊,莫名其妙。我向他解释,这 是身心愉快的表现,他信以为真。我穿好了衣服,好象两个老相识似的跟他热烈吻别,离开 了他。 你们不要问我,在我初次委身于这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之后,我是怎样行事的。你们只 要知道这样一点就够了:在约摸两年的时间里,我以这种方式或者那种方式,象第一次那样 直接了当地或者通过别人远非大公无私的牵线,我终于把我喜爱的时髦服饰统统都买到了 手。请注意,我这样行事只不过是为了我的装束打扮:除此以外,我仍然象以往那样生活, 在大学里勤奋而颇有收获地学习,在家庭里跟我的父母亲和三个兄弟和睦相处。顺便说,我 已经订了婚,我的未婚夫跟我在大学的同一个系念书。我很爱他,他也很爱我:不过我始终 没有放弃以原先的方式来获得那些时装。当然,如果我不再迷恋摩登服装了,我会停止卖淫 的。可是,好象我家庭里的妇女世世代代都是穿着破衣烂衫似的,时装仍然使我心醉神迷。 我所说的“一切都称心如意”持续了约摸两年的光景。后来,出乎我的意料,我发现,我 怀孕了。于是,我的未婚夫和我决定提前结婚,当初我们曾经同意把婚礼推迟到他的处境改 善的时候举行。眼看举行婚礼的日子临近了,我却迷恋上了市中心一家商店橱窗展出的一件 纯毛的,口袋挺大,金属钮扣的外衣。其实这是件挺普通的衣服,可是,象往常一样,我无 力把它弄到手,于是它成了我崇拜的偶像。我大白天想它,夜里做梦也想它。我忽然害怕起 来,如果我不把它弄到手,将来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肯定会在身上的某个部位或脸颊上打 上达件纯毛外衣的印记。我没有别的法子可想,只好决定重操卖淫旧业。 -23-
- 23 - 裸露的电线发生接触,突然走电了,刹那间迸发的火花照亮了我的思路。突然间,一个连我 自己都大吃一惊的念头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我喜欢那条裙子,他喜欢我。那末,他应当 把我买下,这样我随之也就能够买下这条裙子。” 我正这么暗自思付,那男子贴近我的身边,不动声色地对我说: “真漂亮!——不,是那条裙子真漂亮!如果你愿意,我们到里面去,我把它买下来送 给你。” 两个站在那里的行人听到这番话,扭过身子来瞧我们。我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站在我 面前的是一个年轻的男子,身躯有点儿肥胖臃肿,神情矫揉造作,但从容不迫。我不加思索 地回答他,嗓门扯得很高,故意让站在那里的行人能够听得见: “一言为定;咱们进去吧。” 我们走进了时装店,我向女售货员指点了那条裙子。女售货员把裙子放在盒子里,细心 包扎好;他就象一个善良的父亲或者体贴的丈夫,到交款处付了钱。他办公的地方就在时装 店附近。在电梯里,后来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的举止行动仍然象一个邂逅相遇,多少有点儿 漫不经心的老朋友。我把装裙子的盆子放在写字桌上,毫不迟疑地开始脱衣服,他却显出一 种不可捉摸的神情,从容不迫地走来走去,忙着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末了,他把一条红绿格 子的苏格兰毛毯扔到黑皮沙发上,朝我扑过来,一把搂住了我。后来,隔壁房间里传来一连 串急促的电话铃声,他顾不得穿上衣服,赤身裸体急急忙忙走出去,把我独个儿撇在办公室 里。 我感到一阵激动的,同时又是惶乱的,几乎是不可置信的战栗,通常只是作出了重大发 现的人才能体味到这种感觉。请你们不要发笑,也不要挖苦我:我从来不曾想到,我方年满 十八岁,天真未泯,尚未走完以家庭和学校为全部内容的人生道路,却发现了一件极其古老、 普通,而又众所周知的东西——卖淫。是的,我发现,我掌握了某种东西,它对于我来说, 纵然是毫无价值的,而男人们却甘心情愿为它支付应有的代价。不过,我尤其注意到,这种 行为——也无妨把它称作买卖——的全过程,完全可以象履行合同似的平心静气地进行,因 此我可以绝对无忧无虑地从事这一活动。这个想法使我欣喜不已。我只穿了一件衬裙,情不 自禁地在房间里跳起舞来,嘴里象咏唱歌曲的叠句似地不断重复:“一切称心如意,一切称 心如意,果真如此吗?——一切称心如意?” 这时,我的主顾——他是我的裙子的买主?还是我身子的买主呢?或者,是这两者的买主? ——走了进来,他瞧见我这副兴高采烈的样子,不禁吃了一惊,莫名其妙。我向他解释,这 是身心愉快的表现,他信以为真。我穿好了衣服,好象两个老相识似的跟他热烈吻别,离开 了他。 你们不要问我,在我初次委身于这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之后,我是怎样行事的。你们只 要知道这样一点就够了:在约摸两年的时间里,我以这种方式或者那种方式,象第一次那样 直接了当地或者通过别人远非大公无私的牵线,我终于把我喜爱的时髦服饰统统都买到了 手。请注意,我这样行事只不过是为了我的装束打扮;除此以外,我仍然象以往那样生活, 在大学里勤奋而颇有收获地学习,在家庭里跟我的父母亲和三个兄弟和睦相处。顺便说,我 已经订了婚,我的未婚夫跟我在大学的同一个系念书。我很爱他,他也很爱我;不过我始终 没有放弃以原先的方式来获得那些时装。当然,如果我不再迷恋摩登服装了,我会停止卖淫 的。可是,好象我家庭里的妇女世世代代都是穿着破衣烂衫似的,时装仍然使我心醉神迷。 我所说的“一切都称心如意”持续了约摸两年的光景。后来,出乎我的意料,我发现,我 怀孕了。于是,我的未婚夫和我决定提前结婚,当初我们曾经同意把婚礼推迟到他的处境改 善的时候举行。眼看举行婚礼的日子临近了,我却迷恋上了市中心一家商店橱窗展出的一件 纯毛的,口袋挺大,金属钮扣的外衣。其实这是件挺普通的衣服,可是,象往常一样,我无 力把它弄到手,于是它成了我崇拜的偶像。我大白天想它,夜里做梦也想它。我忽然害怕起 来,如果我不把它弄到手,将来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肯定会在身上的某个部位或脸颊上打 上达件纯毛外衣的印记。我没有别的法子可想,只好决定重操卖淫旧业

就在这当儿,一个通常被称作体面的问题一由于它们的暧味和微妙一开始折磨着 我。事情是这样:我已经向自己信誓旦旦地保证,结婚以后坚决不再卖淫。不过,买毛外衣 的钱我虽说可以在结婚“以前”挣到手,但这件衣服要等到结婚“以后”跟我的未婚夫到他的家 乡南方地区作蜜月旅行的时候,我才正式穿它。干么要赌咒发誓呢?归根到底,也说不出是 什么道理。或许,因为我觉得,一旦有了需要我操心的丈夫、孩子和家庭,追求时髦衣饰的 癖好便会一劳永逸地从我的脑子里消失了。那么,结婚以后,居然还穿上那件毛衣是不是违 背我的誓言呢?这个微妙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 有一天,我到首饰店去选购两只结婚戒指,那是为了我的未婚夫和我在教堂里举行婚礼 的时候交换用的。这爿小小的首饰店,大约是一个小家庭经营的,我走进去的时候,柜台里 站着一名中年妇女,还有一名跟我年纪相近的姑娘,相貌很象那个中年女子,看来是她的女 儿。 那姑娘脸上流露出很不耐烦的神色,正打开一个珠宝盒,给一个女顾客挑选:珠宝盒里 的黑天鹅绒上缀满了各色各样的珠宝:蓝宝石、红宝石、翠玉、钻石。我请那母亲拿几只结 婚戒指给我挑选,同时却又冷冷地瞟着那珠宝盒,我不由得暗暗盘算,我只要得到盒子中的 一枚宝石,哪怕是处理品,也足以立即解决现在令我苦恼的问题,甚至连其他诸如此类的麻 烦也就迎刃而解了。 你们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刹那间,我又一次感受到一阵激动的,同时又是其可名 状地慌乱的(几乎是不可置信的)战栗:两年以前,我出乎意料地揭开了明目张胆的、堕落 的卖淫的秘密时,就曾经体验过这种情绪。而这一次,我发现了另一样极其古老、普通而众 所周知的东西一盗窃:不过,对于我而言,它仍然散发着异常新奇诱人的色彩和气息。真 奇怪,在此以前我怎么会没有想到它呢?这么说来,最隐蔽的东西,恰恰是那些最引人注目, 甚至可以说是摆在鼻子尖底下的东西啰。 现在,女顾客什么也没有买,朝外面走去,那女儿送她到店门口。恰恰在这当儿,那母 亲转过身去,不晓得开一个什么抽屉。我敏捷地从首饰盒里拿了一枚带红宝石的戒指,把我 原先试戴在手指上的一枚毫无价值的结婚戒子脱下来,放到首饰盒里。我戴上了红宝石戒指, 又重新戴上手套。然后,我对母女俩说,我没有选到合适的戒指,便径自走了。 我走到大街上,立即折入一曲楼房的门廊里,脱下宝石戒指,把它放进贴肉的紧身衣里。 宝石戒指多少有点儿份量,从我的胸口直往下滑溜,滑到我的肚皮上,一宜滑到我的孩子将 来要从那里降临人世的地方才停住。我自信这一切都做得干净利落:于是我一面继续朝前走, 一向狂喜地不断重复:“一切称心如意,一切称心如意,果真如此吗?一一切称心如意?” 突然,我觉得我的一条胳膊猛地被人揪住了:我转过身来,是珠宝店里那上年纪的女人。 她的脸急得扭曲了,灰白的头发放风吹得乱蓬蓬的,气喘吁吁地对我说: “戒指,少了一枚戒指,红宝石戒指!” 我冷冷地不动声色,跟她一起回到珠宝店。走进店里,我摊开没有戴任何戒指的双手, 把我随身带的手提包里的东西一古脑儿倾倒在柜台上,扯高嗓门大声抗议。中年妇女心慌意 乱、气急败坏地不断重复: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首饰盒里这只戒指,是您方才拿去试戴的,这是一只便 宜戒指,宝石是假造的,首饰盒里本来没有,现在却放在原先那只红宝石戒指的位置上。” 女儿站在她身边,一声不吭,只是用那异样的、锐利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然后,终 于下了决心,对她母亲说: “我想跟这位小姐单独地谈谈。您愿意跟我到那边去吗?” 她向我做了个手势,我便随着她走进了珠宝店的后房。 她关上房门,然后很温柔地对我说: “我瞧见你拿了红宝石戒指。我把女顾客送到门口,转过身来,正好瞧见你伸手拿那只 宝石戒指。可我没有对妈妈说,我本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揭穿这件事的,是她发现了宝 石戒指不翼而飞了。” -24-
- 24 - 就在这当儿,一个通常被称作体面的问题——由于它们的暧昧和微妙——开始折磨着 我。事情是这样:我已经向自己信誓旦旦地保证,结婚以后坚决不再卖淫。不过,买毛外衣 的钱我虽说可以在结婚“以前”挣到手,但这件衣服要等到结婚“以后”跟我的未婚夫到他的家 乡南方地区作蜜月旅行的时候,我才正式穿它。干么要赌咒发誓呢?归根到底,也说不出是 什么道理。或许,因为我觉得,一旦有了需要我操心的丈夫、孩子和家庭,追求时髦衣饰的 癖好便会一劳永逸地从我的脑子里消失了。那么,结婚以后,居然还穿上那件毛衣是不是违 背我的誓言呢?这个微妙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 有一天,我到首饰店去选购两只结婚戒指,那是为了我的未婚夫和我在教堂里举行婚礼 的时候交换用的。这爿小小的首饰店,大约是一个小家庭经营的,我走进去的时候,柜台里 站着一名中年妇女,还有一名跟我年纪相近的姑娘,相貌很象那个中年女子,看来是她的女 儿。 那姑娘脸上流露出很不耐烦的神色,正打开一个珠宝盒,给一个女顾客挑选;珠宝盒里 的黑天鹅绒上缀满了各色各样的珠宝:蓝宝石、红宝石、翠玉、钻石。我请那母亲拿几只结 婚戒指给我挑选,同时却又冷冷地瞟着那珠宝盒,我不由得暗暗盘算,我只要得到盒子中的 一枚宝石,哪怕是处理品,也足以立即解决现在令我苦恼的问题,甚至连其他诸如此类的麻 烦也就迎刃而解了。 你们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刹那间,我又一次感受到一阵激动的,同时又是其可名 状地慌乱的(几乎是不可置信的)战栗;两年以前,我出乎意料地揭开了明目张胆的、堕落 的卖淫的秘密时,就曾经体验过这种情绪。而这一次,我发现了另一样极其古老、普通而众 所周知的东西——盗窃;不过,对于我而言,它仍然散发着异常新奇诱人的色彩和气息。真 奇怪,在此以前我怎么会没有想到它呢?这么说来,最隐蔽的东西,恰恰是那些最引人注目, 甚至可以说是摆在鼻子尖底下的东西啰。 现在,女顾客什么也没有买,朝外面走去,那女儿送她到店门口。恰恰在这当儿,那母 亲转过身去,不晓得开一个什么抽屉。我敏捷地从首饰盒里拿了一枚带红宝石的戒指,把我 原先试戴在手指上的一枚毫无价值的结婚戒子脱下来,放到首饰盒里。我戴上了红宝石戒指, 又重新戴上手套。然后,我对母女俩说,我没有选到合适的戒指,便径自走了。 我走到大街上,立即折入一曲楼房的门廊里,脱下宝石戒指,把它放进贴肉的紧身衣里。 宝石戒指多少有点儿份量,从我的胸口直往下滑溜,滑到我的肚皮上,一宜滑到我的孩子将 来要从那里降临人世的地方才停住。我自信这一切都做得干净利落;于是我一面继续朝前走, 一向狂喜地不断重复:“一切称心如意,一切称心如意,果真如此吗?——一切称心如意?” 突然,我觉得我的一条胳膊猛地被人揪住了;我转过身来,是珠宝店里那上年纪的女人。 她的脸急得扭曲了,灰白的头发放风吹得乱蓬蓬的,气喘吁吁地对我说: “戒指,少了一枚戒指,红宝石戒指!” 我冷冷地不动声色,跟她一起回到珠宝店。走进店里,我摊开没有戴任何戒指的双手, 把我随身带的手提包里的东西一古脑儿倾倒在柜台上,扯高嗓门大声抗议。中年妇女心慌意 乱、气急败坏地不断重复: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首饰盒里这只戒指,是您方才拿去试戴的,这是一只便 宜戒指,宝石是假造的,首饰盒里本来没有,现在却放在原先那只红宝石戒指的位置上。” 女儿站在她身边,一声不吭,只是用那异样的、锐利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然后,终 于下了决心,对她母亲说: “我想跟这位小姐单独地谈谈。您愿意跟我到那边去吗?” 她向我做了个手势,我便随着她走进了珠宝店的后房。 她关上房门,然后很温柔地对我说: “我瞧见你拿了红宝石戒指。我把女顾客送到门口,转过身来,正好瞧见你伸手拿那只 宝石戒指。可我没有对妈妈说,我本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揭穿这件事的,是她发现了宝 石戒指不翼而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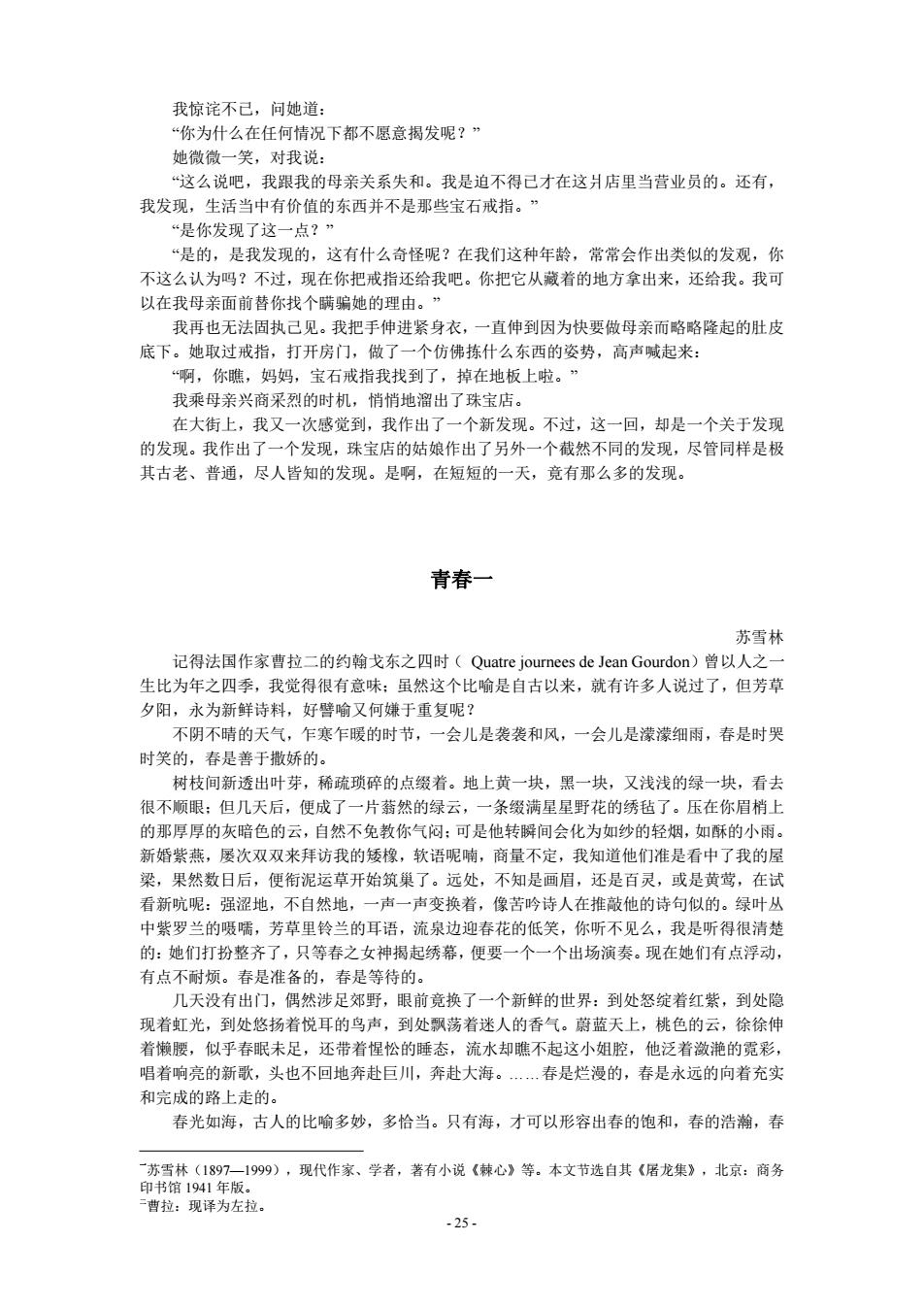
我惊诧不己,问她道: “你为什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揭发呢?” 她微微一笑,对我说: “这么说吧,我跟我的母亲关系失和。我是迫不得已才在这H店里当营业员的。还有, 我发现,生活当中有价值的东西并不是那些宝石戒指。” “是你发现了这一点?” “是的,是我发现的,这有什么奇怪呢?在我们这种年龄,常常会作出类似的发观,你 不这么认为吗?不过,现在你把戒指还给我吧。你把它从藏着的地方拿出来,还给我。我可 以在我母亲面前替你找个瞒骗她的理由。” 我再也无法固执己见。我把手伸进紧身衣,一直伸到因为快要做母亲而略略隆起的肚皮 底下。她取过戒指,打开房门,做了一个仿佛拣什么东西的姿势,高声喊起来: “啊,你瞧,妈妈,宝石戒指我找到了,掉在地板上啦。” 我乘母亲兴商采烈的时机,悄悄地溜出了珠宝店。 在大街上,我又一次感觉到,我作出了一个新发现。不过,这一回,却是一个关于发现 的发现。我作出了一个发现,珠宝店的姑娘作出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发现,尽管同样是极 其古老、普通,尽人皆知的发现。是啊,在短短的一天,竞有那么多的发现。 青春一 苏雪林 记得法国作家曹拉二的约翰戈东之四时(Quatre journees de Jean Gourdon)曾以人之一 生比为年之四季,我觉得很有意味:虽然这个比喻是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人说过了,但芳草 夕阳,永为新鲜诗料,好譬喻又何嫌于重复呢? 不阴不晴的天气,乍寒乍暖的时节,一会儿是袭袭和风,一会儿是濛濛细雨,春是时哭 时笑的,春是善于撒娇的。 树枝间新透出叶芽,稀疏琐碎的点缀着。地上黄一块,黑一块,又浅浅的绿一块,看去 很不顺眼:但几天后,便成了一片蓊然的绿云,一条缀满星星野花的绣毡了。压在你眉梢上 的那厚厚的灰暗色的云,自然不免教你气闷:可是他转瞬间会化为如纱的轻烟,如酥的小雨。 新婚紫燕,屡次双双来拜访我的矮橡,软语呢喃,商量不定,我知道他们准是看中了我的屋 梁,果然数日后,便衔泥运草开始筑巢了。远处,不知是画眉,还是百灵,或是黄莺,在试 看新吭呢:强涩地,不自然地,一声一声变换着,像苦吟诗人在推敲他的诗句似的。绿叶丛 中紫罗兰的嗫嚅,芳草里铃兰的耳语,流泉边迎春花的低笑,你听不见么,我是听得很清楚 的:她们打扮整齐了,只等春之女神揭起绣幕,便要一个一个出场演奏。现在她们有点浮动, 有点不耐烦。春是准备的,春是等待的。 几天没有出门,偶然涉足郊野,眼前竞换了一个新鲜的世界:到处怒绽着红紫,到处隐 现着虹光,到处悠扬着悦耳的鸟声,到处飘荡着迷人的香气。蔚蓝天上,桃色的云,徐徐伸 着懒腰,似乎春眠未足,还带着惺忪的睡态,流水却瞧不起这小姐腔,他泛着潋滟的霓彩, 唱着响亮的新歌,头也不回地奔赴巨川,奔赴大海。.春是烂漫的,春是永远的向着充实 和完成的路上走的。 春光如海,古人的比喻多妙,多恰当。只有海,才可以形容出春的饱和,春的浩瀚,春 苏雪林(1897一1999),现代作家、学者,著有小说《棘心》等。本文节选自其《屠龙集》,北京:商务 印书馆1941年版。 曹拉:现译为左拉。 -25-
- 25 - 我惊诧不已,问她道: “你为什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揭发呢?” 她微微一笑,对我说: “这么说吧,我跟我的母亲关系失和。我是迫不得已才在这爿店里当营业员的。还有, 我发现,生活当中有价值的东西并不是那些宝石戒指。” “是你发现了这一点?” “是的,是我发现的,这有什么奇怪呢?在我们这种年龄,常常会作出类似的发观,你 不这么认为吗?不过,现在你把戒指还给我吧。你把它从藏着的地方拿出来,还给我。我可 以在我母亲面前替你找个瞒骗她的理由。” 我再也无法固执己见。我把手伸进紧身衣,一直伸到因为快要做母亲而略略隆起的肚皮 底下。她取过戒指,打开房门,做了一个仿佛拣什么东西的姿势,高声喊起来: “啊,你瞧,妈妈,宝石戒指我找到了,掉在地板上啦。” 我乘母亲兴商采烈的时机,悄悄地溜出了珠宝店。 在大街上,我又一次感觉到,我作出了一个新发现。不过,这一回,却是一个关于发现 的发现。我作出了一个发现,珠宝店的姑娘作出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发现,尽管同样是极 其古老、普通,尽人皆知的发现。是啊,在短短的一天,竟有那么多的发现。 青春一 苏雪林 记得法国作家曹拉二的约翰戈东之四时( Quatre journees de Jean Gourdon)曾以人之一 生比为年之四季,我觉得很有意味;虽然这个比喻是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人说过了,但芳草 夕阳,永为新鲜诗料,好譬喻又何嫌于重复呢? 不阴不晴的天气,乍寒乍暖的时节,一会儿是袭袭和风,一会儿是濛濛细雨,春是时哭 时笑的,春是善于撒娇的。 树枝间新透出叶芽,稀疏琐碎的点缀着。地上黄一块,黑一块,又浅浅的绿一块,看去 很不顺眼;但几天后,便成了一片蓊然的绿云,一条缀满星星野花的绣毡了。压在你眉梢上 的那厚厚的灰暗色的云,自然不免教你气闷;可是他转瞬间会化为如纱的轻烟,如酥的小雨。 新婚紫燕,屡次双双来拜访我的矮橡,软语呢喃,商量不定,我知道他们准是看中了我的屋 梁,果然数日后,便衔泥运草开始筑巢了。远处,不知是画眉,还是百灵,或是黄莺,在试 看新吭呢:强涩地,不自然地,一声一声变换着,像苦吟诗人在推敲他的诗句似的。绿叶丛 中紫罗兰的嗫嚅,芳草里铃兰的耳语,流泉边迎春花的低笑,你听不见么,我是听得很清楚 的:她们打扮整齐了,只等春之女神揭起绣幕,便要一个一个出场演奏。现在她们有点浮动, 有点不耐烦。春是准备的,春是等待的。 几天没有出门,偶然涉足郊野,眼前竟换了一个新鲜的世界:到处怒绽着红紫,到处隐 现着虹光,到处悠扬着悦耳的鸟声,到处飘荡着迷人的香气。蔚蓝天上,桃色的云,徐徐伸 着懒腰,似乎春眠未足,还带着惺忪的睡态,流水却瞧不起这小姐腔,他泛着潋滟的霓彩, 唱着响亮的新歌,头也不回地奔赴巨川,奔赴大海。……春是烂漫的,春是永远的向着充实 和完成的路上走的。 春光如海,古人的比喻多妙,多恰当。只有海,才可以形容出春的饱和,春的浩瀚,春 一苏雪林(1897—1999),现代作家、学者,著有小说《棘心》等。本文节选自其《屠龙集》,北京:商务 印书馆 1941 年版。 二曹拉:现译为左拉